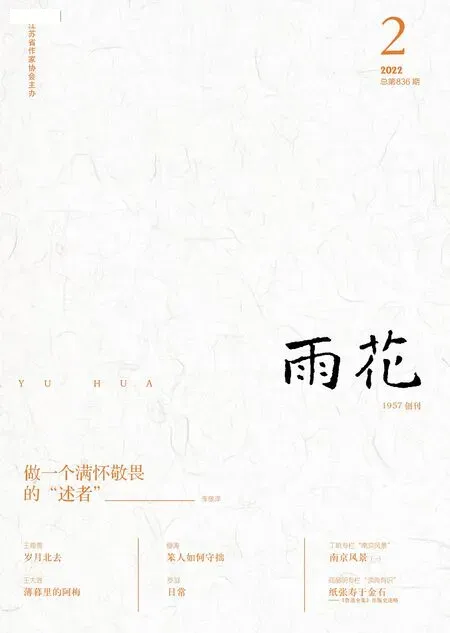做一個滿懷敬畏的“述者”
——在“鳳凰文學之夜”的演講
李敬澤
來到南京,往往觸類而思,因物興感。昨天開會的時候,對面的墻上掛著一幅孫曉云的字,是宋濂的《閱江樓記》,“閱江”是看盡一條大江,“見波濤之浩蕩,風帆之上下”,也是讀一條大江,從六朝風骨讀到今日。這便是金陵氣象,外人來此,往往目眩神搖。
金陵有“慨而慷”、有“今勝昔”,有“虎踞”、有“龍蟠”,還有“鳳凰”。這兩天開“鳳凰作者年會”,天地之大,品類之盛,身處其間,我是誠惶誠恐,越發地不敢伸腿不敢張口。蘇童老師、畢飛宇老師、韓東老師,還有剛才的各位,哪一位都是比我更好的作者,都寫出了比我更好的作品。特別是下午見到了丘成桐先生,我馬上想到:人和人之間的DNA 差別據說只有千分之一,但這千分之一有時就是千里萬里,邱先生在云端上,而我的數學才華只夠在地面上加減乘除。
作為一個作者、一個文學人,登閱江樓,那是我所欲也,我怕的是上“閱書樓”,我很怕去書店,也不愛去圖書館。每次去書店、去圖書館,我都覺得特別受傷。面對那么多書,你真會覺得,天下的真理和道理都被人說完了,天下的好故事都被人講完了,天下的美辭章也被人寫盡了。而且,他們還寫了那么多!這個時候,你就會陷入自我懷疑,回到家,面對電腦,孤燈長夜,搜索枯腸一個字一個字寫下去,這到底有多大的意義?世間是否真的就少你這一本書?這次參加“鳳凰作者年會”,對我來說,就相當于泡了一次書店與圖書館,內力大損。但是,轉念一想,這樣的境遇和這樣的想法,其實不僅我有,我們的老祖宗、我們的孔夫子,他也和我一樣。
孔夫子“述而不作”。他一生不承認自己是一個“作者”,他不打算成為一個作者。這是因為,孔夫子覺得,面對自然大化,面對人間萬象,面對先人的智慧,我們只能謙卑地做一個“述者”,我們無法成為“作者”。
在中國傳統中真正確立起“作者”這個概念,是自司馬遷始。寫一部書,藏之名山,傳諸后世,這部書的后面立一個不朽的作者。然而,在我們整個的古典時代,“述”的精神依然是文學的基本精神,所謂“文以載道”,就是承認在我們的書寫之上和之中,有一個更高更大的“道”,我們的“作”不過是在“述”道。我們的小說,四部古典,都很偉大,但其實,直到現在,它們的作者是誰也不過是姑妄言之姑妄信之。這不僅僅是文化條件所限,那些作者,《三國演義》的作者、《水滸傳》的作者、《西游記》的作者,還有《紅樓夢》的作者,他們也許真的不太在意自己是張三還是李四,是施主還是吳子,他們把自己看作一個述者,故事天下流傳,他們只是再講一遍。人家告訴我們,《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但是,我們讀一讀《紅樓夢》的第一回,雪芹把自己的名字放在那里,但他并沒有承認自己就是作者,他只是說我在悼紅軒里“批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已經有了一個稿子在那里,這個稿子在石頭上,我只是一個“編者”,是個編輯。這是謙虛,也是大驕傲,因為孔子所做的事也不過是披閱增刪,孔子就是一個偉大的編者、述者。
這件事到了現代就不一樣了,我們必須是個作者,否則就什么都不是。“作者”完全是一個現代概念,我們設定,一個“作者”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因為獨一無二的自我必須通過作品實現和展開。這時就沒有什么編和述了,他是在創造。什么叫作“創造”?就是要有光,于是有了光,創造這個詞就是“作”,是孔夫子不敢說的,孔夫子不認為自己在面對自然、面對傳統時可以說:我在“創造”;在西方,古典藝術的根本原則是摹仿,這也是“述”,后來上帝死了,才有了浪漫主義的“創造”。現代性設定和建構了這么一個“創造”的概念,在“創造”的背后,有一個獨一無二的、非常了不起的“自我”。這個自我是一個意義中心,由自我出發,我們去創造,去實現這個自我;所以創造的目的是為了證明:我們確實有一個了不起的、獨一無二的自我。
很好,我沒有意見。自現代以來,所有的作家都是這么想的,我也常常這么想。雖然我也常常覺得,這很像我家的那只貓,它最喜歡的游戲就是循環論證,自己追咬自己的尾巴。
但是,我們現在又進入了一個特別有意思的時代。在過去,成為一個作者、寫一本書,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可慰平生,可告祖先;但是現在,刷一刷微博,看看朋友圈,你就會發現,其實每一個人都成了作者,每個人都覺得:我有一個獨一無二的“自我”,要天天展開,要言說、表達和創造。這當然是好事,天大的好事,但有時我也會想,我們真的有那么多來自自我的東西需要表達嗎?我們真的有那么獨特以至于不說不足以平天下?我們以為自己是作者,是不是此處應該念平聲,我們其實只是“作”者?
互聯網時代是一個盛產自我的時代,你到微博上、到朋友圈里去看看,每日每時我們都在源源不斷地釋放著自我的碎片,天天都有一地的雞毛。當然,這其實也是在給平臺打工,是為互聯網資本日復一日不計報酬地生產勞動,這種勞動,是以不斷地生產“自我”、不斷地輸出無數“獨一無二的自我”為形式的。
趕上了這樣一個時代,或許可以讓我們重新理解,藝術中、文學中的“自我”,到底是什么?這件事如果展開談,今天晚上談到半夜,可能還是沒法說清楚。索性我就跳過論證,直接說出結論—我不認為自己是什么“作者”,或者說,我并不首先要成為一個“作者”;當然,我也不敢說自己是一個創造者,我并不相信,我有一個獨一無二的自我,盡管人和人的差別可以像我和丘成桐先生那么大,但是,我并不想站在這個千分之一的差別點上顧盼自雄,我寧愿向著那千分之九百九十九敞開,向我們的孔夫子學習,努力做一個“述者”。
多少年沒見的老朋友郭平,他寫了一部書,叫作《廣陵散》,他寫的是古琴。我相信自己是一張琴,也許是一張好琴,也許是一張破琴,好琴破琴都是那七根弦,金木水火土文武,這世界的風吹拂著我,人類的手撥動著我,我才發出了聲音。面對著山河大地,面對著人間萬象,面對著我們的傳統、我們的偉大祖國與時代,我想做一個滿懷敬畏、傾盡全力的“述者”。
做一個“述者”也不是容易的事。孔夫子“韋編三絕”,我們也要《每天挖地不止》(林那北小說),還要《嚼鐵屑》(甫躍輝小說)。同時,我也認為,不能僅僅在現代尺度里看待我們的志業,在更長的文明尺度上,在一個科幻式的宇宙視域里,“述者”可能是更重要的,正如孔夫子比我們所有人都重要一樣。所以,只好向孔夫子學習,做一個“述者”,在“述”中去爭取那一點點的“作”、一點點的“創造”。
“鳳凰”是一定要飛的。鳳凰于飛,翙翙其羽,在飛起來的鳳凰身上,羽毛五色斑斕。在座的都是鳳凰頭頂上的毛、翅膀上的毛,而我希望自己能夠聊附鳳尾,做鳳凰尾巴上的、小小的一根羽毛。隨著鳳凰的高飛,也許,我也能夠跟著飛起來,看到波濤浩蕩、風帆上下,同時,在鳳凰的《不老》(葉彌小說)中想象自己的不老。
但不老也是不可能的,我們的身體終究都會老去,我們的那點浮名也會變老,直至煙消云散;只有山河、歲月,這個壯闊的人間,才會真正地、永遠地不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