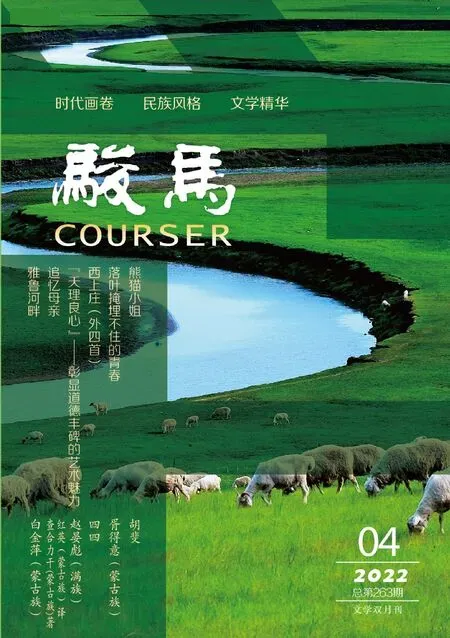庭院美麗
■韓高琦
一
抽枝開花前,紫薇的主干被漠視,
皮膚罩著一層泥色。
枯燥,不加微笑和運動系數,
如堅持著的自我放逐,
如初冬的一次遠足卻從未抵達。
皂花雀偶爾停棲,
爪趾緋紅,細小,分享邊緣生活的支點,
惹人憐愛的構圖。
叫聲依舊,我的布衣口袋依舊。
竹屋一角,立著一個土陶壇子,
裝得下五斤黃酒,
熱血的年齡離開我很久了。
我撿到它時,有一根羽毛
落在里面,空虛顯得很具體。
拿小石子輕叩幾下,
如是我聞:回音雄渾
二
獨門獨院。
法國冬青抬高籬笆墻的倔強頭顱,
二哥說:不修不剪——
隨心所欲的樣子,難得一見,
無為哲學,人身上的隱形翅膀,
忘了飛翔,始于何時?
它們從未歇息,
警覺,如貓鼬直立,
一年四季說著同一種護衛的語言。
我的安心純屬審美疲勞。
西廂的那叢芭蕉,可以聽雨。
虛擬者,切開一個檸檬,
清涼的陰影下,
可以撫琴,可以吟嘯,
可以入夢——
冉冉之姿與午后的怔忡相匹配。
再遠的薄荷知音,也在眼前。
三
大樹有三:一棵沙樸,一棵香樟,
另一棵也是香樟。
我不想細寫:它們太顯眼,
占據東、南、西三面。
東方既白,紫氣籠罩的翠竹,
儼然韓星圓的身姿,
脫俗,愛理不理,閨閣幽閉。
一貫的格調,潔癖和距離,
拔節的清風呵,早晚摩挲,
家族最高的顏值,對著朗月吟哦。
墻角邊散落著數株竹柏,
明顯營養不良,
傘狀的造型始終沒有達標。
沿階的忘憂草卻是不依不饒。
孿生的一對玉蘭樹被分開移栽,
十幾年下來,
變成一大一小的搭檔,
深喉中的怨懟,不被我理睬。
四
當然,石榴的寓意純屬本地特色,
與愛琴海的吟唱無關。
我栽下她的那一刻,
沒有多想——
眼下,燈籠花齊發,
梧桐韓家的虎紋基因被徹夜照亮。
耕讀傳統不變,
從泥土到草根,到蛹,
從胚胎字母到蒲公英的鵝黃發音,
從風鈴到雄黃,到香囊,
陽光芬芳,燕子斜飛,
報春的消息來自出門打拼的后輩們,
年邁的母親眼神清澈,
雙耳拒絕塵世間的噪音,
她坐在竹屋的廊檐下,誦經。
五
屋宇深藏大海的寓意,
正陽門,兩側八字排開,
分別侍立著一棵鐵樹——
哦,兩米高的鎧甲武士,
雌雄一對,威勢旗鼓相當:
全身的劍戟怒張,未曾一刻懈怠。
“請止步,”左邊發話,
“進門前要安檢。”右邊補充。
假想敵又是誰呢?
一個巨嬰時代,怎樣學會自處和拒絕?
獨門獨院。天地留白處,
分明就是陶潛三分地,
父母替我在打理,
那里種植著蔥蒜,星月和五行數學題,
答案留待宮叔回歸的秋季,
留待寂茶室打造完工的那一天。
漫不經心,移步到庭院中央,
我牽手橢圓形的花壇,
沿著順時針方向走一圈,
接著,又逆時針走一圈。
如此反復往還,
一如七星瓢蟲牽手奧特曼,
一如紅花檵木牽手毛葉丁香的執著,
一如鄉愁牽手詩人半生的奔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