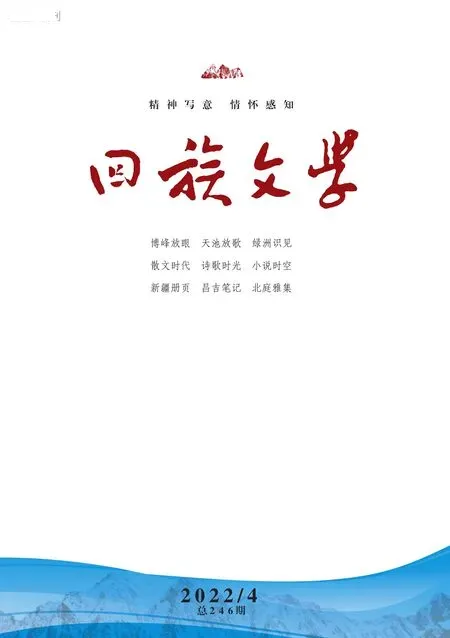小說改良芻議
李銜夏
梁啟超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中認為:“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我以為,詩歌最重語言,散文偏于情感,戲劇依附性強,而小說突出人和事,最能承載思想和生活,貼近大眾,有改造靈魂的能量,因此,談文學改良,當從小說改良開始。就像一百年前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是漫天飛花,其后魯迅《狂人日記》出手,作了一錘定音。白話小說誕生一個世紀后的今天,形成了一些定式和慣性,需要小說家予以警惕,又因面臨電影、電視劇、圖冊、網絡視頻等挑戰,出現滅亡的危機,是時候要作一番反省和重塑了。我姑且拋磚引玉,談八點不成熟的想法,供同人討論。
一、回歸人本
現代小說有一個趨勢,是逐漸消隱作者或者敘事者的聲音,呈現以自然為主、人為輔的狀態,發展到法國新小說時達到了極致,徹底物化、去人化。這顯然是一條嘩眾取寵的歧途,只會把小說更快推向滅亡。文學存在的首要價值是給人閱讀,人永遠是小說的主宰,永遠無法抹去。周作人《人的文學》提出:文學即人學。只有在小說中不斷強化人的地位,探討人性和人的本質,重構人的存在困境,解決人面臨的問題,才能持續獲得傳承發展的力量。西方小說過分追求人性的人的自由,其實是創作上的自我孤立。他者不但是地獄,也是天堂。“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人的本質和意義應該在人與人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世界的關系、人與自己的關系等一切關系中尋找獲得。我主張中國小說要回歸人本,上接兩千年儒家傳統,通過梳理人的關系,捋出人的本質。小說小說,離不開“說”,寫小說就應該不斷強化說的成分,加強敘事者作為人的聲音。
二、改造語言
小說家的悲憫情懷,首先不是鞭撻了多少社會問題,書寫了多少底層人民,而應該是拯救小說本身。在小說中,小說才是第一弱勢群體,因為它正走向小眾、走向滅亡。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拯救小說應該是小說家的第一使命。要拯救小說,就必須找到小說繼續存在的價值憑據。角色、主題、結構、故事、場景等等,都是很容易被電影電視劇挪去的,而且后者會做得更逼真更吸引人。我以為只有語言是別的藝術無法“拿來主義”的。比如魯迅寫過一句話:“在我的后園,可以看見墻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別的藝術無論如何改編都是無法達到這句話在語言層面上的意境的。小說的價值在于語言,而語言的意義在于創造和革新的過程中,改變讀者乃至人類的思考習慣、思維模式,從而改造世界。正如普魯斯特《追憶逝水年華》開創了意識流語言,人們閱讀的習慣也有所改變,于是思考問題的方式隨之改變,越來越能接受一些碎片化、綿密化、雜亂化的信息,世界逐漸進入到新的時代。其他藝術往往受時間限制,比如音樂是細化的節奏時間,電影總體限制了觀影時長,而以語言為其本質的文學則可超越時間。同一本小說,有人看一周,有人看一年,因此,文學是最有能力突破時間的。偉大的小說家一定是文體家,偉大的小說一定是對語言有所創新、有所改造的小說,這對當前小說語言的平淡化、簡約化、輕逸化、通俗化的趨勢提出了更高期許。好的小說語言可以注入詩性和散文化氣息,詩性近神,散文化近真。好的小說,應該是無法被改編成電影的,或者一改編就注定失敗的,這是小說活下去的底氣。
三、融入情感
當下,零度寫作是一種很有影響的小說潮流,簡單來說,就是小說家克制自己的情感,隱藏自己的態度和聲音,使小說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前面我已經談了文學首先是人的文學,這就決定了文學不可能離開情感,一切摒絕情感的創作追求都只是一廂情愿。血液運轉帶給一個人生命的溫度,情感對于小說而言亦然。小說如果不融入作者的情感,它就是沒有溫度、沒有生命體征的死物。當然,石頭也有它的價值,但它至少是沒有靈魂的。作者向小說注入自己的情感,讓情感在字里行間流淌,就是注入了自己的思想、態度和力量。阿來曾說:“小說的深度不是思想的深度,而是情感。”從寫作的角度來看,零度寫作是簡單的,只有準確并恰如其分地融入自己的情感,從而感染讀者,才是真正的向難度挑戰。因此,既要有燙手或凍腳的文字,又要有傳遞溫度引起共鳴的內容。
四、強化意志
很多小說“大師”或者評論家總是故作高深地反對在小說中說教或者所謂的概念先行、主題先行。寫作本質就是表達,既然如此,為什么要表達得扭扭捏捏、畏畏縮縮呢?像魯迅的《狂人日記》《阿Q正傳》,其觀點和態度是那么明確,就是要揭露封建禮教的“吃人”本質以及中國人普遍存在的“精神勝利法”。某種程度上說,這何嘗不是一種說教,至少也是概念先行,但絲毫不影響魯迅小說的偉大,反而更增其啟迪民智的感染力。再比如《水滸傳》,頂在頭上的就是“忠義”二字,而《紅樓夢》通篇都是佛道的“虛空”。小說本就是人的小說,必然繞不開人的意志。值得注意的是,意志并不直接等同于觀點、態度、意念。叔本華、尼采等大哲學家都認為,意志是萬物的本源。那么在小說中摒棄意志,就是自斷祖根。寫小說不應該掩耳盜鈴、自欺欺人,而應該勇于表達自我,宣泄內心最真實的想法,將個人的意志熔鑄成小說強勁的精神力量,震撼讀者,震撼世界。是意志,就會有對錯,小說家要敢于獻丑,也要有超拔于世人的思想力。讀者可以不認同一個小說家的意志,但必然會折服于小說家在捍衛自己哪怕錯誤的意志時所展現出的強大自信。強化小說的個人意志,是接續中國“詩言志”“文以載道”的優秀傳統。
五、務去輕常
今時今日的小說,故事化傾向越來越嚴重,輕盈化、庸常化非常明顯。很多人甚至從卡爾維諾的《未來千年文學備忘錄》中找到了理論的立足點:卡氏放在最前面的兩點,就是輕盈、迅捷。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快餐小說。但很多人忽略了卡氏同時提出的“繁復”。大概因為輕盈和迅捷是比較容易做到的,而繁復則既考驗寫作能力、知識儲備,又考驗小說家的耐性和邏輯吧。我期待像曹雪芹《紅樓夢》、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馬佐夫兄弟》、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普魯斯特《追憶逝水年華》這樣的百科全書式小說的傳統可以得以接續,而雄壯的大手筆本身就標志了一個小說家的大理想、大氣魄、大格局。生活本就是復雜的、厚重的、千頭萬緒的,簡化生活是哲學家的任務,還原生活、重構生活、盡可能全面地表現生活,才是小說家的本職。務去輕常,還可以探索將生活尖銳化、極端化、類型化。志怪傳奇是中國小說非常重要的傳統,它與嚴肅文學是不矛盾的。如果小說過分追求所謂純文學的“純”,到頭來只能淪為一杯索然寡味的純凈水。
六、活用閑筆
為什么看短詩的人比看長詩的人多,看短散文的人比看長散文的人多,但是看短篇小說的人卻比看長篇小說的人少呢?這是一個很奇怪、很悖謬的問題。以“小”字命名的小說,居然是以大和長為美的。在幾千年時間里,中國一直是詩歌大國、散文大國,小說被定義為“道聽途說,街談巷議”的閑文閑書,登不上大雅之堂。小說的崛起是近幾百年的事,但很快后來居上,一躍成為文學之王。某種程度上說,小說的本質就是一個字:閑。之前被人瞧不起是因為閑,后來被大眾追捧也是因為閑,成也是閑,敗也是閑。而小說里面又有一種重要的筆法,叫作“閑筆”。閑筆是小說中最見真功夫的點睛之筆,是最引人入勝的懸崖之花。一個“閑”字大概就解釋了短篇為什么沒有長篇受歡迎了。人們看小說追求的是閑情逸致,是從容不迫,是優哉游哉,短篇往往把作者和讀者逼得太緊迫了,長篇猶如長廊,可以讓人閑庭信步、漫不經心、慢條斯理、漫無邊際。當下太多追求輕盈和純潔的“輕純”派,過于迷信海明威的冰山理論和卡佛的極簡主義,力圖把小說寫成電報。但現實是,電報基本被淘汰了,電話或者視頻電話之所以取代電報,是因為它們可以給人更多的生動、逼真、溫暖。小說何嘗不是這樣,水至清則無魚啊。閑筆其實就是突出小說家或敘事者的聲音,突出其情感和意志,給讀者更多可感可親可觸的形象,給冰冷的閱讀增添一點講述的生氣和興味。偉大的文學應該是什么樣的?我認為,偉大的文學是謠言那樣的,是流言蜚語那樣的。我們知道,傳播信息和消遣是文學的重要基本功能,而流言蜚語則是這兩個方面的佼佼者,而且流言蜚語每經過一個人就會有一次新的添油加醋、藝術加工,越來越精彩、越來越吸引人。因此,我認為流言蜚語是一種活的文學,諸如手抄本、口傳文學等,都是它的一些具象形式。我們從事文學創作,不妨以流言蜚語作為標桿,其實我國燦若星河的話本小說、章回小說,絕大部分都是為了方便說書人、評書人講繹而寫就的,這就能讓占了當時社會大頭的不識字、不讀書的人也欣賞到小說里的人物和故事。流言蜚語之所以如此吸引人,能夠深入人心靈魂,歸根結底是契合了人類的某種愿景、情感或者欲望,從而引起了人們內心的共鳴,甚而點燃了人們參與創作和表達的激情。流言蜚語還有兩種極致的形式:墓志銘和歷史。墓志銘都是寫一個人一生中好的一面,這本身就具有謠言的性質;墓志銘其實是用有限的篇幅,來塑造一個永恒的人。而歷史是謠言的最高形式。歷史一般是統治階級修編的,統治階級為了維護政權的穩定性和持續性,會捏造很多謊言,有些歷史學家甚至認為,在歷史中,假的成分比真的還要多。歷史本身就是一部刻畫人物、塑造人物的小說,它仿佛是一大群人的墓志銘,它的目標同樣是把里面的人送入永恒殿堂。寫小說,不妨以墓志銘和歷史的模式來寫。
七、駕馭假惡
自福樓拜《包法利夫人》以降,似乎作家們都沉迷于通過技術來編造謊言,以讀者讀不出雕琢痕跡為目標。這其實是對小說生命力、讀者接受力的低估,實則是掩耳盜鈴。小說的特點或者魅力所在,恰恰在于虛構。小說家應該敢于承認小說的虛構性,自豪地亮出虛構的名片,充分發揮自由想象力,構建屬于自己的獨特的文學世界。向讀者坦陳謊言,本身就是一種誠實。小說跟魔術是非常相像的,兩者都是以假亂真。如果一個小說家可以明明白白地告訴讀者,自己所寫的內容是虛假的,但又讓讀者為之著迷、動容,則可以充分體現出作者高強的寫作能力。韓東曾有一個觀點,叫作“把真的寫假”。亮出故事層面的“假”,是為了直達精神層面的“真”。小說不能偏居于真善美,還要能夠駕馭假惡丑。作為人的小說,要體現出人性兼具的神性和魔性,缺失了魔性,人就不可能真正建立起對神性的敬畏。
八、揮灑浪漫
國內曾經興起關于現代和現實兩大主義的大爭論,這其實是一個偽命題。現代主義強調的是前衛性和永恒性,但這個提法卻是鼠目寸光的表現。文學藝術創作的兩大主流應該是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所謂的現代主義,不過是浪漫主義的一種現代性表述。我們看到的所有先鋒探索與創新,比如表現主義、后現代主義、魔幻現實主義、結構主義等等,本質上都只是浪漫主義的某些支流,有個別最終流成了未來的主脈,但依然是在浪漫主義的范疇內。浪漫主義跟現實主義一樣古遠,也將一樣永恒不滅。它既古老又現代,既精英又大眾。小說家要有浪漫主義情懷,浪漫主義情懷就是理想主義品格。中國的屈原、李白、吳承恩代表的浪漫主義一脈,是那么孤獨又那么閃亮。浪漫主義并不是狹隘的夸張、變形,更高的追求應該是文無定法,是孔子所說的“從心所欲而不逾矩”。
結 論
上述八點,一言以蔽之,無非是:小說是人的小說。只有像創造人一樣寫作小說,才能賦予小說以人一般的生命。以人來談小說,并不是什么新鮮論調。談一件事物的本質,是不存在出新問題的,因為本質早已存在,只是各人看法不一罷了。胡適《文學改良芻議》也概莫能外。本文承認是老調重彈,正如小說應該承認自己的虛構身份。真理是不可以創造的,它只能被發現或者被重申。本文正是致力于給自以為的“真理”擦塵去垢,供志同道合的仁兄們觀之樂之。小說尚且強調人,本文自不會幼稚地要求所有人都趨同于所談的八點,人各有異嘛。本文最大的快樂,在于作為人的發聲過程,唯愿有幸引得更多人發聲。我不知道21世紀是不是亞洲文學的世紀,但我期待一種亞洲小說的復興。在此謹以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一句收尾:“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