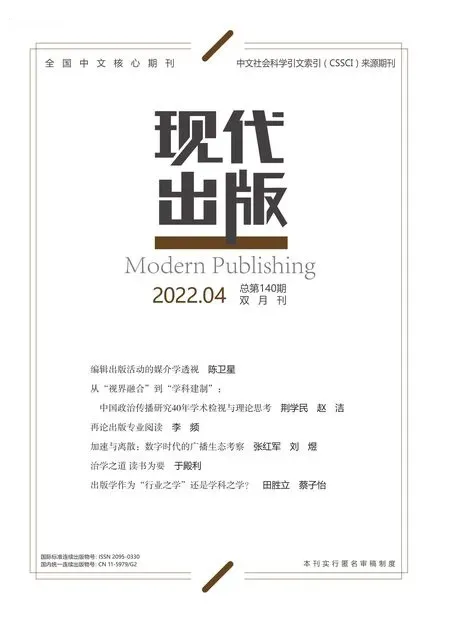編輯出版活動的媒介學透視
陳衛星
從專業定義出發,編輯是“對資料和已有的作品進行選擇、整理和加工的社會文化活動”,出版是“對作品進行選擇、編輯、復制,向公眾傳播的專業活動”。綜合起來說,編輯出版是基于特定的信息介質或信息載體,對以文字和符號為基礎的相關信息進行公開化編輯,予以出版,組織發行和促進推廣,由此形成不斷延伸的信息平臺和產業領域,也培育一個不斷探討信息的內容制作和載體形式的發展演變的學科。今天面對電子文明的數字時代,傳統意義上的學科命題和專業視域正在發生變化,不僅涉及信息生態的變化,也折射出傳播情境的變遷,這促使我們借助媒介學提供的后視鏡式的回溯來重新審視這一變化。
本文試圖從符號學、傳播學、歷史學和人類學的交叉視角出發,為媒介化的信息生成方式及其傳播機制提供一種媒介學的闡釋。在文字信息的編輯活動中,視覺與文本之間的關系形成思維經驗的線性模式。如果說經驗是意識的媒介,當“現在”的意識重新賦予“過去”的意義時,不僅讓人們更易于認知歷史經驗如何鑄就當時的期望,同時,也有助于我們透視過去和未來之間存有一種共生的關聯,從而形成一個動態的、創造性的認識論跳板,幫助我們在信息流變的當今語境下更深入地認知和評析以編輯出版活動為中介的信息傳播正在經歷的轉型和挑戰。從我們的分析視角出發,本文所探討的問題出發點是:首先,著眼于從媒介學原理透視信息傳播活動的意義邏輯,探討作為編輯出版活動基礎的文字符號能夠建構什么樣的社會關系。其次,分析編輯出版的行為主體和行業資源的關系結構,從媒介形式、技術環境和社會結構的媒介學圖式中,理解媒介學的創新價值是形成聚合技術平臺和社會配置的二元結構。再次,剖析媒介作為一種社會性的文化擴散和文化傳遞的實體結構,在強化知識的標準化的同時,伴隨著豐富信息的人格化樣式,而編輯出版活動的專業化活力在于開辟社會化的潛力和空間。
一、符號傳播的媒介學定位
在人類文明史上,用視覺符號表現口頭表達的聲音和概念是文字產生的來源,“全部人類經驗無一例外地都是一種以符號為媒介和支撐的詮釋性結構”。作為一種文明史的實物性載體,符號經歷了從自然挪用到人工制作的演變過程。
人類最初的文化活動借助于自然環境本身的符號載體功能。2017年,考古學家在印度尼西亞發現刻有蘇拉威西疣豬(Sulawesi warty pig)的壁畫,距今約45 000年,它被認為是史前人類留下的最早的文化符號。早在6 000多年前甚至更早的歷史時期,人類在西亞兩河流域的蘇美爾地區,用黏土燒制刻有各種象形符號的楔形字板,這幾乎就是文明史上最早的信息文檔。意大利旅行家在1657年最早發現楔形文字。到2012年,考古學界在土耳其挖掘到24 000份楔形字板,它們近乎雕塑品,卻是人類社會最早的賬單、稅單和發票,等同于經濟活動的票據的憑證。從一開始,產生符號功能的信息媒介就是從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出發來建構實踐關系的。
用文字符號來把握世界,是推動人們以文字符號來記錄并保存社會運行的信息軌跡。一方面,通過文字對事物的陳述,呈現事實或描述現實;另一方面,又通過語言文字的指向性,對社會行為產生歸納和指引的作用,打造人類社會主觀能動的操作平臺。一旦文字通過印刷形成社會的主要傳播媒介,“通過文字創造出想象的現實,就能讓大批互不相識的人有效合作”。從閱讀開始形成的受眾圈,可以把趣味性的文學主題拓展到社會乃至更大的范圍,衍生出各式各樣的手稿、印刷品、書籍、報紙、期刊以及不定期出版物、非正式出版物等等。借助不同的物質載體、編碼方式及流通模式,傳播效應往往是從社會組合的同心圓結構開始,發酵社會的輿論心態,標點社會的心理指標。
媒介在記述事件的同時,也是在參與創造事件。從17世紀開始,在西歐出現以文學作者圈及其最核心的社會關系網構成的“文人共和國”,隨后擴散為以文學沙龍和咖啡館為起點的“公共領域”,是信息符號的增長和擴散在構造社會想象的彌散空間,一種物質性文本的增長催化了非物質性的想象,在被俘獲的空間中生產標志社會心理層次的欲望、身份和價值觀。“實際上,那時候的社會似乎根本沒有那種在自由而平等的參與者之間進行的坦誠而公開的討論,即尤爾根·哈貝馬斯所謂的公共輿論。如果我們去研究語境或背景因素,比如新興出版業的指數級增長、閱讀活動和印刷文本傳播帶來的影響,那么理解公共領域的興起就會變得更容易。”事實上,是在印刷文本的流量被擴大的背景框架中,新的語言、話題、隱喻和想法的循環推進,逐漸導致話語的裂變和意識的創新,通過紙質媒體的信息周轉創造新的社會關系,改變權力的運行方式或增加權力的支配模式。
自15世紀以來,以出版業為核心的編輯出版活動使得閱讀的可能性和閱讀的實踐成為社會發展的重要變量。在20世紀中期,蜚聲世界人文學界的法國年鑒學派第一代大師呂西安·費夫賀就聚焦于印刷書,在《印刷書的誕生》一書中很關切地提出書籍的問世和發展所蘊含的歷史使命問題:“究竟它滿足了哪些需求?承擔了怎樣的角色?實現了或未能實現的目標有哪些?”史學大師之所以要提出這樣的問題,顯然不只是著眼于編輯出版的技術發明,更好奇編輯出版活動的產業運作所牽引的意識流動,與此相應的觀念演變又產生出什么樣的傳播效率,標志新的歷史路標。從生產力革命啟發生產關系革命的歷史唯物主義視角而言,機械印刷在中世紀末期的文藝復興初期獲得發展機遇,結果是印刷文明所產生的權力分化效應,不僅把上帝和自然予以分離,同時也在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進行信息剝離。隨著公共機構和宗教傳統的分離以及個體自由的社會化,逐漸孕育社會意識的轉折和革命,培育新的社會階層,呼喚新的社會關系,從部落-集群走向民族-國家,正如傳播學多倫多學派的麥克盧漢所說:“部落這一血親家族形式由于印刷術的出現而爆裂,取而代之的是經過相似訓練的個體組合而成的群體。民族主義到來時展示出群體命運和地位的一種強烈而新鮮的形象;民族主義的到來有賴于印刷術問世之前未曾有過的信息運動速度。”換言之,文明變遷或社會演變的可能性離不開新媒介的介質的功能轉換和效率提升,如接觸性、移動性和可塑性等等。
物質流動的社會史和信息流動的文明史的合流,才是文化史學者眼中的文化秩序的源頭:“話語之秩序不可能脫離其時代的書籍形式。”社會創新的時代議題始終離不開媒介的暗示或引導,當創新的互鑒意味著文化市場的邊緣存在多樣性的時候,文化市場的中心是最小公分母的同質文化,好比當下微信圈的互相模仿或信息繭房的層級效應。今天基于手機屏幕的碎片化閱讀往往被質疑,因為不利于開放性的知識增長。從本身攜帶傳播意圖的既定立場、觀察條件乃至趣味取向出發,被推送的各種信息幾乎都會有一套模式化或個性化的分析邏輯和評判方式,甚至還有語調的出其不意和信息驚悚度的創意,從而達到收獲流量的傳播效果。
媒介學家總是把物質化形式的可能性作為問題的出發點:“思想只有通過物質化才能存在,只有通過流露才能持久。”從6 000年前的楔形字板到2 000年前的竹簡,從15世紀的印刷術到20世紀的互聯網,從20世紀末的搜索引擎到今天日新月異的算法序列,文明史的演化趨勢不僅是信息媒介的物質性平臺的功能轉換,也從信息的物質性呈現走向信息的虛擬性展演。媒介史的這種演化指向媒介學的邏輯重心,即信息的內容品質越來越倚重于信息的形式結構,如果用德布雷的話來說,“就是讓符號向痕跡靠攏,話語向過程靠攏,闡釋向儀器靠攏,文本向資料靠攏,文字向書寫靠攏,傳播本身向傳播途徑(道路、運河、鐵路)靠攏,口語向發聲器官靠攏,記憶向存儲器靠攏”。簡而言之,媒介的競爭效率與媒介所培育的感覺能力和知性能力有關,這就把媒介競爭引向媒介平臺的功能和性能的競爭。
每一種新媒介的文化環境同時形成舊媒介的短路狀態,新舊媒介的并列或重疊總會導致新一輪的不對稱競爭。從表面上看,任何一個信息文本的文案處理過程,都可以被納入媒介感知和媒介操作的實務;但實際上,不同時代、時期或歷史節點的媒介工作者,需要從不同的經驗流程和技術規范出發來進行信息媒介化的具體操作。從媒介關系出發,媒介學指明一種主觀的視角是如何基于一種客觀化的界面,客體的再現功能規定主觀性的意義范圍。根據這一原理,我們可以理解印刷出版業當中書籍制作的不拘一格,不僅僅是依據功能指向、信息類型或讀者類別,同時也可能在題材和風格上不斷創新,讓文本類型更具有多功能開發價值,讓代碼的符號性本身更具有接近性,比如說通過記錄聲音而形成的紙質書或直接還原客觀世界視聽信息的電子書,以及開本、紙型的差異或電子閱讀器和電子墨水屏的性能,等等。借助媒體的傳播活動,多少會存留人際傳播的習性。譬如,早在印刷文化剛剛問世的中世紀末期,機械性質的排版印刷就在改變口述文化的同時,又對其進行了記載和保留。今天全天候擴散的短視頻和手機世界的數據庫風靡一時不僅僅是對人際傳播的還原,同時也是信息技術創新的附加值組合,英國學者約翰·湯普森就將其特點歸納為輕松訪問的可接近性、更新能力的低成本、信息合成的規模效應、關鍵詞的檢索機制、可攜帶性的方便、可選擇性的靈活、超鏈接的互文性景觀和多媒體的相互穿插。
如果說,所有的文化現象可以被理解為一個不斷循環和更新的媒介系統、一種對客觀世界的積累性或重復性的態度反應、一種心照不宣的默契再疊加一個價值評判的刻度,那么,我們對世界的感知和認識,事實上是通過媒介系統的信息代碼的再現功能來完成的。在20世紀中期,信息論的問世逐步推演出媒介發展的另一條路徑:“用香農-韋弗的術語來說,媒介的人性化趨勢進化可以被描述為一場媒介從最小化的編碼和最大化的解碼向最大化的編碼和最小化的解碼靠近的運動。”這就意味著,媒介的進化趨勢是傳播者編碼的技術程序越來越復雜,而受眾解碼的接受步驟則越來越簡便,看來“媒體的競爭是基于接受性能和成本的競爭”。僅僅就性能而言,在時空界面上越來越方便接近的視聽傳播與文字傳播相比有天然的競爭優勢,視覺關系的接近性甚至可以簡化信息組織的操作。但是,信息價值的社會等級還是通過社會關系的序列來確認的,好比最重要的事件認證是通過權威機構的正式文件的公開信息來確定的。特定歷史時期/時刻的信息制度,規定信息生產和知識傳播的性質,這包括信息編碼、傳播流程、接受方式和闡釋文本的技術格式和組織過程的縱向結構。
媒介形態的發展演變,往往牽動著社會結構形式、經濟增長比例和文化演變方式中的功能轉換。而媒介學的視角是通過形而下的揭示和闡釋來達到去觀念化、去神圣化的效果,同時也試圖為新的媒介載體的可持續性推廣提煉一種抽象品質并歸納其心理動機,特別強調在信息傳播過程中,要注意辨析其中的技術系統和意義結構的耦合機制:“印刷、視聽、計算機文字,這些傳遞系統中的任何一個都被其使用者根據他們的價值和利益予以過濾、修補、改變。這是無可爭議的。”按照媒介學對中世紀末以來媒介發展線索的歷史階段的分期,可以把這里列出的印刷、視聽和計算機文字視為三種不同的代表性媒介,每一次的技術創新不僅是制造歷史事件,醞釀社會氛圍,同時是一個社會心理的重要轉折,在開辟新的愿景的同時,不斷推進并豐富個體讀者、受眾、網民連接外部世界的一元關系(metaconnection),不斷修改社會關系的生產邏輯和組織邏輯,從而讓未來世界的投射幻化為一個充滿各種不同預測景觀的萬花筒。
二、信息循環的媒介學路徑
在20世紀80年代,法國著名學者貝爾納·米涅及其學術團隊就在傳播政治學研究上取得重要突破,尤其是聚焦于信息和文化的工業化,著力分析出文化傳播行業的產業經濟學特征。到2000年,他把文化傳播產業的運作模式分為五類:編輯模式,即基于市場預測的文化產品概念的創意設計;流模式,即以視聽方式出現的連續播出所生產的娛樂和文化;寫作模式,即自由撰稿人(可以類比今天的自媒體經營者)模式;程序化產品模式,包括各種軟件包、家用軟件和公共場所的傳播技術設備及耗材;現場直播模式,各種表演、儀式和事件現場的直播和轉播。通過歷史性的觀察和實證性的研究,這里的歸納勾勒出后工業化時代的經濟活動的消費轉向,為多元化形態的文化產業的合法化提供學術分析的基礎架構。
編輯出版活動對應著出版業的市場形態,自然延伸出經濟社會學的扇面結構。其中包含不同的行為主體和組織機構、類型和數量各不相同的力量和資源,以及運作過程中的各種競爭合作和回報,等等。英國學者邁克爾·巴斯卡爾認為,編輯出版在今后如何發展的學術研究可能有六大指向:“出版的公開性和體制性,進而解釋是什么使得某件事被公之于眾;作為一種媒介,出版所扮演的角色;各式各樣的前人對出版的理解;各式各樣的出版媒介形式;有關出版的各方面,如(金融)風險、出版內容和市場構成之間的關系;出版的歷史以及當前它與數字媒體是如何共處的。”這涉及出版業的市場環境的若干要素,比如說市場準入的制度設計、文化趣味的話語導向和知識框架的類型學、商業性和文化性的差異性評估、出版產業與宏觀經濟的關系結構、內容供給與市場周期的時差節奏、創作人力資源的組織和整合,以及編輯出版作為文化能動者的角色扮演,等等。
當代的編輯出版活動,正在經歷兩種博弈:一是要面對文本形式的變化。書籍形式和閱讀實踐會因為技術主導的體驗差異而發生變化,甚至形成代際差異。在以往的閱讀史經驗中,就先后有過從卷軸到翻頁、從紙版到電子、從無聲到有聲的變化。二是受眾身份的變化,信息時代本身使得書籍信息所提供的機會成本價值相對被稀釋。在信息只是量變因素的時代,書籍的內容因為持續時間長而顯得經典,每每有人回顧漫長一生當中與一本書或幾本書的幸會所留下的終身受益的佳話。而在信息成為社會生產力要素的產業化時代,信息的供需結構日新月異且常態化。因此,如何選擇書籍,或者說如何進行閱讀,就成為一種生活趣味的直白、一種思想觀念的泄露、一種批判視野的獲得,或者抵御異化和消費主義的文化盾牌。當讀者的社會實踐活動在不時穿越社會心理學意義上的前臺和后臺時,其心理需求和身份認同是一個活動指標,由此激發書籍信息在儲存、檢索和傳播方面的競爭效率,連接相互交叉的話題時尚和社區人群。
今天的出版業所追求的信息供給,無論是在產品種類還是印刷數量上,會有一種意味復雜的此起彼伏的增長態勢,“一方面是‘可讀空間’,即文本的物質和話語形式;另一方面是控制其‘現實化’之具體環境的空間,即各種閱讀:閱讀被理解為一系列具體實踐和一系列詮釋步驟”。就前者而言,書籍的物質形式產生閱讀信息界面的可接觸性和可選擇性;就后者來說,書籍的傳播過程則提示閱讀信息空間可以根據信息對象的定位產生組合變換,再現一種新的社會主體的身份認同。“一個文本通過印刷品而傳播,并非一個中性的現象,而是造成一些讀者共同體的形成。”如果說16世紀的非拉丁文版《圣經》曾經在發生宗教分裂的歐美培育了新教徒,那么今天的閱讀指南本身可能圍繞著各種活動、工程和項目的光環或是以亞文化面目出現的消費熱潮或心理痛點。
有史以來的信息環境不是一種單純的物理空間,而是確定意義范圍的一種社會生態。譬如,今天能見度較高的一個名詞“社會面”即說明信息循環的意義就在于它本身所體現的社會編程:“歷史上某一傳播環境的具體成形是依托某些社會傳播裝置,在該裝置內部完成的。這種空間的建設依靠的是由占有者、擔保者、推薦者、聯系人等各類人群組成的網絡,并以該網絡為基礎。”這差不多就是說,在信息產業中,內容制作的前提——觀念的形成、意義的分類和組織的建構幾乎是同步的,站位策略決定闡釋結構,由此啟動權力機制和管理程序。從行政規制出發的信息市場管理,手段和方式是一個表象,重點在于管理目的驅動的概念轉移,產生一種對受眾對象的意識的剝削,即基于信息表象的“非物質開發”(immaterial exploitation),培育新的信息市場和輿論市場。隨著物質性社會福利的普遍提升,非物質貧困化(immaterial pauperization)逐漸成為傳播議題相互競爭的動機,激發信息傳播和編輯出版的活動熱度。這樣一來,通過信息生產的調適技巧和分配機制,把信息循環自覺納入社會管理的媒介學環路。
信息循環可以被視為媒介現象的晶體化過程,這包括傳播者的身份演繹、文本符號的象征權力、傳播渠道的技術配置和話語實踐的社會功能,恰恰是媒介技術的演變使得媒介學成為其來有自的命題,即針對以媒介為中心的物質對象的生成、生產和接受的過程進行分析。這一方面是符號形式和信息技術的流變,另一方面也是文化建構和知識擴散的版圖。在社會實踐的平臺化邏輯中,這包括新受眾的發現和培育、新媒介的載體和類型,以及新媒介鏈接的新界面。總之,是技術和文化的互動塑造社會意識導向和心理趨向,從而見證媒介的秩序如何校正或調適社會的秩序,重新建立媒介形式、技術環境和社會結構之間的媒介學圖式。
媒介的技術創新意味著對既定權力結構的分化,因此具有創新性的工具發明能否得以推廣,和特定歷史時期的管理機制有關。從15世紀開始,在當時的歐洲南部和中部,開始迅速采用源于中國的印刷術,約翰·谷騰堡能夠把印刷作坊從美因茨搬到斯特拉斯堡,馬丁·路德以印刷企業家的身份推廣新教觀念,威廉·廷代爾躲在荷蘭出版在顛覆性中充滿美感的《圣經》英譯本:這些傳播現象之所以能夠成為現實,是因為當時權力分散的行政管理對創新的態度更為友好。與此形成對比的是,西亞的奧斯曼帝國和南亞的莫臥兒王朝對印刷術的禁止長達三個世紀。直到20世紀早期的工業化時代,開始逐漸涌現大眾傳播的組織模型和優化方式,各類信息的編輯出版成為一種管理需求和產業選項。從媒介學的物質性原理來說,“同一個文本,只要呈現形式大異其趣,就不再是‘同一個’文本了。每種形式都有一套特定規范,每套規范都會根據自己的法則來區分作品并用不同方式將其與別的文本、體裁和藝術聯系起來”。從更早時期至20世紀的線裝本到21世紀的電子書,如果我們回顧一下閱讀載體的形式演變的歷史進程,不難看出,信息傳播的對象化是通過對主體性需求的定位和開發來推進知識增長和意識變化的,新的媒介形式總是指向新的社會人群,直到形成總體上是借助于書籍提供的知識信息所打造的具有新社會階層意識的“知識共同體”。
在20世紀中期,歸納過傳播學的功能指標的拉斯韋爾提出了五個W,為什么要把傳播者放在第一位?因為人類文明的發展動力就內含知識的民主化,即傳播者容量的歷時性擴大,這如同著名文化史學家羅伯特·達恩頓在21世紀早期所歸納的那樣:“18世紀的文人共和國已轉變為專業化的知識共和國,現在已經向業余愛好者開放——就‘業余愛好者’這個詞的最積極意義來說,它指的是普羅大眾中的知識愛好者。”從手抄本到印本書,從機械印刷到電子自媒體,有關書籍的媒介發生學的生成軌跡始終伴隨著知識權力的建構和解構,即從具有壟斷性質的管理模式逐漸過渡到自由流動的開放市場,進而言之,是通過對信息不對稱的稀釋來緩解權力不對稱的張力,激發信息市場的活力是現象,擴大社會空間的容量是結果。
在21世紀的今天,基于互聯網的數據庫的繁衍和超文本鏈接的延伸,信息傳播模式幾乎可以以實時的方式同時在時空兩個維度展開,受眾或網民在接收傳播者的信息和評論者的意見的同時,又在對觀點的構想和理解的尺度主動或被動地進行差異化的處理。當我們身處互聯網時代,尤其是當下的流媒體季節,更多同時是網民的讀者在傳播實踐中的行為選擇本身決定著信息(包括書籍)的傳播效力,信息的短平快成為一種競爭指標。比如說,今天的讀者究竟是更加習慣于咨詢紙版的《辭源》《辭海》類的工具書還是“百度”在線編輯的各類數字百科全書,這就不僅僅是一個信息供給的權威性問題,而同時涉及信息的可接近性、信息的辨識度以及信息評估的豐富性和多元性等維度,并挑戰意愿和知識之間的界限。與此同時,古典人文知識的價值評判成為話題,傳統人文知識的信息擴散開始遭遇審視態度,以確定不同的心理距離和時間效率的結算等,信息的擴散自然會伴隨著信息的阻擊。
“一部書、一部手稿及一部印本的誕生,象征著知識從作者個人擁有的狀態中脫離出來,最終進入讀者手中。”被編輯出版的印刷品實際上是穿越社會上不同知識和行動領域的媒介,既有符號屬性,體現著一種標準化的認知方式,又具有技術屬性,其本身的技術格式體現著一種特定的工藝水平:“正如內容往往都會擁有框架一樣,一種內容也總是會伴隨著某種模式。”作為一種信息生產的模式,出版物的市場反應及其價值趨勢自然被納入投入-產出的產業經濟學評估系統。當然,編輯出版活動與社會的互動總是凸顯媒介社會化的新指向,引導受眾的意識建構和身份變遷,尤其是龐大的教育系統的功能性需求,并通過出版物本身的印刷量、印制成本、庫存管理、流通周期和市場可接近性折射出來。
就組織推進信息傳播活動而言,媒介學的創新價值提出了一個辯證法模型,即媒介本身是一個二元結構。一個是技術性手段的配置,即機體化的物質(matière organisée)。要記錄符號的表面,從物質操作的角度說,這包括書籍的呈現方式從最早的竹簡、羊皮書到后來的布面燙金版、硬殼精裝版、輕型口袋書,再演變為今天的電子書的各種版式,概括地說是基于平面印刷、載波信號或虛擬世界的解碼程序所引導的各種信息被接受的方式,還包括信息內容的存量與增量的組合比例所暗示的市場半徑,以及擴散手段的基礎設施的管理和運營,譬如發行渠道和發行網絡的層級性和流動性。這往往是通過技術主義的指標來體現樂觀主義的愿望。另一個是組織性觀念的配置,即有形化的組織(organisation matérialisée)所形成的社會裝置,如知識觀念體系、編輯出版制度、語言文體范式、信息推廣儀式的創建和普及,而這些運作方式往往都與情境相適應,融入社會主體實踐活動的組織性架構,體現文化主義的延續或歷史主義的再現,即內容傳播的模式和信息內容的框架不可分離。
三、文本形式的文化人類學
從大眾傳播活動的近代史來看,信息的編輯出版不是一個簡單的市場化程序,也會借助于人際傳播的社會效應來形成一種信任委托機制,即最終以人際傳播的可靠性作為傳播心理的支撐物。如果說最有效的激情源自信仰的誘惑,那么情緒支撐的信任或熱情驅動的皈依,總是會更有效地加速贊同的擴散。這就是為什么一直到15世紀,在繁華的意大利威尼斯街頭,人工抄寫的“手抄報”仍然比印刷的“報紙”具有更大的傳播優勢。當時人們認為印刷工坊出品的讀物需要經受檢查而滯后或變形,如果在信息事件現場采訪當事人,通過現場筆錄而獲取的信息則是不脛而走的。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段中,人們對人工信息的信任度高于機械方式生產的信息,尤其是在一個信息本身具有不定性或信息供給不具有飽和性的傳播環境中,甚至至今還為可能擴散的謠言和流言預留一個非規則的傳播空間。
人類發明的信息工具也可能是文化人類學的展臺,以此為媒介來溝通人類社會和外部環境,為觀念意識的發育開辟技術資源。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扮演著文明使者的角色:“印本書,一個基于中國紙和印刷術發明的非凡產物,擴展了文字著作的受眾和內容,使它們更易于遷移和傳遞,對受過教育的精英和社會大眾更有用。”根據20世紀的法國著名古人類學家和考古學家勒魯瓦-古蘭的分析,就人性的演變發展而言,人類制造工具和工具影響人類是一個問題的兩個面向,即“一個發自內在環境的、逐漸攫取外在環境的運動”。而在21世紀初期,西方學者在總結多倫多學派創始人哈羅德·英尼斯的傳播思想時,就強調他從世俗社會的角度思考媒介提供的話語空間與社會管控的權力機制的重合:“隨著壟斷的發生,某種特定的媒介或許成為社會傳播的唯一實在機構,從而也就完全控制了知識的特性與擴散。這種關乎人類心智的壟斷機制不但能夠不斷加固自身的地位,更可從根本上左右社會關注,為世界賦予某些對自己有利的圖景并維護社會權力結構的現狀。”簡言之,媒介是一種社會表象結構的外觀方式和維護手段。
如果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來說,人工書寫符號的出現為人類社會的主體性成長提供了一個操作平臺。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在20世紀前期在巴西亞馬孫河流域進行田野考察,在其中一個只有渾濁而低沉的表音語言的印第安人部落南比夸那(Nambikwara),他在給當地人頒發紙張和鉛筆后,發現當地的酋長特別善于領會其符號性用途,用隨機涂抹的波浪形線紋來和他進行似乎是心領神會的交流,或者是把被提問的問題的答案畫在紙上,或者是用筆標示相互交換的物品并大聲“念”出來。“列維-斯特勞斯意識到,那頭目寫下的涂鴉其實是有意義的,哪怕不是字面的意義。憑著直覺,這個頭目了解到紙張、筆記本、筆和記號是包含力量的,而民族學的問答則猶如一種神秘的儀式。”在這里,對文字符號的模仿性書寫,是連接外部世界乃至控制與外部世界接觸的方式。列維-斯特勞斯站在現代文明的角度,當然意識到文字書寫所表達的信息權力的社會軌跡:“書寫文字可以說是一種人工記憶。書寫文字的發展應該是使人類對自己的過去有更清楚的認識,因此而大大增加人類組織安排目前與未來的能力。”這里的田野實踐,無疑是一種象征權力的模擬性平移。所以,這里的酋長借用裝模作樣的書寫來表現自身的智識能力,和從自然環境中采集的裝飾物的符號功能相比,抽象性質的線條符號似乎意味著更大的神秘和魅力,至少可以為酋長自身的象征權力增加新的砝碼。
毫無疑問,每一種新媒介都在對人類的記憶建構和信息類別提供新的選項和合成方式,但任何一種新媒介本身都只不過是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的一個階段性選項。今天的人們很難想象,早在半個世紀前的1972年,麥克盧漢就基于媒介與環境的互動結構,提出了一種在書籍之外的信息編碼的問題,認為這有可能成為未來社會傳媒化的規定動作:“書籍的未來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人是否能夠根據印刷書籍以外的其他文明模式來給自己的社會生活編程。毫無疑問,不借助書籍,沒有文字素養的訓練,人們也能夠結成大規模的社群。”當時沒有互聯網,麥克盧漢只是基于媒介的演化機制提出大膽的推測,這涉及內容載體的文本形式是可以變化的,從而使得文本變體和文本實現(即文本最后的形式)被納入一個演化過程。半個世紀后,至少從人口學意義上的“90后”或“00后”這一社會群體開始,他們開始習慣于二次元世界(今天改稱元宇宙)并與之相互依存,成為新時代受眾的媒介化行為的社會性標志的起點,從亞文化領域開始裂變出新的受眾指稱,如鍵盤俠、彈幕族等等。從中世紀的手抄本到后現代的觸摸屏,媒介技術的線性發展似乎永遠上演著知識的標準化和信息的人格化相互博弈的腳本。
的確,今天在分析一種社會性的文化建構的演變趨勢時,不能夠省略一種媒介考古學式的問題性和正當性。從幾萬年前的巖洞壁畫到今天的虛擬世界,從歷史學意義上的檔案咨詢出發,媒介學的懸疑始終針對文化擴散或文化傳遞的關系結構,包括如何看待人機關系的分離和連接,如何評估技術對象的可能性和豐富性。如果說傳播學是通過內容組合有效地生產受眾,那么媒介學就會進一步分析受眾變遷的物質誘因和環境參數,即“象征有效性的路徑和手段”。換言之,一個信息的真確性不再取決于對其內容的研究,而是要正視其行動手段、表象系統和擴散方式。譬如今天的數字出版模式所營造的營銷網絡,這是一個基于連接、數據傳輸、鏈接方式的聯系網,可以使得一本電子出版物在虛擬世界的超時空范圍中瞬間被無限復制和分享。這至少產生三種后果,即降低信息生產的技術門檻,縮短信息競爭的市場周期,顛覆信息構成的形式規則,這就對信息文本的價值評判提出了一個嚴峻的挑戰。只有那些同時具有探索性和包容性的文本,才有可能蘊含潛在的自我更新能力,從而成為能夠經受時間挑戰的經典文本,或者是提示不同時間性(temporalities)相互交叉的文本標簽。
經典文本從何而來?根據文化史學者的歷史總結,它包括文本循環五大環節:出版、制作、發行、接受和流傳,同時受到四個“領域”的影響:思想影響,政治、法律和宗教影響,商業上的壓力,社會行為和趣味。編輯出版的產業鏈結構之所以能夠循環,不僅是作者、出版社、印刷廠、發行網、讀者之間形成一種表面上的閉環結構,同時基于讀者群體的市場反應使得有影響力和生命力的創意繼續擴展,轉換為新的信息,從而擴大信息生產的共時性和流動性,把觀念體系的貫穿效應轉化為多元信息的動態競爭。這意味著文化產品的同質化與異質化不是一種零和博弈的關系,而是有主流和適位(niche)的同時并存。這種產業結構在當下面臨的挑戰和應對,印證著文化產品的包容性,因為“媒介學的方法或氣質在于指出知識生活、物質生活與社會生活之間的交叉”,正是這種交叉的相互競爭,使得編輯出版作為當代社會實踐、經濟生產和文化交流當中的必要構成,繼續提升知識增長、產業轉型和文化媒介化的復合指數的豐度和厚度。商品化模式的主題營銷總是在制造對個體和群體的閱讀需求的導向和路標,這其實也是一種市場波動的透視,由此反射表明專業化的編輯能力和社會化的閱讀潛力的相互競爭。
從市場反應的速度效應來說,爆款產品之所以成為爆款是因為它能夠滿足瞬間的情感消費或情緒消費。而經典文本的傳播效力源于其文本本身啟動循環的能力,這種循環更多源自能夠跨越時空的信息,也是判定一個社會群體的文化坐標的潛力和能力的參照系。“‘文化’這一術語的使用很關鍵:它所關注的并非百科全書、菜譜、實用指南,或那些只具有純粹信息價值的東西;它來自一種給予文學、傳記、學問——尤其是人文學科,以及任何具有潛在文化價值的東西的特權地位。”價值的持久性和心理的懷舊感成為文本性信息的客觀支持和主觀寄托,并就此開發感知字典,擴充價值庫存,支撐與未來進行對話的話語平臺。編輯出版業的未來,必然是在技術革命的成本競爭、商業模式的市場激勵和人文情懷的主體價值的相互競爭中尋求主動,至少求取平衡的中庸之道。
結語
專業知識的有效性,在于能夠面對實踐領域的新形態和新模式。與以往使用的文獻數量、訪談信息、調查數據和統計資料相比,今天的數字信息的容量和體量每天都有巨量的增長。“‘信息’作為被傳遞的對象,在認知的意義上同‘知識’的意思是一樣的。”這就使得更新學科認知的問題域(la problématique)成為一種必要,驅動我們更新專業概念的觀察視角,走出一種因為固定觀察視角而形成的相對主義,從研究對象的縱向連續性和橫向關聯性出發,根據當下的專業語境重新回顧學科理論的基點,這是本文提出的媒介學視角的題中之意。
如果說媒介關系與社會關系等價,那么媒介與人的距離確定信息的滲透率;進一步推論,信息背后的觀念機制及其實踐方式亦是評估社會知性的參照系。德布雷在1980年發表其研究思想文化史的著作《抄寫人》,其中就對在中世紀修道院謄抄《圣經》的經院學者的職能提出一種看法:“讓社會思想的運行邏輯大白于天下,這有助于在思想事實和權威事實之間形成對應規則,更準確地說,是在傳遞或傳播的事實與統治的事實之間形成一種透視。”我們在本文中試圖通過符號生產、信息循環和文本形式的視角來考察編輯出版活動的象征效力,目的是對信息的生產和擴散所形成的各種文化權力進行追根溯源,求證信息傳遞及其所循環的信任委托所勾勒出的媒介學三角形,即信息需求的路線圖為信息傳遞的合理化展開問題域的討論空間的開放性。
①編輯出版學名詞審定委員會.編輯與出版學名詞[M]北京:科學出版社,2022:2,5.
② 迪利.符號學基礎:第六版[M].張祖建,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6.
③化石網.印尼蘇拉威西島這幅4萬5500年前的疣豬壁畫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動物形藝術品[EB/OL].(2021-01-28)[2022-07-15].http://www.uua.cn/show-7-11428-1.html.
④ 默克斯基.焚毀書籍[M].韓玉,張遠,林菲璜,譯.北京:電子工業出版社,2016:16.
⑤ 赫拉利.人類簡史[M].林俊宏,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34.
⑥ 費羅內.啟蒙觀念史[M].馬濤,曾允,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216.
⑦ 馬爾坦.印刷書的誕生[M].李鴻志,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3.
⑧ 麥克盧漢.理解媒介[M].何道寬,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225.
⑨?? 夏蒂埃.書籍的秩序[M].吳泓渺,張璐,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26,88,2.
⑩? 德布雷.普通媒介學教程[M].陳衛星,王楊,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4:70,77.
??? 德布雷.媒介學宣言[M].黃春柳,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48,15-16,18.
? 湯普森.文化商人:21世紀的出版業.張志強,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6:264-267.
? 萊文森.人類歷程回放:媒介進化論[M].鄔建中,譯.重慶: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8.
? 陳衛星.新媒體的媒介學問題[J].南京社會科學,2016(2):114-122.
? MIèGE BERNARD.Les industries du contenu face à l’ardre informationnel.Grenoble: PUG,2000:43.
?? 巴斯卡爾.內容為王[M].趙丹,梁嘉馨,譯.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17:XII,118.
? 韓琦.中國和歐洲:印刷術與書籍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203.
? 里德利.創新的起源[M].王大鵬,張智慧,譯.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21:253.
? 達恩頓.閱讀的未來[M].熊祥,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11.
?? 周紹明.書籍的社會史[M].何朝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103,4.
? DEBRAY RèGIS.Histoire des quatre[M]//Les cahiers des médiologie 6.Paris: Gallimard,1998:15.
? 馬尼奧.紙上威尼斯:16世紀威尼斯出版業如何改變了世界[M].李依臻,譯.上海:文匯出版社,2019:238.
? 斯蒂格勒.技術與時間:愛比米修斯的過失[M].裴程,譯.上海:譯林出版社,2000:70.
? 卡茨,彼得斯,利比斯,等.媒介研究經典文本解讀[M].常江,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177.
? 威肯.實驗室里的詩人:列維-施特勞斯.廣州:新世紀出版社,2012:116.
? 斯特勞斯.憂郁的熱帶[M].王志明,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383.
? 麥克盧漢.麥克盧漢如是說:理解我[M].何道寬,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121.
? DEBRAY RèGIS.Manifestes médiologiques.Paris: Gallimard,1994:16.
?? 芬克爾斯坦,麥克利里.書史導論[M].何朝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33,195-196.
? 馬克盧普.美國的知識生產與分配[M].孫耀君,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12.
? DEBRAY RèGIS.Le Scribe.Paris: Edition Grasset et Fasquelle,198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