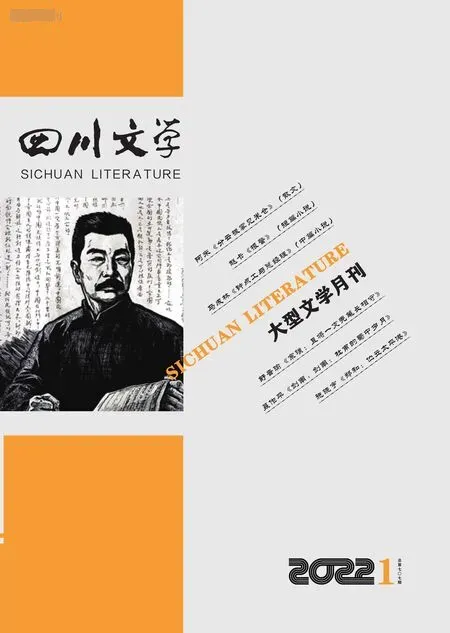報警
□文/趙卡
我們這棟樓臨街,有十幾間門臉房,小超市是開在大門口旁邊的。小超市門前的臺階,幾乎成了孫飛虎的專座,每次他老婆接了他的車后,他不先急著回家,而是到小賣部買一瓶冰過的雪鹿啤酒,坐在小賣部門旁的臺階上,先灌一大口,然后再一小口一小口地喝完;喝完后,他把啤酒瓶子拎在手里,點上一支煙,開始和人閑聊,聊到一支煙抽完,煙屁塞進(jìn)了啤酒瓶,才拍拍屁股起身回家。
孫飛虎長得虎背熊腰啤酒肚,晃著一顆夜壺似的光頭,看起來威猛,卻總是一副怏怏不樂的樣子,心里像有什么苦惱的事。他的家在我們這棟樓的五單元六樓,前年租的,聽說他們兩口子有房,我很奇怪明明有房為什么還要在外面租房,天哪,他們咋回事,腦子沒毛病吧?直到有一回樓下小賣部的老板娘說了原因我才知道,他們的房子是按揭的,在新城區(qū),同等面積,新城區(qū)的租價高出舊城區(qū)三成,所以,他們兩口子精打細(xì)算,把新城區(qū)的大房子租出去,在舊城區(qū)租了一個小房子,其中的差價就是賺的。
孫飛虎的小舅子叫帽帽,也住在我們這棟樓里,他是剛租了不久的,住的是二單元六樓。帽帽在城里也有房,不過他那是門臉房,屬于臨建,一百多個平方米,租給他人做飯館了。姐夫小舅子都有房又都在我們這棟樓租房住,我真搞不清楚他們要干嗎,幾天后帽帽請我老婆吃飯,并喊上了我,我才知道,帽帽是因為我老婆才到我們這棟樓里租房住的。此處需要說明一下,帽帽和我老婆并沒有一腿,我老婆跟我說過,帽帽是為了上她們的壺方便才臨時來租住的,這么一說我肯定放心了,我也就不覺得帽帽租住在我們這棟樓有啥不對勁兒了。
壺就是賭博場子,我老婆她姐立起的,一開始不行,靠不多幾個人勉強(qiáng)維持,慢慢地,有了點名氣,來賭的人多了,生意也就好起來,人手不夠的時候,我老婆就在她姐的壺上幫忙。壺不大,卻是一個小社會,上壺的啥人都有,當(dāng)然都是些壞人,好人誰上壺呢,上了就下不來了。帽帽就是個壞人,他上壺的第一天,我老婆就把他的情況摸了一個大概,因打架斗毆將人致殘,坐了八年大牢剛出來不久。我老婆還打聽到,在坐這八年大牢之前,帽帽還坐過三次大牢,每次三到五年不等,所犯的罪都不輕,罪名幾乎一樣,重傷害。可以這么說,自十八歲以后,帽帽就是牢房的常客了。帽帽出來后,消停了不長時間又和以前所謂道上的朋友聯(lián)系上了,幫討了幾回債,按比例掙了一些傭金,沒多少但買完一臺二手奧迪A6后還剩了些。討債這種臟活兒不是經(jīng)常有,沒事的時候帽帽就在城郊接合部的幾個壺上轉(zhuǎn),有一天就轉(zhuǎn)到我老婆她姐起的這個壺上了。
一開始,帽帽和其他上壺的賭徒一樣,并沒有吸引多少人的注意,大伙兒都是來耍錢的,耍了幾天,帽帽就在壺上有點鶴立雞群了。我老婆說,帽帽的錢多,耍得也大,還看淡輸贏。按壺長的說法,這種人才是好貨。一個壺,能否長久地立下去,主要取決于帽帽這樣的好貨多寡,如果賴貨多了,好貨少了,壺就沒法維系下去了。
從我老婆認(rèn)識帽帽那天開始,帽帽就一直戴著一頂灰不溜秋的棒球帽,帽邊兒上像密密麻麻地縫了一圈污漬,看上去很臟,但從未有人見他脫下來過。如此,人們就明白他為啥叫帽帽了。我問過我老婆,帽帽真叫帽帽嗎?我老婆說當(dāng)然不是了,帽帽的真名是馬樹林。后來,我才從我老婆那里知道,帽帽之所以不會當(dāng)著別人的面脫下他的帽子,是因為他的頭上全是刀疤,他擔(dān)心他那顆破破爛爛的頭會把別人嚇壞。
其實,帽帽根本沒必要擔(dān)心自己那副尊容,在壺上,哪怕你的頭被人割了,也不會有多少人吃驚的,大家只關(guān)心輸贏。
帽帽是混社會的人,壺上的人都知道,但他肯定不是老大,因為老大不可能像他那樣親自上壺的。這行當(dāng)?shù)囊?guī)矩,老大一般是罩場子的,只要說好價錢,老大會派出小弟看著場子,不管大壺還是小壺,沒人罩著幾乎連半個鐘頭都開不下去,就像我老婆她姐的這個壺,自立起的頭一天就有人罩上了,罩著她們的人叫二扶。二扶有多厲害,這么說吧,如果給他一個師的兵力外加兩艘航母,他就敢打美國,可誰知這么厲害的老大,有一天竟被帽帽掀翻在地。
按說,帽帽是招惹不起二扶的。混社會的人都知道,一個老大有一個老大的地盤,平素都井水不犯河水,偶爾還有合作,這是道上的規(guī)矩。二扶的地盤在城南,當(dāng)然在城南他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的主兒,城南起的壺自然全由他罩著,按月收費,大壺一個月3萬元,中壺一個月2萬元,小壺一個月1萬元,我老婆她姐的壺屬于小壺,每個月準(zhǔn)時上交1萬元,這都沒啥毛病。唯一的毛病就是二扶一旦喝了酒,就會過來砸場子,本來是你罩的場子,為啥還來砸呀,我老婆她姐質(zhì)問二扶,二扶噴著滿嘴酒氣說,以后你這壺按中的算,每個月須準(zhǔn)時上交2萬元——好在,二扶是喝大了酒說的,酒醒后沒當(dāng)真。我老婆怕二扶有一天當(dāng)了真,就很擔(dān)心她姐這壺還能不能立住,帽帽給她建議說,這家伙這么貪婪,不如你們換個人罩住場子。這話不知咋回事被二扶聽見了,他又喝了酒,帶著十幾個小弟,拎著一支雙筒獵槍要來壺上給帽帽一個好看,我老婆消息靈通,及時通知了帽帽,帽帽嚇得開著他的二手奧迪A6跑了。
沒過兩天,帽帽又上壺來了,這回他帶著兩個人,都是坐過大牢的,揣著刀,揚言只要看見二扶就會一刀捅死他。這陣勢,把我老婆和她姐嚇壞了,生怕壺上鬧出人命,好在,二扶那段時間在別處尋釁滋事,沒來壺上。來到壺上的是二扶的一個弟兄,叫三滿,附近村子里的,噴頭挺大,我老婆聽說過他的名頭,滿家五虎的老三。三滿帶著五六個人是來壺上賭錢的,并不是替二扶找帽帽茬兒的,再說了,他壓根兒就不認(rèn)識帽帽。頭一兩天,三滿贏了幾萬塊,高興得不行,誰料第三天手氣就不行了,把頭一兩天贏下的幾萬塊錢倒出去不說,連本錢也輸光了,賭徒的心理無人不知,越輸越想往回扳本兒,于是,輸光了身上錢的三滿就向壺上的款車借錢。
壺上一般都備有兩三個款車,利息統(tǒng)一而穩(wěn)定,日利一毛錢,這種錢,一般人是不敢借的,除非他家有礦,借一萬塊錢一天的利息就是一千塊錢。但賭徒敢借,賭徒這個物種,無論思想還是肉體,和別的物種真不一樣,膽頭子大起來時,別說是日利一毛錢了,就是一塊錢他都敢借。所以,壺上的款車掙的是暴利,擔(dān)的也是大風(fēng)險,因為沒有任何抵押,不管輸贏,賭徒必須日結(jié),結(jié)不了,那就想辦法了,比如跟人到家里去要,或者有人擔(dān)保幾天內(nèi)還清,實在還不了,那只能上手段了,比如,各種無底線的精神恐嚇和肉罰等。
三滿那天沒向別的款車借錢,從我老婆手里借了九千塊錢,按規(guī)矩,壺一散場就要還回一萬塊來,問題是,三滿的手氣實在太臭了,壺還沒散場他又輸光了。沒辦法,錢一時半會兒還不回來了,每逢這種時候,借錢的人要么帶放款的人去家里取,要么找人給擔(dān)保,必須要給款車一個交代的。但那天三滿輸急眼了,沒給我老婆任何交代,拍拍屁股鉆進(jìn)他的越野車?yán)锞妥撸蚨紱]尿拼命跟在他車后不停要錢的我老婆。
我老婆肯定追不上三滿的車,她知道,三滿跑了,借給三滿的錢也就等于跑了,這種事,壺上時有發(fā)生,該認(rèn)倒霉得認(rèn)倒霉。就在這時,帽帽開著他的二手奧迪A6也跑了,前面是三滿的越野車,后面是帽帽的奧迪A6,路上刮起一炮黃塵,不知道的人還以為他們在賽車呢。我老婆當(dāng)時挺納悶,帽帽并沒從她手里借錢,跑啥呢?這時就得說說二扶了,二扶從壺上按月拿看場子的錢,除了維護(hù)場子的秩序,還有一個職責(zé)是追債,像三滿這種欠了錢要跑的賭徒,如果二扶在,那是跑不了的,就算跑了也不怕,二扶能找到他家使了手段讓他把錢還了。可是,二扶并不在壺上,看場子成了一句空話。
“唉,今天又遇見鬼了!”我老婆沒有辦法,一個人坐在地上生悶氣。
她姐就給二扶打電話,打了一氣打不通,二扶電話那邊翻來覆去就一句話,您撥打的電話不在服務(wù)區(qū)。
“二扶不是死了吧?”她姐懊惱地罵道。
壺要散場時,帽帽開著車回來了,讓我老婆驚訝不已的是他把三滿借她的錢連本帶利給要回來了。怎么要回來的,我老婆晚上回家后對我說,不是帽帽有多厲害能從三滿手里把錢要回來,而是帽帽攔住了三滿的車,報了一個人的名字后,三滿乖乖地給他幾個弟兄打電話,讓他們馬上送錢過來。
帽帽報出的那個人,名叫白志軍,外號“白臉”,在本市屬于一般人惹不起的人物,別說滿家五虎了,就是二扶見了他都要繞道走。
這事的直接后果,壺上一怒之下不給二扶交保護(hù)費了。這不能怪壺上,要怪也只能怪二扶自己只管收錢不管事的吃相,吃相的確難看。“這樣做,二扶肯定不會放過你們的,你們小心點吧!”我替我老婆她姐擔(dān)憂,我老婆卻不以為然,似乎她們早想好了對付二扶的辦法。
果然,沒多久二扶就帶了一群小弟找上了壺,那天他又喝了酒,拎著一支雙筒獵槍,先朝天放了槍,然后重新給壺上定出了保護(hù)費,一個月3萬元,一次性交齊,否則,就不要立壺了。我老婆和她姐當(dāng)時嚇壞了,正在耍錢的賭徒面面相覷,沒一個敢站出來吭聲的,除了帽帽。帽帽是講理的人,他說二扶太不講究了,都是道上混的,哪有這么做事的,誰知話音未落,二扶就把槍戳在他頭上了,叫他閉嘴,一個叫騰拉爾的小弟還過來踢了他一腳。帽帽故技重施,又報出了白志軍的名字,但這回不管用了,一來二扶喝了酒,酒勁兒正給他壯著膽呢,二來他手里有槍,槍比酒更壯膽。
“那我打個電話……”帽帽對二扶說。
“當(dāng)然可以。你打吧,”二扶知道帽帽要叫人來,這是道上混的一種套路,他還特意叮囑了帽帽一聲,“盡量多叫幾個,把白臉也叫過來,我還真想看看他的臉到底有多白。”
電話通了,帽帽在二扶的注視下簡單說了下他這兒的情況,雖然看不見電話那頭是什么人,但從帽帽的神色來看,他嚴(yán)肅得像一個殺手。
不大一會兒,壺上來了一臺黑色的大奔,后面跟著兩臺金杯面包車,一個穿著一身白西服的瘦子剛從大奔里下來,帽帽就大聲吆喝上了:“軍哥,在這兒呢!”
那瘦子長著一張寡白的臉,背略微有點駝,放慢腳步徑直朝二扶走過來,使二扶吃了一驚,他認(rèn)得,這就是道上人稱“白臉”的白志軍,果然來了。白志軍后面緊跟著的小弟有十幾個,手里都帶著劈斧和鎬把,還有兩個小弟手里端著霰彈槍,一看就比二扶的破雙筒獵槍威力大。
白志軍人狠話不多,他甚至都沒工夫辨認(rèn)一下眼前這個人是不是二扶,就突然停下腳步,對二扶的人輕言慢語了一句:“你們都散了吧!”
二扶打了一個寒戰(zhàn),他的人像聽到咒語一樣,果然都掉轉(zhuǎn)身散了,除了踢過帽帽一腳的騰拉爾。
“軍哥。”帽帽激動地上前叫了一聲。
“你在這兒耍呢?”白志軍斜了他一眼,問。
帽帽應(yīng)了一聲“啊”,然后一把奪下二扶手里的雙筒獵槍,揮起槍托砸在二扶的面門上,二扶仰面朝天跌倒在地,雙手捂著血臉聲嘶力竭地號喊起來。帽帽又用槍指了指騰拉爾,騰拉爾識相,當(dāng)場就給帽帽跪下了,帽帽照著他的腦袋狠狠踢了一腳后罵道:
“狗崽子!”
接下來的事就好辦了,壺上的保護(hù)費要交給白志軍,每個月準(zhǔn)時上交1.5萬;當(dāng)然了,白志軍也是用名聲看場子,人是不可能到這種小壺上的,他的名聲比二扶好使一萬倍。
時間長了我老婆就發(fā)現(xiàn),帽帽和他姐夫?qū)O飛虎不怎么對付,不怎么對付的原因很簡單,帽帽每一次犯事,包括坐牢,都要花不少錢的;這錢,除了他的老大白志軍自掏腰包給他打點各個環(huán)節(jié)出過一些,主要是他姐出。他姐家并不富裕,兩口子跑出租車維持一家生計,每天很辛苦的,給帽帽花一次錢,半年的辛苦錢就沒了。
“瞧你這個當(dāng)姐夫的,不要那么小氣嘛!”我老婆到小區(qū)門口的小賣部買東西,碰見孫飛虎,就對他開玩笑說,“你小舅子現(xiàn)在可掙上大錢了,放心吧,他以后會報答你們的。”
“嗤!”孫飛虎把手里的煙頭塞進(jìn)了剛喝完的啤酒瓶,站起身拍了拍屁股罵道,“那個喪門星,他咋不死呀?他要是死了,就算他報答過我了。”
“老孫,你這話說得就難聽了,”小賣部的老板娘用白眼瞅了他一下,“沒你還有他姐呢,畢竟人家是親姐弟倆,姐姐不管弟弟能行嗎?”
“我看他姐早晚有一天——”孫飛虎從褲兜里掏出十塊錢,遞給老板娘。“被這個喪門星害了……再拿包煙,就紅云吧!”
看來我老婆說的帽帽掙上大錢的事,孫飛虎是不相信的。實際上帽帽真的掙上大錢了,自從白志軍嚇退二扶接了我老婆她姐壺上的看場子活兒后,帽帽就成了白志軍派往壺上的小弟,白志軍的名聲太好使了,壺上有一段時間再無各路紅皮黑鬼鬧事,賭徒們來的也多,壺上也就掙了一些好錢,帽帽也跟著掙了一些。帽帽掙的是放高利貸錢,一毛錢的日利比攔路搶劫都利大,如果持續(xù)干下去,以帽帽手里的本錢,一年就可掙到兩百萬。
“帽帽哪來的本錢啊?”我曾問我老婆。
我老婆說:“他拉了一個賣過藥的人給他投資,那人叫小蓮,手里有百八十萬閑錢,投資到他這里比存銀行強(qiáng)過一百倍。”
原來是這樣,我心想這個叫小蓮的人錢可真閑心可真大。很多人不知道壺上放高利貸的風(fēng)險有多大,雖然俗話說高風(fēng)險伴隨著高利潤,但其中道理其實很淺顯,再高的利潤也架不住高風(fēng)險,比方說原來在壺上放高利貸的我老婆,她的四十萬元本錢是我從銀行卡給她透支出來的,放了半年如今連本錢都要不回來了,但我老婆總是信心滿滿地說能要回來,外面連本帶利已經(jīng)欠她一百多萬了。
果然,連三個月都沒到,帽帽就把從小蓮那里拿到的八十多萬元全打水漂了。我以為帽帽和我老婆一樣,放出去的款一時半會兒收不回來而已,在壺上,放出去的款一時半會兒收不回來是正常的,慢慢收唄,反正拖一天是一天的利息,他是混社會的,后面又有白志軍撐腰,根本不怕人欠錢,他有的是辦法要錢;再一問,才知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把小蓮給他的錢全輸了。我老婆給我說了原委,帽帽嫌放高利貸來錢慢,要來個痛快的,就背著小蓮在壺上賭,誰知手氣和運氣都不在他這頭。
這下別說利息了,連本錢都沒保住,小蓮聞訊后當(dāng)然不干了。以前小蓮十天半月和帽帽不見一面也能拿到利息,自從帽帽輸光錢后,他就每天跟在帽帽屁股后面要錢,后來都貼上了飯錢、煙錢和油錢,他只要本錢不要利息,但沒用,按壺上的說法,帽帽已經(jīng)成了沒毛的干公雞。不急眼是不可能的,小蓮開始給帽帽放狠話,揚言要把他送進(jìn)牢里。壺上的人都知道他們之間的關(guān)系,也知道他們那點破事,不過都在看小蓮的笑話,帽帽這種人,頭上的刀疤比小蓮臉上的皺紋都多,他能從帽帽手里連本帶利拿回錢來嗎?當(dāng)時我也是這么想的,結(jié)果證明我們的想法是完全錯誤的。我老婆對我說,小蓮有個親戚在市檢察院當(dāng)二把手,別說帽帽了,就是白志軍也不敢輕易惹小蓮的,大家都在混社會,都明白一物降一物的道理。
帽帽在小蓮的面前認(rèn)慫了,承諾在兩個月內(nèi)給他歸還本錢。我不知道他拿什么來給小蓮歸還本錢,他的房子是租的,那臺二手奧迪A6充其量賣個十幾萬,除了搶銀行的押款車,我不知道他還能琢磨出別的什么辦法來。誰知我又錯了,沒幾天我就看見帽帽的車?yán)镒粋€雙下巴女人,雖說又肥又丑,但渾身珠光寶氣的,帽帽說那是他的女朋友。我問我老婆,就算帽帽坐過大牢,但他那女朋友又肥又丑不說了,起碼比他大15歲吧,睡在一起不嫌惡心嗎?我老婆笑著對我說,如果一頭老母豬能借給帽帽100萬,老母豬就是帽帽的女朋友。我明白了,帽帽這家伙,為了搞到錢,主意都打到老女人身上了。
過了兩天,帽帽請我和我老婆吃粥火鍋,還帶著他那個雙下巴女朋友,聊了一會兒才知道,雙下巴女人叫汪美麗,她老公也是賣藥的,發(fā)大了,給了她一筆錢和兩套房子后就離了婚。吃喝了一陣后,帽帽把我的情況給汪美麗說了,說我經(jīng)營著一個牛肉干廠,產(chǎn)品暢銷全國,很有本事的一個人。“哦?”汪美麗當(dāng)時驚訝地把嘴噘成了一朵菊花,“沒想到,這么有本事的人還長得這么帥,馬樹林要不說,我還真看不出來——”緊接著她還和我老婆開起了玩笑,“妹子啊,你可得把你老公看住了,別被那些缺男人的小賤貨們給搶跑了。”
我老婆并不覺得我有多么帥,更不覺得我有多大的本事,因為我那個牛肉干廠都快撐不下去了。所以對于汪美麗跟她開的玩笑,她是不以為然的。
“趙總他們這個行當(dāng)對牛肉的需求量很大,就他們那個廠一年大概消耗100噸不止。”帽帽對汪美麗說,“我打聽過了,他們主要用進(jìn)口牛肉,比如巴西、烏拉圭和阿根廷的,肉販子們都賺大錢了。”
汪美麗望著我,似乎在問我帽帽說的是不是事實。
我點點頭,給她簡單講了一下我們這個行當(dāng)?shù)那闆r。凡是開小牛肉干廠的,一個月的用肉量也就10噸左右,都沒有直接從港口拿肉的實力,必須從專業(yè)的肉販子那里買;專業(yè)的肉販子都從港口往回拉肉,拉一個貨柜的肉最少200萬元,回來就被這些小廠子分了,刨去各種費用后,賣一柜肉大概能賺到30萬元。
“這么多哦!”汪美麗對帽帽說。
“所以我算過了,販牛肉是一樁穩(wěn)賺不賠的買賣,我沒和你開玩笑吧,美麗?”帽帽一邊說著話一邊把他的臉湊近了汪美麗的臉,讓人以為他倆要當(dāng)著我的面親兩口似的。
“嗯,我不喜歡開玩笑的。”汪美麗略微歪了歪頭,仿佛在自言自語地說。
我當(dāng)時就明白了,帽帽帶著他的雙下巴女友請我和我老婆吃飯,原來是要我配合他一下說販牛肉能輕松賺到錢。販牛肉當(dāng)然能賺到錢了,但每一柜動用的資金太大,動輒兩百萬以上,但這還不是問題,關(guān)鍵的問題我沒告訴他倆,連我老婆都不知道,販牛肉只能賺到白菜錢,只有販走私牛肉才能賺到大錢。
吃完飯后,帽帽要請我和我老婆唱KTV,我老婆興致挺大,我卻借口太累推掉了。我心想哪有帶自己老婆去唱KTV的,那多沒意思呀!
一晃幾天過去了,帽帽還沒從汪美麗那里搞出販牛肉的本錢來,我以為汪美麗壓根兒就拿不出200萬的本錢,哪曾想完全不是這么回事,我老婆對我說,帽帽這點小伎倆,汪美麗一眼就看穿了。原來,帽帽讓我配合他說販牛肉利大純屬是個幌子,他只想從汪美麗的手里騙出錢來再去壺上賭,賭徒嘛,在哪個壺上輸了錢,就會想辦法從哪個壺上再劃回來,輸?shù)迷綉K,想劃回來的念頭就越重,當(dāng)然了,對本錢的需要也越大。汪美麗又不是小孩子,她知道帽帽是干嗎的,所以,帽帽的這個計策失敗了。
帽帽這人屬于屢敗屢戰(zhàn)的那號狠角兒,汪美麗這頭沒了希望后,他就甩了他這個又肥又丑的女朋友,開始打起我老婆的主意來。我倒不是說我老婆多漂亮,被他惦記上了,而是——我老婆突然有一天跟我說,帽帽要和她合伙做生意,從南方往回販冰。我一開始還以為聽錯了,冰這東西一到冬天北方到處都是,白給都沒人要還用從南方販,腦子進(jìn)了冰水吧?“不是水凍成的那種冰——”我老婆給我解釋,“是人吸溜的那種冰毒,利可大了。”這下把我氣壞了,我對她很不客氣地講,你姐搞賭博,你販毒,你們一家子都可以組建犯罪集團(tuán)了;賭博嘛,被抓了最多坐幾天班房罰點款就沒事了,販毒可是要掉腦袋的。我老婆一聽這是掉腦袋的事就害怕,于是她找了個借口拒絕了帽帽。
就在我老婆拒絕和帽帽合伙做生意的第三天,帽帽從壺上消失了,但小蓮還每天來壺上,他在向帽帽催債的那段時間里,也喜歡上了賭錢,癮頭還挺大。
一個月后的一天,我到樓下賣手機(jī)的趙四那兒看他新上的幾款手機(jī),趙四給我推薦了一款OPPO的,他說這款手機(jī)的攝像功能非常強(qiáng)大,他和女友開房時試過了,連汗毛都能一根根清晰地拍出來。我手里沒那么多錢,想從趙四這兒賒一臺,誰知趙四搖著茶壺似的腦袋拒絕了我。“不是不給趙哥面子,”趙四說,“我現(xiàn)在手頭緊得不行,賣一臺手機(jī)最多掙50塊錢,我可以不掙你趙哥的錢,但賒賬是真不行呀!”
不行那就算了,我也不是真急著要買一部新手機(jī),我就對趙四說我是開玩笑,等這款OPPO降價時再來買。
趙四的生意不算太好,我待在他那兒的幾分鐘里,只有兩個讓他代繳話費的小攤販,還有一個過來買手機(jī)殼套的中年婦女。趁著空當(dāng)兒,我讓趙四給我轉(zhuǎn)發(fā)幾個黃色小視頻,他在這方面的存貨多,趙四一邊給我轉(zhuǎn)發(fā)一邊問我最近見帽帽的面沒,我說沒有。
“他不是在你老婆的壺上放款嗎?”趙四問。
“他早就是干公雞了拿啥放款,拿命放啊?”我一邊播放他發(fā)過來的黃色小視頻,一邊說。黃色小視頻是趙四和一個女的真人自拍,十幾秒的樣子,頭臉都不清晰,呻吟聲也不大。
“操,上疙泡當(dāng)了!”趙四突然喊了一聲,那樣子真是滑稽。
“咋了這是,一驚一乍的?”我關(guān)了黃色小視頻問他。
“這疙泡借了我4萬塊,說好的就這幾天還,可電話打不通,微信也不回,到他家找了,敲不開門……”趙四神色不安,說話也結(jié)結(jié)巴巴起來,“他他……不是出出……了啥事事……吧?”
還有這么一出事,我就像聽到一個比狗還大的笑話。“啊——”我吃驚又幸災(zāi)樂禍地說,“真是怪了,這年頭還敢給帽帽借錢的?咳,就當(dāng)肉包子打狗算了!”
趙四張大眼睛,一下就面如土色了。“噢!趙哥,”他懇求起我來,“你回去問下嫂子,帽帽到底去哪了,這要找不見他,我的4萬塊……4萬塊吶!趙哥,求你千萬千萬回去問下嫂子,咋能找見帽帽?”
看趙四那副可憐樣兒,我答應(yīng)了他,條件是他一有新的真人自拍視頻,必須第一時間給我發(fā)過來。
我老婆每天晚上回得晚,因為散壺后壺長要細(xì)細(xì)地算一天的賬,人欠的和欠人的,還要處理一些亂七八糟的事,我老婆是在壺上幫忙的,肯定不能早回。“帽帽到底去哪了,咋能找見帽帽?”當(dāng)晚,我把趙四的問題轉(zhuǎn)述給了我老婆,我老婆說:“帽帽可能出事了,我也是剛得到的信兒。”
帽帽出事的消息讓我吃了一驚,我忙問我老婆她是咋知道的,我老婆說她給白志軍上交保護(hù)費時白志軍告訴他的。“說是販冰,但公安局還沒拿住確鑿的證據(jù),這幾天正調(diào)查呢……這家伙不是真去販冰了吧?嚇?biāo)牢伊恕蔽依掀拍樕n白地對我說。
我第二天才把消息告訴趙四,當(dāng)晚沒告訴他,是怕他睡不著覺時會氣死。趙四一聽帽帽有可能販冰被抓了,差點氣得嘴歪眼斜,大罵帽帽不是個東西,詛咒他早日吃了槍子兒。我在一旁默不作聲地笑著。趙四問我笑啥,我只好給他講,帽帽要是吃了槍子兒,他那4萬塊別說利了,就連本都拿不回來了。
“這倒也是……”趙四懇求我給他出個主意,如何才能逮住帽帽的蹤影。“哥,求你了,只要能拿回我那4萬塊錢,我就送你一個新款OPPO。”
這下我高興了,決定給他出個主意。我的主意是,給帽帽停在小區(qū)院里的車安個追蹤器。因為,雖然傳言帽帽被抓了,但誰也不知真假,但他的車還在小區(qū)里,說明消息未必確鑿。
帽帽是賣了他那臺二手奧迪A6后又買了一臺二手三菱越野車的,不過停在小區(qū)院里有一個多月了。我記得帽帽剛買回這臺車時我還問過他,放下好好的奧迪A6不開搞個三菱越野干嗎,帽帽當(dāng)時就回答了我一句話,“能走遠(yuǎn)路呀!”我當(dāng)時還尋思,他這欠了人一屁股債,搞不好要跑路。
汽車追蹤器不貴,才幾百塊錢的事,趙四買上后先跟他的手機(jī)聯(lián)了網(wǎng),接著就和我到小區(qū)院里,正準(zhǔn)備給帽帽的車安裝時,忽然院里進(jìn)來五六個警察,問我們鬼鬼祟祟干什么,我只好替趙四老老實實地交代了緣由,警察才放過我們,不過,我們的手機(jī)號他們都記下了。然后,警察用拖車把帽帽的二手三菱越野拖走了。
“這東西白買了!”趙四晃了晃手里的汽車追蹤器,苦笑了一下對我說。
又過了幾天,我老婆跟我說,帽帽的確被拘了。當(dāng)然,我老婆的消息還是白志軍給她的。帽帽販冰,公安局已經(jīng)人贓俱獲,那個人,就是她姐,那個贓物,在她姐家,她姐全交代了。
要不是孫飛虎,我們小區(qū)里的人,包括趙四,誰也不可能知道帽帽和她姐到底是怎么販冰被抓的。新聞是后來在電視和報紙上報道出來的。
人們好幾天沒見孫飛虎的面了,以為他不開出租車干別的營生去了,沒想到有一天,孫飛虎回來了,那顆夜壺似的腦袋像上了釉彩,長了滿臉黝黑的胡子;他還是老樣子,坐在小賣部門旁的臺階上,像往常一樣不先急著回家,不,是干脆就不回家了,吆喝小賣部老板娘給他拎出啤酒來。“要冰過的,先拿一捆。”孫飛虎說。他先灌了一大口,然后再一小口一小口地喝完;喝完后,不像從前那樣,把啤酒瓶子拎在手里,點上一支煙開始和人閑聊,聊到一支煙抽完,煙屁塞進(jìn)了啤酒瓶,才拍拍屁股起身回家——而是,他幾乎相信自己是坐在酒吧里,沒完沒了地灌,灌了五六瓶,灌暈乎了,才點起一支煙,紅著眼圈兒和圍著他的人說,他家的出租車已被公安局暫扣了,暫扣的理由是涉嫌運毒。
“啊……”圍著他的人都愣了。“你這說啥呢……肯定是喝多了!”
孫飛虎一看就很痛苦,把手里的空煙盒握成一個團(tuán)兒后,轉(zhuǎn)過身對小賣部老板娘喊道:“給我拿一盒兒煙來,紅云!”
老板娘給他遞了一盒硬殼紅云。煙不貴,才7塊錢,孫飛虎平時就抽這個。
“是我報的警,嘿嘿!”孫飛虎抽了一口煙,得意地說。
他的笑聲回蕩在小賣部四周,圍著他的人又愣了一回,但孫飛虎并不像突發(fā)神經(jīng)病,瞧神色的話應(yīng)該是真的。
“狗日的。”孫飛虎一揮手,將手里抽了半截的煙頭扔出去了,這氣勢,全然沒有平時在他老婆面前逆來順受的樣兒。
這時小賣部老板娘問了一句:“那你老婆……”
“進(jìn)去了!”孫飛虎說。
小賣部門前圍攏過來的人又多了幾個,包括趙四(我發(fā)微信叫他過來的),都是一棟樓里住的鄰居,每日抬頭不見低頭見,大伙兒都很關(guān)心他們兩口子——出了什么事。“虎哥,”趙四大喊了一聲,“你小舅子是不是也讓抓起來了?聽說他販冰……那可是搬罐子的營生。”天哪,趙四的腦子是不是有毛病,咋能當(dāng)著孫飛虎的面說這種事呢,我沒忍住踢了他一腳,提醒他注意點說話分寸。
孫飛虎又點了一支煙,看著趙四,他倆都笑了,尤其是孫飛虎,笑得啤酒肚都在抖動。他還能笑出聲來,估計已不在乎他老婆和他小舅子的死活了。“沒錯,姐弟倆都被抓進(jìn)去了,是我報的警。”孫飛虎腹中的酒勁兒漸漸散開,他有點發(fā)暈,憤怒地說起了他小舅子和他老婆販冰的事,以及他為什么要報警的原因。
我聽明白了,孫飛虎并非大義滅親,他只是被他老婆和小舅子氣壞了。
前頭我就說過,帽帽拿了小蓮的錢放高利貸,連本帶利都打水漂了,其實他不只欠小蓮一個人的,我老婆說,帽帽還借了好多人的錢,最后都被他輸在壺上了。欠人的錢,不還是不可能的,哪怕有白志軍這樣的人物給他撐腰,所以,在騙不到老女人錢的情況下,經(jīng)高人指點,帽帽決定鋌而走險販冰。畢竟,販冰的利潤太大了,大到可以讓人不懼危險,帽帽肯定想過了,只要成功了這一趟就能把他欠人的錢全還清了。但販冰是需要本錢的,帽帽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求到了他姐的名下,他姐就他這么一個親弟弟,咬了咬牙,背著孫飛虎把他們在新城區(qū)的那套大房子抵押出去,拿到了一筆錢。這事辦得見不得光,一開始孫飛虎不知道,但世上沒有不透風(fēng)的墻,沒幾天孫飛虎就知道了,他要當(dāng)面問他老婆一個清楚,但他老婆就是躲著他,連出租車也不給他交了,他就沒完沒了地打電話,有時一天能打上百個,但他老婆就是不回。
“狗日的不回吧?好,我叫你不回電話——”孫飛虎像胸口劇痛似的用夾煙的手捂了捂,然后抽搐著嘴角說,“我報警……我還就不信了!”
圍觀的人們被他逗笑了,只有我和趙四沒笑。
孫飛虎報警時咋說的……我萬萬沒想到,他竟然信口胡說他老婆的出租車上藏了兩公斤冰。雖然我無法想象孫飛虎報警時的神態(tài),但我相信他的口氣迫切而堅決,這還了得,公安局立馬出動警力,按他提供的車牌號去抓捕他老婆的出租車,不費吹灰之力就人贓俱獲了。
整個事情的經(jīng)過還是后來我老婆告訴我的。
我老婆她姐的壺停了,停的直接原因,和帽帽被抓有關(guān)。帽帽是白志軍的小弟,按常理分析,帽帽要干這么大一樁生意,白志軍不可能不知道,甚至,白志軍就是幕后的老板,但白志軍對帽帽販冰的事真的一無所知。我老婆去給白志軍送當(dāng)月保護(hù)費時,白志軍讓我老婆轉(zhuǎn)告她姐,馬上把壺停了,他跑了幾趟公安局,打聽到公安局正在調(diào)查所有和帽帽有關(guān)系的人。“這家伙膽頭子太大了,多大的買賣他都敢干,差點把我也連累進(jìn)去!”白志軍真是被帽帽氣得夠嗆。
原來,帽帽已經(jīng)被小蓮他們追逼得厲害,實在沒辦法了,就讓他姐給他借一筆錢出來,他沒說要去販冰,只是說做一筆很大的買賣,萬無一失,他姐沒錢,被他連煽帶騙把房子偷偷地抵押出去搞了一筆錢出來。這一溜操作,都是瞞著孫飛虎的,帽帽給她姐承諾,用不了一個月的時間錢就回來了。帽帽要去南方取冰的地方,是個多山多河的省,他那臺二手奧迪A6是肯定不適合遠(yuǎn)途,所以他就把二手奧迪賣了又買了臺二手三菱越野車,準(zhǔn)備就緒后他獨自一人駕車走了。白志軍和我老婆說,帽帽從南方拿貨很順利,只是一回城就發(fā)現(xiàn)了不對勁,有一臺捷達(dá)車始終在跟隨著他,他于是加大油門穿街過巷專揀生僻的地方狂奔,發(fā)現(xiàn)根本甩不脫跟蹤他的車,于是他冒險從一個他很熟悉的小巷里進(jìn)去,把裝了冰的包扔進(jìn)了一個無人住的舊院里,然后把車開到大街上連闖兩個紅燈,故意讓交警攔下,交警問他為什么闖紅燈,他說他的駕照找不見了,心里慌得不行才誤闖的。交警信了帽帽,開完罰單手續(xù)就放了他,然后他開著車又瞎轉(zhuǎn)了幾個地方,瞎轉(zhuǎn)的時候他給他姐打了一個電話,讓她到一個小巷的舊院里取個東西。帽帽打完電話后發(fā)現(xiàn),跟蹤他的那臺捷達(dá)車早不見了,他才懷疑那臺車根本就不是跟蹤他的,可能是他的神經(jīng)太緊張了。
“然后他姐就按帽帽說的地方取了貨,走在大街上時被警察攔住了……”我對我老婆說。
“咦,你咋知道的?”我老婆驚訝地問。
“我掐指一算,”我齜牙一笑說,“算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