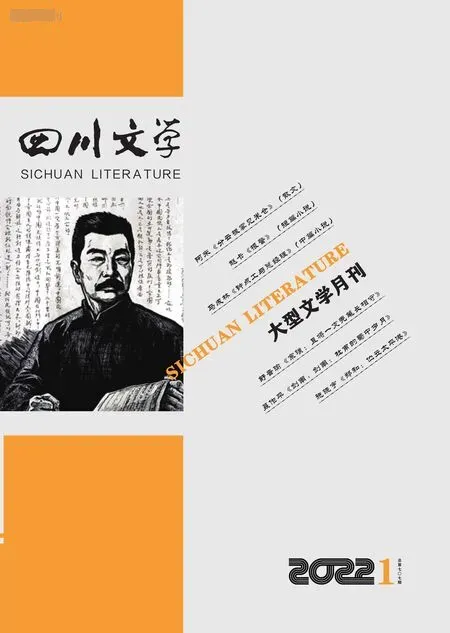短歌行
○ 孫大順
○ 毛拾貳
○ 吳群芝
○ 戴長伸
○ 木公
○ 胡文彬
○ 李巖
山村公路(外三首)
○ 孫大順
公路圍繞著山攀緣,有一段曾嘗試進入
山的內部,仿佛要把山鏤
但公路無法空山命名。山村才是公路之心
狗呔、雞飛,鴨子搖晃著
走向低處的小溪。淡淡的炊煙
在不見的地方雙手合十
山不旁觀,就像一個巨人
早晚要被人間的秘密壓垮
樹向公路招手,乘著汽車的公路
在我們胸膛奔馳
山村與公路,不遠離,不聚集
永恒的耐心是個謎
那些彎腰,把一粒粒陽光
撿起來的人,在方言里留守
在發亮的地名里老去
蘆 花
夕陽給蘆葦的記號愈合了
年久失修的黃昏,就要帶走
蹲在人間,老得掉牙的風
雪停了,野鴨子回了家
空蕩的湖面,蘆花彎著脖子,踩著
潦倒的灘涂,向北移動
舊書里的情節
像舊書里,一段似曾相識的情節
父親在前,與我保持一句話的距離
走過喧鬧嘈雜的菜市場
人間的粗糙與纖細,委身于
買賣聲中不能自拔。蔬菜和糧食
這唯一沒有落差的綠色血液
連通著城市與鄉村,也連通著我們
但父親與我依舊沒搭上話柄
做不完的農事,趕不完的熟路
攆得父親的步子又快又大
許多年過去了,父親的背影
總是不能,像陽光一樣亮在心頭
越來越重,生活的磨礪
也沒能拉近我們的距離
人來車往,向晚的城市。容納了
一條條心事重重的商業街
低著頭,橫穿馬路的父親
險些被一輛出租車帶倒
很少進城的父親,顯出少有的慌張
過了街道,生性倔強的父親
忽然彎下腰來,裝著去緊
原本就沒松開的鞋帶
父親生澀的舉動,是僅有的示弱
是想讓那個年輕高大的男人
離自己近一點。更近一點
只有父親停下來,我才能超過他
但我們依然無話可說。突然一陣狂風
吹來幾聲響雷,天空垂了下來
壓得城市暗無天日
街上匆忙的人群也慌亂起來
凌厲的剎車聲,拉長這個不安的黃昏
這時我感到一只微涼
布滿老繭的手伸了過來
慢慢地抓著我的右手,就像小時候
我抓住父親的手,緊緊地不松開
依舊無話可說,但我和父親步伐一致
內心的洪水一浪高過一浪
黃 昏
我看見天空正落入水中
那些等待的樹枝,拍打
臂彎下陌生的風,這唯一的動作
把春天引開,黃昏清冷,我在等待手持燭光的人
捎來月光的口信,我知道,有點什么事
要在這個黃昏的眉梢,停留或者發生
當春潮淹沒月亮(外三首)
○ 毛拾貳
我能在湖邊邊枯坐上一整天
像一片云,不屬于湖心
只是暫時紋飾水的表面
群山用眼神把我推開,抑或沉默著
將我從古老又神秘的布景中區分出
我與那塊沉啞的巨石同屬一類
我們無法計算自身的承重
僅是長久地站在河灘,反復磨洗
然后護送水流——
同時滑出風與直線的輕盈
當春潮淹沒月亮,隱隱地
我竊聽到它以水月的口吻
為一朵苔花的失眠備好了辯詞
而它的酣眠,被淹沒遙遠的視線
注定讓我只會對眼下的波瀾
模糊不清
靜謐時刻
靜謐時刻,羊群在風中回味甘草
母親蜷縮花椒樹下,割取茂盛
萬物的生命在黃昏中接近某個支撐點
云雀騰空,翅膀與余暉相互摩擦
一種靜謐之間的相互交換
我們眼中的黃昏是神秘的啟示錄
也是光陰造訪意志的產物
如果能夠把握好黃昏,把握好
萬物榮枯的分寸。就能在六月
伴隨向下俯沖的果子
捕捉到歲月流逝的影子
綠皮書:苦難的胎記
男子悄無聲息地靠近了水果攤
在眾目睽睽之下,他挑了一個
沒有褐斑的蘋果。隨手
在衣服上擦拭了幾下
之后痛快地咬下,他咬得很甜
我生怕,甜壞他的牙
我想,要怎么披星戴月,才能
痛快地對著月光飲下尖銳和甜蜜
干了不少體力活,燒了不少血
對著病入膏肓的骨骼,喝不少草藥
這是他的生活!他緊咬著他的生活
明明是他,死咬著生活不放
可為何我的舌苔也會不自覺泛苦
我們都在向生活取證,可說真的
我還是不會證明“我,是我”
本人不能,那戶口簿、身份證、學生證
此等身外之物它們能嗎?就像他
一個苦出身的孩子,用二十年時間
去洗脫背上的黃土。誰能證明
他洗掉的是泥土,而不是苦難的胎記
小夜曲
在夜里,我過多地使用了聽覺
將頭沉入一張密不透風的網
村莊沉睡,但還有燈光不肯熄滅
只有在一切沉入睡眠的時候
才發現,我孑然一身、無比清醒
門外水泥路上呼嘯而過摩托車
車胎軋到坑洼處,發出離合的聲響
鄰居給醉酒的男人留了門
他推門而入的聲音,多么像
一陣風馱不動囈語
我翻了一個身
沒有人意識到我翻了一個身
我雙肘如槐木,翻來翻去
翻到的都是舊的玫瑰和禮物
我是黑夜的漏網之魚
過多地依靠漆黑、繁衍自己的聽覺
他們想把鳥也釣回去(外三首)
○ 吳群芝
釣魚者甩出漁線
他們拋鉤,收鉤
——就有魚,游進魚簍
鳥在河面上
飛來飛去,像是旁觀者
走向河邊
洗衣,洗菜,洗身子——
夕陽落在水上
所有人都回家了
魚不回家,它們沒有家
釣魚人有家,但他們不回
他們想把鳥
也釣回去,把沒有家的
都放進魚簍
魚 竿
看釣魚人釣魚
每天晚上都會來看
河水里的燈光也是
只是看不說話,這跟我沒有區別
他們不說話,只是釣魚
偶爾發出的聲音
沿著高高的河堤,有風提了提
還是聽不清,只有收上來的魚竿亮著燈
這多像死了的人
棺柩前也被人放了一盞燈
死者是釣魚者,也可能是放燈人
那些年
鏡子里那些回光
不會縫合一個人碎成玻璃或沙礫的碎片
不會扶起一針下去就與人間失聯的爺爺
那些年,炊煙潦草,鳥聲膽怯
唯有高枝上嘰嘰喳喳的喜鵲
槐花一樣叩向額頭,給人歡喜與期待
不到七十歲患病嚴重的爺爺
每天趔趄走出家門,坐在河邊
目視河那邊來來往往的汽車
以及,劃過河來的船舟
看是否有他當兵去了幾年
還未回家探親的小兒子,我的八叔
叔叔接到電報回來的時候
爺爺沒有在河邊等他
他在最后一次發病時
被一針切斷了呼吸
而燕子越飛越遠
燕子飛過秋天,一場雨
落下來,一首詩掉光了葉子
泡桐,銀杏,樟木,楓葉,霜降——
像秋水打著水漂,那些跳躍的石頭
多少預知未知的心事,就這樣吧
背負秋天的人不追汽車,火車和落葉
你說的,我們慢慢地走,我們——
哎,月月歲歲,歲歲月月,那又怎么樣呢
多少浮懸的事物,竹籃在天空里晃來晃去
蘆葦躥升天上,像一片樹葉
掛在另一個秋天里,而燕子越飛越遠
不像我們——
這么暖的陽光(組詩)
○ 戴長伸
十月二十六日深夜
忽然間覺得那些詰問毫無意義
面對終將謝幕的人生,再多輝煌
也不過是曲終人散前的狂歡
也不過是致幻劑殘存的清醒
面對時聚時散的命運,明滅的天空
忽然間,覺得某些質問毫無意義
四 月
四月,被稱為惦念的事物漸生疑竇
比如這春色
比如握不住的彷徨
再比如,這注定要游走的魚、飛遠的鳥
四月,被稱為惦念的只是一堆誤解
盛在春天的筐里,最終將無處安放
陽光下
陽光真好啊
我坐擁一大片白花花的草原
想到自己居然可以這么富有
我忍不住痛哭起來
愣神
天越來越冷,需要關心的事越來越少
值得忽略的人越來越多
想喝酒的時候我會捂住杯子
想你的時候,我會愣一愣神
眩 暈——致程川
我達不到的地方,你替我完成
我嗤之以鼻的優秀,你替我承受
我徹骨的眩暈
你我先后體味:生活的苦累,盲目的命
一粒沙里有多少號叫不出的咸澀……
嘩嘩作響的才華,弄醒垂淚、迷茫的青春
我難言的心情仿佛今夜窗外飄過的車燈
搖擺不定,又像你我曾經的青蔥少年
夾竹桃(外一首)
○ 木公
與竹迥異
也不結桃
名字實在費猜費解
土坡上,溝渠旁
成叢聚簇而生
分泌一種異香
讓蚊蟲蒼蠅遠逃
滅蚊的東西越來越多
天生的夾竹桃,和夾竹桃人
卻越來越少了
苦 楝
總有一株苦楝樹,扎在我記憶最深處
故鄉,安放我童年的小山村
后園,一片秀麗的苦楝林
花開淡紫,向陽而生
酸棗樣的果實,一串串
放大了當年的饑餓貧困
微毒微苦,使蟲豸不敢近身
也像嚴厲的警語
斥退了我們肚子里的饞蟲
一口苦楝木箱。父親親手打造
整整六年的中學時光
它像忠誠的學伴,時刻提醒
勤學苦練,苦盡甘來
今天,我在滿城華燈與
車流里迷離,只有一株苦楝
路標一樣,指引我找到故鄉找到父親
奶奶(外二首)
○ 胡文彬
奶奶曬太陽的大槐樹底下
今年垛滿了帶秧子的花生
每次那些干透的花生在夜里
窸窸窣窣地響
好幾次我都以為是奶奶回來了
可是推開房門,除了月光
只有秋風
和我撞個滿懷
雪落到緩慢的鐘聲上
雪落到半生寺緩慢的鐘聲上
也落到早落下的雪上
一個人在半生寺剃度,這遠不是結束,
也不是開始
沒有什么是過不去的,也沒有什么是放
不下的
就像生死,世間的愛那么多,不去恨了
雪落到雪上,雪成全了雪
黃昏沒有迷路,冒雪一頭扎進了
茫茫的夜色
蘭花草
山中的蘭花草
在山坡上,高過其他的草
它清瘦的花,高過葉片,但低于它頭頂
的松枝
這邊草叢里的蘭花
與小溪那邊草叢里的蘭花
還有巖石后面的蘭花
這么多的蘭花,山外來客
沒看見蘭花之前
三里地之外,早已被
蘭花的清香
洗凈了內心的雜蕪
香樟樹(外二首)
○ 李巖
昨夜的雨后,空氣中
少了點什么,雨水從鋸掉的香樟葉
斷落,那片湖似乎又
長高了一寸。
陽光透過樹干,投下
一道孤獨的影子。我久久站在樹下
終于摸到,受傷的第三根肋骨
一個人看雨
一個人看雨,落下來,感覺自己也在下
雨,我們各自下著
各自,兩不相干
雨無始無終,下成了雨自己
我的雨安靜下來
就像打點滴
鐵皮青蛙
上緊發條,鐵皮青蛙
彈出別樣的節奏
繃緊的神經,也跟著跳舞
起泡的啤酒花,渾濁的液體
流經左心房,咚咚咚,打鼓樣
再來一杯,再來一杯
一根無繩的線,拖拽著中年,像要永遠跳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