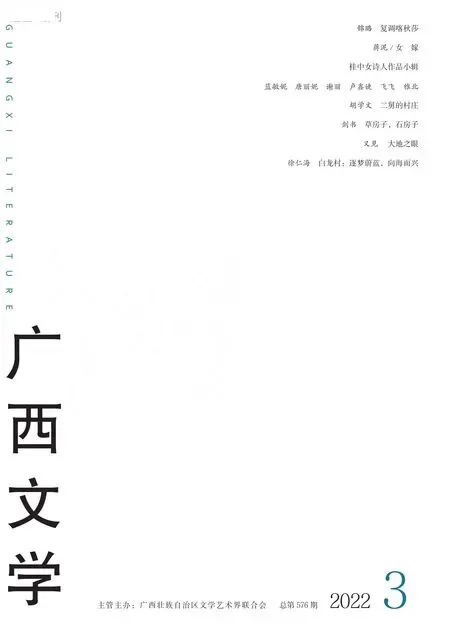她們中的她們
劉 頻
她們,都是“麻雀”詩群的詩人,堅持“麻雀”低調、真誠、樸實的寫作態度,但她們從不在眾鳥喧嘩的時代出讓內心的天空,從不讓虛妄的事物攪亂自己的飛行軌跡。
藍敏妮一直寫詩、作畫,特別喜歡中國古典戲劇。她的詩歌表現出對現實生活天性的、獨特的敏感和懷疑。兩年前,在“麻雀”詩群十周年慶典的頒獎會上,我給獲得“先銳”獎的藍敏妮寫的授獎詞是:“藍敏妮的詩歌一直有其個人很強的辨識度。無論是詩意造境、語言體系,還是詩歌意味,都有她獨有的一套。她的作品有美,有智,有態;常常從古典意境出發,直擊現實生存背陰處的隱痛,并且讓這種隱痛跨越時間。她力求在日常的細節中夸大、變異,給出各種出乎意料的詩意和哲思。在古典和現代擠壓的針尖上,她找到了自己的立足之地”。在《九面埋伏》這組詩里,她更加從容開闊,有如萬物皆備于我,信手拈來,舉重若輕。《青衣戲》《大戲》《橘種》《九面埋伏》等篇什,體現出一種置身于人生幽秘處的發現者洞若觀火的能力,在點破人生本相之后能夠優雅地微笑,在人生的靜寂與緊張感之中能夠妥帖地平衡。她有她個性化的語調和留白,有她獨特的言外之意。在語言技術上,她是在后退中抵達先鋒的,體現出東方魔幻現實主義的魅力。謝麗多年向佛,近些年來寫戲收獲頗豐。她的作品一向大氣,體現出一座工業城市滋育出的氣質。無獨有偶,謝麗也是以戲為題材,聚焦于舞臺上的光,她的《光之偈頌》輕松突破水做的枷鎖,令我激賞,這是具有人生深度和智慧的一組詩歌。在《追光》《天地排光》《頂光》《余光》等作品里,謝麗將佛光和舞臺之光融合一體,于光里和光外、臺上和臺下、幕前和幕后中,詩歌的慧眼窺盡人生的破綻或圓滿而不嗔不怨、不喜不悲、不疾不徐,在出世中入世,在入世中出世。在《看向青山》里,看到的是她的另一幀剪影,她就在那里,在內生的豐盈處,于生命的局限中尋找、抵達無限的可能性。我特別喜歡《不過是一顆心》這首詩,她在浮世中分開亂象,回歸本心,示人間以愛和悲憫的底色,這是當下詩歌彌足珍貴的品質。
盧鑫婕是一位鐵路警察,也是一位年輕的母親。她的作品從不給人以制服和鐵軌的威嚴及冷峻的感覺,而是呈現出一種雪地上小鹿奔跑的詩性曲線和蹄印。與之過往作品相比,她的組詩《開在天空的花》顯示了在日常生活中向內、沉潛的努力,《毛線》《長命鎖》《長羽毛的人》《一朵開在天空的花》,依然保持著她對日常生活習慣性的變形和整合的美學能力。生命的美好和溫暖,抑或影影綽綽的憂傷,徐徐彌漫在寓言式的抒寫里。《背風箏的人》體現出她進一步的成熟度,在這里,生命的輕與重、命運的溫情與嚴峻、心靈的傷痛與撫慰、人生的執著與妥協,都在一種理想主義的光暈中獲得情感邏輯的妥善安排。
我曾說過:“作為侗族女詩人,飛飛有明確的詩歌源頭,在被當代物質稀釋的文化語境里,她的名字依然叫侗族。她的寫作體現出在當下生活的焦灼中回歸出生地的努力。她的詩歌在少數族裔情懷和普羅大眾思想之間、在傳統價值和現代文明之間、在迷惘的城市和遙遠的家園之間、在舊時光和新生活之間形成對抗、交織、融合,在節制和隱忍的文字中鋪設情感世界的緩沖地帶。”飛飛喜歡先鋒文化特別是先鋒電影,《在第五季舒適生長》這個組詩里,體現出她更趨前衛的姿態。像一張A4紙,她的背面是侗鄉,正面是城市,形成一種既對立又融合的詩歌二元結構。她的作品富于電影畫面感,語言促迫、鋒利,故意將現實與夢境混淆起來,從而更方便對現實進行切割、組合,如《第五季》《和一只鳥睡在一起》。而《不如》《無主之城》,則凸顯出一種在后工業時代中確立自我存在、人性尊嚴的渴望。于是,詩人的肉體之痛直抵精神之痛,在疼痛的光芒中救贖自身;甚至,她需要制造出假想敵去確認個體生命的價值,需要用古典英雄主義精神去慰藉被物質年代異化的靈魂。
雅北、唐麗妮均來自柳州國有大型企業,在鋼鐵和機械的超重低音里,她們依然保持著詩歌的柔軟性。雅北近兩年來詩鋒甚健,異軍突起,這個出自書香門第、會寫舊體詩詞的年輕詩人,在這組作品里,有她個性化的氣息和呢喃,將人間煙火、自然世界、農事生活的柔美、安恬和幸福九轉回腸地書寫出來,安靜與萬物對話,從外物滲入內心。《一都米的醇香》《荷苑旭日》《一種愉悅的時刻》,如暖色調的油畫一般明亮、豐美,既能展示世界的曠闊,又能保持細節的清晰,并富于情感的層次感。《單車上的童年》《青云街》,在并不新鮮的題材里依然彌散出一種新鮮的氣息,這有賴于語言的魔力和情氛的營造。唐麗妮是一位嫻靜的女子,在小說、散文、詩歌的寫作中都有所斬獲。在這里,她以自語的方式和安謐的語調,從隱隱的憂傷中透溢出愛的安詳。《看云是我喜歡的事物》《在我們之間有一面鏡子》《沒有月光望不到的地方》,用一種清澈的文字和心靈,去化解生鐵一般的生活,去過濾現實的沉重。《紅高粱在傾聽麥曲的教誨》,有一種向美而死、向美而生的精神蝶變,掘進式地挖探深化了人生感悟。
六個“麻雀”詩群的詩人,從她們的隊伍中一個個走出來,成為一個個卓然獨立的她。——這,是這個春天里令人欣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