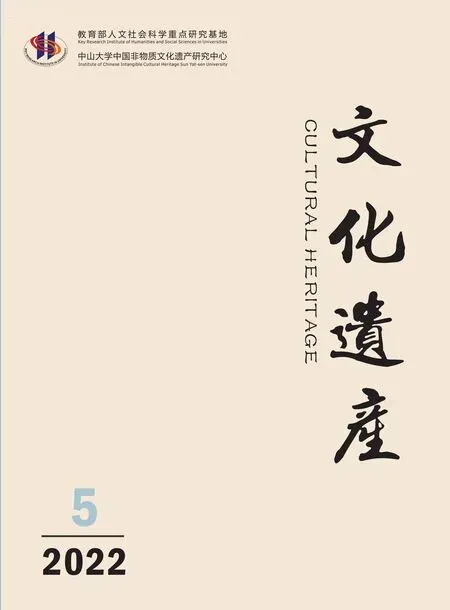論南戲開場腳色“踏場數調”
劉敘武
南戲《張協狀元》開場部分有:“(末白)……后行腳色,力齊鼓兒,饒個攛掇,末泥色饒個踏場。(下)(生上白)……后行子弟,饒個【燭影搖紅】斷送。(眾動樂器)(生踏場數調)……”劇本未說明腳色緣何且如何“踏場數調”。宋元時演劇有一些固定套路,劇本不需詳寫,僅作簡單提示,演員、讀者也很清楚場上將演什么、為什么演。錢南揚先生注云:“踏場數調——謂按照樂調的節奏,在戲臺上舞蹈。成化本《白兔記》一出有【紅芍藥】一曲,有聲無辭,情況雖與這里不盡同,也還留存一些踏場數調的痕跡。”成化本《白兔記》開場為:“(扮末上開云)……奉請越樂班,真宰遙,鸞駕早赴華筵。今宵夜,愿白舌入地府,赤口上清天。奉神三巡六儀,化真金錢。齊攢斷,喧天鼓板,奉送樂中仙。(末唱)【紅芍藥】哩啰連啰啰哩連,哩連哩啰哩連哩。連啰連哩連啰哩,啰連啰哩連哩。連啰連哩連啰連,啰□□□啰哩,連啰哩啰哩。”依錢先生所言,末唱【紅芍藥】曲時要按照樂調節奏在戲臺上舞蹈,【紅芍藥】曲即踏場之調。俞為民先生注“哩啰連”曰:“曲之和聲,有聲無義。”前人對南戲開場腳色“踏場數調”的來源、意義、消亡等問題未做過專門研究,本文試作探討。
一、“啰哩嗹”是源自梵語的戲神咒
成化本《白兔記》中末唱【紅芍藥】曲是為“奉神”,即奉“樂中仙”,這屬于“三巡六儀”之儀軌,顯示出【紅芍藥】曲具有強烈的宗教祭祀意味,是南戲開場程式重要組成部分。“哩”“啰”“連”三字排列順序似無規律可循,以此三字或同音異寫字記音的聲調廣泛存在于宋元以來諸宮調、南戲、雜劇、傳奇、傀儡戲、某些地方戲、儺儀、佛教贊歌、道教曲辭和咒語、宋金元詞、南音、琴曲、民歌及南方少數民族民歌、戲曲中,學界一般稱之為“啰哩嗹”。除錢南揚、俞為民二位外,王季思、吳曉鈴、饒宗頤、張燕瑾、彌松頤、趙日和、趙尊岳、劉念茲、胡雪岡、白之(Cyril Birch)、鄭孟津、吳平山、侯百朋、劉浩然、康保成、廖奔、翁敏華、沈沉、袁賓、黃杰、徐時儀、孟凡玉、孫星群、王昊、陳燕婷、葉明生、吳寧華、陳建華、卓玫君、倪博洋、黃建興等學者也研究過“啰哩嗹”,相關成果十分豐富。
胡忌先生《宋金雜劇考》引《莆劇談屑》云:“莆劇在未正式演出時,由后臺先打‘三鑼鼓’……過后,有彩棚……內念四句大白是:盛世江南景,春風晝錦堂。一枝紅芍藥,開出滿天紅……念完,唱下詞尾。下詞尾沒有曲文,只‘哩啰嗹’三字顛倒唱出。這三字是咒文,為得怕舞臺上‘不潔凈’‘穢瀆’了‘神明’,唱這咒文,便可保臺上大家平安。”“莆劇”即莆仙戲,開場還保留了后臺先打鑼鼓——這與《張協狀元》中“后行腳色,力齊鼓兒,饒個攛掇”“眾動樂器”及成化本《白兔記》中“齊攢斷,喧天鼓板”相同;內白提到【紅芍藥】;沒有曲文的下詞尾以“哩啰嗹”三字顛倒唱出。《莆劇談屑》指“哩啰嗹”是祛污穢、保平安的咒文,與成化本《白兔記》中唱【紅芍藥】曲“奉送樂中仙”意義指向一致——祛污穢才能迎神明,迎神明方可保平安,在這一過程中念咒文顯得尤為重要,顯示出莆仙戲開場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未經文人改竄的早期南戲傳統。同為閩南地方戲的梨園戲、傀儡戲亦有隨“啰哩嗹”曲進行的“踏棚”活動,這些都有力佐證了錢南揚先生的論斷不誤。

饒先生的研究對以后的學者影響很大,康保成、徐時儀、陳建華、倪博洋等明確支持饒先生的觀點。不過,也有學者認為“啰哩嗹”并非源于梵語。黃杰先生說:“與其說‘啰哩啰’之類的和聲起源與(原文如此——引者注)佛教唱頌,毋寧說為中國本土的歌唱習慣所致”;孟凡玉先生說:“‘啰哩嗹’民歌襯詞源于中國古代生殖崇拜”,又說:“‘啰哩嗹’……源自本土方言、民俗及歌唱習慣”;陳燕婷先生認為“啰哩嗹”根源于儺儀中的驅邪咒語。
筆者贊同“啰哩嗹”源于外來語的觀點。宣德寫本《金釵記》第四十出有:“(末)叫番奴唱番曲。(丑凈唱)【雁兒舞】阿不干沃虔答刺速,散哩答歹蒙古喥嚕嚕,干別吉忒可速也,呵罕獨滿八木里。(齊舞)哩嗹維嗹哩嗹嗹,唻啰哩啰啰哩嗹,啰哩□啰嗹哩嗹,啰哩嗹啰啰哩嗹啰哩嗹。”既然“啰哩嗹”是“番曲”,就不是中原本有的。倪博洋深入研究了金元全真詞中和聲“哩啰”,以較生僻的“嗹”字為考察窗口,發現“嗹”相對晚出,最早出現于《張協狀元》,得出“‘啰’‘哩’‘嗹’為密咒對音用字是令人信服的……‘啰哩嗹’可能最初只是用于南戲之中的咒語”的結論。倪文論據翔實、論證嚴謹,論點較可信。不過,康保成先生對梵語四流母音傳入中原時間有不同看法,他認為唐人南卓《羯鼓錄》所附“諸宮曲”之“太簇宮”下“羅犁羅”曲與“啰哩嗹”有關,又據《晉書·五行志》、明人方以智《通雅》等推斷:“‘啰哩嗹’是梵曲,最遲(西)晉時已傳入中原”。陳建華先生認為四流母音隨悉曇傳入中國當在劉宋之前。
饒先生后來又詳細解釋了“啰哩嗹”何以具有祛穢、迎神、保平安之效:首先是晚唐、北宋禪僧每于上堂作偈語、制頌贊,喜用“啰哩”作為和聲,具有入道成佛的特殊作用,特別是密宗很容易把它看成咒語;道教有許多儀式從佛教脫胎而來,于是金全真教徒倚聲傳道的作品好用“啰哩?”作為助聲;再后來,南宋與金時期的謳歌、南戲、諸宮調中也唱“哩啰”或“哩啰嗹”;到了明初,“啰哩嗹”已被充分用于南戲,祭祀戲神清源祖師也要唱“啰哩嗹”,因祭祀清源以田、竇二將軍配享,田將軍即閩人所祀之田元帥,“啰哩嗹”又演變成田元帥咒,用以趨吉避兇。
“啰哩嗹”在中國流傳時間久、范圍廣,滲透進各類文本,出現位置、形式復雜多樣。康保成先生總結“啰哩嗹”往往用于四種場合:祭祀戲神時所唱咒語,與婚戀有關的喜慶場合,乞兒乞討時所唱蓮花落,作為襯字、幫腔起烘托氣氛作用。沈沉先生歸納“啰哩嗹”的五種功能包括:經言咒語,呼叫與應答,指代不便明言的隱語,依托與模擬某些聲音,襯腔、幫合與和聲。孫星群先生梳理了“啰哩嗹”六種分布情況:在佛經、道教及巫術音樂中,在木偶、戲曲音樂中,在民歌、民間歌舞中,在福建南音中,在南戲、諸宮調中,在其他史料中;八種不同用場:凈臺,敬奉田都元帥,木偶戲酬神演出開場唱【大出蘇】,為主人求愿、還愿、求平安,用于祭祀,高興順口唱,和聲,調情、合歡隱語。陳燕婷先生將“啰哩嗹”的用場和功能統合為三種:驅邪祈福、婚戀隱語、和聲。吳寧華先生研究了廣西賀州、田林兩地瑤族還盤王愿儀式中的啰哩嗹曲調,通過分析比較其音樂形態、功能、作用,指出:“啰哩嗹”在儀式中最重要的作用是無固定音高、用來幫助記憶曲調的襯詞。可以說既有分類研究已經相當全面、細致了。
饒宗頤、趙日和、白之、劉浩然、康保成、廖奔、沈沉、孫星群、葉明生、陳燕婷等學者認為,在以上諸種情況中,凡在南戲、傀儡戲開場部分唱的“啰哩嗹”就是驅祟逐邪、召請戲神的迎神曲,也叫“相公咒”“凈臺咒”。筆者認為這個判斷是不錯的。清代《梨園原·論戲統》云:
古時戲,始一出鬼門道,必先唱【紅芍藥】一詞。何也?因傳奇內必有神、佛、仙、賢、君王、臣宰及說法、宣咒等事,故先持一咒,以釋其罪;兼利諸己——隔宿昧爽,因喉音閉塞,故齊聲而揚。古制云:“太子【千秋歲】,春圍【晝錦堂】,一株【紅芍藥】,開遍【滿庭芳】。”
這則材料可與前引文獻及相關研究結論相印證。
以上確認了踏場之調“啰哩嗹”是源自梵語的戲神咒,接下來討論“踏場”的意義。
二、“踏場”是腳色在模仿傀儡舞步
如果我們把“踏場”解釋為演員伴隨迎神曲以踏步作節奏,就像歌舞戲《踏謠娘》里“且步且歌”那樣,似乎完全說得通。不過,聯系到上文所述莆仙戲開場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早期南戲傳統以及同為閩南地方戲的梨園戲、傀儡戲藝人把隨“啰哩嗹”曲進行的“踏場”活動稱為“踏棚”,我們不得不對此再做一番探究,至少應說明“踏場”因何被稱作“踏棚”。
陳建華先生在饒宗頤先生論述基礎上進一步梳理了梵語四流母音演變為戲神咒過程中各環節的邏輯關系:“魯、流、盧、樓”本為南印度婆羅門階層所用梵語,因與俗語不同被賦予神秘色彩,又隨悉曇文字傳入中國被密宗誤讀和神秘化而作為咒語,再經巫道借用佛門僧侶咒語、傀儡戲移植巫道咒語兩個關鍵環節,最終成為戲神咒。可見,陳先生認為“啰哩嗹”作為戲神咒最初是從傀儡戲開始的。明人殷士儋所作散曲《冬夜許殿卿潘望甫載酒過訪觀傀儡聽兒盤彈琴二公即席各惠佳句走筆述謝》中有一則傀儡戲唱“啰哩嗹”的記錄:“【幺】新妝傀儡供歡笑,向樽前喝采聲囂。啰哩嗹,紅芍藥。一任他喧嘩呼噪,權當做賞元宵。【滿庭芳】呈妍獻巧,謾道是真珠絡臂、百寶妝腰。想悲歡離合虛圈套,看破極高。半虛空弄幾條線索,平白地做百樣軀勞。打一會蓮花落,舞一會堯民鮑老,說一會絮叨叨。”陳建華先生認為:“由于傀儡本來具有宗教含義,再加上受到巫道文化的輻射與影響,傀儡戲自然也染上一層巫道色彩,巫道咒語啰哩嗹也就傳到傀儡戲之中了。”陳志勇先生表達了不同看法,他認為是佛教咒語先影響了傀儡戲,再傳播至道教道壇。黃建興先生同樣認為是傀儡戲戲神的神格功能對道教田公元帥信仰產生影響,使后者咒語帶有“啰哩嗹”,“在福建眾多閭山派的神明咒語當中,只有田公元帥的咒語有此特征……”這就是說,假使“啰哩嗹”是先在道教道壇中流傳的,除戲神咒之外的其他閭山派咒語中也應有“啰哩嗹”。黃先生的說法很有說服力。倪博洋以“嗹”字為標準梳理歷史文獻,認為梵語四流母音傳入中國后呈現兩個發展方向:一是南戲、蓮花落中的和聲“啰哩嗹”,一是佛道助聲“啰啰哩哩”,兩者性質不同。這一觀點可與黃建興先生的觀點相參考。筆者認同“啰哩嗹”從梵語四流母音變為戲神咒不必經由巫道咒語這一環節。
陳建華先生據成化本《白兔記》開場部分有末腳唱“啰哩嗹”推斷:“南戲的開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傀儡戲的影響和啟發,或者就是某種形式的借用……南戲劇目開場的‘哩羅嗹’,也很大程度上是從傀儡戲中吸收而來。”陳先生的意見很有道理。時至今日,在福建泉州傀儡戲中“啰哩嗹”使用頻率仍遠高于梨園戲和南音。不過,陳先生的意見與前引倪博洋提出的“‘啰哩嗹’可能最初只是用于南戲”的觀點產生了分歧。于是我們產生一個疑問:戲神咒“啰哩嗹”究竟是先出現在南戲中的,還是先出現在傀儡戲中的?雖說難以立下判斷,但這一問題將我們的思考引向南戲開場與傀儡戲的關系。倘若我們能理清兩者之間的關系,不僅可以解答上述問題,對于理解“踏場”無疑也是有助益的。
《張協狀元》和成化本《白兔記》可證:南戲原是以院本為開場戲的,其中包含副末唱念諸宮調報告戲情、副凈與副末插科打諢。據元末明初人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和夏庭芝《青樓集志》的說法:“院本……又謂之五花爨弄。”《張協狀元》開場部分生唱:“真個梨園院體,論詼諧除師怎比……一個若抹土搽灰,趍槍出沒人皆喜。”“趍槍”(原文為“鎗”,當與“蹌”因形近訛誤)即趍搶、趨蹌。據《宦門子弟錯立身》題目“沖州撞府妝旦色,走南投北俏郎君;戾家行院學踏爨,宦門子弟錯立身”及該劇錢南揚校注本第十二出“(末白)不嫁做雜劇的,只嫁個做院本的。(生唱)【調笑令】我這爨體,不查梨,格樣,全學賈校尉。趍搶嘴臉天生會,偏宜抹土搽灰……”錢先生注云:“爨體,即院體,院本的規模、格樣。”趍搶即踏爨,是爨弄的最主要特征——伴隨音樂的強烈、夸張、獨特的足部動作。
伴隨“啰哩嗹”曲進行的“踏場”活動與爨弄里的“踏爨”因南戲開場形式產生了關聯,但至此尚不足以完全說明兩者之間的關系以及“踏場”的含義,仍需繼續討論。
元代南戲《耿文遠》佚曲【喜還京】云:“鼓鑼鼓鑼聲催,施逞百戲,抹土搽灰做硬鬼。看傀儡舞,傀儡呈院本,身分詼諧越樣美。”明人徐充《暖姝由筆》說:“有白有唱者名雜劇,用弦索者名套數,扮演戲跳而不唱者名院本。”“扮演戲跳而不唱”說明院本表演者只做動作而不歌唱,顯然是肉傀儡戲。宋懋澄《九籥集》卷十“御戲”條載:“院本皆作傀儡舞……”清人翟灝《通俗編》卷三十一《俳優》“按”稱:“院本只般演而不唱,今學般演者流俗謂之串戲,當是爨字。”點明表演院本時演員只演而不唱,這種表演就是“爨戲”。清末民初人徐珂《清稗類鈔》云:“蓋院本始于金、元,唱者在內,演者在外,與日本之演舊劇者相仿。”唱者與演者各司其職,唱者在幕內、演者在幕外,兩者不一齊出現在觀眾面前,這明顯是肉傀儡戲的搬演形式。今存最早記述院本演出的文獻是金末元初人杜仁杰散套【般涉調·耍孩兒】《莊家不識勾欄》,據程民生先生考證,該散套描寫的是金朝末年開封城里的一次院本演出。這是一出滑稽戲,演員有說亦有做,顯然不是肉傀儡戲。杜仁杰散套的真實性不容懷疑,前引文獻指院本是肉傀儡戲則需進一步求證。
《明刊閩南戲曲弦管選本三種》中有萬歷甲辰(1604)瀚海書林李碧峰、陳我含刊本《新刻增補戲隊錦曲大全滿天春》選本,內有一出《戲上戲劉奎》,又名《呂云英花園遇劉圭》。該劇是人扮傀儡的一個例證,講的是主婢二人做傀儡戲“請相公(即戲神田公)”的“請神”段落,丑腳扮女婢模仿傀儡表演請田相公下降的戲,口中還唱“嗹里羅嗹羅嗹”,旦腳責備丑腳做的動作怪模怪樣。這是一段滑稽搞笑的戲弄表演。葉明生先生認為:“小梨園的‘提蘇’應是這個人演傀儡的‘肉傀儡’表演形式的沿(原文如此——引者注)續現象。”“提蘇”演的即是仿傀儡提演戲神田公元帥(俗稱“蘇相公”)踏棚去煞的儀式。所謂“戲上戲”就是“戲前之戲”,是正戲開演前演出的開場戲。筆者已證:金代“院本”非雜劇之別名,而是雜劇中的專名,特指放在正雜劇前演出的小段雜劇,體制功能相當于宋雜劇艷段,院本可與正雜劇結合,也可與正戲文結合,都起導引正戲的作用。“戲上戲”應是明代閩南民間對院本的另一種叫法。這則材料可作為院本是肉傀儡戲的一個旁證。
《莊家不識勾欄》首曲所用曲牌為【耍孩兒】。康保成、張哲先生指出:“金元時期已廣泛使用的曲牌【耍孩兒】,來自將幼童扛在肩上玩耍的一種游戲,亦即‘肉傀儡’。”杜仁杰選此曲牌描寫院本演出,是否含有表示院本原為肉傀儡戲之意,也是值得留意的。
綜上,我們有理由推論,早期院本是一種肉傀儡戲,或至少包含肉傀儡表演,表演者有對傀儡動作的刻意模仿,杜仁杰《莊家不識勾欄》描寫的是金末院本演出情況,此時距爨弄傳入中原已逾百年,院本已演變為演員有說亦有做的戲劇。
戲神咒“啰哩嗹”看似與爨弄風馬牛不相及,但從“啰哩嗹”作為踏場之調聯系到爨弄中的踏爨動作,其中的邏輯脈絡是有跡可循的。我們可得出如下結論:梵語戲神咒首先出現在傀儡戲中,作為傀儡踏場之調,后來隨肉傀儡表演進入南戲開場部分。于是,南戲開場腳色一邊唱“啰哩嗹”一邊踏場的意思就很清楚了——這是在模仿傀儡舞步。畢竟傀儡不如人靈活,其舞蹈時足部動作非常接近“踏”。又因為“啰哩嗹”有聲無義,當省略了肉傀儡戲的唱者、將其職責轉交給舞者,模仿傀儡表演的腳色唱“啰哩嗹”并不違背肉傀儡戲“舞者不唱,唱者不舞”的基本原則。
鄭守治先生指出:“棚”作量詞用時,“主要稱量傀儡(偶人)、傀儡戲等戲劇事物……最初借用自‘傀儡棚’之‘棚’……”筆者認為,閩南莆仙戲、梨園戲、傀儡戲藝人所用“踏棚”一語應比“踏場”更為古老,源于傀儡戲。
三、文人清除南戲開場中的祭祀成分


文人參與民間文藝樣式創作,不僅要改造其形式,還會根據自己的意圖改變其功能,南戲開場的祭祀成分在文人劇作中遭到徹底清除。高明的《琵琶記》是第一部由文人劇作家創作的南戲作品,此劇是高明借前人之作改編而成的,其開場部分簡潔明了:
(末上白)【水調歌頭】秋燈明翠幙,夜案覽蕓編。今來古往,其間故事幾多般。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瑣碎不堪觀。正是:不關風化體,縱好也徒然。 論傳奇,樂人易,動人難。知音君子,這般另做眼兒看。休論插科打諢,也不尋宮數調,只看子孝共妻賢。驊騮方獨步,萬馬敢爭先?
【沁園春】趙女姿容,蔡邕文業,兩月夫妻。奈朝廷黃榜,遍招賢士;高堂嚴命,強赴春闈。一舉鰲頭,再婚牛氏,利綰名牽竟不歸。饑荒歲,雙親俱喪,此際實堪悲。 堪悲,趙女支持,剪下香云送舅姑。羅裙包土,筑成墳墓;琵琶寫怨,竟往京畿。孝矣伯喈,賢哉牛氏,書館相逢最慘凄。重廬墓,一夫二婦,旌表耀門閭。
讀者不難發現,相較于《張協狀元》和成化本《白兔記》開場部分,作者省去了副凈、副末插科打諢(“休論插科打諢”),并以高度概括劇情的文人詞取代冗長的諸宮調(“也不尋宮數調”),更刪掉了“奉送樂中仙”的踏場數調儀式。
高明清除南戲開場中祭祀戲神成分的主要原因大約有兩點:受儒家傳統“子不語怪力亂神”思想影響,不愿在劇作中保留迎戲神、保平安儀式,要將作品世俗化;《張協狀元》《宦門子弟錯立身》《小孫屠》開場部分都沒有交代作者創作意圖的文字,但從《琵琶記》開始,文人劇作家越來越重視在開場部分宣示自己的創作意圖,高明特意提醒讀者和觀眾“只看子孝共妻賢”,注意把握“不關風化體,縱好也徒然”的主旨,在正戲文演出前踏場數調無疑會干擾這一意圖傳達——這也是刪除插科打諢和諸宮調的原因所在。
《琵琶記》被后世尊為“傳奇之祖”,成為創作典范,其開場體制為明清南戲、傳奇繼承。雖說在《琵琶記》問世以后的文人劇作中看不到“踏場數調”了,但在民間演出中“踏場”或曰“踏棚”并未絕跡,尤其在保存了早期南戲傳統的閩南地方戲、傀儡戲中是比較明顯的。此外還有其他形式——《清稗類鈔》在說完“蓋院本始于金、元”之后還說:“今開幕之跳加官,即其遺意。”意思是,在正戲開演前演出的吉慶儀式戲《跳加官》來源于院本。清人孔尚任寫過一套【商調·集賢賓】《博古閑情》曲子,在附記中寫道:“此出敘作傳填詞之由,雖冠冕全本,而不必登優孟之場;倘能譜入笙歌,以易加官惡套,亦覺大雅不群矣。”孔尚任是順治至康熙年間人,這說明,至晚到康熙朝,正戲開演前演出《跳加官》已非常普遍。《跳加官》作為開場戲,除有一般意義的祝禱、祈福之義外,我們還可從其舞臺形式——演員表演時戴面具、不出聲、只有“做”,還有特殊、夸張的足部動作——看出這是對開場院本中肉傀儡表演形式的繼承。
余論 爨弄是傣泰民族先民的表演藝術
陶宗儀《南村輟耕錄》“院本名目”條說:“院本……又謂之五花爨弄。或曰,宋徽宗見爨國人來朝,衣裝鞋履巾裹,傅粉墨,舉動如此,使優人效之以為戲。”顧峰先生指出:“爨本來是東晉、南北朝至唐初的南中大姓,統治云南地區的大世族……并未自建爨國,子孫世襲,據地自雄。唐開元時為南詔所滅。但‘爨國’這個概念一直為當時的中原人士所習稱。甚至到南詔國和大理國時仍然沿稱。意指元代以前的云南。”陶宗儀所謂“爨國”實際是中原五代至宋時“白蠻”段氏建立的地方政權大理國,轄境包括今云南省全部及四川省西南部。《宋史》卷四百八十八“列傳第二百四十七·外國四·大理”載:“大理國,即唐南詔也……政和……六年,遣進奉使天駟爽彥賁李紫琮、副使坦綽李伯祥來……七年二月,至京師,貢馬三百八十匹及麝香、牛黃、細氈、碧玕山諸物。”可知李紫琮等到達汴京時間是政和七年(1117)。不過《宋史》未提及爨弄。明末清初人馮甦《滇考·段氏大理國始末》載:“政和六年,遣使李紫琮等貢馬三百八十匹及麝香、牛黃、細氈、碧玗山諸物,又有樂人,善幻戲,即大秦犁鞬之遺,名‘五花爨弄’,徽宗愛之,以供歡宴,賞賜不貲。”可知李紫琮等帶去爨弄演員的記載真實可信,殆因樂人非貢物,故《宋史》未載。爨弄在其原生地必已高度成熟,有自己特色,宋徽宗才會命宮廷演員模仿以為戲。梵語咒語成為戲神咒必在1116年以前。
元人李京《云南志略·諸夷風俗》載:
金齒百夷,記識無文字,刻木為約……男子文身,去髭須鬢眉睫,以赤白土傅面,彩繒束發,衣赤黑衣,躡繡履,帶鏡,呼痛之聲曰“阿也韋”,絕類中國優人。不事稼穡,唯護小兒。天寶中,隨爨歸王入朝于唐,今之爨弄實原于此。
可知爨弄是金齒百夷的表演藝術。據顧峰先生考證,并非“爨歸王入朝于唐”,而是其子守隅到長安朝貢,時在唐德宗貞元十年(794)。爨弄傳入中原不止一次,且時間跨度很大,影響最大的就是北宋徽宗政和七年這次。
金齒百夷至今猶存。據研究:“元代,在漢族歷史學家的文獻中將今天傣族的先民稱為‘金齒百夷’,有時也單獨分開稱為‘金齒’或者‘百夷’,但這些都是他稱,他們的自稱是傣。”可見爨弄是今天傣族先民的表演藝術。
傣族是一個跨境而居的民族,泰國、柬埔寨、越南的泰族(Thai),老撾的老族(Lao),緬甸的撣族(Shan),印度阿薩姆邦的阿洪(Ahom)都與中國的傣族(Dai)有著共同文化和共同族源,他們其實是同一民族因分布在不同國家被分成不同民族,但其族人均自稱Tai。由越南北部向老撾、中國云南、柬埔寨、泰國、緬甸、印度伸延,形成一條長達一千五百千米的傣泰民族文化帶。傣泰民族深受印度婆羅門教、佛教文化影響是人所共知的事實。有一個頗有意思的現象值得一提:如今泰國演員在演出傳統戲劇之前也是要用梵語或巴利語而非泰語念戲神咒的;泰國傳統戲劇孔劇的表演形式就是肉傀儡戲,演員表演時有非常明顯的模仿傀儡的程式化動作,足部動作最主要特征就是“踏”。《張協狀元》中提到丑腳的面部化裝特征是“烏嘴”——“(丑)……我恁地白白凈凈底……。(末)只是嘴烏。”“(丑)……愿我捉得一盝粉,一鋌墨。把墨來畫烏觜,把粉去門上畫個白鹿。”從北宋末期、金代早期墓葬中出土了詼諧之意甚濃、畫有“烏嘴”的雜劇人物磚雕殘頭。而今天泰國滑稽戲演員的化裝特征正是“烏嘴”。我們很難以“巧合”來解釋這種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