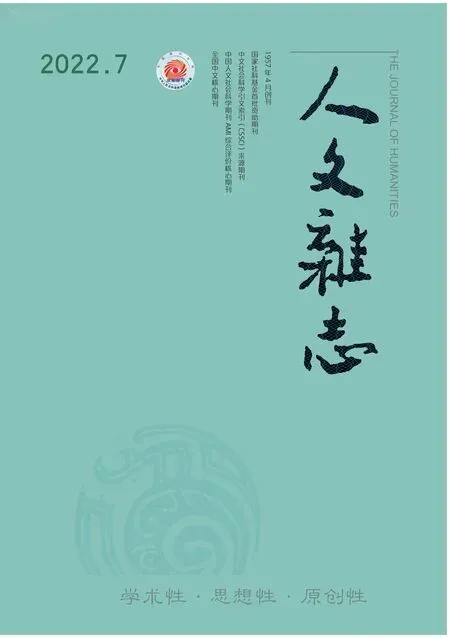《莊子》“小大之辨”之主旨是“大其心”*
“小大之辯”
是《莊子》一書開宗明義提出的首個哲學問題,它不僅是理解《逍遙游》思想的必經之途,亦是詮解《齊物論》思想之關鍵,對其的理解關乎《莊子》文章結構的合理性及其根本哲學主旨的把握。概而言之,莊學史各注家對“小大之辨”思想詮釋的價值取向,其類有三:一是向秀、郭象的“小大同揚”說,二是支遁的“小大同抑”說,三是明清時期流行的“抑小揚大”說。
此三種詮釋路徑已基本窮盡“小大之辨”所有可能的價值立場,近代學者雖不能提出新的可能的詮釋路徑,然亦力圖提出異于古之注述家的新見解,更為深入推進“小大之辨”之研究,表現在:
其一,擇“小大之辨”三種價值取向其中一種予以辯護,如有學者持抑小揚大說,而批評向郭適性逍遙說乃曲解莊子原意,
亦有學者持支遁之說,而批向郭逍遙說,
整體而言,此一研究路向未關注到《逍遙游》《齊物論》間的思想“矛盾”,不免落于舊時注疏之窠臼;其二,聯系《齊物論》,試圖緩和《逍遙游》之“小大不齊”與《齊物論》之“小大齊同”間的張力,有學者將“小大之辨”聯系“物道”關系做解,
有學者從《逍遙游》《齊物論》二者主體的不同來試圖解決這一矛盾,
整體而言,此一研究路徑雖稍緩和《逍遙游》《齊物論》二篇之思想“矛盾”,但未能注意到《逍遙游》《齊物論》之“小大之辨”各有其不同的思想意旨;其三,試圖通過重新厘清“小大”之內涵,并以外境與內智的新角度析辨外境之小大與內智之小大間所存的辯證邏輯關系,有學者指出外境對心智有重要影響,
有學者進一步將之明確為“正向關聯關系”,
然此種論述更側重于從主體生就的規定性與能力范圍兩方面進行分析,多忽視了“心”在此關系中的關鍵意義。
基于此,本文在“小大之辨”外在物性與內在心境之兩層分殊的基礎上,試圖以“小大”間靜態橫向(心之可大,性小而心大)與動態縱向(心之可齊,大心而齊物)的兩種關系模式,給予“小大之辨”以新的詮釋框架,揭示其“大其心”之理論意旨與具體的修養路徑。
一、心之可大,性小而心大
要探析“小大之辨”之哲學意旨,需先厘清其字面意涵,“小大之辨”語出《逍遙游》:
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為鯤。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云,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云氣,負青天,然后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本文系統的闡述了青海柴達木盆地周緣殘山地球化學景觀區地形、地貌、水系發育程度;水系沉積物、土壤、鈣積層和風成物的分布特點;風成物和鈣積層的分布對水系沉積物樣品的干擾程度等。通過采樣對比分析,認為排除干擾最有效的辦法是剔除表層干擾物,直接采集基巖風化的巖屑物質代替水系沉積物。在野外采樣過程中應用水系沉積物采樣有效控制匯水域的思想,用放射的樹枝狀結構多點組合、主副點結合的化探采樣方法,盡可能的提高每個樣品的有效性和代表性,野外采用化探采樣航跡監控系統對主副點進行監控,確保采樣到位率,使得所采集的巖屑組合樣能有效代替控制匯水域范圍內下伏基巖的化學成份,保證獲得質量可靠的第一手資料。
因而,縱向“小大”間存在“心之可齊,大心而齊”的動態過程:萬物之外在物性本不齊,不必要齊,亦無法可齊;而萬物之內在心境則不然,任一主體在縱向時間維度都有大心之可能;且《莊子》在內在心境上亦持有“抑小揚大”之價值取向,心可大亦需大。就行為主體之心由小而大之可能性與必要性而言,萬物是一致的,是為“心之可齊,大心而齊物”。由此而言,可通過“大其心”而齊同不齊之萬物,“小大之辨”旨歸就是“大其心”。
戴菲兒死去那天,秦川陪她整整一夜。死去的戴菲兒靜靜地躺在靈柩里,她形銷骨立,全然沒有一點動人模樣。然后來了殯儀車,然后有人將靈柩抬上殯儀車,再然后,殯儀車離開豪宅,消失在山林之中。艾莉問秦川,你不去看看?秦川說,你認為將一個女人扔進報廢機很好看嗎?艾莉說,可是他們……秦川說,他們都是演員。靈柩和殯儀車,只是演出的道具。
而“小大”為相對性概念,是對事物具象之形體、抽象之價值等各方面的形容,有豐富的能指性。
由具體的小鳥大鵬推及萬物,
不同的小大之物在“性—境—心”方面,體現出不同的特質(不齊);但不齊之萬物在“性—境—心”的關系上,由性而境,由境而心,又具有相同的“正相關、非因果”關系,該關系中前者的變化會影響后者,但不必然決定后者,“心”不必然受“性”之限定,無論該物之“性”如何,其都有“大其心”之可能性。
一是完善征收征用集體土地的補償標準。我國《土地管理法》第47條和《物權法》第42條規定的土地補償標準主要依據被征收土地的原有用途,對土地被征收后的用途和收益缺乏考慮。為保障農業領域PPP穩定發展,應當建立征收征用農村集體土地的補償標準與被征收土地的市場價值掛鉤的制度,以兼顧國家、集體、個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
其一,大能而大境。行為主體可通過能力的提升而前往更大的環境,如鯤之化鵬,鯤本義為魚子,表明鯤本身就有成長的潛能,只要其將這一潛能擴充即可,其化而為鵬,就有飛至九萬里之能,前往更大的南冥。但能力之提升終歸有限,如蜩鳩,其潛能本就不具備成為鵬的特質,無論其怎樣努力,都無法在形體上成為似鵬般的大物,無法依憑自己的能力飛往南冥。而根據《逍遙游》“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等表述,莊子并未就二蟲之能進行評價,二蟲受限之因在“知”,而“惟知能變化”,
故欲大其境,關鍵在“大其知”。
綜上所述,本文將萬物橫向對比,發現萬物雖然在“性—境—心”方面各不相同(不齊),但其在“性—境—心”方面皆存在“正相關、非因果”關系,此關系之意義在于揭示“心之可大,性小而心大”之理。也即于萬物而言,其先天之“性”(外在物性)的小大會影響其所處之“境”(外在環境)的小大,而所處之“境”的小大又會影響其“心”(心胸、心境)之小大,但這只是正相關的影響關系,而非必然決定性關系,萬物之“心”不必然受先天之“性”的束縛,大性者易至大境,易有大心,亦有心小之可能;性小者會局限于小境、小心,但亦有心大之潛力,心之可大,性小而心大。
同理,“小性—小境—小心”的正相關關系亦可成立,形小易境小,境小易心小。蜩鳩微尺之軀,無論如何都無法依靠自己的力量企及九萬里高空,形小導致其能小,“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進一步,導致境小,之二蟲只能“翱翔蓬蒿之間”。境小而知小,生活空間的逼仄限制了其眼界見識:首先,二蟲所知之物有限,它們不知蓬蒿之外還有南冥的存在;其次,它們志向有限,提出“彼且奚適”的疑問,無法理解大鵬的圖南之舉。而知小則易致心小,《逍遙游》中蜩鳩、斥鴳的出場,都帶著對大鵬的嘲笑,“笑之曰”體現了其心境之小,正所謂“蜩、鳩,蓋井蛙、醯雞之徒,不知世界有如許之大者,故其見若此,只緣胸中原無所積”。
故蜩鳩之心小關鍵在于其不自知其小,在于它們自以為是地對外物的哂笑與鄙夷。由此可知,“小性—小境—小能”的正相關關系亦成立,小性者因先天小形、小能的限制而生活于小境,逼仄的環境又限制了其眼界見識,從而容易造成其不能理解、包容他物的狹小心境。
但此非絕對必然的因果關系,形小、性小者亦可心大。同屬小物之“鷦鷯”,其形小、能小、所處之境小,“鷦鷯巢于深林,不過一枝”,但這并不妨礙鷦鷯之知大,它并不覬覦整片森林,安于自己基礎需求的滿足。而這種對自己本然生活知足的狀態,鷦鷯與蜩鳩相同,“各取足而自勝”,
不同的是鷦鷯并未將自己的生活視為最優而貶低他者,蜩鳩則更多地是自傲,充滿了對大鵬圖南的不屑。故鷦鷯所知之大,在于其懂得知足,更在于其懂得對他者生活的尊重,體現出自適、自足、自得的心境之大。
再如莊周所夢之蝴蝶,其形小而能大。自然界中,蝴蝶對外物的依賴較少,吸風飲露便可存活,因而其受到的外在制約就少,故其可成為莊子所求之自由逍遙境界的代表。
由蝴蝶之“小形—大能”,或鷦鷯之“小形—小境—大知—大心”可知,性小者不必然會受“小”之限制,亦可有大能、大知、大心。
本文以紹興一些著名旅游景點為例,探討了功能翻譯理論對景觀名稱和景觀介紹翻譯的指導作用。正如Venuti所主張的,“翻譯是在不同語言、不同文化中尋找共同的過程。”這一過程要求譯者不拘泥于任何一種方式,而要采取各種策略,其最終目的是要使交際目的得以實現。
因而,形大之鯤鵬,能大之帝堯、宋榮子,形小之蜩鳩、井蛙、醯雞、蝴蝶,知大之鷦鷯、鼴鼠等,其先天規定之形體、能力差異萬千,展現出萬物“性之不齊”的特點。而不齊之萬物,在“性—境—心”方面,又有同樣的“正相關、非因果”關系,即先天之形體、能力會影響行為主體的眼界、智識,進一步影響其所處環境,從而塑造其心境。但這只是一種正向影響關系,而非必然決定關系,性大者亦會心小,性小者亦可心大。
然上述關系并非必然的因果關系,性大者不必然心大。如“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的宋榮子,其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較于世俗之人,此乃大能大性之體現,但他仍“猶有未樹也”,因他“猶然笑之”,以大笑小,展現出一副自傲自夸者面容,“猶有內外、寵辱之見存,未能超然樹立,空所依傍也”。
而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尚書·堯典》),乃大能、大性之代表,其讓天下于許由,“雖能忘功,而未忘讓之之名”,
心中仍有掛礙。可見,如帝堯、宋榮子一般的大能、大性之人,亦會滯于小知,追求“名尸,謀府,事任,知主”(《應帝王》)。故大能、大性者,不一定會有大知、大心,“性—境—心”的關系中,前者只是后者的正向條件,而非決定因素,大性者并不必然能至大境,更不必然會有大心。
二、心之可齊,大心而齊物
另一方面,通過“虛其心”而行“負的工夫”,虛心而大心。莊子亦繼承老子之“虛心”說,認為“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人間世》),“虛室”才能“生白”,空明之心才能朗現生命本然之清澈空闊。
而具體所虛之對象,即行為主體對“名、功、己”的執著。
根據上文“性—境—心”間的“正相關、非因果”關系,“心之不齊”受“性之不齊”的影響,故首先需探索該以何種態度面對萬物性之不齊。莊子肯定萬物在客觀物性方面之不齊,并要破除對于不齊之物性的執著與追求,因為外在物性本就無法齊同,并不存在一個絕對的評價體系使外在物性統一,“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駢姆》)。長短高低,美丑胖瘦等等外在形體的小大概念,皆非莊子討論重點,這明顯地體現在其對“鯤”的處理中:“鯤”的本義是魚子,
乃至小之物,莊子卻用之來表述“不知其幾千里”的至大之物,如此對于常識的打破,本身就奠定了莊子于“小大之辨”的態度基調,即認為外在物性種種差別之模糊與不重要。況且“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者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駢拇》),以鉤繩規矩或繩索膠漆為標準要求萬物,是對萬物本然之性的扭曲,是削性侵德之舉。故外在物性不必要齊,亦無法可齊。
在“性不可齊”的角度,向秀、郭象提出“適性”而齊說:“茍足于其性,則雖大鵬無以自貴于小鳥,小鳥無羨于天池,而榮愿有余矣。故小大雖殊,逍遙一也。”
其認為小大間有天壤之別,但只要二者安于先天規定性,不逾越性分之界限,皆可至逍遙之境。但問題在于,蜩鳩之小的關鍵并不是其在物性領域的小形、小能,而在于其不自知其小,在于其以自己的生活經驗為準則,認為自己的“蓬蒿之間”便已然是“飛之至也”,從而嘲笑大鵬的圖南之舉。向郭未看到“心”之域的“小大之別”,在此意義上消解了心境領域的“小大之辨”。故本文認為當將重點放在“心”上,“大心”而齊。
一方面,莊子在“心”之領域抑小揚大。首先,《莊子》多次出現對“心大者”的肯定與對“心小者”的諷刺——《逍遙游》中,當蜩鳩笑鵬時,莊子言“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表達其對蜩鳩心智的否定;當眾人皆欲比壽于彭祖時,他以“不亦悲乎”表達對于眾人求壽之心的悲憫;當惠子以有用之眼光看待“大瓠之種”時,莊子言“夫子固拙于用大矣”,“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逍遙游》),表達對心中負累過多的惠子的同情——都表明“大心”之主題。其次,莊子對“心之小大”有具體描述:他推崇“以明之心、葆光之心”(《齊物論》),反對“有蓬之心”,認為行為主體當摒棄以自己為價值中心的“成心”,
正是出于自我利益的成心導致了種種是非的價值評判,如此之成心,乃知見之窠臼、心境之桎梏。正如蜩鳩囿于一孔之見而笑圖南之鵬一樣,他們為成心所縛而無法體會大鵬的逍遙之樂。因而,莊子反對“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以自我為中心去度量天下的“小心”,而推崇“以明、葆光”的“大心”。可知莊子在心境方面抑小揚大,不同主體都可追求心智與心境的擴大。
4.應與城鎮、工業區及港區規劃相協調,使之成為一個統一和諧的整體,做到有利生產、方便生活;有利擴建,方便施工。
另一方面,“大其心”有其可能性,任何主體之心皆可由小至大。如《應帝王》之列子:起初,列子拘泥于形體功名,見到能“知人之生死存亡,禍福壽夭”的季咸便“心醉”,而在壺子與季咸虛以委蛇后,他便明白外在身形并非修行根本,內心之澄明通透才是。于是“于事無與親,雕琢復樸,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在紛繁復雜的環境中抱守專一之道而不被干擾,終身如此,心境由小而大,最后“同于大通”。再如《秋水》中的河伯,未見大海時“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自囿于所知,心靈未可容納他物,“正是自我中心主義者心境的寫照”,
此處之河伯,欣然自喜之貌與《逍遙游》洋洋得意之蜩鳩相同。而在見到“不見水端”的北海后,他望洋興嘆,“吾非至于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于大方之家”,羞愧于自己之前的傲慢自大。由洋洋自得到望洋興嘆,河伯亦體現心境由小而大之可能,故“大其心”有其可能性。
就“小大之辨”字面含義而言,“小”即斥鴳,“大”即鯤鵬,“辨”即分別,“小大之辨”也即斥鴳與鯤鵬間的分別,“鯤鵬之圖南,斥鴳笑之;斥鴳之騰躍,自以為足矣,此小大之不同也,故曰此小大之辯也”,
小大之不同即小大之辨。此文本中,小大間的不同直觀體現在“性—境—心”三方面:“性”指行為主體之種種先天規定性,“性者,生之質也”(《庚桑楚》),“性”乃生就的本質特征,含括形體、能力等先天規定的部分,本文所指之性乃性、貌、能等外在物性,如斥鴳形體之小與鯤鵬形體之大,斥鴳飛翔之能小與大鵬飛翔之能大;“境”指小大之物所處的外在環境,如斥鴳所處的蓬蒿之間與大鵬所處的青天之上;“心”在中國哲學中有多種含義指向,
本文所指之“心”,乃行為主體的心胸、心境之精神主宰。“此篇極意形容出個致廣大的道理,令人展拓胸次,空諸所有,一切不為世故所累,然后可進于道”,
可見“心胸之心”于本篇之重要,故本文著重分析心之“心胸、心境”意。
三、由大境、虛心,而大心
如上所述,通過橫縱兩個維度對《莊子》“小大”之物進行分析可知:“小大”間的橫向關系是對空間上同時并存之物的既定形態進行比較,側重于不同主體間的靜態對比,“心之可大,性小而心大”,萬物在“性—境—心”上不齊,存在種種差異,但其共同遵循的“正相關、非因果”關系,表明“心”不必然受“性”之限制,如此可打破不齊之“性”對“心”的束縛,同時大性可為“大心”提供基礎;“小大”間的縱向關系強調單個事物與過去或未來某個時間的狀態進行比較,側重于同一主體內的動態發展,“心之可齊,大心而齊物”,外在物性無法可齊,所齊在心,任何主體之心皆有擴大之必要與可能,故“小大”橫縱維度都落于“大其心”,“小大之辨”之旨歸就是“大其心”。
“那些在小大之辯中主張‘小不及大’的《莊子》闡釋者,無不將‘大’引向大其心智”,
但亦多停留于此,未能闡明具體工夫路徑,而究竟如何“大其心”,則是本文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除了天成控股業績預告與實際不符外,海南椰島(600238.SH)、嘉應制藥(002198.SZ)和迪威訊(300167.SZ),都曾發布過 2017年度經審計業績與業績快報存在重大差異暨致歉公告。上交所對海南椰島及責任人予以公開譴責,嘉應制藥及公司當事人收到廣東證監局警示函,迪威訊時任財務總監收到深交所創業板公司部監管函。
大性可至大境,大境可獲大心。鯤鵬之“性大”表現為其“形大”,而其大形又為其大能奠基,鵬“怒而飛”便可“絕云氣,負青天”,有高飛之能。而大形、大能一方面要求其活動于宏闊之大境,“直以大物必自生于大處”;
另一方面也使大物更易追求大境,如鵬“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地去往南冥。進一步,大境為大心提供可能,鵬面對蜩鳩之嘲笑,以沉默待之,“若鵬必不輕易笑人”,
不以二蟲之笑為意,這與二蟲將自己的“蓬蒿之間”視為“飛之至”的傲慢形成對比。故而有容乃大,對萬物的包容之心才是大鵬逍遙之因,若鵬亦笑乎二蟲,那其絕非“逍遙”之象征,“小者笑大,大者悲小,皆未適于逍遙者也。”
對大鵬意象之分析,可得出“大性—大境—大心”這樣的正相關關系,在此關系鏈條中,前者有更大的概率影響后者,大性者可至大境,大境處可獲大心。
一方面,通過“大其境”而行“正的工夫”,大境而大心。根據小大間“性—境—心”之正相關、非因果的辯證關系,可知“大其境”可為“大其心”提供條件。
二個月以后,也就是蔣利學把假牙從我的氣管中取出后的某一天,我還躺在哈爾濱市第一醫院呼吸科的病床上,我曾這樣想,蔣利學或許就是為我而生的。不然,為什么身處兩地我們會以這樣一種戲劇性的方式相識?現在想來,似乎他大我十幾歲也是上天有意安排的,讓他早我十幾年來到這個世界,學好醫術,在哈爾濱市第一醫院等著我。
其二,大知而大境。于能力有限之主體,更重要的是擴大見識,知道世界除了自己的一方天地外,還有更宏大的“六合之外”。蜩鳩二蟲之見小,以為自己的“蓬蒿之間”便是飛之至,自然無法突破自己的飛行局限、提升能力,更無法理解大鵬的圖南之行。《秋水》中河伯起初亦同蜩鳩般“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但其“出于崖涘,觀于大海”,見到北海則明曉自己之淺薄,如此方“可與語大理矣”,有了更大的見識,才能明白自己確切的位置,更好地認識自我,從而擴大心境,故而見識之知的增加可讓能小之物看到自我之外的更多可能性,從而為心境的擴大提供基礎。
因而,行為主體既可通過提升能力而擴大所處之境,亦可通過擴大見識之知而看到更大的世界與更多的可能,從而為“大其心”提供條件。而根據前述之“性—境—心”的正相關、非因果關系,“大其境”可為“大其心”提供正向條件。而除此間接方式外,還可直接對心進行涵養。
由上可知,“小大之辨”字面含義即“小大有別”“小大不齊”,而行為主體該以何種態度對待此不齊,則是縱向分析要解決的問題。萬物之“心”不必然受“性”之限定,皆有由小至大的可能性,就此動態發展的可能性而言,我們可齊同不齊之萬物,是為“心之可齊,大心而齊物”。
其一,無名。“名者,實之賓也”(《逍遙游》),相較于生命本身而言,外在之名不過是他人所貼標簽,“名不出于我而出于人,則是在外者也”。
若為求虛名而內喪己身,便是“以身殉名”,如《人間世》所論述的關龍逢與比干,“皆修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最終“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因其好修名之心而陷之”,
為名喪身。與之相反,便是不受天下之許由、莊子等人,超越世俗名利之捆綁,明晰生命之本質,不為外在虛名而動心,才能體會到“出游從容”的魚之樂,擁有閑適安逸之心境。
其二,無功。為功之根本在于行為主體對于圣王之治的固執,其目的在于以一己之標準匡扶天下,而非順應大化之自然發展。《在宥》言:“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莊子明確反對圣王以自己的標準管理天下,人為的功業,反而是對萬物自然本性的戕害。“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游于無有者也”(《應帝王》)。真正的“明王”,不是兢兢業業的“向疾強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倦”之人(《應帝王》),而是順其自然,不干預萬物發展之人,是“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逍遙游》),不以功業為目標之人。如此,萬物生長而不知所主,物自治而民自化。
This research is conducted on the basis of Qingdao harbor, Dong Jiakou port, bulk grain project. on the basis of this situation, to do this research on conveyor head or tail frame′s forces as follow shown in Figure 1.
其三,無己。較于無功無名而言,無己更為根本。逐于功名之根本在貴己,而“世人不得如此逍遙者,只被一個‘我’字拘礙,故凡有所作,只為自己一身上求功求名。”
對功名的追求根本而言是對自我的在意,“無功無名”是不想讓自己為功名所縛,從而“全己”,故其根本還是以己為主,“至人無己”才是最高層次。
“無己”與慎到之“棄知去己”不同,“去己”強調完全舍去生命的自主性,失去視聽食息,如草木等“無知之物”般“于物無擇,與之俱往”(《天下》);而“無己”是跳出以自我為標準的自我中心主義,是看到萬物本然的存在與價值,從而理解他者的境界。
蜩鳩正是蔽于我見,以自己所處的蓬蒿之間為萬物“飛之至”,以己度人,不理解大鵬的圖南之志。“無己,故順物,順物而至矣。”
在超越了對于自我價值的高舉后,便能從世俗狹小的眼界中跳躍出來,觀照到他物存在的本然價值,也即“心靈無窮地開放,與外物相冥合。如此,則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能隨遇而安,自由自在。”
正因無己,面對世俗中無所可用的“五石之瓠”,莊子能去除實用主義的視角,順應其“大”,“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體會生命之閑適;同樣,面對“大而無用”的大樗樹,他亦徹底拋卻世俗實用主義的價值論,“樹之于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逍遙游》),真正體會生命原本的通透與自主。
綜上所述,“小大之辨”之理論意旨在于“大其心”,就具體的修養路徑而言:一方面,行為主體可以通過“大其能、大其知”而“大其境”,從而為“大其心”間接地創造正向條件;另一方面,行為主體亦可通過對“名、功、己”做“負”的工夫,去除冗雜之負累,讓心由虛而大,最終達至“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齊物論》),“獨與天地精神往來”(《天下》)之境。
四、結語
莊學史上,向秀、郭象的“小大同揚”說、支遁的“小大同抑”說影響深遠,自晉之后創見甚少,經宋代王雱“易解小大”與林希逸“樂解小大”后,“小大之辨”之“大其心”理論意旨于明清時期才開始被各注家大力宣揚,
近現代仍有激烈討論,但“大其心”之意旨少被提及。本文回應《逍遙游》《齊物論》間之思想“矛盾”,通過對“小大之辨”兩層分殊(外在物性與內在心境)、兩種關系(橫縱)的分析,知“小大之辨”旨歸“大其心”,重新闡明“心”在此問題中的關鍵意義,并闡明具體的修養路徑。
新媒體閱讀依托互聯網平臺快速發展,越來越顯示出其強大的市場,也越開越成為當代大學生在閱讀時喜歡的對象。誠然,新媒體閱讀時代沖擊了傳統紙質書籍在傳播知識、文化的地位。但是,這是當今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面對這個新舊交替、機遇與挑戰并存的閱讀時代。我們要善于抓住機遇,利用好新媒體閱讀平臺的優勢,充分開發新技術應用,猶如為圖書館閱讀推廣插上雙翼,也為大學生的思想認識提高的廣泛提供一種新型平臺。
“小大”間的橫向關系體現了不同主體間的靜態比較關系:萬物在“性—境—心”上存在豐富差別;而在“性—境—心”間又存在“正相關、非因果”關系,“外在物性”之小大會影響“內在心境”之小大,但這種影響非必然的,萬物之“心”不必然受“性”之限制,物之性小亦可心大,故“心之可大,性小而心大”。“小大”間的縱向關系體現了同一主體的動態發展過程:不同主體之性與心皆不齊,性無法被齊,而心可以,且《莊子》在內在心境上持有“抑小揚大”之基本價值取向,故心可大亦需大,行為主體應將重點置于心之修養。任一主體之心皆存在由小至大的發展可能性,就此心之由小而大之可能性而言,萬物可齊,故“心之可齊,大心而齊物”。
因此,《莊子》“小大之辨”哲學之旨并非辨小大之物,亦非萬物在物性、價值上的小大之別,其思想更為根本的指向是其理論意旨——大其心:根據小大間“性—境—心”的橫向關系,主體可通過“大其能、大其知”而“大其境”,從而為大其心提供正向條件;根據“小大”間縱向關系,任一主體都可通過“無名、無功、無己”之負的修養直接涵養內心,虛心而大心,從而容納萬物,清揚生命,達至逍遙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