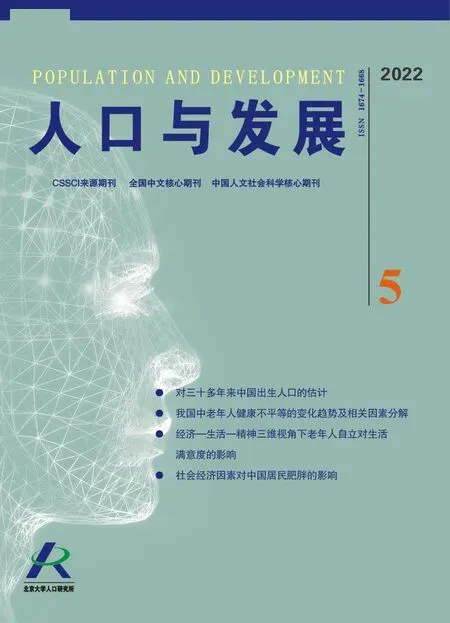我國中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變化趨勢及相關因素分解
劉瑞平,李建新
(1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 治安學院,北京 100038;2 北京大學 社會學系,北京 100871)
1 引言
健康不平等已成為全球所面臨的重要公共衛生問題(Gakidou et al.,2000;Siegrist & Marmot,2004)。促進健康平等化,緩解健康不公平既是當務之急,也是一項道德義務(Marmot et al.,2008)。大多數國家尤為關注那些處于健康劣勢的群體,并采取相關政策改善對他們健康不利的條件,力圖減少不同群體之間的健康差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的主要矛盾已經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穩定解決了14億人口的溫飽問題,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人們對公平、正義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當下人們在追求個體健康的同時,越來越關注健康公平,特別是隨著人口老齡化社會不斷加劇,中老年人的健康不平等成為重要議題,未來維護中老年人健康公平將越來越成為政府工作的重要議程。2021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加強新時代老齡工作的意見》,提出“堅持整合資源、協調發展,聚焦解決老年人健康養老最緊迫的問題,堅持保基本、促公平、提質量,確保人人享有基本養老服務和公共衛生服務”。加強我國中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相關研究,為篩查并干預處于健康最劣勢地位的中老年群體提供實證依據,這將有利于發揮政策在資源配置中的公平性功能,對推進實施健康中國和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具有重要的借鑒和參考價值。鑒于此,本文在對健康不平等概念進行梳理、對易混淆概念進行了區分和澄清的基礎上,重點討論以下三個研究問題:我國中老年人是否存在健康不平等現象?我國中老年人健康不平等有怎樣的變化趨勢(縮小抑或擴大)?影響我國中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因素有哪些?
2 文獻綜述
2.1 健康不平等的概念界定
目前學術界對健康不平等(Health Inequality)概念的界定和測量并沒有達成共識,經常與健康不公平(Health Inequity)混淆使用,但二者仍存在一定的差異。健康不公平是指“一些不必要、可避免的,并且被認為是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健康差異”(Whitehead,1992)。健康公平意味著在理想情況下,每個人都應該有公平的機會來實現其全部健康潛力,更確切地說,如果可以避免,任何人都不應在實現這一潛力時處于不利地位。健康不公平帶有較強的譴責、價值判斷和倫理的口吻和含義(Braveman,2003)。判斷健康差異是否公平的標準主要在于判別導致這種健康較差的結果是個人無法掌控的被迫選擇還是在個體主觀能動性下的自愿選擇(Le Grand,1991;Whitehead,1992)。
健康不平等的定義更為繁多,其內涵大致可以分為三種。第一種,僅是一個不帶有任何道德判斷色彩的描述性術語,它是指個人和群體間的健康結果差異、變異和差距的總稱(Woodward & Kawachi,2000;Gakidou et al.,2000)。也可以說是健康平等的剩余范疇,健康平等是指健康狀況平均分布在不同分析單位人群中,而健康不平等則是指除了健康平等分布的其他所有健康分布(Asada,2005)。第二種,用以特指由于社會弱勢地位所造成的、似乎可以避免的一種特殊類型的健康差異(主要受制度安排或政策等結構性因素的影響)。例如與處于有利地位的社會群體相比,窮人、女性或其他長期經歷社會不利或歧視的群體可能經歷更多的健康風險以及其健康惡化的速度更快(Braveman,2003;2006;2011)。健康不平等與健康不公平是密不可分的,健康不平等是衡量實現健康公平的重要指標,健康不平等的減少意味著健康朝著越來越公平的方向發展(Braveman,2014)。這一觀點下的健康不平等帶有價值判斷色彩,可以看作健康不公平的一個子集。第三種內涵更為直觀,是把社會決定因素導致的健康差距,尤其是社會地位形成的健康狀況分層,被看作真正意義上的健康不平等,又被稱為“健康的社會梯度”(Social Gradient in Health)和“地位綜合征”(Status Syndrome)(Marmot,2004;2005)。即使是吸煙、喝酒等這些具有理性選擇的生活方式所造成的健康差異,也是因為社會環境導致的人們無法掌控自己的生活,使個體最終做出不利于健康的選擇(Marmot,2015)。這種內涵下的健康不平等和健康不公平基本上是等價的。
健康不平等相關概念的爭議,限制了國家之間、國家內部、隨著時間變化的健康不平等的比較分析(Murray et al.,1999)。研究健康不平等的目的是采取干預措施使群體健康朝著公平性方向發展,而那些無法避免、無法干預的健康不平等影響因素,既難以測量,也難以改變,因此不應該把所有以變量分層下的健康差異都歸于健康不平等。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健康不平等的研究更應該側重于社會決定因素方面,尤其是研究那些與社會經濟地位相關的健康不平等才更有意義(Wagstaff et al.,1991)。通過梳理以往對健康不平等的認識,本文所研究的健康不平等,主要是指健康結果在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群體間的分布差異。
2.2 健康不平等的狀況及其相關因素
國外大量研究表明,不管是西方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健康水平的社會經濟地位差距普遍存在,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生活方式、社會保障等因素與健康不平等密切相關(Lantz et al.,2001;Huisman et al.,2003;Yiengprugsawan et al.,2007;Brinda et al.,2016;Gu et al.,2019;Fonta et al.,2020),其中教育和家庭資產等對健康不平等的貢獻率最高(Nedjat et al.,2012)。一些研究發現,健康不平等的程度在英國、瑞典、加拿大等一些西方發達國家呈現不斷加劇的趨勢(Kunst,2005;Hajizadeh,2016;Hu et al.,2016;Linder et al.,2018)。例如,瑞典人口中與收入相關的心理健康不平等現象較為嚴峻,在1994-2011年期間,無論心理健康的絕對不平等還是相對不平等都呈現顯著加劇趨勢,心理疾病越來越集中在受教育程度較低、女性、失業等處于不利地位的群體中(Linder et al.,2018)。
在對我國人口的健康不平等研究中也發現了相似結論,結果顯示,我國中老年人在自評健康(李艷麗等,2015;阮航清、陳功,2017;張志堅、苗艷青,2020;Wang & Yu,2016;Cai et al.,2017;Gu et al.,2019)、抑郁(Xu et al.,2016;趙曉航、阮航清,2019)以及包括日常生活能力、精神健康、認知功能的多維健康狀況(周鼒等,2018)等都存在親富人(或偏富人)的不平等現象,即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人群擁有更好的健康狀況,收入、教育、就業狀況、鍛煉等因素對健康不平等具有顯著的貢獻作用(趙曉航、阮航清,2019;顧海,2019;張志堅、苗艷青,2020;Xu et al.,2016;Gu et al.,2019)。有學者基于2010年之前的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數據,分析發現我國人口的平均收入成倍增長,但自評健康的不平等程度卻呈現不斷加劇趨勢(Wang & Yu,2016),日常活動能力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薛新東,2015)。從區域差異來看,農村地區的健康不平等程度高于城市地區,前者呈現不斷上升趨勢,而后者呈現波動下降趨勢(Cai et al.,2017)。有學者利用2002~2014年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數據分析發現,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和醫療制度的深入改革,雖然農村老年人仍存在有利于富人的健康不平等狀況,但健康不平等程度呈現下降趨勢(Pan et al.,2019)。
通過以上文獻梳理,可以發現,對健康不平等的研究重要關注于某一健康指標,較少對不同健康指標的結果進行比較;對我國健康不平等變化趨勢的研究結論具有矛盾性;涉及到我國中老年人的健康不平等研究相對較少。相比于當前中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相關文獻,本文可能的創新和貢獻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采用測量健康的4個指標,關注健康的客觀和主觀兩種屬性,并通過測量健康不平等的客觀方法,即集中指數,分析中老年人不同健康指標的不平等狀況及群體差異。第二,納入動態性視角,描述從2011年至2018年我國中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變動趨勢。第三,通過集中指數分解方法,深入探討影響中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相關因素。
3 數據與方法
3.1 數據來源
本文采用的數據來自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簡稱 “CHARLS”)。CHARLS是由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主持、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執行的大型長期追蹤調查項目。該調查于2011 年開展,采用分層多階段(縣/區-村/社區-家戶)抽樣方法,以縣區(包括城鎮和農村)作為初級抽樣單位(PSU),對45歲及以上中老年住戶人群進行調查。樣本覆蓋了不包括西藏在內的中國大陸28 個省150 個縣區的450 個村、居,調查應答率超過80%(農村地區94%,城鎮地區69%),樣本加權后的人口特征與2010年人口普查非常接近,說明該數據對中國中老年群體具有很好的代表性,該項目于2013、2015和2018年對基線樣本進行追蹤調查(趙耀輝等,2013;趙耀輝等,2019)。本文將基于四期截面數據,分析2011~2018年我國中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現狀及其變化趨勢,并對中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相關因素進行分解。
3.2 變量測量
3.2.1 因變量
本文的因變量健康有四個,分別是日常生活自理能力(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簡稱“ADL”)、工具型日常生活自理能力(Instrumental Activity of Daily Living,簡稱“IADL”)、健康自評和抑郁。ADL的測量包括6個指標,分別是穿衣、洗澡、吃飯、上下床、如廁、控制大小便,IADL的測量包括5個指標,分別為做家務、做飯、購物、吃藥、管理財務,這兩個量表的Cronbach’s Alpha都超高了0.8,表明其內部一致性較好。ADL和IADL的每個指標的問題選項分為“沒有困難”“有困難但仍可以完成”“有困難,需要幫助”和“無法完成”,如果有任意指標選擇后兩項(“有困難,需要幫助”和“無法完成”)即為ADL或IADL受損,編碼為1,前兩項為完好,編碼為0。ADL和IADL是反映了中老年人客觀身體功能的指標。
健康自評是一個被廣泛應用的主客觀綜合性健康測量指標,它是發病率和死亡率的有效和可靠的預測因素(Jylh?,2009),與某些疾病密切相關(Manor et al.,2003)。在CHARLS問卷中,健康自評分為“很好”“好”“一般”“不好”“很不好”5個等級。本文將其轉化為虛擬變量,把“很好”“好”和“一般”合并為自評健康狀況較好,賦值為0,把“不好”和“很不好”合并為自評健康狀況較差,賦值為1。
本文的最后一個因變量抑郁反映了中老年人主觀的心理健康狀況,CHARLS問卷對抑郁的測量使用的是流行病研究中心抑郁量表簡表(簡稱CES-D10)。CES-D10的10問題是詢問受訪者過去一周是否因一些小事而煩惱、做事很難集中精力、感到情緒低落、做任何事都很費勁、對未來充滿希望、感到害怕、睡眠不好、很愉快、很孤獨、無法繼續生活,其中有8個為消極陳述,2個為積極陳述,每個問題分為“很少或者根本沒有(<1天)”“不太多(1-2天)”“有時或者說有一半的時間(3-4天)”“大多數時間(4-7天)”四個選項。對于消極陳述,對應這四個選項分別賦值0、1、2、3,而積極陳述賦值與之相反,分別賦值3、2、1、0,最終抑郁分值區間為0~30,得分越高,表示抑郁程度越高。
3.2.2 自變量
根據以上對健康不平等相關因素的文獻梳理,本文的控制變量主要有四個方面:第一,基本人口特征,包括年齡、性別、婚姻;第二,社會經濟地位,包括戶口、受教育年限、家庭人均生活月消費、家庭固定資產(1)問卷中的問題是“您或您配偶是否有以下家用設備、耐用消費品和其他貴重物品”,選項汽車、電動自行車、摩托車等17項。;第三,生活方式和疾病,包括吸煙、喝酒、鍛煉、慢性病;第四,社會保障,包括養老保險和社會醫療保險。
3.3 健康不平等的測量與分解
3.3.1 集中指數
在各種測量健康不平等的指標中,集中指數(Concentration Index,“CI”)應用廣泛(Masseria et al.,2010),它是衡量與收入相關的健康不平等程度的一個相對指標,其結果允許跨國家、跨地區和跨時間的比較(Wagstaff et al.,1989)。集中指數是基于洛倫茲曲線和基尼系數而發展形成,洛倫茲曲線以圖示直觀地展示了人口中收入不平等的狀況,集中曲線與其類似,用x軸表示按收入或其他社會經濟地位指標排序的人口累積比例(從最窮到最富的人口),用y軸表示健康較差的累積比例(從最好到最差的人口),集中曲線則表示為x與y之間的關系,而集中指數被定義為集中曲線與完全平等線(對角線)之間面積的兩倍,其值范圍在-1至+1之間。集中曲線距離完全平等線越遠,社會經濟分配中的健康不平等程度越大,當集中曲線位于完全平等線上方,則集中指數為負值,表示健康狀況的分布有利于較富裕的個體,即偏/親富人的健康不平等;當集中曲線位于完全平等線下方,則集中指數為正值,表示健康狀況的分布有利于較貧窮的個體,即偏/親窮人的健康不平等;當集中曲線與完全平等線重合,則集中指數為0,表示健康狀況的分布的社會經濟梯度不存在(Wagstaff,et al.,2003)。集中指數的表達公式較多,最初的公式如下:
后來被經常應用的公式如下:
公式中C表示集中指數,yi是所研究的健康變量,μ是yi的均值,Ri表示第i個個體在社會經濟等級分布中的排序,第二個公式利用這個“方便的協方差”結果可以很容易地計算C,也直觀地表示集中指數是健康變量與根據社會經濟變量進行個人排序之間的關聯。Kakwani等人(1997)則建議使用相對等級上健康狀況的“便捷”回歸來計算集中指數,將以上公式以回歸方程定義如下:

相對于其他健康不平等的測量指標,集中指數具有較多的優勢,它能夠捕捉到最為關鍵的健康不平等的社會經濟梯度,通過集中曲線表示健康不平等的狀況,具有更為直觀的視覺效果,并且能夠進行時空比較分析(Wagstaff et al.,1991)。另外,在選擇社會經濟指標對個體進行排序時,無論是以消費還是以資產為基礎的財富指數來衡量健康不平等的差異性并不是很大(Wagstaff & Watanabe,2003)。本文為選擇合適的社會經濟地位指標排序,分別計算了以受教育年限、家庭人均月消費、家庭固定資產(家庭耐用消費品數量)進行排序的中老年人的健康不平等集中指數CI。通過結果比較,所有排序結果的CI都為負值,說明健康較差狀況主要集中在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中老年人,我國存在偏富人的中老年健康不平等現象,并且各個社會經濟地位指標計算的CI的趨勢也是一致。但以家庭固定資產排序的健康不平等測量基本都略高于受教育年限、家庭人均月消費,這說明以家庭固定資產作為社會經濟地位指標對我國中老年健康不平等測量結果更為敏感。鑒于此,對于我國中老年人健康集中指數的計算統一采用家庭固定資產作為排序變量。
3.3.2 集中指數的分解
為了解釋健康不平等的根源,Wagstaff等人(2003)將健康的集中指數表示為人口特征、社會經濟地位等各種因素的貢獻之和,以及未解釋的殘余成分。假設一個線性回歸模型把健康變量y與一組相關因素聯系起來,即:
上式中的α為截距,βk為系數,ε為殘差項。而對于y的集中指數被改寫為:



以上集中指數的分解方法適用于OLS回歸模型,但在健康領域研究中,健康狀況的測量很少是連續性變量,二分類變量(如健康或不健康)更常見。有學者使用Probit回歸代替線性回歸,處理因變量從0到1的離散變化(Doorslaer et al.,2004),其公式如下:

圖1 2011-2018年中老年總體的健康集中曲線變動趨勢注:以上結果已對個體層面的無應答進行了加權

表1 2011~2018年中老年人健康的集中指數(CI)
4 中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狀況及變動趨勢
下圖1的集中曲線和表1的集中指數展示了健康不平等的狀況及其變化趨勢。結果顯示,歷年的中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集中曲線都在對角線的上方,說明集中指數均為負值,健康較差的中老年人主要集中在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群體中,我國中老年人存在偏富人的健康不平等現象。歷年不同健康測量指標的不平等程度由高到低依次是ADL、IADL、健康自評和抑郁。由此可見,更為客觀的健康測量指標的不平等程度更大,而較為主觀的健康測量指標的不平等程度較小,其中抑郁不平等程度最小。本文使用Stata命令conindex(O’Donnell et al.,2016)計算2011~2018年的集中指數,并且檢驗不同時期截面數據的集中指數的差異性。結果表明,從2011年至2018年,我國中老年人的健康自評的社會經濟地位不平等雖然略有增加,但歷年的健康自評不平等狀況并沒有呈現顯著差異(P值為0.726)。中老年人的ADL和IADL的不平等狀況呈現波動加劇趨勢,并且歷年的健康不平等狀況都有顯著差異。比較健康自評、ADL和IADL健康測量指標不平等的加劇速度,ADL不平等的速度最快,年均增長率為6.66%,健康自評的速度最慢,年均增長率為0.83%。與其他健康指標的變動趨勢不同,中老年人的抑郁不平等程度呈現顯著地波動下降趨勢,其年均增長率為-2.61%,說明近些年來我國中老年人抑郁不平等狀況呈現緩解趨勢。
表2展示了2011~2018年中老年人的總體健康狀況以及按照家庭固定資產分組統計的健康狀況。從變動趨勢來看,從2011~2018年,健康自評較差的比例呈現先下降后上升的趨勢,整體上為波動下降的趨勢;ADL和IADL受損的比例呈現上升趨勢;抑郁得分平均值基本保持著穩定態勢。通過比較各健康指標測量中最窮組與最富組的健康較差比例的比值來看不平等程度,其中客觀健康指標,即ADL和IADL的不平等程度最大,并且這兩個群體差距增加速度也最快。2011年,最窮組的ADL受損和IADL受損比例分別是最富組的3.85倍和3.12倍;到2015年,二者差距分別增加到接近10倍和7倍;直到2018年,二者的差距雖有所縮減,但仍遠高于2011年差距,其比值分別為8.32和5.32。
分家庭固定資產組別來看,結果顯示,歷年調查樣本中的資產排序越高,中老年人健康自評較差、ADL受損、IADL受損的比例越低,抑郁得分越低,這說明,富裕組中老年人的健康狀況好于貧困組。從最窮組與最富組健康較差的比例的比值和抑郁平均值的比值來看,ADL的差距最大,接下來依次是IADL、健康自評和抑郁。從2011~2018年按資產排序的健康狀況的趨勢來看,最窮組健康自評較差、ADL受損、IADL受損的比例不斷增加,抑郁平均值呈現先下降后上升的趨勢,但總體上保持著基本穩定狀態。Q2組的健康自評較差的比例和抑郁平均值呈現先下降后略微上升趨勢,但總體上呈現波動下降的趨勢,該組的ADL和IADL受損的比例卻呈現先下降后上升趨勢,總體上呈現上升趨勢。Q3組健康自評較差、ADL受損的比例以及抑郁得分平均值呈現先下降后上升趨勢,其IADL受損比例呈現先上升后下降趨勢,但總體上該組的健康狀況呈現向好發展趨勢。Q4組的健康自評較差的比例呈現持續下降趨勢,其ADL受損的比例呈現先下降后上升的趨勢,但總體上呈現波動下降趨勢,其IADL受損的比例和抑郁平均得分呈現波動上升趨勢。最富組的健康自評較差和IADL的比例呈現先下降后上升的趨勢,其ADL受損的比例和抑郁得分平均值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總體上,該組的健康自評較差、ADL受損和IADL受損的比例呈現波動下降趨勢,但抑郁平均值呈現波動上升趨勢。

表2 2011~2018年按家庭固定資產分組的中老年人健康狀況
圖2清晰地展示了按家庭固定資產分組的中老年健康狀況的變化趨勢。可以看出,2011~2018年,僅有最窮組中老年人的健康自評較差的比例呈現上升趨勢,并且該組的ADL和IADL受損比例上升的速度最快,遠高于其他組人群;其他組健康自評較差的比例呈下降趨勢,其中最富組下降的速度最慢,Q2組下降的速度最快。Q3、Q4和最富組的中老年人ADL受損的比例都呈現下降趨勢,其中Q3組下降的速度最快,Q4組下降的速度最慢。只有Q3和最富組中老年人的IADL受損的比例呈現下降趨勢,其中,最富組人群其比例下降速度最快。從不同組的抑郁變化趨勢來看,最窮組基本保持著穩定不變的狀態,Q2和Q3組呈現改善趨勢,而Q4和最富組呈現惡化趨勢,其中最富組抑郁狀況變差的速度較快。整體比較各組健康變化趨勢來看,最窮組主客觀各個健康指標測量的狀況都沒有表現出向好發展的態勢,而最富組的綜合指標健康自評和更為客觀的ADL和IADL的狀況都表現出向好發展的態勢,但抑郁呈現惡化的趨勢。

圖2 2011-2018年按家庭固定資產分組的中老年健康較差的年均增長率 注:以上結果已對個體層面的無應答進行了加權
5 中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相關因素分解
為了進一步分析相關因素對健康不平等的貢獻狀況,本文對2018年中老年人各個健康指標(包括ADL、IADL、健康自評和抑郁)的集中指數進行了分解。如下表3所示,從中老年人ADL集中指數分解的結果來看,在人口基本特征方面,僅有年齡平方對中老年人ADL有顯著影響,其對ADL不平等的貢獻率約為13%。在社會經濟地位方面,受教育年限和家庭固定資產對中老年人的ADL具有顯著的影響作用,分別增加了ADL不平等的3.8%和29%,而戶口、家庭人均消費對其的影響作用都沒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平。生活方式和慢性病對中老年人ADL都存在顯著的影響作用,相對于吸煙、不喝酒、不鍛煉和有慢性病的中老年人,不吸煙、喝酒、鍛煉、沒有慢性病的中老年人的ADL狀況更好,其中日常鍛煉對ADL不平等的影響作用最強,其貢獻率約為11%。在社會保障方面,各個因素對中老年人的ADL的影響都沒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平。
從中老年人IADL集中指數的分解結果來看,在人口基本特征方面,年齡、性別對中老人的IADL都有顯著影響作用,年齡對其貢獻率要遠大于性別。在社會經濟地位方面,教育、家庭人均生活月消費、家庭固定資產對中老年人的IADL具有顯著的影響作用,它們對IADL不平等貢獻率分別為19.5%、2.9%、33.4%,受教育年限越長、家庭人均月消費越高、家庭固定資產越多的中老年人的IADL狀況越好。生活方式和慢性病對中老年人IADL都存在顯著的影響作用,但吸煙對其IADL集中指數的貢獻率極低,僅為0.13%,鍛煉對其IADL集中指數的貢獻率較高,約為9.4%,相對于吸煙、不喝酒、不鍛煉和患有慢性病的中老年人,不吸煙、喝酒、鍛煉、沒有慢性病的中老年人的IADL受損的可能性更低。在社會保障方面,養老保險對中老年人的IADL并沒有顯著的影響作用,但參與醫療保險中老年人的IADL受損狀況具有較大的差異性,相比于新農合,參與城鄉居民醫療保險和城鎮職工醫療保險的中老年人的IADL受損的可能性更低,其對IADL集中指數的貢獻率分別約為-0.22%、2.3%。值得注意的是,新農合、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和其他醫療保險制度都對中老年人IADL不平等具有加劇作用,但近些年來全國逐漸推行的城鎮居民醫療保險與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合并的統一城鄉居民醫療保險制度反而能夠有效地緩解中老年人IADL不平等,這說明我國醫療制度改革在減少健康不平等和促進公平性方面具有顯著成效。
從我國中老年人健康自評的不平等相關因素分解結果來看,從回歸系數可知,年齡與中老年人自評健康為較差的關系呈現倒“U”型曲線。在社會經濟地位方面,受教育年限越長、家庭固定資產越多的中老年人健康自評狀況越好,其中家庭固定資產對健康自評不平等的貢獻最大,其增加了約52.7%,教育使健康自評不平等增加了約16.5%。在生活方式和慢性病方面,喝酒、鍛煉和慢性病能夠顯著地增加了健康自評的不平等狀況,相比于不喝酒、不鍛煉、有慢性病的中老年人,喝酒、鍛煉和沒有慢性病的中老年人的健康自評狀況更好。在社會保障方面,養老保險對中老年人的健康自評的影響并沒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平,但養老保險對健康自評的不平等具有一定的緩解作用,其貢獻率約為-0.92%。醫療保險對健康自評的影響和其不平等貢獻的方向是不一致的,相比于參與新農合人群,參與城鄉居民醫療保險、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和其他醫療保險的中老年人的自我身體評估為好的可能性更高。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新農合,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和其他醫療保險顯著增加了中老年健康自評的不平等程度,而城鄉居民醫療保險對其不平等具有顯著的降低作用。

表3 中老年健康不平等的相關因素分解(N=17731)
從中老年人抑郁水平集中指數的分解結果來看,在人口基本特征方面,年齡、年齡平方、性別和婚姻狀況對中老人的抑郁程度都有顯著的影響作用,男性和有配偶的中老年人的抑郁水平較低,年齡與中老年人的抑郁水平呈現倒“U”型曲線,即首先隨著年齡的增加,中老年人的抑郁水平持續升高,達到高峰之后開始呈現不斷下降趨勢。結果顯示,總體上,年齡能夠有效地降低中老年人的抑郁不平等狀況,而性別和婚姻狀況對中老年人的抑郁不平等具有加劇作用,其貢獻率分別為2%和6.3%。在社會經濟地位方面,戶口、教育和家庭固定資產對中老年人抑郁水平產生顯著影響,它們都進一步拉大了中老年人的抑郁不平等程度,其貢獻率分別為3.4%、21.4%、46.9%,擁有非農業戶口、較長的受教育年限和較多的家庭固定資產的中老年人抑郁程度相對較低。生活方式各因素和慢性病都對中老年人抑郁不平等起到加劇作用,不吸煙、喝酒、加強鍛煉以及沒有慢性病能夠顯著降低中老年人的抑郁水平。在社會保障方面,雖然養老保險對中老年人抑郁水平并沒有顯著的影響作用,但從貢獻率方向來看,其對中老年抑郁不平等起到一定的緩解作用,貢獻率為-0.8%。參與醫療保險中老年人的抑郁程度具有較大的差異性,相比于新農合人群,參與城鄉居民醫療保險、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和其他醫療保險的中老年人抑郁程度更低,其對抑郁集中指數的貢獻率分別約為-0.3%、6.5%、1.2%,并且全國逐漸推行統一城鄉居民醫療保險制度能夠有效地緩解中老年人抑郁不平等程度,但所起到作用有限,遠低于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對中老年人抑郁不平等的加劇作用。
6 結論與討論
本文基于CHARLS2011年至2018年四期數據,分析了我國中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狀況及其變動趨勢,在此基礎上,對中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相關因素進行了分解,分析不同因素對中老年人各健康指標的影響及其對健康不平等的貢獻狀況。結果顯示,我國中老年人呈現偏富人的健康不平等現象,即健康較差的中老年人主要集中在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人群中,并且更為客觀的健康測量指標的不平等程度更大,而較為主觀的健康測量指標的不平等程度較小,其中歷年中老年人的ADL不平等程度最高,抑郁不平等程度最低。與以往對我國總體人群的研究結果不同(如薛新東,2015;Wang & Yu,2016),本文研究發現,對于不同的健康指標,中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趨勢并非一致。從2011~2018年的變化趨勢來看,我國中老年人的健康自評不平等呈現穩定趨勢,ADL、IADL不平等呈現不斷拉大的趨勢,其中ADL不平等的加劇速度最快,中老年人的抑郁不平等呈現縮小趨勢。總體而言,在客觀健康指標的方面,我國中老年人的健康不平等表現出一致的加劇趨勢,這與國外一些研究結論相似(如Kunst,2005;Hajizadeh,2016;Hu et al.,2016),但在主觀健康指標方面,我國中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不平等狀況呈現緩解趨勢。這種不同維度所反映的健康不平等變化趨勢的不一致,主要在于社會經濟地位內部群體的異質性。通過不同家庭固定資產來看中老年人的健康狀況的變化趨勢,結果顯示,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中老年人的ADL、IADL狀況表現出向好發展趨勢,其抑郁狀況則表現出惡化發展趨勢,但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中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變動趨勢正好與之相反。有學者基于與本文基本相同時間的不同數據(2011~2018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同樣發現中國成年人抑郁不平等呈現緩解趨勢,并推測原因可能是由于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人群受經濟放緩、城鎮化和人口遷移/流動的不利影響(Luo & Zhao,2021)。本文通過健康不平等的相關因素分解發現,我國近些年來的基本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系統的完善是健康不平等縮小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基本醫療保險全覆蓋的大力推進以及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改革。從生命歷程來看,中老年人的健康不平等是由長時期的資源優勢/劣勢累積作用形成的結果,當前一切有利于改善弱勢群體的生活處境、縮小社會經濟地位差距的社會制度優化和政策設計,對縮小中老年人客觀身體健康不平等的效果可能不如主觀心理健康理想。
通過比較各方面的相關因素對中老年人各個健康指標的不平等的貢獻方向和程度,研究發現,社會經濟地位成為健康不平等的首要因素,其在抑郁和健康自評不平等的占比更大,超過50%,而在ADL和IADL不平等的占比相對較小。從年齡的影響來看,衰老所帶來的身體健康惡化是無法避免的,但衰老并不一定帶來心理健康的惡化。結果顯示,年齡的增加使客觀指標健康ADL和IADL的狀況不斷惡化,但年齡與中老年人的抑郁水平的關系呈現倒“U”型曲線,這與以往研究發現相一致(趙曉航、阮航清,2019)。中年時期,面臨更多的生活壓力,心理狀況可能較差;到了老年,尤其是進入中高齡時期,年齡越大的老年人可能越成熟,心態越好,能夠很好地掌控自己的情緒。但年齡對中老年人健康自評并沒有起到顯著的影響作用。從年齡對中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貢獻率方向來看,年齡對ADL、IADL和健康自評不平等都起到擴大作用,但對抑郁不平等起到有效的緩解作用。是否吸煙、喝酒和鍛煉等生活方式對各健康指標不平等的程度都起到加劇作用,且對ADL和IADL不平等的貢獻要高于健康自評和抑郁。患有慢性病對中老年人的各個健康指標都產生不利影響,但相比于ADL和IADL,其對抑郁和健康自評不平等的貢獻率更大。這說明當前慢性病狀況既會對中老年人的客觀身體健康能力產生不利影響,也可能使他們產生消極和悲觀情緒,對晚年心理健康的發展更為不利。我國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推行對于促進健康公平做出了較大努力,并取得了明顯成效。本文結果顯示,除了IADL指標,社會保障制度對中老年人各健康指標不平等具有縮小作用。醫療保險對中老年人的健康不平等所起的作用具有差異性,其中逐漸推行的城鄉居民醫療保險對健康自評、IADL和抑郁不平等程度都起到了顯著地緩解作用,而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對其都具有加劇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僅是利用歷年截面數據,重點對我國中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變動趨勢進行描述性分析,并對其相關因素進行分解,但這并非是對中老年人健康不平等影響因素進行的因果推斷,因此本文主要的不足之處在于沒有對一些內生性問題進行處理。從時間性來看,反向因果關系可能多處存在,例如本文發現生活方式對中老年人的健康具有顯著影響,也可能是健康狀況迫使他們選擇當下的生活方式。因此,IADL和ADL受損可能會限制中老年人的積極鍛煉的良好生活方式,但并非不積極鍛煉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導致了他們不良的健康狀況。雖然分析過程依然存在內生性問題,并不會對本文的研究結論產生實質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