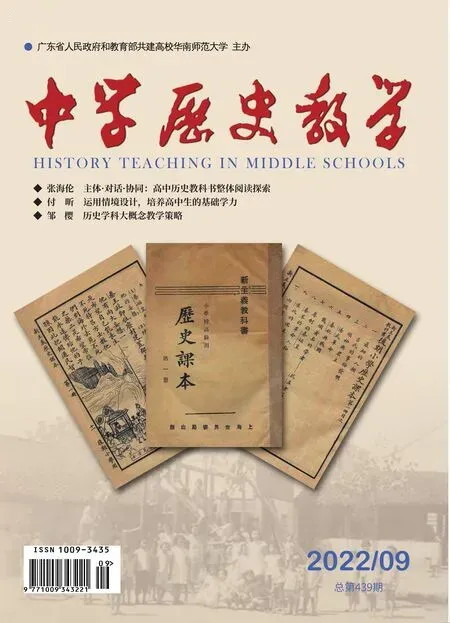量規(guī)的概念、分類與編制*
——兼與楊家平先生商榷
◎ 潘慶云 華南師范大學(xué)歷史文化學(xué)院2022 級課程與教學(xué)論碩士研究生
量規(guī)具有“評價標準公開透明”、“學(xué)生明確努力方向”、“便于學(xué)生自我評價”等優(yōu)點。中山市濠頭中學(xué)的楊家平老師在《馬扎諾教育目標新分類學(xué)視閾下的歷史學(xué)習(xí)目標量規(guī)運用》(刊于《中學(xué)歷史教學(xué)》2021年第12 期,以下簡稱:《量規(guī)運用》)中,借鑒了卡拉·摩爾、莉比·H.加斯特、羅伯特·J.馬扎諾等學(xué)者的研究成果,對表現(xiàn)量規(guī)的編制與使用等問題進行了探討。筆者閱讀后產(chǎn)生了如下兩個困惑。
首先,《量規(guī)運用》所呈現(xiàn)的“表現(xiàn)量規(guī)”能否稱為“量規(guī)”?馬扎諾指出:“‘量表’(scale)和‘量規(guī)’(rubric)兩個詞經(jīng)常互換使用,但是彼此之間存在很大的區(qū)別。量規(guī)往往用于一項特定的任務(wù),例如,教師可能設(shè)計一份量規(guī)以具體的書面提示來檢測學(xué)生的表現(xiàn);而量表更加普遍,用來描述在知識或技能掌握過程中的進展。”他傾向于將類似于《量規(guī)運用》所呈現(xiàn)的“學(xué)生生成型量規(guī)”稱為“scale”而非“rubric”。在馬扎諾編著的(中文譯名為《編制與使用學(xué)習(xí)目標和表現(xiàn)量規(guī):教師如何作出最佳教學(xué)決策》,下簡稱《編制與使用》)一書中,他使用的就是“scale”這一術(shù)語。
其次,關(guān)于“如何編制表現(xiàn)量規(guī)”,《量規(guī)運用》列舉了四個步驟,但論述不詳。如何確定目標的分類等級、確定目標的量規(guī)水平、整合基礎(chǔ)目標和復(fù)雜認知目標,進而編制出量規(guī)?這些步驟尚不明晰。
筆者將在下文呈現(xiàn)對上述兩個問題的思考,獻芹方家,以求教正。
一、量規(guī)的概念
要解答第一個困惑,需首先明確量規(guī)的概念。量規(guī)所對應(yīng)的英文單詞“rubric”在中世紀時是指用紅色書寫或印刷的關(guān)于禮拜儀式的行為準則,漸引申為“權(quán)威性的規(guī)則”。教育測量與評價專家后來將這一術(shù)語引介到教育領(lǐng)域,并對其賦予了特定的含義。很多學(xué)者都嘗試對“量規(guī)”這一概念進行界定,如:Heidi G.Andrade、Barbara M.Moskal、Craig A.Mertler、Judith Arter、Susan M.Brookhart、祝智庭、鐘志賢等。他們所作的定義本質(zhì)上無太大差別。量規(guī)是一種由評價者開發(fā)出的結(jié)構(gòu)化評價工具,用于評價學(xué)生的學(xué)習(xí)結(jié)果,促進和指導(dǎo)教學(xué)。量規(guī)常以二維表格的形式呈現(xiàn),一般有三個組成要素:評價維度、等級、質(zhì)量描述(如表1所示)。值得注意的是量規(guī)與等級量表(rating scales)這兩種評價工具的區(qū)別。等級量表與量規(guī)相比,最顯著的區(qū)別就在于缺少各等級的質(zhì)量描述。因此,從等級量表中所獲得的反饋信息只有各維度的等級結(jié)果。而量規(guī)既能反饋等級結(jié)果,又能提供促進學(xué)生學(xué)習(xí)的描述性信息。

表1 量規(guī)示例
根據(jù)上述定義,《量規(guī)運用》中的“表現(xiàn)量規(guī)”雖未明確標出“評價維度”“等級”“質(zhì)量描述”的字樣,但三個要素一應(yīng)俱全,是一個合乎定義的量規(guī)。馬扎諾“量規(guī)往往用于一項特定的任務(wù)”這一說法窄化了“量規(guī)”這一概念的外延。實際上,也有不少量規(guī)是可應(yīng)用于多項任務(wù)的,這種量規(guī)也被稱為通用量規(guī)或一般量規(guī)(general rubric)。
二、量規(guī)的分類
不同類型量規(guī)的編制方法會存在一定的差異。因而,在探討“如何編制量規(guī)”這一問題之前,需明確量規(guī)的分類。學(xué)界一般認為,根據(jù)量規(guī)適用范圍的不同,可將量規(guī)劃分為一般量規(guī)和具體任務(wù)量規(guī)(task-specific rubric)。“一般量規(guī)關(guān)注的是學(xué)生知識和技能的發(fā)展”,“指向整體學(xué)習(xí)成果而不是某一具體任務(wù)”,可以在給學(xué)生布置任務(wù)時公布,可以在同類任務(wù)中反復(fù)使用。而具體任務(wù)量規(guī)中各等級的質(zhì)量描述則“僅針對特定任務(wù)的具體內(nèi)容(如提供答案、詳述結(jié)論)”。關(guān)于一般量規(guī)與具體任務(wù)量規(guī)的區(qū)別,Judith Arter、Jay McTighe 曾舉例進行較詳細的說明,筆者對此不再展開贅述。
Susan M.Brookhart 將《量規(guī)運用》所呈現(xiàn)的這種“表現(xiàn)量規(guī)”稱為“水平量規(guī)”(proficiencybased rubric,為避免歧義,下文將這類量規(guī)統(tǒng)稱為:學(xué)業(yè)水平量規(guī))。Brookhart認為,學(xué)業(yè)水平量規(guī)是“一類特殊量規(guī)”,是“從標準的角度來記錄學(xué)生學(xué)業(yè)水平層級的”一般量規(guī)。所謂的“標準”,即課程標準,“反映了國家對學(xué)生學(xué)習(xí)成果的期望”,“是對學(xué)生在經(jīng)過一段時間的學(xué)習(xí)后應(yīng)該知道什么和能做什么(what students should know and be able to do)的界定和表述”。
《義務(wù)教育歷史課程標準(2022年版)》指出,“要制訂單元評價指標,從課程內(nèi)容、核心素養(yǎng)等維度來評價學(xué)生”,“單元評價主要運用紙筆測試和作業(yè)”。在進行作業(yè)評價時,“教師應(yīng)和學(xué)生一起設(shè)計可行的量規(guī)”,“對學(xué)生的作業(yè)進行公正、合理的評價”。這意味著歷史教師在開展學(xué)業(yè)評價前要進行整體的規(guī)劃和設(shè)計,除了設(shè)計具體任務(wù)量規(guī),還應(yīng)針對單元內(nèi)容以及要考查的核心素養(yǎng)側(cè)重點設(shè)計學(xué)業(yè)水平量規(guī),不僅關(guān)注學(xué)生在某項具體任務(wù)中的完成情況,更要著眼于學(xué)生在完成一個單元的學(xué)習(xí)后所達到的學(xué)業(yè)成就。
三、量規(guī)的編制
關(guān)于“量規(guī)編制方法”的研究成果頗豐。Nitko和Brookhart 總結(jié)出編制量規(guī)的兩種主要方法:自上而下法和自下而上法。但已有的研究對學(xué)業(yè)水平量規(guī)這類特殊量規(guī)的關(guān)注不多。《量規(guī)運用》借鑒卡拉·摩爾、莉比·H.加斯特、羅伯特·J.馬扎諾等學(xué)者的研究成果,以《馬克思主義誕生與傳播》為例,對“如何編制學(xué)業(yè)水平量規(guī)”這一問題進行了探討,無疑是有益的嘗試。
編制學(xué)業(yè)水平量規(guī)實質(zhì)上是一個將課程標準中的內(nèi)容標準和表現(xiàn)標準轉(zhuǎn)化為可測量的學(xué)習(xí)目標,并對學(xué)習(xí)目標進行分層分類的過程。然而,無論是《義務(wù)教育歷史課程標準(2022年版)》還是《普通高中歷史課程標準(2017年版2020年修訂)》都仍存在“行為動詞不明確”的缺陷。為彌補這一缺陷,我們可以借鑒教育目標分類學(xué)的研究成果。高凌飚認為,“相對于布魯姆、SOLO、安德森和其他分類理論,馬扎諾的分類理論是最新的理論,它借鑒了上述各類理論的優(yōu)點”,“在理論性和實踐可行性方面都達到一個新的高度”。即便如此,馬扎諾的相關(guān)研究成果也不宜原封不動地照搬至中國。為使其得到推廣,需做兩方面的工作:一是參照馬扎諾教育目標分類模型,確定我國歷史課程標準中認知行為的層次;二是優(yōu)化馬扎諾等學(xué)者所提出的量規(guī)編制步驟。
(一)確定認知行為的層次
如何在短時間內(nèi)確定一個學(xué)習(xí)目標的思維層次?如何依據(jù)課程標準,參照馬扎諾教育目標分類模型,快速編寫出具有不同思維層次的學(xué)習(xí)目標?這是兩個亟需破解的技術(shù)疑難。為方便未曾系統(tǒng)研習(xí)馬扎諾教育目標分類學(xué)的中學(xué)一線教師編制量規(guī),筆者初步探索出我國歷史課程標準中所涉及的認知行為動詞與馬扎諾教育目標分類模型認知系統(tǒng)中四個思維層次之間的對應(yīng)關(guān)系(如表2所示)。

表2 認知行為動詞及其思維層次
(二)優(yōu)化量規(guī)編制的步驟
《量規(guī)運用》指出,一個量規(guī)從無到有需要以下八個步驟:(1)鎖定課程標準中的陳述性知識與程序性知識、(2)細分鎖定的陳述性知識與程序性知識、(3)編制基礎(chǔ)目標、(4)編制復(fù)雜認知目標、(5)確定目標的分類等級、(6)確定目標的量規(guī)水平、(7)整合之前的基礎(chǔ)目標、(8)插入之前確定的復(fù)雜認知目標。其中前四步是基于課程標準設(shè)計學(xué)習(xí)目標,后四步是將編制好的學(xué)習(xí)目標按照目標的分類等級填入量規(guī)模板(表3)中。
筆者認為,這個編制步驟不盡合理。《編制與使用》一書指出,學(xué)習(xí)目標(learning targets)包括必達目標(learning goal targets)、基礎(chǔ)目標(foundational targets)、復(fù)雜認知目標(cognitively complex targets)三種類型;這三類學(xué)習(xí)目標是依據(jù)馬扎諾教育目標分類模型進行思維層次劃分的。必達目標直接來源于國家的課程標準,它描述學(xué)生在一個學(xué)年或一門課程結(jié)束時應(yīng)該知道什么和能做什么。而基礎(chǔ)目標則包含達成必達目標所需的基礎(chǔ)知識和基本過程,在思維層次上低于(不高于)必達目標;復(fù)雜認知目標則是在思維層次上高于(不低于)必達目標的學(xué)習(xí)目標。從邏輯上看,應(yīng)該先依據(jù)馬扎諾教育目標分類模型,確定必達目標的思維層次,再據(jù)此編制基礎(chǔ)目標和復(fù)雜認知目標。而《量規(guī)運用》中的編制步驟是先憑經(jīng)驗編制“基礎(chǔ)目標”和“復(fù)雜認知目標”,再參照馬扎諾教育目標分類模型確定所有學(xué)習(xí)目標的思維層次。因此,需對上述編制步驟進行優(yōu)化。
下以《馬克思主義誕生與傳播》為例,對優(yōu)化后的量規(guī)編制步驟予以介紹。
1.確定課程標準中涉及本課(單元)的陳述性知識與程序性知識。示例見《量規(guī)運用》。
2.將標準細分為若干個必達目標。示例見《量規(guī)運用》。
3.確定必達目標的分類等級。例:參照表3,“能簡述《共產(chǎn)黨宣言》的主要內(nèi)容”這一必達目標屬于“理解”層次;“能了解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探索”這一必達目標屬于“信息提取”層次;“能理解馬克思主義產(chǎn)生的世界意義”這一必達目標屬于“分析”層次。
4.編制基礎(chǔ)目標。示例見《量規(guī)運用》。
5.編制復(fù)雜認知目標。由于思維層次最高的必達目標已達到“分析”層次,復(fù)雜認知目標應(yīng)達到“知識應(yīng)用”層次。《〈普通高中歷史課程標準(2017年版)〉解讀》指出:“教師在教學(xué)中可引導(dǎo)學(xué)生進一步探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源和實踐意義,進一步深化對唯物史觀的理解。對高中生來說,德國古典哲學(xué)、英國古典政治經(jīng)濟學(xué)的內(nèi)容比較難理解,因此在教學(xué)上不作要求。”部編高中歷史教材在“學(xué)習(xí)拓展”也提供了一個任務(wù)“查找資料,進一步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xué)對德國古典哲學(xué)的繼承和超越”。因而,參照表3,可把復(fù)雜認知目標設(shè)定為“能結(jié)合材料論述馬克思主義哲學(xué)對德國古典哲學(xué)的繼承和超越”(“知識應(yīng)用”層次)。

表3 學(xué)業(yè)水平量規(guī)模板
6.確定目標的量規(guī)水平。將復(fù)雜認知目標記為4.0 級,將思維層次最高的必達目標記為3.0 級,將剩余的學(xué)習(xí)目標記為2.0 級。例:“能理解馬克思主義產(chǎn)生的世界意義”是思維層次最高的必達目標,將其標記為3.0 級。“能了解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探索”屬于思維層次較低的必達目標,將其標記為2.0 級。
7.將目標填入量規(guī)模板。在步驟6 的基礎(chǔ)上,將學(xué)習(xí)目標填入表3。
8.對量規(guī)進行修訂潤色。“對于許多學(xué)生來說,量規(guī)每個表現(xiàn)水平的目標可能都需要解釋,并轉(zhuǎn)化成學(xué)生易于理解的語言,才能使得學(xué)習(xí)過程更有意義。”對于包含“了解”、“知道”、“認識”、“理解”等行為動詞的學(xué)習(xí)目標,教師可以在不改變原意的基礎(chǔ)上,增添可作為目標達成證據(jù)的具體學(xué)習(xí)結(jié)果予以闡釋。示例:“學(xué)生能理解馬克思主義產(chǎn)生的世界意義(具體學(xué)習(xí)成果:學(xué)生能結(jié)合材料準確分析馬克思主義給世界帶來的積極影響)”。
量規(guī)的編制方法是多元的,沒有固定的模式。本研究提供的只是量規(guī)編制的一種方法,未必是最優(yōu)的方法。感興趣的同行還可嘗試以一個單元為例,借鑒布魯姆、SOLO 等分類理論編制學(xué)業(yè)水平量規(guī)。
[1]黃牧航:《高中歷史科學(xué)業(yè)評價體系研究》,長春:長春出版社,2011年,第53頁。
[2]羅伯特·J·馬扎諾著,盛群力等譯:《新教學(xué)藝術(shù)與科學(xué)》,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13頁。
[3][4][5][7]蘇珊·布魯克哈特著,杭秀、陳曉曦譯:《如何編制和使用量規(guī):面向形成性評估與評分》,寧波:寧波出版社,2020年,第11、8、10、68頁。
[6]Judith Arter,Jay McTighe 著,國家基礎(chǔ)教育課程改革“促進教師發(fā)展與學(xué)生成長的評價研究”項目組譯:《課堂教學(xué)評分規(guī)則》,北京:中國輕工業(yè)出版社,2005年,第25—29頁。
[8]崔允漷:《基于標準的學(xué)生學(xué)業(yè)成就評價》,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8年,第11頁。
[9][10]教育部:《義務(wù)教育歷史課程標準(2022年版)》,北京: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第62頁。
[11]馬扎諾、肯德爾著,高凌飚、吳有昌、蘇峻譯:《教育目標的新分類學(xué)》(第2 版),北京:教育科學(xué)出版社,2012年,第9頁。
[12]楊家平:《馬扎諾教育目標新分類學(xué)視閾下的歷史學(xué)習(xí)目標量規(guī)運用》,《中學(xué)歷史教學(xué)》2021年第12 期,第16頁。
[13]在管頤翻譯、肖龍海校對的《編制與使用學(xué)習(xí)目標和表現(xiàn)量規(guī):教師如何作出最佳教學(xué)決策》一書中,譯者將“l(fā)earning targets”和“l(fā)earning goal targets”都翻譯為學(xué)習(xí)目標,筆者認為這樣翻譯方式會造成概念的混淆。因而,筆者采用意譯的方式,將“l(fā)earning goal targets”譯為“必達目標”,對兩個概念以示區(qū)分。
[14]徐藍,朱漢國:《〈普通高中歷史課程標準(2017年版)〉解讀》,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109頁。
[15]教育部:《中外歷史綱要(下)》,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67頁。
[16]卡拉·摩爾、莉比·加斯特、羅伯特·馬扎諾著,管頤譯:《編制與使用學(xué)習(xí)目標和表現(xiàn)量規(guī):教師如何作出最佳教學(xué)決策》,鄭州:大象出版社,2018年,第6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