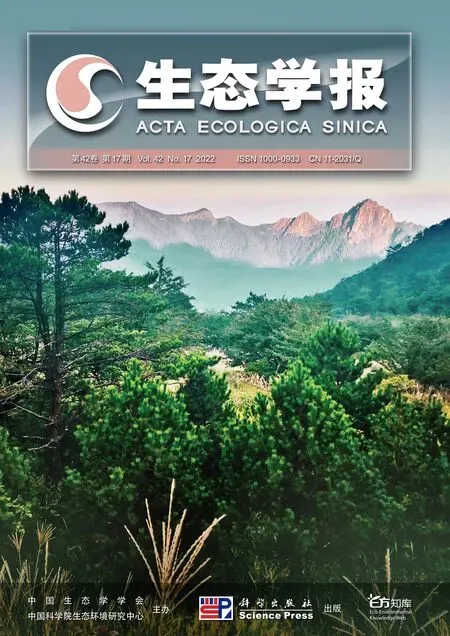城市化背景下小微濕地景觀動態變化及其驅動因素
袁 藝,周立志,*
1 安徽大學資源與環境工程學院, 合肥 230601 2 安徽大學濕地生態保護與修復安徽省重點實驗室, 合肥 230601
中國政府于2018年10月在濕地公約第十三屆締約方大會上提交《小微濕地保護與管理》決議草案并順利通過,小微濕地(Small wetland)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1]。小微濕地是指自然界在長期演變過程中形成的較穩定的一些小型、微型濕地,具有雨洪滯蓄、凈化水質、生物多樣性保護及景觀游憩等重要的生態功能[1—3]。目前國際上對小微濕地的面積還未有明確的界定,許多保護條例將面積小于8 hm2的濕地界定為小微濕地,具體包括小型湖泊、水庫、坑塘及寬度小于10 m、長度在5 km以內的小型河道、溝渠等自然和人工濕地[4—6]。國外對小微濕地的研究多集中于生境質量評估[7]、生物多樣性[8]、水文過程[9—10]等方面。國內的多數研究還處于介紹小微濕地的形成與發展和保護與管理的階段[2,6,11]。因此,對區域內小微濕地景觀結構特征和動態變化的了解和分析顯得緊迫而必要[12—14]。
與河流、湖泊等大型濕地相比,小微濕地作為能夠在城市中廣泛分布的濕地類型,能夠緩解土地資源緊張而帶來的區域生態資源本底不足和生態空間空缺的情況,滿足城市居民對多樣性親水空間的需求,同時為各類農業活動提供灌溉水源[11,15—16]。然而,小微濕地面積小,生態結構不穩定,城市快速發展導致小微濕地大量減少[17]。已有研究分析了城市化背景下小微濕地損失的程度,并確定了一些潛在的驅動因素,如城市化所帶來的建設用地和農業擴張、人口增加及交通用地變化等經濟社會因素,以及氣候、水文、地形等自然因素[12,18—21]。也有學者認為,小微濕地景觀動態變化的驅動力應該從自身景觀屬性的角度分析[22—26],如1926—1960年間,臺灣桃園地區小微濕地的損失主要是小微濕地形狀和大小等自身景觀結構的影響而非建成區面積、距河流距離等外部驅動力的作用[26]。
Logistic回歸、相關性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等模型是小微濕地景觀動態變化及驅動力分析的常用方法[18—19,27]。然而,分析一些可以預見到的因素與小微濕地景觀動態變化的相關性,包括對小微濕地損失影響的概率大小,缺乏實際研究意義。一方面,由于預測變量與響應變量之間的非線性關系使得小微濕地損失決定因素的評估變得復雜[12,21,26,28];另一方面,傳統全局回歸模型假定回歸參數在空間上是穩定不變的[29],而小微濕地損失本質上是在空間上發生的,其與預測變量的關系也不一定是固定的。有學者應用地理探測器對小微濕地景觀動態變化進行分析,解釋預測變量的空間異質性問題[30],然而,大多數學者忽略了將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本文應用增強回歸樹(Boosted Regression Tree, BRT)模型量化預測變量相對重要性,探索預測變量與小微濕地損失間的非線性關系[31],同時結合地理加權邏輯回歸(Geographically Weighted Logistic Regression, GWLR)模型分析預測變量的空間非平穩性特征[32]。
合肥作為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副中心城市,市內的包河區不僅經濟質量發展居全市前列,濕地資源也極為豐富,特別是小微濕地數量多、分布廣,各類小微濕地不僅為區域內農業提供灌溉功能,也形成了該地區特色的自然和人文景觀[30]。2006年以來,隨著以土地開發為導向的城市規劃和副中心城區濱湖新區的建設,包河區作為合肥市城鎮建設和人類活動最活躍的地區之一,土地利用方式發生較大變化,小微濕地景觀也發生較大改變。本文旨在了解城市發展背景下包河區小微濕地景觀動態變化,以及利用BRT和GWLR模型分析一系列預測變量對小微濕地損失的影響,以期為城市化地區小微濕地的保護與管理提供決策支持。
1 研究區概況
包河區位于合肥市主城區東南部,總面積約290 km2(其中巢湖水域面積約70 km2)。地勢較平坦,北高南低;屬北亞熱帶季風氣候,氣候溫和,年均氣溫約15.7 ℃;年際降水量變化較大,降水量以夏季較為集中,年降雨量近1000 mm。該區是合肥市四大主城區中濕地資源最豐富的城區,區內水系發達,南部緊鄰巢湖,有包河、南淝河、十五里河、塘西河、派河等多條河流和高王水庫、周崗水庫等水庫分布其中,形成了各類水庫相通,蓄排水和農田灌溉及其它用水系統相互連接的網絡。
根據《合肥市城市總體規劃(1995—2010年)》、《合肥市土地利用規劃(2006—2020年)》、《合肥市城市總體規劃(2011—2020年)》、《包河區濕地保護總體規劃(2018—2030年)》,結合城市發展情況以及小微濕地分布情況,將包河區除巢湖以外部分劃分為4個片區,分別為老城區、經濟開發區(以下簡稱經開區)、濱湖新區核心區、圩區(圖1)。

圖1 研究區域地理位置Fig.1 Location of study area
2 研究方法
2.1 數據來源及處理
遙感影像數據來源于美國地質調查局USGS平臺(https://earthexplorer.usgs.gov/),研究選取季相較為一致,質量較好,軌道號均為121 / 038的4期Landsat ETM+ / OLI影像(2006年6月20日、2010年6月15日、2014年6月10日、2018年7月31日)為基礎數據,空間分辨率均為30 m。經輻射定標、大氣校正、融合等操作,得到的影像分辨率均為15 m。根據研究區實際情況,參考土地利用現狀分類標準(GB/T 21010—2017),利用ENVI 5.3對4期遙感影像進行人機交互解譯,結合野外抽樣驗證及Google Earth歷史影像對分類結果進行校驗、修改,得到4期土地利用類型數據,包括水體、旱地、水田、林地、草地、建設用地、其他用地共7類。對分類結果進行精度驗證,4期分類總體精度均大于90.0%,Kappa系數均大于0.88,符合精度所需要求(表1)。然后利用ArcMap 10.7繪制提取面積小于8 hm2的水體和水田作為本文研究的小微濕地,所提取小微濕地的最小面積均為0.02 hm2,2006年、2010年、2014年、2018年最大面積依次為7.90 hm2、7.94 hm2、7.83 hm2、7.81 hm2。最后得到包含小微濕地在內的共計8類土地利用類型數據(表2)。

表1 土地利用類型分類精度驗證
2.2 景觀格局指數
景觀格局指數能夠定量反映小微濕地景觀結構組成和空間配置等方面的特征[30]。分別從斑塊水平統計小微濕地斑塊數量和斑塊面積;從景觀水平計算小微濕地平均周長面積比、斑塊密度、平均歐式最鄰近距離和聚合度指數。景觀格局指數計算在Fragstats 4.2.1軟件中進行。
2.3 驅動機制
2.3.1變量選擇與處理
分別以2006—2010年、2010—2014年、2014—2018年、2006—2018年4個時期的小微濕地變化值作為響應變量。“1”表示小微濕地損失區域,“0”表示小微濕地不變的區域。利用ArcMap 10.7創建隨機點工具在小微濕地變化空間分布圖上生成采樣點,“0”和“1”的采樣點數量大致相同。
基于以往研究[18,33],結合研究區實際情況及數據的可獲得性,選取13個預測變量(表3)。預測變量處理中,為了量化小微濕地周邊用地類型的變化,且考慮到小微濕地斑塊面積可能具有尺度效應,利用ArcMap10.7的創建漁網工具分別設定150 m、300 m、450 m、600 m、750 m、900 m的6種正方形網格,分別計算4個年份不同網格尺度下小微濕地斑塊面積的變異函數模型,比較分析后發現較小的網格會破壞小微濕地的空間聯系,較大的網格則可能掩蓋小微濕地的細節特征。300 m的網格尺度在刻畫小微濕地的空間特征與模型運行效率方面取得較好的平衡。因此,選擇300 m的網格(共計3454個)對小微濕地斑塊面積和各類土地利用變化量進行計算。為統一像元大小,所有預測變量均基于300 m的網格計算。

表3 網格單元預測變量描述
2.3.2增強回歸樹模型
BRT模型構建于傳統的分類回歸樹算法基礎之上,通過不斷地隨機選擇和自學習方法產生多重回歸樹,進而提高模型的穩定性和預測精度[34]。其優勢在于能夠處理不同類型的預測變量,對數據的共線性問題不敏感,無需事先進行數據變換或者剔除異常值,可以擬合復雜的非線性關系和交互作用,輸出的預測變量相對貢獻率和擬合函數曲線較為直觀[35]。
模型擬合調用R 4.1.0軟件中“caret”、“gbm”和“dismo”等包實現。模型擬合中,有學習速率、樹復雜度、袋分數和分布函數4個參數需要設置。由于本文的響應變量為二分類變量,通常設置分布函數為“bernoulli”,其余參數設置比較幾種參數組合,學習速率:0.005、0.01、0.05、0.1,樹復雜度:4、5、6,袋分數:0.5和0.75。對數據集進行10折交叉驗證,將交叉驗證后與測試集最高平均精度相對應的參數組合作為最優參數設置,同時將該參數組合下交叉驗證精度最高的一組作為測試集,其余作為訓練集重新構建模型。利用受試者工作特征曲線下面積(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AUC)進行模型評估,一般AUC值大于0.70的模型較為合適[36]。BRT模型結果將相對影響進行縮放,使其相加和為100%,相對影響值越大表示對小微濕地損失的影響越大。與傳統的回歸模型相比,BRT模型沒有P值來表示變量的顯著性意義[34]。本文預測變量的重要性通過與相對影響中位數值的大小比較得出,相對影響超過中位數值的預測變量被認為是高重要性變量,反之為低重要性[37]。
2.3.3地理加權邏輯回歸模型
GWLR模型是經典邏輯回歸模型的擴展,允許局部而非全局的參數估計,以探索驅動因素的空間差異性,其實質是利用基于距離加權的局部樣本估計出每個樣本點各自獨立的參數值[29]。模型通過計算每個測量點的系數來反映空間異質性,同時能夠得到每個測量點系數的P值[38]。模型表達式為:
式中,(ui,vi)為采樣點i的坐標;βk(ui,vi)為采樣點i上的第k個回歸參數,是關于地理位置的函數;pi是響應變量為1(小微濕地損失)的發生概率。
BRT模型得到的高重要性變量,利用GWLR模型依次對單個變量進行擬合,然后借助ArcMap 10.7的反距離權重插值對GWLR所得的每個數據點的估計系數和系數的P值可視化呈現,確定預測變量的空間異質性。GWLR模型擬合涉及核函數類型選擇、最優帶寬選擇方法和帶寬選擇標準。本文選擇自適應雙重平方函數為核函數類型計算空間權重矩陣,采用黃金分割搜索法產生系列帶寬,赤池信息準則確定最優帶寬。模型擬合過程借助MGWR 2.2.0軟件實現。
3 結果
3.1 研究區土地利用變化

圖2 研究區土地利用類型及面積占比Fig.2 Land-use type and the proportion of land-use type areas in study area
從圖2可以看出,2006—2018年,旱地和建設用地分別是研究區減少和增加最為明顯的土地利用類型。2006年,旱地是研究區主要用地類型,占土地利用總面積的30.9%,隨后逐年降低,2018年僅占總面積的15.0%,濱湖新區核心區附近旱地消失最明顯。建設用地面積由2006年的6625.84 hm2增加至2018年的10432.43 hm2,成為研究區主要的用地類型,建設用地發展的方向由老城區和濱湖新區核心區西部逐漸向巢湖方向擴散。草地面積整體呈上升趨勢,在2014—2018年期間增加最為明顯,增加了1439.92 hm2。林地面積呈現出逐年緩慢增長的趨勢。水田面積則從2006年的1539.68 hm2減少到2018年的104.04 hm2,減少了93.2%,是研究區減少幅度最大的用地類型。其他用地在2006—2014年從216.01 hm2增加到1009.37 hm2,到2018年又降至471.89 hm2。水體面積的變化較為穩定,其中包括7000 hm2左右固定巢湖水面面積。2006—2018年,小微濕地面積從1684.66 hm2減少到659.70 hm2,減少了60.8%,2010—2014年是小微濕地面積減少最多的時期,減少了433.47 hm2。
3.2 小微濕地景觀動態變化
3.2.1小微濕地景觀格局指數變化
從表4可以看出,2006—2018年,小微濕地總的斑塊數量減少了60.5%。其中,水體型小微濕地數量呈持續減少的趨勢,水田型小微濕地斑塊數量則是呈先上升后下降趨勢,最大值出現在2010年。水田型和水體型小微濕地斑塊面積分別減少了585.37 hm2和439.59 hm2。其中,2006—2010年是水體型小微濕地斑塊面積減少最多的時期,減少了207.54 hm2。2010—2014年是水田型小微濕地斑塊面積減少最多的時期,減少了304.15 hm2。從斑塊面積的分布情況來看,水田型小微濕地的平均斑塊面積總體上大于水體型小微濕地。水體型小微濕地的平均斑塊面積整體變化幅度較小,略有上升,水田型小微濕地平均斑塊面積則是呈先下降后上升趨勢,最小值出現在2010年。此外,4個研究時期,75%的水體型小微濕地面積都不超過0.80 hm2,說明研究區水體型小微濕地以較小斑塊為主。2006—2018年,水體型小微濕地斑塊面積的第一四分位數由0.09 hm2上升到0.18 hm2,說明有相當一部分小面積的水體型小微濕地斑塊消失。

表4 斑塊水平小微濕地景觀格局指數變化
斑塊周長面積比是衡量景觀中斑塊形狀特征的指標,可以用來表征小微濕地斑塊的邊界效應。表5顯示,小微濕地的平均周長面積比呈波動下降趨勢,最大值出現在2014年,可以看出小微濕地斑塊邊緣的復雜程度整體上是下降的。小微濕地斑塊密度呈先上升后下降趨勢,最大值同樣出現在2014年,2018年斑塊密度達到最低,說明小微濕地在斑塊破碎化程度達到最大后有一個大量消失的過程。小微濕地斑塊間的平均歐式最鄰近距離逐漸增加,在2018年達到最大,同時,聚合度指數持續降低,在2018年達到最小值。

表5 景觀水平小微濕地景觀格局指數變化
3.2.2小微濕地空間分布
圖3可以看出,2006—2018年,小微濕地在整個研究區大范圍減少,濱湖新區核心區是損失較為嚴重的區域,小微濕地損失的同時也有少量小微濕地斑塊的增加,主要分布在十五里河沿岸和西南部的圩區。不同時間段的小微濕地空間變化呈現出明顯的異質性特征。2006—2010年,濱湖新區核心區西部是小微濕地損失較為嚴重的區域,老城區和經開區也有不同程度的小微濕地損失。2010—2014年,小微濕地損失嚴重的區域由濱湖新區核心區西部向東部移動。2014—2018年,小微濕地的變化范圍明顯縮小,損失主要發生在十五里河沿岸和西南部的養殖漁場附近。

圖3 小微濕地空間分布變化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nges of small wetland
3.3 小微濕地變化驅動機制
3.3.1BRT模型評價
從表6可以看出,4個時間段訓練集、測試集、數據集的AUC值分別在0.81—0.91、0.74—0.87、0.80—0.91之間,均大于0.70,說明模型擬合效果較好。

表6 BRT模型參數設置及模型評估結果
3.3.2預測變量相對影響
從圖4可以看出,小微濕地斑塊面積、建設用地變化、旱地變化、林地變化、草地變化、坡度在4個時間段均屬于高重要性變量,這些變量共分別解釋了65.9%(2006—2010年)、63.0%(2010—2014年)、61.5%(2014—2018年)、64.6%(2006—2018年)的小微濕地損失。人口變化、數字高程模型、其他用地變化、水田變化、水體變化、距道路距離、距河流距離在4個時間段均不屬于高重要性變量。2006—2010年對小微濕地損失影響最大的前4位均是小微濕地周邊土地利用變化,其相對影響的總和為48.3%。2010—2018年,建設用地變化和斑塊面積是最重要的兩個預測變量。
2006—2018年,建設用地變化是對小微濕地損失影響最大的因素(14.4%),其次是小微濕地斑塊面積(13.5%),其余高重要性變量的相對影響依次為:旱地變化(11.1%)、坡度(10.1%)、林地變化(8.5%)、草地變化(7.0%)。

圖4 預測變量對小微濕地損失的相對影響Fig.4 Relative influence of predictor variables on the loss of small wetlands
3.3.3高重要性變量驅動機制
進一步對4個時期相對影響大于中位數變量的高重要性變量繪制部分依賴圖,部分依賴圖表示在控制其他所有變量均值不變的情況下,某一變量對小微濕地損失的影響。從圖5可以看出,不同時間段,小微濕地損失對同一個變量的響應趨勢相似。小微濕地斑塊面積越小,小微濕地損失的可能性越高;小微濕地的損失可能性隨小微濕地周邊土地利用類型面積的增加而上升,增加到某一閾值時,對小微濕地損失的影響可能不再增大;坡度對小微濕地損失的影響趨勢總體較為平穩。
2006—2018年,當斑塊面積在0.02—3.2 hm2范圍內時與小微濕地損失呈正相關。小微濕地周邊建設用地擴張對小微濕地損失的影響閾值在2.5—6.5 hm2,面積增加超過6.5 hm2對小微濕地損失的影響不再增大。同樣地,旱地面積增加到2.7 hm2左右會威脅到小微濕地的生存。此外,林地和草地面積增加對小微濕地的損失的影響也不容忽視,林地面積增加超過2.4 hm2時與小微濕地損失呈正比,隨著林地面積的增加,對小微濕地損失的影響有不斷增加的趨勢。草地面積增加超過2.3 hm2時與小微濕地損失呈正比;坡度大于2.6°的區域與小微濕地損失呈正相關。

圖5 高重要性變量對小微濕地損失影響的部分依賴圖Fig.5 Partial dependence plots of the influence of high-importance variables on the loss of small wetlandsx軸向外的刻度表示預測變量的數據范圍,向內的刻度表示預測變量的十分位數據分布;y軸的數值大于0表示預測變量與小微濕地損失呈正相關,小于0表示負相關,等于0表示無相關關系
圖6顯示2006—2018年高重要性變量對小微濕地損失的影響隨空間位置的變化。對變量采樣點處的系數值和系數的P值進行空間插值并疊加,設顯著性水平α= 0.05,P值小于0.05的采樣點所形成的插值面表示變量對小微濕地損失有顯著性影響的區域,暖色調和冷色調分別表示顯著正向和負向影響,白色區域表示變量對小微濕地損失無顯著性影響的區域(P≥ 0.05)和巢湖水面。此外,由于小微濕地斑塊面積屬于小微濕地自身景觀結構特征,系數的空間可視化無解釋意義,故不在模型結果中體現。

圖6 2006—2018年地理加權邏輯回歸模型高重要性變量系數空間分布Fig.6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high-importance variable coefficients in GWLR model from 2006 to 2018
圖6可以看出,變量系數存在明顯的空間差異。除去與小微濕地損失無相關性的區域,建設用地變化整體與小微濕地損失呈顯著正相關關系(P<0.05),系數最大值分別出現在老城區和濱湖新區核心區西部,系數的大小往巢湖方向逐漸降低;林地變化整體與小微濕地損失呈顯著負相關關系(P<0.05),系數最小值為-0.64;旱地變化僅在西南部的圩區附近與小微濕地損失呈顯著正相關(P<0.05),其余區域對小微濕地損失無顯著正向影響;草地變化在濱湖新區核心區東部與小微濕地損失顯著正相關(P<0.05),其余區域與小微濕地損失呈顯著負相關(P<0.05)或無相關關系;坡度在研究區大部分區域與小微濕地損失呈顯著負相關(P<0.05)或無相關關系,在研究區東北角和東南部有小片區域與小微濕地損失呈顯著正相關關系(P<0.05)。
4 討論
4.1 小微濕地景觀動態變化及驅動因素
城市快速發展背景下,包河區內小微濕地在2006—2018年間大范圍消失,總面積和總斑塊數量減少均超過60%,這種減少趨勢同樣出現在其他一些城市快速發展的地區[19—20,30]。小微濕地損失的主要驅動因素包括周邊土地利用變化、自身景觀屬性和地形條件3個方面,各驅動因素對小微濕地損失的影響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征。2005年,合肥市提出“141”城市空間發展戰略,其中一個重要的舉措是規劃沿巢湖建立濱湖新區,以實現合肥市通過巢湖、走入長江、融入長三角城市群的發展目標。2006年,包河區內啟動濱湖新區建設,開啟了現代化濱湖城市建設的新篇章。城市快速發展初期(2006—2010年),城市建設以先修路,后沿道路向外延伸開發為主[39],當小微濕地所能夠帶來的經濟效益低于周邊土地利用方式改變帶來的效益時就容易發生轉變[18,26]。在此開發背景下,相比于自身景觀屬性和地形條件等因素,周邊土地利用(建設用地、旱地、林地和草地)變化對小微濕地損失的影響顯得更為重要。在該階段所能觀察到研究區兩種類型的小微濕地有著不同的變化,水體型小微濕地表現為數量急速下降,而水田型小微濕地數量卻有所增加,可能是由于水體型小微濕地平均斑塊面積較小,往往會先消失,而平均斑塊面積相對較大的水田型小微濕地更容易被分割[11,21,28]。中后期(2010—2018年),合肥市進一步提出“1331”市域空間發展規劃,加快了包河區城鎮化、工業化、農業集約化發展速度,城市建設由“擴張式”變為“填充式”發展[39]。隨著城市建設大范圍擴張的趨勢有所緩解,各類型周邊土地利用變化的相對影響相較于前期也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斑塊面積和坡度對小微濕地損失的驅動作用逐漸凸顯。該階段,與水體型小微濕地數量持續下降不同的是,水田型小微濕地經歷斑塊破碎化后數量急速下降的過程。有研究表明,較大面積的小微濕地逐漸被分裂成較小的斑塊,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先消失的那一部分小的斑塊,進而快速消失[21]。從小微濕地景觀空間分布格局來看,斑塊數量的減少使得剩余小微濕地間的空間距離增加,聚集程度降低,這種變化會導致小微濕地生態系統服務功能不成比例的損失[40—41],小微濕地間距離的增加會阻礙物種遷移,從而對生物多樣性造成負面影響[27,42]。
建設用地變化是2006年到2018年小微濕地損失的最主要驅動因素,建設用地變化對小微濕地損失的影響大小由老城區和濱湖新區核心區西部向巢湖方向逐漸降低。盡管濱湖新區核心區是建設用地增加最明顯的區域,但是對小微濕地損失的影響卻不是最大的,老城區建設用地變化的影響反而更高。可能是由于老城區作為最早的城市中心,居住區和商業用地密集,內部填充空間有限,在建設用地擴張過程中更容易導致小微濕地損失,而濱湖新區屬于近期規劃的城市新區,在建設過程中更注重保留濕地,加強生態景觀與城市風貌的協調建設[20,24,39,43]。BRT模型還得到小微濕地損失對于土地利用變化的響應閾值(圖5),如小微濕地周邊旱地面積增加2.7 hm2左右會威脅到小微濕地的生存。實際上,由于建設用地侵占、退耕還林工程等因素的影響,研究區內旱地面積大量減少,僅在圩區保留少量基本農田,但是,圩區作為農用地重點整理區域,大范圍調整農業結構,水田和水體型小微濕地被疏浚或排干,改造為旱地,以滿足生態農業對作物多樣性的需求[44],這就解釋了除西南部圩區以外,旱地變化對小微濕地損失無顯著正向影響的原因。值得一提的是,隨著退耕還林工程和環巢湖生態示范區建設等項目的持續推進,研究區林、草地面積有所增加,BRT顯示周邊林、草地面積增加超過2.4 hm2左右時會導致小微濕地損失,但是GWLR模型結果顯示周邊林、草地面積變化對小微濕地的持續存在有一定的正向促進作用。究其原因,盡管研究區林、草地面積有所增加,但更多的是“見縫插綠”而非成片增加。相關研究表明,林、草地對周邊水質的凈化有一定的正效應[45—46],且周圍有林、草地的小微濕地,其綜合生態系統服務的質量較高[18]。
以往的一些研究表明,城市中大多數小微濕地是人為創建的,小微濕地的存在或消失更多是基于管理者的意愿[24,47],所以小微濕地自身景觀屬性的影響很容易被忽略。本文研究結果顯示,斑塊面積對小微濕地損失的相對影響排在第2位,小微濕地損失對于網格單元內斑塊面積變化的響應閾值在0.02—3.2 hm2之間。一方面,說明小微濕地面積越小損失的可能性越大。面積較小的小微濕地除了更容易被人為侵占外[12],相比于較大面積的小微濕地,小面積的小微濕地通常有更小的徑流輸入量和更大的單位面積淺層地下水流出量,因而更容易損失[10,20];另一方面,說明小微濕地在小范圍內的聚集程度越高,越不容易損失,有研究表明,多個小而集中的小微濕地在養分截留和對污染物的凈化方面比等面積的大濕地效率更高[48—49]。本文利用Google Earth高清歷史影像結合實地調查,觀察了研究區幾個不同區域的小微濕地情況,發現面積較小的小微濕地一般都是村塘、季節性水塘,其蓄水能力差、自身結構不完善,主要依附降水與鄰近水體間的水源聯系,這些小微濕地容易被污染、廢棄或受到自然演替的影響[33];小范圍集中分布的小微濕地多為河流沿岸聚集的養殖塘、灌溉塘和水田等,這些小微濕地的水系連通性較強,不易損失[13,27]。最后,本文還得出坡度對于小微濕地損失的相對影響較高,這可能是由于下墊面地形條件對小微濕地的變化有著重要的影響[30]。當坡度小于2.6°時,與小微濕地損失呈負相關,從水文學角度來看,坡度陡緩是影響地表水匯流情況的主要因素[50],坡度平緩地區的小微濕地更容易接受來自高地的徑流輸入[10]。
本文利用BRT模型量化預測變量的相對影響,擬合高重要性變量與小微濕地損失之間的非線性關系,結合GWLR模型分析高重要性變量的空間異質性,改進了以往僅采用單一全局回歸模型或者單一空間回歸模型對小微濕地損失的驅動力研究。同時,文章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在預測變量選取時,由于數據獲取限制,未能選擇氣候、水文因素分析對小微濕地損失的影響。另外,受限于遙感影像精度,本文所能提取最小面積的小微濕地僅為0.02 hm2,研究區還應當存在大量的、面積更小的小微濕地[17]。在后續的研究中,將通過野外調查或利用更高精度的遙感影像作為手段,更全面地研究影響小微濕地損失的因素并對面積更小的小微濕地予以關注。
4.2 小微濕地保護與管理
城市化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應當對小面積的小微濕地或者是在小范圍內集中分布的小微濕地予以特別關注,加強小微濕地間、小微濕地與其他濕地間的水系連通性,防止其進一步損失。在后續的城市開發過程中,要充分意識小微濕地生態價值,加強小微濕地的編目和價值評估,加強小微濕地生態服務功能和生態服務價值的宣傳與示范,將城市小微濕地與林地一樣納入城市綠地保護的剛性要求。同時,建議在城市不同發展區域新建一批小微濕地修復示范工程,注重綠地資源的合理配置,在小微濕地保護與恢復的前提下,積極探索小微濕地保護與開發的平衡點,合理利用其生態服務功能。最后,已有部分地區將小微濕地納入濕地保護體系[4—5],未來還應盡快制定與小微濕地有關的國家、行業及地方標準,建立小微濕地生態保護與恢復的激勵機制,指導小微濕地保護與開發的科學開展。
5 結論
城市化背景下,包河區小微濕地的景觀格局發生較大改變,表現為數量和面積急劇下降,伴隨著斑塊邊緣復雜程度的降低,空間分布更加“孤立”。2006至2018年間,導致研究區小微濕地損失的高重要性變量可以概括為周邊土地利用變化、自身景觀屬性和地形條件三個方面。周邊土地利用變化方面,建設用地變化是導致小微濕地損失的最主要因素,其在整個研究區均與小微濕地損失呈正相關。從自身景觀屬性看,小微濕地斑塊面積對其自身的影響表現為小面積的斑塊更容易消失。小微濕地的損失與地形條件也密切相關,坡度越陡,小微濕地損失越明顯。小微濕地在城市中廣泛分布,具有重要的生態價值,在當前小微濕地備受關注和亟需保護的背景下,本研究結果可以為快速城市化地區的小微濕地保護提供一定的理論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