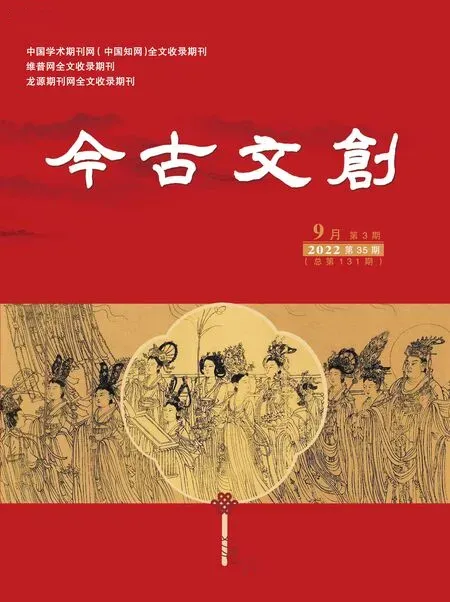韓國小說《蟲子》的女性主義地理學解讀
◎張金鍇
(閩南師范大學 文學院 福建 漳州 363000)
隨著“文化轉向”和“空間轉向”的興起,人們對時空的概念發生實質的變化,空間不再被狹隘地理解為容納物質存在和社會行動的器皿,而是將其理解為“一切公共空間生活形式的基礎,是一切權力運作的基礎”,同時也是復雜社會生產的一部分。空間的生產涉及諸多權力關系的運作,性別就是關鍵要素之一。受到第二次女性主義運動的沖擊,一批學者開始將女性主義思潮與人文地理學研究結合起來,對看似中性的地方和空間從社會性別視角進行分析,揭示出“男造環境”中的性別不平等,從而開始了一支新興的人文地理學分支——女性主義地理學。女性主義地理學以“空間”和“性別”為立足點,以揭露空間中的性別不平等現象為初始目的,進而“調查、解釋并挑戰性別劃分和空間區分的關系,揭露它們的相互構成,質疑它們表面上的自然特性”。女性主義地理學不僅為重新認識性別和空間之間的關系提供了一種全新的研究路徑和思維方式,同時也為今后的文學研究提供了不同的向度和可能。
《蟲子》出自新世紀韓國作家金愛爛的第三部小說集《你的夏天還好嗎?》。金愛爛憑借多部作品斬獲韓國諸多獎項,被媒體冠以“韓國文壇最大的收獲之一”。金愛爛“之所以廣受新世紀韓國文壇的好評,一方面是因為其作品兼具藝術性和可讀性,另一方面則是由于這些作品有非常濃厚的代際特征。她專注于講述自己這一代人的故事,小說充滿朝氣,以富有張力而輕松自在的文筆挑戰倫理陳規和文化禁忌,令人耳目一新”。在《你的夏天還好嗎?》中,作者透過人們看似平淡的細小生活片段,集中反映了現代韓國人的情感生活
經歷,塑造了形形色色的面臨絕境的人物。《蟲子》的主人公是一位家庭主婦,生活基本限于公寓之中,在公寓里循環往復、日復一日地完成洗刷、做飯等家庭瑣事。經濟上她完全依靠丈夫在社會中的打拼換取的微薄薪資,精神上也完全依賴丈夫。丈夫則忙于工作,在家的時間僅限于睡覺的時間,疏于對妻子關心。作者對日常現實生活進行細致的描繪,再現了女主人公真實的內心情感世界和精神狀態,敏銳地發現男性與女性在空間中的不平等地位,女性局限在私人家庭空間,而男性可以游刃有余地出入社會公共空間。本文認為男女主人公對空間占有的不同狀況,顯示了男女兩性對于空間的占有具有不平等性。父權社會既有的性別分工和性別氣質刻板印象使男性獲得更廣闊的生活、工作空間,而以女主人公為代表的女性群體被局限于女性化的私人空間里,這再現并強化了女性群體的弱者地位,限制了自身的發展和保護自我的能力。
一、角色期待與空間區隔
父權制中傳統的性別觀念認為兩性間存在固化的性別氣質與社會分工,因此對男女兩性有著不同的角色期待,認為男性是公共空間里的支薪勞動者,可以在經濟、政治、軍事等領域建功立業、創造社會價值;女性則是家庭私人空間里的賢妻良母,從事再生產勞動力的活動,不直接生產社會價值,為男性做好后勤保障等一系列家務,生育、照顧小孩,在經濟、社會地位等方面都依賴于男性。金愛爛的小說《蟲子》中男、女主人公的主要活動空間的區別基本符合這種鮮明的性別二元分工和父權社會對兩性不同的角色期待。
“受傳統農業生產條件和儒家禮教影響,韓國傳統的家庭結構是幾代同堂的大家庭,男子被賦予代表、支撐和保護一個家庭的責任,丈夫或父親是一家之主即家長,家長在家庭中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擁有家庭的財產分配權、祭祀權以及對家庭成員行為的監督權。家庭中,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內,提倡‘賢妻良母’,家務勞動幾乎全落在婦女身上……一直到現代,韓國婦女外出工作的比例仍然比較低,特別是已經結婚的婦女,即使獲得高學所文憑也一般都守在家里,伺候丈夫和老人,撫養孩子。”小說中的女主人公就是一位典型的韓國家庭婦女。她每天花費大量的時間完成清掃擦拭、買菜做飯、整理歸納等家庭瑣事,活動范圍基本局限在私人家庭空間內。她沒有工作,完全以家庭、丈夫為生活重心,很少參與社會事務方面的活動。作為社會的一分子,女主人公偶爾會通過另外一種形式參與社會活動,如購物。“買菜做飯,也不忘結識干洗店、副食店和肉店的老板,開拓值得經常光顧的店鋪。”但其外出購物并非單純的休閑娛樂和以滿足自我為前提。因此實際上女主人公對社會事務的參與仍然是一種以服務家庭、滿足再生產需求為出行目的的家務型外出,即使已經進入到城市公共空間領域也仍然沒有擺脫私人家庭空間的束縛。懷孕之后女主人公更是因為行動不便就整日待在家中。
女主人公不光身體上局限在家庭空間內,精神上同樣過度依賴家庭空間內的成員,即她的丈夫。女主人公即將分娩時,心情敏感,情緒波動很大,“有時候荷爾蒙加重了憂郁癥,我會因為爬過地板的鼠婦蟲而萌生想死的沖動”。她總想跟丈夫通話,類似的電話打了很多遍,而丈夫日漸忙碌,壓力加大,同樣陷入焦慮的情緒,“丈夫良久無語。我感受到了電話那頭丈夫的疲勞、嘆息和煩躁”。過度依賴丈夫的女主人公沒有社會交往,所有的苦惱只能向丈夫的傾訴。再加上身為孕婦敏感的情緒和挺著孕肚行為不便帶來的不快,加劇了妻子的不安與焦慮,她迫切地希望她依賴的人能夠為她解決問題、安撫情緒。但她依賴的丈夫只給了一個敷衍的反應,隨便應付幾句,匆匆掛斷電話。在丈夫身上體現出一種父權制社會的規范秩序,他希望妻子能安心地待在家里,安守屬于女性的私人領域,專注家庭,不要反抗也不要抱怨。妻子的抱怨和焦慮是對空間內部秩序的質疑和掙脫,違反了父權社會對女性成為聽話的賢妻良母的角色期待。
女主人公的丈夫是一名中小型制果企業的銷售人員。繁忙的工作和頻繁的出差使得丈夫每天更多的時間甚至全部的時間在家庭空間外部的社會公共空間度過。社會公共空間的工作場所是丈夫的主要活動領域,是他度過一天中大部分甚至全部時間的地方:“丈夫不像我這樣經常看見蟲子。他一回家就睡得昏天黑地,好像很長時間沒睡覺似的”“丈夫經常加夜班……他在我身邊的時間越來越少”。“列斐伏爾在論及社會空間的時候曾經很犀利地指出,住宅對男性而言是休息和休閑的場所,對女性則是勞動的場所。”對于丈夫而言,家庭空間是離開社會公共空間,暫停工作競爭,進行休閑娛樂和勞動力再生產的地方,停留的時間遠遠少于妻子,所以丈夫不會知道妻子在家中從早到晚忍受著拆遷區域惱人的噪音,也不會知道妻子在家中會發現無處不在的各種各樣的駭人的蟲子。不同的性別角色期待造成空間區隔,使得丈夫根本無法與長期處在私人家庭空間的妻子感同身受。
父權制對男女兩性不同的角色期待,使得空間被劃分為歸屬于男性的社會公共空間和歸屬于女性的私人家庭空間。這兩個空間的特征迥然不同,女主人公的空間是處在拆遷區的老舊的公寓,周圍都是拆遷的灰塵和從早到晚的噪音,充斥著降低生活質量的家務勞動和不知從何處來的無窮盡的蟲子。而丈夫的空間則是充滿社會交往的更能體現社會價值的公共領域。女主人公對丈夫的工作環境和工作內容并不了解,不知道丈夫因為巧克巧克薯片里發現了蛆蟲而焦急,不了解丈夫在職場中承受什么樣的壓力;丈夫對妻子在家中遭遇的噪音和蟲子的侵擾也滿不在乎,也不知道拆遷區中那棵佇立已久的大樹的倒下對妻子產生的影響。空間的分隔不僅反映了夫妻雙方在空間資源占有上的失衡,影射了兩性權力的微妙差異,也在夫妻之間形成溝壑,本應互敬互愛的夫妻心生怨懟,埋下不和諧的隱患。
二、家庭空間內部的兩性關系
傳統的家務勞動分工的結果往往是女性放棄工作中的自我實現機會,而男性被鼓勵在事業發展和繼續教育上投入大部分的精力。這造成了女性發展落后于男性,女性被排斥在公共領域以外,在經濟上和意識上依賴男性。在這種情況下,女性被動地存在著,處于被壓迫的邊緣地帶,排斥于社會之外。
“為了找房子,我們吃了不少苦頭。利率太低,幾乎沒有傳貰房。即使有傳貰房,傳貰金也比我們手頭的錢貴出幾千萬。騰房的日子臨近了,還沒有找到合適的房子,正在著急的時候,我們發現了薔薇公寓。”小說中這份決定由她的丈夫——空間內實際權力的掌控者做出的。雖然女主人公是私人家庭空間的女主人,但她在自己的領地內只有勞動再生產的義務,并無實質權力。“丈夫總是強調說,同樣的面積,一居室要好過兩居室。搬家后我慶幸自己聽了他的話。”女主人公對于丈夫的決定表現出順從和依賴,將丈夫的決定置于真理地位,失去了自己的聲音。當后期女主人公向丈夫抱怨房子噪音太大時,“挑選房子的時候表現積極的丈夫顯得悶悶不樂”,于是女主人公只能繼續忍受糟糕的環境,不再發出自己的聲音。父權社會要求女性遵循父權制社會的規范秩序,安心地待在家里,安守屬于女性的私人領域,支持父權代言者父親或者丈夫的決定,而女性被父權社會的規范秩序所馴化,認可了不均等的性別權力。丈夫的“悶悶不樂”一方面是因為悲觀的經濟狀況,無法改變居住情況,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因為自己當初做出的買房的決定受到了質疑與抱怨。這也就暗示了夫妻二人之間的關系并非平等。丈夫身為男性有著父權社會中優越的性別身份,能夠自由進出社會公共空間獲取生活資源,獲得經濟收入,因此即使丈夫不常生活在家庭私人空間但仍然掌握著家庭空間中的實際權力,居于主動、主導的地位。女主人公是家庭主婦,不直接生產社會價值,沒有經濟來源,因此雖然操持著家庭空間中的大小事宜但沒有做出重大決定的實際權力,只能聽從丈夫的安排,迎合社會期待,處于被動、依附的地位。
女主人公與丈夫是新婚的夫婦,即使是女主人公臨近分娩,不能同房,戀愛時的緊張和激情減少,夫妻間仍然恩愛有加,仍舊貪戀和依賴彼此的身體。女主人公認為他們夫妻之間感情很好,但在丈夫因為工作經常加班推遲回家的時間甚至是徹夜不歸時,她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他會不會有別的女人”的疑問和緊張。女主人公作為家庭主婦,對丈夫在社會公共空間的工作和交際幾乎一無所知。面對關機無法聯系的丈夫,煩躁和怨恨中的女主人公能想到的唯一的報復是“這個時候如果發生讓他終生后悔的和內疚的小事故就好了”,而這就像一個不吉利的暗示,暗示女主人公即將發生的不幸,同時也披露了一個殘忍的真相:女性只能通過傷害自己身體的方式對男性進行報復。因為在父權社會中,女性的身體作為一種空間也是屬于男性的。
空間的性別分工將女性束縛在家庭之中,生活平靜,沒有社會競爭,看起來提供了某種庇護,但實際上,女性在這種束縛中,弱勢地位更加強化,甚至失去自我保護能力。當女主人公為了找尋意義非凡的戒指而下樓來到A區域遭遇危險時,她根本無法自救。小說以女主人公獨自走出家庭私人空間后遭遇不測的象征,闡明了性別刻板印象和性別分工造成的空間分隔,不僅不能保護女性,束縛其發展前景的同時,也剝奪了其自我保護的能力。
三、結語
作者金愛爛感受到兩性在空間占有上的極大區別,以其細膩的文筆用一位家庭主婦的平淡的日常生活的故事寫下了自己的考慮與反思。看似女主人公享受專屬于女性私人空間的生活,但實際上她也承受著這個空間中過量的家庭勞動、長時間一個人的孤獨、缺乏社會交流的苦悶與焦慮。地理學家哈維認為,寓居(dwelling)或家乃是人與物達成精神統一的關鍵位置,家具有庇護、安全和愉悅的特質,是人類自發產生歸屬感的關鍵元素。然而,當家庭成為女性角色的專屬空間,成為性別刻板印象的有力工具時,家庭空間對于女性,有可能是牢籠、陷阱和監獄,是被“他者化”的地方。
父權社會對男女兩性不同性別氣質的刻板印象生成了社會對于兩性不同的角色期待:期待女性成為家庭空間內的“賢妻良母”,成為男性的依附者;默認男性果敢、剛強,可以在社會公共空間游刃有余。對女性的角色期待將女性局限在私人家庭空間內部,限制了女性對不同空間的自由選擇,束縛了女性對自身品質才能的發揮,作繭自縛,困在家庭主婦的角色里,失去保護自己、掌控自我命運的能力。空間區隔的存在不僅再現、強化了女性的弱者地位,同時在一定程度上阻隔了兩性的交流和相互理解,對男女兩性的和諧關系的發展造成了困擾和隔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