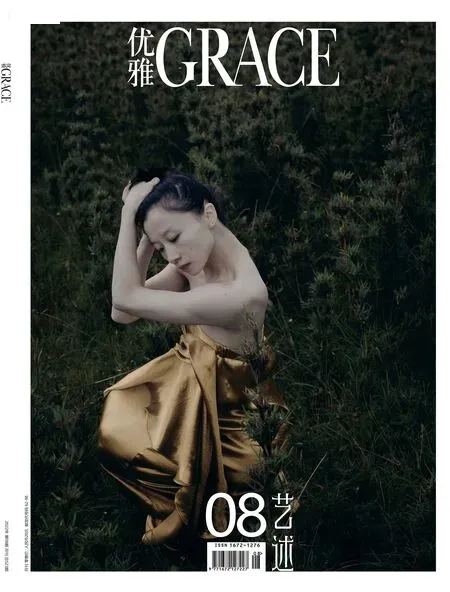余爾格 夢由舞境
編輯/文:錢雪嬌 攝影:羅勁超 圖:余爾格提供

余爾格,法國巴黎Cite des art Paris國際藝術(shù)城和A4國際駐留藝術(shù)中心藝術(shù)家,獲選瑞士文化基金會(huì)駐留藝術(shù)家。國家一級(jí)演員,受邀于巴黎蓬皮杜藝術(shù)中心40周年慶典現(xiàn)場演出及2020年在蓬皮杜藝術(shù)中心劇場表演作品《LES CHAUVES SOURIS DU VOLCAN》以及作品《Biopigs》在瑞士洛桑“Arsenic”演出。
余爾格的名字和跳舞時(shí)的她一樣特別,“余”代表我,“爾”代表你,“格”是她出生地哈爾濱(滿族人叫姑娘為格格),合在一起就是“我和你的格格”,表達(dá)著父母對(duì)余爾格滿滿的愛。余爾格形容自己是個(gè)愛“折騰”的人,在我看來,不如說她是個(gè)愛冒險(xiǎn)的人。在擁有一份穩(wěn)定的高校舞蹈老師的工作時(shí),因?yàn)閷?duì)舞臺(tái)的熱愛,卻毅然選擇出國深造;去到人生地不熟的法國,在舞蹈團(tuán)做舞蹈演員的同時(shí),還要攻克語言關(guān);有著扎實(shí)傳統(tǒng)舞基本功的她,卻一頭扎進(jìn)現(xiàn)代舞領(lǐng)域,從零開始;后來,又從一個(gè)舞者,向一個(gè)舞臺(tái)創(chuàng)作者的身份進(jìn)發(fā)。用她自己的話來說,她喜歡“飄”一點(diǎn)的生活。在疫情之前,她在中國與法國之間已往來近十年,她用一種自己喜歡的方式,享受著當(dāng)下,感受著舞蹈在她生命里帶來的新鮮與刺激。
跳舞一點(diǎn)都不累,不跳,才累
余爾格的身材比我想象中的更加纖細(xì)嬌小,就在這副小小的身軀里卻有著驚人的能量。“跳舞時(shí),我總有一種‘噴火’的感覺,特別有爆發(fā)感和凝聚感。”能夠成為一名舞者,余爾格坦言自己很幸運(yùn)。因?yàn)閾碛形璧柑熨x的人有很多,但不一定都能成為最后的舞者,就像一顆種子有了土壤、陽光與水,也不一定能長成參天大樹;那些最終能夠成就自己的人,除卻先天的機(jī)遇以外,更多的是在把握契機(jī)的同時(shí),自身不斷地努力。余爾格同樣有著舞蹈表演的天賦,但想跳到最好,收獲更多的喝彩和掌聲,她深知,她的身體依然需要火淬冰蝕般的錘打。每一個(gè)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對(duì)生命的辜負(fù)。排練室最后一盞燈多數(shù)時(shí)間由余爾格來熄滅。“在舞蹈中,天賦要有,但努力更重要,因?yàn)榕褪且环N難能可貴的天賦。”
或許,在余爾格的身體里,有兩個(gè)她存在,一個(gè)溫柔,一個(gè)野性。傳統(tǒng)舞出身的余爾格,因?yàn)樯聿膵尚。J(rèn)為自己并不適合大型舞團(tuán),于是畢業(yè)后選擇留校任教,成為一名舞蹈老師。2009年,法國編舞家海蒂·瑪萊姆來到成都,與四川省歌舞劇院聯(lián)手重排經(jīng)典舞劇《春之祭》。本來演員都已選定,但余爾格自薦,要和演員們?cè)谂啪殨r(shí)一起即興表演,最終她獲得參加這部現(xiàn)代舞劇演出的機(jī)會(huì)。這次現(xiàn)代舞的表演給一直以傳統(tǒng)舞表演為主的余爾格帶來全然不同的藝術(shù)體驗(yàn),也促成她將自己的舞蹈事業(yè)重心轉(zhuǎn)向現(xiàn)代舞的決心。隨后一邊在校任教一邊在歐洲各地演出的她,對(duì)現(xiàn)代舞所具有的當(dāng)代精神與表演形式,有了更多的喜愛,于是產(chǎn)生出國深造的念頭。現(xiàn)代舞看似簡單,只要擅于表達(dá)自己,就可以跳得很動(dòng)人。但想要有所突破,不僅僅是技巧,更多是感悟、是思想、是傳達(dá)。它的魅力在于,沒有刻意的痕跡,卻能從彼此的喘息聲中,感受到作為一名現(xiàn)代舞者,對(duì)自身與他人靈魂更多的探索。無論是音樂還是肢體,就連赤裸的雙腳與地面摩擦?xí)r發(fā)出的聲音都有著生命的節(jié)奏,直逼人心。

舞蹈的種類有很多,共通點(diǎn)都是需要對(duì)身體具有很強(qiáng)的控制力和表現(xiàn)力。現(xiàn)代舞源于西方,是一種與古典芭蕾相對(duì)立的舞蹈派別。在中國,幾乎所有的現(xiàn)代舞舞者都是在傳統(tǒng)舞的基礎(chǔ)上,轉(zhuǎn)型至現(xiàn)代舞表演。如果說傳統(tǒng)舞需要一種含蓄內(nèi)斂的情緒在舞臺(tái)上表達(dá),那現(xiàn)代舞剛好相反,它脫離固定的動(dòng)作規(guī)范,用一種更為自由奔放的肢體語言展現(xiàn)著舞蹈的魅力。余爾格最初接觸現(xiàn)代舞時(shí),發(fā)現(xiàn)自己能在兩種舞種之間自如地切換,她覺得很有意思。但隨著對(duì)現(xiàn)代舞表演的理解不斷深入,兩種情緒漸漸在她體內(nèi)模糊混淆。她琢磨著其間原因,同時(shí)跳兩個(gè)舞種不是不可以,只是傳統(tǒng)舞和現(xiàn)代舞從技巧、表現(xiàn)力、審美方式等方面都各不相同,如果想要認(rèn)真專注地把舞跳好,只能擇其一。深思熟慮之后余爾格最終選擇了現(xiàn)代舞。
跳舞的第一位是感染自己,然后再通過自己的肢體表達(dá)去帶動(dòng)他人。一個(gè)人在舞蹈過程中,他的下肢是基礎(chǔ),上身是外在表現(xiàn)。下肢的功底越扎實(shí),那么上身就有更多的展示空間。如果用動(dòng)作比作血肉,那情緒永遠(yuǎn)是舞蹈的靈魂。沉浸角色,帶入情緒,演員必須把自己變成角色。走路時(shí)思考角色會(huì)怎么走,洗漱時(shí)看著鏡子,想象角色會(huì)怎么哭。余爾格的身體能力很強(qiáng),但更重要的是她通過恰當(dāng)?shù)闹w表現(xiàn)傳達(dá)出自身的情緒,并試圖使觀者受到感染,如果能與她的舞蹈共情,就算得上是一名舞者的幸福。“舞者在舞臺(tái)上的生命力和感染力,是會(huì)讓臺(tái)下的人不自覺地起雞皮疙瘩。我欣賞這樣的舞者,也希望自己能擁有這樣的能力。”余爾格道。現(xiàn)代舞屬于小眾舞種,盡管這幾年隨著電視節(jié)目的推廣讓它在不斷“破圈”,但大部分的觀眾表示對(duì)它還是有“看不懂”的第一印象。現(xiàn)代舞舞者就像舞臺(tái)上飄揚(yáng)的云彩,如何欣賞現(xiàn)代舞,就像看這些云彩,它們漂浮、聚散,我們看到的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感受到什么。“藝術(shù)需要百花齊放,不能太單一化,不要因?yàn)榭床欢陀X得它離自己很遠(yuǎn)。堅(jiān)持做自己的東西,總會(huì)有人懂”。對(duì)于舞者來說,現(xiàn)代舞不是屬于某一地域的舞蹈,而是屬于每個(gè)個(gè)體的舞蹈,應(yīng)該找到屬于自己的身體語言。即便小眾,余爾格始終堅(jiān)信現(xiàn)代舞在未來會(huì)變得越來越好,

關(guān)于舞 從肢體到意識(shí)的覺醒
余爾格長期往返國內(nèi)外,生活的歷練使她對(duì)藝術(shù)的體悟有了更多畫面感,對(duì)舞臺(tái)設(shè)計(jì)也有了一些想法,她想將這些積累轉(zhuǎn)化成舞蹈創(chuàng)作以此表達(dá)自己對(duì)于這個(gè)世界的觀念。她不再只站在表演者的位置,而是以一個(gè)創(chuàng)作者的身份,大膽開啟自己的編導(dǎo)之路。2016年,余爾格創(chuàng)作了第一部現(xiàn)代舞劇《偶然》。舞劇中創(chuàng)新的藝術(shù)形式和嫻熟的舞蹈動(dòng)作都恰到好處,沒有宏大的敘事和厚重的歷史,只有余爾格所引領(lǐng)的一批舞者對(duì)靈魂的探尋,并被觀眾們稱之為有著“清水煮白菜”一樣的干凈。身為編導(dǎo),排練中余爾格一邊解讀劇本,一邊用有節(jié)奏感的數(shù)字展示舞蹈的每一個(gè)動(dòng)作,然后像數(shù)學(xué)公式一樣拆分和組合,實(shí)現(xiàn)串聯(lián)。這種特別的方式源自一種“數(shù)字身體”的理念,通過一些有邏輯的數(shù)字構(gòu)成的動(dòng)作組合,完成一段完整的表演。在這部現(xiàn)代舞劇里,余爾格通過“行、遇、離”三個(gè)部分,身著不同服裝的不同個(gè)體,以豐富的肢體語匯,講述著人從陌生到熟悉,經(jīng)歷了打量、試探到熟悉的過程。它還綜合了音樂、舞美,利用光影藝術(shù)營造的舞臺(tái),打破時(shí)間與空間的維度,講述著一首詩的背后,人與人之間的交織關(guān)系。每個(gè)人都是獨(dú)立的,處在人群之中,又從來不是孤立的,仿佛身在眾人之間,又一直是孑然自處,只身來,只身去。三年后她創(chuàng)作了第二部個(gè)人編創(chuàng)舞劇《時(shí)輪》。作品從個(gè)人和女性視角出發(fā),匯集無數(shù)碎片化的人生片段,生命、人性、欲望、性別、回歸等正在發(fā)生的主題從時(shí)間齒輪的輪轉(zhuǎn)中投下側(cè)影,最終又回歸到時(shí)間的流逝之中。多維時(shí)空重疊、夢與現(xiàn)實(shí)交織的舞臺(tái)上,氣質(zhì)豐富多變的音樂下,肢體跟隨著節(jié)奏共振。在可控和未知的間隙里,不確定性依附著肢體技巧,也對(duì)抗著“框架”與技術(shù)。余爾格認(rèn)為,肢體技巧要服務(wù)于想表達(dá)的內(nèi)容,關(guān)鍵在于取舍和平衡。余爾格喜歡暗黑基調(diào)的作品,她的《時(shí)輪》開始于很多畫面,慢慢地把這些畫面發(fā)散,就逐漸形成《時(shí)輪》。層疊的人生圖景中有參與者也有旁觀者,還有著流動(dòng)在邊界的游離者,生活在時(shí)間的流逝下產(chǎn)生的不同經(jīng)歷和變化,自我與他人,神性與人性,死亡與重生,以及輪轉(zhuǎn)著的流動(dòng)著的生命,透著一種人與人之間的疏離感、蠻荒感和宿命感。這似乎是永恒在發(fā)生,開始并結(jié)束的關(guān)系和故事,一切都在“時(shí)輪”之中。此外,她還與譜造司、一出劇場一起聯(lián)合制作原創(chuàng)多媒體交互式現(xiàn)代舞作品《流》;作為客座編舞為中國香港舞蹈團(tuán)編導(dǎo)和表演的作品《Jing》等。無論是做一名舞者還是編導(dǎo),各自都有不同的難度。相對(duì)而言,舞蹈更簡單一點(diǎn),跳舞時(shí)的余爾格只需將自己舞蹈的部分跳好就行。但編導(dǎo)不同,它需要具備很強(qiáng)的與人溝通和處理問題的能力。除了把握舞蹈演員和作品質(zhì)量,還得掌控?zé)艄狻⒁魳贰⑽杳赖榷鄠€(gè)方面,才能讓一個(gè)完美的作品在自己手下豐滿成型。


《Moli》

《流》

《時(shí)輪》

《夜鷹》
余爾格的作品里總帶著不同的表達(dá),從中還能看到一絲行為藝術(shù)的色彩。2019年,余爾格獲得法國巴黎國際城市藝術(shù)駐留cité Internationale des art的機(jī)會(huì),她要求自己一定拿出點(diǎn)什么東西來,于是,她把自己關(guān)在房間里,一個(gè)人對(duì)著攝影機(jī),不斷地跳,整整三個(gè)月,有了獨(dú)舞短劇《Moli》。這是一部由她自導(dǎo)自演的肢體獨(dú)角戲,講述一個(gè)女人的暮年與青春的自我對(duì)話。余爾格從自我出發(fā),從一個(gè)女人出發(fā),以倒敘的方式,從暮年到年輕,以及一些回憶,講述一個(gè)女人的一生。這是一出視覺化,且充滿詩意、富有節(jié)奏的表演。從巴黎駐留回到成都后,《Moli》又入選北京青年國際戲劇節(jié)、深圳雙年展等演出,余爾格對(duì)其進(jìn)行重新編排,在集火藝術(shù)空間以直播的方式再次上演。她喜歡這樣以另一種“觀賞”角度對(duì)作品進(jìn)行的二度創(chuàng)作,再次的打磨使得新的感覺不斷涌現(xiàn)。

去年,經(jīng)過在A4國際駐留藝術(shù)中心的三個(gè)月駐地創(chuàng)作,余爾格的肢體戲劇作品《夜鷹》在第二屆麓湖社區(qū)藝術(shù)季首演。“夜鷹(nighthawk)”意指在夜晚行動(dòng)的人。這部作品的名字來源于愛德華·霍普的一幅同名油畫。受海明威作品《殺手》的啟發(fā),霍普復(fù)刻了小說中幾位殺手挾持餐廳里的服務(wù)生,等待“獵物”出現(xiàn)的場景。《夜鷹》創(chuàng)作的初期,余爾格實(shí)地走訪黑盒子空間、南坡草坪旁的山丘與施工現(xiàn)場,這些場地都曾帶給她許多靈感。比較特別的體驗(yàn)是走到成都麓湖社區(qū)的“麓營地”時(shí),她注意到陽光折射下自己在玻璃窗上的光影,那些關(guān)于人性與社會(huì)的記憶碎片或是想象的畫面開始在腦海中呈現(xiàn),《夜鷹》的劇作由此逐漸成型。在余爾格的劇場,15扇“櫥窗”穿插于不同的情景之中,時(shí)而是映射社會(huì)或窺探他人的鏡子,時(shí)而是欲望訴諸的窗口。玻璃窗不再是隔閡,而是一次盛情的邀請(qǐng):當(dāng)觀眾身臨《夜鷹》的劇場,在與演出者產(chǎn)生情緒的共鳴時(shí),又或是在安靜的間隙里窺見現(xiàn)代生活中人的迷惘時(shí),不由得深思——“櫥窗”內(nèi)外,誰又不是孤獨(dú)的夜行者。這個(gè)作品也被受邀2022年阿那亞戲劇節(jié)。
余爾格將絕大部分的時(shí)間留給舞蹈,生活中的她也有著閱讀的習(xí)慣。包里隨時(shí)都會(huì)裝著一本書,閑暇之余就拿出來翻讀幾頁。她閱讀的范圍很廣,既有經(jīng)典的《紅樓夢》,也有關(guān)乎探討與現(xiàn)實(shí)的《月亮與六便士》《百年孤獨(dú)》《城堡》等,它們給予她看待世界的不同視角,在這個(gè)浮躁的社會(huì)中慢慢變得從容淡定,不斷重新審視著社會(huì)、生活、工作等一些或宏大、或細(xì)微的議題。她也喜歡通過電影、音樂、裝置等多元化的藝術(shù)方式,培養(yǎng)自己的審美。在她看來,藝術(shù)是相通的,她從中汲取靈感和經(jīng)驗(yàn),從一個(gè)看客的角度思考別人是如何表現(xiàn)美、傳達(dá)美。
如果用一段關(guān)系形容自己和舞蹈的關(guān)系,余爾格給出的答案是——親密的朋友。肢體表達(dá)作為人類最初始的語言,她會(huì)每天去思考它、和它溝通,這樣無論是以舞者還是編導(dǎo)的身份,都可以通過自己或他人用足尖的藝術(shù)去傳達(dá)思緒和情感。她從不把自己框定在一個(gè)舞蹈家或是藝術(shù)家的范疇,畢竟破繭成蝶,是一條漫長而美妙的路。她相信,如果自己是一個(gè)好的舞者或是編導(dǎo),那自然而然會(huì)成為一名好的藝術(shù)家。擁有跳舞者身體、編舞者大腦的余爾格,當(dāng)下在她自己編織的夢里,用盡全力地活出生命的豐盈,成為自己,創(chuàng)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