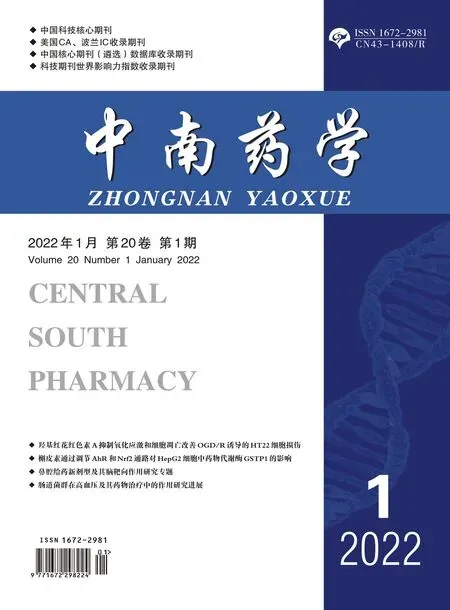腸道菌群在高血壓及其藥物治療中的作用研究進展
陳慧青,羅建權,龔金玉,邢開,彭思銀(中南大學湘雅二醫院,.藥學部;2.腫瘤中心,長沙 400)
高血壓是臨床上常見的心血管疾病,也是心腦血管和腎臟疾病的重要誘發因素。隨患病率不斷上升,高血壓已成為全球公共衛生問題[1]。高血壓的發病機制復雜,涉及因素眾多,如遺傳因素和環境因素。近40年來,降壓藥(如β受體阻滯劑、鈣通道阻滯劑、血管緊張素轉換酶抑制劑和血管緊張素受體阻滯劑等)的廣泛使用使高血壓患者的血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根據2018版中國高血壓防治指南,我國高血壓的治療率和控制率仍較低,分別為45.8%和16.8%[2]。其中,多種因素影響著血壓調節。腎素-血管緊張素-醛固酮系統在血壓調節中發揮重要作用,血管緊張素Ⅱ可以引起短暫的血壓升高,還可促進醛固酮的合成,誘發水鈉潴留,導致血壓水平進一步升高[3-4];巨噬細胞極化可通過促進炎癥反應,刺激交感神經,引起血壓升高[5]。此外,離子通道的狀態也可改變神經元的興奮性,影響神經元的信號傳導,調節血壓水平[6]。隨著近年來人們對腸道菌群與高血壓疾病的深入研究,腸道菌群及其代謝衍生物可能成為調節血壓的重要因素,如短鏈脂肪酸(short-chain fatty acids,SCFAs)和三甲胺-N-氧化物(trimethylamine-Noxide,TMAO)[7]。同時,腸道菌群被視為人體的 “隱形器官”,在藥物代謝中發揮的作用備受關注[8]。腸道菌群是藥物吸收的重要場所,其可能參與高血壓的藥物治療,改變藥物療效,間接影響血壓調節。因此,為了探索腸道菌群對血壓的影響,本文對腸道菌群與高血壓及抗高血壓藥物的相關研究進行論述。
1 腸道菌群對高血壓的影響
腸道菌群的結構組成與血壓調節有著密切聯系。人類腸道分布著1000 多種微生物,數量達1014級。其中,厚壁菌門和擬桿菌門占菌群總數的80%~90%,厚壁菌門與擬桿菌門的比值(firmicutes/bacteroidetesratio,F/B)是菌群失調的重要指標[9]。研究發現,高血壓患者的腸道菌群會出現豐富度下降、菌群數量減少及F/B 增加等特征[10]。例如,Yang 等[11]對自發性高血壓大鼠(spontaneously hypertensive rats,SHR)進行分析,SHR 腸道菌群的豐度、多樣性及均勻性都顯著降低,F/B 比率增加。這一結論不僅在動物實驗得到驗證,在臨床試驗中也充分得到了證實。Li 等[12]對41 名健康對照組、56 名高血壓前期患者和99 名原發性高血壓患者的腸道菌群進行宏基因組和代謝組學分析,結果高血壓患者的腸道菌群豐富度和多樣性顯著降低,菌群的結構組成發生改變,如普氏菌和克雷伯菌的數量增加。為了進一步研究高血壓與腸道菌群的關系,研究者將高血壓患者糞便中的菌群移植到無菌小鼠體內,發現小鼠血壓顯著升高,表明腸道菌群直接影響著血壓調節。
腸道菌群的代謝衍生物SCFAs 和TMAO 在血壓調節中也扮演著重要角色。SCFA 是腸道菌群重要的代謝衍生物,其主要有乙酸、丙酸和丁酸等[13]。據報道,高血壓患者的腸道菌群會出現菌群失調現象,同時其腸道代謝衍生物的含量也會發生改變,如SCFA 減少[14]。在一項針對SHR的研究中,腸道菌群的F/B 比值增加,而長期服用SCFAs 逆轉F/B 比值,降低了血壓水平[11]。從機制上分析,SCFAs 可以刺激宿主G 蛋白耦聯受體(G protein-coupled receptor,GPR)調節血壓,如G 蛋白耦聯受體41(G protein-coupled receptor 41,GPR41)和嗅覺受體78(olfactory receptor 78,Olfr78)。研究發現,GPR41基因敲除小鼠患有單純的收縮期高血壓,表明SCFAs 可以通過作用于大血管的平滑肌細胞和腎臟表達的GPR41 降低血壓[15];Olfr78 主要在腎傳入小動脈和外周血管系統中的平滑肌細胞中表達,SCFAs 可以通過激活血管Olfr78 調節血壓,增加腎素釋放,升高血壓[16]。此外,腸道菌群中的脂質代謝物TMAO 對血壓調節也有重要影響。飲食中的磷脂酰膽堿、左旋肉堿及甜菜堿經腸道菌群轉化為三甲胺,在黃素單加氧酶家族氧化作用下形成TMAO[17],研究發現單獨注射TMAO 不會影響大鼠血壓,但合用低劑量血管緊張素Ⅱ可延長血管緊張素Ⅱ的升壓效應,升高血壓[18](見圖1)。

圖1 腸道菌群代謝衍生物調節血壓的機制Fig 1 Mechanism of gut microbiota metabolites on blood pressure regulation
2 腸道菌群與抗高血壓藥物[19-44]
腸道菌群和抗高血壓藥物存在復雜的相互作用。腸道菌群的代謝能力與肝臟相似,都具有較高代謝活性[19]。藥物口服后在胃腸道接觸大量的腸道菌群[20],腸道菌群可產生一系列具有催化代謝作用的特異性酶(氧化還原酶、水解酶和轉移酶等)改變藥物成分結構,從而激活、滅活或重新激活藥物[21]。這些酶也參與了藥物代謝的相關反應,如水解、還原、乙酰化、脫氨和脫羧等反應,影響藥物吸收、分布、代謝過程[22];腸道菌群中代謝衍生物(SCFA、膽汁酸、吲哚衍生物)也具有代謝宿主藥物的潛力,影響藥物藥代動力學。腸道菌群可以通過特異性酶和代謝衍生物對口服藥物進行生物轉化,最終影響藥物的毒性和藥效。此外,藥物進入體內后也可能改變腸道菌群的組成比例,對其結構和代謝產生重要影響[23]。例如,肥胖小鼠給予羥基紅花黃色素A 后,小鼠腸道中乙酸、丙酸和丁酸的含量以及產SCFA 菌的數量增加[24]。因此,藥物在體內的生物轉化與腸道菌群會相互影響。一方面,腸道菌群能代謝藥物,影響藥物的生物利用度和毒性;另一方面,藥物可以改變腸道菌群的結構組成,影響腸道菌群的營養代謝狀況[25]。
經典的降壓藥主要有鈣離子拮抗劑、血管緊張素Ⅱ受體拮抗劑、血管緊張素轉換酶抑制劑和β受體阻滯劑等。不同種類的降壓藥在降低血壓的機制上存在著差異,它們與腸道菌群的相互作用也不同,下面將介紹腸道菌群和一線降壓藥的相互關系(見表1)。

表1 抗高血壓藥物-菌群相互作用Tab 1 Interaction between antihypertensive drugs and microbiota
2.1 鈣離子拮抗劑
2.1.1 氨氯地平 氨氯地平是典型的鈣通道阻滯劑,是治療高血壓常用的處方藥之一。氨氯地平在胃腸道吸收相對較好,口服生物利用度約為60%[26]。氨氯地平在體內主要經肝臟代謝酶代謝為吡啶代謝物,再經氧化脫氨、脫酯和脂肪族羥基化等反應進行藥物代謝[27]。最近一項體外研究報道,除了肝臟代謝酶,腸道菌群也可能參與了氨氯地平的代謝。研究者將氨氯地平與人和大鼠糞便一起孵育,發現隨著孵育時間增加,吡啶代謝物逐漸增加,殘留的氨氯地平含量減少。在孵育24 和72 h 后,殘留的氨氯地平分別減少了8.9% 和21.3%,表明腸道菌群可能參與氨氯地平的生物轉化,影響了其藥代動力學。隨后,通過抗菌藥物與氨氯地平聯合給藥,發現口服氨芐青霉素可增加氨氯地平的生物利用度。因此,抗菌藥物可能影響腸道菌群,減少腸道微生物群對氨氯地平的代謝,最終提高藥物的生物利用度[17]。
2.1.2 硝苯地平 硝苯地平是二氫吡啶鈣通道阻滯劑,主要用于治療心絞痛、高血壓等心血管疾病。硝苯地平是一種非極性藥物,可被人體胃腸道吸收[28]。在此過程,腸道菌群極有可能參與硝苯地平的生物轉化,改變藥物生物利用度及療效[29]。張娟紅等[30]探究腸道菌群與硝苯地平代謝的關系,分別以對照組和抗菌藥物處理組的大鼠糞便提取液為基質,加入等量硝苯地平,均勻混合后進行避光孵育。在相等的時間間隔內取出孵育后的提取液進行分析,孵育12 和24 h 后,硝苯地平組和抗菌藥物+硝苯地平組中硝苯地平的含量減少,說明糞便中的腸道菌群參與了硝苯地平的代謝。此外,抗菌藥物處理組中硝苯地平的含量下降更為緩慢。孵育24 h 后,硝苯地平組剩余量為0.0396 μmol·L-1、抗菌藥物處理組為0.0504 μmol·L-1,表明經抗菌藥物處理后,腸道菌群減慢了對硝苯地平代謝。由此而知,腸道菌群參與硝苯地平進入血液循環前的代謝,使其含量減少,表明腸道菌群可通過影響硝苯地平的生物利用度,從而影響藥物療效。
2.2 血管緊張素Ⅱ受體拮抗劑(氯沙坦)
氯沙坦是典型的血管緊張素受體阻滯劑,是常用的降壓藥。氯沙坦的降壓作用與腸道菌群密切相關。總所周知,F/B 是高血壓患者腸道失調的標志[6],SHR 的F/B 高出Wistar-Kyoto(WKY)大鼠約3 倍,但氯沙坦治療可以使SHR腸道中F/B 恢復到與WKY 大鼠相似的水平;與WKY 大鼠組相比,SHR 的腸道菌群中Verrucommicrobiaceae、Pedobacter 和Akkermansia 數量顯著減少,而Lactobacillaceae 和Lactobacillus 的數量增加,氯沙坦治療也恢復了這些菌群的結構組成;氯沙坦治療還增加了SHR 中產生乙酸酯和丙酸的細菌數量。因此,氯沙坦治療通過改善SHR腸道完整性和恢復腸道菌群的穩態來調節血壓。此外,氯沙坦治療可促使α-防御素生成,減少SHR 腸道功能障礙。這種作用似乎與其減少腸道內交感神經驅動、改善腸道完整性的能力有關。氯沙坦引起腸道菌群變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保護血管和降低血壓[31]。
2.3 血管緊張素轉換酶抑制劑
2.3.1 卡托普利 卡托普利是第一代血管緊張素轉換酶抑制劑,通過抑制腎素-血管緊張素-醛固酮系統來降低血壓,從而逆轉腸道病理[32]。為了探究卡托普利與腸道菌群之間的關系,Yang等[33]用卡托普利給SHR 和WKY 大鼠治療4 周,停藥16 周后,發現卡托普利對腸道微生物的組成、腸道通透性和病理及后腦活動具有重大而持久的影響。SHR 經卡托普利治療后,血壓下降并且細菌孢量增加。與WKY 大鼠相比,治療至第4 周的SHR 的Firmicum、Proteobacteria 和Tenericum 等顯著富集且Bacteroides 減少,SHR的腸道菌群均勻性增加。停藥后,SHR 中的腸道菌群仍存在均勻性增加的趨勢。此外,該研究也表明卡托普利可以改善腸道病理和腸道通透性,由此推測其他血管緊張素轉換酶抑制劑降低血壓也可能會改變腸道菌群結構組成。
2.3.2 貝那普利 貝那普利是第二代血管緊張素轉換酶抑制劑,廣泛用于治療高血壓和充血性心力衰竭[34]。徐興華等[35]比較了SHR 組、WKY 組和SHR 貝那普利治療組的糞便,發現貝那普利治療與腸道菌群有密切關系。與WKY 大鼠相比,貝那普利治療后的SHR 腸道菌群的結構組成發生了變化。從門水平分析,貝那普利治療降低了SHR 腸道中Proteobacteria 的比例;從屬水平分析,SHR 腸道中Streptococcus 屬多于WKY 大鼠,而貝那普利治療減少了SHR 腸道中Streptococcus 屬的數量。分析Ace 指數、Category 指數、Simpson指數和Chao1 指數發現,貝那普利干預后對SHR腸道微生物群落的豐富度和多樣性有良性影響,說明貝那普利在一定程度上能促進SHR 腸道菌群結構的恢復,從而降低血壓[35]。
2.3.3 依那普利 依那普利是典型的血管緊張素轉化酶抑制劑,是治療心血管疾病的重要藥物,可顯著降低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有研究表明,SHR 血漿中TMAO 水平顯著高于WKY 大鼠。經過依那普利治療后,SHR 血漿TMAO 水平卻顯著降低[36]。血液中的TMAO 主要來自腸道微生物(Clostridium、Collinsella、Desulfovibrio 和Lactobacillus 等)的新陳代謝[37],所以依那普利可能影響了腸道菌群的組成比例。為了證實依那普利與腸道菌群之間的關系,Konop 等[38]將Wistar 大鼠分為依那普利治療組和自來水對照組進行研究,發現腸道菌群組成在兩組差異不大。與對照組相比,依那普利治療組大鼠腸道內Collinsella 含量稍降低,而Clostridium 略微增加。通過數據分析,所有實驗組中均表現出相似的多樣性。此外,24 h 后,依那普利治療的大鼠尿中TMAO 排泄增加,推測依那普利很可能參與控制尿排泄,參與控制尿中甲胺類的排泄。同時,依那普利還可能通過影響腸道菌群的代謝活動來降低TMAO 水平[38]。
2.4 β 受體阻滯劑(美托洛爾)
美托洛爾是一種β受體阻滯劑,與阿替洛爾調節血壓的機制相似。美托洛爾主要通過可飽和的代謝途徑,通過肝細胞色素2D6(CYP2D6)進行代謝。除許多內源激素外,它還負責約25%外源生物的代謝。美托洛爾和相關代謝物主要從尿中排出。Brocker 等[39]對服用了美托洛爾患者的尿液進行代謝組學數據分析,發現馬尿酸、羥基馬尿酸和甲基尿酸水平含量升高,這3 種化合物被認為是腸道菌群的代謝產物。其中,馬尿酸是腸道菌群多樣性的代謝組學標志物,羥基馬尿酸是腸道菌群衍生的終產物,兩者均源于腸道菌群的多酚代謝。這些化合物反映腸道菌群的組成,而服用美托洛爾的患者中這3 種化合物均顯著升高[40],說明美托洛爾長期治療可能會影響胃腸道內的微生物組成和多樣性。此外,對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血管疾病患者糞便樣本的宏基因組學分析,美托洛爾治療與宏基因組連鎖群(MLG)的變化成正相關[41]。提示,該藥物可能通過影響腸道微生物組中基因表達來影響微生物組。
以上幾種典型的降壓藥與腸道菌群之間的研究表明,腸道菌群的變化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藥物代謝,從而影響藥物吸收,甚至改變藥物藥理效力。同時,藥物的代謝過程也會影響腸道菌群的結構組成和數量變化。
3 總結
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腸道菌群參與高血壓的發生、發展和維持,對血壓調節有至關重要的作用。Yan 等[42]通過糞便移植實驗表明腸道菌群異常是引起高血壓疾病的關鍵原因,而不是高血壓導致的結果或伴隨現象。因此,在后續的研究中,研究者應多關注高血壓患者的腸道菌群的組成和結構的變化,可以通過益生菌療法、糞便移植技術和抗菌藥物使腸道菌群恢復到穩態。此外,腸道菌群的代謝衍生物也可能成為未來治療高血壓的重要方向。目前,高血壓與腸道菌群的研究還有待深入,并且需要考慮將腸道菌群這一因素運用到高血壓的臨床治療。
藥物治療是高血壓疾病的重要治療途徑,腸道菌群與抗高血壓藥物的關系也得到了廣泛的關注。基于大量的體外和動物體內實驗,本文總結出腸道菌群與抗高血壓藥物的相互關系,且這種相互關系對藥效產生重要作用。隨著研究的深入,也面臨一些挑戰,腸道菌群和藥物的研究主要基于動物研究,缺少臨床試驗研究。而在實際的臨床治療中,聯合用藥的治療策略可能會干擾對單一藥物的研究。例如,曹曉紅等[45]研究藥物對糖尿病患者腸道菌群是否有影響,發現和單用磷酸西格列汀患者相比,聯合應用阿卡波糖患者的腸道菌群數量和球菌桿比值都顯著升高。在高血壓的藥物治療中,抗高血壓藥物也常與多種藥物聯合用藥,如抗菌藥物,將干擾抗高血壓藥物研究的結果的準確性。其次,動物實驗的結果推及人的結果不一定相同,如同人體的腸道菌群之間存在一些差異,動物及不同動物品系和人腸道菌群同樣存在差異。因此,僅通過16sRNA、代謝組學和基因測序等手段不足以分析腸道菌群與藥物代謝之間的機制,需要運用分子生物學、藥理學和毒理學等多學科的研究手段進行綜合分析,獲取更低毒性和更好藥效的藥物,推進藥物合理使用。最后,在結合臨床用藥時,臨床醫師也需要考慮到腸道微生物對藥物代謝的影響,這對于指導臨床合理用藥和改善高血壓患者的預后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