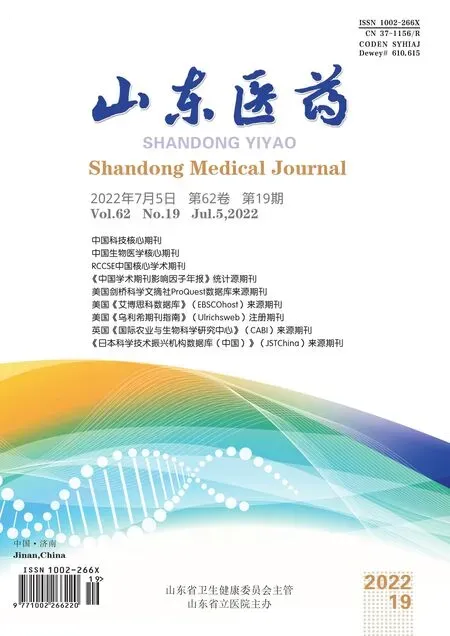血漿激活素-A水平對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患者預后的預測價值
趙瀅,韓婧
貴州省人民醫院呼吸與危重癥醫學科,貴陽 550000
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ARDS)是臨床常見病,每年發病率為78.9/100 000[1]。全球ARDS 患者占所有ICU 入院人數的10.4%,總病死率為35.3%[2]。盡管幾十年來一直在進行ARDS 相關的研究,但仍有一系列問題尚未解決。危重癥患者評分系統如急性生理與慢性健康評分Ⅱ(APACHE Ⅱ評分)或肺損傷嚴重程度評分可評價患者的預后,但未能對特定疾病過程患者群體的死亡風險提供一致和準確的預測性估計[3]。采用可靠的生物標志物進行ARDS患者預后分層可優化患者治療方案及預后判斷[4]。激活素(ACT)是由抑制素的兩個亞單位通過二硫鍵連接而成的二聚多肽,屬于生長和分化因子的轉化生長因子(TGF)超家族。目前已在哺乳動物中分離出五種亞單位類型,包括ACT-A、ACT-B、ACT-AB、ACT-C、ACT-E,但只有ACT-A、ACT-B、ACT-AB 具有明確的生物學活性[5]。研究證實,血漿ACT-A 水平是膿毒癥嚴重程度的預測指標,也是膿毒癥危重患者預后的評估指標。膿毒癥早期血漿ACT-A 水平與ICU 入院時的預后指標及ICU 病死率相關[6]。據報道,ARDS 患者支氣管肺泡灌洗液(BALF)中ACTA 水平升高[7]。在臨床工作中,血漿比BALF 更易獲得,然而目前有關血漿ACT 水平與ARDS 患者死亡的關系尚不清楚。因此,本研究探索血漿ACT-A 水平對危重患者ARDS預后的預測價值。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選擇本院2020 年1 月—2021 年12月收治的ARDS 患者53 例,均符合ARDS 柏林定義診斷標準[8],其中男17 例、女36 例,年齡48~87 歲;入院28 d 死亡28 例(死亡組)、存活25 例(存活組)。排除標準:年齡<18 歲;接受免疫抑制劑或長期接受糖皮質激素治療;確診或可疑惡性腫瘤病史;已納入其他研究。本研究經貴州省人民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2020)455],患者或其家屬知情同意并簽署同意書。
1.2 臨床資料收集 收集患者病歷資料,主要終點事件設置為入院28 d 死亡[9]。于患者出院或死亡時完善各項信息,包括年齡、性別、基礎疾病情況、APACHE Ⅱ評分、簡明急性生理學評分Ⅱ(SAPS Ⅱ)評分、氧合指數、機械通氣、呼氣末正壓(PEEP)及WBC、PCT、CRP、N 等。根據序貫器官衰竭的檢測評分評估患者器官衰竭情況,統計感染性休克、急性腎功能衰竭、肝功能衰竭、凝血功能障礙等發生情況。
1.3 血漿ACT-A檢測 ARDS患者入住RICU第1天,抽取外周血5 mL,于4 ℃下3 000 r/min(半徑10 cm)離心15 min,留取血漿凍存于-80 ℃冰箱。用酶聯免疫吸附法測定血漿ACT-A,采用英國Abcam 公司人Activin-A ELISA檢測試劑盒。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19.0 統計軟件。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用±s表示,比較采用t檢驗;不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用M(P25,P75)表示,比較采用秩和檢驗。計數資比較采用χ2檢驗或Fisher檢驗。繪制受試者工作特征(ROC)曲線,用曲線下面積評價各指標對ARDS患者死亡的預測價值。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臨床資料比較 見表1。

表1 兩組臨床資料比較
2.2 ACT-A 及其他相關指標對ARDS 患者死亡的預測價值 各指標對ARDS患者死亡預測的ROC曲線下面積排序從高到低依次為SPAS Ⅱ評分(0.789)、APACHE Ⅱ評 分(0.772)、氧 合 指 數(0.719)、WBC(0.689)、CRP(0.685)、PCT(0.680)、ACT-A(0.660)。ACT-A 的曲線下面積小于SPAS Ⅱ評分、APACHE Ⅱ評分、氧合指數(P均<0.05),與PCT、CRP、WBC 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均>0.05)。見表2。

表2 各指標對ARDS患者死亡的預測價值
3 討論
ACT-A 是轉化生長因子-β(TGF-β)超家族的成員之一,是影響細胞發育和功能的多效性調節因子[10]。ACT-A在人類疾病(系統性紅斑狼瘡、類風濕性關節炎和肺泡蛋白沉積癥等自身免疫性疾病、過敏性哮喘和特應性皮炎、癌癥和微生物感染)的發生發展中具有重要作用[11]。ACT-A在小鼠氣道中的過度表達導致了小鼠肺部急性肺損傷。此外,ARDS患者支氣管肺泡灌洗液中ACT-A 水平也明顯高于對照組[7]。研究表明,ARDS患者血漿ACT-A水平升高[12],ACT-A在急性炎癥、炎癥晚期和氣道重塑中也起重要作用[13]。評估ACT-A 對ARDS預后的預測價值,可為臨床診治提供參考。
SPAS Ⅱ評分、APACHE Ⅱ評分對重癥患者預后的判斷有一定意義[14]。本研究死亡組與存活組SPAS Ⅱ評分、APACHE Ⅱ評分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這兩項常用的評分可快速對重癥患者預后進行初步預判。嚴重低氧的ARDS 患者搶救及治療依賴機械通氣,機械通氣后氧合指數仍較低的患者甚至需要體外膜肺氧合治療[15]。本研究死亡組與存活組氧合指數、機械通氣時間、PEEP 水平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這與ARDS 病情嚴重程度相關。患者肺部病變越嚴重,PEEP 就越高。但研究表明,用高PEEP 及高壓肺復張策略治療的ARDS 患者病死率高于常規治療組,提示高PEEP 策略并非所有ARDS 患者都能獲益[16],目前臨床較為推薦的方法是根據患者的肺順應性進行PEEP 的滴定設置合適的數值。研究證實,PCT、CRP 在判斷膿毒血癥、ARDS預后中具有重要意義[12]。WBC 特別是中性粒細胞在肺和肺泡腔中的積聚具有臨床意義[17]。活化的中性粒細胞和血小板在受損的肺組織中相互作用,形成中性粒細胞胞外陷阱、絲狀染色質纖維和中性粒細胞衍生蛋白的復合物,這可能有助于隔離病原體,但也會造成肺損傷[18]。本研究中,死亡組與存活組血漿PCT、CRP、WBC 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提示PCT、CRP、WBC 可以作為ARDS 患者預后判斷的指標。
近年來,由于新型冠狀病毒-19(COVID-19)的大流行,導致ARDS 患病率增加[16],ACT-A 水平升高與COVID-19 感染導致的ARDS 不良預后相關[19]。在多種炎癥反應中,血漿ACT-A 水平有助于評估炎癥反應中的器官功能,急性腎損傷的膿毒癥患者血漿ACT-A 水平明顯升高[20]。此外,在動物實驗中,干擾ACT-A 誘導的IL-6 分泌對癌癥導致的惡病質具有一定的治療潛力[21]。本研究檢測了入住RICU第1 天53 例ARDS 患者血漿ACT-A,死亡組與存活組血漿ACT-A 水平差異有統計學意義,ACT-A 對預測ARDS 預后有一定價值。目前的研究不僅局限于ACT-A 是否能作為臨床診斷ARDS 標志物,同時也在探討其是否能作為潛在的治療靶點。針對ACT-A異常表達引起的小鼠急性肺損傷/ARDS,使用中和ACT-A治療后,減輕早期的炎癥反應,促進了后期的組織修復[7]。在非典型冠狀病毒-2 感染的倉鼠模型中,通過阻斷ACT-A 信號傳導證實使用抗ACT-A 抗體不會使疾病惡化,并且沒有證據表明肺病毒載量和病理學增加。該研究表明,阻斷ACT 信號可用于治療COVID-19感染的ARDS的患者[19]。
既往研究顯示,ARDS 患者ACT-A 水平升高,但其水平與ARDS 預后的相關性較差[22]。本研究繪制ROC 曲線顯示,血漿ACT-A 預測ARDS 預后的曲線下面積為0.660,提示ACT-A對ARDS預后有一定預測價值。各指標對ARDS患者死亡預測的ROC曲線下面積排序從高到低依次為SPAS Ⅱ評分(0.789)、APACHE Ⅱ評分(0.772)、氧合指數(0.719)、WBC(0.689)、CRP(0.685)、PCT(0.680)、ACT-A(0.660)。ACT-A 較其他指標曲線下面積小,但ACT-A 是一個多功能的細胞因子,不僅可作為生物標記物,還是潛在的治療靶點。一項納入97例患者的研究中,ACT-A 對ARDS 死亡風險預測曲線下面積大于APACHE Ⅱ評分(0.591)[22]。兩個研究的差異考慮與樣本量均較少相關,需要更多大量的臨床研究證實ACT-A對ARDS預后的預測價值。
綜上所述,血漿ACT-A 可作為評估ARDS 患者預后的指標,為臨床治療ARDS 提供一個潛在的靶點,但預測效能較低。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糖皮質激素對TGF-β 水平有影響[23],而ACT-A 正是TGF-β 超家族成員,故研究排除了長期使用糖皮質激素的患者,但該類患者在急性感染后并發ARDS的風險更高。此外,未動態監測ACT-A 水平,研究表明ACT-A水平的波動與患者疾病預后有關[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