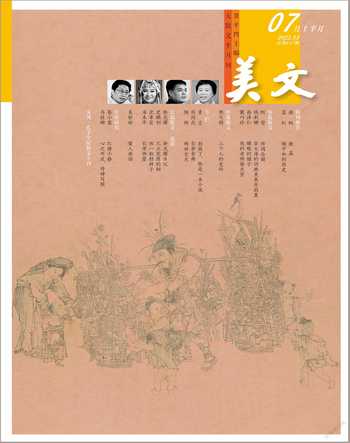徐光耀日記

徐光耀
早起聽警報機一響,急忙爬起來,披上衣服就往車站上跑,氣喘吁吁。剛剛跑到,火車已經進站了。一堆人從車上下來。風從南面卷來沙粒,我尋不著熟人。剛想戴上眼鏡,猛抬頭見廠民同志來了,后面跟著一個女同志。我急急把眼鏡裝入袋里,跑上前去和他握手,他的手握得很緊,使我感到溫暖。他跟我趕快到大會去報到,并穿衣服,說在車上凍壞了。
在下坡處,他給我介紹說那個女人就是丁玲同志,我忙點頭微笑,表示很幸運,她卻似睬也不睬。我想何以這樣冷淡呢?
陳企霞同志竟沒有來,叫人失望。聽說他到正定去了。
我帶廠、丁報到,看房子,洗臉之后,便回來學習。
早飯后,聽曹政委擴兵總結報告。
外面下著雨,下得很大,房上流著水,地下凈是泥。
晚飯后,踏著泥去廠民那里滿懷熱情地找他,掃興的是沒有見,估計往丁玲那兒去了。去吧,不認識,何況眼皮又那樣不高興抬一抬呢。不去吧,實在想念廠民、何洛同志。在門口躊躇很久,得問到一通信員,廠、何確實在里面。我斗膽進去,果然是冷冰冰的,正吃花生。坐在炕沿上聽他們說話,間或也插一二句,但,自己也覺得太無味。
總之,今日之晤見,很令人灰氣。
華大已經有了音院、劇院、美院,只無文院。現在丁玲、田間都在籌備成立文學研究院,并已由田間起草,送交黨委批去了。丁玲回來大概要著手辦這件事。
陳淼說他向丁玲把我提了一下,丁玲說消息不發表也可以寫信向組織上請求的,讓他們指名調可能性很小,主要看我自己的奮力爭取了。
丁玲的計劃非常之大,她用很大精力來搞這個所,她計劃一定要辦出些成績來,準備拿出幾百萬字給周總理。
陳淼說丁玲這人對事情非常認真負責,對青年特別關心熱情,感情很豐富。陳淼去鞍鋼就是她的主張。她臨上車去蘇聯了,還給陳淼打電話,祝他努力和成功!雖短短兩語,給陳淼鼓勵極大。
老天又賦予我一副凡事認真的脾氣。假如不去拼死拼活招架呢,也許不致累成這樣子。但脾氣使我即使娛樂也還不能吊兒郎當。
2點鐘,在課廳開會,田間說了一下明年第一季的教學計劃和編組。編組分為甲乙兩班,然后有互助組的形式為輔助。
之后,張天翼講了幾句。他病了還沒有好。開始一立起來,說話聲音很大,丁玲在一旁忙警告他道:“小聲點,小聲點。”——看,她就是這樣細微地體貼和關心著一個作家,生怕說得累了會觸犯他的病。——張天翼只強調大家好好學學辯證法和唯物主義。
最后,丁玲講話。講了一個多鐘頭,沒有人感到疲勞,聽來親切有趣,使你感到熱情的溫暖、鼓舞的力量!聽著,心就像放在熨斗上一樣,舒舒貼貼的。聽著,就像陶醉于勇敢雄壯的進行曲中,恨不能立即跳起來,前進,前進!不管她過去在生活上意識上有過什么缺點,而她的品質還是純潔的,尤其在專心致力于培養青年作家,在對青年人的熱情這一點上,更為可欽、可感!
她大致上談了五點:
1.我們都有個理想。我們被這理想鼓舞著,你們有,我也有。我們總覺得中國作品太少,可是,真的少嗎?并不。文藝雜志數十種,沒有誰可以全部看得過來。然而,沒有像這樣的作品,如我們看了《水滸傳》,就想去對人說李逵怎樣,武松怎樣。看了《紅樓夢》,大家就吵架,你愛黛玉,我愛湘云了。可是看了我們的書呢?常常說生活豐富,語言很好。但不久,也就把它忘記了。(寫到這,我不能不感到興奮,同時更感到慚愧和警惕地記下她這樣一段話。她說:“我們在人民大學去講演時就吹了,《平原烈火》比起西蒙諾夫的《日日夜夜》來,只差了一點點,只是這樣一點點,那就是人物周鐵漢還有點概念化。”)——她這段話,我必須立即確定對待它的態度和看法。不然,將對我產生極壞的影響和作用。她的話,只是用來鼓勵我(但仍是有些過火),也用來鼓勵諸位同學。她是在讓我更加勁,更虛心,兢兢業業去刻苦學習,創作真正像樣的作品。尤其人物刻畫,更要注意下苦功夫。如果把她的話理解為對我的一種估價,是一種表揚,因而趾高氣揚,突感身價十倍,因而盛氣凌人,覺得比別人都高一頭,竟也可以與西蒙諾夫拍拍肩膀,因而便驕傲自滿,看不起人,放松了對驕傲的警惕、對事業的刻苦追求,那便是大錯特錯,給自己堵塞光明,而頹向墮落,也嚴重地違背了丁玲的本來意思!——她繼續說:所以,我們每人都想出幾本好書。我開頭給人吹牛,文學研究所終了時,要寫出像《火光在前》《平原烈火》這樣五六本,這是太著急了。這是不可能的。研究員同志們也不少急著想寫東西,說我過去有生活,得這樣個環境和條件不容易,你們快幫助我寫出東西來吧。這也太急了,急是不行的。你們都還十分年輕嘛,哪有這樣快呢?像古鑒茲,睡了一覺起來,就想寫個長篇,就想當個成名作家,他今年才20歲,我的孩子也已20歲了呀(人們大笑)。這怎么行呢?我們主要是學習的,創作要搞,但不要搞得太多。不能希望創作出多少東西來的。那是吹牛!
2.主要靠自己學。單等人教是教條主義,有些東西是自己慢慢體會來的,不是教會的。如果教得會,整天請郭沫若、茅盾來給大家講,能講出幾十個作家來嗎?文學所的成立,就是給大家一個環境,一些條件上的方便。
3.要加強政治學習,不學這個是傻瓜。她說,他們沒有好好學不知吃了多少虧,走了多少彎路。下辛苦不小,卻弄不出東西(生活并不就是創作),就是因為看不見問題。她主張政治學習一定學好。她表示要堅決弄個政治教員來。
4.互相學習。她說:平常我們常說下鄉,跟群眾學習,到鄉村中找個老大娘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學了一點點。現在,我們為什么不找吳長英好好學習呢?為什么不找工人好好學習呢?互相幫助,互相愛護和關心,從幫助別人中學東西,在對別人的關心中獲得別人的幫助。
5.要批判地學。她主張要批評,要多談(談創作,不是清談),要直爽。直爽地批評,才是好批評,對人對自己有用的。她附帶批判了胡風的讀書主張“喜歡讀什么就讀什么”。她認為“要跨到新的時代來”,喜歡張恨水就不能去讀他,不能浪費那時間。學新文學史,就應該圍繞著找些“五四”以來的作品讀。讀書是應該有目的、有計劃、有重點的。胡風是詩人,感受力大,我們比不得他的。作品太強調主觀和感情也不對,應先考察一下自己的感情對不對。
最后她說:“我的脾氣,向來講話是沒有準備,扯到哪兒算哪兒。人們還愛聽,我就多講些,看著不大感興趣,我就不講了。我講的不一定對,你們大家也批判著聽。如果認為有些對呢,那你們就來偷取一點吧!不,送給大家吧!如果以為沒有什么對,那只當打了一場球。反正我是心里有什么說什么,即使你們得不到什么,也可以了解我這個‘人物’吧(逗得人們哈哈大笑,鼓掌散會)!”
經丁玲這一宣揚,《平原烈火》立刻有點兒轟動,李納就打聽哪個是徐光耀,歌焚忙指著我告訴她。潘之汀說前天還見一個青年學生問《平原烈火》出版沒有,他一直等,還未找到。別人也說是怎樣怎樣感動。晚上,李納竟問我是否平原省來的。——我對這些只好逃避和感到赧然!
來了,卻只有韓雪野一人,伴著來的有曾在四野當過政治干部的一位朝鮮翻譯(現在朝鮮大使館)。丁玲、陳企霞、田間、康濯、呂劍,大家直立,脫帽鼓掌。落坐后,韓先生要求隨便說,大家提問。這一點,我們全無準備。丁玲很機動,立即問了一下朝鮮作家在前線的情況,韓先生講了好大一陣。隨即又提出一個人民軍中的文藝活動問題,他又談了。于是,問題提不出,丁玲也應付不來了。怎么辦?韓先生要求大家都講一講。丁玲第一個便看到我,伸手招呼,叫我講一講。后來陳企霞也要我講,康濯也直點頭。丁玲并通過翻譯向韓先生介紹,說我從小在部隊長大,現在25歲,曾在華大學習過,是《平原烈火》的作者,那是一部很好的小說。韓先生居然也給予極大注意,把我的名字和書名登時記了下來。這之后,丁玲更催緊了,一定要我講。我說:“沒有準備呀!”她說:“向朝鮮人民致敬嘛!致敬,致敬!”我對致敬尤其沒有辦法,這一套是從不曾有過任何留心的。陳企霞就讓我講講自己的文學道路和經歷,這才稍稍鼓了一下勇氣。我想起了給蘇聯大使館寫的自傳和在天津文代會上的發言,那些中心內容是可以應付一下的。于是決定講了。未開口,先掏出手帕來擦了擦臉上的汗,引得大家一陣哄笑。說了兩三句,汗又激出來,脖子里也在流,背上蒸得發燙,便又用手帕擦一次汗,又引起大家一陣哄笑。我從入伍談起,逐步談到開始寫通訊,開始對文藝發生興趣。正談著,忽覺得不對頭,便問丁玲道:是否需要翻譯呀?她說要。我于是停住,小翻譯就給韓先生說起來。我雖然仍發燒,臉雖仍然紅,可是既講開頭了,也就沉住了氣。
翻罷了第一段,我接下去講“五一掃蕩”,把那時期的戰斗也著實形容了一番。不知韓先生怎樣,別人聽著似頗有所動。打住以后,陳企霞上來告訴我,段落可以分得更小一些。我點頭。趁翻譯機會,我偷眼看看同學們,他們一遇到我的眼光,馬上就笑了。我也就跟著傻笑。奇怪的是,我每次停住之后,并不想往下該說什么,只是留神大家的反應。他翻完了,我便自然而然地接下去,一面說著也就有了剪裁。大概說了有五六段吧,把經歷談完了。最后一段,無論如何也要講一講對朝鮮人民的感情了。匆匆地想了想,然而畢竟太緊張,太沒有經驗,又確實沒有什么內容。結果說得亂七八糟,不成體統。當然,這種話也沒有人去追究它的好壞的,只說明有那份心思就行了。
阿彌陀佛!我過了一關,自信這一關過得還不壞。但是,我付出了多么嚴重的一頭汗啊!
今天丁玲說,中國人一定要寫出中國的東西,不能寫成外國的,那是太糟糕的事情。然而,生活貧乏,卻逼著你“偷”外國的。這《卡賓槍》誰曉得有幾分像中國人呢?丁玲說:“魯迅先生看外國極多,可是,他沒有一點兒外國味道,全是中國作風、中國氣派。”我們要怎樣去學習呀!
上午,開“生活創作”座談會,丁玲又一次提出來胸懷要寬大,生活要愉快,情緒要飽滿。時代是明朗的,性格也必須明朗,否則便不能感受這樣偉大時代的偉大情感!
丁玲說:“不熟悉的人,即使偉大,死了,于我們無所動;一個熟悉的人,說他死了,立即有甚大反響。”我們的友誼是根深蒂固的,全是形象化得來的。
中午,董彥夫拿來幾張照片,是禮拜(天)他在游行中照的。其中一張是我和陳淼、丁玲談話時照的。丁玲模糊不堪,而我是在幾張中人物最清楚的一個,叉著腿,若即若離地在聽丁玲談什么,很有點小孩子的天真模樣。
下午到田間房子去交卷,推開門,正逢著丁玲在那里。我交了剛要去,她把我叫住了,拍著身旁的沙發說:“來,玩一玩。”我只好坐下來,心中立即感到,她想鍛煉我了,并且,主動地找我說話。她給我介紹正在小桌上吃飯的白朗,女作家,我們握了手。
她問我近來干什么,我回答看《種谷記》。她馬上問:“你感到怎么樣?”我立即感到她在“盤問”我了。我提一口氣正準備回答,田間走上來給打斷了。——我坐在那里聽他們關于《人民文學》也要出叢書的談話,聽來也有趣。但極端奇怪而令人驚異的現象是,我恰在那幾分鐘里渴思睡覺,極力振作,眼皮仍是打架。我感到,即使在丁玲“盤”我的時候,也有可能倒頭睡熟。這究竟是個什么道理,是生理上有了什么衰老的變化,還是怎的?何至于竟嚴重到這般程度呢?奇怪死了!
丁玲沒有堅持“盤問”下去,隨后就談起了《高干大》來。她說,這本書技巧高,有味兒。她說,看一本書,不一定非去死摳什么思想、人物不可,你能感受到一種味道就好。寫作品也一樣,味道總要寫出一點兒來,叫人感到新鮮,能得到東西才行。她同意孫犁的作品有味道,《種谷記》也有。《腹地》她看不下去,不承認它有味道。其實,《腹地》還是有味道的,而且是很有味道。她說,歐陽山不懂合作社,也不熟悉生活,可是,他寫出來了,就是技巧高。《高干大》中間把主題也變了,然而,使你感覺不出來,不生硬,這便是技巧。
她又問,讀了李廣田的兩篇講義、兩篇報告沒有,問好不好。我說好。她說一看就知道李廣田是個會寫文章的,他有生活,這樣說不出來,他就轉彎抹角另想個法,總要說出來。她說我們應該學習這種本領,應該用多種多樣的方法,表達自己的意思。她認為學學寫散文雜文是很必要的。
中午飯時,康濯告訴我,丁玲把《卡賓槍》丟掉了,很抱歉,不好意思給我說,問我有無底稿,有的話最好再抄一份。這要是別人,我非要大罵特罵不可。然而,丁玲不是不曉得創作痛苦的人,也不是漠不關心別人東西的人。我理解她丟掉以后的心情,我表示很愿意再抄一份。
丁玲幾次強調我們應培養最好的品質,而最好品質的最高標準,也不過是廣泛地真誠地愛人民、愛大眾!
下午,聽丁玲的關于《實踐論》的創作問題:《創作與生活》。她提出創作不是“寫生活”,創作也是個實踐與理論的統一體。
明天丁玲同志召集本所女同志開座談會,紀念“三八”,談的題目是“結婚與事業的關系”。
9點鐘,葛文來催,叫小組派男同志的代表到會議室去參加婦女座談會。我拉上孟冰,高高興興跑去了。不料,一進門,一大群女同志就噼里啪啦一頓鼓掌,我急得不知所措,連忙找個凳子坐下了。丁玲同志對大家說:“你們看,徐光耀參加婦女會也臉紅的。”人們又一陣笑,我連忙給自己解嘲:“你的眼真是厲害!”
最后是丁玲講話了。可惜,我沒有帶記錄本子去。
她說:戀愛的事,不可太認真了,差不多就算了,不要花太大的注意力。一二十年一閃就過去的,我們做工作的時間卻少得很,哪有很多條件去訂計劃,比條件呢?
又說:婦女的解放主要是靠自己。是的,舊社會有制度壓迫我們,有禮教來壓迫我們,今天是不是就沒有壓迫了呢?還有的。我們自己在壓迫我們,舊的影響在壓迫我們,把我們束縛住了。如有的要找個“政治強的”,能“幫助”自己的,地位高的對自己就是壓迫。要解放,先要擺脫這種壓迫。
她又主張夫妻應熱烈地相愛。不要過多挑剔,一切都和自己的愛好、性格完全相投是沒有的事,只能大致上差不多就行了。兩個什么都一樣,世界上是找不到的。但,也不能馬虎、勉強,對他只有三點愛,另兩點不愛,湊合了吧,也不行的。這還是個復雜的應謹慎的問題。
戀愛要勇敢、真誠,怎樣就怎樣。看看你對心,就去直接對你說。吳長英就很好,碰了回來,也至多是一禮拜嘛,過去就完啦!不要等著,等著人家來看,在家里擺著。他X的你是個什么東西呢?你是件商品,是玩物嗎?你等人家來挑選,來講價錢,你還想拿一把,抬高市價,不像話嘛!你不解放,你自己找的嘛(她很激憤地罵了一頓)!
她還批判了婦女的狹隘(她說男同志也狹隘,稍輕就是了),狹隘是政治不開展的表現。世界這樣前進,有什么過不去呢?有什么不能解決的呢?都可以解決的。她當初在延安時孩子什么不要,只要活著就行了,餓不死就行了。現在不是很好嗎?夫妻之間生了氣,你罵了我,我看他真生了氣,不理他算了。對他的罵沒有反應,是麻木的。那么他罵過一兩句便會感到寂寞,就不會再罵,等到不生氣了,再給他講理:你罵了我,我不是沒聽見,只是裝聽不見,我對你不對。問題該可以解決了。
最后,她談到品質問題。認為人的品質包括很多,空談品質并不能解決問題,也不能提高的。提高品質得慢慢地一步一步來,一個一個具體問題解決了,才逐漸提高。而且品質的好壞,也不能從一件事情上看。品質的好壞,也不是永久不變的。兩人離婚了,看來不是男方便是婦方品質不好。可是,兩人確實合不來,離了反而對雙方對黨都好些,又有什么不好的呢?
她希望大家不要常常談戀愛問題,總是談也不能解決問題。這問題不同其他,可由討論解決得了的。大家只要差不多,碰去就是了。
她的話很活潑,也很深刻,可惜不能都記下來。
(責任編輯:孫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