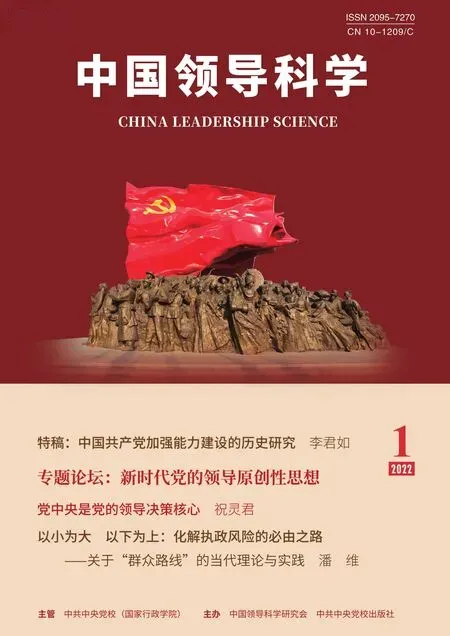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對黨的領導理論的創新
——基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教訓的分析
◎鄭 寰
黨的領導是世界馬克思主義政黨共同創造的理論。自19 世紀以來,世界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斷創新和發展黨的領導理論,結合各國實際進行了豐富多樣的探索。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深刻汲取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教訓,不斷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的認識,對黨的領導理論和實踐問題進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學判斷,形成了一系列原創性思想。我們從歷史的比較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理論貢獻,具有重大的世界意義。
一、黨的領導理論是世界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共同創造
自共產主義者同盟建立以來,世界上許多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政黨都高度重視黨的領導理論建設。馬克思和恩格斯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締造者,他們共同奠定了黨的領導的理論基礎,圍繞無產階級領導權等關鍵問題作出深刻論述。在總結德國1848年革命的教訓時,恩格斯論述了無產階級領導權和工農聯盟問題;在反思1871年巴黎公社失敗教訓時,恩格斯批判了反權威主義的觀點,深刻闡發了權威與自治的關系。許多歐洲十九世紀的社會主義政黨都把共產黨的領導視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建設的規律。
1917年,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奪取政權后,建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通過不斷完善黨的領導體制,建立了以民主集中制為核心的黨的領導制度。列寧對黨的領導理論進行了一系列原創性的論述,對領袖、政黨、階級和群眾之間的相互關系、黨的領導和群眾路線、黨的領導方式等問題進行了深刻闡發。列寧認為:“黨是無產階級聯合的最高形式。它代表著無產階級和全體勞動群眾的利益,并領導他們的一切聯合行動。不正確地了解黨的領導作用,就是在理論上根本違背共產主義。”[1]在蘇聯共產黨的影響下,世界上許多共產黨借鑒和模仿了列寧式政黨的領導理念和體制。
伴隨20 世紀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黨的領導活動的內容、方式和方法變得越來越豐富、完善和多樣化。一些國家的共產黨結合國情,對黨的領導理論進行了創新。例如意大利共產黨的創立者安東尼·葛蘭西深刻闡述了“領導權”概念,對政黨所行使的領導權職能或政治領導職能進行了深刻的思考。他認為“政治藝術和政治學的首要問題是怎樣才能實行最有效的領導,又怎樣才能最好地培養領導者”,“黨是培養制導者和發揮領導能力的最有效的方式”,“政黨的職責就是選拔、培養和擴大必要的領導人員的隊伍”,“無產階級政黨在奪取政權后的核心問題,就是要確保領導權不致落到特權集團手里,防止出現領導權危機”[2]。
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上,馬克思主義共產黨普遍重視黨的領導理論問題。盡管他們各有特點,圍繞完成各自面臨的任務采取了不同的工作方式和方法,但普遍認同黨的領導的共同規律,強調黨對社會變革過程的影響,堅持黨對國家和社會組織、對社會生活的物質和精神方面發展的政治領導;鞏固和擴大黨同工人階級以及社會主義社會其他勞動人民階級和社會階層的聯系;遵循黨的民主集中制和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加強黨的思想、政治和組織的統一,提高黨的干部和全體共產黨員執行黨的決議的責任感。[3]
二、蘇聯晚期改革對黨的領導存在嚴重的認識誤區和歷史教訓
蘇聯共產黨人曾對黨的領導理論建設作出過重大貢獻,對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產生過巨大影響。20 世紀70年代,蘇共思想理論界曾對黨的領導理論進行過系統闡述,并把黨的領導寫入了憲法。蘇共理論界認為:“執政的共產黨在社會主義社會的政治體系中居于中心地位,是這個政治體系的核心。在所有的社會主義中,以及在其他政治黨派中,共產黨是主要的、關鍵的環節。在蘇聯已經發展到成熟的社會主義階段,全面發揮黨的領導作用更為必要、更加迫切。”[4]然而,20 世紀80年代末,蘇共領導層對黨的領導理論進行了一系列重大調整,在實踐中推動了一系列顛覆性改革,導致了黨的垮臺和國家的解體。
(一)蘇共領導層對黨的領導地位問題出現了認識偏差
回顧蘇聯晚期改革的過程,蘇共領導層對黨的領導的認識經歷了一個變化過程。改革初期,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曾認為“黨的領導作用是社會主義發揮作用和得到發展的必備條件”,“能夠領導國家走革新道路的政治力量正是黨”[5]。但當初期的改革遭遇阻礙之后,戈爾巴喬夫認為蘇共已經落后于時代,成了改革的對象。他主張“從改革年代形成的新情況、從對黨在社會中的地位、黨的職能以及實現黨的政策的形式、手段和方法的認識出發,對黨進行革新”[6]。蘇共中央的革新戰略是根本改變蘇共在蘇聯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這意味著要使黨從總體上一貫正確、從追求對一切進行領導、從政治壟斷的地位中擺脫出來。”[7]“黨要經歷對自身在社會的作用,對幾十年來所形成的建黨原則和活動方法進行重新認識。”[8]蘇共領導層對黨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理論認識,偏離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為一系列激進政治改革提供了理論基礎。
(二)蘇共晚期改革沒有處理好黨和法治的關系
在蘇共執政史上一共制定過三部憲法,黨的領導作用逐步通過法律形式固定下來。1977年10月7日,蘇聯第九屆最高蘇維埃第七次非常會議通過的憲法第六條明確了黨的領導的法定地位,即蘇聯共產黨已成為全體人民的先鋒隊,它是蘇聯社會的領導力量和指導力量,是蘇聯社會政治制度以及一切國家機關和社會團體的核心。憲法強調,蘇共是國家政治制度的核心力量,它協調這個制度一切環節的活動,協調著蘇維埃機關、經濟機關和社會團體的活動。然而,在戈爾巴喬夫改革時期,蘇共部分領導人把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對立起來。在蘇共黨內外民主派和反對派勢力的強烈呼吁下,修改憲法第六條變成了“十萬火急”的問題。戈爾巴喬夫對修改憲法第六條態度左搖右擺,最終走向了取消黨的領導地位的方向。他認為“黨的地位不應當依靠憲法來強行合法化,蘇共自然要為取得執政黨地位而斗爭,放棄某種法律和政治優越地提出自己的綱領”[9]。經過多方較量,1990年蘇聯第二次人民代表大會上修改憲法第六條,取消了蘇共領導的法定地位。
(三)蘇共晚期改革沒有很好地處理黨政職能分開的問題
蘇共在改革中,對黨和國家機關的職能關系進行了重大調整。戈爾巴喬夫在1988年蘇共中央全會上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根本問題涉及劃分黨和國家機關的職能”,“黨不能也不應當指揮國家機構、經濟機構和社會團體”,“黨委會不能通過含有對國家機關、經濟機關和社會組織直接指示的決定”[10]。他說:“讓我們的議會去起草法律吧,讓政府去行使執行權力吧,讓法院去審理案件吧。”蘇共在改革中推動了黨政職能分開,強化各級蘇維埃的獨立性和司法的獨立,大大削減黨的工作機構,限制黨的領導的范圍。由于在黨政關系問題上的認識錯誤,加之處理黨和國家機關、經濟機關和社會團體關系方面的失誤,導致了嚴重的政治后果。
(四)蘇共晚期改革不斷削弱黨的政治領導、思想領導和組織領導
戈爾巴喬夫提出,要在黨的職能變化中對黨的領導方式進行改革。在組織方面,他認為“黨革新的必要條件是根本改變黨同國家機關和經濟機關的關系,放棄向他們發號施令和越權代行他們的職能的做法”[11]。強調黨不能對國家和社會結構“發號施令”,應當保持獨立性。在思想方面,戈爾巴喬夫等人主張摒棄所謂的“精神壟斷”和“思想壟斷”,主動放棄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最終難以形成統一意志,各種不同政見、不同觀點甚囂塵上,出現了嚴重的思想混亂。
(五)蘇共晚期改革中沒有正確地認識黨中央權威和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的作用
從蘇聯的歷史教訓來看,片面強調集體領導制度,把民主集中制原則和黨內民主對立起來,無法形成領導核心是改革失敗的重要原因。在改革中,戈爾巴喬夫夸大黨內民主和集體領導的作用。他認為“黨的地位應該是黨本身進行深刻的民主改革的結果”,“作為蘇共的建設和活動的基礎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在一定階段在很大程度上被官僚主義的中央集權制取代了”。為此,要對黨本身進行內部的堅決的民主改革。改革后期,尤其是實行總統制,戈爾巴喬夫當選為蘇聯總統后,沒有很好地處理黨的領袖和黨中央的關系,甚至擺脫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進行決策,把黨中央的權威削弱了。由于缺乏正確的集中機制,導致黨的領袖和黨中央之間發生矛盾,黨內團結和統一難以實現,最后導致蘇共黨內斗爭白熱化,引發了黨和國家的危機。

蘇聯解體后,烏克蘭基輔一軍事學校的士兵將列寧紀念館中的戈爾巴喬夫肖像摘下
(六)蘇共晚期改革對黨的領導方式的認識存在重大缺陷
在改革中,戈爾巴喬夫認為“現行的政治體制幾十年來不是在法律范圍內組織社會生活,而主要是執行強制命令和指示”。在他看來,“黨包攬了許多經濟的、管理的、甚至行政的問題,可又來不及都去做,而國家機關卻荒疏了自己的工作”。為此,蘇共需要審視自己的工作和領導方法,不能用命令確定黨在社會革新中的地位。在黨的二十八大的黨章修改中明確“蘇共基層黨組織不再認為可以監督,而且實際上也無權監督企業和團體的行政機關的活動,以及各部和主管部門及蘇維埃機關和經濟機關的工作。黨組織的新作用是,在會議、代表大會集體確定立場,通報給相應的國家機關和經濟機關,在公開討論中闡明立場”。通過黨章的修改,直接取消了基層黨組織的領導職能。
總體來看,執政74年的蘇聯共產黨之所以垮臺,一個關鍵原因就是對黨的領導的理論認識出現嚴重錯誤,在實踐中取消黨的領導的法定地位,全面放棄黨的領導。對黨的領導作用,蘇聯共產黨原書記處書記利加喬夫曾做過深刻反思。他說:“之所以在我國能發生這一切,最主要在于,蘇共在社會中的領導作用先是弱化,而后被完全消除。蘇共被從政治中、從思想和組織中排擠出去。在黨內形成各種派別,投機分子、民族分裂分子向黨和國家、共和國黨和權力機構的領導層滲透。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國家領導形成派別,他們的立場轉向消滅共產黨和蘇維埃國家——所有這些都是毀滅蘇共鏈條的環節。”[12]蘇聯晚期改革的歷史過程顯示,蘇共領導層對黨的領導理論的認識,已經違背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和建設的規律,造成了災難性的后果。
三、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對黨的領導理論進行創造性地發展
黨的十八大以來,新時代的中國共產黨人科學總結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的教訓,吸取和借鑒有益的經驗,不斷推動黨的領導的理論創新。習近平總書記對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的重大意義、方向原則、觀念體制、方式方法進行了深刻闡述,澄清了一系列思想認識上的誤區,創造性地回答了一系列理論難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黨的領導理論。
(一)創造性地回答了黨的領導與社會主義關系的問題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從中蘇兩黨兩國的不同歷史命運來認識黨的全面領導問題,把黨的領導堅強有力、堅如磐石視為中國共產黨沒有垮下去的最根本原因。他指出:“如果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也在蘇聯解體、蘇共垮臺、東歐劇變那場多米諾骨牌式的變化中倒塌了,或者因為其他原因失敗了,那社會主義實踐就可能又要長期在黑暗中徘徊了,又要像馬克思所說的那樣作為一個幽靈在世界上徘徊了。”[13]他反復強調“一定要認清,中國最大的國情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什么是中國特色?這就是中國特色”[14]。“在堅持黨的領導這個重大原則問題上,我們腦子要特別清醒、眼睛要特別明亮、立場要特別堅定,絕不能有任何含糊和動搖。”特別是他鮮明地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黨的領導的重大理論判斷,糾正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把社會主義改革和黨的領導對立起來的錯誤認識。
(二)創造性地回答了黨和法治關系的問題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從“最根本保證”“最大區別”“根和魂”等角度,深刻地闡明了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的內在關系。他提出“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之魂”,“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最根本保證”,“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最根本的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等重大論斷。[15]他指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這件大事能不能辦好,最關鍵的是方向是不是正確、政治保證是不是堅強有力”。“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要有利于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有利于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完成黨的執政使命,決不是削弱黨的領導。”[16]由此,黨在十九大后推動了憲法修改,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對第79 條第三款的規定進行完善,健全了國家領導體制,為黨和國家長治久安奠定了法理基礎。
(三)創造性地回答了黨政關系的問題
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由于存在“黨政分開”“劃分黨政界限”等認識誤區,經常造成黨政關系紊亂,在黨政分開和黨政合一兩個極端之間搖擺。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深刻總結以往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澄清了關于“黨政分開”等一系列思想認識上的誤區。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處理好黨政關系,首先要堅持黨的領導,在這個大前提下才是各有分工,而且無論怎么分工,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黨的領導地位和執政的地位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權力是不可分割的。不能簡單講黨政分開或黨政合一,而是要適應不同領域特點和基礎條件,不斷改進和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17]由此,黨中央作出了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重大決策部署,對新時代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統籌設置黨政機構,提高黨和政府效能進行了深入思考,理順了黨政機構的關系。
(四)深刻論述了關于堅持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理論
回顧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教訓,許多共產黨把黨內民主和民主集中制對立起來,不能正確對待黨的集中統一問題,喪失了黨中央權威。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堅持黨的領導,最根本的是堅持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他強調“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是我國革命、建設、改革的重要經驗,是一個成熟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重大建黨原則”,要“正確理解和把握堅持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這個根本點”。“民主集中制是黨的根本組織原則、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發揚黨內民主和實行集中統一領導是一致的,并不矛盾。”他明確指出“要堅持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和解決黨內問題相互統一。不能因為黨內存在問題就削弱甚至否認黨的領導,走到自斷肱骨、自毀長城的歪路上去”[18]。由此,黨中央把實行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作為黨的政治建設的首要任務,作為明確的政治準則和根本的政治要求,深化了關于正確處理集中統一領導和分工負責的理論認識。
(五)深化了關于政治領導、思想領導、組織領導的認識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黨的領導包括政治領導、思想領導和組織領導,放棄或忽視其中任何一點,都不可能實現黨的領導。”在黨的政治領導方面,習近平總書記系統闡述政治領導力的基本理論,創造性地提出了“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要求領導干部不斷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在思想領導方面,黨中央不斷深化對宣傳思想工作的規律性認識,創造性地提出“黨管宣傳、黨管意識形態、黨管媒體是堅持黨的領導的重要方面”,“必須把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時候都不能旁落,否則就要犯無可挽回的歷史性錯誤”[19]。在組織領導方面,黨中央深刻吸取蘇共放棄民主集中制、實行自治化原則的教訓,創造性地提出“黨的全面領導要靠黨的堅強組織體系去實現”的重大論斷,著力加強組織領導,全面完善黨的組織體系。
(六)原創性地闡發了黨的領導制度體系問題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不斷推進黨的領導制度化、法治化,不斷完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把制度建設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推進黨的領導制度化、法治化,既是加強黨的領導的應有之義,也是法治建設的重要任務。”通過法律和黨內法規的修改,黨的領導作用得到了制度化保障。比如,十九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加強和維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若干規定》,制定出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工作條例》,對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領導體制、領導職權、領導方式、決策部署、自身建設等作出全面規定。再比如,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黨的領導制度體系,從六個方面規定了制度體系的主要內容,大大深化了對黨的領導制度的理論認識。
(七)原創性地回答了黨的領導方式方法的重大問題
總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教訓,對黨的領導方法的認識往往過于簡單化。在蘇共晚期改革中,經常由于不顧各個領域的特點和條件,片面認識黨的領導方式,使得黨的領導實踐出現錯位、越位或者缺位。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針對黨對不同領域的領導方式進行了系統性論述。例如,針對人大、政府、政協、監察、審判、檢察機關、人民團體、企事業單位、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社會組織等,要求加強“全面領導”;針對軍隊等武裝力量和國家安全工作,強調堅持“絕對領導”等等,確保黨的領導落實到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各領域各方面各環節。
四、新時代中國共產黨領導理論創新具有深遠影響和世界意義
新時代的中國共產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領導理論。中國共產黨的理論貢獻,是在深刻總結世界社會主義興衰成敗的理論和實踐中實現的。一方面吸取了蘇共晚期改革在黨的領導問題上的教訓,另一方面,也是更為重要的,是總結我們黨長期以來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成功經驗,進而科學地回答了黨和社會主義關系、黨和法治關系、黨政關系以及黨的領導制度、黨的領導方式等重大理論問題。
當前,世界格局正發生深刻調整,國際社會出現了領導權轉移的勢頭。美國智庫蘭德公司2020年發布了《美國影響力的衰退與拯救》研究報告,認為美國過去20年的影響力急劇下滑,全球關注度下降,面臨著嚴重的領導力危機。該報告分析指出:21 世紀美國影響力下降有多種原因,包括冷戰后美國推行單極霸權主義、政客們傲慢自大、黨派的兩極分化、“帝王式總統”的權力擴張等。[20]在新冠肺炎疫情應對中,美國領導體制暴露出一系列重大缺陷,政策制定前后不一致、缺乏執行力和國際合作、肆意推卸責任、反應遲緩等,嚴重損害了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
面對時代變局,中國共產黨保持戰略定力,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不斷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為世界各國政黨強黨興黨提供了中國方案。新時代的中國共產黨立足實際,推動馬克思主義黨的領導學說本土化和中國化,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領導理論和話語體系。在實踐中,中國共產黨充分發揮黨的領導政治優勢,把黨的領導落實到黨和國家事業各領域各方面各環節。黨的領導的創新理論指導偉大實踐取得巨大成功,在應對國際變局、國家治理、脫貧攻堅、疫情防控、高質量發展、生態環保等各個方面得到了系統檢驗,并被賦予新的內涵。實踐證明黨的領導理論創新凸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具有更加堅強的領導力。
當前,人類社會正面臨共同挑戰,當今世界出現了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反建制和反全球化趨勢抬頭的傾向。面對這些挑戰,需要中國共產黨同各國政治力量一道,共同推動人類進步事業。毫無疑問,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方案具有世界意義。為此,我們要在國際間科學地傳播和交流黨的領導理論,回應國際社會的種種誤讀和曲解,同時使國際社會在歷史比較中,準確把握中國共產黨人對黨的領導理論的原創性貢獻,深化對政黨領導理論的規律性認識。■
[注 釋]
[1]列寧. 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1.
[2]葛蘭西. 葛蘭西文選(1916-1935)[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21.
[3][4]蘇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集體編寫. 社會主義國家黨的建設[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5:31, 12.
[5][6][7][8][9][10][11]蘇聯改革的軌跡——戈爾巴喬夫言論輯錄[M].1990:19, 14,19,13,22,41,42.
[12]葉·庫·利加喬夫. 警示[M]. 錢乃成等譯. 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01:353.
[13][19]習近平.論黨的宣傳思想工作[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2020:313, 181.
[14][15][16][17]習近平.論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231, 76, 77, 231.
[18]習近平關于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論述摘編[M].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160.
[20]詹姆斯·多賓斯、加布里埃·塔里.美國外交政策中:“迷失的一代”: 美國影響力的衰退與拯救[EB/OL]. 2020.09.https://www.rand.org / RAND_PEA232-2.zhs.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