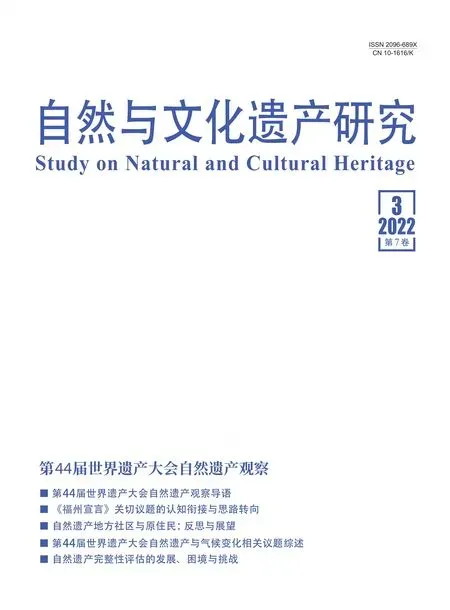《福州宣言》關切議題的認知銜接與思路轉向
陳昱陽,孫 鐵,宋 峰*
(1.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北京 100871;2.國家林業和草原局自然保護地管理司,北京 100013)
1 世界遺產大會宣言:不同背景下的共識性思考
世界遺產大會宣言是世界遺產中心同《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以下簡稱《公約》)締約國、世界遺產委員會、國際組織及其他國際機構多方聯合,在世界遺產大會期間形成工作組,對世界遺產國際事務中重要問題的方針、政策,原則、立場,觀點、態度等進行磋商,后形成共同主張,并向國際社會宣布的外交文書,代表著締約國對《公約》框架和發展趨勢下重要議題和國際責任的認識和聲明。
21世紀全球可持續發展背景給世界遺產領域帶來了新的工作方向與思考,多個熱點問題應運而生,至今仍引發世界遺產范圍的廣泛關注與討論。2000年以來,諸多宣言文件在世界遺產相關國際會議上被接續發表,宣言文件本身及其對應的世界遺產工作背景和重點,持續向全球可持續發展大背景靠攏。由于所依托的事務或會議背景不同,宣言的關注重點和主旨也有所不同(表1),但基本都包含世界遺產可持續保護管理的理論、方法和對象3個方面,融合對應的時代背景持續增加新觀點或完善既有的討論。

表1 2000年以來世界遺產相關國際宣言文件的產生背景及內容主旨

續表1
2021年第44屆世界遺產大會對氣候變化、沖突遺產、能力建設、自然與文化融合等議題展開磋商,凸顯出:在近中期和當下階段世界遺產所關注的問題再一次被提醒重視,同時也在新形勢下注入新思考。這些重大議題此前就被給予了高度關注,這一點在系列國際會議和宣言中已明顯體現。由于較多宣言發布的背景和指向的范疇存在差異,因此,筆者重點關注2000年以來世界遺產大會會上發布的、具有總攬性特征的宣言,特別是與2021年第44屆世界遺產大會及《福州宣言》進一步強調的議題密切相關的宣言,對熱點議題及背景予以解析,試圖對其在世界遺產領域產生關切與行動的過程形成較為集中和全面的理解。經過梳理,選出了包括2002年第26屆大會通過的《布達佩斯宣言》、2015年第39屆大會通過的《波恩宣言》、2016年第40屆大會通過的《保護世界遺產的伊斯坦布爾宣言》、2019年第43屆大會通過的《巴庫宣言》和2021年第44屆大會通過的《福州宣言》。本文試圖回顧其在對應背景下形成的代表性議題及有關討論(表2),分析其至今表現出的銜接性和轉向性。

表2 世界遺產大會宣言反映出的關注議題
2 世界遺產多元化關注重點的集中體現
2.1 《布達佩斯宣言》:對“人與社區”的關注是世界遺產可持續發展的重點
21世紀初期,在國際關系趨向于和平安穩發展的背景下,世界遺產對于保護與可持續發展關系的討論聲逐漸沸騰,其中社區與遺產地的關系受到了廣泛重視。聯合國《二十一世紀議程》中突出強調了社區對可持續發展的作用[1],對應《公約》第5條與第27條中關于遺產和社區發展之間聯系的隱晦表述[2],顯然早期《公約》的實施并不太關注當地社區的參與,導致了后續世界遺產保護管理過程中的諸多問題[3-4]。后續遺產領域出現了針對文化多樣性和社區角色地位的反思和實踐,包括遺產類型的增加和相關概念的理解,由此社區的概念才逐漸被重視起來[5-6]。
2002年,第26屆世界遺產大會上以南非共和國為代表的委員國強調《公約》與人類社會福祉和發展息息相關,公眾認知意識對于世界遺產的發展至關重要[7]。本屆大會的議程討論認知到遺產地社區與土著居民是重要的參與主體[7-8],大會通過的《布達佩斯宣言》以可持續發展為導向,闡明對上述觀點的考量和主張,建立了“4C”戰略目標,意在通過搭建一個合作框架,來建議世界遺產利益相關者共同參與世界遺產保護,以增強《世界遺產名錄》的公信力(包括突出普遍價值的代表性和區域平衡)。《布達佩斯宣言》通過后,2007年在新西蘭基督城舉辦的第31屆世界遺產大會上,世界遺產委員會在“4C”戰略目標中增加了“社區”(community),首次明確強調世界遺產地所在區域的社區在保護世界遺產方面的重要作用[1,9]。但在2012年以前,世界遺產中心尚未在《實施〈世界遺產公約〉操作指南》(以下簡稱《操作指南》)補充說明社區與世界遺產關聯性的內容。
以上反映出:在21世紀初期“可持續發展戰略”剛剛進入全球視野之時,“人與社區”這一項戰略重點在世界遺產工作中還處于“理論形成和初步探索階段”,也為至今世界遺產領域對“社區”的熱切關注和多方實踐奠定了基礎,為社區可持續發展納入世界遺產保護管理工作框架提供了基本思路。
2.2 《波恩宣言》:憶及沖突遺產的相關決議,重申締約國職責
關于沖突遺產的集中性討論開展于第39屆世界遺產大會之后,更準確的則以2018年法國和比利時聯合申報“一戰(西線)墓地和紀念地”項目遭委員會推遲審議為節點,沖突遺產成了世界遺產領域持續至今的重大議題之一。對比時下世界遺產關于沖突記憶遺產議題的討論,第39屆世界遺產大會及之前關于沖突遺產的關注,僅局限于對近期受國際政治及軍事武裝沖突影響的已列入遺產范疇,暫未考慮到已列入或將列入《預備清單》的遺產所涉及的領土爭議、文化爭議、民族認同爭議等問題。
大會以當時的中東戰亂局勢背景為依托,重點關注受自然災害和沖突戰亂影響的遺產地[10]。武裝沖突一直是世界遺產最大的威脅因素之一,其對世界遺產的影響重點在對遺產本身造成毀滅性破壞;同時,武裝沖突局勢下的無政府管理、反動勢力或者特殊社會事件也將對文化和自然遺產的保護管理造成打擊[11-12]。中東戰亂局勢下,世界遺產受到毀滅性打擊的同時,那些在自然和人為因素雙重影響下的世界遺產,其長期以來面臨著的威脅,在戰爭狀態結束后仍將長期存在[13]。
大會重申世界遺產締約國以正義、自由與和平為目的的保護責任,警惕對世界遺產的過度開發、自然災害、戰亂沖突的破壞性行為,和以此產生的嚴重國際影響[10]。委員會憶及早期出臺的《關于武裝沖突情況下保護文化遺產的海牙公約》及《開羅宣言》《教科文組織關于蓄意破壞文化遺產問題的宣言》等關于保護伊拉克、敘利亞和利比亞文化遺產所發表的宣言,回顧針對中東地區文化遺產受損一事舉行的各次議會產生的決議,包括伊斯蘭合作組織(OIC)支持前述執行局決議所發表的宣言、2015年4月舉行的歐洲議會決議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70年公約》第3次締約國大會通過的決議,認為有必要加強以上宣言文件之間的關聯性,并提出了關乎受損遺產修復和后續保護的措施。國家層面,措施包括落實法律約束、簽署相關國際公約、加強多方合作參與、建立世界遺產緊急援助資金,以及考慮雙邊或多邊項目和各種形式合作等;國際層面則是呼吁締約國與UNESCO之間形成合作框架,以及開展“全球聯盟”運動以及其他基于人道主義的、針對專業團體和個人開展的相關遺產運動,共同致力保護文化遺產。關于以上措施的建議,表明了《波恩宣言》及戰局背景下召開的世界遺產大會對國際沖突問題在世界遺產范疇內構建應對體系的響應。
2.3 《保護世界遺產的伊斯坦布爾宣言》:對可持續發展的再認識和新關注
世界遺產工作一直以來體現著世界遺產委員會對可持續發展的積極響應,2015年聯合國發布的《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是此后世界遺產可持續發展路徑探索的重要指向[14]。此后,各屆世界遺產大會設立可持續發展議題,針對文化和自然遺產對人類價值、認同和記憶以及社會與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進行探討。以第40屆世界遺產大會及《保護世界遺產的伊斯坦布爾宣言》為開端,主要綜合了先前世界遺產大會的重點議題和既有宣言所關注的、當今仍需給予關注的熱點,包括對可持續發展戰略(SDGs)、文化多樣性和沖突遺產的持續關注,同時也提及了近年世界遺產領域所關注的全球性復雜問題,例如氣候變化、環境災害、社會經濟壓力等。
第40屆大會結合《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首次對不同地區當前文化多樣性的保護情況、趨勢、威脅和機會進行綜合戰略性分析,普遍認知到遺產保護、文化推廣作為可持續發展的驅動力,其文化與文化多樣性的保護在可持續發展中具有重要作用[15]。關于持續發生的環境災害,會議呼吁締約國采取相關積極政策,特別針對當前已經列入《瀕危世界遺產名錄》的遺產地實施,突出對《瀕危世界遺產名錄》遺產治理的重視。另外,“社會、經濟發展壓力的增大將阻礙《公約》的正當實施和可持續發展進程”這一觀點,在本次會議中已形成共識性意見,認為有必要通過建立國際援助機制,提供給締約國一致性的技術和資源供給途徑,從而深化國際合作,共渡難關。
同時,大會發布的《保護世界遺產的伊斯坦布爾宣言》反映出本屆會議對彼時仍未解決的文物盜竊、劫掠和非法販運問題仍保持關注,再次重申《波恩宣言》中對締約國保護責任和各項文化公約之間聯合重要性的觀點,并對締約國的保護管理提出更多呼吁,包括創新解決方案以應對發展需求,通過額外方式捐助資金,將文化與自然遺產的保護工作提升至國家安全戰略高度等。以上呼吁和建議體現出:無論是象征意義層面的宣言文件,還是實際意義層面的會議討論,都有對以往會議的關注重點有所繼承。
還需要關注到,受《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影響,UNESCO早在2007年就已經對受氣候變化影響的遺產地做調查評估,并編寫了《氣候變化與世界遺產案例分析》,此后多次世界遺產大會也表示對氣候變化問題的關注。2014年起,IUCN的工作報告中開始進行氣候變化對世界自然遺產破壞作用的論述[16],但關于氣候變化對世界遺產的影響先前未在大會議程進行正式討論。2016年UNESCO與聯合國規劃署發布《氣候變化下的世界遺產和旅游業》,對世界遺產提出一系列應對氣候變化的建議[15]。同年,第40屆大會就《世界遺產與可持續發展》的工作報告中體現出世界遺產與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13“氣候行動”的銜接[15],突出對氣候變化影響下的世界遺產,特別是 《瀕危世界遺產名錄》的關注,由此氣候變化在世界遺產范疇內開始由個例和區域性擴大成為世界范圍內的共同關注。
2.4 《巴庫宣言》:重視締約國能力建設,呼吁加強文化和《生物多樣性公約》之間的協同作用
第43屆世界遺產大會持續關注世界遺產遭受的外部影響及對保護與可持續發展平衡的討論,這是自2000年以來世界遺產的共同認知。第43屆會議對此又進行重申,強調重視遺產保護與修復、促進國際和平安全、增強團結凝聚力以及促進對話交流的重要性,同時還提出了符合國際可持續發展背景進程的新觀點[17]。
受沖突遺產遺留問題影響,本屆大會上法國“諾曼底登陸地點”項目和羅馬尼亞“塔爾古久紀念建筑群”項目也被推遲審議。會上再次憶及《海牙公約》《聯合國1970年公約》及聯合國安理會關于文化遺產保護的各項重要決議,提出支持《重振摩蘇爾精神的倡議》,并敦促締約國采取一系列適當的法律和政策措施保護管理具有沖突問題的遺產,同時要求委員會就沖突遺產項目申報是否合乎世界遺產標準進行討論[17]。世界遺產委員會顯然已經意識到沖突遺產范疇需要擴展,意識到關于歷史記憶和文化認同問題的沖突遺產的申報和保護管理問題之復雜。即使ICOMOS在《評估與近期沖突記憶相關遺產的世界遺產申報》中對“沖突遺產”進行了明確定義,但就近期沖突遺產討論范疇和內涵的復雜趨勢來看,沖突遺產所涉及的其他方面,包括在不同歷史文化背景的判定、申報程序的普遍適用性和后續沖突問題的避免,早已跳出了ICOMOS單一的準則限定。
本屆大會也生成了多項創新倡議,包括對能力建設和協同重要性的認識以及自然與文化融合觀的顯現。阿塞拜疆主辦方認為:締約國之間的協同有利于以更加多元和全面的方式處理沖突問題,主張通過增加能力建設活動為弱勢國家提供援助。會議憶及2016年UNESCO關于非洲世界遺產可持續發展的討論和《恩戈羅恩戈羅宣言》,正式將“非洲優先”提升至世界遺產能力建設戰略層面,引起世界遺產領域的廣泛討論[18]。
據《巴庫宣言》表述:大會通過回顧《全球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評估報告》,認識到自然遺產生態環境和生態系統服務受氣候變暖等環境影響而惡化,將會削弱遺產價值,以至于損害人類福祉與未來生存[17]。因此,有必要認識到《生物多樣性公約》在加強遺產保護方面的重要性,呼吁世界遺產中心進一步加強文化和《生物多樣性公約》之間的協同作用,從而確保對遺產保護采取更為全面有效的方法,這是世界遺產“自然與文化融合”呼聲響起以來,首次在世界遺產大會宣言文件中的響應。
2.5 《福州宣言》:嚴峻形勢下需秉持“人類命運與共”和“自然與文化有機融合”理念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嚴峻局勢給世界遺產造成了沖擊,第44屆世界遺產大會及《福州宣言》在對既有議題和重點倡議的重申與深化的基礎上,結合全球發展背景和“中國智慧”,提出了一些新的關注方向和倡議。
在新冠肺炎全球防治的背景下,大會及《福州宣言》進一步強調遺產領域現存的薄弱問題,包括資源過度開發和沖突事件等,受疫情影響可能會進一步加劇,同時疫情可能會暫緩可持續發展戰略與世界遺產的協同。與此同時,疫情期間社區居民與遺產地聯系的加強,使遺產地社區的重要性得到提升,有必要繼續結合嚴峻背景思考應對方式。
響應第43屆世界遺產大會對氣候變化、能力建設等議題的關切,大會就氣候變化開展議程討論,呼吁在氣候變化導致極端天氣、自然災害等負面影響日益頻繁的現狀下,盡快形成有益于解決遺產問題的主張與方法[19]。能力建設方面,大會提出了關于世界遺產能力建設和實施的創新建議,包括廣泛使用數字技術以及青年教育,并基于上屆會議提出的“非洲優先”戰略展開持續討論[17],認為其有助于建立具有平衡性、可信度和地域平等代表性的《世界遺產名錄》,也有利于提高有需要國家的認識和能力。
除對往屆會議議題的延續,本屆大會主旨及《福州宣言》的納新之處在于:提出了秉持人類命運與共的理念,以及強調“自然與文化保護有機融合以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的主張,表現出鮮明的“中國智慧”特色和締約大國對世界遺產趨勢的關切。若要解決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世界遺產面臨的社會經濟壓力,需秉持“人類命運與共”的理念,以加強環境、經濟、社會不同領域的全球合作,推動實現遺產保護與可持續發展之間的平衡。“秉持全人類共同價值”的理念,是對當前世界遺產在全球多邊主義框架內應對挑戰和把握機遇的精妙表述。“進一步加強與文化和《生物多樣性公約》之間的協同,形成人與自然新型關系,采用綜合性方法保護自然遺產和文化遺產地”是中國基于對當今融合發展趨勢的判斷所正式提出的世界遺產保護管理思路。
3 世界遺產重點議題的銜接深化與認知演進
3.1 與聯合國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逐步銜接
基于全球可持續議程的發展和世界遺產響應行動,自21世紀起,二者銜接和融合的過程可以劃分為2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為2000—2015年,這一時期《聯合國千年宣言》公布了基于可持續性討論的8個發展目標,世界遺產與可持續發展的“接軌”仍處于初期階段。2002年第26屆世界遺產大會及《布達佩斯宣言》正式將“可持續發展”概念與世界遺產戰略目標并置,此后世界遺產大會都相繼對《公約》、遺產保護和可持續發展關系的理論討論和實踐審議給予了支持。之后UNESCO分別在第34屆世界遺產大會和2012年舉辦的專家會議上,聲明世界遺產界迫切需要更有效地參與可持續發展議程,并呼吁制定一項具體政策,將對可持續發展的關注納入《公約》的運作過程[7]。2014年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上,委員會要求世界遺產中心在咨詢機構的支持下,組建一個小型的國際工作組,為將可持續發展納入《公約》的進程制定一項政策建議[20]。
以2015年作為分界點,《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提出,使全球轉向可持續發展道路的第二階段。此后歷次世界遺產大會宣言都相應重申和關注“可持續發展與世界遺產的關聯性”這一命題。以2015年世界遺產大會通過《世界遺產與可持續發展》開創性政策為標志,提出了世界遺產可持續發展四要素[21],同時第39屆大會和《波恩宣言》以對戰后沖突遺產的關注為切入點,重申自由、和平和安全以及尊重人權等發展目標,旨在聲明世界遺產系統與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議程保持一致。2016年第40屆世界遺產大會就可持續政策文件的實施情況作了報告,《保護世界遺產的伊斯坦布爾宣言》指向性地提出文化在世界遺產可持續發展處于驅動性地位,響應了可持續發展戰略新增的對文化重要性的關注。2019年《巴庫宣言》針對仍處于沖突局勢下的世界遺產保護問題,再次提出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促進溝通交流的重要性,呼應SDGs就全球伙伴關系提出的戰略目標,指出世界遺產締約國能力建設和協同的重要性與后續開展工作的建議。2021年《福州宣言》基于新冠肺炎疫情背景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視角,深化了對世界遺產可持續發展問題的剖析,重申當前發展仍存在的阻礙問題,并呼吁締約國實施創新舉措。
可以看出:UNESCO及世界遺產中心最早便開始重視可持續發展與世界遺產的關聯性,并相應開展行動以將可持續發展戰略與世界遺產工作進行融合,目前已形成較為完整的理論和操作體系,這在歷屆世界遺產大會議程及其宣言文件中得以體現。盡管歷屆大會對應的時代背景和世界遺產保護階段性問題不同,但總體反映出對世界遺產與可持續發展目標關聯性的認知思考和實現世界遺產可持續發展工作的落實建議是逐步完善、多元全面和承接遞進的。
3.2 自然與文化融合趨勢的逐漸體現
世界遺產由“自然與文化分離”到“自然與文化融合”的轉向經歷了漫長的探索階段[22]。長期的反思和實踐極大地豐富了對“自然與文化融合”的討論,自然與文化的“不可分割性”受到了世界遺產中心、咨詢機構和締約國的普遍認可。21世紀開始,世界遺產中心、咨詢機構及締約國相繼開展了諸多“自然與文化融合”理論探索與實踐活動,例如“5C”戰略形成、IUCN保護地分類更新、數次操作指南修訂、歷次咨詢機構例會的討論和承諾文件的發布、國際研討會及工作坊的開展等,當前這一主題已經被置于世界遺產工作的主體地位[23-24]。
繼2014年“連接實踐項目”和2016年“自然與文化之旅”2個標志性實踐項目實施后,2017年世界遺產開始重視“自然與文化融合”路徑的探索,同年大會提及思考文化公約和《生物多樣性公約》的協同性,重視“自然與文化融合保護”的整體性方法,自此,世界遺產大會都圍繞這一要求進行理念、方法及程序上的探索和深化,越發地突出強調世界對于自然與文化有機融合的重要性的共識。就第44屆大會有關“人與自然新型關系”的討論,意味著世界遺產或有必要在面對過去及當前問題的基礎上,思考新形勢下自然與文化融合發展的方式和方向,在自然要素與文化多樣性的“關聯性”無法以固定的標準和審議、評估程序來加以限定和評判的情況下,如何實現操作程序的“自我革新”。
3.3 氣候變化對世界遺產的影響越發得到重視
2007年起,在《關于氣候變化對世界遺產影響的政策文件》(以下簡稱《政策文件》)的影響下,氣候變化一題正式進入了世界遺產工作視野。盡管UNESCO先后就氣候問題進行國際討論,但就早先形成的會議共識性內容來看,彼時對于遺產所遭到的人為威脅的關注程度要強于對自然影響因素的關注。直至2020年,IUCN第三次《世界遺產展望報告》中提出氣候變化已是當前世界自然遺產面臨的最大威脅[25],由此,世界遺產范圍開始明確意識到:氣候變化給世界遺產帶來的影響是長期且難以通過緊急補救措施而逆轉的。第44屆世界遺產大會就氣候變化專門設置議題進行磋商,氣候變化議題當前已上升至熱點事件層面。
氣候變化對于世界遺產的影響不容小覷。雖然世界遺產組織持續監測遭受氣候變化的遺產地并相應開展國際援助,特別是《瀕危世界遺產名錄》中的遺產地,但關于氣候問題的應對亟待國際社會以及多方利益相關者的共識與協作。以澳大利亞大堡礁為例,受海洋熱潮影響,大堡礁中出現嚴重的珊瑚白化和死亡,當前已嚴重影響了遺產地海洋生態系統的完整性,世界遺產中心及締約國對其保護狀況表示擔憂,要求澳方立即采取保護恢復措施。由于遭受到澳方的強烈阻撓,“大堡礁是否被列入《瀕危世界遺產名錄》”一事被延遲討論至今,遺產地生態環境治理也未見成效。顯然,由于當地政府的“本末倒置”,對自然環境對遺產地的不可逆影響保持漠視,反而強調遺產地旅游開發對遺產地發展和社區生計的重要性,這一事件凸顯出氣候問題雖已形成意見性的共識,仍需一段時間予以一致行動,其中彌補對“可持續性”的短見以及增強締約國能力建設尤為重要。
3.4 沖突遺產問題的有效解決途徑持續被討論
世界遺產工作一直試圖建立一套有效保護沖突遺產的機制,包括國際法律約束和針對性工作的共同實施。以中東沖突局勢下的第39屆大會及《波恩宣言》為開端,此后,在遭受過或正在面臨動蕩局勢的背景下,第40屆大會土耳其主辦方和第43屆大會阿塞拜疆主辦方顯然都更加強調沖突遺產問題的解決,反映在《保護世界遺產的伊斯坦布爾宣言》《巴庫宣言》中則是相繼對于沖突遺產保護文件之間的關聯和協調提出倡議,突出對沖突遺產問題的關注和對該議題生成有效操作程序的需求。
從歷次宣言就沖突遺產保護問題所宣布的主張和建議內容來看,關于沖突遺產問題的解決,最早各項文化遺產相關國際文件中都有提及,但彼此之間缺乏實施的關聯性。因此,當前世界遺產工作認為:沖突遺產在面臨實質性風險威脅時,加強相關國際文化保護文件中的關聯性,有利于UNESCO聯同締約國制訂有效的應對方案。聯系到近年武裝沖突對世界遺產造成的毀滅性打擊和近期世界遺產委員會就歷史沖突事件影響下的記憶遺產列入程序問題的討論,此類歷史沖突事件和近期沖突事件背后的原因是相當復雜的,且必然涉及國際政治問題。不無諷刺意味的是,憶及第39屆大會日本明治時期工業革命遺址的列入,彼時世界遺產大會主席國主席采取獨斷的方式強行通過了日本該項遺產的申報,不顧韓國、中國及其他非政府組織和受害者代表的強烈反對。這一事件就是對這屆世界遺產大會《波恩宣言》的無情嘲諷。這一事件不僅表現出世界遺產審議程序上的疏漏,還表現出世界遺產就沖突議事往往強調于解決近期發生的沖突問題,忽略了長期遺留下來的歷史沖突。明治時期工業革命遺址的武斷列入,不僅給中、日、韓等國就沖突事件的和平磋商帶來了惡劣影響,一定程度上也是至今UNESCO及締約國就記憶遺產列入一事開展特設工作會議的導火索。
鑒于當前世界遺產相關事務政治化傾向明顯,同時沖突的原因與背后的問題受不同國家的歷史發展和社會經濟文化背景影響而具有差異性和復雜性,如何清晰化地處理以上問題,對于世界遺產中心當前致力于構建沖突遺產列入和保護機制的行為來說是十分困難的。人類社會的和平共處、文明互鑒任重而道遠,在沖突遺產話題下,世界遺產實現其和平、正義的愿景仍然充滿挑戰。
4 結束語
立足于2000年全球進入可持續發展的背景,世界遺產以持續響應全球可持續發展戰略為大方向,清晰認知,此背景下氣候變化、武裝沖突等全球問題對其自身發展的影響,在保護管理過程中逐漸認識到“自然與文化融合”的重要性,在問題導向下進行銜接性和革新性的討論,這是世界遺產為了呼應全球政治、文化格局變化而自主積極采取的一系列適應性行動。這一特征在中國主辦的第44屆世界遺產大會中已明顯體現。就目前世界遺產已出現且長期存在的威脅風險、文化多樣性和政治化傾向而言,在形成世界遺產可持續發展成熟模式的目標導向下,世界遺產對既有議題的關注仍將呈現“承上啟下”的規律,在完善深化既有討論的同時,也必定會在此基礎上增添新的關注熱點和舉措建議,從而與特定時間的國際背景和世界遺產發展需求相適應,彰顯世界遺產是“人類命運與共”實現世界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