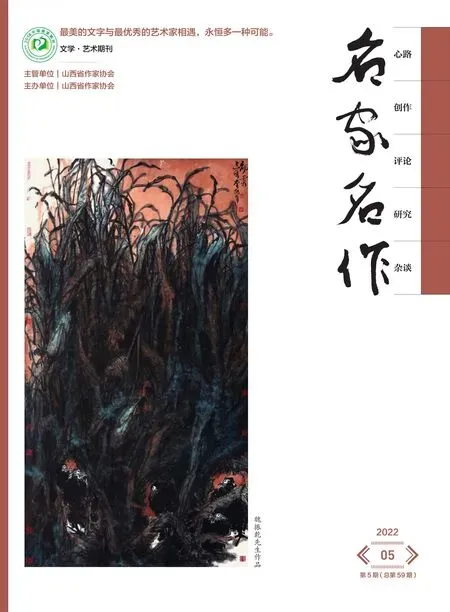從文學(xué)手法探討《不朽》復(fù)調(diào)對(duì)位結(jié)構(gòu)之構(gòu)成
張振宇
在對(duì)昆德拉小說(shuō)的研究中,關(guān)于昆德拉小說(shuō)形式或者小說(shuō)復(fù)調(diào)結(jié)構(gòu)的研究,大都是對(duì)昆德拉小說(shuō)藝術(shù)特點(diǎn)的整體概括,缺乏對(duì)昆德拉具體作品復(fù)調(diào)結(jié)構(gòu)的分析。本文嘗試從文本文學(xué)手法層級(jí)考查《不朽》復(fù)調(diào)對(duì)位結(jié)構(gòu)的構(gòu)成,以具體探討《不朽》復(fù)調(diào)對(duì)位結(jié)構(gòu)的特點(diǎn),體味《不朽》復(fù)調(diào)對(duì)位結(jié)構(gòu)的文學(xué)魅力。
整一文學(xué)手法是以單一完整文學(xué)想象具象切分的最小文學(xué)手法的橫組合片段,它包括兩大類(lèi),一是敘事作品中單一完整事件,二是抒情詩(shī)中單一完整意象。單一完整事件,出自亞里士多德的《詩(shī)學(xué)》,即“詩(shī)是對(duì)行動(dòng)的模仿”。由于《不朽》在相當(dāng)大程度上有意識(shí)叛逆?zhèn)鹘y(tǒng)整一性情節(jié),因此,本文的整一文學(xué)手法除了單一完整事件、單一完整意象外,我們用昆德拉的話補(bǔ)充了單一完整“片段”和單一完整“隨筆”。
文本文學(xué)手法指以文本為單位切分的整一文學(xué)手法橫組合片段與文本情節(jié)、意象相互作用構(gòu)成的第三者。從情節(jié)結(jié)構(gòu)角度看,文本手法即文本情節(jié)、文本事件。
最小文學(xué)手法是自然語(yǔ)言符號(hào)以不可再分文學(xué)想象具象再次切分的橫組合片段,自然語(yǔ)言是其能指,不可再分文學(xué)想象具象是其所指,是兩者相互作用轉(zhuǎn)換生成的第三者,它不是自然語(yǔ)言符號(hào)與文學(xué)想象具象二者累加之和。其間,既不存在文學(xué)想象具象的物質(zhì)化,也不存在自然語(yǔ)言的圖像化。
關(guān)于小說(shuō)的形式,昆德拉有比較詳盡的論述,多收于昆德拉的理論著作《小說(shuō)的藝術(shù)》和《背叛的遺囑》中。復(fù)調(diào)對(duì)位結(jié)構(gòu),就是為了表達(dá)“存在”之思,昆德拉自覺(jué)運(yùn)用的全新的藝術(shù)表現(xiàn)手法。
在《小說(shuō)的藝術(shù)》《背叛的遺囑》中,昆德拉多次提到對(duì)巴赫賦格音樂(lè)的欣賞,在他看來(lái),巴赫的曲式是一種精心制作的“手工技術(shù)”活,具有一種裝飾性質(zhì)。“兩種各自屬于一個(gè)不同的旋律的結(jié)合會(huì)產(chǎn)生一種神奇的效果:就像現(xiàn)實(shí)與寓言的結(jié)合。”昆德拉認(rèn)為音樂(lè)復(fù)調(diào)指的是兩個(gè)或多個(gè)聲部同時(shí)展開(kāi),雖然完美地結(jié)合在一起,卻仍保留各自的獨(dú)立性。他認(rèn)為“小說(shuō)的復(fù)調(diào)亦是聲部的平等,即沒(méi)有任何一個(gè)復(fù)調(diào)聲部可以占主導(dǎo)地位”。在小說(shuō)復(fù)調(diào)中,對(duì)位法的必要條件是“各條線的平等性和整體的不可分性”,復(fù)調(diào)對(duì)位結(jié)構(gòu) “是哲學(xué)、敘述與夢(mèng)幻的統(tǒng)一”。
如前所述,復(fù)調(diào)小說(shuō)中對(duì)位法的必要條件是各條線的平等性和不可分性。昆德拉小說(shuō)《不朽》一共有三條敘述線索:第一,應(yīng)該名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的小說(shuō)中阿涅絲及其親友的故事;第二,歌德和貝蒂娜的故事;第三,寫(xiě)作應(yīng)該名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的小說(shuō)作者昆德拉先生與他的朋友阿弗納琉斯教授的故事。
上述三條線索在《不朽》中相互獨(dú)立但又相互作用,如同復(fù)調(diào)音樂(lè)中旋律與旋律的互相作用,同時(shí),三條線索都統(tǒng)一于“存在”主題,體現(xiàn)了小說(shuō)復(fù)調(diào)對(duì)位結(jié)構(gòu)的統(tǒng)一性或者說(shuō)整體不可分性。
一、《不朽》線索之一:阿涅絲及其親友的故事
(一)阿涅絲與洛拉的對(duì)位
阿涅絲及其親友的故事,是《不朽》中主要的故事,小說(shuō)作者昆德拉認(rèn)為,這部小說(shuō)更應(yīng)該名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
在這個(gè)故事中,阿涅絲與洛拉兩姐妹的對(duì)位就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中拉斯科爾尼科夫與索尼婭的對(duì)位。在對(duì)位中,主人公各自有屬于自己的一套價(jià)值判斷。如在《罪與罰》中,拉斯科爾尼科夫代表的超人哲學(xué)觀念與索尼婭代表的東正教傳統(tǒng)意識(shí)構(gòu)成復(fù)調(diào)對(duì)位。
阿涅絲的存在方式主要是“減法”的方式,即減去“我”的所有外在的無(wú)意義的東西,以追求她自身的本真存在的意義,而洛拉的存在方式主要是“加法”的方式,即努力在自己身上加上各種對(duì)自己并沒(méi)有意義的外在東西并占為己有,以使“我”在熟人圈子中更加顯眼,達(dá)到一個(gè)小的不朽即“一個(gè)人在認(rèn)識(shí)他的人的心中留下記憶”。
從文本情節(jié)上看,阿涅絲與洛拉的故事是貫穿《不朽》始終的一條線索。與阿涅絲有關(guān)的故事主要分布在第一部、第五部及第六部,洛拉的故事主要出現(xiàn)在第三部、第七部。
第一部與第三部,主要寫(xiě)阿涅絲、洛拉所代表的兩種存在者關(guān)于存在的選擇,由于阿涅絲的減法存在方式與洛拉的加法存在方式體現(xiàn)了截然不同的兩種存在者的選擇,因此,在應(yīng)該叫作《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的小說(shuō)中,阿涅絲與洛拉的故事構(gòu)成了相互獨(dú)立、相互平等、相互作用的復(fù)調(diào)對(duì)位結(jié)構(gòu)。
(二)阿涅絲的本真存在
小說(shuō)中阿涅絲有自己的手勢(shì)。阿涅絲的手勢(shì)是從父親喜歡的女秘書(shū)那里得來(lái),她第一次使用這個(gè)手勢(shì)是和一個(gè)喜歡她的男孩子告別時(shí)做的。而當(dāng)她看見(jiàn)手勢(shì)被妹妹模仿時(shí)她便不再使用,直到阿涅絲最后一次與父親道別,為了讓生病的父親安心,阿涅絲不自覺(jué)地又做出了這個(gè)手勢(shì),而她認(rèn)為手勢(shì)在此時(shí)也才富有了意義。可以說(shuō),阿涅絲每次手勢(shì)的運(yùn)用都蘊(yùn)含了自己的感情,手勢(shì)成為感情的一種載體。而她更看重具有真實(shí)情感的東西,如當(dāng)她使用手勢(shì)時(shí),傳達(dá)出的是一種關(guān)于愛(ài)的真正情感。
對(duì)于阿涅絲來(lái)說(shuō),外在的無(wú)意義的東西應(yīng)努力減去,甚至包括肉體。當(dāng)她看到雜志上各種各樣的臉時(shí),她感受到任何臉都不復(fù)存在,并為丈夫保羅認(rèn)識(shí)她僅僅是因?yàn)樗J(rèn)識(shí)她的臉,讓她感到無(wú)法溝通進(jìn)而悲傷。
也正因如此,阿涅絲三次產(chǎn)生了關(guān)于無(wú)臉人的幻覺(jué)。她認(rèn)為自己就是和無(wú)臉人來(lái)自同一國(guó)度,無(wú)臉人的邀請(qǐng)則體現(xiàn)了阿涅絲對(duì)于本真存在的執(zhí)著追求。至少在無(wú)臉人的國(guó)度,人與人的區(qū)別并不是以臉來(lái)作為基本的區(qū)分的。
(三)洛拉的非本真存在
如果說(shuō)阿涅絲在使用手勢(shì),那么在洛拉身上,手勢(shì)則是在使用洛拉。洛拉根本就不知道阿涅絲手勢(shì)對(duì)阿涅絲的意義而盲目模仿阿涅絲的手勢(shì)。洛拉的存在方式是想盡辦法將各種外在的、對(duì)她自身毫無(wú)意義的東西化為自身的一部分,如同在做加法。就像阿涅絲戴墨鏡洛拉也模仿阿涅絲戴墨鏡,并且賦予墨鏡自己的含義即“悲傷”。
在洛拉的加法存在方式中,不僅物質(zhì)的意義喪失了,甚至肉體、做愛(ài)對(duì)于存在者本身的意義也異化了,她將男女做愛(ài)視為一種斗爭(zhēng)的方式。當(dāng)洛拉的情人貝爾納因?yàn)槟觊L(zhǎng)的洛拉而感到恥辱時(shí),已經(jīng)不想再跟她有關(guān)系。此時(shí)的貝爾納對(duì)于洛拉而言可以說(shuō)毫無(wú)意義,可是,洛拉仍然為了留住貝爾納繼續(xù)她對(duì)貝爾納的斗爭(zhēng)。相對(duì)于阿涅絲對(duì)于自己毫無(wú)意義的外在之物的減法式的放棄,洛拉拼命追求、占為己有的東西,其實(shí)都是不屬于她自身的東西,都是對(duì)于她自身沒(méi)有意義的東西。
洛拉不斷地對(duì)外在毫無(wú)意義的事物進(jìn)行接收、模仿,似乎抓住了很多外在的東西,但是,這都是對(duì)于她自身的存在毫無(wú)意義的東西。在此意義上,阿涅絲是此在的象征,洛拉是貌似獲得自身卻失去自身的非此在的象征。阿涅絲與洛拉兩種存在者的選擇,不僅共同構(gòu)成了更應(yīng)該叫《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的復(fù)調(diào)對(duì)位結(jié)構(gòu),而且共同表達(dá)了作者關(guān)于存在意義之領(lǐng)悟。
(四)阿涅絲與洛拉復(fù)調(diào)對(duì)位的最小文學(xué)手法構(gòu)成
從最小文學(xué)手法來(lái)看,阿涅絲與洛拉的故事主要由敘述的片段和議論的隨筆構(gòu)成。在敘述片段中,除了傳統(tǒng)小說(shuō)的連續(xù)敘述、倒敘等手法,還有現(xiàn)代小說(shuō)的斷裂敘述、夢(mèng)幻敘述手法。在隨筆中,除了敘述者直接議論,還有敘述者從小說(shuō)人物角度出發(fā)的議論,此外,還出現(xiàn)了小說(shuō)主人公的議論。正是較多的斷裂敘述手法,打斷了故事情節(jié)事件的連續(xù)性、整一性,使小說(shuō)敘述呈現(xiàn)出昆德拉小說(shuō)特別注重的片段,沒(méi)有傳統(tǒng)小說(shuō)的完整獨(dú)立事件,更沒(méi)有傳統(tǒng)小說(shuō)情節(jié)的生動(dòng)性、曲折性等。
相對(duì)來(lái)說(shuō),阿涅絲的故事主要在小說(shuō)第一部《臉》,洛拉的故事主要在小說(shuō)第二部《斗爭(zhēng)》。
作者對(duì)阿涅絲在父親去世五周年的那個(gè)星期六的下午,在桑拿房、街上、客廳、路燈下等不同地點(diǎn)的片段敘述中,時(shí)常夾雜阿涅絲的回憶、思考、阿涅絲自己的議論,以及敘述者顯身的議論,這些隨筆占了《不朽》第一部將近一半的篇幅,有效地表達(dá)了作為此在的阿涅絲對(duì)人的存在意義的領(lǐng)悟,體現(xiàn)了現(xiàn)代主義小說(shuō)的哲理性以及不同于浪漫主義的主觀性。
阿涅絲的故事所使用的最小文學(xué)手法很豐富,包括了敘述、回憶、描寫(xiě)、議論等。其中,敘述包括順敘與倒敘(4處)、連續(xù)敘述(3處)、斷裂敘述(4處)、夢(mèng)幻敘述(3處)等;議論包括主人公議論(3處)與敘述者從小說(shuō)人物出發(fā)的議論(1處)。在阿涅絲的故事中出現(xiàn)了少量的描寫(xiě),包括心理描寫(xiě)(1處)、對(duì)話描寫(xiě)(2處)。
在阿涅絲的故事中,要特別提及的是關(guān)于無(wú)臉人的夢(mèng)幻敘述手法。這種夢(mèng)幻敘述手法與卡夫卡《變形記》的手法相通,是夢(mèng)境與現(xiàn)實(shí)的絲絲入扣的交融,“既是向現(xiàn)代世界投去最清醒的目光,又是最不受拘束的想象,是比較典型的現(xiàn)代小說(shuō)的夢(mèng)幻手法”。現(xiàn)代小說(shuō)的夢(mèng)幻敘述手法,有效表現(xiàn)了阿涅絲作為此在的存在者對(duì)自己本身存在意義的探索和對(duì)自己本身沒(méi)有意義的東西的忽略。
在阿涅絲的故事中,不僅敘述手法與小說(shuō)的哲理性是一致的,就是描寫(xiě)手法也是體現(xiàn)小說(shuō)存在主題的手段。阿涅絲故事中的兩次對(duì)話描寫(xiě),都是阿涅絲與保羅的爭(zhēng)論,都體現(xiàn)了此在存在者與一般存在者兩種選擇的不同。
相對(duì)于阿涅絲的故事,洛拉的故事有一個(gè)獨(dú)立完整事件——洛拉的失戀,有一個(gè)獨(dú)立完整片段構(gòu)成的事件——阿涅絲與洛拉的斷交。洛拉的故事敘述手法更多屬于傳統(tǒng)小說(shuō)的敘述手法,而且,敘述手法種類(lèi)比較少。在洛拉的故事中,主要最小文學(xué)手法是傳統(tǒng)小說(shuō)的倒敘與順敘,倒敘主要用兩處連續(xù)敘述手法介紹了洛拉與阿涅絲的關(guān)系,順敘用九處連續(xù)敘述手法講述了相對(duì)獨(dú)立完整的洛拉失戀的事件(七處)以及洛拉與阿涅絲斷交的片段(兩處)。在洛拉故事中出現(xiàn)了一次斷裂敘述手法,但該敘述手法并沒(méi)有打斷洛拉故事敘述本身的情節(jié)事件,而是插入了另外一處虛構(gòu)空間的人物教授A在大街上遇到洛拉,體現(xiàn)了《不朽》獨(dú)特的不同時(shí)空交錯(cuò)的結(jié)構(gòu)特點(diǎn)。
在洛拉的故事中,議論雖然也有四次,但是,議論種類(lèi)不同。洛拉自己從來(lái)沒(méi)有一次議論,換言之,沒(méi)有主人公的議論。這四次議論包括敘述者從人物出發(fā)的兩次議論和兩次敘述者直接出面的議論。相對(duì)而言,洛拉的故事中,隨筆的主觀性是敘述者顯身的議論體現(xiàn)的。洛拉故事的相對(duì)客觀性,與作為普通存在者的洛拉本身就沒(méi)有關(guān)于存在的意義的領(lǐng)悟是一致的。
二、《不朽》線索之二:歌德與貝蒂娜的故事
昆德拉曾在《背叛的遺囑》中高度評(píng)價(jià)了“兩種旋律——各自屬于不同的時(shí)代,彼此相隔好幾個(gè)世紀(jì)——的交融擁抱產(chǎn)生的離奇效果”。這種效果就像“現(xiàn)實(shí)與寓言的結(jié)合”。
在《不朽》這部小說(shuō)中,敘事者作家昆德拉先生創(chuàng)作出的原本應(yīng)叫《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的小說(shuō)即屬于現(xiàn)實(shí)層面,《不朽》中所寫(xiě)的與歌德相關(guān)的部分則屬于歷史類(lèi)的寓言。
(一)歌德與貝蒂娜的對(duì)位
如果說(shuō)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中阿涅絲是定旋律,而洛拉是對(duì)位旋律,那么在歷史寓言中,歌德則是譜寫(xiě)貝蒂娜故事的定旋律。因?yàn)樵诟璧碌臍v史寓言中他最終也看清楚了關(guān)于存在的本質(zhì),即死了便無(wú)所謂存在了,這與阿涅絲的父親剪照片的行為具有同樣的性質(zhì)。而貝蒂娜卻一直癡迷于對(duì)不朽的追逐,她去歌德家做客,像孩子一樣坐在歌德的膝蓋上;無(wú)數(shù)次地用親密的稱(chēng)謂寫(xiě)信給歌德,談的全是愛(ài)情;在歌德母親那里聽(tīng)歌德幼年時(shí)期的故事,為的是從歌德那里獲得大不朽。她的方式是讓“自己躲在童年背后”裝成“孩子”,因?yàn)椴粫?huì)有人會(huì)對(duì)孩子做狠心的事。從中可以知道,貝蒂娜并未選擇自己的本真性的存在,而是為了不朽將自己的本真壓抑扭曲了。直至歌德死后,貝蒂娜也為自己的不朽塑造著形象。因此,在線索二中,歌德的對(duì)存在的覺(jué)悟與貝蒂娜不斷追求不朽而失去真正的“我”的存在方式形成了對(duì)位。
歌德與貝蒂娜的故事主要出現(xiàn)在第二部與第四部中,主要寫(xiě)了歌德寫(xiě)《詩(shī)與真》的時(shí)期及歌德死后。從敘事方式看,歌德生前多用傳記式的敘事,主要講述了歌德在1811年至死前與貝蒂娜的故事。在歌德死后則用夢(mèng)幻敘事的方式講述了歌德的靈魂對(duì)不朽和存在的思考。
(二)歌德對(duì)不朽的追求和參悟
與阿涅絲姐妹的故事不同,歌德線索中此在的存在者對(duì)本真和非本真的選擇不僅僅是通過(guò)兩種不同類(lèi)型的人的對(duì)位來(lái)體現(xiàn),還通過(guò)歌德生前和死后兩種不一樣的態(tài)度來(lái)體現(xiàn)。即一個(gè)人的一生之中,既有本真的狀態(tài),也可能會(huì)出現(xiàn)非本真的狀態(tài)。
與阿涅絲一直執(zhí)著于對(duì)本真的追求不同,歌德在第二部未死之前,一直努力為自己不朽的形象作著斗爭(zhēng)。如他為了使自己不朽的形象更加光輝,在拿破侖召見(jiàn)他時(shí),他立刻放下手中的《詩(shī)與真》與拿破侖共進(jìn)早餐,而事實(shí)上,這次面并無(wú)太大意義,倆人都知道他們是在相互擁抱著不朽。此外歌德為了自己的不朽形象而編寫(xiě)《詩(shī)與真》,為了不使自己的形象受曲解,他還特意邀請(qǐng)貝蒂娜來(lái)參與寫(xiě)作,原因是此時(shí)的貝蒂娜正想以自己的名義為歌德寫(xiě)一部童年敘事的書(shū)。可以說(shuō),寫(xiě)《詩(shī)與真》時(shí)期的歌德是追求不朽形象、看重他人目光的非本真性的存在者。
但在之后對(duì)歌德死后的夢(mèng)幻敘事中,歌德為人們已經(jīng)不再關(guān)注他的作品,而去關(guān)注他自身而感到恐懼。他夢(mèng)到他在木偶劇場(chǎng)的后臺(tái)親自牽線并背誦《浮士德》的劇本,隨后他因場(chǎng)子里沒(méi)有一個(gè)人而十分沮喪。突然間他發(fā)現(xiàn)這些觀眾都在后臺(tái)看著他,這使他感到十分恐懼。最終,在參與永恒審判時(shí),他醒悟到“為自己形象而操心是人的不可救藥的不成熟的表現(xiàn)”,并在最后一次與海明威的相見(jiàn)中,他奉勸海明威要正確地對(duì)待死亡,因?yàn)槿怂篮蟊悴粫?huì)存在于書(shū)中或其他東西里面。
歌德最早出現(xiàn)是借助阿涅絲的父親,正是在歌德詩(shī)歌的影響下,阿涅絲感受到了一種生命的寧?kù)o。這表明歌德的詩(shī)歌文本是一種此在的本真性的表現(xiàn)。可以說(shuō),作為一個(gè)復(fù)雜的存在者,根據(jù)不同時(shí)期的經(jīng)歷,他對(duì)存在的本真性和非本真性的選擇可能會(huì)發(fā)生變化,而并非一成不變。從歌德的詩(shī)歌文本到追求不朽的歌德,再到參加完永恒審判的歌德,無(wú)疑是此在的存在者偏離本真又回歸本真的一個(gè)過(guò)程。
(三)貝蒂娜對(duì)不朽的執(zhí)迷
歌德真正的不朽源于他曾創(chuàng)造出反映本真的作品(這些作品在之后也影響著阿涅絲的父親和阿涅絲)。而貝蒂娜的不朽則來(lái)源于將臉努力湊向類(lèi)似歌德、貝多芬這樣的名人。貝蒂娜努力塑造自己不朽的形象,在為了不朽的斗爭(zhēng)中,她甚至失去了最基本的感受,1807年至1811年間,她同時(shí)與歌德和貝多芬調(diào)情,歌德已經(jīng)是六十多歲的老人,“歌德的老,與貝多芬的丑”一點(diǎn)都不讓她難受,反而更加吸引她,因?yàn)橹挥邢墒帕说母璧禄蜇惗喾也拍軤恐氖謱⑺腿氩恍嗟牡钐谩?/p>
歌德死后,她從歌德的遺物中要回了她與歌德的通信,并將歌德與自己的通信大幅度地改編成《歌德與一個(gè)女孩的通信》,里面將“我親愛(ài)的朋友”改成了“我親愛(ài)的心肝”,她改變?nèi)掌冢h掉一些不合適的段落,讓他人感到兩人存在著曖昧的關(guān)系。但最終隨著原稿的被發(fā)現(xiàn),貝蒂娜因?yàn)樽约核茉斓牟恍嘈蜗笞罱K淪為可笑的不朽。
(四)現(xiàn)實(shí)與歷史寓言的對(duì)位特點(diǎn)
小說(shuō)與歷史寓言由時(shí)間差異構(gòu)成了《不朽》中更高一級(jí)的對(duì)位。文本中,歌德的故事與阿涅絲的故事沒(méi)有相交,屬于兩個(gè)同時(shí)進(jìn)行的旋律,共同作為對(duì)存在主題的回答而產(chǎn)生對(duì)位的效果。阿涅絲深受歌德詩(shī)歌文本中本真的影響,對(duì)寧?kù)o產(chǎn)生向往,而洛拉也有與貝蒂娜的相同之處,她們都追求不朽,擁有著相同的手勢(shì)和曖昧的態(tài)度。他們形成的即是在歷史時(shí)空中的對(duì)位,這樣的對(duì)位說(shuō)明在不同的時(shí)空中仍舊存在著對(duì)本真和非本真兩種不同的選擇,再一次體現(xiàn)出昆德拉要表現(xiàn)的不同的人對(duì)存在的不同選擇。
阿涅絲和歌德在各自的故事中都作為自己旋律中的定旋律而存在,而昆德拉在敘述上卻做了兩種不同的處理。阿涅絲的故事中采取的是模糊時(shí)間的片段式的描寫(xiě),她的故事大致可以概括為她父親去世五周年的那個(gè)星期六的下午發(fā)生的一系列事情(第一部),與她死之前的下午所發(fā)生的事情(第五部)。可以說(shuō),節(jié)奏在阿涅絲的故事中表現(xiàn)得十分緩慢,突出的是現(xiàn)代小說(shuō)的模糊敘事、意識(shí)流等特點(diǎn)。
而歌德的故事在第二部中則有明確的時(shí)間和地點(diǎn),如一開(kāi)始的1811年的展覽廳貝蒂娜與歌德之妻發(fā)生爭(zhēng)吵,之后在歌德房間的客廳,與貝蒂娜的幾次接觸有些還有文獻(xiàn)出處。讓人感到昆德拉是用真實(shí)的歷史來(lái)對(duì)存在進(jìn)行說(shuō)明。但此部的時(shí)間跨度比阿涅絲的故事明顯要多,因此在故事節(jié)奏上稍顯快速。
(五)歌德與貝蒂娜復(fù)調(diào)對(duì)位的最小文學(xué)手法構(gòu)成
歌德與貝蒂娜的故事主要由敘述的事件構(gòu)成,在敘述中,可以看到昆德拉采用的是傳統(tǒng)傳記類(lèi)文學(xué)的寫(xiě)法,主要以時(shí)間線索為主。在寫(xiě)作技巧上,運(yùn)用了與《荷馬史詩(shī)》相同的手法,即先將最激烈的矛盾沖突置于開(kāi)始的位置,之后再將事件的起因、經(jīng)過(guò)與結(jié)局慢慢道來(lái)。此部分的敘事更服從事件整一性,主要講了歌德和貝蒂娜各自為著自己的不朽形象而做出的努力。
與之前阿涅絲與洛拉的部分不同,除了最后一處的夢(mèng)幻敘事,整部敘事給人以一種歷史的真實(shí)感,昆德拉在歌德和貝蒂娜的故事中點(diǎn)明了事發(fā)的時(shí)間和地點(diǎn),有時(shí)甚至?xí)o出具體的文獻(xiàn)。
同時(shí),此章的議論均為作者從人物出發(fā)的議論。敘述者對(duì)每次發(fā)生的事件進(jìn)行點(diǎn)評(píng),如同《史記》中的“太史公曰”,從而引起讀者更進(jìn)一步的思考。敘述者在此時(shí),并不是現(xiàn)代小說(shuō)一樣的零度敘事,而是明顯帶有褒貶的色彩。對(duì)于癡迷追逐不朽的貝蒂娜,作者總是在她所做的事情之后,一語(yǔ)道破她的動(dòng)機(jī)。這種歷史敘事的方式讓人感到一種嚴(yán)肅性。
而在第四部中則又通篇為夢(mèng)幻敘事,產(chǎn)生一種張力。第四部分出現(xiàn)在永恒法庭上,里克爾、羅曼·羅蘭等人都是已故的文人,他們?cè)谟篮惴ㄍド咸岢鰧?duì)歌德的訟詞。他們控訴歌德,但此時(shí)歌德并沒(méi)有直接出來(lái)為自己辯護(hù),而是作者直接以第三人稱(chēng)的方式對(duì)這些人的證詞進(jìn)行反駁。昆德拉曾表示他喜歡“時(shí)不時(shí)的直接介入”小說(shuō),以一種“游戲、諷刺、挑釁”的口吻。因此文中直接出現(xiàn)了對(duì)貝蒂娜反映出的靈魂的惡性膨脹的思考和對(duì)羅曼·羅蘭這位“工人之友”支持貝蒂娜而不是作為女工的克里斯蒂娜的立場(chǎng)的反駁。
三、《不朽》線索之三:敘述者作家昆德拉及阿弗納琉斯教授的故事
作家昆德拉先生作為一個(gè)角色出現(xiàn)在《不朽》的文本中,并且以第一人稱(chēng)敘述方式講述他正在寫(xiě)一部名字應(yīng)該叫作《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的小說(shuō)。在寫(xiě)作過(guò)程中,他經(jīng)常與他的朋友阿弗納琉斯教授見(jiàn)面并展開(kāi)討論,最后,作家昆德拉先生完成了小說(shuō),與教授一起慶祝。作家昆德拉先生與教授的故事是貫穿《不朽》始終的另一條線索,猶如阿涅絲與洛拉的故事,只是阿涅絲與洛拉的故事發(fā)生在作家昆德拉先生虛構(gòu)的小說(shuō)空間,作家昆德拉先生與教授的故事相對(duì)而言似乎發(fā)生在現(xiàn)實(shí)的空間——其實(shí)也是《不朽》的虛構(gòu)空間,阿涅絲與洛拉的故事相對(duì)詳盡一些,作家昆德拉先生與教授的故事相對(duì)更為簡(jiǎn)略一些。
(一)作家與阿弗納琉斯教授的對(duì)位
在敘述者作家的世界中,作家與教授同樣作為兩種不同的存在者而存在。如果說(shuō)阿涅絲為定旋律,那么在作家昆德拉的世界中,嚴(yán)肅地思考著存在問(wèn)題的作家昆德拉“我”與滑稽的“與世界做游戲”的阿弗納琉斯教授也形成了一個(gè)對(duì)位。
敘述者“我”與教授的故事斷斷續(xù)續(xù)地貫穿《不朽》文本的始終。雖然“我”和教授在文本中進(jìn)行對(duì)話的次數(shù)多達(dá)6次,但是,在《不朽》第一部開(kāi)始創(chuàng)造阿涅絲、在《不朽》第七部懷念阿涅絲,想象抱著一盆花的阿涅絲走過(guò)她嫌惡的大街,并始終對(duì)存在意義進(jìn)行思考的終究只有敘述者作家昆德拉先生“我”。
從《不朽》第一部、第三部及第五部可以看出,“我”經(jīng)常引出阿涅絲的故事,而教授則總與洛拉的故事相連,并產(chǎn)生交織,教授還直言不諱地表示自己更喜歡洛拉。不論是在第三部中阿弗納琉斯教授與洛拉的相遇,給貝爾納頒發(fā)“十足的蠢驢”的證書(shū),還是之后在戳車(chē)胎時(shí)被當(dāng)作強(qiáng)奸犯被抓,從而導(dǎo)致保羅開(kāi)車(chē)去救出了車(chē)禍的阿涅絲的時(shí)候因?yàn)檩喬牧说⒄`了時(shí)間,后來(lái),保羅還做了教授的辯護(hù)律師。在《不朽》的第七部,教授向作家昆德拉先生介紹保羅,保羅向教授以及小說(shuō)家昆德拉介紹他的新妻子洛拉,以及新婚后的家庭生活的煩惱——孩子。在現(xiàn)實(shí)空間中,與教授發(fā)生直接關(guān)系的都是非本真存在狀態(tài)下的人,帶有物以類(lèi)聚的色彩。
在作者“我”的世界中,阿弗納琉斯教授是一個(gè)滑稽的存在,每天晚上堅(jiān)持帶著大刀跑步,趁人不注意時(shí)將街上的車(chē)胎戳破以此來(lái)保護(hù)自然環(huán)境。不過(guò),教授與洛拉不同,洛拉需要?jiǎng)e人的理解,她失戀了需要向阿涅絲夫婦傾訴,而教授不需要?jiǎng)e人的理解,因此在戳車(chē)胎的過(guò)程中被人當(dāng)作強(qiáng)奸犯而被捕,在辯護(hù)之時(shí)寧愿被人當(dāng)作強(qiáng)奸犯而不說(shuō)出自己帶刀的真正原因。同時(shí),阿弗納琉斯教授是洛拉的欣賞者,在第三部與第七部中與洛拉相遇,并被敘述者懷疑兩人發(fā)生過(guò)性關(guān)系。因此,嚴(yán)肅的“我”與滑稽的教授不僅構(gòu)成《不朽》的復(fù)調(diào)對(duì)位,而且使《不朽》帶上崇高莊嚴(yán)與滑稽可笑混雜的風(fēng)格,與《唐·吉訶德》相似。
(二)敘事者世界與小說(shuō)世界的對(duì)位特點(diǎn)
從《不朽》第一部開(kāi)始與最后一部的結(jié)尾可以看出,作家昆德拉先生“我”創(chuàng)作這部應(yīng)該叫作《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的小說(shuō)是《不朽》文本自始至終的一條線,它不同于歌德的故事,在《不朽》第四部之后就結(jié)束了。“我”和阿弗納琉斯教授的故事在《不朽》一開(kāi)始是作為賦格主題出現(xiàn)的,在《不朽》第一部中出現(xiàn)得并不多,似乎可以說(shuō)阿涅絲的故事在《不朽》第一部中是對(duì)位主題的展開(kāi)。但是,在《不朽》第五部,“我”的故事開(kāi)始與阿涅絲故事交錯(cuò)出現(xiàn),似乎構(gòu)成了《不朽》中另一個(gè)復(fù)調(diào)對(duì)位結(jié)構(gòu)。不過(guò),《不朽》第五部的這個(gè)復(fù)調(diào)對(duì)位,相對(duì)于《不朽》第一部到第四部阿涅絲故事與歌德寓言的對(duì)位,顯得節(jié)奏更加輕快緊湊。中間穿插了第六部魯本斯的插曲,在《不朽》第七部中,阿涅絲的小說(shuō)世界與“我”的現(xiàn)實(shí)世界,超越了小說(shuō)與現(xiàn)實(shí)的界限滑稽地融合在了一起。
從《不朽》第五部可以看出,小說(shuō)結(jié)構(gòu)安排上同一時(shí)間寫(xiě)不同空間發(fā)生的兩件事情,一個(gè)是阿涅絲從阿爾卑斯山回家的那天下午發(fā)生的事;另一個(gè)是“我”與教授見(jiàn)面后發(fā)生的事。阿涅絲和洛拉代表的線索與“我”和教授的線索在此章中的對(duì)位十分明顯。此時(shí)的兩條線索有規(guī)律地反復(fù)出現(xiàn),形成一個(gè)比較明顯的復(fù)調(diào)對(duì)位。
與歌德的寓言世界和阿涅絲的現(xiàn)實(shí)世界以時(shí)間為主的對(duì)位方式不同,在《不朽》第五部中主要是以空間的方式進(jìn)行對(duì)位,阿涅絲所在的阿爾卑斯山,顯然與“我”和教授所在的游泳池不同,但又因表達(dá)方式“當(dāng)……時(shí)”而并行在了一起。這里出現(xiàn)的是一種濃縮的對(duì)位方式。這種對(duì)位直至一個(gè)自殺的少女那里進(jìn)行交匯,自殺的少女是作者昆德拉從廣播里聽(tīng)來(lái)的新聞中的人物,“我”和阿弗納琉斯教授在餐桌上吃飯時(shí)談到了這個(gè)少女,之后這個(gè)少女在阿涅絲的世界引起了阿涅絲的死亡。而急著見(jiàn)阿涅絲的保羅的車(chē)胎又被晚上跑步的教授戳破。兩個(gè)世界再一次發(fā)生關(guān)聯(lián),而阿弗納琉斯教授就如同是連接兩個(gè)世界的橋梁,架在兩個(gè)世界之間。
第七部分為“我”寫(xiě)完小說(shuō)而慶祝。昆德拉本人曾說(shuō)“將最嚴(yán)重的一面跟形式最輕薄的一面相結(jié)合”向來(lái)是他的雄心。第七部無(wú)疑充分地體現(xiàn)了他的雄心。較之第一段直言不諱地說(shuō)出阿涅絲是“我”故事的主人公,最后一部中阿涅絲丈夫保羅經(jīng)阿弗納琉斯教授的介紹與“我”見(jiàn)面,再一次表現(xiàn)出了昆德拉復(fù)調(diào)的獨(dú)有特色比起傳統(tǒng)小說(shuō)在情節(jié)上出人意料的不同,在最后的兩條線索相交的處理方式上,超越了一般讀者的期待視野。
從第一部與第七部可以看出,與《罪與罰》最大的不同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的作家昆德拉先生一出場(chǎng)就交代“因?yàn)橐粋€(gè)老太太的手勢(shì)”他想到了他將要寫(xiě)的小說(shuō)的主人公阿涅絲,進(jìn)而發(fā)出了對(duì)手勢(shì)和存在的疑問(wèn)。這一疑問(wèn)如同賦格中第一聲部的賦格主題的呈現(xiàn),之后的故事都圍繞著“存在”問(wèn)題而展開(kāi)。小說(shuō)《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作為賦格主題的延續(xù),回答了不同的人對(duì)存在的不同選擇,為賦格主題的對(duì)位主題。而在最后,當(dāng)教授晚上拿刀戳車(chē)胎被當(dāng)作強(qiáng)奸犯而被捕從而認(rèn)識(shí)了小說(shuō)中身為律師的保羅,保羅又因車(chē)胎被戳破無(wú)法趕上與小說(shuō)女主角阿涅絲的最后一面。之后保羅又在教授的介紹之下與創(chuàng)造阿涅絲的“我”相見(jiàn)。這種跨時(shí)空的連續(xù)性敘事是在昆德拉之前的作品中不可見(jiàn)的。而這也正是《不朽》復(fù)調(diào)對(duì)位處理突破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傳統(tǒng)復(fù)調(diào)的地方。
此外,《不朽》與傳統(tǒng)復(fù)調(diào)的另一個(gè)不同之處在于對(duì)第六部分插曲的運(yùn)用。第六部與其他幾部不同,里面并沒(méi)有出現(xiàn)對(duì)位的技法,所有敘事圍繞魯本斯而進(jìn)行,形成一個(gè)單線敘事。在結(jié)構(gòu)上形成了昆德拉所鐘愛(ài)的“突兀的并置”。魯本斯同樣作為一個(gè)存在者,開(kāi)始沉迷于肉欲的感悟,直到遇見(jiàn)阿涅絲之后,才慢慢發(fā)現(xiàn)有關(guān)愛(ài)情本質(zhì)的東西,即看一個(gè)人的靈魂而非肉體。他稱(chēng)阿涅絲為“詩(shī)琴?gòu)椬嗾摺焙汀案缣厥降奶幣保聦?shí)上是對(duì)阿涅絲存在本質(zhì)的隱喻。這與阿涅絲的丈夫保羅通過(guò)人的臉來(lái)認(rèn)識(shí)阿涅絲存在差別。在第六部中有個(gè)關(guān)于魯本斯的夢(mèng)幻敘事,在敘事中,阿涅絲變成耶穌的樣子被釘在山頂?shù)氖旨苌希蝗巳河^察議論,而此時(shí)阿涅絲自己仿佛也面對(duì)著巨大的鏡子觀察著自己。作為阿涅絲的情夫,阿涅絲與魯本斯互為插曲而存在。但是當(dāng)魯本斯得知阿涅絲死了之后,發(fā)現(xiàn)自己已進(jìn)入了最后一個(gè)鐘面,即暫時(shí)斷絕與其他女人的來(lái)往。可以說(shuō),阿涅絲對(duì)自我本真的探尋不知不覺(jué)影響到了本為非本真存在的魯本斯。而當(dāng)阿涅絲死后,作為插曲的她卻影響了之后的魯本斯,可謂達(dá)到了一個(gè)真正小的不朽。因而,第六部雖為一個(gè)與前面部分沒(méi)有關(guān)系的突兀部分出現(xiàn),但仍舊點(diǎn)明了關(guān)于存在的主題。
四、結(jié)語(yǔ)
昆德拉小說(shuō)中的對(duì)位技巧,在他的小說(shuō)《不朽》中達(dá)到了最大程度的展現(xiàn),其對(duì)位的方式不僅表現(xiàn)在主人公阿涅絲、歌德的主線上,在其內(nèi)容中更是相互穿插和照應(yīng)。就像昆德拉自己最欣賞的音樂(lè)一樣,難以捉摸,難以熟記,難以縮減為一個(gè)短短的套式,形成一種令人神魂顛倒的錯(cuò)綜復(fù)雜的旋律。
盡管《不朽》的復(fù)調(diào)的復(fù)雜性在閱讀上會(huì)給讀者帶來(lái)一定的閱讀障礙,但也正因復(fù)調(diào)的相互對(duì)位產(chǎn)生一種耐人尋味的效果。昆德拉作為一個(gè)在形式上有自覺(jué)革新意識(shí)的作家,醉心于形式的編織與制作。從《不朽》中不同線索的對(duì)位及線索下不同人物的對(duì)位,將探索存在的哲學(xué)主題與敘述的多種形式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也正是這種形式,達(dá)成了文學(xué)性與哲學(xué)思考的完美交融。
同時(shí)通過(guò)筆者對(duì)《不朽》各個(gè)層級(jí)的劃分還可以看出,《不朽》的復(fù)調(diào)對(duì)位形式既是昆德拉自己創(chuàng)作的一個(gè)集大成,也是對(duì)傳統(tǒng)復(fù)調(diào)結(jié)構(gòu)的超越和突破。這種超越時(shí)間、空間、文體的形式開(kāi)拓了復(fù)調(diào)小說(shuō)新的疆域,昆德拉也因《不朽》的形式而在文學(xué)史上取得自己不朽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