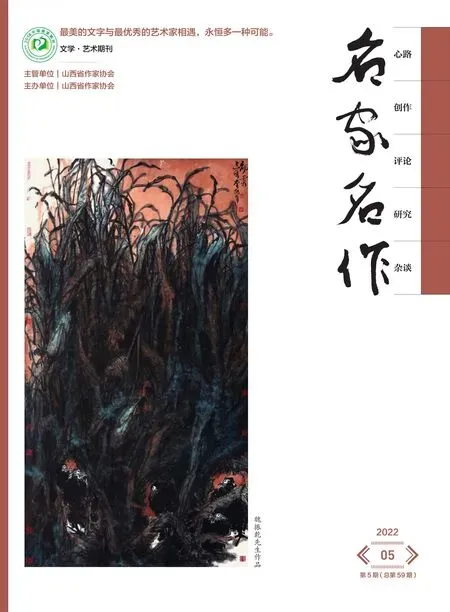傳統與現代—評托馬斯·哈代詩作《針線盒》
邵 妍 石青環
托馬斯·哈代(1840—1928)的小說家地位無可非議,詩人之名卻曾頗具爭議。喜愛者稱之為經典之作、開現代主義先河,批評者稱其詞句拗口,技巧欠佳。表面看來,繼1895年《無名的裘德》出版之后來自多方的負面評論令他心灰意冷,一心正式投入詩歌創作。實際上他從青年時期一直都在堅持寫詩歌,而且認為小說用以糊口,詩歌才是他真正熱情所在。如他自己所言,詩歌是他所創作的文學作品中最能體現自我的部分,和小說相比,他的詩歌更加清晰地反映了他的哲學思想和個人體驗。自1898年底《威塞克斯詩集》出版之后,哈代寫詩不輟,留下八本詩集和史詩劇《列王》。現今看來,他在英國傳統詩與現代詩斷層間占據關鍵地位。貫穿于哈代詩中的是反傳統的態度和對存在困境的思考,他寫詩的主要素材是并不浪漫且很難入詩的“中性的灰色和偶然”(《他從未期望過高》),他秉信的哲學理念是真實。
《針線盒》選自詩集《境遇的嘲弄》()。這首詩以民謠的風格講述了一出戲劇場景。這一幕戲劇其實有四位參與者:講述者(旁白),丈夫,妻子,死者(未出場)。木匠丈夫送給新婚的妻子一個針線盒,得知木料的來源后,妻子大驚失色,暗示出一個悲傷的愛情故事。
全詩如下:
“瞧這個針線盒,愛妻,
是我用光潔的橡木做的。”
他,是村里的細木匠,
她呢,從鎮上嫁到此地。
他把禮物遞給妻子,
妻子走近來面帶笑容,
對送禮的丈夫回答道:
“這針線盒夠我一輩子用!”
“這我能擔保。還不止呢。
這盒子用的是邊角料,
給約翰·韋沃德做棺材剩下的,
他為何死去,誰也不知道。
“你看這鱗狀的木紋
似乎到你的盒邊已經結束,
其實卻繼續向前延伸,
沿著伴他長眠的棺木。
“我做活時不禁心中思量:
木料有不同的命數:
這一寸在人們吃喝的世上,
第二寸卻進了墳墓。
“親愛的,你怎么臉色發白,
干嗎把臉轉到一旁?
你不至于認得那個青年吧?
雖說他和你該是同鄉?”
“雖然他和我來自一個鎮里,
我又怎么會認得他?
他一定早已離開了本地,
而我那時怕還沒長大。”
“噢,那么,我早該想到,
準是這件事嚇壞了你:
我給你這一頭木料,
那一頭卻在墳墓里!”
“親愛的,別小看我的智力,
純粹偶然的事物
從不至于影響我的心理,
弄得我心神恍惚。”
但她的嘴唇蒼白,發顫,
她的臉仍躲向一邊,
仿佛她不但認識約翰,
還知道他死的根源。
從形式上來看,該詩有10小節,基本使用抑揚格,屬于傳統詩歌民謠體:4行詩節,2、4行押韻,1、3行各4音步,2、4行各三音步,以疊句和重復來增強音樂效果。內容上這是一個愛情悲劇,有許多值得推敲的細節。
一、講述者的弱化
詩歌的講述者極力弱化自己的地位,主要以對話呈現情節。1、2節介紹場景,新婚夫妻的出身,丈夫送給妻子針線盒,妻子含笑接過,勾勒出溫馨的家庭生活畫面。3、4、5節丈夫道出木料的來源乃是棺材的邊角料,抒發感慨;6、7、8、9節夫妻之間一問一答,丈夫猜測妻子大驚失色的原因,妻子一一否認;最后一節,講述者采用暗示性的旁觀者視角,點出暗含的愛情悲劇。
故事情節中暗含過去和現在。講述者更像是一個不帶主觀色彩的旁觀者,從一開始對新婚夫妻場景的介紹,到最后對妻子行為的解讀,從溫馨的氛圍到殘酷的暗示,情節的變化沒有影響講述者主觀感情的變化,或者說,這個客觀的講述者知曉全情,卻不露聲色。
為什么詩人沒有用妻子之口講述這個故事,也沒有用講述者的口吻直接表達他自己的思想?他努力避免自己的直接出現,整個情節的完整需要讀者來補足:妻子本期待這個針線盒夠用一輩子,結尾處這種對未來的憧憬蕩然無存,以后日常要使用針線盒就會想起逝去的昔日戀人,連提及都充滿痛苦,面對更加難忍。和小說不同,這首詩的講述者有意弱化了自己的全知身份,也盡力避免發出主觀論斷。它像是一幕劇,在真相幾近揭曉之刻戛然而止。詩人的目的已經達到:人類的生存狀態就是如此。愛情的真相就是命運的真理,“偶然”背后是一種“必然”。
二、并置的意象、場景和主題
小小的針線盒另一方是棺材,溫馨的家庭場景背后是陰暗的墓地,無果的愛情元兇是無動于衷的命運。這種巧合似乎帶有某種命定,“命數”一詞,哈代借丈夫之口指出其無常:“你看這鱗狀的木紋/似乎到你的盒邊已經結束,/其實卻繼續向前延伸,/沿著伴他長眠的棺木。”“我做活時不禁心中思量:木料有不同的命數:這一寸在人們吃喝的世上,第二寸卻進了墳墓。”
這兩個詩節中冥冥之中的偶然如同宿命,其實哈代揭示的是人類共同的生活狀態。他筆下的命運之神是冷漠、乖戾,對人間疾苦毫無同情。他詩集的書名中出現的“笑柄”“嘲弄”“片刻”等詞,反映人在命運和境遇面前的謙虛。人在冷漠宇宙中微不足道,唯有依靠記憶和想象營造自己的理想世界。
妻子口中是“偶然”,丈夫認為是“命數”,導致同一塊木材的天壤之別。在這里,哈代十分純熟地使用意象并置技巧(針線盒和棺木)來表達命運主題。到現代派手里,用并置意象連接生死成為常態,承認受哈代影響頗深的狄蘭·托馬斯就寫下如下詩句:
通過綠色莖管催動花朵的力
也催動我的綠色年華;使樹根毀滅的力
也是我的毀滅者
……
我也無言可告情人的墓穴
我的衾枕上也爬動著同樣的蛆蟲。
狄蘭·托馬斯的詩歌往往以異于常規的語言方式排列,利用各種語言手段打破語言規律的束縛,從而凸顯現代主義詩歌語言的美學張力。他的意象是跳躍性的藝術狂想,同內心意識的流動相吻合,看來如同以超越邏輯的語言表達非理性的怪誕意象。他對生與死、創造與毀滅的思考蘊含著豐富超凡的想象力和洶涌激烈的內心情感。詩人試圖潛入意識的深海,以看似匪夷所思的意象并置來體現詩人內心世界的神秘莫測。他一脈相承了哈代對人生、生死、愛情的哲思,只是表現形式超越了邏輯和理性。同現代詩人將自然與人類、愛情與死亡以更直接的方式并置相比,哈代同樣深刻,卻更加樸素,這源于他土生土長的英國氣質和對傳統的堅持。處于傳統和現代斷層期的他,致力于表達他心目中的真實,對愛情和命運有著獨到的見解。
三、哈代式真實:曾經的愛情與強大又漠然的命運
由于悲劇意識和憂患意識,哈代經常被貼上“悲觀主義”的貶義標簽,他對此很不以為然。他只是客觀反映人類生存的基本問題,把個人經歷與人類經驗,把過去、現在和將來結合在一起,愛情和命運交錯,一切皆是偶然。
哈代筆下的愛情往往是悲劇性的,苔絲與安琪,裘德與淑, 游苔莎與克林,刻骨銘心的感情往往不得善終,令人生出一種身不由己之感。《針線盒》中的愛情故事也是如此。新娘和約翰青梅竹馬,最終一個嫁到他鄉,另一個離開人世。讀者無法像讀小說那樣得知來龍去脈,詩人也無意詳述過程,僅點出“命運”或者“命數”使然。
妻子對丈夫的猜測極力否認,卻漏洞百出:一邊稱呼逝者為小伙子,可見兩人年齡相仿,一邊聲稱兩人年齡差別大(“……他一定早已離開了本地,而我那時怕還沒長大。”)愛情主題為何如此不和諧?哈代的詩歌很少見甜蜜的愛情場面,惦念亡妻的《艾瑪組詩》(收入《境遇的嘲弄》)在回憶過去的同時滿懷悔恨,昔日你儂我儂都變成如今聚散兩茫茫。愛情存在過,但敵不過時間,或者說,命運這個強大的主題。
詩人借丈夫之口,道出想要表達的主題,即命運的無常。在愛情層面,這位丈夫是無知的:兩次猜測妻子面色大變的原因,被一再否定,對妻子的自相矛盾視而不見,茫然不知,真相還要靠講述者點出。但他無意間的喟嘆卻道出了詩歌的主題。在哈代的詩歌中,局外人比當事人更有洞察力,幽靈比生者更接近本質。
在哈代看來,歸根結底,命運既沒有好意也沒有惡意,它實質上就是無動于衷的客觀性。不同于希臘悲劇中神意規定無可逃遁的必然宿命,哈代認為的命運其實是偶然,而偶然一旦發生就成了必然,對于這種偶然,人類投訴無門,困惑無助;獲得安慰的手段就是記憶和想象。詩人視詩歌為記錄形式反映生活,極力弱化傳統的全能講述者的地位,如戲劇一般呈現給讀者生活的真相。
愛情和命運的雙主題是由兩個“局外人”視角揭示的:妻子和約翰的愛情主題是由講述者暗示的,丈夫不知情;無常的命運主題是借丈夫之口說出的,其余角色(妻子,講述人)未予評論。就連無果的愛情雙方,對于愛情的真相都是含糊的表示:約翰已深眠地下,無法開口,詩人也沒有像在其他詩歌中那樣,給幽靈以開口的權利表達真知灼見;妻子更是一再否認,言語中漏洞百出,只有蒼白不安的神情被講述者透露實情。對于無常的命運,講述者沒有直接抒發感嘆,只有愛情情節中的局外人丈夫表明思想,而且分外精辟。這就呈現出一種有趣的“偶然”:愛情的局外人洞悉了命運的真理,這感慨也是偶發的。過去不知現在之知,當局者不如局外人之知。
四、哈代的哲學思想
哈代的生活年代適逢各種文學流派的風起云涌和工業文明的步步入侵,伴隨而來的是以叔本華為代表的悲觀主義哲學思想。表面的繁榮背后深刻的社會、經濟、政治、信仰危機逐漸深化。生長在傳統的維多利亞時代,哈代目睹了現代工業文明帶來的社會發展以及與之相伴的對鄉村生活的破壞,他的小說和詩歌中就數次出現了火車這個意象,暗示社會發展突飛猛進,而車上的人們被動地搭載著時代的列車,好奇而又茫然地駛向未知的前方。身處歷史的漩渦,哈代的思想歷程也經歷了跌宕起伏。在他的詩歌中既有對傳統信仰情不自禁的崇敬,也有失落之后深刻的思考。他開始反思這個與人類情感和原來價值觀格格不入的世界。他廣泛地閱讀同時代的哲學著作,叔本華、尼采的作品都在他的研讀之列,并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哲學視角。
讀者在閱讀哈代的作品時常為彌漫其中的悲觀色彩和宿命感所震撼。其實他悲觀的底色既不是怨天尤人的哀嘆,也不是居高臨下的悲憫,他捕捉的是人類面對掌控其命運的宇宙“內在意志”體現出來的渺小。那不可控制的內在于宇宙的意志力,如同冷酷無情的怪獸,推進著人類走進自己“偶然”的命運。這股力量如此強大,人類意志無法與之抗衡,詩人能做的唯有記錄下這矛盾的一切——有神論與無神論的碰撞,強大的內在意志與人類強烈情感的矛盾,他清醒而又不安,既無法與傳統的信仰決裂,也不能完全擁抱新思想,種種矛盾碰撞在這首小詩的多重視角和多重解讀中盡顯。
總之,哈代從不滿足于采取單一角度展開觀察和描述生活,他的詩作是哈代式真實的典型呈現:它包括用感官觀察到的自然力量和事物,再加上觀察和理智無法解釋的情感。宇宙的內在意志冷靜地推進著人類的命運,一無所知的人們在自己的人生舞臺上上演著自己的悲歡離合。不同于傳統有神論的人生美好萬物可愛,也不同于現代信仰缺失的一切混沌,這位承上啟下的偉大詩人身處古老主流傳統的同時兼具現代的深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