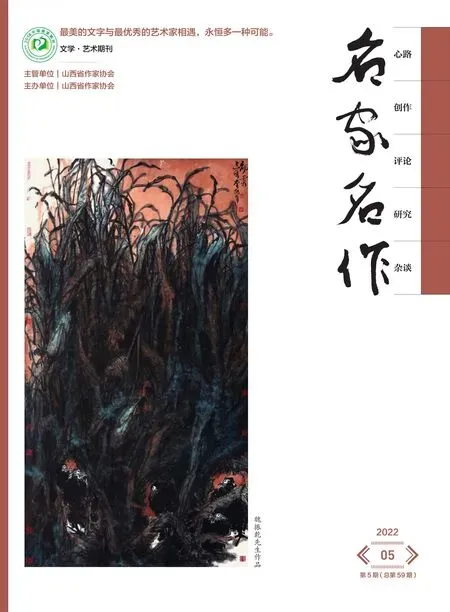以沈從文的《邊城》為例分析京派文學的流派特征
殷顥綺
京派文學遠離政治和商業(yè),追求創(chuàng)作的獨立和自由,是一支逆時代潮流,選擇特立獨行的流派。本文以沈從文的《邊城》為例,從秉持文化保守主義思想、沈從文筆下的湘西世界、抒情體樣式小說、崇尚理性與古典主義四個方面來闡述京派文學的流派特征。
一、秉持文化保守主義思想
京派是“新文學中心南移到上海以后,三十年代繼續(xù)活動于北平的作家群所形成的一個特定的文學流派”,京派作家秉持著京城的風度:不迎俗趨時,不翻新冒進,保持著清高淡泊的人格。此外,京派作家大多是高等學府中的教授或者準教授,他們的經濟收入穩(wěn)定,學問上各有造詣,因此,他們在創(chuàng)作上反對浮躁的商業(yè)化、政治化、“現代化”的海派文學,追求文學的自由和純正,要求作品以“節(jié)制、和諧而圓融”作為審美追求。他們的作品傾向古典主義,追求理性、崇尚古典,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在樸實的鄉(xiāng)村尋找純凈的人性。京派作家的作品高蹈于時代之外,因而呈現出文化保守主義的立場。
文化保守主義的主旨是“立足于傳統(tǒng)文化,力圖融合古今,也有選擇地吸納外來文化,以適應時代需要的思想傾向或思想派別”。沈從文的保守主義思想特質是以優(yōu)秀民間文化為民族重造的根本基地,以鄉(xiāng)下人的眼光來觀照城市、現代文明,將鄉(xiāng)村和城市的文化對立,反思現代文明中的弊病,意圖從民間發(fā)現中華文化的活力,重塑民族品德。沈從文在《〈從文小說習作選〉代序》中也說道:“我實在是個鄉(xiāng)下人,說鄉(xiāng)下人我也毫無驕傲,也不在自貶。鄉(xiāng)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遠是鄉(xiāng)巴佬的性情,愛憎和哀樂自有它獨特的式樣,與城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頑固,愛土地,也不缺少機警,卻不甚懂詭詐。”我們可以在沈從文的作品中窺見他思想中“鄉(xiāng)下人”的保守一面。
二、沈從文筆下的湘西世界
京派作家的創(chuàng)作內容以鄉(xiāng)村中國為主,同時作家將自身的精神世界與之融為一體,呈現出獨特的鄉(xiāng)土風情。京派作者通過描寫他們的家鄉(xiāng),例如蘆焚筆下的河南、汪曾祺筆下的高郵、蕭乾筆下的北京,在古老的土地上追尋著純潔的人性,展現了京派節(jié)制、和諧而圓融,散發(fā)著隱逸氣的審美文化心境。沈從文的湘西世界亦是如此,比如其代表作《邊城》,便是一曲靈秀悲遠的田園牧歌。
《邊城》以湘西邊境的一個小山城為背景,敘述翠翠與儺送的愛情故事,表現了純潔的人性和生命的莊嚴。湘西邊境那個名叫“茶峒”的小山城,臨溪而住的是一個老人和一個女孩子,還有一條黃狗。通過依山傍水的地理環(huán)境,描繪了一個沖和淡遠的文化世界,而生活在這里的人們,自幼受天地靈氣的熏陶,也展現溫順善良的“鄉(xiāng)下人”的特點,他們用“愛”構建著這個桃花源一般的湘西世界。
沈從文為讀者描繪了一幅風景優(yōu)美、民風淳樸的自然風俗畫。茶峒有著獨特的風俗,例如在端午節(jié),人們可以去城里看龍舟,或是在河里捉鴨子,誰捉到就歸誰。在捉鴨子的游戲里,儺送與翠翠相識。茶峒的婚嫁習俗也很特別,走車路,是家長做主,請媒人說親,走馬路則是自己做主,要為女孩唱三年六個月的歌。儺送若是娶王團總的女兒,便可以過上富足的生活,但他拒絕做碾坊的主人,甘心撐一艘小船,可見儺送是個不貪圖物質的人。儺送在追求翠翠的時候,也免去了俗套,主動走馬路,通過為翠翠唱歌的方式來表達愛意。淳樸的民風之下彰顯了人物的人性美。翠翠和爺爺雖然生活拮據,但爺爺渡船時若有人執(zhí)意要給錢,是會被爺爺狠狠回絕的,而若有喜事,爺爺便會欣喜地收下過路人的紅包。船長順順為人仗義,看到這爺孫倆生活不易,節(jié)日里便派人送去許多三角粽。高尚的人性與淳樸的民風相互映襯,共同構成了沈從文筆下美好的湘西世界。
此外,與海派文學展現的五光十色的霓虹燈相比,京派文學則透露出純凈的底色。沈從文小說的底色是翠綠色,不僅是因為茶峒多竹篁,也是翠翠名字的由來,這種翠綠色包含了生命和永恒的意蘊。優(yōu)美的自然環(huán)境和純潔的人性相映成趣,這也印證了京派作家對于人與自然和諧的追求。
三、抒情體樣式小說
沈從文的小說被稱為文化小說、詩小說和抒情小說。“京派作家把作品寫成了雅致瑩潔而帶著矜持的憂郁的人生抒情詩和蕭閑淡雅而散發(fā)出悟道于自然的隱逸氣息的鄉(xiāng)土抒情詩。”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融入了較多個人的主觀感受,因而極具作家本人的個性特色。沈從文在他的小說中便用“愛”去構建世界,去反映邊城的人性美和自然美,給讀者展現出化外之境的優(yōu)美和諧,與城市世界呈現出對抗性。此外,《邊城》通過象征、隱喻的手法,注重散文化的筆調,讓讀者在閱讀時如同在看散文詩一般。
沈從文在《邊城》一書中淡化情節(jié)、時間和人物,將自然景物情感化,環(huán)境是人物的外化,進而抒情。一方面透過自然景物來塑造人,景即人。“翠翠在風日里長養(yǎng)著,故把皮膚曬得黑黑的,觸目為青山綠水,對眸子清明入水晶。自然既長養(yǎng)她且教育她,為人天真活潑,處處儼然如一只小獸物。”翠翠是由大自然孕育的精靈,故而簡單天真,極具神性。另一方面,環(huán)境作為抒情主人公的出場背景,能渲染氛圍。在小說的第二章作者不急于交代人物和情節(jié),而是通過一大段文字對邊城的風光進行了描繪:茶峒地方憑水依山筑城,近山一面,城墻儼然如一條長龍,緣山爬去。臨水一面則在城外河邊留出余地設碼頭、灣泊小小篷船……沈從文向讀者介紹了吊腳樓、白河,通過詩情畫意的自然環(huán)境描寫,展示了茶峒淳樸的民風民俗,將讀者帶入一種慢節(jié)奏的生活中,進入湘西世界。
“作者、敘述者和主人公三者合一,作者直接參與到故事中去感受、去抒情。”沈從文將自己置身于故事之中,他以鄉(xiāng)下人的眼光去審視現代文明,通過描繪世外桃源——茶峒,歌頌這個小村莊里人性的至真、至善、至美,將茶峒與現實世界區(qū)別開來,反襯出現代文明的弊病。此外,沈從文身為鄉(xiāng)下人,對茶峒這個小村莊,是基于自身生活的感悟和對鄉(xiāng)村獨特的情感,因此,以“我”為主體的抒情,流露出的情意真摯自然。
沈從文用“愛”構建了這個湘西世界,甚至當人物之間發(fā)生沖突、矛盾之時,都用“愛”來一一化解,“愛”成為這個小說的主旋律。爺爺怕自己走后,無人照顧翠翠,便想早早替翠翠找到好的歸宿,這是爺爺對翠翠的愛。儺送和天保都愛上了同一個姑娘,但是兩人公平競爭,天保意外死去,儺送得知后,顧及兄弟之情,毅然出走。沈從文在《致布德》的信中這樣寫:唯一特別處,即一生受社會或個人任何種糟蹋挫折,都經歷一種掙扎苦痛過程,反報之以愛。……因這個印象而發(fā)展,影響到我一生用筆,對人生的悲憫,強者欺弱者的悲憫,因之筆下充滿了對人的愛和對自然的愛。
《邊城》飽含著深厚的悲劇意蘊,是一首優(yōu)美哀婉的抒情歌謠,用湘西人構建湘西世界,借由美人美景來抒發(fā)哀婉之情。人物的發(fā)展受命運的牽制,最終導致悲劇,但是他們在面對強大的命運時,卻表現出人性的真與美。作者希望讀者在作品之外有所啟發(fā),感受到另一種人生,收獲“向善”的力量。
四、崇尚理性與古典主義
京派小說主張人物的個性鮮明、情感克制,呈現出理性的色彩,在新舊的變革中追尋逝去的美。這與西方古典主義的基本特征有相似之處,中國現代古典主義文學是在西方古典主義的基礎上,結合了中國特殊的時代背景、文學語境和文學生態(tài),其在理論和創(chuàng)作上表現為推崇理性、崇尚古典、追求自然人性。此外,沈從文立足于傳統(tǒng)文化,有選擇地吸納外來文化,因此其創(chuàng)作適應時代的發(fā)展。
《邊城》中的語言是克制的。從語言結構的角度說,沈從文注重長短句的間隔使用,以保持其內在節(jié)奏感,使文章的語言像散文詩一般。此外,小說里人物的情感也是理性克制的,例如主人公翠翠,對于二佬的出走,她并沒有產生過于強烈的情感起伏,只是平靜地等待二佬的歸來。
再例如小說的結尾:“這個人也許永遠不回來了,也許‘明天’回來。”這樣的結局帶著一種挽歌式的悲傷,起到了言有盡而意無窮的留白作用。京派作家筆下的作品,就是這樣的一種“優(yōu)美”的古典審美,構成了悲劇美學特質。“美的悲劇性存在或者毀滅有時不是由于人性的弱點,而是由于被稱之為命運的力量,或偶然的因素所支配。”同時,對于這樣的傷感情緒,作者在描寫的時候又是隱忍克制的,“也許‘明天’回來”雖然讓讀者看到了希望,但是,這樣的希望是否真實存在,又引人陷入深思。如此詩化的語言,帶給讀者一種平和沖淡的美感。
生活在茶峒的百姓生性淳樸善良,他們的生活不受外界干擾,呈現在讀者面前的就是自然本真的人物形象。順順為人大方,性情灑脫,喜交朋友;大佬豪放豁達,不拘小節(jié);二佬聰明靈秀,重情重義;爺爺恪守本分,為人敦厚。此外,翠翠對于男女感情的羞澀表現也是自然流露,她因愛萌動而去摘虎耳草,愛看嫁新娘;對生活有了煩惱,和爺爺也有不能言說的心事;當爺爺提及讓儺送唱歌提親時,翠翠懇請爺爺不要說笑話。而儺送的出走,也是遵循了自然人性,他若不走,對于哥哥退讓后的意外遇險,他心里會過意不去,同時,他對于老船夫的行為也是有些厭惡和怨氣的,在這樣矛盾的心境里,他無法面對翠翠,他的出走也是必然的。
在茶峒,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是和睦友愛的,無論是鄰里、兄弟、朋友,還是和一面之交的陌生人。比如爺爺不收過渡人的錢,反倒還慷慨地送人一把煙草。遭世俗厭棄的妓女在這里得到尊重,并且和水手有著真摯的情感。除此之外,人與自然也是和諧共處的。翠翠取名于自然,同時,也是自然孕育了她的生命,使她成為一個堅韌成熟的女性,更加扎實地生活在這片土地上。“不許哭,做一個大人,不管有什么事情都不許哭。要硬扎一點兒,結實一點兒,方配活到這塊土地上。”“怕什么?一切要來的都得來,不必怕!”這是爺爺死前對翠翠說過的話,也展現了這一方土地上生命的堅韌。
五、結語
由于現代文明對傳統(tǒng)文明的沖擊,京派作家感慨傳統(tǒng)文化的即將逝去,在無法挽留的情況下,他們在思想上的矛盾愈加激烈。因而,他們的作品呈現出一邊歌頌美好的人性,一邊感慨命運的無常的復雜狀態(tài)。
沈從文在題記里寫道:“我將把這個民族為歷史所帶走向一個不可知的命運中前進時,一些小人物在變動中的憂患,與由于營養(yǎng)不足所產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樣活下去’的觀念和欲望,來作樸素的敘述。”他認為作家應當有社會責任感,有義務為這個社會的進步做出貢獻,抑或是能喚醒讀者們對現實的關注。他期望讀者可以記住這些為民族復興大業(yè)而努力的人們,給予他們力量與勇氣去努力活下去。
綜上所述,以沈從文的《邊城》為例透視京派小說的流派特征,我們看到了京派小說逆潮流而上的魄力與秉持傳統(tǒng)的毅力,京派作家力求展現出人性純凈的光輝和崇高的人道主義精神,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但同時,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其局限性,京派小說所描繪的生活過于理想化,與現代工業(yè)社會前進的方向相背離。總的來說,京派小說的文學風韻和語言魅力都給后人留下了一筆寶貴的財富,值得我們細細品味和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