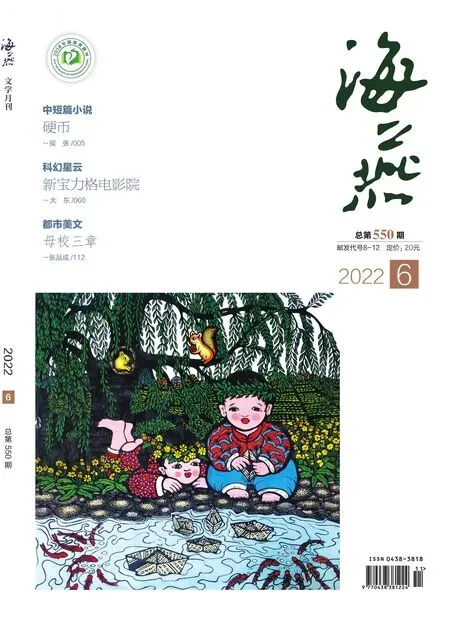顛倒夢想
文 郝萬民
一
趙清醒走進局長辦公室,用亮亮的眼睛看著李長文,臉上閃爍著自豪興奮得意激動,同時又夾雜著不安和難為情,搞得堂堂的局長李長文有些不知所措。
李長文問:“怎么啦?有事?”趙清醒生出些許不快,心想他對我怎么還是這樣的態(tài)度?還問我怎么啦有沒有事,我來的目的你難道不知道?雖然不快,卻不能明顯地表現(xiàn)出來,那樣會顯得胸襟不寬。也不能沉不住氣顯露痕跡直接提醒,那樣會顯得不夠深沉。趙清醒仍然什么都不說,繼續(xù)盯著李長文看得目不轉睛。李長文更加摸不著頭腦,又問趙清醒到底有沒有事,趙清醒心中的不快抑制不住了,在臉上顯現(xiàn)出一絲絲不滿,說:“局長,我的事您是不是應該安排一下?”
李長文已經(jīng)莫名其妙了,說:“你什么事?安排什么?”這時輪到趙清醒丈二和尚了,心想局長這是怎么啦?順理成章的事干嘛這般對待?是在打馬虎眼?不對,沒有誰會對如此嚴肅的事打馬虎眼。想反悔?就更不對了,事情根本就不是他說了算。又一想,心中忽然開竅了,局長這是在刁難自己,想給自己一個下馬威,免得自己以后有所膨脹有所驕傲。更重要的是把自己繼續(xù)抓在手心,免得自己羽翼豐滿后向他的權威發(fā)起挑戰(zhàn)。還有,自己馬上要面臨一個站隊的問題,局長應該是在欲擒故縱,讓自己明白他才是真正的老大,不要把形勢看錯。
瞬間想得如此明白,趙清醒定下心,把一絲絲不快收起,又誠懇又真摯地說:“局長放心,我在您手下鞍前馬后十多年了,從來沒有過二心,以后對您也不會有任何二心。以前我工作扎扎實實,以后仍然會扎扎實實。我地位變了,但我不會驕傲自滿,甚至可以夾著尾巴做人。”

趙清醒口中這樣說心里卻不以為然,覺得李長文用這樣的方法對付自己有些過分。至于搞得如此曖昧如此神秘嗎?有什么話不可以明明白白地說?當官控制下屬確實需要手段,可是那是要分對象的。以前自己是中層干部,你用這樣的方法無可厚非,現(xiàn)在我趙清醒也是高層干部了跟你只差半級,這樣做不等于小兒科嗎?趙清醒暗暗下定決心,今天的事絕對不能不了了之,以后一定找機會想辦法給李長文添一些堵讓他過得不痛快。
此時李長文已經(jīng)墜入五里霧中,看著趙清醒,覺得世界顛倒錯亂得無法看清無法把握了。李長文灌一大口茶,帶著一些猶豫,說:“我到現(xiàn)在也沒弄清楚你的意思,請你說明白一些好嗎?”趙清醒更加氣憤,卻仍然沒在臉上表現(xiàn)出來,說:“你就別跟我開玩笑了,盡快幫我安排了我好馬上開展工作。”李長文更加迷惑,說:“你讓我安排什么?你說你地位變了,怎么個變法?”
趙清醒的怒氣再也壓制不住,臉上現(xiàn)出不滿,聲音提高一些,說:“局長,這就不對了吧,干嘛明知故問?昨天全局大會,組織部領導宣布,不是讓我當副局長了嗎?你應該讓辦公室盡快給我安排辦公室,召開會議明確我的主管方向。”
趙清醒的一席話,聽得李長文目瞪口呆。怎么回事?空穴來風?怎么來得這么大這么莫名其妙?昨天根本沒開過會啊!昨天是星期天所有人都不上班,怎么可能開過會?局里一個副局長退休了是要弄一個副局長,候選人有好幾個,趙清醒是其中之一。
一段時間以來,所有候選人都使出渾身解數(shù)活動來活動去,搞得整個系統(tǒng)混亂不堪。趙清醒活動力度相對較小,但也沒閑著。可是到底選哪個組織部正在研究,最快也得一個月后才能確定。在如此敏感的時間段趙清醒怎么來了這么一出?是在跟我這個局長耍花招?不像,趙清醒在群眾藝術處處長的位置好幾年了,工作一直做得不錯,可以說是一個挑不出什么毛病的中層干部,基本上不搞陰謀詭計,待人誠懇,算得上聰明人但只是普通聰明,應該玩不出什么花樣。是在開玩笑?也不像,玩笑可以開,文化局嘛,除了政策法規(guī)處大家工作都比較輕松,有時甚至比較隨意,開玩笑的事常有發(fā)生。可是再輕松再隨意,也不能把玩笑開到這樣的程度吧?作為老牌處級干部,這個度他趙清醒應該是能把握好的。
李長文最終得出結論,趙清醒不是在跟他耍花招,也不是在跟他開玩笑,而是精神失常了。李長文覺得好笑,臉上現(xiàn)出笑意,說:“清醒啊,清醒清醒吧,回去好好工作,別胡思亂想。”趙清醒說:“局長您怎么可以這樣說話?我怎么可能不清醒?怎么會是胡思亂想?你是不是覺得我當副局長不夠格?可是那不是你說了算,是組織部說了算。就算你想把我的副局長撤掉,也沒有那個權力吧!”
李長文狠狠地拍一下桌子,大聲說:“夠啦,別在這兒胡說八道了,趕緊回去工作,實在不行去精神病醫(yī)院好好檢查檢查。”趙清醒也拍一下桌子,沒有李長文拍得響,卻也讓放在桌子上的電腦顯示器搖晃了好幾下,大聲說:“李長文,你不要侮辱我,不能我沒表示跟你站隊就打擊我,你作為局長要有胸懷有格局。”李長文說:“好吧,我沒有胸懷沒有格局。但我提醒你一下,沒有人宣布你當上了副局長,那只不過是你想當然了。”趙清醒說:“怎么可能?明明昨天開的大會。”李長文說:“昨天是星期日根本沒有人上班,是鬼跟你開了會吧?”
二
出局長辦公室,趙清醒在走廊里走得很慢,腦殼里的大腦已經(jīng)變成混亂不堪的豆腐渣。迎面碰上了自己的下屬小張,攔下來,問:“小張,今天星期幾?”小張說:“星期一。”趙清醒說:“昨天呢?”小張像看怪物一樣看著趙清醒,說:“昨天,那就應該是星期日呀。”趙清醒說:“你確定?”小張說:“確定一定以及肯定,今天星期一昨天星期日,處長你沒事吧?”趙清醒說:“沒事沒事,你去忙吧。”小張慢慢走開,一邊走一邊回頭,臉上現(xiàn)出濃濃的不可思議。
趙清醒來到政策法規(guī)處,見到了處長老孫。老孫很客氣,說:“怎么百忙中來我這里啦?有指示?”趙清醒說:“你干的這一套我一竅不通,哪能有什么指示。啥事沒有,就是隨便過來坐一會兒。”老孫說:“你們處清閑,還能隨便過來坐一會兒。我就不行了,哪也去不了,事情一個接一個。”趙清醒說:“是啊,全局數(shù)你最忙,聽說你們昨天又加班了?”老孫說:“沒有啊,昨天我跟幾個哥們兒去釣魚了。釣出來馬上燉,真新鮮,下回帶你一起去。”趙清醒說:“好好好,一起去,我請客。”
回到自己的辦公室,趙清醒緊緊地關上門,坐在沙發(fā)上,做幾個深呼吸,打電話給妻子錢艷玲。趙清醒說:“艷玲,今天星期幾?”錢艷玲沒好氣地說:“你傻啦?問這樣的問題?”趙清醒說:“我沒傻,告訴我星期幾。”錢艷玲說:“星期一,別沒事瞎打電話,我忙著呢。”趙清醒說:“我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事要問你,昨天我是不是加班啦?”錢艷玲說:“加什么班加班,昨天你一直在家看電視,我讓你幫我洗衣服你還跟我吵了一架,到現(xiàn)在我的氣還沒消呢。”趙清醒說:“這怎么可能……”錢艷玲說:“腦袋讓門擠了吧?晚上回家看我怎么收拾你。”趙清醒還想說什么,手機里卻傳出了嘟嘟嘟的聲音,趙清醒只得把手機放下,腦袋靠在沙發(fā)的靠背上,閉了眼睛,細細地想到底出了什么事。
趙清醒記得清清楚楚,昨天確實開會了,自己被任命為副局長了,所有細節(jié)此時仍然在腦袋里放電影一般明明白白。宣布后組織部領導發(fā)表講話,勉勵他要嚴于律己團結同志,很好地發(fā)揮作用。自己也發(fā)了言,表示不會辜負組織上對自己的信任和同事們對自己的支持,一定不遺余力地把工作做好。發(fā)言時對所有人進行了觀察,發(fā)現(xiàn)大多數(shù)人投向自己的目光都帶著羨慕和鼓勵,只有一小部分人帶著嫉妒和不甘。
如此清晰明白的一件事,怎么會像沒發(fā)生一樣,其他人沒有一點印象?難道確實沒有發(fā)生?不可能,自己記得清清楚楚,肯定真真實實地發(fā)生了。既然發(fā)生了,所有人卻都不承認,那么很明顯,有人設計了一個類似于指鹿為馬的陰謀。這個陰謀絕對大手筆,下的力氣大得難以想象。不但要把全局的人設計在其中,還要把省委組織部納入其內(nèi)。否則自己在文化局這邊無法揭開,在組織部那邊也能打開突破口。更讓趙清醒覺得難以置信的是,把他的愛人錢艷玲也設計進去了。錢艷玲跟他結婚二十多年了,他們的兒子已經(jīng)上大學,兩個人感情說不上如膠似漆卻也算相濡以沫。現(xiàn)在錢艷玲的胳膊肘卻拐向了外面還拐得那么自然,設計陰謀之人該有多么神通廣大。更加不可思議的是,在這個陰謀中時間是錯亂的,那個人或者那些人是怎么做到的?難道他們能打破時空,讓時光倒流或向前跳躍?
趙清醒情不自禁地來到窗前,憑窗向外眺望。他的辦公室在五樓,能看到很多高樓大廈很多縱橫交錯的街道,街道上車輛川流不息行人熙熙攘攘。天是晴的,天空不是很藍但也算清明。太陽懸掛在東南方,光芒耀眼無法正視。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時空有一絲一毫的不正常。
三
趙清醒想把事情的底牌揭出,想了好半天卻沒想出任何辦法。無奈,只得坐回到辦公桌前,思考接下來怎么辦。想了十多分鐘,還是沒有任何眉目。心情不好,大腦混亂不堪,趙清醒自然什么也做不下去,進而覺得必須找一個人說說話,同時對事情進行進一步求證。找誰呢?想了片刻,趙清醒拿起手機,打給徐芳華。
徐芳華是省歌舞團的團長,舞蹈演員出身,四十好幾了,名副其實一個徐娘半老,卻風韻十足,比二十出頭的小姑娘味道更濃。趙清醒跟徐芳華相識好多年了,上周日關系發(fā)生了質(zhì)的飛躍,兩個人在一家賓館開了房間。那天兩個人不但睡了覺,還說了很多知心話。趙清醒這個年紀的處級干部跟人說知心話的機會極少,跟徐芳華卻說得淋漓盡致,說明兩個人是有共同語言的,是能走進彼此內(nèi)心的。趙清醒跟錢艷玲也有共同語言,但說的是俗不可耐的家長里短,跟徐芳華說的卻是陽春白雪的藝術和人生。另外,徐芳華活動能力特別強,圈子內(nèi)交往廣泛,對很多事都了如指掌,此時跟徐芳華談一談或許能解開謎團。
徐芳華很快接電話了,說:“趙處長,有什么指示?”趙清醒說:“芳華,中午有時間嗎?出來坐坐?”徐芳華應該是愣了一下,說:“趙大處長怎么想起來請我出去坐?太陽從北邊出來啦?”趙清醒說:“別開玩笑,我有一些話想跟你說。”徐芳華說:“太不正常。”趙清醒說:“憑咱倆的關系,怎么能說不正常呢?你要是下午到晚上一直沒事,我們還可以干點兒別的。”徐芳華說:“我怎么聽著有點兒不對勁?”趙清醒心想這個娘們兒,還跟我裝上了,但沒有表示不滿,說:“就這樣定了,十一點半,太原街皇金海鮮菜館,不見不散。”徐芳華沉默片刻,有些無奈地說:“好吧。”
十一點剛過,趙清醒就來到皇金海鮮菜館了,要了一個包間,點了好幾個硬菜。十一點半,徐芳華準時到來。徐芳華風風火火,進房間后坐下,說:“趙大處長,我下午有事,咱們快點兒吃,有啥話快點兒說。”趙清醒說:“干嘛搞得那么忙?我真有很多話想跟你說。”徐芳華說:“一個小時應該啥話都說完了吧?十二點半我準時撤。”趙清醒心想這個壞女人,還不好意思了,不過也好,她要是太好意思,自己對她反而沒興趣了。女人就應該有足夠的深度,否則男人就少了征服和探索的興趣。趙清醒決定先不往曖昧方面說,先把那個疑問弄清楚,一邊給徐芳華和自己倒酒,一邊說:“你聽沒聽到消息?”徐芳華說:“什么消息?”趙清醒說:“我提副局長的消息?”徐芳華愣一下,說:“是宣布了還是聽了小道消息?”趙清醒說:“昨天開會正式宣布的。”徐芳華說:“不對啊,昨天不是星期日嗎?而且我聽說人選還在研究,最快也得半個多月后才能定下來。”
趙清醒立刻出了一身冷汗,看著徐芳華什么也說不出來了。自己已經(jīng)把事情想得非常嚴重,但現(xiàn)在看來,還是把嚴重性低估了。那個巨大的陰謀竟然把徐芳華這樣關系極小的人也包括進去了。僅僅十幾個小時,還要跨一個夜晚,那個人是怎么做到的?也不過就是一個副局級位置,至于搞得如此大張旗鼓嗎?
徐芳華開始大吃大喝,一邊吃喝一邊哼哼哈哈地打了一通電話,打完后說:“趙大處長,確認過了,根本沒那么回事兒。你干嘛跟我編這樣一個謊言?開玩笑嗎?別的事可以開玩笑,這樣的事是不能開玩笑的。再說了,這樣的玩笑不應該跟我開啊。”趙清醒似是自言自語地說:“難道真的是玩笑?不會啊,怎么可能是玩笑?”徐芳華說:“你是不是因為特別緊張搞出了幻覺?”趙清醒說:“絕對不是幻覺,確實是昨天開的會,組織部領導公開宣布的。可是今天,所有人都回避這件事否定這件事,現(xiàn)在連你也說沒那回事了,我覺得這是一個陰謀。芳華,我現(xiàn)在不知道該怎么辦了,你幫幫我,幫我把這個陰謀弄清楚。”徐芳華說:“首先,我認為這不是陰謀。第二,就算是陰謀跟我也沒關系,干嘛讓我?guī)湍悖俊?/p>
趙清醒說:“想來想去,我覺得只有你能幫我了。”徐芳華說:“為什么?”趙清醒說:“你怎么啦?因為我們關系不一般啊。自從我們上周有了那樣的事,我已經(jīng)把你當作這個世界上最親的人啦。我愿意為你付出一切,請你幫個忙不是很正常的嗎?”徐芳華說:“你什么意思?”趙清醒說:“啥什么意思?你不會忘了吧?上個星期日,我們在海天大酒店,那個夜晩,是我這么多年來感覺最幸福最快樂的夜晚。”
徐芳華霍地起身,胸脯前傾,指著趙清醒的鼻子說:“你……你……”趙清醒說:“怎么啦?這里又沒有別人,用得著掩飾嗎?”徐芳華說:“你……你個老流氓,只會胡說八道。我啥時候跟你去海天大酒店啦?做夢呢吧?就你這個熊樣,我會跟你去酒店?”說完把大半杯啤酒潑在趙清醒臉上,嘩啦一聲把幾盤菜掃到地上,然后揚長而去。
四
接下來的一段時間,趙清醒一直在求證兩件事,自己到底是不是當上了副局長,是不是跟徐芳華有過一腿婚外情。如果兩件事是真的,別人為什么會矢口否認。如果兩件事是假的,自己為什么記得那么真實,切身體驗清清楚楚。求證方式多種多樣,幾乎把能用的都用上了,比如向各種各樣的相關人員詢問,查看工作記錄,甚至在公安局工作的朋友的幫助下到海天大酒店翻閱了入住登記。最終,沒有發(fā)現(xiàn)任何的蛛絲馬跡。
這天早晨趙清醒醒來后起床,穿衣服時覺得自己不是剛剛從床上下到地上,而是剛剛從外面回來。自己是去北京領獎了,去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大海波濤》獲得了茅盾文學獎。那是一個盛大的頒獎大會,連副國級領導都參加了,自己不僅得了獲獎證書,還得了百萬元獎金。會議開完就急匆匆趕回來了,所有細節(jié)此時仍然歷歷在目。趙清醒愣住了,自己到底是剛剛起床,還是剛剛從外面回來?看看身上,衣服還沒穿利落呢。再看看床上,被子還亂亂的,把手伸到被子下,還是熱的。再看四周,沒有任何剛剛從外面回來的跡象。
臥室的門開著,趙清醒來到門邊,看到錢艷玲正在往餐桌上擺東西,有面包牛奶煎雞蛋香腸片小咸菜,算得上豐盛。錢艷玲看到趙清醒了,氣哼哼地說:“現(xiàn)在好多家庭都是男的做早飯,你倒好,一次都不做就知道睡懶覺。不喊你是不是還不起?趕緊把你的臭牙刷干凈過來吃,吃完趕緊上班。你們局副局長人選不是快公布了嗎?就算希望不大也得爭一爭,別在關鍵時刻讓人抓了把柄。”趙清醒說:“是你把我喊醒的?”錢艷玲目光中閃出警惕,說:“不是我還能有誰?你是不是指望著有另外一個人?”趙清醒說:“胡說八道,我怎么會指望有另外什么人?”錢艷玲說:“我一直懷疑你外面有小狐貍精,看來還真有啊。”趙清醒說:“你別疑神疑鬼胡思亂想了。”
能夠確定了,自己是剛剛起床,不是剛剛從外面回來。而且趙清醒還想清楚一件事,茅盾文學獎揭曉是在兩個月后,跟自己沒有一毛錢關系。自己是出版了長篇小說《大海波濤》,但那是一部跟茅盾文學獎沾不上邊的作品,是找關系贊助出版的,相當于自費,根本沒有參評。那樣的作品拿出去參評,不但注定得不了獎,還會成為一個笑話。
呆呆地站了片刻,趙清醒心有所動,覺得窺到了事情的關鍵之處。
五
趙清醒又一次來到李長文的辦公室,隨意地坐在沙發(fā)上。李長文瞄了趙清醒一眼,沒說什么繼續(xù)看手里的文件。文件看完,發(fā)現(xiàn)趙清醒沏了茶,正喝得滋滋潤潤。李長文眉頭皺得更緊,心想他這是要干什么?真不拿自己當外人啦?真覺得當上了副局長,能跟我平起平坐啦?本來這幾天趙清醒沒有再明顯地表現(xiàn)出不正常,李長文已經(jīng)把那件事忘得差不多了,最起碼不怎么在意了,甚至認為已經(jīng)結束了。可是現(xiàn)在,李長文發(fā)現(xiàn)事情沒有那么簡單,不但沒有結束,還出現(xiàn)了發(fā)展下去的跡象。如此一來,就有必要采取一些措施了。先跟他談一談,談得好一切都好說,談不好,就只能跟他的家屬取得聯(lián)系,帶他去精神病醫(yī)院檢查了。
李長文來到趙清醒旁邊,坐下,語重心長地說:“清醒啊,是不是工作壓力太大了?”趙清醒說:“沒有啊,我在工作方面一直沒有任何壓力。”李長文說:“生活方面有壓力?”趙清醒說:“生活方面也沒有壓力。”李長文說:“可是我覺得你最近狀態(tài)不對。”趙清醒說:“沒什么不對吧,一切都正常得很。”李長文說:“那你連個招呼都不打,坐在我這里就是喝茶,是什么意思?”趙清醒說:“沒什么意思啊,就是來你這里坐一會兒。你沒關門,我就沒敲門,你在看文件,我就沒打擾你。”
李長文說:“副局長的事別太在意,能上當然好,不能上也別想太多,總之要相信組織。”趙清醒說:“局長放心,是否能上我根本不在意。”李長文說:“你這樣說我就放心了,以后別再弄那些不著邊際的事,只要扎扎實實地把工作做好,機會有的是。”
趙清醒臉上現(xiàn)出莫名其妙,說:“局長,我什么時候弄不著邊際的事啦?”李長文說:“已經(jīng)過去了,沒必要再計較啦,而且我是理解的。那件事只有你我兩個人知道,我不會說出去,也不會對你產(chǎn)生不好的印象,我們都當沒有發(fā)生過就行了。”趙清醒有些急了,說:“不行不行,局長,必須得說清楚,我到底做了什么不該做的事?”李長文說:“你難道忘了?”趙清醒說:“忘不忘的,您得說什么事啊。”
李長文非常生氣,把趙清醒自己認為當上副局長的事說了一遍。趙清醒完全徹底地蒙了,臉上滿滿的不可思議,說:“怎么可能?這件事我半點兒印象都沒有啊。我在您手下工作十多年了您是了解我的,您可以想一想,我可能做出那樣的事嗎?”李長文說:“我也認為你不應該做出那樣的事,可是你確實那樣做了。放心,我已經(jīng)說過我不在意,所以你用不著辯解。”趙清醒說:“我真的沒做過那樣的事,一定是您搞錯了。”李長文說:“事情清清楚楚,我怎么可能搞錯?”趙清醒說:“那可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了,根本沒有的事,您老人家竟然當成真實的了。”
李長文是一個善于察言觀色的人,能夠通過言行舉止了解一個人的內(nèi)心世界,此時從趙清醒的臉上身上沒有看出任何不自然不自在,對自己的判斷也就產(chǎn)生了一絲絲的不自信。不過李長文的思緒仍然是清晰的,覺得趙清醒如此這般無非兩種可能,一種是想用演戲的方式把做過的蠢事抵賴過去,一種是精神上確實出了問題。前一種可能需要深到可怕的心機和精湛的表演技藝,可是李長文認為那樣的東西趙清醒根本不具備。如此一來,就只有第二種可能了。李長文已經(jīng)在內(nèi)心做出決定讓精神病醫(yī)生或心理專家介入,卻還是想在那之前對趙清醒進行一些安慰,于是慢慢起身,說:“清醒,回去工作吧,這件事到此為止了。”趙清醒也站起來,一邊往外走一邊說:“局長,人有時會把根本沒發(fā)生過的事當成真實的,有時會把真正發(fā)生過的事當成是虛幻的。那件事確實沒發(fā)生過,您還是好好想一想吧。很明顯,我們之間產(chǎn)生了一些問題。希望您不要只從我身上找根源,也在自己身上找一找。”
門被趙清醒在外面重重地關上,李長文在沙發(fā)上重新坐下,腦袋里那一絲絲不自信開始慢慢放大。作為一個文化系統(tǒng)的局級干部,李長文對事物的認識是有獨到之處的,對趙清醒最后那幾句話在一定程度上是認可的。的確,紛繁復雜的世間,真實和虛幻并沒有明顯的分界線。一些事情看上去真實其實并不存在,一些事情看上去虛幻,卻實實在在地發(fā)生了。比如大約一年前的一天,自己的兒子突然間成了國家級專家,享受的待遇讓他這個局級干部都目瞪口呆,好多人大張旗鼓地向他表示祝賀,表情中有真誠有虛偽,有羨慕有嫉妒……可是當兒子再次出現(xiàn)在他面前時,他發(fā)現(xiàn)那根本就是一場虛幻,連正經(jīng)工作都沒找到的兒子仍然畏畏縮縮,一副爛泥扶不上墻的樣子,伸手就跟他要錢,說再不給他一些錢他老婆就會跟野男人私奔,他也就沒辦法活下去了。
大約兩個月前,李長文下班剛到家老婆就跟他大吵大鬧,說他跟京劇團的一個小妖精不干不凈。李長文一直嚴格要求自己,那樣的事是不可能發(fā)生的。可是不論他如何解釋,老婆就是不依不饒,一定要跟他離婚并讓他凈身出戶。老婆的證據(jù)非常充分,其中有好多細節(jié)。爭扯到最后,李長文竟然覺得那樣的事真的發(fā)生了。進而,老婆所指出的那些細節(jié),竟然成了親身體驗了。李長文深知一旦離婚勢必會滿城風雨,對自己的影響是致命的,于是便向老婆承認錯誤,說一定跟小妖精斷絕關系,類似的事再也不會出現(xiàn)了。最終老婆胸襟寬闊地讓步,說可以原諒他,但如果他食言再犯,絕對會要了他的老命。那之后李長文多次見到過那個小妖精,每次見到都覺得自己確實跟她有過那么一腿,一些細節(jié)還能清晰地在眼前出現(xiàn)甚至能在感覺上重溫。
雖然趙清醒那件事歷歷在目,此時李長文卻對其產(chǎn)生了一些疑問。李長文強迫自己讓理性占據(jù)上風,開始對事情進行進一步分析。先分析動機。趙清醒就算想當副局長想到癡迷而搞一些動作,也不會搞出那樣的動作。趙清醒算不上聰明人,但絕對不是蠢人,能夠弄明白那樣的動作不會給他加分只會給他減分。再分析可行性。那件事實在荒唐透頂,只要腦袋沒被門徹底擠成碎片就不可能做出來。很明顯,趙清醒的腦袋沒有被擠到那樣的程度。動機不成立,可行性不存在,那么,那件事真的沒有發(fā)生過嗎?
這樣的懷疑把李長文嚇了一跳,接下來點上一支煙,猛吸一口讓自己冷靜下來,決定進行求證。李長文記得那件事是發(fā)生在兩周前的周一上午,在手機上打開日歷,查到是6月7日。翻開那天的工作日志,見上面清清楚楚地記載著上午是在省里開會。李長文身體一僵,出了一身冷汗。趕緊喊來秘書小孫,說:“小孫,我6月7號在省里開會拿回的文件是不是在你那里?”小孫想了片刻,說:“6月7號,您應該沒到省里開會。”李長文說:“不對啊,工作日志上記著呢,那天上午是在省里開會。”小孫拿出手機翻看片刻,說:“那天本來是要去開會的,但后來會議取消了。您那天上午是去省委組織部,跟他們研究副局長人選了。”李長文說:“你是說,那天上午我沒到局里來?”小孫說:“是的。”李長文愣了片刻,說:“沒事了,你去忙吧。”
小孫離開后,李長文長長地嘆了口氣,產(chǎn)生了一種無助的虛弱感。很明顯了,自己把一件子虛烏有的事當成真的了。為什么會這樣?如果說兒子那件事源于期盼兒子有出息的愿望,小妖精那件事源于潛意識中的企圖,那么趙清醒這件事又源于什么呢?自己作為局長,作為趙清醒的直接領導,為什么會編排出那樣一件事?是自己對他有成見?不可能,自己對任何人都沒有成見。成見是領導干部最不該有的東西。成見等于把人或事看死,可是人和事不是死的,而是不斷變化的。自己對幾個副局長候選人一直一視同仁,向組織部提出的建議是客觀的,出發(fā)點都是把真正有能力有德行的人提到領導崗位,是為局里的工作著想。自己受什么人的慫恿要對趙清醒進行打擊?那就更不可能了,自己歷來堂堂正正,怎么可能是那樣的小人?難道自己的精神出問題了?也不可能,自己無論是肉體還是精神,都健康得很。
沒能找到原因,李長文索性不再找,接下來則覺得有點兒對不起趙清醒,思考片刻,決定找趙清醒談一談。李長文打電話把趙清醒叫過來,親自給趙清醒沏了茶,坐在趙清醒對面,說:“清醒啊,那件事就讓它過去吧,我們都當它沒發(fā)生過。你是知道的,很多事只要當它沒發(fā)生,那它就等于沒發(fā)生。”趙清醒說:“局長是這樣的態(tài)度,我特別高興。”李長文說:“世界上的事奇妙得很,真正分辨真假需要智慧。更進一步,不在乎真假,則需要大智慧。你說呢?”趙清醒說:“理解,局長就有大智慧。”
六
離開李長文,趙清醒似乎卸掉了千斤重枷,長長地松了一口氣。慢慢經(jīng)過走廊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在沙發(fā)上坐下看向四周,覺得世界上的一些事確實特別有意思。
接下來還有一件事必須盡快做,找徐芳華談一談。拿出手機打過去,徐芳華很快接了,語氣中透著一些無可奈何,說:“趙大處長又找我有什么事?”趙清醒說:“又找你?我最近找過你嗎?”徐芳華說:“我忙得很,沒時間跟你嚼舌頭,有事說,沒事掛了。”趙清醒說:“別掛,有事,請你吃飯,你不會不賞光吧?”徐芳華說:“沒興趣,忙,不賞光。”趙清醒說:“這么多年朋友了,還是賞個光吧,否則我會覺得特別沒面子。”徐芳華似乎想了片刻,最終說:“好吧,你趙大處長是我的主管領導,我可不敢得罪,說吧,時間,地點。”趙清醒說:“南洋美食宮,五點半。”
趙清醒按時來到南洋美食宮的一個包間,剛坐下徐芳華便到了。兩個人簡單地寒暄兩句,趙清醒喊來服務員點菜,一邊看菜譜一邊說:“芳華,我們有三個多月沒見了吧?”徐芳華一愣,說:“貴人多忘事嗎?我們兩周前見過的。”趙清醒說:“兩周前?我怎么沒有印象?”徐芳華臉上現(xiàn)出不可思議,說:“趙大處長是想掩飾什么嗎?兩周前,海天大酒店,你說了很多混賬話,我倒了你一身啤酒,掀了桌子,你應該印象深刻啊。”趙清醒說:“我確實一點兒印象沒有,是不是你弄錯啦?”徐芳華說:“不可能,我記得清清楚楚。”
菜點完,把服務員打發(fā)走,趙清醒十分嚴肅地說:“兩周前一起吃飯我確實沒有半點兒印象,但是有件事我是感興趣的,就是你說的我說了很多混賬話。你能不能說一下,我都說了什么混賬話?”徐芳華說:“既然沒印象,就當沒發(fā)生過吧。既然沒發(fā)生過,也就沒必要重復了。”趙清醒說:“不行,那些話肯定對你有所傷害,我需要知道然后引以為戒。”
徐芳華說:“好吧,告訴你,你編排了一件子虛烏有的事,說我們倆在酒店開過房。”趙清醒皺著眉頭想了片刻,說:“真那樣說,確實是混賬話。不過你應該是弄錯了,我保證我沒說過那樣的話。你可以認真想一想,我可能說出那樣的話嗎?做什么事說什么話都是有目的的,我說那樣的話目的是什么?”徐芳華說:“我怎么知道你目的是什么?恐怕沒什么目的,只是精神錯亂吧。”趙清醒說:“你覺得我是精神錯亂的人嗎?”徐芳華說:“你還說你當上副局長了,說得有鼻子有眼的。”趙清醒說:“那就更不可能了,我就算再想當副局長,也不會如此沒有理智地胡說八道吧。”
徐芳華此時對趙清醒產(chǎn)生了明顯的鄙夷,心想這個王八犢子這是怎么啦?說過的話做過的事干嘛不承認?那件事確實令人討厭讓人惡心,可是事實上也算不上多么了不得的大事,而且只有天知地知你趙清醒知我徐芳華知,過去了不再提了不也就跟沒發(fā)生過一樣消失了嗎?有什么必要費這么多心機進行遮掩進行否認?從另一個角度講,那甚至可以當成一個玩笑。事實上徐芳華對自己那天的反應是有一些后悔的,覺得那樣做過分了,當成玩笑一笑置之也就過去了,沒必要把趙清醒斥為流氓又是掀桌子又是潑啤酒。一些事本來沒什么大不了,覺得它大不了它才大不了,不覺得它大不了它就沒什么大不了。甚至徐芳華還想過找機會跟趙清醒解釋一下說一句對不起。雖然歌舞團自負盈虧,但名義上是受趙清醒領導的,得罪了趙清醒被他給穿上小鞋,不論是唱歌還是跳舞勢必都會像戴上枷鎖那般束手束腳。
菜上來了,兩個人開吃開喝,氣氛平平淡淡,說的都是些無關緊要的瑣碎之事,只有兩個人,情緒又略帶壓抑,酒便喝得沒有味道更沒有激情。最終把話題轉移到重要方向的是趙清醒。趙清醒跟徐芳華碰一下杯,喝一大口啤酒,說:“芳華,你還覺得兩周前我們在海天大酒店吃過飯嗎?”徐芳華說:“不是我覺得,是事實。”趙清醒說:“那你認為覺得和事實是什么關系?”徐芳華愣一下,說:“趙大處長怎么會提出這么奇怪的問題?都把我搞蒙了。我才疏學淺,這樣的問題回答不上來。”趙清醒說:“這就是我們?nèi)祟愃季S的一個誤區(qū),因為種種原因,我們經(jīng)常會把真實當成虛幻,把虛幻當成真實。我再強調(diào)一遍,那件事真的沒有發(fā)生,是你的感覺出現(xiàn)了偏差。”
雖然跟趙清醒認識很多年了,徐芳華卻從來沒有研究過趙清醒,這時見趙清醒如此反常,覺得值得研究一番了,于是開始研究。自己已經(jīng)強調(diào)那件事過去了,可以當它沒有發(fā)生了,趙清醒卻仍然在辯解在開脫在挽回,用的是一種荒唐可笑的方式。他這是在玩指鹿為馬三人成虎?是在進行精神催眠?把我徐芳華看成腦殘啦?這也太小兒科了吧。如此看來,這個王八蛋根本就是一個心胸狹窄的人。往嚴重了說甚至可以說是一個斤斤計較的小人。太不灑脫了,太沒有格局了,甚至有一些猥瑣了。這樣一個人竟然還想當副局長,而且認為自己能當上副局長,實在是滑稽得不能再滑稽了。
徐芳華已經(jīng)在文藝界混了二十多年。從一個小小的舞蹈演員混成了歌舞團的團長,不能說心機多么深,對付人的手段還是有一些的。此時徐芳華把趙清醒放入小人之列,對他也就生起了戒心,進而則盤算是不是弄點顏色讓他看一看。給他顏色看卻不能得罪他,就需要一些技巧。他試圖讓真實成為虛幻,試圖對別人進行精神綁架,說明他在這方面有所陷入了,子虛烏有地覺得自己當上了副局長覺得跟自己開過房就是明證,那為什么不讓他陷得更深呢?真讓他陷入其中不能自拔,該是多么有趣的事。徐芳華思考片刻,說:“你這么一說,我還真不敢肯定了,也許那件事真沒有發(fā)生。”趙清醒說:“不是也許,本來就沒發(fā)生。”徐芳華說:“太神奇了,沒發(fā)生的事,竟然感覺那么真實。”趙清醒說:“世界就是這么奇妙。”徐芳華說:“那是不是我們應該對所有的事都提高警惕?因為看似真實其實是虛幻,看似虛幻其實是真實。”趙清醒說:“當然,必須提高警惕,不論是把真實當成虛幻還是把虛幻當成真實,都會造成嚴重的后果。”
徐芳華說:“那趙處長有沒有想過,你的生活中很多事很可能都是不真實的。比如你在文化局當了十幾年處長,你和你老婆結婚二十多年了感情不錯,你的兒子正在上大學。”趙清醒說:“這樣的事就用不著懷疑了,有很多證據(jù)可以證明是真實的。”徐芳華說:“事情都可以是虛幻的,證據(jù)難道沒有可能是虛幻的?比如你跟你老婆結婚這件事你可以拿結婚證證明,可是結婚證有可能是虛幻的。你可以用跟你兒子說話看你兒子的東西證明你有兒子,可是那些也有可能是虛幻的。難道你認為可以用虛幻證明真實?”趙清醒說:“你不要把事情說得那么可怕。”徐芳華說:“沒什么可怕的,虛幻和真實本來就沒辦法分清,很多人都是生活在虛幻之中,你和我都不能例外。現(xiàn)在我問你,我們倆在酒店開房這件事到底是虛幻的還是真實的?”
趙清醒說:“那是我胡說八道,不是真實的。”徐芳華說:“你錯了,那是真實的,我們確實在酒店開過房,度過了很有激情的一個夜晚。”趙清醒說:“不可能,我查過酒店的入住登記,沒有我們開房的記錄。”徐芳華說:“那只能證明入住登記是虛幻的,或者說你去酒店查入住登記這件事是虛幻的。你這個人太無情無義了,人家冒著巨大的風險陪了你一夜,你竟然推得一干二凈不承認有那么回事。”趙清醒心中劇震,沉默片刻,說:“難道真有那么回事?”徐芳華說:“那天的一些細節(jié)直到現(xiàn)在還歷歷在目呢,我們說的每句話我都記得清清楚楚,用不用我給你重復一下?”趙清醒說:“不不不,不用重復,我腦袋有點兒亂,你讓我好好想一想。”
接下來趙清醒陷入了沉思,一直到飯局結束再也沒吃幾口菜喝幾口酒,也沒說過幾句話。徐芳華卻吃了很多喝得很痛快,用風卷殘云形容都不為過。效果遠遠超過預期,讓徐芳華即得意又覺得詭異可笑,同時還有一些疑惑。這是真實的嗎?一個好好的處級大男人,真的陷入到虛實顛倒中無法自拔了?
七
文化局副局長沒有從文化局內(nèi)部產(chǎn)生,是作家協(xié)會的一個處長空降而至。省委組織部的領導把人送到文化局,召開全體大會公開宣布,要求全局對新任副局長予以支持。
趙清醒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坐在沙發(fā)上抽煙喝茶。趙清醒對能不能當上副局長不怎么在意,此時卻也產(chǎn)生了空落沉重之感。剛才的會議是真實的嗎?當上副局長的不是自己,而是那個比自己小好幾歲的年輕人,不是虛幻嗎?需不需要求證一下?比如去會議室看一下有沒有剛剛開過會的跡象,比如跟自己的手下或者別的處室的人談一談。想了片刻,覺得沒有那個必要,不論是真實的還是虛幻的,對自己來說都沒有意義了。真正有意義的是自己怎么看,自己既然已經(jīng)無法分辨真實與虛幻,也就無需再去分辨。
如果說剛才那個會議是真實的,那么組織部領導宣布的副局長會不會是我趙清醒而不是別人?沒錯,就是這樣的,虛幻和真實的分界線就在此處。如此一想,趙清醒心頭的空落和沉重立刻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充實和輕松,進而則是振奮和激動。從現(xiàn)在起,不,從大約半個小時前開始,自己是副局長了。以后要在各方面更加嚴格地要求自己,跟班子成員搞好團結,跟下屬搞好關系,要把自己的聰明才智盡可能地發(fā)揮出來,為社會文化的發(fā)展作出突出的貢獻。
趙清醒立刻給錢艷玲打電話,說:“老婆,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剛開過會,我當上副局長了。”錢艷玲很高興,說:“太好啦,晚上回家好好犒勞犒勞你。”趙清醒說:“應該犒勞,你多弄幾個菜,我們好好喝幾杯。”
掛斷錢艷玲的電話,趙清醒又打給徐芳華,說:“芳華,得到消息了吧?”徐芳華說:“趙處長指的是副局長吧,得到啦。”趙清醒說:“那你為什么不向我表示祝賀?”徐芳華愣了一下,說:“向你,表示祝賀?”趙清醒說:“是啊,以我們的特殊關系,我最想聽到的就是來自你的祝賀。”徐芳華說:“對對對,是該向您老人家表示祝賀,希望您老人家當上副局長后繼續(xù)對我們歌舞團進行關照,哈哈哈……”趙清醒說:“你笑什么?”徐芳華說:“沒,沒笑什么,就是覺得太有意思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