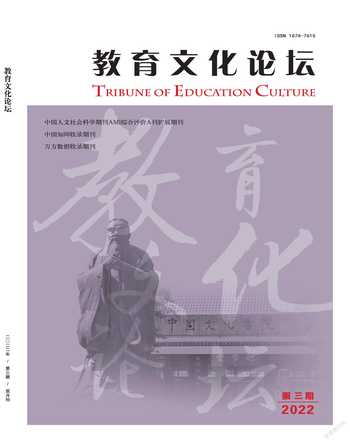我國民族基礎教育政策的發展歷程、演進邏輯及未來走向
姚佳勝 林曉文
摘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我國民族基礎教育政策的發展經歷了四個階段:一是以加快發展初等教育為前提的初始起步階段,二是以實施九年義務教育為重點的恢復調整階段,三是以實現教育協調發展為目標的加速追趕階段,四是以尋求民族特色發展為根本的融合發展階段。在政策演進過程中,逐漸呈現出以管理體制變遷為核心的政策動力機制,從“社會本位”向“個人本位”轉變的政策價值取向,以運用多種政策工具為手段的實施過程保障,以政治學話語與經濟學話語為主導的政策話語規則。未來我國民族基礎教育政策應呈現出“兩團體”統一協作為原則的政策動力機制,多元視角的政策價值取向,多種政策工具有機結合的實施過程保障,多方參與的政策話語體系。
關鍵詞:民族基礎教育政策;民族教育;發展歷程;演進邏輯;未來走向
中圖分類號:G520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4-7615(2022)03-0091-09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2-03-014
民族基礎教育是我國教育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我國高度重視民族基礎教育,黨和政府出臺了一系列相關政策,推動了我國民族基礎教育的發展,使其教育規模逐漸擴大,教學質量不斷提升,教育體系趨于完善。但與此同時,民族基礎教育發展過程中也逐漸凸顯諸多問題,如財政投入不足,師資力量匱乏,教學設備陳舊等[1]。因此,加強對民族基礎教育政策的研究至關重要。本研究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我國民族基礎教育政策的發展脈絡進行系統梳理,探尋教育政策的演進邏輯,并對其未來走向進行展望,以期為民族基礎教育的未來發展提供思考與借鑒。
一、民族基礎教育政策的發展歷程
縱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國家出臺的民族基礎教育政策,根據民族基礎教育自身發展的階段性特征以及重要政策的發布時間,可將我國民族基礎教育的發展歷程劃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一)以加快發展初等教育為前提的初始起步階段(1949—1977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伊始,我國教育事業百廢待興。進行社會和政治改革,改變教育落后現狀,成為少數民族地區發展的迫切需要[2]。1949年出臺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提出,“人民政府應幫助各少數民族的人民大眾發展其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的建設事業”,至此,我國民族基礎教育建設正式被提上議事日程。在此階段,國家相繼出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195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關于少數民族教育事業經費問題的指示》(1956年)等政策,在國家政策的推動下,民族基礎教育穩步發展。
1.加大民族教育經費投入,擴充初等教育辦學規模
1951年,第一次全國民族教育會議成功召開,會議提出,“少數民族地區除按一般開支標準撥給教育經費外,另撥專款幫助解決學校設備、教師待遇、學生生活等方面的特殊困難”。《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關于少數民族教育事業經費問題的指示》同樣提到了經費補助問題。教育經費投入極大地促進了學校基礎設施建設,為更多適齡入學群體提供了接受教育的可能性。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相比,政策推行后的一段時間內,無論是學校規模、在校生人數還是專任教師數量,都有顯著提升,到1952年底,民族自治地方小學數量共59 597所,在校生人數467-31萬,專任教師數量5-98萬;至1978年底,三者數量分別提升至142 865所、1 705.24萬、31-02萬[3]。
2.使用民族語言文字教學,促進民族文化自由發展
1950年,政務院批準的《培養少數民族干部試行方案》提出,“少數民族學生除學好本民族語文外,亦應學習漢語漢文”。次年舉辦的第一次全國民族教育會議提出,“凡有現行通用文字的民族,小學和中學的各科課程必須用本民族語文教學”。在國家民族語言政策的指引下,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教學得到較快發展,一方面為少數民族學生學習提供了語言環境,另一方面為未來雙語教學的實施與發展奠定了一定基礎。
(二)以實施九年義務教育為重點的恢復調整階段(1978—1991年)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成功召開,標志著我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新階段,少數民族基礎教育也理應邁入一個全新的發展時期,但由于“文革”期間民族基礎教育遭到嚴重破壞,因此,該階段所推行的政策主要圍繞恢復與調整展開。此階段較具代表性的政策文件有:《教育部、國家民委關于加強民族教育工作的意見》(198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1984年),《國家教委關于繼續組織高中教師支援西藏的通知》(1986年),《國家教育委員會、財政部關于下達民族教育專項補助經費的通知》(1990年)等。
1.經費補助與師資支援并行,推動教育資源均衡配置
1980年出臺的《教育部、國家民委關于加強民族教育工作的意見》提出,“保證民族自治地方在教育事業上的自主權,教育規劃、教師任用和招聘、經費的管理和使用等應由自治地方根據實際情況決定”。管理權限的下放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當地群眾和企業積極投入到基礎教育的建設中去,但由于改革開放初期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客觀上導致了教育資源的差異化分布。對此,國家積極調整民族教育方針,出臺了一系列優惠政策,以彌補區域之間教育資源配置不均的問題[4]:一方面,國家通過加大對民族地區的教育經費投入,設立教育補助專款等方式來確保民族基礎教育的穩定發展。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強調“加大對民族自治地方的教育投入”,《國家教育委員會、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關于申請民族教育專項補助經費的指示》《國家教育委員會、財政部關于下達民族教育專項補助經費的通知》提出,“國家每年增列一筆專項補助費”“補助經費的使用要實行項目管理、專款專用”。另一方面,針對少數民族地區師資匱乏、師資質量不高的問題,國家出臺了《關于繼續選派第五批援藏中學教師的通知》《教育部、國家計委關于落實中央關于在內地為西藏辦學培養人才指示的通知》等相關政策,不僅鼓勵內地教師前去民族地區支援,而且積極籌備內地班(校),推動教育資源均衡分布,進而提升民族地區的教學水平。
2.集中力量辦好民辦學校,逐步實施九年義務教育
《教育部、國家民委關于加強民族教育工作的意見》提出,要“切實抓好小學教育,辦好寄宿制學校”;1984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提出,要“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并提出了辦好寄宿制學校的關鍵舉措。大力發展以寄宿制為主的民辦學校,減輕了學生的經濟負擔,為少數民族的適齡入學群體提供了更多的就學機會,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學生的入學率與鞏固率,為逐步實施九年義務教育提供了制度保障。
3.積極開展民族雙語教學,推廣使用全國通用語言
改革開放以后,隨著經濟建設的不斷發展,不同區域間的經濟文化往來不斷加強,通用語言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促進信息的溝通與傳播。1984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提出,要“根據情況從小學低年級或高年級起開設漢語文課程,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和規范漢字”,1988年頒布的《五省、自治區藏族教育研討會紀要》重申了積極開展雙語教學的指令。普通話的推廣不僅能保證各民族間的經濟往來,促進區域間的經濟發展;也能提高少數民族學生實際運用漢語的能力,使其更好地適應未來生活、工作和社會發展的需要。
(三)以實現教育協調發展為目標的加速趕追階段(1992—2009年)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上一些國家和地區因民族問題導致動蕩甚至分裂,民族問題成為國家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之一[5]。由此,黨中央和國務院高度關注民族教育工作,1992年,國家教委、國家民委發布《關于加強民族教育工作若干問題的意見》,為此后民族教育的發展指明了方向,成為此階段指導民族基礎教育發展的綱領性文件。除此之外,這一時期還陸續出臺了《關于在全國中小學開展民族團結教育活動的通知》(1999年)、《關于內地有關城市開辦新疆高中班的實施意見》(2000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民族工作加快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決定》(2005年)等政策。此階段的政策主要圍繞對口支援與民族團結教育展開,目的是通過教育援助的實施與民族意識的養成,盡快實現基礎教育的協調發展。
1.繼續加大民族經費投入,確保實現“兩基”攻堅計劃
為響應《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提出的“20世紀前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以及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簡稱“兩基”)的戰略目標,少數民族區域積極開展“兩基”攻堅計劃,但由于少數民族地區大多處于山區、牧區等地域,導致了民族教育發展的艱巨性與長期性,截至2001年底,民族自治地區699個縣級單位中,僅有358個縣實現“兩基”目標,占總數的51%[6]。為此,國務院在2002年頒布的《關于深化改革加快發展民族地區教育的決定》中,首次將“兩基”置于民族教育重中之重的地位,并指出要“加大經費投入,加快推進進程”。此后出臺的《國家西部地區“兩基”攻堅計劃》進一步加大了攻堅的執行力度,確保了攻堅計劃的順利實現。
2.開展內地援藏援疆行動,實現基礎教育協調發展
1992年,第四次全國民族教育工作會議提出,“民族教育要與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相適應”。針對西藏教育落后、人才匱乏的狀況,為了進一步滿足西藏經濟建設的需求,國家加大了對援藏工作的重視力度,于1992年推出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內地西藏班工作的意見》和《內地西藏中學班(校)管理實施細則》,并于1993年頒布了《關于進一步加強教育援藏工作的請示》,從經費補助、學校管理等方面加強了對藏區的教育支援。邁入21世紀,通過借鑒內地西藏班的辦學經驗,教育部發布了《關于內地有關城市開辦新疆高中班的實施意見》和《關于擴大內地新疆高中班招生規模的意見》。內地西藏班、新疆班的成功舉辦,為民族地區基礎教育的發展帶來了活力,為實現基礎教育協調發展注入了力量。
3.加強師資隊伍建設,提升民族地區教學水平
與前期注重教師數量、緩解師資短缺的狀況相比,本階段的重點在于提升民族地區的師資水平,建設合格的雙語教師隊伍。2002年出臺的《國務院關于深化改革加快發展民族教育的決定》提出,要加強少數民族地區的師資隊伍建設,把培養“雙語”教師作為當前師資培訓的重點,“提高教師學歷學位層次”。一方面,國家注重民族教師的學歷水平與教學能力提升;另一方面,也注重對雙語教師隊伍的培養,目的是保證民族地區教師素養,提升民族地區教學水平。
4.大力發展民族團結教育,增強民族學生團結意識
加強民族團結教育不僅是培養社會主義建設者與接班人的需要,更是祖國統一和各民族平等團結、共同繁榮發展的需要[7]。1999年,教育部與國家民委發布《關于在全國中小學開展民族團結教育活動的通知》,強調應依據學生的學段有層次地開展不同主題的團結教育活動。步入21世紀后,國家高度重視民族地區的德育工作,接連發布了《教育部辦公廳國家民委辦公廳關于在中小學進一步大力推進民族團結教育工作的通知》《學校民族團結教育指導綱要(試行)的通知》等政策,并積極推進民族團結教育基地建設,增強學生的團結意識與愛國意識,確保民族團結教育工作的穩步實施。
(四)以尋求民族特色發展為根本的融合發展階段(2010年至今)
隨著少數民族地區經濟水平的不斷提升,文化需求的不斷增長,以往所遵從的追求外在價值、實現外在目的的外延式發展模式已不能滿足新時期少數民族人民對教育的需求[4]。關注民族教育的內在價值,尋求自身發展的文化內涵,已然成為此階段的重要需求。這一時期,國家相繼出臺了《關于印發扶持人口較少民族發展規劃2011—2015的通知》(2011年)、《關于印發少數民族事業十二五規劃的通知》(2012年)、《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民族教育的決定》(2015年)等政策,既關注到少數民族地區特有文化的發展,又強化了各民族間交流融合的價值理念,努力實現多元一體的全新圖景。
1.普及現代遠程教育工程,努力實現教育資源共享
為了進一步實現優質教育資源共享,黨中央還大力推行現代遠程教育工程。2010年出臺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支持民族地區發展現代遠程教育,擴大優質資源覆蓋面”;2015年出臺的《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民族教育的決定》,也提到了加強民族地區基礎教育信息化建設的相關問題。除此之外,國家還注重少數民族地區教師的信息化應用能力,通過師資培訓方式提高教師運用現代教學設備的水平,保證少數民族地區的教學質量。
2.保障弱勢群體受教權利,依法履行控輟保學職責
“兩基”目標基本實現后,保障農村轉移人口、少數民族地區兒童等弱勢群體的受教權利成為國家關注的又一重點。2012年出臺的《關于進一步加強民族工作,加快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決定》提出,“應注重保護少數民族兒童尤其是女童受教育的權利”;2015年出臺的《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民族教育的決定》,再次提到保障弱勢群體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并且要將控輟保學作為接下來的重點之一,依法履行控輟保學職責。2017年,國務院指出,各地應因地制宜地采取相關措施,切實保障適齡群體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以期實現義務教育全面普及的終極目標。
3.鞏固義務教育普及成果,全面加強學前雙語教學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大力推進雙語教學,全面開設漢語文課程、國家通用文字,全面加強學前雙語教育”。與之前所提到的雙語教育政策不同,此階段出臺的政策將工作重點放在學前兒童的教育上。2020年6月,《教育部等十部門關于進一步加強控輟保學工作健全義務教育有保障長效機制的若干意見》,重申了加強少數民族地區學前兒童雙語教學、學習普通話的指令,旨在讓學前兒童為將來的學習打好語言基礎,使其更順暢、熟練地接受義務教育,促使民族地區義務教育普及成果更為顯著。
4.開設少數民族特色課程,深度挖掘內在文化價值
2011年出臺的《關于印發扶持人口較少民族發展規劃2011—2015的通知》首次提出應在人口較少的民族中開展校本課程,《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民族教育的決定》也提到應“開設具有民族特色的地方課程與學校課程”。校本課程與地方課程的開展準確地貫徹了交流融合的概念。通過民族地區優秀文化與傳統課堂知識的結合,既能實現民族特色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同樣能夠增進民族間的理解與認同,實現民族團結與民族共同進步,從而有效促進民族地區各項事業的全面發展[8]。
二、民族基礎教育政策的演進邏輯
教育政策的分析可以采取不同種類的模式,一般情況下可概括為以下四種分析模式:發生學取向、目的取向、過程取向與政策話語取向[9]172-173。發生學取向的分析模式是通過解釋和分析教育政策的產生機制,對政策作出分析;目的取向的分析模式指的是從政策目標的角度對政策進行分析,主要研究教育政策與目標之間的關系;過程取向的分析模式是指對教育政策的實施進行過程性分析,重視的是教育政策的實踐過程;政策話語的分析模式主要是結合一定的社會文化與權力背景,分析一定教育政策表述結構背后的文化規則,以及這些文化規則與政策的關系[9]173-179。本文依據上述四種分析模式,對我國民族基礎教育政策文本的演進邏輯進行系統梳理。
(一)以管理體制變遷為核心的政策動力機制
教育政策是不同利益相關者之間相互作用的產物,政策變遷有其固定的范式,其動力機制集中體現于管理權的變化[10]。根據管理體制的變遷,可將民族基礎教育政策的演進劃分為以下三個階段:一是中央集中管理階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民族地區的各項事業均處于起步階段,為了加強對民族教育工作的領導,推動民族教育的全面發展,我國采取中央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通過在中央政府內設民族教育司來對民族地區的各項教育工作進行統一規劃。二是統一領導下的自主管理階段。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濟體制發生了轉變,教育管理體制也出現了相應的變遷。中央政府對民族教育的管理權限逐漸下移,由之前的集中管理轉變為“合作模式”。此階段中央主要負責宏觀方針的制定,具體的管理職能,例如學校辦學體制、教學內容、人才編制以及經費使用等方面均由自治區根據實際情況決定。權力責任的下移使地方的辦學自主權不斷擴大,地方政府作為主要利益相關者的功能逐漸凸顯,“地方負責、分級管理”的民族基礎管理體系逐漸明晰。三是自主管理與宏觀統籌相結合階段。進入21世紀以來,為了進一步提升民族地區的辦學活力,改變以往辦學主體單一的局面,中央政府于2002年出臺的《國務院關于深化改革加快發展民族教育的決定》強調,“要以民族地區自力更生為主,國家扶持及發達地區進行對口支援相結合”。較上一階段相比,這一時期地方政府的管理權限再次擴大,地方政府在政策執行過程中的決策功能逐漸加強,契合當地特色發展的相關政策相繼出臺,管理體制更趨于合理化,執行效率大大增強。
(二)從“社會本位”向“個人本位”轉變的政策價值取向
價值取向是指一定主體基于自己的價值觀,在面對或處理各種矛盾、沖突或關系時所持的基本立場、價值態度以及所表現出來的價值傾向[11]。由于不同時期民族教育所處的時代背景不同,人們對于教育的理解和要求也有所不同,這影響了不同時期民族基礎教育政策的價值取向問題[12]。一是以社會需求為主導的價值取向階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秉承“鞏固祖國統一與民族團結,保障各民族在一切權力方面的平等”的理念,黨中央積極采取民族基礎教育政策傾斜,穩步推進民族基礎教育的發展,以保證社會總體形態的平穩運行。歷經“文革”期間的“左傾”錯誤之后,中央政府把民族基礎教育的工作重點放在恢復與發展上。通過重建民族教育行政機構、民族中小學,恢復民族語言等優惠政策,加大對基礎教育的扶持。總體而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后的一段時間內,教育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是基于社會、政治的時代訴求,社會本位的價值取向在此階段占據主導地位。二是兼顧“社會本位”與“個人本位”的價值取向階段。一方面,改革開放以后,決策者們逐漸意識到教育與經濟的緊密聯系,在1992年召開的第四次全國民族教育工作會議上,黨中央提出了“民族教育要與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全新戰略,將教育視為大力促進經濟發展的有效途徑之一。另一方面,援藏援疆、雙語教學、團結教育等活動的積極開展,為少數民族地區學生提供了更為豐富與優質的教育資源,既確保教育過程中的權利平等,也保證學生個體的全面發展。這一階段的基礎教育決策克服了上一階段中社會本位占據壟斷地位的弊端,開始強調教育者的主體地位,關注教育公平的重要作用,將社會政治、經濟和諧穩定與促進學生群體個人發展有機結合起來。三是凸顯以人為本的價值取向階段。2010年出臺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提出,應“廣泛開展民族團結教育活動,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祖國觀、民族觀以及宗教觀”,將核心觀念通過學科課程以及課外活動等方式外顯出來,增強民族學生的民族認同感以及國家認同感,培養能夠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此外,通過對近十年來的政策分析,也可以發現“加強學前雙語教育、開設民族校本課程、推動普通高中特色化發展”等注重個體發展的新舉措。總體來說,中央政府逐漸開始關注到民族地區的特殊性,由注重物質扶持轉變為尊重民族特色,一切從實際出發,以個人本位為主導的價值取向逐漸明晰。
(三)以運用多種政策工具為手段的實施過程保障
政策實施的過程保障是指通過具體的規則與要求來使政策得以貫徹和實施,并在實施過程中對其變量進行了解與掌控。為了更好地實施民族基礎教育政策,國家采取了多種政策工具相結合的方式,實現效果最優化。結合麥克唐納、埃爾莫爾、施耐德和英格拉姆對政策工具的分類,可將政策工具分為權威工具、激勵工具、象征與勸誡工具、能力建設工具、系統變革工具以及學習工具等六種類型[13]。權威工具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政策手段,主要是指政府為了達成某項目標,運用法律、條例以及管理制度等方式對個人或機構進行支配行為。權威工具在政策執行過程中是最為普遍的。例如,在民族地區大力加強基礎教育,有計劃實施九年義務教育,在基礎教育階段開展雙語教學,加強援藏援疆工作等,都是權威工具在政策執行中的具體表現。激勵工具是指政府利用正向或負向反饋來誘使目標對象遵從或采取相應行為,通常表現為獎勵或者懲罰。例如,為鼓勵內地教師前往山區、牧區等少數民族地區支教,采取教職工編制適當放寬、發放專項補助、工資待遇略高于所在地其他教職工的薪資等舉措。象征與勸誡工具是指通過影響目標群體的價值觀與信念,促使該群體采取與政策目標相一致的動機與決定。為了進一步調動民族地區辦學活力與積極性,黨中央充分調動廣大群眾與干部辦學的積極性,希望借助外部力量提高民族地區基礎教育的辦學水平與教育質量。能力建設工具是指為個體、群體或者機構提供采取行為或做出決策所必需的相關信息、培訓、教育以及資源,目的是幫助目標群體做出對既定目標有利的行為和決策,在政策中具體表現為向雙語教師提供師資培訓以增強雙語教學水平,為民族地區教師提供信息技術應用能力培訓以提升課堂教學水平等。系統變革工具是指政府權威在個人與機構之間出現轉移的情況,通常表現為新組織的建構或者已有組織的撤銷合并。如2011年設立的教育部民族教育發展中心,2014年成立的全國民族教育專家委員會,都是系統變革工具在民族基礎教育中的重要體現。學習工具是指目標群體依靠自身能力去解決不了解或不清楚的具體問題,它是一種過程性工具,通常體現于政策文本中。例如,各部門或學校為了加強民族團結意識,樹立國家認同感與民族認同感而采取的具體課程或活動。
(四)以政治學話語與經濟學話語為主導的政策話語規則
公共政策話語分析是一股潛力巨大的新潮流,為政策科學的發展注入了新鮮的活力,其理論價值具體體現于以下兩方面:一是能夠更好地幫助人們從意義的維度理解公共政策領域的結構與變遷,二是擅于揭示出隱匿于語言背后的權力結構與意識形態[14]。縱觀民族基礎教育政策的演進歷程可以發現,話語規則以政治學話語與經濟學話語為主導。一是以政治學話語為主導的話語規則階段。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進行政治改造、強調社會需求的任務是迫切且急需完成的,為此該階段的政策文本陸續提出了“少數民族教育應滿足各民族政治、文化建設需要”“少數民族教育必須為新民主主義內容,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的政治理念。二是以經濟學話語為主導的話語規則階段。在教育政策領域中,經濟學話語體系影響頗深,主要包含教育與經濟的關系、教育投資與教育財政、教育成本與收益、教育制度變革與創新、教育資源利用與效益[15]。經濟學話語一方面體現于教育投資與教育財政方面,例如,設立少數民族教育專項補助費,從支援邊境地區以及不發達地區的專項費用中劃出適當比例用于民族教育;另一方面體現于教育與經濟的關系上,例如,辦學形式應符合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需要,加快民族地區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等。三是其他學科政策話語的重要地位逐漸顯現的話語規則階段。隨著民族基礎教育政策的變遷,其話語體系不再局限于政治學與經濟學話語,社會學、倫理學等因素也逐漸在政策文本中顯露出來。例如,保障農村轉移人口以及進城務工子女平等接受義務教育權利,建立健全農村留守兒童關愛服務機制等舉措,都體現出政策話語規則逐漸走向多元化。
三、民族基礎教育政策的未來走向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在中央政府的正確決策下,我國民族基礎教育的發展取得了較大程度的進步。但在政策實施的演進過程中,逐漸發現以下問題:動力機制模糊主體間的協調配合,價值取向忽視民族文化內涵,政策工具之間的處理方式不恰當,政策話語體系缺乏民主協商性。為了進一步促進民族基礎教育政策的制度化與科學化,在未來的政策制定與實施過程中,應對動力機制、價值取向、過程保障以及話語規則等四方面加以調整與完善。
1.建立“兩團體”統一協作為原則的政策動力機制
制度變遷理論認為,推動制度變遷的力量主要包含兩大主體:初級行動團體與次級行動團體。初級行動團體是制度變遷的決策單位,是變遷過程中的主要推動力量;次級行動團體主要指制度變遷的實施者,目的在于幫助初級行動團體推進行動變遷的進程。兩類團體都是推動制度變遷的主體。就民族基礎教育政策而言,可將政府視為初級行動團體,各民族地區依據中央制定的大政方針與自身需求完善基礎教育體系;次級行動團體則為各級學校以及社會群體,在既定的政策框架下履行職責,維護教育體系的平穩運行。如何在這兩類團體尋求利益訴求的平衡,是促進民族基礎教育穩步發展的關鍵舉措之一。一方面,建立中央政府主導,各級部門協調配合的管理體系。在中央政府的宏觀指導下,各部門應明確自身的職責與權力,做到科學配合,避免職能重疊,將教育政策的制定與實施發揮出最大功效。此外,各地方政府應準確行使自身權力,確保政策的精準實施,并充分發揮內部監督的作用,避免“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政策失真現象產生。另一方面,加強大眾團體的參與意識,調動社會群體參與積極性。首先,要積極調動社會群體參與民族基礎教育的建設中去。由于地理因素的限制,民族地區大多處于經濟發展較為落后的區域,依靠當地自身發展與中央統一扶持仍難以實現教育發展的預設目標。因此,首先,要鼓勵社會群體的積極參與,借助東中部等經濟發達地區的大力扶持,促進民族地區辦學水平與教學質量的提升;其次,在政策制定與實施過程中,難免出現社會群體利益與統治階層利益相沖突的現象,這時就要秉承以人為本的理念,將民眾利益置于首位,確保政府執行的公開化、透明化,建構民眾主導的監督體系,有效提升教育政策執行的質量與水平。
2.倡導多元視角的政策價值取向
制定民族基礎教育政策時,應堅持在以人為本的基礎上,進一步實現教育公平,真正實現“工具理性”向“價值理性”的轉變。第一,深化以人為本的價值取向。人的各種行為由動機所引導、維持和導向,而人的動機以需求為基礎。教育政策的需求來源于教育客體,教育政策的制定也應尊重教育客體的需求[16],因此,政策的制定要關注到不同民族地區受教育者的需求,為受教育者提供多樣化的選擇,使其獲得更多的發展機會,讓每一個獨立個體能夠依據自身需求與興趣,選擇最有利于自身發展的途徑,實現自我的全面發展。第二,注重民族文化“內生式”發展。基于民族地區自然因素與歷史因素的特殊性,在制定政策時既要關注區域特殊性,又不能忽略文化普遍性。在新時代的背景下,基于文化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的張力所提出的“意識三態觀”為我們提供了新的思路與借鑒意義。該理論是一種包含宏觀、中觀與微觀視野的三維綜合觀。在主體多樣化的背景下,民族基礎教育需整合不同的利益與價值訴求,將國家認同、民族認同與自我認同三者結合起來,通過學校這一多元文化匯集的場域,尋求能夠使各種文化平衡并有機整合為一體的方式[17]。一方面,借助學校教育傳承地方文化,為地方文化的保留與傳承提供空間;另一方面,通過學校教育有效地塑造國家認同感與民族自豪感,使學生成為國家與民族文化的編織者[18]。第三,在公平的基礎上尋求效率最大化。一直以來,效率取向與公平取向的兩難選擇一直存在于各類教育政策研究之中。從以往的民族基礎教育政策來看,大多是通過物質性補償而采取的優惠性政策,這與羅爾斯所代表的契約主義平等觀相類似,即給“弱者”一定補償來取得結果平等。盡管這有利于保障公平,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效率的損耗,不利于整體教育質量的提高[19]。因此,從當前我國國情來看,我們既要注重民族地區的公平問題,加大對民族基礎教育的政策扶持與傾斜力度,滿足少數民族學生的最大教育利益;同時要兼顧到教育資源的合理分配問題,其他學生的受益須以少數民族學生受益為前提,在此基礎上,統籌各方利益與價值需求,做到因地制宜,以實現效率最大化。
3.實行多種政策工具有機結合的實施過程保障
民族基礎教育領域的改革與發展兼具復雜性與多變性,在具體的政策實施過程中,需要多種政策工具的有機結合,才有利于解決經費投入不足、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等問題。第一,加大對民族地區基礎教育經費投入力度。中央政府要利用權威工具科學、合理制定經費預算機制,并規定用于民族地區教育的專項資金不可挪作他用。另外,政府同樣應積極利用激勵工具,鼓勵當地干部、群眾以及經濟發達地區的社會大眾投入到民族地區基礎教育的建設中去,為民族地區增添辦學活力。第二,針對教育資源分配不均衡的現象,一方面要吸引優質教師資源前往民族地區,另一方面應積極在當地實行現代遠程教育。首先,可以利用提升職稱、提高薪資水平等方式鼓勵內地優秀教師前往民族地區支教,同時運用能力建設工具為當地教師提供師資培訓、信息共享等手段。其次,加強民族地區教育信息化的基礎設施建設工作,并為當地教師提供相應的應用能力培訓,借助現代遠程教育促進優質教育資源共享,保障民族地區基礎教育階段的學生接受到相對公平的教育。第三,加大對控輟保學的關注力度,必要時采取相應的懲罰措施,進一步健全民族地區義務教育辦學保障機制,加強寄宿制學校的辦學質量,并加強師資隊伍建設,鞏固義務教育階段的現有成果。針對個別因家庭教育觀念而導致的學生輟學,要強化家校共育、地校協作等理念,采取教育勸導、適當懲戒等方式,讓《義務教育法》真正既能落下去,又能硬起來[20]。第四,加強宏觀管理,建立執行監督機制。中央政府應合理使用系統變革工具,設立具有嚴格監管力度的督查部門和評估部門,對民族地區基礎教育的各項工作實行具體且有操作性的法律法規[21]。此外,針對具體的民族教育評估工作,要建立科學、系統的評價指標,真正發揮監督以及評估的政策保障作用。
4.構建多方參與式的政策話語體系
后實證主義者認為,傳統的政策分析主要是社會精英通過話語控制民主決策的過程,將政治議題轉化為技術性的事務。因此,他們倡導一種參與式的政策分析與制定過程,即依靠利益相關者間的對話來尋找問題的解決方式[22]。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應采取在政府的宏觀引導下,構建多方參與式的政策話語體系,形成以民眾需求為導向的政治理念。第一,政府應做好宏觀統籌工作,通過制定信息公開制度與構建民意表達渠道來切實保障多方民眾參與的權利與義務。首先,應積極制定透明化、簡易化的信息公開制度,保證民眾知情權,擴大信息公開范圍,增強信息傳播廣度,讓不同受眾都能夠通過相關媒介掌握到準確且前沿的政策信息。其次,應疏通民眾表達渠道,促成政府與民眾間的良性互動。政府可采取實地調查、走訪調研的方式深入群眾之中,也可設立民意調查與反饋制度、聽證會制度等權威機制,真正做到傾聽民聲、體現民意、集納民智。第二,應重視邊緣參與者的參與力度。除了政府及專家學者,民族基礎教育的利益相關者還包含基礎教育機構的教職員工、學生以及家長群體[23],雖然這類群體不是政策制定的核心參與者,但深受教育政策影響,是政策的直接目標群體。應為該類群體參與政策制定提供適當的機會,使其能夠通過多種途徑表達自身的利益訴求,這將直接作用于民族基礎教育政策的制定、調整乃至完善。總之,在未來的民族基礎教育話語體系建設中,應進一步加大多方主體的參與力度,不斷提升不同主體參與政策制定的能力與意識,開創民族基礎教育發展的嶄新局面。
參考文獻:
[1]倪勝利,張詩亞.民族基礎教育為什么打基礎[J].民族教育研究,2007(1):5-8.
[2]孫杰遠,韓小凡.70年少數民族基礎教育發展的“中國經驗”[J].民族教育研究,2019,30(6):5-14.
[3]國家民委經濟司,國家統計局綜合司.中國民族統計1949—1990[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1:217-227.
[4]袁梅,張良,田聯剛.民族基礎教育政策變遷歷程、邏輯及展望[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20,41(5):219-225.
[5]陳立鵬.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民族教育政策回顧與評析[J].民族研究,2008(5):16-24+108.
[6]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民族教育[EB/OL].(2020-11-04)[2021-12-27].http://www.moe.gov.cn/jyb_sjzl/moe_364/moe_302/moe_377/tnull_4501.html.
[7]康春英.對民族院校開展民族團結教育的認識和思考[J].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05(1):51-54.
[8]龍立軍.間斷平衡理論視角下70年中國少數民族教育政策變遷分析[J].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37(1):22-31.
[9]謝維和.教育活動的社會學分析[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7.
[10]祁占勇,李瑩.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高等教育政策的演進邏輯與理性選擇[J].高等教育研究,2018,39(4):16-22.
[11]唐日新,李湘舟,鄧克謀.價值取向與價值導向[M].長沙:中南工業大學出版社,1996:20.
[12]袁梅,劉玉杰.改革開放四十年我國民族教育政策價值取向的演進[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9,40(4):214-219.
[13]陳學飛.教育政策研究基礎[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1:323.
[14]李亞,尹旭,何鑒孜.政策話語分析:如何成為一種方法論[J].公共行政評論,2015,8(5):55-73+187-188.
[15]李桂榮.中國教育經濟學話語演進二十年[J].教育研究,2004(12):23-31.
[16]王謙.改革開放以來民族教育政策價值取向演變研究[D].重慶:西南大學,2016.
[17]袁同凱,丁月牙,巴戰龍,等.構建民族教育研究的中國話語(筆談)[J].民族教育研究,2018,29(3):5-13.
[18]錢民輝,沈洪成.從意識三態觀重新審視現代性與民族教育之關系[J].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34(4):2-6.
[19]王平.對我國民族基礎教育政策的幾點認識[J].民族教育研究,2010,21(4):9-13.
[20]賈偉.新時代我國義務教育控輟保學的內在機理、現實困境及破解對策[J].教育與經濟,2020,36(4):50-57.
[21]姚佳勝,方媛.政策工具視角下我國流動兒童教育政策的量化分析[J].教育科學,2020(6):85-93.
[22]何鑒孜,李亞.政策科學的“二次革命”——后實證主義政策分析的興起與發展[J].中國行政管理,2014(2):95-101+121.
[23]李德顯,房磊.促進專業技術人員階層形成的教育機制[J].復旦教育論壇,2020,18(5):19-25.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Evolution Logic and Future Trend of Ethnic Basic Education Policy in China
YAO Jiasheng, LIN Xiaowen
(School of Education,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China,116029)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thnic basic education policy has experienced the initial stage on the premise of speeding up the development of primary education, the recovery and adjustment stage focusing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nine-year compulsory education, the accelerated catch-up stage with the goal of realiz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nd the stage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based on seeking development of ethnic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rocess of policy evolution, it gradually presents the policy dynamic mechanism with the change of management system as the core, the policy value orientation from "social standard" to "individual standard", the guarantee of implementation process by means of various policy tools, and the policy discourse rules dominated by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economic discourse. In the future, the policy of basic education for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should present the policy dynamic mechanism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unity and cooperation of "two groups", the policy value orientation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the guarantee of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various policy tools, and the policy discourse system of multi-participation.
Key words:
ethnic basic education policy; ethnic education; development process; evolution logic; future trend
收稿日期: 2022-02-13
基金項目:全國教育科學規劃教育部重點課題“我國城鄉義務教育師資均衡配置政策評價與優化策略研究”(DFA200299)。
作者簡介:姚佳勝,男,遼寧北鎮人,博士,遼寧師范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
林曉文,女,黑龍江哈爾濱人,遼寧師范大學教育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