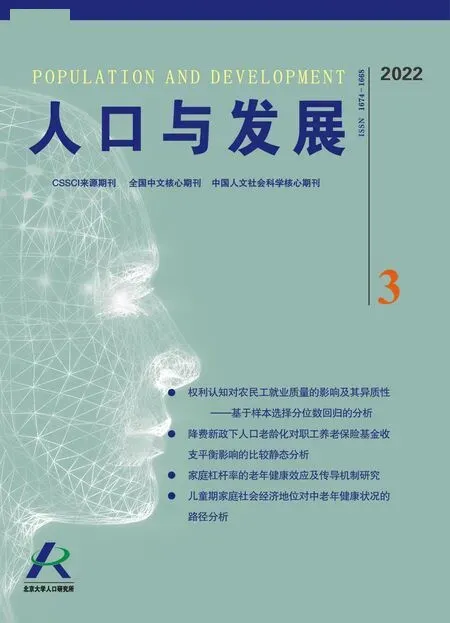跨戶籍婚姻與流動人口的本地身份認同
——來自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的證據
孫楠
(復旦大學 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上海 200433)
1 研究背景
對于流動人口來說,流動過程不僅僅是地理空間的變化,包括居住、就業、行為模式、社會網絡等一系列要素都面臨在流入地的重構(蔡禾,曹志剛,2009)。在此過程中要如何回答“我是誰”,就是流動人口所面臨的身份認同問題。尋找身份認同是流動人口群體無一例外要經歷的過程。它“是行動者獲取意義的源泉”(盧暉臨,潘毅,2014),并引發明顯的社會和經濟效應(鄧睿,2019;周明寶,2004)。流動人口的身份認同可以反映他們的社會融入程度,這也是我國新型城鎮化能否順利推進的關鍵。許多研究探討了影響流動人口社會融入的因素(張文宏,雷開春,2008;楊菊華等,2016;史毅,2016)。這些因素在微觀層面主要包括個人和家庭特征,就家庭特征而言,諸多文獻著重考察了家庭化遷移對于流動人口社會融入的影響(褚清華、楊云彥,2014;王春超,張呈磊,2017),但從婚姻角度予以關注的研究較少。
人口流動范圍擴大和流動規模增加導致通婚圈拓展(張翼,尹木子,2017),在此過程中一些流動人口于流入地結識配偶并與之結婚安家,呈現出婚姻的跨戶籍性。在農村到城市為人口流動主導方向的階段,這種跨戶籍婚姻主要表現為城鄉通婚,反映出戶籍類型的差異。但隨著城鄉二元結構弱化,以及城-城流動人口增加,跨戶籍婚姻更普遍體現為跨越戶籍屬地,即本地人與外地人的結合。從“城鄉之別”到“內外之分”,折射出我國戶籍改革的現實進程(Felicia F.Tiana et al.,2018)。2014年國務院明確提出取消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性質區分和由此衍生的藍印戶口等戶口類型(1)國務院《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2014年7月30日。,統一登記為居民戶口,旨在進一步縮小城鄉居民公共福利水平,提供更加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務。在逐漸削弱戶籍類型特殊性的同時,戶籍屬地在引導和管理屬地內流動人口方面的作用卻在強化。由于地方政府更多地對與戶籍屬地相關的政策負責,包括制定落戶標準和確定本地戶籍福利待遇的自主權,戶籍屬地決定了人們能否在特定的城市享受當地的福利和社會服務。這種本地人與外地人結合的婚姻模式會對個人及家庭生活產生什么影響便是順應而生的問題。另一方面,通婚是國外社會融入研究領域的重要內容之一,研究發現跨族群婚姻不僅反映出社會融入的程度,也對少數族裔或移民的社會融入產生進一步的影響。而在國內研究中,基于戶籍屬地的異質性,一些文獻關注了這種跨戶籍婚姻的現狀、演變(高穎,張秀蘭,2014;趙曄琴等,2016),但其對流動人口社會融入所產生的影響尚缺乏研究,而這也正是本文期待回答的問題。
本文將“跨戶籍婚姻”定義為本地戶籍人口與流動人口結合的婚姻模式,利用2017年全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數據,就跨戶籍婚姻對流動人口本地身份認同的影響進行定量考察。文章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第三部分介紹數據、變量和研究方法,第四部分匯報實證結果,第五部分是穩健性檢驗,第六部分是全文的總結與討論。
2 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米爾頓·戈登在其經典同化論中,系統性劃分了移民社會融入的過程,包括文化融入、結構性整合、通婚、身份認同、態度認同,行為接受和公民性同化七個層面(Milton Gordon,1964)。通婚作為其中的重要一環,一方面體現為不同社會群體間交往增強的結果,另一方面繼續促進移民心理層面的融入。盡管一些國外研究認為,跨族群婚姻與社會融入的關系并非那么絕對(Chow,2000;Song,2007),但這主要是由于種族和宗教問題的復雜性。就國內情況而言,與本地人結婚仍然是流動人口實現非制度性社會融入的快速通道(靳小怡,2016)。
根據社會身份理論,個體在人際交往互動中獲得特定的社會身份角色并據此形成自我觀念,由此產生身份認同(Hogg et al.,2010)。從本質上來看,這種人際交往互動就是社會資本的表現形式,密切的交往互動有助于形成豐富的社會資源量,拓展個體的社會網絡,獲得更多社會支持(李斌,張貴生,2019)。有學者發現,農民工的社會資本越廣泛,越有利于消除群體偏見和改變身份認同(王桂新,武俊奎,2011)。這也正是理解從跨戶籍婚姻到本地身份認同這一跨越的關鍵。
跨戶籍婚姻促進了流動人口與當地社會成員建立關聯,參與各種活動,進入本地機構(Uzi Rebhun,2015),成為其本地社會資本的來源。首先,與本地人結婚的流動人口更可能進入本土生活空間,通過打破居住隔離增加和豐富流動者本地化的生活體驗,減少所感知到的社會排斥。正如有研究發現以本地人為主的鄰里構成會顯著提高流動人口的本地身份認同(祝仲坤,冷晨昕,2018);第二,通過跨戶籍婚姻,流動人口進入本地家庭并成為其中一員,得以分享配偶及其家庭的本地資源與網絡(Ryan & Mulholland,2013;Koelet et al.,2017)。此外,配偶的本地戶籍屬性以及與戶籍相關的社會福利與保障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削減制度隔閡帶給流動人口的心理距離。對于非法移民來說,婚姻制度更是合法化其自身或子女公民身份的手段之一(Passel & Taylor 2010)。而這種后致性的社會資本在許多研究中被發現有利于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合,增強其本地歸屬感(悅中山等,2011;任遠,陶力,2012)。
因此本文提出假設1:跨戶籍婚姻會顯著提高流動人口的本地身份認同;假設2:本地社會資本在跨戶籍婚姻對身份認同的影響中具有中介作用。
跨戶籍婚姻為流動人口融入當地社會提供了通道,然而,個體需要在多大程度上借助婚姻進行社會資本積累和實現本地身份認同,或者說流動人口對于本地配偶依附程度的強弱,實際上與個體客觀的社會融入能力密切相關。比如景曉芬,李松柏(2013)發現,一些客觀條件較差,通過婚姻遷移實現從“低”到“高”流動的農村女性,當遷入地的環境優于自己以前所處的環境,更容易形成“自己屬于這里”的身份認同。也就是說,當個體自身的社會融入能力較差,需要借助婚姻實現本地身份認同的程度就會增強。這種客觀能力主要由人力資本水平反映。大量研究發現,人力資本水平越高,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情況越好(Wang et al.,2018;劉濤等,2020;楊菊華,張嬌嬌,2016)。良好的受教育水平使流動人口在城市生活具備更大的優勢,并突出反映在就業市場。比如有研究發現,就業質量是流動人口人力資本影響其城市融入的中介變量(李強,何龍斌,2016);教育也是擴展社會網絡的有力手段,并正向影響流動人口的社區參與(楊菊華等,2013),受過高中以上教育的農民工更可能與流入地市民交往(李樹茁等,2008);從政策層面來看,一些特大城市和大城市更是將流動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與落戶直接掛鉤。在這種宏觀政策的影響下,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流動人口,受到的社會排斥越少,越有能力適應新環境,提高社會資本積累(杜鵬等,2005),在社會融入的過程中發揮主觀能動性。
因此本文提出假設3:隨著個體受教育水平提高,跨戶籍婚姻對流動人口的本地身份認同的影響會弱化。
盡管已有研究關注了跨戶籍婚姻的社會效應,但現有研究多著眼于跨戶籍婚姻中的女性群體,即“外來媳婦”。一是由于“從夫居”的傳統,女性更容易成為遷移的那一方;二是在“流動者”與“外來者”的雙重身份下,這些流動女性更可能處于“他者”邊緣(譚琳等,2003)。由此可見,跨戶籍婚姻帶給流動人口的是一種性別化的生活體驗,那么跨戶籍婚姻對其本地身份認同的影響也可能存在性別差異。社會性別理論認為,男女之間一種不對稱的、不平等的社會性差異,通過在文化場所中的建構,形成支配與從屬的權力關系(凱特·米莉特,1999)。女性在兩性權利關系中被建構為從屬的一方,強調其身為依附者的角色。比如在農村社會,女性婚后往往須依附于丈夫獲得在親屬體系和家族村落體制中的正式地位(楊華,2018)。對于農村女性來說,婚姻更是其獲取向上社會流動的主要方式(韋艷,蔡文禎,2014)。與本地已婚女性相比,婚姻遷移女性在經濟、社會支持和家庭關系福利等方面呈現出優越性(韋艷等,2014)。階層認知的相關研究也發現,“通過配偶而與生產資料建立的聯系”,在女性的自身階層地位感知中以間接的階級位置發揮作用(許琪,熊略宏,2016)。另一方面,被嵌入性別意涵的文化結構形塑著兩性的資源、機會、行為和心理等方面(劉愛玉等,2015),一定程度上這解釋了女性在社會生活和家庭生活的相對弱勢地位。雖然流動經歷在一些研究中被發現有助于女性的賦權增能(邱幼云,2017),但相對來說,流動女性在就業機會、就業穩定性、工資收入、社會參與等多方面仍然處于劣勢(羅俊峰,童玉芬,2015;吳際等,2017),相對男性,她們的社會融入渠道更為單一(向華麗,2013),這都有可能強化流動女性在構建身份認同的過程中對于婚姻的依附。
因此本文提出假設4:相對男性,跨戶籍婚姻對于女性流動人口本地身份認同的促進作用更為顯著。
3 數據、變量和方法
3.1 數據
本文的研究數據來自2017年全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CMDS),調查樣本為在中國大陸31個省(區、市)與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抽樣地區居住超過一個月而非當地戶口的人口。由于本文關鍵自變量為配偶戶籍性質,并以此界定樣本的婚姻模式是否屬于跨戶籍婚姻,因此只保留初婚、處于勞動年齡(16-59周歲)的樣本。對年齡進行限制是由于流動人口的經濟活動具有重要意義,限定在勞動年齡內可以排除退休等因素對于分析的干擾。在篩選樣本記錄后,最終得到120,901個有效研究樣本。
3.2 變量
因變量:本地身份認同。通過問卷中“是否同意‘我覺得我已經是本地人了’這個說法?”來反映,“完全同意”和“基本同意”取值為“1”,“不同意”和“完全不同意”取值為“0”,該變量為二分變量。
自變量:跨戶籍婚姻。本文中的“跨戶籍婚姻”定義為本地戶籍人口與外地流動人口結合的婚姻模式。由于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所針對的樣本群體均為流動人口,因此只需樣本配偶是否本地戶籍這個信息就可以判定該樣本的婚姻是否屬于跨戶籍婚姻。配偶為本地戶籍人口時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該變量為二分變量。
控制變量則依據已有研究所發現的影響流動人口身份認同的因素而選取。具體包括流動人口的社會人口學特征:性別、年齡、戶籍性質、健康狀況、工作狀況、子女數量;還包括流動特征:流動范圍、流動時間、流動經歷;以及住房性質、是否辦理居住證、是否擁有社保卡、是否購買醫療保險等社會保障因素。此外還將流入、流出地區域處理為虛擬變量加以控制。就本文所關注的本地社會資本變量,參照相關文獻(任遠,陶力,2012),本文從兩方面加以考察,一是社會交往,二是社會參與。前者通過“您業余時間在本地和誰來往最多?”反映,選擇“本地人口”視為1,其他視為“0”;后者通過過去一年在本地參加過工會活動/志愿者協會活動/同學會活動/老鄉會活動/家鄉商會活動/其他活動的總量來反映,參加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加總后按連續型變量處理。
3.3 方法
本研究使用了二元邏輯斯蒂回歸方法(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研究跨戶籍婚姻對流動人口本地身份認同的影響。模型的被解釋變量“身份認同”是二分類變量,建立模型如下:
Pr{identity=1|X}=Φ(β0+β1marriage+β2Adjust+β3Control+μ)
其中,identity是因變量,表示身份認同;marriage是自變量,表示跨戶籍婚姻;Adjust和Control分別代表前文所指出的調節變量和一系列控制變量;考慮到可能的內生性問題,本文將采用工具變量和傾向值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方法嘗試提高估計的精準性。
4 實證結果
4.1 描述統計
表1展示了變量設置情況及描述統計結果。可以看出,研究樣本實現了本地身份認同的占比為77%,9%屬于跨戶籍婚姻。樣本性別分布較為均勻,平均年齡為37.34歲,平均受教育年限為9.87年,從戶口性質來看,絕大部分樣本來自農村(79%)。圖1進一步列出了總體、分性別和戶籍的跨戶籍婚姻與本地身份認同情況。首先,女性樣本中實現跨戶籍婚姻的比例(10.4%)要高于男性(7.18%),城鎮流動人口(15.83%)實現跨戶籍婚姻的比例高于農村人口(6.87%);從認同本地身份的比例來看,男性(76.81%)和女性(76.37%)之間差異較小,城鎮流動人口(82.16%)認同本地身份的比例要高于農村流動人口(75.12%)。進一步與跨戶籍婚姻樣本實現本地身份認同的比例做比較發現,無論是總體還是分性別、戶籍來看,跨戶籍婚姻樣本認可本地身份的比例都要更高。

圖1 總體、分性別和戶籍樣本跨戶籍婚姻和本地身份認同情況(%)

表1 變量及描述統計
4.2 回歸結果
在控制了個體的社會人口學相關變量、流動特征、社會保障因素以及區域虛擬變量后,表2第一列的模型回歸結果顯示跨戶籍婚姻變量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跨戶籍婚姻對于流動人口的本地身份認同有顯著積極影響,即與當地人結婚的流動人口實現本地身份認同的概率更高,符合本文預期,研究假設1得到證實。
本文以社會交往和社會參與來反映流動人口的本地社會資本,并認為這在跨戶籍婚姻對其本地身份認同的影響中起到一定中介作用。表2第二列在第一列回歸模型的基礎上納入“社會交往”和“社會參與”變量,結果表明,社會參與和社會交往與流動人口本地身份認同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即相較非本地人口,與本地人口交往的流動人口實現本地身份認同的概率更高,參與本地社會活動越多則更加認同本地身份。在納入這兩個變量后,跨戶籍婚姻對本地身份認同的影響依然在同樣的置信水平下顯著為正,但是系數變小。因此,就跨戶籍婚姻對流動人口本地身份認同的影響來說,本地社會資本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假設2得到驗證。
跨戶籍婚姻在不同受教育水平和性別群體中的作用強度是否存在差異是本文所感興趣的問題。表2第三、四列回歸模型針對研究假設3、4進行驗證。在控制其他變量的情況下分別納入“跨戶籍婚姻”和“受教育水平”以及“跨戶籍婚姻”和“性別”的交互項。從回歸結果來看,“跨戶籍婚姻”與“受教育水平”的交互項顯著為負,這意味著受教育水平在跨戶籍婚姻對流動人口本地身份認同的影響中存在調節效應,受教育程度越高,跨戶籍婚姻對流動人口本地身份認同的正向作用則越小,假設3得到驗證。受教育水平作為個體重要的人力資本要素,可以通過促進勞動參與、提高社會經濟地位、增強社會交往等途徑作用于個體的本地身份認同,并通過形成更加獨立平等的性別觀和家庭觀,調節跨戶籍婚姻對流動人口本地身份認同的影響;從表2第四列回歸結果來看,“跨戶籍婚姻”與“性別”的交互項顯著同樣為負,這意味著跨戶籍婚姻對于流動女性本地身份認同的促進作用更強,假設4得到驗證。一方面,這可能與女性所持有的相對傳統的婚姻和家庭觀念有關,即在身份建構的過程中更可能依附于配偶。另一方面,也可能與流動女性在勞動參與、經濟收入、社會網絡構建等方面處于相對弱勢地位的客觀情況有關。

表2 跨戶籍婚姻對流動人口本地身份認同的影響
此外,一些控制變量對于流動人口的本地身份認同也具有顯著影響。男性相較于女性、城鎮人口相較于農村人口,實現本地身份認同的概率更高;年齡對身份認同的影響呈倒U形,隨著年齡增長更有可能認同本地身份,但繼而會產生負面影響,這里可能包含老年流動人口在社會融入方面所隱含的問題;受教育水平和健康狀況都與本地身份認同呈顯著正相關;但相對沒有工作的流動人口來說,工作的流動人口實現本地身份認同的概率反而更低,這可以理解為在勞動力市場所感知到的歧視與隔閡可能不利于流動人口的心理融入,而沒有參與工作的流動人口群體很可能是家庭隨遷者或者退休人員,對于社會隔閡的感知反而相對更少;子女數量越多,越不利于流動人口的本地身份認同。從流動特征來說,相較省內流動,跨省流動人口實現本地身份認同的概率更低;隨著流動時間增長,更加可能實現身份認同;相對而言,初次流動的人口更可能實現本地身份認同。研究還發現,擁有自有住房和辦理個人社會保障卡均對流動人口的本地身份認同具有積極影響,擁有住房產權有助于減少流動人口的漂泊感(徐延輝,邱嘯,2017),社會保障因素對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具有關鍵作用;辦理居住/暫住證與本地身份認同顯著負相關,盡管在一些城市依托居住證制度為流動人口提供相應的基本公共服務,但相較本地戶口,居住/暫住證可能仍然給流動人口以“臨時落腳”的心理體驗,因此呈現出顯著負相關的結果;流入地為東部地區則流動人口實現本地身份認同的概率更低,但來自東部地區的流動人口實現本地身份認同的概率更高,相比之下,來自西部的流動人口更不易實現本地身份認同。
考慮到鄉-城和城-城流動人口的差異性,即他們在流入地的生活體驗、感知以及建構身份認同的情境有所不同,有必要進行分樣本回歸分析。從表3的回歸結果來看,跨戶籍婚姻的影響系數在兩組樣本中均顯著為正,需要說明的是,考慮到邏輯斯蒂回歸模型中隨機擾動項方差異質性的影響,我們對模型結果計算了APE(average partial effect)系數(2)城鎮樣本中跨戶籍婚姻對身份認同影響的APE系數為0.071,農村樣本這一系數為0.099。。這一系數幾乎不會受到與自變量無關的未觀測異質性的影響,并可以進行模型間、樣本間的系數比較(洪巖璧,2015)。比較可知,跨戶籍婚姻對鄉-城流動人口的身份認同促進作用更強。

表3 跨戶籍婚姻對流動人口本地身份認同影響的分樣本回歸
5 穩健性檢驗
盡管身份認同常用以反映更高層次的心理融入,并被認為與其他維度的社會融入存在發展脈絡上的遞進順序,但由于融入過程本身的動態性和復雜性,跨戶籍婚姻和本地身份認同之間仍然存在可能的反向因果問題。因此,本文選取流入地所在地區跨戶籍婚姻的比例作為工具變量,采用IV-probit方法嘗試處理這一問題。選擇這一工具變量的原因有二:一是婚姻行為可能具有群體內的示范效應,在跨戶籍婚姻比例更高的空間范圍內,流動人口與本地人結婚的概率可能更大;二是在一定程度上這個指標可以反映區域婚姻文化,比如有些地區更為盛行本地嫁娶的傳統,有些地區這種傳統相對較弱,而這對于流動人口跨戶籍婚姻的實現可能有重要影響。這一變量影響流動人口的婚姻選擇,但對其本地身份認同應無明顯的直接影響。從表4的結果來看,第一階段回歸結果表明,地區層面跨戶籍婚姻的比例與流動人口的婚姻選擇顯著正相關,符合本文的預期;第二階段回歸表明跨戶籍婚姻確實對流動人口本地身份認同有顯著正面影響。可見,跨戶籍婚姻會提高流動人口本地身份認同,再一次驗證了本文的研究假設。

表4 工具變量回歸
此外,由于作用于流動人口本地身份認同的因素可能也同時作用于其是否選擇跨戶籍婚姻,即存在樣本自選擇的可能。因此本文采用傾向值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以處理組平均處理效應(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for the treated,ATT)方法來計算處理效應。
具體的操作步驟如下:首先,將樣本分為兩組——處理組:跨戶籍婚姻組,控制組:非跨戶籍婚姻組;然后根據流動人口相關信息來估計樣本進入跨戶籍婚姻組和非跨戶籍婚姻組的概率,得到傾向得分值(Propensity Score);其次,根據傾向得分值大小進行匹配;再次,將匹配好的、與跨戶籍婚姻樣本的傾向得分最接近的非跨戶籍婚姻樣本作為其反事實;最后,比較兩組間身份認同的差異,再對計算出來的差異取均值,得到流動人口跨戶籍婚姻對于其身份認同的平均處理效(ATT)。
本研究采用Logit模型獲得實現跨戶籍婚姻的傾向匹配得分值。具體模型如下:
Pr{marriage=1|X}=Φ(β0+β1Adjust+β2Control+μ)
其中,marriage表示跨戶籍婚姻;Adjust和Control分別代表前文所指出的一系列調節變量和控制變量。也就是一系列可能影響流動人口與本地戶籍人口結婚的特征變量,這里選取了包括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健康狀況、戶籍類型、流動范圍、流動經歷、流出地區域、流入地區域等在內的因素,由此計算出每個樣本與本地戶籍人口結婚的概率值。在估計出每個個體的傾向得分后,依據得分的共同支撐域(common support)來匹配處理組和控制組。本文主要采取“最近鄰匹配法”(Nearest Neighbor Matching)進行匹配,同時,也分城鄉對研究結論進行檢驗。處理結果如表5,在匹配消除了控制組和處理組樣本系統性誤差后,跨戶籍婚姻依然顯著促進了流動人口的本地身份認同。

表5 ATT估計結果
6 結論與討論
本地身份認同在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以及新型城鎮化的推進過程中具有重要意義。本文以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CMDS)2017年數據為基礎,按照戶籍屬地的異質性定義了跨戶籍婚姻,考察了與本地戶籍人口結婚對流動人口本地身份認同的影響,以及性別、人力資本的調節作用和本地社會資本的中介作用。研究發現:
(1)跨戶籍婚姻對流動人口本地身份認同存在積極影響,分城鄉來看,這種影響在農村人口更加明顯;在運用傾向得分匹配和工具變量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之后,結果基本一致;
(2)本地社會資本在跨戶籍婚姻對身份認同的影響中起到中介作用。通過跨戶籍婚姻,流動人口增加了本地社會參與和社會交往,進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本地身份認同;
(3)性別和人力資本對此影響具有調節作用。跨戶籍婚姻對于本地身份認同的促進作用在女性流動人口群體中更為強烈;個體受教育程度越高,跨戶籍婚姻對其本地身份認同的促進作用越小;
(4)流動人口的本地身份認同還受到諸多其他因素影響,包括受教育水平、健康狀況、住房性質、流動范圍、流動時間、福利保障等因素。
在不同規模與城鎮化率的地區,流動人口的融入特征與困境是有區別的,這是考察跨戶籍婚姻對于流動人口本地身份認同影響的現實背景。在特大城市和大城市,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問題尤為突出(劉濤等,2020)。盡管大城市擁有更多的就業機會、更高的收入水平,以及更全面優質的社會保障服務。但另一方面,相較中小城市、縣城,大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以及政策因素構成流動人口社會融入的巨大挑戰,流動人口面臨更多社會融入的制度性壁壘和隱形的文化障礙。跨戶籍婚姻的意義也因此不僅僅是簡單的擇偶決策,而是流動人口融入當地社會的快速通道。
從這個角度來說,在看到跨戶籍婚姻積極社會效應的同時,更應該豐富和拓展流動人口融入城市生活的途徑,幫助他們進行人力資本的開發,增強其社會融入能力,比如提供職業培訓、增強繼續教育、提升健康水平等。較高的人力資本水平可以為流動人口帶來更好的就業機會、更高的勞動收入、更多的價值認可,以及更強的適應能力,這都有助于他們積極定位自己的本地身份。尤其在超大城市和大城市較為嚴苛的落戶政策背景下,流動人口的人力資本水平更是與落戶條件直接掛鉤。跨戶籍婚姻對流動人口身份認同的促進作用隨著個體受教育水平提高而下降這一研究結果進一步表明,人力資本水平是流動人口在新的社會空間中立足、適應并融入的重要自致性因素,可以使流動人口在婚姻之外擁有更多相對獨立去建構本地身份認同的機會。研究結果還表明,制定相應政策要具備性別視角和城鄉視角,政策受眾尤其要關注女性和農村流動人口。跨戶籍婚姻的身份認同促進效應之所以在女性流動人口和農村流動人口中更為顯著,除了跨戶籍婚姻本身具有一定的選擇性之外(沈文捷,風笑天,2013),更可能與這部分群體的相對弱勢地位有關。這不僅反映在勞動力市場,還體現在他們所獲得的社會支持等方面(Parrado & Flippen,2005)。比如農村人口更可能面臨流動帶來的文化沖擊和制度排斥(劉娜,2019),流動女性更可能面臨原生家庭支持網絡的弱化與斷裂(祖群英,2014)。因此,應格外關注這部分群體在社會融入中所面臨的障礙和挑戰。
跨戶籍婚姻對流動人口本地身份認同的促進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本地社會資本的積累實現的。跨戶籍婚姻增加了流動人口的本地社會交往和社會參與,在此過程中構建起本地關系網絡,積累了社會資本,進而產生積極的身份定位。但在實現流動人口社會融入的目標導向下,不能僅僅將跨戶籍婚姻看作手段,事實上跨戶籍婚姻也是流動人口與本地人口間社會距離縮小的重要信號(Song,2009)。未來政策的著眼點應在于營造開放包容的社會環境,促進本地人口與流動人口之間的社會交往,強化流動人口在公共社會領域的嵌入程度。
本文還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跨戶籍婚姻究竟如何作用于流動人口的身份認同,本文提出的影響機制仍十分有限,現實情況顯然會更復雜,比如跨戶籍婚姻如何從家庭生活內部作用于他們的身份認同仍然需要進一步探索;第二,結合流入和流出地相關特征,跨戶籍婚姻的社會融入效應可能具有一定異質性,但受限于數據,本文未能對此進行充分討論;第三,盡管本文采取了傾向得分匹配和工具變量方法,但更好地進行因果推斷還應采用追蹤數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