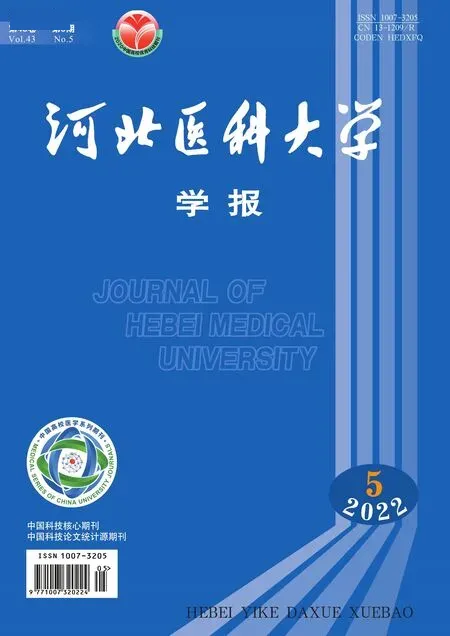磁共振波譜測量下的精神分裂癥高危人群腦內谷氨酸水平Meta分析
王 強,周 爽,馮 玥,任會鵬
(河北醫科大學第一醫院精神衛生中心,河北 石家莊 050031)
精神分裂癥是一種成年早期發病的神經發育性障礙,也是全球殘疾的主要原因[1]。有研究表明,對于精神分裂癥患者來說,早期干預可以更好的改善患者預后和社會功能[2]。因此,很多人關注于精神分裂癥高風險人群的研究,這類人群主要包括兩類,一是臨床高危險人群或超高危險人群,該人群以輕微陽性癥狀或短暫癥狀表現為主,二是遺傳高危險人群,即精神分裂癥患者的父母、兄弟姐妹、子女,該人群也稱精神分裂癥的一級親屬。既往有Meta分析顯示,大腦谷氨酸(glutamate,Glu)能的異常是精神分裂癥主要神經生化改變之一[3-4]。精神分裂癥的Glu假說認為,腦內的Glu能途徑紊亂和Glu受體信號傳導障礙與精神分裂癥的發病有關,是精神分裂癥的病理生理機制多巴胺假說的補充理論[5]。也有研究表明,Glu受體拮抗劑如苯環己哌啶可在正常受試者身上引起精神病性癥狀[6],這為Glu假說提供了證據。而精神分裂癥高風險階段的腦內Glu是否已經出現異常成為近年來研究人員更為關注的問題,因為這為精神分裂癥的早期診斷和預防提供了新的思路。而目前關于精神分裂癥高風險階段的Glu的研究結果也尚存爭議。磁共振波譜成像技術是一種可以無創性測量大腦中代謝物濃度的成像方法,是目前測量腦內Glu濃度的主要方法。大多數有活性的Glu來源于谷氨酰胺,而在較低電場強度下,由于結構相似,Glu和谷氨酰胺很難被分離出來,也因此合稱為Glu類化合物(glutamine,Glx=Glu+谷氨酰胺)。隨著高場強核磁的應用,即3T及以上場強可以更容易分離出Glu和谷氨酰胺。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對精神分裂癥高危人群在磁共振波普的測量下Glu和Glx的濃度進行Meta分析,以評估Glu濃度對精神分裂癥風險人群的識別作用。
1 資料與方法
1.1文獻檢索 計算機檢索從建庫至2020年10月31日,中文和英文發表的相關文獻。英文檢索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數據庫;中文檢索SinoMed、中國知網、萬方數據庫。英文檢索題目/摘要:①Schizophrenia/Psychosis;②Ultra high risk/Genetic high risk/Clinical high risk/High risk/Prodrome;③Glutamate/Glutamine/Neurotransmitter;④MRS/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1H-MRS。中文檢索關鍵詞:①精神分裂癥/精神病;②磁共振波譜/磁共振。分別對以上的英文數據庫①②③④和中文數據庫①②組合進行檢索。同時手工檢索相關參考文獻。初步檢索到2 486篇相關文獻。
1.2文獻納入與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①研究對象:通過精神病風險狀態綜合評估(Community Assessment of At-Risk Mental States,CAARMS)[7]精神病風險綜合征結構式訪談(Structured Interview for Prodromal Syndromes,SIPS)[8]、前驅癥狀量表(Scale of Prodromal Symptoms,SOPS)[9]評估后符合精神病風險綜合征者,以及無癥狀的遺傳高風險受試者;②研究設計包括精神分裂癥高危人群組和正常對照組兩組數據,如果在同一人群中進行了多次掃描,只納入基線值,使用磁共振波譜進行測量;③文獻報告了樣本量、性別、核磁場強等。
排除標準:①非臨床研究(包括動物實驗、細胞研究、基因研究等);②非病例對照研究(綜述、Meta分析、專家評論、個案報道等);③文獻信息不完整。
1.3文獻質量評估 文獻質量評估病例-對照研究采用紐卡斯爾-渥太華量表(Newcastle-Ottawa Scale,NOS)[10]進行評價,NOS包括3個維度8個條目:研究對象的選擇(4個條目)、組間可比性(1個條目)、結果測量或暴露因素測量(3個條目),除條目組間可比性為2分外,其余各條目為1分,評分范圍為0~9分。
1.4統計學方法 應用RevMan 5.3統計軟件分析數據。Meta分析,根據異質性檢驗結果選擇固定效應模型或隨機效應模型,并根據各腦區進行亞組分組。采用漏斗圖進行發表偏倚評定。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 果
2.1文獻檢索結果及納入文獻基本情況 本次研究初步檢索出2 486篇相關文獻,刪除重復發表的文章,并根據文獻排除標準篩選后,最終納入27篇文獻,43組數據。各文獻基本情況見表1,流程圖見圖1。

表1 納入文獻基本特征

圖1 文獻篩選流程
2.2效應量分析
2.2.1精神分裂癥高危人群組與正常對照組之間Glx的Meta分析 腦內異質性結果顯示存在異質性χ2=87.89,P=0.53,I2=54%),采用隨機效應模型。Meta分析結果顯示腦內Glx的效應值為(MD=0.04,95%CI:-0.09~0.17,P=0.53)提示腦內Glx在精神分裂癥高危人群組和正常對照組之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各腦區亞組分析結果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圖2)。

圖2 兩組各腦區的Glx濃度比較
2.2.2精神分裂癥高危人群組與正常對照組之間Glu的Meta分析 腦內異質性結果顯示存在質性(χ2=52.49,P=0.07,I2=60%),采用隨機效應模型。Meta分析結果顯示腦內Glu的效應值為(MD=-0.16,95%CI:-0.34~0.02,P=0.07)提示腦內Glu在精神分裂癥高危人群組和正常對照組之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亞組分析結果顯示丘腦Glu的效應值為(MD=-0.36,95%CI:-0.64~-0.09,P=0.01)提示丘腦Glu在精神分裂癥高危人群組和正常對照組之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背外側前額葉Glu的效應值為(MD=-0.76,95%CI:-0.15~-0.03,P=0.04)提示背外側前額葉Glu在精神分裂癥高危人群組和正常對照組之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顳葉Glu的效應值為(MD=-1.15,95%CI:-1.88~-0.43,P=0.002)提示顳Glu在精神分裂癥高危人群組和正常對照組之間差異統計學意義;其余各腦區亞組分析結果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圖3)。
2.3發表偏倚 對研究采用漏斗圖進行發表偏倚評定,結果發現在精神分裂癥高危人群組和正常對照組的在腦內Glx研究集中在漏斗圖中部,漏斗圖基本呈左右對稱,表明不存在發表偏倚(圖4)。在腦內Glu研究的漏斗圖基本左右對稱,表明不存在發表偏倚(圖5)。

圖4 腦內Glx漏斗圖

圖5 腦內Glu漏斗圖
3 討 論
對精神分裂癥病理生理學的更好理解有利于該病的診療發展,通過研究有發展這種病理風險的受試者,一方面可以確定潛在的早期危險性因素,另一方面,探索早期干預,以限制高風險者進行性的功能減退。本研究的目的是探索精神分裂癥高危人群在磁共振波普的測量下Glu和Glx的濃度,以評估其對精神分裂癥風險人群的識別作用。盡管近年來已有前人發表相關的Meta分析[38],但較之而言,我們檢索了更全面的中英文數據庫,納入了新近發表的相關研究;對Glu和Glx的濃度按照內前額葉、背外側前額葉、顳葉、枕葉、海馬、紋狀體等不同腦區進行了亞組分析,結果更具有說服力[12,27,37]。
Glu被認為是大腦中最豐富的興奮性氨基酸神經遞質[39]。谷氨酰胺是Glu的酰胺。Glu可以激活G蛋白偶聯代謝型受體和親離子受體,根據其對高親和性、選擇性配體的敏感性,可將其分為3種亞型:NMDAR、α-氨基-3-羥基-5-甲基異氧唑醇-4-丙酸受體和鉀鹽鎂礬受體。與非NMDAR離子性谷氨酸受體相比,NMDAR表現出相對緩慢和不完全的脫敏,因此,認為精神分裂癥是由NMDAR功能減退引起的[40-42]。NMDAR的激活需要三個同時發生的事件:①突觸后去極化;②甘氨酸或d-絲氨酸占據GluN1上的位置;③神經遞質Glu與其在GluN2上的受體結合,打開通道并允許鈣離子進入。鈣誘導細胞內的級聯反應,介導局部、急性功能突觸可塑性和基因表達的變化,促進長期神經結構可塑性[43]。本研究結果顯示,較健康對照組相比,精神分裂癥高危人群組的丘腦Glu濃度明顯降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0);這符合了上述NMDAR功能減退的假說。該結果與最近的Wenneberg等[38]的Meta分析結果相同,本研究在丘腦區的亞組分析中,Wenneberg的研究多納入了一篇研究[37],且異質性低(I2=35%,P=0.20),結果較為穩健。這表明丘腦Glu濃度降低可能是精神分裂癥發作前的風險標志物。
此外,本研究結果顯示,背外側前額葉、顳葉的Glu濃度在精神分裂癥高危人群組和健康對照組間差異也有統計學意義。但是這兩個腦區僅納入了一篇文獻,缺乏可靠性。除此之外,本研究沒有發現其他腦區的Glu和Glx濃度在兩組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這可能是由于各腦區樣本量較少造成的,且Glu在許多腦代謝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包括蛋白質合成和線粒體能量代謝[44],因此存在于許多細胞類型,也存在于細胞內和細胞外空間,而1H-MRS研究僅提供整個組織測量,無法區分細胞內、細胞外室,或神經元外室[45],這進一步限制了這些測量的特異性。因此,盡管其他腦區的Glx、Glu濃度差異無統計學意義,但受到目前檢測手段的限制,也不能排除其他腦區在Glu神經傳遞的特定方面發生改變,這些也許被掩蓋在總信號或代償性改變中[46]。
本研究納入臨床高風險人群的使用的三種檢查工具具有較高的一致性。CAARMS是由澳大利亞墨爾本的Yung等[7]開發的半定式檢查工具,而SIPS是由美國的Miller等[8]開發的一個半定式檢查工具,這兩種量表的高風險評判標準均為符合以下l條或以上:①輕微陽性癥狀綜合征;②短暫性、間歇性精神病癥狀綜合征;③遺傳風險及惡化綜合征。而SOPS則是SIPS訪談中的一種量化的量表,按照受試者具體分數評判是否符合高風險綜合征[9]。
本研究存在幾個局限性,一是人群存在一定的差異,因為本研究是使用CAARMS、SIPS、SOPS三種量表來評估有癥狀的高風險受試者和無癥狀的遺傳高風險受試者;二是磁共振場強存在一定的差異,因為納入的研究有6篇1.5T,20篇3.0T以及1篇7T的文獻;三是體素(指大腦三維空間內切割的單位體積)存在一定的差異,包括體素的位置和大小;四是方法存在一定的差異,所納入的研究中,23篇研究直接測得Glx、Glu,而由于腦脊液是流動的,為了減小偏倚,有4篇研究是計算Glx、Glu與相對穩定的代謝物之比(如Glx/Cr、Glx/Cho)。最后,研究中所納入的文獻缺少對精神分裂癥高危人群轉化情況的研究,無法進一步探索Glx、Glu的濃度隨著高危人群發病進展的動態變化。
綜上所述,精神分裂癥高危人群丘腦的Glu的濃度降低,為NMDAR功能減退假說提供了證據,即一些腦代謝物濃度(如Clu)可能在高危人群過渡到發病之前出現異常,這可以被認為是危險性因素。未來的研究應該繼續研究這一主題,以便更好地理解精神分裂癥的病理生理,并開發可能改變臨床實踐的生物標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