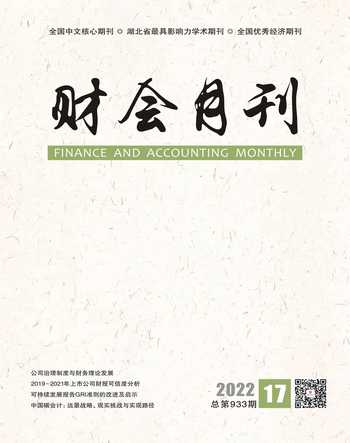高管晉升制度創新與企業績效
賀云龍 黃欣 鄭琦



【摘要】本文以2010 ~ 2019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 實證檢驗高管晉升制度創新的過密化與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 研究結論表明: 高管晉升與企業績效顯著正相關, 高管職級差距在閾值內愈高, 導致的利益趨同效應愈顯著, 企業績效也愈好; 高管晉升制度創新與企業邊際績效顯著負相關, 陷入過密化困境, 高管職級差距超出閾值時, 非理性競爭增強, 高管晉升制度對企業績效的提升作用減弱。 進一步研究發現: 國有企業高管政治晉升激勵效應比非國有企業更顯著, 非國有企業因晉升資源較少, 更容易出現過密化; 高管性別歧視會抑制晉升的激勵效應。 基于上述結論, 從優化高管晉升制度創新資源分配機制、完善高管晉升監督體系與協同推進高管激勵機制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議。
【關鍵詞】企業績效;高管晉升;制度創新;過密化
【中圖分類號】F275.5? ? ? 【文獻標識碼】A? ? ? 【文章編號】1004-0994(2022)17-0040-10
一、引言
黨的十八大以來, 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以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大決策相繼發布, 以企業為主體的創新型經濟體系依序構建。 在此期間, 企業創新經濟先后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 一是以技術創新為主、非技術創新為輔; 二是新常態下以制度創新為核心、以非技術創新漸進為另一主導; 三是“雙主導”模式下以制度創新為技術創新提供保障。 隨著技術創新機制的日趨成熟, 制度創新逐漸成為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關鍵驅動因素。 但國有企業突出的“內部人控制”現象與民營企業突出的“逆向選擇”問題, 及其衍生的“管理漩渦”現象(如用人唯親、裙帶關系等), 導致制度創新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效率有待進一步提升。
企業高管晉升制度在制度創新體系建設中非常重要。 高管“德才不配位”會導致企業管理低效并妨礙其長期發展, 擇優選才的高管晉升制度如體現為制度創新的過密化則不利于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高管晉升對企業績效的邊際效用銳減, 愈高的高管晉升制度創新成本與愈低的企業績效增量相對應。 多數學者沿著高管晉升對企業績效的短期效用這一邏輯鏈條來探究高管晉升制度與企業可持續發展之間的關系, 并未從動態視角考察企業高管晉升對其績效的邊際效用, 更未揭示高管晉升制度創新的過密化問題。 高管非理性競爭導致管理危機始終存在, 對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阻礙更甚于“紅皇后效應”①。 因此, 關注企業競爭戰略中高管晉升制度創新的過密化趨勢, 將有助于在提升高管晉升制度績效的同時進一步優化其競爭戰略, 從而促進企業可持續發展, 不斷提升企業價值。
本文沿著企業在競爭中取得可持續績效的軌跡, 完善“競爭戰略—制度約束—企業績效”這一邏輯鏈條, 探究高管晉升制度創新對企業績效的作用。 這將有利于完善制度創新理論, 構建高管晉升制度與企業創新績效之間的邏輯框架, 從而拓寬可持續發展理論, 協同完善激勵與約束相容機制。
二、文獻回顧與理論分析
(一)文獻回顧
高管晉升制度創新是企業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 其對于企業構筑持續競爭優勢具有顯著成效[1] , 在企業可持續發展中發揮著關鍵作用[2] 。
1. 高管晉升激勵及問題導向下的制度創新。 企業高管晉升從屬于隱性激勵。 基于錦標賽理論, 高管晉升激勵具有明顯的凸性特征。 Kini等[3] 發現, 高管晉升將獲取更多的貨幣薪酬與更大的職權, 顯、隱性激勵效應皆更顯著。 基于參照點理論, 高管晉升的個人職級與薪酬參照落差一并存在且前后映射: 職級參照物為職權、薪酬與福利待遇, 這些都會因高管內部參照生成落差。 步丹璐等[4] 發現, 晉升預期并未緩解國有企業的委托代理問題, 國有企業高管政治晉升欲望強于晉升自利動機, 其個人職級參照落差顯著, 背離社會公平的高管職級差距會減弱晉升的激勵效應。 因此, 高管晉升機制雖能彌補薪酬激勵機制的缺陷[5] , 但仍需在問題意識下不斷創新。
相對而言, 國有企業政治晉升激勵的雙刃效應顯著, 高管晉升制度創新能削弱政治晉升激勵的負面效應并強化其正面效應。 周銘山等[6] 發現, 政治晉升激勵能提高企業創新產出, 支持政治晉升激勵下CEO創新“真才實干”假說。 盧馨等[7] 發現, 政治晉升激勵會導致國有企業高管為達到政績要求而做出違規、違紀的不當行為, 并非徹底改革企業激勵機制的長久之計。 因此, 政治晉升激勵應發揮長效作用而非帶來短暫繁榮, 企業應該約束高管的政治迎合行為動機。 約束機制下高管的政治自利行為減少, 從而保障企業管理于政治晉升激勵中長期受益。
2. 高管晉升制度創新與企業績效。 高管晉升制度創新具備制度創新對企業績效的共性作用, 其與企業績效存在特殊的關聯。 基于企業價值鏈, 制度創新上經市場形勢、下經產業系統對企業管理施加影響。 羅小芳等[8] 認為, 制度性激勵體系有效轉型能提高制度適應性效率, 促使市場在資源配置與產業發展中起決定性作用。 蔡烏趕[9] 認為, 制度創新與技術創新及產業系統演進呈螺旋式協同演化趨勢, 制度創新是產業系統演進的基礎。 除了提升企業管理、資源配置與產業演進效率, 自上而下地推動企業績效發展, 高管晉升制度創新還將協同影響高管的自利與利企行為。 王震等[10] 發現, 管理制度會強化員工的創新能力與服務動機。 趙金金等[11] 從社會比較視角發現, 知識性員工會因表層相似性與權力差距產生情景妒忌與職業倦怠。 因此, 若晉升制度創新不失公平, 高管無情景妒忌導致其自利與利企動機趨于均衡, 則有助于提升企業績效; 反之, 則無益或有害于企業績效。
高管晉升制度創新有助于推動企業可持續發展, 但其對企業邊際績效的作用未能引起應有的關注, 從而高管晉升制度創新的過密化趨勢未得到相應揭示。 Duara[12] 將“過密化”概念引入國家政治領域, Huang[13] 發現了治理體系中的過密化現象, 組織管理的過密化問題不斷凸顯(主要是管理制度與流程的過密化)。 將“過密化”的內涵邏輯應用于企業創新領域, 解釋低效且重復的高創新成本內耗競爭怪象, 可以促進企業“去過密化”的可持續發展。
制度創新對于“去過密化”的普適性早已明了, 但制度創新機制尚未成熟, 高管晉升制度創新作為制度創新的有機構成內容, 其過密化現象更未引起應有的關注。 高管晉升制度也未完善, 制度創新績效有待提升。 因此, 企業未來的制度創新必須高度關注與遏制高管晉升制度創新過密化, 有效避免非理性競爭, 從而形成競爭優勢。
(二)理論分析
1. 高管晉升與企業績效。 企業成長依賴制度、技術與創新。 企業的經濟增長根源于技術變革, 制度則決定了技術變革的性質、速度與范圍[14] 。 歸根結底, 技術在這一依賴關系中充當中介, 以高管晉升為核心的管理制度是企業持續發展的主要驅動因素之一。
高管在晉升錦標賽中以工作業績爭取高薪酬、福利及權力。 依據高管薪酬分布探究高管在晉升錦標賽中的相對排序, 以職級差異為主的高管晉升體系如圖1所示。 圖1中的兩條曲線皆為右偏長尾的分布類型, 表明高管薪酬存在較大的離群值, 且多數高管的薪酬低于均值、差距較大。 最高薪酬的高管在晉升錦標賽中居于領先位置, 其薪酬分布的偏度與峰度皆高于前三名薪酬②, 最高職級的高管數目與薪酬相對有限, 在晉升錦標賽中所占比重較小。 引入職級差距后薪酬分布在向右偏移的同時更為平緩, 向正態分布靠攏, 這表明高管晉升錦標賽以高管業績的相對排序為基礎, 各職級職務共同形成的高管晉升機制反映為企業高管的競爭常態。
高管晉升制度于高管而言既是激勵也是約束。 一方面, 基于錦標賽理論, 高管晉升約束機制嚴格規范高管晉升通道, 依據高管相對業績排序的職級體系使得高管職位變動可追溯、核查與監管, 剛性約束高管晉升行為以構建理性的競爭格局、優化企業人事管理流程, 進而提高企業經營績效。 另一方面, 高管晉升激勵機制以層次分明的職級體系為基礎[15] , 以差異化薪酬與職權滿足高管的多層次需求③, 促使高管提高企業績效、參與錦標賽, 且高管晉升需求與制度供給達到均衡時, 企業內部晉升催生的激勵效應向同級或低層級員工擴散, 實現人力資源要素最優配置, 從而對企業績效產生積極作用。 因此, 高管晉升制度的激勵與約束并重, 共同削弱了高管的機會主義行為動機, 降低了企業的經營風險, 提高了企業的經營績效。
受制于高管晉升制度, 高管的晉升動機適用“激勵—保健”理論。 高管晉升制度能彌補薪酬激勵對隱性動機無效的缺陷, 形成互補激勵機制以削弱高管的不滿情緒, 為企業長遠發展削減保健因素。 然而, 公平理論下過大的職級差距會對企業績效產生不利影響。 高管會因晉升優待而提高工作積極性, 削弱不滿情緒④, 但也會因職級待遇懸殊而不滿[16] , 降低工作積極性, 從而加重道德風險, 甚至導致逆向選擇問題。 根據中心極限定理, 高管晉升體系下我國企業薪酬整體趨于正態分布, 反映了高管晉升制度下各職級待遇也呈正態分布, 企業高管職級差距總體較為合理且極端情況并不普遍, 經職級差異界定的高管待遇差別也以一致認可的制度規范的形式對外公開, 不會觸發普遍的不滿情緒而導致消極的群聚行為危及企業績效。 因此, 基于公平理論, 職級差距尚未造成不利績效的群聚現象, 高管晉升因滿足高管的隱性動機而產生顯著的激勵效應, 有助于企業績效的提升[17] 。 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1: 高管晉升與企業績效顯著正相關。
2. 高管晉升制度創新與企業績效。 高管晉升制度創新是一個揚棄的過程, 其在揚棄中不斷完善, 能有效提升企業的經營績效。 這是因為: 首先, 高管晉升機制在建設初期存在諸多問題⑤, 未能充分發揮提升企業績效的作用; 其次, 制度創新下的高管晉升機制鼓勵組織競爭從而具有顯著的激勵效應[15] 。 基于動機理論, 高管為晉升而適度競爭會促進企業人力資源的流動及配置, 過度競爭則會導致企業人力資源內耗成本高于收益。 因此, 高管晉升制度創新推崇內部競爭會導致其過密化。
“過程—目的”悖論與制度創新的過密化無異。 機構悖論認為, 組織超出職能范圍的創新資源投入無益于制度創新, 用于制度創新的資源增量將不會轉化為實際創新, 其額外支出反而會降低組織績效, 導致革命悖論[18] 。 因此, 高管晉升制度創新對企業績效的效用不升反降, 即高管晉升制度創新陷入內耗, 體現為企業管理政策過度細化與高管非理性競爭, 在管理系統的不斷自我復制下企業有增長但不發展, 有進步卻不和諧。
根據高管年薪差距趨勢圖(詳見圖2), 年薪區間與錦標賽梯隊一致: 第一梯隊高管(第一年薪區間)的競爭波動性最強, 相同職級變動下該梯隊高管薪酬的波幅遠比其余梯隊大; 中間梯隊高管的競爭明顯同質化; 底層高管競爭呈異質化, 第五梯隊高管的競爭強度比最后梯隊大, 后者高管流動性弱, 明顯處于晉升錦標賽的邊緣位置; 2019 ~ 2020年高管年薪差距整體呈下降趨勢。 這充分證明了高管晉升機制的復雜性、層次性與動態性[19] , 其以內部競爭機制為核心協調高管的職業流動, 導致高管晉升制度創新對企業績效存在兩種可能的影響: 一是若高管通過理性競爭謀求高業績, 則其與企業目標一致, 會產生利益趨同效應⑥; 二是若高管陷入非理性困境, 則會造成人力資源冗余, 危害企業績效。
以高管晉升制度對企業績效的作用趨勢判斷高管晉升制度創新是否過密化, 有助于高管晉升制度在揚棄的創新過程中實現企業績效的螺旋式上升, 從而穩固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模式: 理性競爭下高管晉升機制愈創新, 其對企業績效的提升作用愈強; 資源內耗下高管晉升機制創新程度愈高, 對內低效復制、對外浮于形式, 則其對企業績效的提升作用愈弱。 然而, 高管晉升制度創新的過密化不可避免, 可持續發展模式下的企業必須以新一輪制度創新為不可持續的管理體系提供穩定的機制[20] 。 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2: 高管晉升制度創新的過密化會導致高管晉升與企業績效的正相關關系愈來愈弱, 即高管晉升制度創新與企業邊際績效顯著負相關。
根據上述理論分析, 高管晉升制度創新與企業績效待驗證的機理關系如圖3所示。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010 ~ 2019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 并對樣本進行了如下篩選: 剔除金融類企業; 剔除ST與?ST企業; 剔除已退市和相關數據無法獲取的企業。 最終得到20588個觀測值。 從迪博數據庫中獲取內部控制質量的數據, 從國泰安數據庫(CSMAR)中獲取其他變量的數據, 并對所有連續型變量進行1%和99%分位的縮尾處理。
通過統計2010 ~ 2019年樣本企業Tobin-Q、高管晉升(高管第一名薪酬/高管薪酬總額)的均值發現: Tobin-Q在2015年達到峰值并開始由升轉降, 成為企業績效的拐點。 自2012年開始股市處于上漲區間, 至2015年股指位于高點, 而從2016年開始股市估值水平回落, 因此2015年年末企業的Tobin-Q處于最高點。 在2015年之前高管晉升無明顯變化, 而2015年后其上升趨勢明顯, 這說明高管競爭日趨激烈。 鑒于此, 本文以2015年作為高管晉升制度創新的拐點年份。
(二)變量設計與模型構建
1. 被解釋變量: 企業績效。 本文借鑒鄧美薇[21] 、楊勝剛等[22] 的做法, 從期間長短兩個維度衡量企業績效: 用Tobin-Q來衡量市場績效, 作為企業長期績效的替代變量; 用資產回報率(ROA)與凈資產收益率(ROE)來衡量會計績效⑦, 作為企業短期績效的替代變量。
2. 解釋變量: 高管晉升。 本文借鑒章琳一[23]的做法, 用高管薪酬差距衡量高管晉升錦標賽, 具體衡量指標為高管最高薪酬在所有高管薪酬中所占的比重。
3. 控制變量。 本文控制了如下變量: 企業特征變量, 包括企業性質、兩權分離率; 企業經營績效的前定變量, 包括企業規模、內部控制質量與高管性別比; 企業財務績效的后定變量, 包括企業自由現金流與財務杠桿。 上述變量皆與企業績效不存在因果關系, 因而不會產生內生性問題。 同時, 本文還控制了個體和年度虛擬變量, 以盡可能降低遺漏變量帶來的內生性問題。 變量定義如表1所示。
4. 模型構建。 首先, 以企業績效為被解釋變量、高管晉升為解釋變量, 構建如下模型:
ROAi,t=β0+β1Prmi,t+∑Controlsi,t+∑Year+∑Id+ε (1)
ROEi,t=β2+β3Prmi,t+∑Controlsi,t+∑Year+∑Id+ε (2)
Tobin-Qi,t=β4+β5Prmi,t+∑Controlsi,t+∑Year+∑Id+ε (3)
其次, 以2015年度為界分別驗證高管晉升制度創新對企業績效的作用, 模型如下:
ROAi,t/ROEi,t/Tobin-Qi,t=β6+β7Prmi,t+∑Controlsi,t+∑Year+∑Id+ε,Year≤2015 (4)
ROAi,t/ROEi,t/Tobin-Qi,t=β8+β9Prmi,t+∑Controlsi,t+∑Year+∑Id+ε,Year>2015 (5)
上述模型中, i表示上市企業, t表示年份, ε為干擾項。 模型(1) ~ (3)用以檢驗H1, 探討高管晉升制度對企業績效的實際影響, 并采用穩健性標準誤的固定效應回歸方法分析總體差異。 模型(4)、(5)分別用以檢驗2015年前、后高管晉升制度創新對企業績效的作用程度, 對比兩者的大小得出高管晉升制度創新對企業績效的影響變化及其是否存在過密化現象, 經豪斯曼檢驗(Hausman Test)拒絕原假設后, 也采用面板固定效應回歸方法分析年度組間差異。
四、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2所示。 企業短期績效ROA的均值為0.05、最小值為0.001、最大值為0.212, ROE的均值為0.087、最小值為0.001、最大值為0.376。 樣本企業短期績效的右偏分布較為明顯, 表明上市企業的短期經營狀況存在較大的盈虧差異, 整體上短期經營水平仍有待提升。 企業長期績效(Tobin-Q)的均值為2.462、最小值為0.8、最大值為17.85。 樣本企業長期績效均為正值且右偏分布十分明顯, 整體而言, 上市企業長期經營狀況較好但差距懸殊, 表明企業普遍注重長期效益, 其對短期效益的態度引致嚴重的長期績效差異。 高管晉升(Prm)的均值為0.172、最小值為0.067、最大值為0.433, 表明上市企業高管晉升制度整體上存在較大差異, 導致其高管的內部競爭狀況也極為不同。 高管性別比(Gen)與內部控制質量(ICQ)的均值分別為0.246與6.586, 兩者皆被視為企業績效的重要影響因素。
(二)相關性分析
本文對主要變量進行了Pearson相關性分析, 結果顯示(表略): 企業績效(ROA、ROE、Tobin-Q)與高管晉升(Prm)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 初步驗證了H1。 企業規模(Size)、高管性別比(Gen)、內部控制質量(ICQ)、兩權分離率(Sep)、企業自由現金流(Flow)皆與企業短期績效指標ROA在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 財務杠桿(Lev)、企業性質(Prt)則與ROA在1%的水平上顯著負相關。 各變量之間未出現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
(三)高管晉升對企業績效的總體影響
高管晉升與企業績效的全樣本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 其中, 高管晉升(Prm)的系數依次為0.026、0.035與3.356, 且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 說明高管晉升與企業績效顯著正相關, 驗證了H1。 高管晉升機制所定職級差距每增加一個標準差, ROA、ROE與Tobin-Q均有相應增加, 表明高管晉升制度有利于企業可持續發展, 高管晉升錦標賽的激勵效應顯著, 即高管內部的理性競爭愈強, 高管利益與企業目標愈趨同, 從而企業績效愈好。
由表3可知, 因高管晉升制度形成的晉升錦標賽以職級差距為基礎, 以職級對應的福利待遇為激勵手段, 合理的薪酬、福利差距符合高管的社會比較心理, 不致使其內心失衡而加重逆向選擇風險。 以制度強制性約束高管出于晉升的隱性動機, 輔以內部控制監管高管行為約束其顯性動機, 能夠使高管晉升制度對高管實現有效激勵并產生利益趨同效應, 這將對企業績效產生積極作用。 此外, 高管晉升與兩個維度的企業績效皆顯著正相關, 高管晉升制度既有助于企業短期財務績效的提升, 也有助于企業長期競爭優勢的構建。 與之相對應, 高管晉升制度創新兼為探索式創新與利用式創新[24] , 其對企業可持續發展的作用則具有累積與延續性。
(四)高管晉升制度創新過密化與企業績效
采用模型(4)、(5)對高管晉升制度創新與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進行分年度回歸, 結果如表4所示。 表4顯示2015年前后企業短期與長期績效具有如下特征: (1)企業短期績效指標(ROA、ROE)與高管晉升(Prm)之間的正相關關系皆由強轉弱, 顯著性水平從2015年前的1%驟降為2015年后的10%。 (2)企業長期績效指標(Tobin-Q)與高管晉升(Prm)由弱顯著(10%)正相關變成強顯著(1%)負相關。 再引入年度虛擬變量Year, 將2015年之后賦值為1, 2015年之前賦值為0, 用交乘項Prm×Year檢驗組間系數差異, 結果如表5所示。 表5中交乘項Prm×Year與企業績效指標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負相關, 說明后期高管晉升制度對企業績效的作用減弱。 這充分表明高管晉升制度創新導致高管晉升對企業績效的積極作用未增反減, 驗證了H2。
目前, 任何形式上的高管晉升制度創新都未深入實質。 基于企業發展愿景, 企業持續投入創新資源以創造可持續經營績效, 其高管晉升制度創新側重于企業人才激勵與管理, 意圖推動企業績效穩步上揚。 然而, 形式而非實質上的創新導致高管晉升制度陷入內耗, 究其原因在于晉升資源稀缺而人力資源冗余。 首先, 企業投入創新資源僅細化與復制格式化的規章, 而忽視了高管“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會比較心理, 不斷加大職級差距以強化激勵, 從而致使晉升資源向兩級分化, 導致高管內部非理性競爭愈演愈烈, 人力資源過剩也使內部競爭的非理性程度提高。 其次, 高管晉升制度對企業績效存在整體時滯性作用, 未達時滯期限則形式創新的實際效用尚未發揮, 來不及應對高管內部“僧多粥少”的晉升問題。 最后, 高管晉升制度創新正處于“過程—目的”悖論的節點, 創新增量與績效增速不成正比。 總之, 高管晉升制度創新方向亟需調整。
高管晉升制度創新并未對企業績效產生應有的遞進式效應, 反而削弱了高管晉升制度對企業短期績效的促進作用, 導致了其對企業長期績效的正向作用反彈, 極不利于企業的長期經營。 企業擴大高管職級差距在短期內導致利益趨同效應驟降, 此時高管與企業的利益協同程度仍超出心理失衡所造成的逆向選擇風險。 但晉升制度創新導致高管的不公平感長期積聚從而難以抑制, 而主觀制定的高管晉升機制并未考量高管的主觀態度與想法, 一味復制與細化原有制度方針, 遠達不到實質創新標準。 因此, 高管晉升制度創新應適當融入人性化管理。 進一步地, 高管晉升制度創新的過密化會導致高管非理性競爭, 有限資源下的非理性競爭反過來又會加重并泛化人才內耗, 企業必須借助新一輪制度創新構建穩定高效的運行機制以應對高管晉升制度創新過密化現象。
高管晉升制度創新對企業邊際績效的顯著負面作用可以從以下兩方面得到證據: (1)高管因晉升制度所受激勵多于不公平感時, 仍有助于提升企業績效, 這說明高管職級差距需適度, 超過其閾值時高管不公平感超出晉升動機, 則會加強對企業邊際績效的負面效應; (2)企業利益相關者視高管晉升制度創新為一個揚棄的過程, 即發揚高管晉升制度中對企業績效的積極部分并拋棄消極部分, 因而利益相關者并未具體考慮高管的社會比較心理, 而是極力推動晉升錦標賽以強化激勵效應, 導致高管晉升制度創新沒有發揮原有優勢, 反而增添劣勢。
(五)高管晉升與高管持股對企業績效的共性影響
高管晉升制度以職務、工資職級差距激勵高管, 減輕委托代理問題, 從而發揮顯著的利益趨同效應, 其與高管持股對企業績效的作用效果一致但機理不同: 高管持股在閾值內利益趨同效應也顯著, 但其以剩余收益權達成激勵, 滿足高管顯性動機; 晉升機制則以潛在的晉升錦標賽刺激高管的隱性動機。 本文以“董監高”年末持股比例之和衡量高管持股(Rat), 以Tobin-Q衡量企業績效, 采用兩者的交互項Prm×Rat來檢驗高管晉升與高管持股對企業績效的交互作用, 回歸結果如表6所示。
由表6可知, 企業績效(Tobin-Q)與高管晉升(Prm)在10%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 與高管持股(Rat)在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 這充分說明高管顯性動機強于隱性動機, 導致高管持股的激勵效應比高管晉升強, 薪酬、福利在晉升動機中所占比重比職權大, 高管晉升制度對企業績效的推動作用源于各職級的薪酬差距所產生的激勵效應。 交互項Prm×Rat的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 表明高管晉升與高管持股對企業績效的交互作用體現為顯著的替代效應, 高管晉升與高管持股機制互為替代性糾正機制, 可以彌補對方機制的缺陷。
此外, 高管晉升的偏作用為0.005, 表明高管晉升制度的激勵效應增強, 會強化高管持股的利益趨同效應。 高管持股的偏作用為-0.189, 表明高管持股機制對職級差距具有調節作用。
(六)高管晉升對不同性質企業績效的影響
根據實際控制人是否為國有將樣本劃分為國企組與非國企組, 進一步考察高管晉升制度對不同產權性質企業績效的作用差異, 所得結果如表7所示(表7中被解釋變量均采用Tobin-Q)。 由表7可知, 國企組中高管晉升(Prm)與企業績效在5%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 而非國企組中兩者呈負相關關系但不顯著。 這充分說明國有企業高管謀求晉升大多出于權力動機, 符合“高管亦官”的制度背景, 國有企業高管晉升機制僅賦予高管不等的職權便能產生激勵作用, 促使高管為提升企業業績而參與晉升錦標賽, 從而推動國有企業績效增長。 非國有企業所處制度環境與國有企業不同, 其高管受雇于利益相關者, 不具備國有企業高管的雙重身份特征, 職級晉升等同于薪酬、福利待遇升級, 政治晉升對其產生的激勵效應并不顯著。 非國有企業以非政治晉升激勵高管, 其晉升資源較國有企業更少且職級薪酬差異更為集中。
高管晉升制度未對高管性別作明確要求, 但部分企業對女性高管的性別歧視始終存在, 女性高管晉升面臨隱形天花板, 其就業成本高于男性[25] , 平均薪酬與職務也普遍低于男性[26] 。 本文以高管性別比(Gen)的均值為標準劃分出低性別比組(女性高管較少)與高性別比組(女性高管較多), 探討高管性別構成對高管晉升制度與企業績效兩者之間關系的影響。 表7中的回歸結果顯示: 低性別比組高管晉升(Prm)與企業績效在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 高性別比組高管晉升(Prm)與企業績效負相關但不顯著。 這充分表明女性高管愈多, 企業薪酬差距愈明顯, 說明企業性別歧視存在且顯著。 基于社會比較心理與薪酬激勵理論, 在低性別比組超額薪酬對男性高管產生激勵作用, 進而積極作用于企業績效; 在高性別比組男性高管的超額薪酬過度, 對企業績效產生消極作用。 因此, 減少性別歧視有助于晉升資源的合理配置, 高管晉升制度應推動晉升中的性別平等。
(七)穩健性檢驗
用ROE替換ROA以檢驗企業短期績效回歸結果的穩健性, 由表3、表4中對應結果可知, 兩者與企業績效的顯著性關系完全一致, 充分說明基于ROA的檢驗結果穩健, 企業短期績效回歸結果與本文假設一致。
用新變量T(若Tobin-Q值大于Tobin-Q均值, 則T賦值為1, 反之賦值為0)替換Tobin-Q, 對企業長期績效回歸結果進行以下穩健性檢驗: (1)更換被解釋變量后進行聚類穩健性標準誤的固定效應回歸。 (2)根據新變量T的“1-0”型數據分布, 換用更符合經濟意義的面板二值選擇模型(xtlogit)固定效應回歸方法。 (3)采用Tobit模型進行穩健性檢驗。 (4)考慮到內生性問題, 本文還進行了以下兩方面的穩健性檢驗: 一是更換解釋變量, 采用高管前三名薪酬與高管薪酬總額的比值(P)衡量整體高管職級差距進行固定效應回歸; 二是把修正后的高管職級差距指標(P)作為解釋變量(Prm)的工具變量進行二階段回歸檢驗。 穩健性檢驗結果如表8所示, 可見高管晉升與企業長期績效顯著正相關, 各穩健性檢驗結果均支持主要研究結論。
五、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文的研究結果表明: (1)當職級體系合理時, 激勵高管所導致的利益趨同效應顯著; 過大的職級差距則會導致高管對工作產生難以彌補的消極心態。 前者適用錦標賽激勵理論, 有利于企業績效的提升, 后者則更傾向于社會公平理論, 不利于企業績效的提升。 (2)以擴大各職級之間的薪酬、福利待遇差距為主的高管晉升制度創新, 不計高管自我評價對其工作績效的影響, 并未強化高管晉升與企業績效之間的正相關關系, 陷入過密化困境。 (3)企業利益相關者視高管晉升制度創新為一個揚棄的過程, 高管晉升制度創新過密化體現為高管晉升資源少且非理性競爭激烈。 進一步研究表明: 高管晉升機制與股權激勵機制能夠協同提升企業績效, 兩者互為替代; 國有企業高管的政治動機強于經濟自利動機, 其政治晉升激勵效應較非國有企業更顯著; 女性高管比例大的企業其晉升資源向男性高管超額傾斜, 會減弱晉升錦標賽對高管的激勵效應。
(二)政策建議
上述研究結論為企業創新高管晉升制度與完善內部晉升機制提供了經驗證據。 面對高管晉升制度創新的過密化問題, 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1. 優化高管晉升制度創新資源的分配機制, 以適應企業可持續發展模式。 若高管晉升資源分配不均, 過度的職級薪酬與待遇差距會背離社會公平, 導致保健因素對高管行為的影響強于激勵因素, 產生逆向選擇風險, 從而危害企業績效。 因此, 企業必須合理分配高管晉升制度創新資源, 對癥下藥, 適度縮小高管職級差距至合理區間, 充分發揮晉升資源對高管的最大激勵效用, 消弭保健因素對企業經營績效的不利影響。 具體而言: 企業應該集中晉升制度創新資源用于各職級待遇的調控, 避免晉升資源兩極分化; 合理細化高管職責確保權責到人, 更多地以承擔責任而非職權大小評定工作業績, 以業績作為晉升標準, 確定職級相對應的薪酬福利。 此外, 高管簽訂契約用業績換取薪酬、福利與權力, 實質是以物換物的商品交易, 得失等值才能維持長久的契約關系, 因而高管職級差距必要但需適度, 企業應關注高管在晉升錦標賽中的自我得失評價, 從中獲取高管對晉升機制的客觀反饋, 為形成健康積極的高管晉升機制夯實基礎。
2. 構建透明平等的晉升監督機制, 著力培育企業良性競爭文化。 即使晉升資源分配得宜也難以消減高管性別歧視, 高管內部不理性、不平等的競爭行為仍需要內外部監督機制加以約束。 企業對內應建立晉升監督機制以防止高管成員固化, 逐漸破除女性高管的“職務天花板”現象; 對外應加強高管特征、職責及晉升流程等信息披露, 倡導高管理性競爭, 發揮激勵擴大效應, 致力營造公平且透明的企業晉升文化。 政治晉升激勵在國有企業中更為顯著, 非國有企業高管的職級差距更容易導致高管晉升制度創新過密, 因此, 非國有企業應該尤為注重高管晉升的公平與透明, 建立嚴密的晉升監督體系, 發揚良性競爭, 從整體上削弱保健因素對企業績效的負面作用。 企業還應在監督過程中及時反饋高管晉升存在的問題, 根據高管業績變動預判管理的內耗并及時應對。
3. 協同高管晉升與股權激勵機制, 共同推動企業長期經營績效管理。 高管晉升與高管持股對企業績效的提升作用一致, 兩者互為替代機制。 高管持股能彌補高管晉升資源匱乏的缺陷, 因此, 推進高管持股可以緩解高管晉升制度創新的過密化困境, 在為新一輪高管晉升制度創新爭取時間的同時有助于維持企業長期經營。 高管晉升與高管持股分別滿足高管的隱性與顯性動機, 在企業激勵機制中皆必不可少, 因此, 企業在優化激勵機制時不應顧此失彼, 而應協同發展兩者并在關鍵時刻充分發揮其替代作用。
【 注 釋 】
①奮力爭先才能維持現狀,若要突破現狀必須加倍投入。企業力圖建立競爭優勢的行動只能讓其競爭狀態維持不變,并未建立真正的優勢,仍屬于理性競爭。
②最高薪酬分布的偏度為1.89,峰度為9.37;前三名薪酬分布的偏度為0.79,峰度為3.9。
③主要指馬斯洛需求模型中的生活需要與自我實現需要。
④主要指對于企業政策、管理措施、工資和福利方面的不滿情緒。
⑤如人才選拔配置單一、激勵機制不合理、高層次人才動力機制不科學以及職業發展通道不公平等。
⑥高管與企業的目標趨同,則委托代理問題減輕,企業績效會相應提高。
⑦凈資產收益率(ROE)的分析結果同時可以當作對資產回報率(ROA)的穩健性檢驗。
【 主 要 參 考 文 獻 】
[1] 余傳鵬,林春培,張振剛,葉寶升.專業化知識搜尋、管理創新與企業績效:認知評價的調節作用[ J].管理世界,2020(1):146 ~ 166+240.
[2] Haseeb M.,Hussain H. I.,Kot S.,et al.. Role of social and technological challenges in achieving a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sustainable business performance[ J]. Sustainability,2019(14):3811.
[3] Kini O.,Williams R.. Tournament incentives,firm risk,and corporate policie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2(2):350 ~ 376.
[4] 步丹璐,張晨宇,林騰.晉升預期降低了國有企業薪酬差距嗎?[ J].會計研究,2017(1):82 ~ 88+96.
[5] Lazear E. P.,Rosen S.. Rank-order tournaments as optimum labor contracts[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1(5):841 ~ 864.
[6] 周銘山,張倩倩.“面子工程”還是“真才實干”?——基于政治晉升激勵下的國有企業創新研究[ J].管理世界,2016(12):116 ~ 132.
[7] 盧馨,何雨晴,吳婷.國企高管政治晉升激勵是長久之計嗎?[ J].經濟管理,2016(7):94 ~ 106.
[8] 羅小芳,盧現祥.制度性激勵體系、適應性效率與經濟結構調整[ J].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16(4):105 ~ 112.
[9] 蔡烏趕.技術創新、制度創新和產業系統的協同演化機理及實證研究[ J].天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5):401 ~ 406.
[10] 王震,宋萌,彭堅,張雨奇.服務創新靠“領導”,還是靠“制度”?服務型領導和服務導向人力資源管理制度對員工服務創新的影響[ J].管理評論,2018(11):46 ~ 56+67.
[11] 趙金金,于水仙,王妍.社會比較視角下同事晉升對知識型員工職業倦怠影響機制研究——基于情景妒忌和面子需要的作用[ J].軟科學,2017(4):75 ~ 79+84.
[12] Duara P.. State involution:A study of local finances in north China,1911-1935[ J].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1987(1):132 ~ 161.
[13] Huang P. C. C.. Development or involu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and China? A review of Kenneth Pomeranz's "The great divergence:China,Europe,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J].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2002(2):501 ~ 538.
[14] Acemoglu D.,Robinson J. A.. Economics versus politics:Pitfalls of policy advice[ 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13(12):4 ~ 28.
[15] 張紅,周黎安,梁建章.公司內部晉升機制及其作用——來自公司人事數據的實證證據[ J].管理世界,2016(4):127 ~ 137+188.
[16] Adams J. S.,Jacobsen P. R.. Effects of wage inequities on work quality[ J]. Th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1964(1):19 ~ 25.
[17] Ridge J. W.,Aime F.,White M. A.. When much more of a difference makes a difference:Social comparison and tournaments in the CEO's top team[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5(4):618 ~ 636.
[18] Mezias S. J.,Glynn M. A.. The three faces of corporate renewal:Institution,revolution,and evolution[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3(2):77 ~ 101.
[19] Saporta I.,Farjoun 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tual promotion and turnover among professional and managerial administrative occupational groups[ J]. Work and Occupations,2003(3):255 ~ 280.
[20] Beers P. J.,Van Mierlo B.. Reflexivity and learning in system innovation processes[ J]. Sociologia Ruralis,2017(3):415 ~ 436.
[21] 鄧美薇.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企業績效的影響——來自中國非金融類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 J].工業技術經濟,2019(2):97 ~ 106.
[22] 楊勝剛,李海彤,成程.外匯風險對沖影響企業績效嗎?[ J].經濟管理,2021(4):139 ~ 154.
[23] 章琳一.高管晉升錦標賽激勵與企業社會責任:來自上市公司的證據[ J].當代財經,2019(10):130 ~ 140.
[24] 李瑞雪,彭燦,楊曉娜.雙元創新與企業可持續發展:短期財務績效與長期競爭優勢的中介作用[ J].科技進步與對策,2019(17):81 ~ 89.
[25] Powell R. M.. Elements of executive promotion[ J].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1963(2):83 ~ 90.
[26] 徐高彥,時孝穎,劉洪,陶顏.高管性別薪酬差距與企業未來經營績效[ J].江蘇社會科學,2020(2):59 ~ 69+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