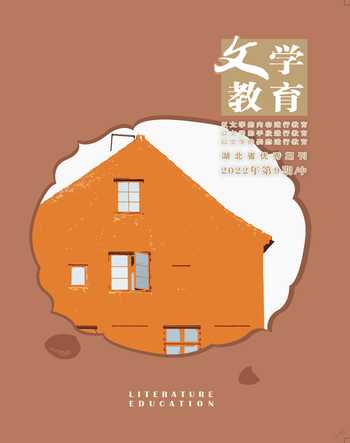華茲華斯詩歌的底層敘事美學
趙燕嬌
內容摘要:在英國浪漫主義文壇上,華茲華斯是一位對底層關照與苦難書寫注入人文關切的詩人,底層勞苦大眾的悲慘生活成為其相當一部分詩歌作品的主題表達。詩人憑借豐富的想象力,將底層人悲慘生活的真實境遇以詩意的敘事方式表達出來,為此,其底層詩歌具有了超越悲苦和困頓表象的穿透力,在詩意美學層面擁有了恒久的魅力。在華茲華斯筆下,勞苦大眾身上蘊含著最為天真的本性,普通民眾才是人們應該回歸的本真狀態,在與大自然的親密接觸中,他們的靈魂更趨于凈化,他們身上流露的美好品性和高貴人格值得歌頌和傳揚。
關鍵詞:華茲華斯 苦難書寫 底層敘事 詩意美學
威廉·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所生活的浪漫主義時代是一個充滿社會變革與革命的時代,整個英國在政治、經濟、教育和文化等領域都經歷著翻天覆地的變化。法國大革命爆發,《獨立宣言》發表,資產階級革命浪潮洶涌,民族民主運動應運而生,資本主義工商業蓬勃發展,圈地運動和工業革命逐漸改變了社會產業模式和生產結構,社會大變革與現代化進程逐漸改變了原有的生活秩序,社會階級逐漸分化,貧富落差和階級壓迫、剝削現象進一步加劇。在新的社會秩序形成過程中,居于社會最底層的勞苦大眾不斷被邊緣化,尤其,在英國爆發工業革命后,機械化生產方式進軍鄉村,隆隆的機器聲和滾滾的濃煙徹底摧毀了農村農耕文明,曾經秀色可餐的田園景象變得滿目瘡痍。與此同時,圈地運動迫使農民背井離鄉,他們不得不遠離故土,涌入城鎮,靠出賣自己廉價的勞動力維持生計,越來越多的農民工因工業發展需要失去了土地,深受貴族階級剝削和壓迫,貧富差距進一步加大。這些底層民眾身份卑微,往往食不果腹,流離失所,在物質需求與精神追求上面臨著雙重困境,面對殘酷的現實,他們忍辱負重,經濟和文化的雙重貧瘠使他們屢遭挫折、不幸甚至死亡。
面對這些顛沛流離的底層人,深受平等與博愛等啟蒙思想感染的華茲華斯極具使命感與道德感,他心存悲憫,情系草根,將勞苦大眾的困境訴諸筆端,傳遞人文關切,通過文字表達底層人的平等、正義和民主訴求,“(華茲華斯)以民主主義和人道主義的觀點,以滿腔的同情與敬意,描寫貧賤農民、牧民、雇工、破產者、流浪者直至乞丐的困苦生活、純良品德和堅忍的意志”[1]。詩人用詩意的敘事表達對底層人的悲憫和同情,創作出大量以當時社會中的平民百姓為題材的詩歌,其筆下有衣衫襤褸的拾荒者,有悲痛欲絕的母親,有妻離子散的老人,有天真爛漫的少女,有誤入歧途的少年等形象,“我們甚至可以說,他(華茲華斯)筆下的世界是一個極其黑暗的世界”[2]。詩人憑借自己豐富的想象力和藝術創作力,將英國浪漫主義時期底層勞苦大眾的生活淋漓盡致地呈現了出來,透過華茲華斯詩歌中的苦難書寫與底層敘事元素,鰥寡孤獨者的酸甜苦辣躍然紙上,透過這面濾鏡,我們得以反窺當時英國社會的全貌,感受英國工業革命繁榮背后隱藏的一系列社會頑疾。
一.華茲華斯的底層敘事
底層敘事指“以一種鮮明的民間立場,以一種平視的眼光來審視底層民眾的生存狀態,書寫他們在生存困境中的人性景觀,再現他們在那種生存困境中的生命情懷、血淚痛苦、掙扎與無奈,揭示他們生存的困境和在這種生存困境面前的精神的堅守與人格的裂變”[3]。19世紀的英國工業化進程突飛猛進,面對歷史和社會前所未有的巨大變革,位于社會最底層的勞苦大眾逐漸成為邊緣化存在,他們凄苦的生活現實成為當時社會的一種普遍現象。
作為一位極具人文主義思想的詩人,華茲華斯敏銳地捕捉到了這一工業社會高速發展帶來的普遍現象,英國底層大眾的悲苦生活成為華茲華斯相當一部分詩歌表達的主題,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抒情謠集》的最后一首敘事詩《邁克爾》。該詩以一個貧窮的老農夫的家庭生活為創作背景,主要描述了底層人在工業化進程中所遭遇的悲慘命運。牧羊人邁克爾年事雖高,但依然辛勤勞作,他“心靈手巧,干什么活計都在行”(45)①。于垂暮之年喜得貴子,給老邁克爾鼓足了生活的勇氣,被他視為生活的動力,“這個孩子給了他柔情和活力,/好比太陽的光輝,天風的音樂”(200-201)。在偏僻的高地上,老邁克爾一家三口相依為命,他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過著忙碌卻又溫暖的田園生活,邁克爾付出畢生心血,終于掙得一份屬于自己的田產,“咱們這塊地剛到我手里的時候,/租子重著呢;到我四十歲那年,/這一份產業還有一半不歸我。/我拼死拼活地苦干;靠著上帝的恩典,/三個星期以前,它全是我的啦”(374-378)。正如英格蘭的許多農民一樣,老邁克爾深愛著自己腳下的土地,一生都在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當災難降臨時,他無法面對失去土地的現實,為了渡過難關,他不得不送自己的獨子到城里去謀生路,期待著他“很快能攢下錢,補上這筆虧空”(352)。但是,事與愿違,路克沒能抵擋住光怪陸離、荒淫浪蕩的城市的誘惑,他“終于陷進了泥坑;丑事和恥辱/弄得他沒臉見人,最后他只得/逃到海外去,找一個藏身之所”(445-447)。失去了心愛的獨子的老邁克爾最終也失去了自己一直以來視為生命的土地。事實上,他選擇犧牲兒子保留土地這一行為一定程度上象征了農村經濟和鄉村文明的衰落,也折射出身居城市的人與自然的疏離和異化等社會問題,“城市成為葬送人生美好前程的罪惡淵源”[4]。老邁克爾是千萬勞苦大眾的代表,他的悲慘境遇是當時英國底層人生活狀態的真實寫照,對他們而言,即便終日辛苦勞作也難逃家破人亡的厄運。對此,華茲華斯用樸素的語言將資本主義高速發展時期勞苦大眾所遭受的沖擊和迫害真實地描述了出來,字里行間洋溢著對農民悲苦命運的深切同情,同時,對工業文明的發展秉持批判態度。
同樣,《露西·格瑞》講述了窮苦人家的小露西在暴風雪之夜斃命于荒野的悲慘故事。天真美麗的少女露西在“人世間千家萬戶的孩子中/就數她甜蜜溫柔”(7-8),但是命運并沒有善待這位天使般的孩子,她遭遇了她這個年紀本不應承受的生活壓力,一天的傍晚時分,暴風雪將至,忙于砍柴的父親差遣女兒在大雪來臨前去接在城里干活的母親,孝順懂事的露西愉快地提著燈上路,但是,“大風暴提前來到了荒原,/荒原上走著露西;/她上坡下坡,翻嶺越山,卻沒能走到城里”(29-32),柔弱無助的孩子在孤寂遼闊的荒野中迷了方向,找不到回家的路,最終,被無情的暴風雪吞沒,留下傷心欲絕的父母在荒野中失聲痛哭。導致露西悲劇的表面原因是大自然的狂暴力量,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畸形社會的統治制度,英國在經歷了圈地運動后,成千上萬的農民失去了自己賴以生存的土地,為了養家糊口,他們別無他法,不得不去城市謀得生計,充當工廠資本家的傭工,露西的母親就是這群勞苦大眾的一個典型代表,她在城市的工廠打工,每日早出晚歸,遭到了資本家的無情盤剝,最終換來的是骨肉分離的悲慘結局。“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工業的興起削弱了原本穩固的家庭紐帶,父母和孩子不得不為生計忙碌而相互離散,工業革命奪走了農家孩子”[5],露西的悲劇正是英國工業革命大背景下無數窮人孩子命運的真實再現。
邁克爾和露西的悲慘境遇是當時英國社會千千萬萬底層勞苦大眾生存困境的縮影,透過華茲華斯對底層苦難生活的詩意再現,我們得以窺探英國工業化進程中底層人生活的真實全貌。作為英國倡導浪漫主義運動的文學先鋒,華茲華斯的詩文并非只有旖旎神秘、祥和安靜的自然風光書寫,他對處于社會巨大變革之中的底層大眾悲情生活的獨到觀察與真實記錄,體現了華茲華斯作為一代文學大師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和責任心。華茲華斯將形形色色的底層勞苦大眾的悲慘生活融入筆端,以凄美詩意的表達方式記錄民間疾苦,充分彰顯了華茲華斯詩歌的時代革新精神特質。
二.底層敘事的詩意美
盡管底層人面臨著物質資源和精神生活的雙重貧瘠,生活的貧苦與艱難是他們最真實的生存狀態,也是底層文學最鮮明的表現符號,但是,華茲華斯的底層敘事詩并不簡單地等同于苦難敘事,悲情并非苦難敘事的唯一表達籌碼。華茲華斯書寫底層悲劇,但并不渲染悲情,他的文字始終是客觀冷靜的,絕不流于說教、不沉湎于悲痛。在華茲華斯看來,底層大眾是一個生命力鮮活的群體,他們身上有時代的烙印,苦難與歡愉并存,黑暗與美好同在。他從人類生活的普遍性出發,用樸素克制的語言與飽含詩意的文字使底層敘事超越了悲情的濫觴,在更高的詩意美學層面給人留下了寶貴的印象。誠然,華氏的文學思維有一種尊嚴和高尚的氣度,這主要在于他“能將人類個體的不幸提升到人間生活普遍狀態的高度”[6]華茲華斯詩意的敘事使日常生活中的渺小、瑣碎與平凡散發出高貴氣質。進一步彰顯了底層文學超越困頓表象,在藝術性與審美性層面的潛在價值。
詩歌《她住在人跡罕至的路邊》描寫了一位獨自居住在荒野的蘇格蘭民間少女。詩歌開篇便將讀者引入一片悠遠寧靜的環境之中,凸顯了少女返璞歸真、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意境,但是,隨即詩人筆鋒一轉,盡管少女像含苞待放的紫羅蘭,因為居住在人跡罕至的路邊,她的美貌與高貴氣質仿佛被禁錮在一個孤獨寂寞的世界中,得不到應有的疼愛,也得不到世人的贊美,她一生默默無聞,好似流星劃過天空一般悄無聲息地死去,“活著時誰知道她在人間,/更有誰知道她夭亡”(10-12)。華茲華斯用低吟的語調和淡淡的筆墨將少女的憂傷娓娓道來,她是萬千孤弱的底層少女中的一位,身份卑微,活著的時候無人知曉,直到生命的盡頭也無人問津。詩人則對這些底層的生命表示出無限的人文關切,他將覺醒的個性意識與超凡脫俗的情感融合在一起,流露出對生命流逝的哀婉與嘆息。
同樣,在詩歌《坎伯蘭的老乞丐》中,詩人并沒有渲染悲劇的悲情,而是通過詩歌藝術本身的魅力來凸顯底層勞苦大眾的苦難生活。該詩描寫了一位身處社會最底層的老乞丐,首先通過畫面感來暗示詩意的內涵,一位衰弱的流浪漢獨自坐在山間的臺階上,周圍是渺無人煙的荒山野嶺,與他相依為命的是一只只前來覓食的小山雀。每當小生物來討要食物,他小心翼翼地取來討來的殘糕剩餅,卻往往不受大腦的支配,雙手微微一顫,碎屑散落一地。行乞的老人雖然佝腰曲背,但并沒有做出怨天尤人之態,凸顯了人立于天地中央的莊嚴而超然的存在,展現了強大的生命力之美。他是一位按照自己的生活習慣與大自然融為一體、盡情感受自由的有限的生命的老者,雖然,老乞丐衣衫襤褸、不修邊幅,靠行乞為生,但是,他棲居在這渺無人煙的山嶺之間,對周遭的一草一木、一石一鳥充滿超越物種的博愛,這是對自然的敬畏,對生命的大愛,流露出底層人身上淳樸而崇高的人性之美。如評論家所言,該詩“在表現個人痛苦時對悲情與審美力的精準控制讓我比閱讀任何一首詩都更加感動”[7]。
華茲華斯記錄底層勞苦大眾生活的窘迫困頓,但是并不刻意大肆渲染。對華茲華斯而言,現實生活中的悲慘人物與苦難事件僅僅給予他創作的素材,他并不滿足于以枯燥乏味的歷史事實記錄手筆或淺薄單調的感傷主義創作手法來呈現當時社會的黑暗。一方面,華茲華斯用質樸的語言記錄底層生活,體會時代傷痛,表達出對底層人的憐恤與同情;另一方面,詩人又跳出傳統底層苦難敘事詩歌苦難疊加、悲情泛濫的圈囿,不乏對自我情感表達的理性克制,在底層敘事詩歌的藝術性層面達到了新的高度,彰顯了苦難書寫的詩意美學特質,取得了“形而上學的慰藉”,表現出華茲華斯在底層文學的苦難書寫和敘事策略維度高超的駕馭能力。
三.底層敘事的人性美
華茲華斯的底層敘事再現了英國工業革命轉型時期底層人的真實生活,同時,他對底層敘事的苦難書寫表現出了卓爾不群的能力,盡管詩歌的故事是悲劇性的,但是詩人跳出了悲情的束縛,擺脫了苦難情節的簡單堆砌,情感表達真摯,對底層大眾既有憐憫之心,又不失理性的克制。他以極為平靜的心態呈現底層苦難,做到了情緒的有效節制和情感的抒發、升華,對底層人微妙的心理世界的刻畫飽含詩意,他們在與身處其中的大自然相交相融的過程中,內在樸實、善良和堅強的天性與之交相輝映,達到了詩意美學的高度,傳達出詩人對底層人高貴人性的贊美,傳達出更為深刻的思想內涵,恰恰印證了華茲華斯對自己創作初衷的論述,“人心是我惟一的主題,它存在于與大自然相處的人中那些最杰出胸膛”[8]而詩人則是“捍衛人性的磐石”[9]。
在詩歌《邁克爾》中,路克最終在沒能抵擋住城市的誘惑,一連串關于他的丑事接踵而至。面對愛子的墮落,老邁克爾深感痛心,但并沒有喪失對生活的信念,依然每天辛勤耕作,體現了底層人的堅強與樸實,“他照樣上山去,/仰望太陽和云彩,聽風的呼喚;/照樣干各種活計,侍弄那群羊,/侍弄那塊地——他那份小小產業。/也時常走向那一片空曠山谷,/給他的羊群砌那座新的羊欄。”(456-461)。逆境面前,老農夫表現出強大的意志力,他始終堅信,“在愛的強大力量中有一種安慰/它能使禍事變得可以忍受”(448-449)。對待生活的苦痛,邁克爾沒有流露出哀怨和悲憤,更沒有喪失對土地和生命的熱愛之情,他在隱忍和堅韌中獨自品嘗生活的酸甜苦辣,最終在夜以繼日的操勞中死去。通過老邁克爾的一生,我們能感受到底層人的強大生命力,尤其,對底層人深處苦難中依舊表現出的慈悲、堅忍的品格表示欽佩。
與此同時,華茲華斯的《決心與自立》也同樣傳達出詩人對底層人的高貴人格和強大生命力的贊賞。該詩主要描寫了一位年老體衰卻要為維持生計四處奔波勞作的老者形象,“他已佝腰曲背,在生活旅途里/他的頭已漸漸靠近他的雙腳”(66-67)。老者依靠打撈水蛭為生,他步履維艱,動作遲緩,在疾病和苦難的現實面前,他并沒有灰心喪氣,依然憑借自己的雙手勞作,每天迎著呼嘯的狂風走過一口口池塘,跨過一片片荒野。華茲華斯對老者充滿同情和悲憫的敘述口吻頓時給人一種凄慘悲涼之感,但是,即便如此,老人的對生活的態度讓人汗顏,“(老者)無力的胸膛吐出無力的話語,/但字兒一個接一個次序井然;/話里還帶著某些高貴的東西”(93-95),面對“我”的好奇和追問,老者沒有抱怨,話語間流露出人窮志不短的堅韌,言談舉止中表現出的淡定透露出人性的堅毅和崇高,“這樣他總算用正當的辦法糊了口”(105)。作為一名勞動者,他自力更生,誠懇樸實,詩人從他身上感受到了底層人強大的生命力與意志力,盡管人生境遇艱辛,但是他依靠自己的雙手掙得口糧和生命的尊嚴。老人的遭遇是當時英國千千萬萬底層大眾生活境況的真實再現,他身上濃縮了一個時代的印記,面對工業化進程中社會變遷帶給人們的生存壓力,底層勞苦大眾內在的生存欲望并沒有減弱,同時,他們內心的堅毅與自力彰顯出偉大的人性之光,體現了強大的生命力和意志力。
華茲華斯是一位對處于英國社會轉型時期勞苦大眾的生活狀態注入人文關切的偉大詩人。一方面,他對底層人的生活處境觀察入微,用細膩的筆觸記錄他們困頓交加的生活日常;另一方面,華茲華斯站在個體生命的高度,挖掘出隱藏在底層勞苦大眾悲慘生活窘境之下的人性之美,探討作為獨一無二的生命體,如何打破外在的社會性符號建構,取得生命的尊嚴與生存的意義,實現“人回到赤身裸體的原始本真狀態之中,但是卻依然擁有凜然的尊嚴,擁有無限的價值”[10]。可以說,華茲華斯的底層敘事詩歌體現了一種超前的時代精神,延拓了苦難敘事文學的表達深度,體現了底層敘事文學深邃的人文之美。
華茲華斯生活的時代是英國乃至歐洲歷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工業化進程加快的同時也伴隨著社會的大變革,階級分化顯著,在此背景下,社會財富為少數資本家所占有,不公平的社會制度使這些底層人的生活變得異常艱辛。華茲華斯用文字批判現實,將這一時期底層群眾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痛苦凝聚在字里行間,他品味民間疾苦,觸摸底層悲痛,對時代變遷進程中底層人所遭受的無助與悲苦給予了深切關懷,可以說,“幾乎沒有哪代作家比布萊克和華茲華斯到雪萊和濟慈這些詩人更有志于投入研究和批判他們所處時代的社會”[11]。華茲華斯的詩歌是對一個時代的文學書寫,彰顯了對時代精神的引領與導向,William Hazlitt認為,“華茲華斯的天才就在于他最好地體現了時代精神”[12]。
華茲華斯的底層敘事詩歌再現了英國工業革命影響下形形色色的勞苦大眾形象,他們大都生活拮據、凄苦,但是,仍然不乏積極向上、勤勞淳樸的品格,展示出人性中最為本真的特質。詩人以客觀、平實的語調描述了現代工業社會中最底層人的生存狀態,再現了社會變革給人帶來的內心創傷,對底層人的遭遇深表同情,與此同時,又完全不失理性的克制,他用富有藝術感染力的語言將勞苦大眾的內在心理淋漓盡致地表現了出來,傳達出社會變革大背景下底層人遭遇的情感沖擊,尤其,華茲華斯的底層敘事詩歌對人物的內心世界描寫細膩、真實、真摯,雖然物質生活貧瘠,但他們人格依然崇高,令人肅然起敬。此外,詩人以大自然為背景,將人物設置在特定的自然環境中,從底層人的生命個體內部出發,探尋底層人在與自然的親密接觸中,如何突破外在物質生活的圈囿,回歸自然,回歸真實,展現生命的尊嚴,他們身上流露出的高貴人格,他們身上蘊含的純真本性才是人們應當回歸的本真狀態。
華茲華斯的底層書寫不僅關注個體的悲苦命運,更是對個體命運中隱含的高貴人性的贊美,這構成了華茲華斯底層敘事的時代精神,達到了詩意美學的高度,具有恒久的藝術價值。一定程度上,華茲華斯的底層詩歌拓寬了底層敘事的悲劇性構成元素,繼承了現代主義文學的發展傳統,傳遞出更為真切的人文關懷,他“‘在世間的(詩人)職責的行為不僅僅發生在后革命時期或他的成熟期,而是散落在生命的各個‘階段”[13],縱觀華茲華斯一生的詩歌創作,他無時無刻不置身于大自然中解讀社會現實,感悟政治冷暖,體會人性善惡,令讀者感悟到了詩人、甚至藝術家的責任意識與時代擔當。
參考文獻
[1]威廉·華茲華斯.華茲華斯詩選[M].楊德豫,譯.湖南:湖南文藝出版社,1996.
[2]Bradley,A. Oxford Lectures on Poetry [M]. New Delhi: Atlantic Publishers and Distributors,2004:124.
[3]何志鈞,單永軍. 荊棘上的生命——檢視近期小說的底層書寫[J]. 理論與寫作,2004(05): 62.
[4]涂慧琴,楊淑芬. 《邁克爾》中的地理空間與人物命運[J]. 世界文學評論,2018: 19.
[5]Purkis, J. A Preface to Wordsworth [M]. Pek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5: 49.
[6]McFarland,T. William Wordsworth: Intensity and Achievement [M].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2: 17.
[7]哈羅德·布魯姆. 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M]. 江康寧,譯. 南京:譯林出版社,2005: 19.
[8]威廉·華茲華斯. 序曲或一位詩人心靈的成長[M]. 丁宏為,譯. 北京: 中國對外翻譯出版,1999: 336.
[9]Gill,S. Ed. William Wordsworth: The Oxford Author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606.
[10]Bloom, H. The Visionary Company: A Reading of English Romantic Poetr[M]. Doubleday & Company,1963: 189.
[11]Williams,R. Culture and Society[M]. New York: Penguin Books,1984: 48.
[12]Hazlitt, W. The Spirit of the Age or Contemporary Portrait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7: 117.
[13]丁宏為.政治結構與詩意重復——《序曲》中的詩意逆流[J].國外文學,2002(4): 100.
注 釋
①引文參照參考楊德豫先生譯作《華茲華斯詩選》,湖南文藝出版社,1996。文中引文只標注頁碼。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