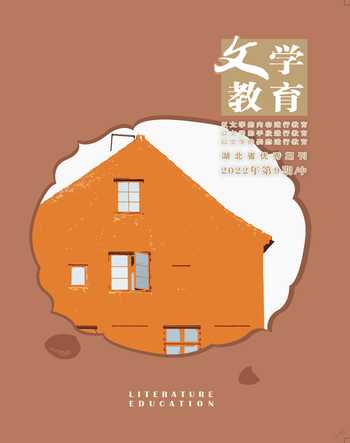蕭紅作品中的流浪意識
魏曉杰

內容摘要:流浪作為一種生存體驗可分為身體流浪和精神流浪。蕭紅作為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崛起的女作家,她的人生經歷具有明顯的“流浪”特質。空間位置上的漂泊不定加上精神世界的尋而不得,使得蕭紅在靈魂深處一直無法安定下來,流浪意識籠罩著蕭紅整個個體生命和文學生命。本文試圖以流浪意識為切入口,以文本細讀的方式探究其對蕭紅的文學創作的影響。并聯系蕭紅本人的人生歷程,追溯流浪意識在后期文學創作中所體現出作家對于故鄉的渴望。
關鍵詞:蕭紅 《呼蘭河傳》 流浪意識
蕭紅作為“東北作家群”中的一位青年女作家,其自身流浪的生活經歷使得作品呈現出鮮明的“流浪意識”,籠罩著蕭紅的個體生命和創作生涯。沉潛在蕭紅靈魂深處的流浪意識將蕭紅對生活的感受得以升華,以作家的良知感應生活的疾苦,從而形成獨特的藝術個性。本文試圖以流浪意識為切入口,探尋蕭紅作品的意義邊界。
一.流浪與流浪文學
流浪是人類的一種生存方式,中國文學自古就有著流浪的印記。無論是在精神流浪中的莊子、政治流亡中的屈原、行萬里路的司馬遷,又或是“大隱”詩人陶淵明、浪漫不羈的“詩仙”李白,還是一生飽嘗艱辛卻樂觀達然的蘇東坡,他們都經歷了流浪與孤獨、艱辛與磨難的生命歷程,并以文本書寫或思鄉、或懷土、或歸根、或隱居、或流亡、或行旅的人生體驗。
流浪和流浪文學的關聯和源頭可以從西方早期作品中找到痕跡。例如《荷馬史詩》中的英雄流浪模式,《圣經·舊約》中的宗教流浪模式,就是圍繞著“家園”的“失落——尋找——回歸——失落”這一反復的歷程而展開的,彰顯了猶太人的流浪品質。此外,莎士比亞戲劇中的精神流浪,也隱現出流浪文學的氣質。學者陳召榮在《流浪母題與西方經典文學闡釋》一書中將流浪文學劃分為內在流浪和外在流浪,外在流浪就是指物理空間上的游移,表現為與屬己的生存場相分離的流浪形式,內在流浪是指人的精神上的失落感、漂泊感、彷徨感、迷惘感、荒誕感,以及心靈上的無可歸依感,是在精神上尋找出路的迷惘,是對人存活的理由、現狀以及未來的懷疑與困惑。[1]
蕭紅作為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作家,她的一生就是流浪的一生,她以自己的流浪經歷為藍本創作出一部部作品。但是蕭紅作品在當時并不被認可,文學界普遍認為蕭紅的作品沒有表達抗日的主題,不符合主流文學的潮流。直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之后,文壇掀起了一股“蕭紅熱”,1978年鐘汝霖的《反帝愛國女作家蕭紅》打開了研究作家蕭紅的新局面,對蕭紅的研究開始進入自覺的階段;美國學者葛浩文的《蕭紅評傳》也較為公正客觀地評價了蕭紅文學的作品價值,吸引了大批國內文學研究者的眼光。他們或是以傳記的形式記錄了作家蕭紅的創作和生活,或是從抗日的角度審視蕭紅的作品,認為蕭紅在作品中對底層民眾生活狀態的描繪深刻地反映了抗戰大后方人們生活的悲慘。這也讓學界開始重新審視蕭紅的作品,并給予正當的評價。
魯迅先生在《生死場》的薦語里寫下:這是北方人民對于生的堅強,死的掙扎。用主流意識形態的觀點去解讀蕭紅的作品成了大多數人的觀點,即認為其作品反映了抗戰后方人們的生與死,以文學的形式傾訴了現實主義。但縱觀蕭紅的人生經歷可發現,她的一生都在居無定所中度過。她的作品皆是在流浪中創作,流浪是貫穿她個體人生和創作經歷的主題。在遠離故土的異鄉漂泊,是外在的身體流浪;而齲齲獨行于傳統女性解放的道路上又可解讀為精神流浪。因此,以流浪的角度來解讀蕭紅的作品,不失為一個獨特的視角。
二.底層和童年視角下的流浪書寫
“20世紀是個動蕩不安,戰亂頻發的時代,兩次世界大戰、冷戰以及冷戰以后的經濟全球化使得上個世紀的許多人被迫離開自己的祖國、自己的故鄉而流亡異地。”使得流亡和文學的關系更加凸顯,產生了流浪文學。[2]一些作家和詩人在時代的轉換中產生迷惘、失落的情緒,并將這種情緒轉化為文本呈現出來。蕭紅作為“東北作家群”的作家之一,因抗日戰爭而從家鄉逃離,流亡中國各個地方,留下了不朽的著作。蕭紅將自己抽象的流浪生存體驗以創作的方式加以呈現。文本中對底層人物生活的細致描摹不乏同情和悲憫;童年的敘述視角是對無拘束生活的向往;散文化的小說是獨立個性的綻放。
1.底層人物的流浪體驗書寫
從自身的流浪生存體驗出發,蕭紅一直默默書寫著底層人物惡劣的生存環境以及在這種環境下的生存狀態。在五四文學革命以前,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大多是描寫達官貴人,妓女強盜,這些典型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在作家的創作中形成了一種寫作趨勢,直到魯迅的作品出現后才也有所改變。堪稱民族魂的魯迅先生對文學革命所作的貢獻之一就是描寫了病態社會里的病態人生,將犀利的筆觸伸向了社會中那些不起眼的小人物,批判了“國民劣根性”,在當時的文壇中掀起層層激浪。深受魯迅影響,從底層走出的作家蕭紅,在作品中也充滿了小人物的哀歌,為小人物立轉。這一類人物平凡且卑微,生活上的貧瘠讓他們喪失了熱情,精神上的窮途末路更是使他們成為時代進步中的“邊緣人”。在《呼蘭河傳》中,有不知名的小人物,如賣豆腐的、賣豆芽菜的、賣饅頭的、賣涼粉的;也有有名有姓的人物,如有二伯、馮歪嘴子、小團圓媳婦等,他們按照自己的命運生活著,用一生來譜成一首首悲涼的曲調。假若你要是問她們活著是為了什么,他們便回答:“活著就是為了吃飯穿衣。”在那里,人的生命是沒有價值可言的,人死了,也就是親人哭一場便被人忘記了;商民之間也是相互欺騙的,只要能使得自己受益,便不惜損害他們的健康;大泥坑子給過往的行人造成極大的不便,但卻沒有一個人將它填上,因為自己做了并不能獲利;自欺欺人地吃著瘟豬肉,說實話的卻要遭打,因為實話挑戰了眾人的“信仰”。愚昧落后的思想也讓這些底層人物無法擺脫貧困的境地,如同動物般生死,存活便沒有了意義,苦難是他們一生的主題。但是作家又不止于此,在批判這些庸眾的冷漠、自私、愚昧時,發現人性的善在此時顯得彌足珍貴。小團圓媳婦用她的真實、可愛來對抗腐朽的傳統惡習,馮歪嘴子用他堅韌的毅力來續寫命運。作者的同情和悲憫讓讀者在這些人物身上窺見了希望。正是蕭紅獨特流浪生存體驗使得她對于底層人物的生活有如此細致的觀察和真切的共情,將北方人民的生與死鮮活地刻畫出來,將同情和悲憫賦予苦難的生活,體現作者的人道主義情懷。
2.兒童的敘述視角下的流浪體驗
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表示到:“因沒有機會讀到蕭紅的小說而表示遺憾”,并且盛贊蕭紅是一位“不朽的作家,幾百年都不朽”,《呼蘭河傳》是一部真的好的不得了的作品。[3]從小說藝術的角度來考察,《呼蘭河傳》體現了蕭紅自覺的文體創造意識,也詮釋了蕭紅作為一位小說家獨特的藝術質素和文體的獨特風格。《呼蘭河傳》中所采用的童年視角是蕭紅一次自覺的文體意識的成功實踐。
物理和精神的流浪中的人們往往具有一種自由而獨立的精神,他們擁有一種真誠、坦然的生活態度,拋去世俗紛繁的眼光,采用一種童真的視角觀察周圍的一切。蕭紅在作品中也多采用兒童視角來進行敘述,表達靈魂的自由和創新的文體意識。蕭紅在創作時聲稱:她不遵循小說一定要寫的像巴爾扎克或契科夫那樣,她認為小說是不拘成法的。《呼蘭河傳》中,作家并不是采用傳統的全知視角的敘述,或是簡單地采用一種視角來去敘述,而是不斷地轉換視角,使作品呈現一種獨特的章法。在第一二章,作者采用全知視角描繪了呼蘭城內的東二道街、西二道街等的景象,以及呼蘭城的民風民俗;第三章采用了兒童的敘述視角,向讀者展示了童年的人和物;第四章又轉變到成人的視角,書寫著“荒涼”;第五、六、七章又以一個孩童眼光來刻畫呼蘭河城的這些人們,寫盡小人物的悲涼,人生的無奈。
在以成人的視角的書寫中,文本是回歸現實的,甚至是更加的荒涼和悲凄。而童年的敘述視角相對于成人的視角多了一些明亮的色彩,充滿了童真趣味和溫情。童年的敘述視角,對應的是沒有邏輯的,無條理的敘述,呈現在文本上便是其散文化的、沒有理性的描繪,毫不關聯的各個章節被串聯成童年的回憶,形成一個整體,充滿著一種童真、詩意的氛圍。“花開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鳥飛了,就像鳥上天了似的。一切都活了。”在這里,動物是和人一般具有靈性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都是自由的。”[4]沒有華麗的辭藻,復雜的寫作技巧,而是簡單的詞匯表達出孩童眼中的世界。在“我”眼里,小團圓媳婦是一個正常的健康的生命,而在她的婆婆、有二伯、大廚子等一些人的眼中,她是奇怪的、不健康的,因為小團圓媳婦所呈現出來的形象不符合他們的“審美哲學”。他們心中的舊式女子的形象特點是溫馴、膽怯、低聲下氣,這種健康向上的生命形態不符合呼蘭城人們的舊式觀念。于是他們便說“小團圓媳婦不像小團圓媳婦”了。她的婆婆便對她施虐,又將自己的行為附加上神鬼的神秘色彩。這是舊時代女子在非人性禮教約束下,從被害者變成施暴者的悲劇,一代代的新生命被摧毀,而他們卻渾然不覺。文本初讀會感到是一些零零碎碎的畫面的拼湊,并不具有一部小說的完整性,沒有貫穿全書的線索,不是一個有機的整體,而之所以呈現這種特征,和蕭紅根據童年看取生活的思維方式有很大的關系。關注片段化生活場景的再現,是蕭紅對童年故鄉記憶的傳達,也是流浪意識在文本中的體現。
3.散文化書寫里的流浪意識
瓦爾特·德里曾說:小說是一種沒有自然的或確定固定存在的實體。[5]可見小說具有包容其他文體的廣泛性和包容性。在蕭紅的《生死場》的序言中,魯迅稱她的小說有一種“越軌的筆致”。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楊義先生也曾說蕭紅是30年代的文學洛神。稱蕭紅為“詩之小說”的作家。[6]初讀蕭紅的小說,第一感覺會驚訝于小說竟然可以這樣寫,沒有一以貫之的主人公、連貫的情節結構,一個個章節呈現出的是一幅幅民俗畫卷。不同于傳統的小說的寫法,蕭紅個體獨特流浪體驗使得她在小說中表現出獨特的藝術價值和審美風范,創作出散文化的小說結構。
南帆認為:“小說的結構技巧更為內在的反映作家關照世界的能力。雖然結構不過是一種再度組合,但是,它卻體現著作家的審美敏感,情感深度,人情練達和哲學水平。”在傳統文學的創作中,小說是一門講故事的文學藝術,人物、故事情節和環境是小說的三要素,但是隨著文學不斷地發展,散文的因素漸漸融入了小說。不少作家進行小說散文化的嘗試。蕭紅也是創作散文化小說的代表。
自我放逐的流浪意識對蕭紅的文學創作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蕭紅以文學的形式展現出她真誠質樸的心靈。流浪的歷程孕育著一種獨立精神和批判立場,因此蕭紅突破傳統的枷鎖,探索新形式的自由。流浪的經歷培育出蕭紅沖破傳統的個性,敢于創新,建立起自己的藝術風格。出于對創作、小說的獨到見解,以及她創作時無拘無束的率真性情和清新筆調,蕭紅的小說從結構和抒寫的側重點來看,不著重寫人物、寫故事,而著重寫印象、寫感覺。蕭紅的小說淡化了人物和情節,善于書寫主觀印象和個人感受。這一特點在《呼蘭河傳》中體現的最為明顯。在作品中,蕭紅打破了小說、散文和詩歌的壁壘,吸取了散文和詩的因素,在小說中呈現出散文和詩的因素。從自然環境到人文環境,《呼蘭河傳》呈現出了一幅有聲有色的民情風俗畫。[7]“這地方的火燒云變化極多,一會紅堂堂的,一會金洞洞的了,一會半紫半紅的,一會半灰半百合色。葡萄灰、大黃梨、紫茄子,這些顏色天空上邊都有,還有些說也說不上來的,見也未曾見過的,諸多種顏色。”這些文字組合起來就是一個個畫面的拼接,并不足以增加小說的情節或人物的功能,但會使得作品籠罩著一種詩意的氛圍,每章獨立出來都是一副絕妙的風俗畫。流浪精神中所體現的浪漫主義情懷在這里一覽無余,充滿詩意的敘述使文本更加別具一格,也體現出蕭紅創作時浪漫主義的情懷。或者說,作家蕭紅本身就是一個充滿浪漫幻想的作家,她將自己的童年以詩意的筆觸抒寫出來,讓讀者在充滿詩意的虛幻描寫中看到現實,美化了現實生活的殘酷。在閱讀小說中也可以看到作家的身影,體會到作家細膩的情感。例如“祖父的眼睛是笑盈盈的,祖父的笑,常常笑的和孩子似的”。在這里祖父是“我”幼年的玩伴,“我”作為一個孩子,與他這個大人是沒有隔閡的。在小說的字里行間可以感受“我”與祖父之間深厚的感情。在“我”專屬的后花園,仿佛這里的一切都是“我”的,別人是不能比“我”知道的多的,當我聽到二姑母家的“蘭哥”居然知道后花園里的李子樹前年就死了,“我心里立即就生出一種嫉妒感,覺得這花園是屬于我的,和屬于祖父的,其余的人不曉得才對。”蕭紅的浪漫情調在流浪中得以體現,滿足作為一個浪漫主義者心理上和美學上的需要。在創作實踐中創造了一種趨于散文化、詩化的新型小說樣式。讀蕭紅的小說,少有扣人心弦的情節,也鮮有傳統的典型人物形象,但是他們自由、清新、多彩的特點會讓人投入其中,與人物同悲共喜。
蕭紅獨特的流浪經歷是她創作的寶庫,若將她的經歷和創作聯系起來,可發現其中緊密的關聯。真切的流浪生活體驗讓她悲憫底層人物,從而深陷身體和精神的雙重貧瘠;充滿靈性的兒童敘述視角不僅是對傳統寫作手法的打破,更是對舊有規矩的一種僭越;散文化結構的小說使得她文本成為一種超時空的存在,永遠煥發持久力。
三.蕭紅小說中的意蘊呈現
流浪者在經歷了無盡的流浪和苦痛之后,會尋找一個可以置放精神和心靈的桃花源圣地。流浪的生活是艱苦、凄涼的,家園、故土也成為作家想要表達的主題。作為流浪者的蕭紅,對家園故土的想象和回憶溢滿字里行間。孤苦無望的流浪記憶,不失為蕭紅人生和創作的底色,但是她用寫作超越了自身的孤獨。苦難的人生經歷沒有讓她耽溺其中,相反,她關注到更廣大的底層人民,在小人物身上發現人性的善與美,在流浪生涯的后期表現出對家的傾情書寫。
1.呼喚人性的善與美
蕭紅在流浪的體驗中,嘗盡了各種磨難和困苦,所以她渴望尋求人性的善和美。小團圓媳婦和馮歪嘴子就是作者所塑造的善與美的形象的體現。在《呼蘭河傳》中,小團圓媳婦在眾人看來是不像小團圓媳婦的,她比普通的姑娘辮子長,她見人不知羞,她長得高,在眾人眼里她不符合傳統女子的標準。于是婆婆百般折磨她,直至“把好好的孩子捉弄死了”。可氣的是有二伯和大廚子在埋葬了小團圓媳婦后他們談論的是老胡家的酒菜怎么樣,對于小團圓媳婦的死漠不關心,這使得小團圓媳婦的悲劇就更加深刻。在同類型的人物中,小團圓媳婦形象的塑造是蕭紅在追求中國傳統女性解放道路上的前進旗幟。正是基于流浪意識的獨立自由思想,使得作者竭力為傳統壓制的女性尋求身體和精神上的解放。在眾人皆無所謂生死,失去生命意義的映襯下,馮歪嘴子形象的塑造顯得鮮活生動。馮歪嘴子住在磨坊里頭,他雖然也沒有出色的才能和先進的思想,但是他是勤奮的農民的代表,他自食其力,依靠勞動維持生存;對人真誠相待,“他有時和我祖父交談,不知祖父走了,他還在那里自說自話,我在后面偷偷地樂。”他賣黏豆糕每見我就給我一片,馮歪嘴子是作品中良善一類人的代表。他生活雖然過得拮據,但是對“王大姐”卻疼愛有加,相敬如賓。當王大姐離他而去,馮歪嘴子也沒有放棄生活,盡管還有個嗷嗷待哺的兒子,無論生活多么艱難,依然是“笑呵呵”,“他家是快樂的”,即使“在眾人看來,看馮歪嘴子的兒子,絕不會給人以時間上的觀感”,他依然會為兒子會笑、會拍手這樣的進步而笑的合不攏嘴,他身上所體現出的生命的堅韌是作者對于故鄉的期冀。在這落后封建的鄉村,這種精神是支撐人們活下去的支柱,大部分人的生活哲學就是放棄自我,過一種給別人看的生活,而從來不去思考自己想要什么,自己是否幸福。人的價值被否定,每個人的命運千篇一律,這是及其悲哀的。蕭紅于顛沛流離中看到了這種生命的悲哀,企圖以這種方式喚醒麻木的人們,去發現自我的價值,活出自己的人生。
2.詩意的棲居
正如海德格爾所言“返鄉就是返回到本源近旁,返鄉的實質乃是超出對家鄉本已生活的純然分得的占有之外對喜悅之本源的敞開”,[8]他認為“詩”是危機的拯救者。“詩意的棲居”是蕭紅應對現實生活中孤獨的良方。在流浪生涯的后期,蕭紅選擇回歸故鄉,盛贊故鄉的溫情與美好,書寫自己的故事和人生感悟,在短暫的人生中不斷地遷徙,在孤寂中尋找歸宿。
西蒙娜·波伏娃曾將女人歸結為第二性。在她的定義中:“男人不是從女人本色,而是相對于男人而言來界定女人的,女人不被看作一個自主的存在。”[9]對于女人來說,“家”是不屬于自己的,她所居住的是丈夫的家、兒子的家、父親的家,唯獨沒有屬于自己的家。這里的家是指物質和精神上的雙重歸屬地。蕭紅也是一位在現代文學中描寫女性文學的作家,她筆下的女性人物形象反映了她不同時期自覺的女性意識。在流浪生活的后期,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的塑造是她對故鄉溫情與美好的抒發。《小城三月》中翠姨比《呼蘭河傳》中的小團圓媳婦更加地具有反抗意識,翠姨她有著自己喜愛的“絨線鞋”,她有著自己的秘密,她也勇敢地去追求自己喜歡的東西,她有自己的喜好,她也愿意去遵從自己的意愿。作者在這里所傳達的是一種對傳統女子悲劇命運的態度,由冷漠轉為溫情的敘述,體現了她后期對故鄉寄予的希望。相對于小團圓媳婦來說,翠姨在女性自我的道路上邁出了第一步,雖然由于學識的缺乏使得她沒有為自己的行為找到充分的理由,但是她的意識已經體現出作家在文本中傳達的是對“人”的價值的肯定,是一種平等觀念的傳輸。作為對鄉土生活的回憶,也體現了作家對于故鄉的肯定和希冀。
從蕭紅后期的作品中對于故鄉環境的描寫中,我們也可以看出蕭紅對家鄉態度的轉變。在《呼蘭河傳》第四章中,多次以“我家的院子是荒涼的”開頭,來回憶我童年時的故居,以及我的“游樂場”,在直白的敘述中作者力圖將這故里的一草一木都描畫出來,展示了這些人生活的“寒涼”的同時,體現了作者對于故鄉的悲憫和思念。作品中寫到祖父教我讀詩,反復提到賀知章的《回鄉偶書》。這并不是一種巧合,一句“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道出了作者此時身居異鄉的凄涼和愁苦,在“祖父死了的時候”里,蕭紅寫到,祖父的死帶走了溫暖和愛,所以作者在生命的最后階段借對故鄉故人的深切懷念來表達她“魂歸故里”的愿望。這種柔軟的心理呈現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蕭紅后期心理的一種成熟,她不再像青年時期對家鄉一味地排斥和逃離,而是選擇去面對,去擁抱這個她曾經生活過的故土,無論曾經在這里她受到了怎樣的傷害,她還是愛它的,她在生命的最后,希望回到這個生她養她的故鄉,尋求生命的完滿。她的回歸是向現實的回歸,人生是一個長久的誘惑,回到屬于自己的本來的生活狀態,是任何一個人都難以拒絕的歸宿,也是對生命母體的一種報答。
古往今來,有許多書寫流浪意識的作家,屈原以《離騷》來書寫身體流浪的苦悶,魯迅的《在酒樓上》《孤獨者》書寫精神的寂寞和彷徨,蕭紅卻在默默訴說著她的流浪,她以自己獨樹一幟的文學寫作,她以自我不羈的個性,向世人彰顯她的倔強。[10]她的流浪意識需要我們從她的文本中仔細去研讀,慢慢去體會,從而去感受這位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的作家是如何在文壇中慢慢綻放,經久不衰。
參考文獻
[1]陳召榮.流浪母題與西方文學經典闡釋[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12):8、17、52.
[2]陳召榮.流浪母題與西方文學經典闡釋[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12):17.
[3]季進:《對優美作品的發現與批評,永遠是我的首要工作——夏志清先生訪談錄》[J].當代作家評論,2005(4).
[4][日]平石淑子.蕭紅傳[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10):39.
[5]華萊士·馬丁.當代敘事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
[6]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卷二[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
[7]劉婷.蕭紅文學創作中的流浪意識的研究[J].山東: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2014(6):8.
[8][德]海德格爾.荷爾德林詩的闡釋[M],孫周興譯,商務印書館,2000:24、32.
[9]波伏娃著.第二性[M].鄭克魯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9:9.
[10]陳召榮.流浪母題與西方文學經典闡釋[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12):52.
(作者單位:安徽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