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義敘事學視域下的廬隱作品研究
趙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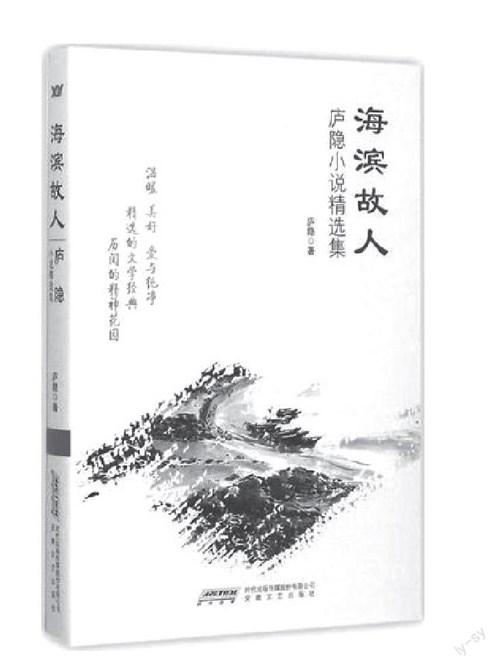
摘要:本文主要從女性主義敘事學角度出發探索廬隱作品中對女性命運的呈現方式及其透視出來的歷史社會意義,主要分為兩個部分:一是從個人敘述聲音到集體敘述聲音的轉變;二是從“交叉性”的角度剖析女性自我拯救失敗的原因。
關鍵詞:廬隱;或人的悲哀;海濱故人;敘事學;女性命運
“五四”以來,女性作家群體嶄露頭角,為中國文學提供了獨特的女性經驗和女性意識,她們曾努力改變女性“被書寫”的局面,成為言說的主體。廬隱便是“五四”一代女作家的代表人物,她與冰心、林徽因齊名并被稱為“福州三大才女”。然而與后兩人不同,廬隱是“五四”時期叛逆的“女兒”,她決絕、勇敢且富于才情,她的作品中充滿著苦澀和憂郁。由于她是父母的棄子,在艱苦的成長過程中過早地嘗盡人間辛酸,也許正是這樣,她敏感地意識到了女性所面臨的“低矮的天空”和“血色的未來”。
廬隱筆下的女性大多面臨著情感和理性的沖突。“在她的文本中,除了情智沖突的困境,幾乎沒有傳統敘事所必須的動作與行動。她的主人公的行動(相愛、結合、組織新式家庭)永遠屬于外文本敘事范疇,而在文本中她們則永恒地處在前途未卜的幽瞑地帶。”[1]
作為“五四”時代女性作家中的代表人物,同時受女性主義浪潮的影響,廬隱是現今研究“五四”女作家的重點對象,目前國內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悲劇意識、女性意識和比較研究三方面。在對于其小說的敘事性及女性主義的探討上,研究成果并不多。大部分論文都鮮少從女性主義敘事的角度分析廬隱的寫作。女性主義聲勢浩大,其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它的思想理念自然也影響到敘事學的研究。女性主義敘事學是女性主義文評和敘事學相結合的產物,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經典敘事學面臨著脫離社會歷史語境的窘境,女性主義敘事學則從敘事與性別權力的關系著手緩解了這種尷尬,并且成為后經典敘事學的一支生力軍。而在本篇論文中,筆者將從女性主義敘事學的角度切入,以《或人的悲哀》和《海濱故人》兩篇作品為例,揭示其女性主人公在那個風云激蕩的年代所面臨的困境,進而窺視“五四”時代女性的真實處境,透析廬隱的敘事所暗示的歷史社會意義。
《或人的悲哀》和《海濱故人》是廬隱在1922年和1925年分別創作的兩部作品,從體裁來看兩篇都是書信體小說。在廬隱的個人寫作中,書信體和日記體的創作隨處可見。她如此執著于這兩種體裁的創作,原因便在于:她的小說多屬于情感氛圍型小說,這兩種體裁可將抒情最大化,將自我剖析進行得十分深刻。另一方面,寫作、出版領域,長期由男性占據。在“五四”時期,民主觀念深入知識分子群體中,女性也由此獲得了寫作和出版的權利,然而男性并不愿意放棄由寫作和出版帶來的輿論高地。而書信體和日記體都明確規定了受述者,講述的往往是個人的經歷,因而具有“私語性”的特點,這種“私語性”限制了女性話語的影響力,減弱了“言論自由”動搖男權社會的能量。可以說書信體和日記體的創作模式正是“男權社會”與“民主自由”相契合的產物,這也就不難解釋為何“五四”時期第一代女作家十分熱衷于書信體和日記體的創作。
然而,在女性話語如此受限的情況下,廬隱還是盡可能地多發聲,在《或人的悲哀》和《海濱故人》中實現了從“個人聲音”到“群體聲音”的轉變。
一、 蛻變的體現:從個人敘述聲音到集體型敘述聲音
女性主義者的聲音通常指現實或虛擬的個人或群體的行為,這些人表達了以女性為中心的觀點和見解。蘭瑟用“個人聲音”(personal voice)來指代“有意講述自己的故事的敘述者”[2]20,而用“集體型敘述聲音”(communal voice)來指代“它們或者表達了一種群體的共同聲音,或者表達了各種聲音的集合”[2]22。《或人的悲哀》完全由9封書信構成,只有單一敘述人,屬于個人敘述聲音的作品;而《海濱故人》則由多個人物輪流敘述,表達女性群體的共同心聲,屬于集體型敘述聲音的作品。由此可見,敘述者由一個變為多個,由單一的聲音變為集體的共言,這無疑增加了女性言說的聲量。
在《或人的悲哀》中只有亞俠一位敘述者,她通過9封書信,前后相隔半年多的時間,不斷地向好友KY述說自己身體上的病痛、思想上的糾結和痛苦。在這些書信中她的聲音顯得“一家獨大”,其聲音所包含的情感力量也不斷地漫延至整個文本,使得讀者只能看見她的痛苦。這種結構上優越的聲音,一方面彰顯了亞俠精神世界,擴充了其情感容量,讓她成為絕對的主體;另一方面也拒斥了其他的聲音的存在,她的掙扎與痛苦得不到其他人的回應,便顯得更為絕望。同時,亞俠用字母“KY”代指好友的名字,其實是用自己的聲音虛化好友的存在,讓好友只得成為一個空洞的傾訴對象,而無任何實存的意義。KY在文本中只發出過4次聲音,其余時候都是由亞俠轉述。這種無實存傾訴對象、無回應的情況,讓亞俠只好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沉淪,獨立舔舐著傷口。
而在《海濱故人》中有5位女性主角,5人分述的形式匯成了同一支女性聲音,即對自由與愛情的天真渴望,但又囿于社會現實的苦楚。她們生活在同一緯度,有3種不同的結局:露沙“一年不通音信”;玲玉、宗瑩、連裳都結婚了,其中宗瑩婚后憔悴了不少;云青研究佛理,想要回鄉避世。這5位女性有3種不同的人生結局,但都揭示了當時的女性所面臨的社會矛盾:作為一個人時,可以追求自由、平等與民主;作為一位女性,便要受制于種種力量的轄制。這5位女性的共言形成了一種集體的力量,她們互相幫助,給對方支招,雖然最后仍然四分五裂,但是這種女性聯盟的形式仍是一種思想上的進步。
二、女性聯盟的失敗:忽視“交叉性”因素
美國女性主義法學學者金伯利·克倫肖(Kimberle Crenshaw)在研究黑人婦女問題時提出了“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概念,她認為黑人女性同時處于種族歧視與性別歧視的交叉路口。由于二者的相互強化,黑人婦女同時被白人女性主導的女性主義運動及男性主導的種族主義運動排斥在外,進而更處于弱勢地位。[3]后來“交叉性”概念被廣泛應用于各種社會性問題的分析之中,蘭瑟也將此引入女性主義敘事學的研究之中。“交叉性指主體所擁有的不同的及多重的身份認同之間互相交叉、彼此作用的性質。它強調不同的社會范疇之間以及各壓迫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4]
(一)男女各異的“交叉性”
《海濱故人》中的女性聯盟以追求婚戀自由來反抗“父親”所代表的封建禮教,正如玲玉和宗瑩。在身份認知上,她們是“子的一輩”,同男性一樣遮蔽在父權的陰影之下。她們接受啟蒙(上新式學堂),與男性站在統一戰線上共同反對家長制的權威。然而她們卻忽視了,在男性面前她們還具有女性的身份,女性在面臨封建專制的壓迫時,也面臨著男權社會的壓迫。推翻了封建專制但并不意味著也推翻了男權社會。宗瑩忤逆了父親,順利地嫁給了師旭,然而卻日漸憔悴,這正是她沒有認識到其身份的復雜性。“女性”和“子輩”雙重身份的疊加,“男權”與“父權”兩種機制的共同運作,讓她們仍然淪為命運的犧牲品。
(二)女性內部的“交叉性”
《海濱故人》確實集聚了一眾出身富庶的知識少女,但是每個人身上仍有其交叉性。正如露沙和云青。露沙從小被家庭拋棄,寄養在乳母家,在青山綠水環繞中成長。她沒有享受過父愛,并且父親早逝,在她的生命中缺乏體會父系權威的經驗,自然也就不會被這種經驗所裹挾。童年時,她沒能在完整的家庭中長大,沒有享受過父愛母慈,而是在優美的自然環境中成長,體會到了自然的靈性,容易使生命得到舒展。她也會陷入愛而不得的痛苦之中,但是她能及時認清男性的面目,看清愛情不過是“戰勝者的勝利品”,并且建立“海濱故人”之居來滿足自己烏托邦的幻想,這正是她從自己的成長歷程中獲得的啟示。然而云青不同,她從小生活在父母之家,享受父親寵愛時自然也會依賴父親的權威,她與父親之間是一種割舍不斷的關系,如果硬要在父親和情人間做出抉擇,她的內心必定痛苦而撕裂,一方是寵愛自己的父親,而另一方是深愛自己的情人,當兩者的矛盾無法調和時,她必定自我放逐,獨自承受著所有的代價。在露沙和云青身上體現出兩種不同的女性身份,一種是“棄兒”,另一種是“寵兒”,這兩者的差異則在于父親經驗是否介入,由此導致兩種不同的結果。
“事先假設有一個‘婦女的范疇在那兒,只需填入各種種族、階級、年齡、族群和性欲等成分就可以變得完整,這是錯誤的想法。”[5]21正如朱迪斯·巴特勒指出的那樣,當建立女性聯盟時,事先規定一個“婦女”的范疇是行不通的。露沙在建立“海濱故人”之居時就是預先框定了她們5位朋友,這等于是把“婦女的范疇”限定在她們5位之間,用她們來代指所有的“婦女”,然而正是身份的交叉性因素讓她的嘗試失敗了。知識分子女性與勞動女性不同,而知識女性內部也有其分化。“海濱故人”的女性一是被隔離在男性主流敘事話語之外,二是與當時廣大的無產階級女性脫離,三是她們自身內部對父系權威的經驗也不同。于是“海濱故人”的女性聯盟嘗試只能是一次女性自救的烏托邦幻想。
三、結語
波伏娃認為,“在存在主義的厭女癥分析范式里,‘主體一直就是男性的,它等同于普遍的事物,與女性‘他者有所區別;女性‘他者外在于人格的普遍規范,無望地成了‘特殊的,具化為肉身,被宣判是物質的存在。”[5]16在“五四”的浪潮里,女性被磨滅了性別特征、暫時隱藏了“他者”地位,遮蔽于男性的“主體”之下,而與男性共同進行反抗,她們雖分享了一部分的成果,但是終究沒有擺脫“肉身”和“物質的存在”,因而也不可能具有自我的超越性。
“五四”女性以反對包辦婚姻、追求自由戀愛來反抗家長制及父系權威,轉而投身于年輕一代的“子輩”,如宗瑩便是。但是不曾想,“子輩”也沒有給她們生存的空間,如宗瑩婚后便患上了病,從此身體孱弱,精神萎靡。無法反抗父輩但又不愿意屈從于父輩之人,如云青,只好繼續宥于原生家庭之中,研究佛理,以尋求精神的解脫。
從這兩篇小說中,可以看出廬隱思想的轉變和成熟,她敏銳地意識到了當時女性所面臨的困境:自我與環境的沖突、自由與束縛的對立、女性自救的困難。但是這些困境背后的原因,她卻鮮少深入分析,可能是由于她缺少如魯迅般犀利的思想與批判的筆法,也可能是因為她只想在女性內部經驗中尋求突破。不管是哪種原因,她都深深根植于女性本身,以感傷細膩的文筆書寫,讓塵封了數千年的女性內心得以敞開,為中國的文學史貢獻了獨有的女性形象。
參考文獻:
〔1〕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
〔2〕蘭瑟.虛構的權威:女性作家與敘述聲音[M].黃必康,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3〕CRENSHAW. Mapping the Margins: Intersectionality, Identity Politics, a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of Color[J].Stanford Law Review, 1991, 43(6):1241-1299.
〔4〕張也.女性主義交叉性理論及其在中國的適用性[J].國外理論動態,2018(7):83-95.
〔5〕巴特勒.性別麻煩:女性主義與身份的顛覆[M].宋素風,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