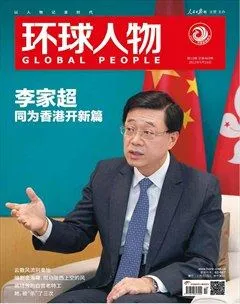一屋見(jiàn)香港
蘇濤
不同時(shí)期香港銀幕上的租客故事,標(biāo)識(shí)出曲折的現(xiàn)代化歷程,以及一段五味雜陳的文化記憶。
房屋,不僅是個(gè)人安身立命的所在,也是重要的社會(huì)空間之一。在寸土寸金的香港,從寮屋、唐樓到公屋、壋(音同蕩)房,各種形態(tài)的房屋構(gòu)成了不同時(shí)期香港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的縮影。棲身于這些房屋的租客與“包租”或業(yè)主之間的關(guān)系,是香港電影常見(jiàn)的主題。銀幕上的方寸空間,透露出香港的人情世故和世態(tài)萬(wàn)象,為我們觀察香港社會(huì)提供了一個(gè)獨(dú)特而有趣的視角。
在中國(guó)早期電影史上,以房屋和租客為主題的影片并不鮮見(jiàn)。《十字街頭》(1937)中,趙丹和白楊飾演的角色寄居同一屋檐下,卻不曾謀面;直到兩人最終走到一起,才發(fā)現(xiàn)彼此竟是一板之隔的鄰居。《烏鴉與麻雀》(1949)是中國(guó)喜劇電影的杰作,從此奠定了租客故事的主題:面對(duì)房東的欺凌,租客們由逆來(lái)順受而逐漸覺(jué)醒,聯(lián)合起來(lái)斗爭(zhēng),表達(dá)了左翼電影的社會(huì)批判。
抗戰(zhàn)結(jié)束后,英國(guó)恢復(fù)了對(duì)香港的殖民統(tǒng)治。隨著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秩序的恢復(fù),大量移民涌入香港。1945—1950年間,香港人口從60萬(wàn)激增至186萬(wàn),到1956年更達(dá)到280萬(wàn)以上。短時(shí)期涌入的大量人口,讓房屋短缺成為一個(gè)嚴(yán)重的社會(huì)問(wèn)題,很多新移民不得不棲身于簡(jiǎn)陋的寮屋,生存條件極為惡劣,發(fā)生連片火災(zāi)的新聞不時(shí)見(jiàn)諸報(bào)端。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香港出現(xiàn)了不少反映住房問(wèn)題的影片。《一板之隔》(1952)、《水火之間》(1955)等影片展現(xiàn)了小人物的求生之艱,透露出鮮明的社會(huì)關(guān)切和人文關(guān)懷。在集體主義的召喚下,同一屋檐下的房客從互不理解、齟齬不斷的陌路人,變成了相互扶持、共渡難關(guān)的朋友,在冷漠的資本主義社會(huì),獲得了繼續(xù)生活下去的勇氣。

《危樓春曉》(1953)里的租客,涵蓋了戰(zhàn)后香港社會(huì)的不同階層。
最能代表20世紀(jì)50年代香港租客故事的影片,大概是粵語(yǔ)片《危樓春曉》(1953)。制作該片的中聯(lián)電影企業(yè)有限公司,是一家由進(jìn)步粵語(yǔ)電影工作者發(fā)起組織的制片機(jī)構(gòu),奉行娛樂(lè)與教育并重的制片方針。《危樓春曉》的故事發(fā)生在一座即將被拆掉的唐樓中。租住在這里的房客,涵蓋了戰(zhàn)后香港社會(huì)的不同階層——出租車(chē)司機(jī)、教師、小販、舞女等。站在租客對(duì)立面的,則是為富不仁的大班黃及其背后的業(yè)主。
影片以知識(shí)分子羅明的視角展開(kāi)。他既是一名對(duì)勞工階層抱有同情的作家,又是唐樓業(yè)主的侄子。影片的線索之一便是羅明如何選擇自己的立場(chǎng):是站在底層大眾一邊,還是站在剝削者一邊。影片結(jié)尾,風(fēng)雨吹襲下的唐樓成為危樓,經(jīng)過(guò)一番洗禮的羅明與租客打成一片,相互扶持,在危機(jī)中迎來(lái)新生。《危樓春曉》中那句著名的臺(tái)詞——“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幾乎成了50年代粵語(yǔ)片精神的寫(xiě)照。
撫平60年代后半期的社會(huì)動(dòng)蕩之后,港英當(dāng)局采取了一系列舉措,試圖緩和社會(huì)矛盾。1971年麥理浩擔(dān)任港督后,大力推動(dòng)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大批公屋在沙田、屯門(mén)等新市鎮(zhèn)拔地而起。70年代,一部以租客為主題的影片大獲成功,不僅生動(dòng)反映了港人的文化心理,而且推動(dòng)了粵語(yǔ)片的復(fù)蘇。這部影片就是楚原導(dǎo)演的《七十二家房客》(1973)。當(dāng)同名舞臺(tái)話劇在香港上演大受歡迎時(shí),楚原敏銳地察覺(jué)到該劇與時(shí)代的微妙共振,將其搬上銀幕。

《七十二家房客》抨擊了各種社會(huì)問(wèn)題。
《七十二家房客》將背景設(shè)置為舊時(shí)代的廣州,一座殘破的院落中寄居著眾多租客,包括醫(yī)生、裁縫、小販、教師、舞女等,“包租”則是刻薄、貪婪的太子炳、八姑夫婦。為了出售地皮獲利,這對(duì)夫婦勾結(jié)警察及惡勢(shì)力,企圖驅(qū)趕租客。經(jīng)過(guò)一連串烏龍事件,這對(duì)夫婦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最終落得兩手空空。
影片以地道的粵語(yǔ)拍攝,活靈活現(xiàn)地描繪了社會(huì)眾生相,以戲謔、嘲諷的口吻抨擊各種社會(huì)問(wèn)題(治安惡化、通貨膨脹、警察貪腐),讓觀眾的情緒得到盡情發(fā)泄。坦率地說(shuō),《七十二家房客》在藝術(shù)品質(zhì)和制作上并無(wú)過(guò)人之處,其取得成功的關(guān)鍵,或許就在于以“洶涌澎湃的新感性”映射現(xiàn)實(shí),喚起觀眾對(duì)經(jīng)典粵語(yǔ)片的記憶。不過(guò),不同于50年代的《危樓春曉》,楚原在《七十二家房客》中追求的已不是社會(huì)寫(xiě)實(shí),而是社會(huì)諷刺,大量運(yùn)用的夸張、挖苦、俚俗,令該片更接近胡鬧劇,而非正劇或悲劇。盡管如此,《七十二家房客》還是出人意料地成了一部現(xiàn)象級(jí)影片,力壓李小龍的《龍爭(zhēng)虎斗》,奪得1973年香港電影票房冠軍。
30多年后,周星馳在《功夫》中對(duì)《七十二家房客》的部分場(chǎng)景進(jìn)行了戲仿。寄居在“豬籠城寨”中的各色租客,不乏深藏不露的功夫高手。憑借天馬行空的想象、“無(wú)厘頭”的風(fēng)格橋段,以及略帶乖張的人物塑造,周星馳賦予傳統(tǒng)租客故事以“后現(xiàn)代”的意味。

左:《功夫》劇照。右:《籠民》劇照。
在70年代,隨著經(jīng)濟(jì)高速發(fā)展,香港成為亞洲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qū)之一。房地產(chǎn)在香港經(jīng)濟(jì)總量中的比重不斷增加,至90年代中期,已超越制造業(yè)、金融業(yè),成為僅次于進(jìn)出口貿(mào)易的第二大行業(yè)。然而,就在香港躋身亞洲最發(fā)達(dá)經(jīng)濟(jì)體之列的同時(shí),還有一群人棲身于狹小、擁擠的公寓,他們被稱(chēng)為“籠民”。
《籠民》(1993)以強(qiáng)烈的社會(huì)關(guān)切和人文關(guān)懷,將鏡頭對(duì)準(zhǔn)香港摩登都會(huì)的另一面,為90年代的香港留下一段不無(wú)悲情、苦澀的影像記錄。影片的故事發(fā)生在一所名為“華夏男子公寓”的破舊房子,這里的租客是被香港現(xiàn)代化進(jìn)程拋在身后的弱勢(shì)群體:老無(wú)所依的長(zhǎng)者、耍猴的街頭藝人、刑滿釋放人員、吸毒者、身份卑微的外籍勞工。
導(dǎo)演張之亮以令人驚嘆的長(zhǎng)鏡頭和復(fù)雜的場(chǎng)面調(diào)度,逼真展現(xiàn)了公寓空間的逼仄和“籠民”的生活。居住環(huán)境惡劣,但“籠民”倒也能在互相幫扶中平靜度日,直到一紙收樓的律師函,打破了他們?cè)械纳钴壽E。影片對(duì)殖民時(shí)代香港的政治生態(tài)做出了委婉的批判,兩名議員聽(tīng)到“籠民”的抗議,在媒體的關(guān)注下,決定與“籠民”共度72小時(shí)。諷刺的是,他們的舉動(dòng)不過(guò)是惺惺作態(tài),一名議員只會(huì)夸夸其談,解決不了任何問(wèn)題;另一名議員則與既得利益集團(tuán)沆瀣一氣。影片結(jié)尾處,“籠民”們被強(qiáng)行驅(qū)離,他們?cè)诨\中無(wú)助的呼喊,不啻是對(duì)殖民時(shí)代香港住房問(wèn)題的控訴,令人動(dòng)容。
《籠民》獲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在于一眾演員出色的表演。喬宏、谷峰、泰迪羅賓、黃家駒、廖啟智等新老搭配的演員陣容,生動(dòng)演繹了掙扎在社會(huì)底層的小人物,不著痕跡地展現(xiàn)了人物從猶豫、動(dòng)搖、怯懦,到團(tuán)結(jié)一致反對(duì)業(yè)主收樓的心理變化。在香港的商業(yè)制片體系下,《籠民》的出現(xiàn)可謂一個(gè)異數(shù)。就是這部沒(méi)有多少噱頭,也沒(méi)有一線明星參演的冷門(mén)影片,成為第十二屆香港電影金像獎(jiǎng)的最大贏家,擊敗了《阮玲玉》《92黑玫瑰對(duì)黑玫瑰》,贏得分量最重的最佳影片,張之亮也榮膺最佳導(dǎo)演獎(jiǎng)。
90年代末期后,受到亞洲金融風(fēng)暴和非典的影響,與房地產(chǎn)高度捆綁的香港經(jīng)濟(jì)一度低迷不振。不斷攀升的房?jī)r(jià),令大量中低收入者望而卻步,就連公屋也成了可望不可即的奢侈品。在新世紀(jì)以來(lái)的很多影片中,一種新的房屋形式——壋房,開(kāi)始出現(xiàn)在銀幕上。那些無(wú)力承擔(dān)高額租金的租客,只能棲身于被層層分隔的尺寸之地,“家”或住所的概念,不過(guò)是一個(gè)床位而已。

《一念無(wú)明》海報(bào)。
在《一念無(wú)明》(2016)中,遭受躁郁癥折磨的主人公,居住在一間只容得下一張床的壋房。逼仄壓抑的空間,恰好成為主人公內(nèi)心世界的外化,透露出糾纏著香港的社會(huì)頑疾和精神痛苦。2021年的小成本影片《濁水漂流》,以一群無(wú)家可歸的邊緣人為主角,他們甚至無(wú)力承擔(dān)壋房的租金,只能在露天搭建的簡(jiǎn)易木板房中容身;即便如此,最終還是逃不過(guò)被驅(qū)離的命運(yùn)。在這個(gè)意義上說(shuō),《濁水漂流》幾乎就是一部新世紀(jì)的《籠民》。
香港銀幕上不同形態(tài)的房屋以及形形色色的房客,衍生出無(wú)數(shù)可悲、可喜、可嘆的故事,從“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集體主義,到嬉笑怒罵的社會(huì)諷喻,再到悲情而徒勞的抗?fàn)帲煌瑫r(shí)期的租客故事被打上了鮮明的時(shí)代烙印,標(biāo)識(shí)出一段曲折的現(xiàn)代化歷程,以及一段五味雜陳的文化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