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時間的夾縫里開花
仇士鵬
這兩年,我從一個忙著上課、備考的本科生變成了擁有學術研究、處理橫向項目的碩士生。最大的變化就是曾經可以肆意揮霍的業余時間從大浪里的沙變成了黃金。
沒時間寫作,這是很多非文科專業的文學愛好者總會遇見的問題。
我曾用瘋狂形容過我本科時的寫作狀態——就像是一支筆穿上我的鞋子行走在人間。
為了給老家報紙投稿,我把市里的所有景點都走了個遍,從5A級景區到不為人知的小公園,甚至是一條只有老人才能叫出它的諢名、地圖上都無法搜索到的河流,每處草坪上都有我的腳印破繭成蝶,每處殘荷旁都有我的耳朵在聽雨。采風和寫作成了大四保研后的主旋律。每天大腦都會被騰出一部分來思考,所見所聞能否以某種角度寫進文章,或是能否提煉出某種生活哲學。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周,每天都強迫自己寫上一兩篇文章,結果五天后眼睛迎風流淚,手掌彎成鼠標的弧度,僵硬難以屈伸。但心是暢快的,心靈充滿了盡情釋放后的酥麻與綿軟。
不過,這樣的隨性和縱情注定要一去不復返了。

讀研后,出差、做項目與改報告循環滾動,讓大腦變成了老式的燒水壺,壺蓋轉著圈跳個不停,生活則像是被爬山虎層層包裹的墻,看不出本身的顏色和質地。寫作,作為在導師眼中會導致不務正業的玩物喪志,不得不轉入了地下。
它從一條浩浩蕩蕩的江河變成了支離破碎的溪流,成了在泥縫間滲漏的地下水。我在等待程序運行的時候寫,在早上起床老師發來消息前寫,在把改好的項目發給老師后用余溫尚存的夜色寫,在地鐵上寫,在出差回賓館后躺在酒店的床上寫……寫作成了見縫插針的活計。但一塊巖石,也正是因為夾縫中生出了一朵嬌艷的花,才有了下自成蹊的魅力,又怎么舍得把她摘下,重歸于平凡和蒙昧。
這種夾縫里的偷閑也改變了我的寫作習慣。以前,我習慣用半天的時間去完成一篇文章從無到有、從模具到成品的創作,要么不寫,要么就把它寫完。而現在,我在空閑時,往往僅寫下只言片語,最多是一個段落,然后用多個日夜將各個段落完成,刪減、增補、潤色后,再串在一起。這樣的文章必然是少了“第一時間”所帶來的鮮活與絕對純粹、真摯的抒情——拉長了戰線會讓人瞻前顧后,對當時的情緒和觀點產生懷疑和猶豫,但也因此,讓文章有了辯證、成熟和圓融的機會。穿越時間的回眸,往往能在一顆心臟之外看見更遼闊的山川。
不過,這種碎片化的寫作肯定不是我本來所期望的。所以剛升入研二時,我時不時就會陷入煩惱與憤懣中。
譬如,當我捕捉到一個罕見的、巧妙的、別出心裁的靈感,并且文章的框架和脈絡都水到渠成地在腦海里浮現,讓我忍不住想大刀闊斧、揮毫潑墨的時候,老師就會發來項目,并且馬上打來電話,強調道:“非常急,無論如何今晚都要發給我!”
等項目做完,已經是夜晚十一點,回宿舍的山路要打開手機的手電筒才能穿行,并且能見度不超過一米,回去就要睡覺了。到了第二天,昨日的靈感已經成了黃花,再也想不起來了,即使昨日曾記下些許內容,但是竟然想不出合理的邏輯把它們銜接在一起,忘記的部分讓它像粗制濫造的木偶,不再活靈活現。郁悶是一場大霧,在道路兩邊彌漫,吞噬了樹林與湖泊,連橘紅色的霞光都無法穿透。
但生活本就是無奈的,生活在其中的人只能選擇和它妥協,無論用怎樣的方式,都要和它達成和解。以某種協議停戰、握手言和,這是唯一的結果。
我開始學會體驗遺憾,撫摸夾縫,沉浸在它帶來的糾結、迷茫與痛苦中,感受著它們如何在細小的血管與神經里奔流,如何把血管撐得鼓鼓囊囊,并且在心里源源不絕的牢騷中找出我舍不得放下與堅守寫作的根源。
我想,我是要感謝夾縫的。相比于草地上的種子,生活在夾縫里的種子更能知道自己會迸發出怎樣的熱愛與沖勁,會怎樣執著地向往、虔誠地祈禱并最終竭盡全力地投入春天。正是一步步地發現、意識到了這種心靈的傾向,我們才能讓生活更加靠近命運在最開始就暗中設置好的傾向。我也漸漸明白,文學可以是一種職業,也可以不是,它更是一種生存方式和生活狀態。如果說文學曾作為一道光,照亮了我陷在陰郁中的瞳孔,那么現在,我自己就是光源,一個發光體。正是處在夾縫里,我才得以一次次地重新觀照文學的初心,并思考在當下人生的階段,我該如何處理文學與生活的矛盾與統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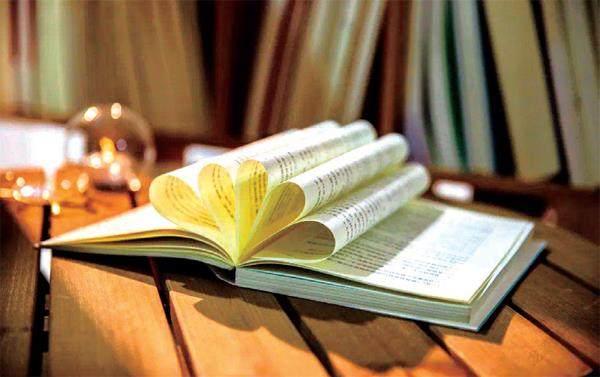
我終于明白,生活的一切和一切的生活都可以成為文學的土壤。它未必需要古色古香的書桌、安靜的窗子和完整的時間,限制了寫作時間的夾縫也可以成為寫作的內容。即便是常被批判的物欲、匆忙和浮躁同樣可以成為文學的誕生地,只不過是用反省的目光去觀照而已。
這株生長在夾縫里的小樹,漸漸地把根須伸向了夾縫之外,扎在了生活的全部。原來夾縫雖然是一種限制,但也是一種成全,一種只有依靠夾縫才能產生的指引與庇佑。
我想,在某種意義上,文學就是自己感動自己,哪怕在旁人眼中你的行為莫名其妙、奇奇怪怪,甚至是矯情、無病呻吟,但只要對自己而言,那一刻的感動是真實的,那么文學就是受孕的,是一顆充滿活力的種子,能在夾縫里開出水靈靈的花朵,讓平庸的、丑陋的裸巖都成為美的代言人。
(編輯·李澤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