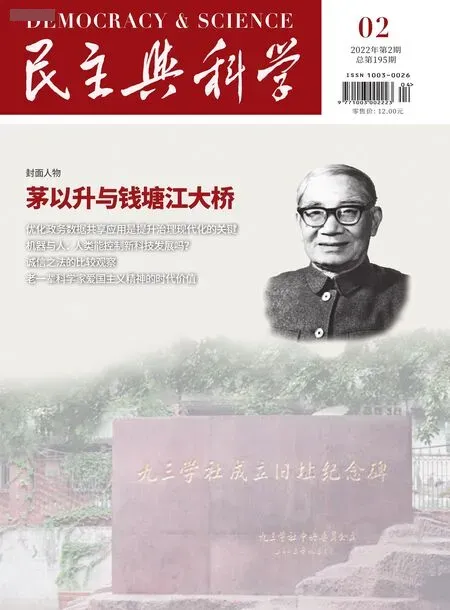最偉大的是思想,最恒久的是文化
人生總該有人行,不枉世間走一程。
是非正誤泰山重,禍福得失鴻毛輕。
國是學理心中事,雞毛蒜皮耳邊風。
可譴舐痔與鄉愿,污染空氣遺膻腥。
——李醒民:人行
還是模仿一位偉人的句式作為“作者后記”起首語吧:余致力于批判學派研究凡四十余年,其目的在求學術之創獲和思想之創見。這一研究是從改革開放的1978年起步的:是年我從渭北高原的富平縣廣播站考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研究生院(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和中國科學院大學的前身),從一名電工工人和無線電技術員轉變為學術界的一分子。1981年,我下了足夠的功夫,完成碩士論文《彭加勒與物理學危機》(17年后才姍姍來遲得以發表)[1]。該文運用翔實的歷史資料,梳理和厘清了科學史和思想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物理學危機與革命,有理有據地駁斥了長期流傳的、居統治地位的傳統觀點。此時,十年浩劫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結束不久,思想啟蒙和思想解放運動剛剛展開,社會上的極“左”思潮和保守勢力還相當頑固地固守一隅之地,不少人還沒有完全擺脫迷信的羈絆,缺乏與時俱進的意識。在這種歷史氛圍中,我的具有超前意識和某種敏感性的論文遲遲難以面世,就是不言而喻或可想而知的事了。因此,我不得不做一些避諱和修飾,才發表了處女作論文和著作——“世紀之交物理學革命中的兩個學派”(1981年)和《激動人心的年代——世紀之交物理學革命的歷史考察和哲學探討》(1983年)。在1980年代,我從已有的起點繼續行進,圍繞作為一個整體的批判學派及其代表人物馬赫、彭加勒、迪昂、奧斯特瓦爾德、皮爾遜深入研究,陸續發表了諸多論文。在1990年代,又先后出版了《理性的沉思——論彭加勒的科學思想與哲學思想》(完成于1986年)《理性的光華——哲人科學家奧斯特瓦爾德》《彭加勒》《馬赫》《偉大心智的漫游——哲人科學家馬赫》《迪昂》《皮爾遜》等著作。進入21世紀,我對批判學派的研究仍在斷斷續續地進行著,多篇研究論文相繼見諸學術雜志。可以說,在學術生涯的前二十年,我花費大半時間和精力集中研究批判學派,而后二十余年則是拾遺補闕、拓展深化。
由于有早先研究批判學派的基礎,最近幾年我集中時間和精力又研讀了民國時期的科學論資料,這樣就有了兩相對照、明辨是非的可能,從而比較順利地完成這本書稿。要是沒有此前數十年關于批判學派的研究,我縱使有無與倫比的神奇想象力,也絕對不會想到確立這個“工程項目”,就更不用提建造這個“空中樓閣”了。從這個現實狀況講,我想即使再過二十年,恐怕也無人能寫出類似的書稿,因為單單對批判學派及其代表人物思想的理解和把握,沒有二十年的鉆研和體悟是不可能做到的。恕我直言,這是一本填補世界學術空白之作,是前不見往者、二十年后也不會見來者的。有人也許認為,你這是口出狂言,不知天高地厚。此語差矣!待我娓娓道來。作為四十余年潛心研究、筆耕不輟的學人,我向來秉實干為正途,視謙遜為美德,始終反對上躥下跳、大轟大嗡,尤其是與媒體沆瀣一氣,把牛皮吹得比天還大,把膿瘡捧得艷若桃花。不過,我也堅信,實話實說不是驕傲狂妄,實至名歸應該理所當然。在這種意義上,我的上述表白和估價只是講出一個真實的事實,并不是信口開河、妄下雌黃。這里有白紙黑字在,是可以經受時間的大浪淘沙和歷史的無情檢驗的——自吹自擂遲早成為笑柄,目空一切難免露出馬腳。我覺得,一個長期默默耕耘且有獨立人格和自由個性的人,有時狂狷一下也沒有什么大不了的,甚至是充分而必要的。在這里,不妨順手拈來兩首舊作“人生”“讀《中國文化的狂者精神》其一”,為向來“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我壯一下膽,助一點威——就算是“老夫聊發少年狂”吧:
人生能有幾回狂,降龍伏虎射天狼?
凌霄猛志囊四海,荼火氣勢吞八荒。
胸藏珠璣任揮灑,筆走龍蛇自成章。
風卷殘云碧空凈,更現天心慨而慷。
神州自古多狂狷,而今熙熙皆鄉愿。
我勸天公重競擇,去曲存直明貴賤。
四十多年來,除了批判學派外,我還緊盯其他十余個課題專門予以研究。[2]讀者只要從我改造(舊瓶裝新酒)或自造(新瓶裝新酒)的相關名詞或術語——批判學派、哲人科學家、兩極張力論、多元張力論、人文的科學主義、科學精神的規范結構、經驗約定論、秩序實在論、綜合實在論、基礎約定論、綱領實在論、理論整體論、意義整體論、宇宙宗教思維方式、宇宙宗教方法、科學論、科學內論、科學外論、科學元論、科學通論、科學個論、臻美方法或審美方法、科學編史學的“四維空時”、民國學術左派和純學術派,以及細枝末節的井蛙主義、夜郎主義、六不主義、三不政策、“四項基本原則”、四唯主義或七唯主義等,即可嘗鼎一臠,窺豹一斑。
多年前在翻閱蘇聯一位學者古留加寫的《康德傳》時,有句話不禁使我眼睛一亮:“哲學家一生的標志就是他的那些著作,而哲學家生活中那些激動人心的事件就是他的思想。”[3]其實,在此之前,作為一個為學術而學術、為思想而思想的學術界中人,我就自始至終把執經問難、染翰操觚、思想創新作為自己的高潔而神圣的使命,而把與此無關的其他一切——包括眾人趨之若鶩、蜂擁爭搶的課題、評獎以及出風頭、露臉、應景、湊熱鬧之類的躁動或妄動一一撇在腦后,心無旁騖、一心一意地做自己感興趣的事情。有舍方可得,有棄才能獲,22部著作、20本譯著、600余篇論文和文章,就是對我最好的報償,也是對我的心靈的最大慰藉。這樣一來,自然而然地,實惠的紅利從身邊悄然溜走,耀眼的冠冕從頭上蕩然滑落。說實在的,實利和虛名并不是我孜孜以求的,甚至被我視之為敝屣一雙。這里有我們“酒中仙”“觀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為證:
鐘鼓饌玉可有無,浮名虛譽任去留。
唯愿酩酊醉曉月,羽化登仙最自由。
人格獨立同天壤,思想自由永三光。
虛名實利若敝屣,丈夫立世腰自剛。
在漫長的學術研究生涯中,我與馮友蘭先生的下述看法能夠強烈共鳴:“學問這東西也很怪,你越是有所為而求它,大概是不能得到它。你若是無所為而求它,它倒是自己來了。作為業余的學術愛好者,為學術而學術尚且可以得到成績,有所貢獻。如果有人能夠把為學術而學術作為本業,那他的成績必定更好,貢獻必定更大。”[4]不難看出,這段話與清代袁枚的詩句“我不覓詩詩覓我,始知天籟本天然”[5]是一脈相承的,說的是一個道理。的的確確,為學術而學術,為思想而思想,實在是學術繁榮、思想勃發之道。而且,學術是有生命的,學術就是我的生命。我的生命與學術的生命已經融為一體:我擁有生命,就順理成章地研究學術;我失去生命,學術研究也就隨之戛然而止;如果我不再從事學術研究,那么生物學意義上的生命對我來說沒有一點現實意義——只不過是丟掉靈魂的行尸走肉而已!在生前,我的著作就是我的肉體,我的思想就是我的精神;在死后,我的著作就是我的幻軀,我的思想就是我的靈魂。
托勒密在《至大論》中說得好:“我知道,我本凡夫俗子,朝生而暮死。但是,當我隨心所欲地追蹤眾天體在軌道上的往復運動時,我感到自己的雙腳不再踏在地球上,而是直接站在天神宙斯面前,盡情享用著諸神的珍饈。”[6]同樣地,在學術研究的過程中,不僅使我的生命能量和激情得以盡情釋放,而且我也從中享受到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樂趣和幸福——這就使我更加熱戀和癡心學術研究了。我對學術研究的志趣和情愫,可由“寫在世界讀書日前夕”“古稀自述”“泛舟學海”三詩略見一斑:
手捧典藏細品茶,侵山抱月堂生華。
逢智增識經綸滿,見賢思齊格調佳。
創文造化思飛揚,潔身濟世氣風發。
動問人間何最美,唯有讀寫樂無涯。
獨寐寤言士林間,永矢弗告意拳拳。
心有幽趣慕嚴斶,身無蓄謀效馮諼。
磊落使才聳天地,慷慨任氣睥權錢。
騰蛟起鳳尋常事,古稀雖逾夢蹁躚。
泛舟學海卌余年,魂牽夢縈思聯翩。
致力廣大目光炯,盡心精微功夫全。
登高行遠自卑邇,磨金鏤石在恒堅。
駿發踔厲永不怠,弄斧方敢班門前。
由于長期與文字打交道,我對中國文字也逐漸生發了一種敬畏和愛戀之情。這里暫且不說倉頡創造的象形文字外形之美妙和內涵之豐盈,而由這些方塊字組成的文辭和詩文,簡直美不勝收,令人拍案叫絕、擊節稱賞。請讀一讀唐詩宋詞或《古文觀止》中的那些美文吧!那豐贍的內容,深邃的思想,優美的意境,對稱的結構,典雅的詞語,和諧的音韻,直使你陶醉于其中,仿佛挾飛仙以遨游,竟至不知今夕何夕。正是出于對中國文字的敬畏和愛戀,我自己從來不敢率爾操觚,而是含毫邈然,三思而后才敢筆走龍蛇。即便如此,幾部漢語詞典一直放在案頭,以備不時繩墨之需。也正是出于對中國文字的敬畏和愛戀,我對那些輕易褻瀆、肆意糟蹋中國文字的行為——比如隨意生造、廣為散播的“粉絲”“小鮮肉”“飯圈”“娘炮”“大V”“大咖”“小確幸”之類——總是本能地反感,且耿耿于懷。我倒不是對麗典華藻的文辭情有獨鐘,那些出自民間、富有生活氣息的俚語土話也惟妙惟肖、別有風味。作為關中人,我樂于向讀者推薦電視劇《關中紀事》的歌詞作為例證:“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頭。金疙瘩銀疙瘩還嫌不夠,天在上地在下你娃甭牛。”這是多么生動、多么鮮活的文字表達呀,更不必說其中的哲學意蘊和人生智慧,足夠你品嘗和回味一陣子了。
世界上最偉大的東西是什么?是思想!因為唯有思想才能夠囊括整個宇宙。世界上最恒久的東西是什么?是文化!因為唯有文化才能標志人類進步。思想迸發和文化創造雖然是個人的產物,但是只有在一定的社會環境或社會條件下才能產生。記得布羅諾烏斯基在《科學與人的價值》中說過:追求真理的人必須是獨立的,尊重真理的社會必須維護他的獨立性;理性的時代總是渴望超出常情的東西——獨立的思想總是超出常情的——但是它必定更渴望保證它們不受打擊;科學的社會必須把高度的價值建立在思想獨立的基礎上。[7]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我向來認為,沒有獨立人格和自主意識的人,是不會有自由的心靈和創新的思維的,無論如何也不可能為人類的精神寶庫增添一粟,為人類的文化發展助一臂之力。不保護和促進人的獨立性和自主性的社會,是一個缺乏創造力的、沒有前途的社會——這是歷史已經反復證明的、顛撲不破的鐵律。因此,每一個社會領導者,每一個社會守望者,每一個社會參與者,都應該深思、再深思這個鐵律,從而將保護和促進人格獨立和思想自由的理念嵌入意識和無意識,并進而付諸行動和實踐。
不管怎么說,人歸根結底是一種精神性的動物——這也許是人與一般動物最大的區別。既然如此,人就應該以精神追求作為主要目標和終極目標,特別是在生產力相當發達、物質生活日漸豐足和充裕的社會里更應如此。在這種與境下,無休止地追逐和攫取實利,對物質享受貪得無厭,像明季朱載堉的《十不足》散曲所描繪的貪婪者[8]那樣貪得無厭、永不饜足,實在不足為訓。即使在精神追求方面,也要保持清醒的頭腦,有所選擇和取舍,這樣才能真正汲取有價值的東西,不致使自己的思想世界變成冗余信息和駁雜傳媒的跑馬場。索爾仁尼琴有句名言講的正是這個意思:“除了知情權外,人也應該擁有不知情權。后者的價值要大得多。它意味著高尚的靈魂不必被那些廢話和空談充斥。過度的信息對于對一個過著充實生活的人來說,是一種不必要的負擔。”[9]
拋棄過度的物質追求的負擔,清理無謂的精神錯亂的牽累,人才能夠有閑暇的時間,才能夠有閑雅的情趣,才能夠有閑適的心地,才能夠真正擁抱閑情逸致,才能夠閑云野鶴般詩意地棲居,才能夠從天地萬物、世事變幻中獲取思維的雅興、審美的妙趣、精神的愉悅、心靈的凈化。請看北宋理學家程顥是怎么寫的:“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云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10]請聽清代文學家張潮是怎么說的:“人莫樂于閑,非無所事事之謂也。閑則能讀書,閑則能游名山,閑則能交益友,閑則能飲酒,閑則能著書。天下之樂,孰大于是?”[11]在退休之前,我就有如此這般的閑心;在退休之后,我的閑趣更上層樓。當時曾有“午睡”“坐書房南窗前觀藍天浮云”記敘其勝,現不妨將兩首小詩附麗于下,權當余興可遣、余勇可賈吧:
午睡不覺日西斜,隨興臥起細品茶。
待到神清目明時,漫游書海覽英華。
白云蒼狗幻復翻,人事滄桑更無端。
心中自有一桿秤,穩坐釣臺覽風帆。
注 釋:
[1]李醒民:《彭加勒與物理學危機》,楊玉圣主編:“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博士碩士文庫”(哲學卷(中)),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1247-1285頁。
[2]李醒民:《李醒民教授的學術研究和學術思想》,李醒民:《激動人心的年代——世紀之交物理學革命的歷史考察和哲學探討》,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當代中國人文大系·哲學)2009年第1版,第174-186頁。李醒民:《卌載筆耕不知止,桃李成蹊慰初心——我的學術研究的歷史軌跡和思想創新》,《社會科學論壇》,2020年第3期,第182-201頁。
[3]https://www.doc88.com/p-747862
7524846.html。
[4]馮友蘭:《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第1版,第363頁。
[5]袁枚:《老來》。
[6]https://book.douban.com/review/
12260911/。
[7]J.Bronowski,Science and Human
Values,London: Hutchinson,1961, p. 60.
[8]明代朱載堉的《十不足》散曲是:“終日奔忙只為饑,才得有食又思衣。置下綾羅身上穿,抬頭又嫌房屋低。蓋下高樓并大廈,床前缺少美貌妻。嬌妻美妾都娶下,又慮門前無馬騎。將錢買下高頭馬,馬前馬后少跟隨。家人招下數十個,有錢沒勢被人欺。一銓銓到知縣位,又說官小勢位卑。一攀攀到閣老位,每日思量要登基。一日南面坐天下,又想神仙來下棋。洞賓與他把棋下,又問哪是上天梯。上天梯子未做下,閻王發牌鬼來催。若非此人大限到,上到天梯還嫌低。”
[9]http://www.kejudati.com/jushow/
600956167d315.html。
[10]程顥:《秋日》。
[11]張潮:《幽夢影》。
(作者為中國科學院《自然辯證法通訊》雜志社教授)
責任編輯:尚國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