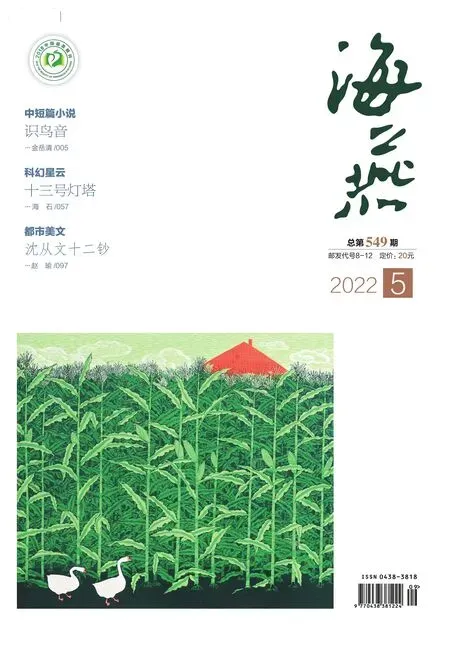蘇北平原的槐香
文 張 巖

立夏
立夏一到,祖母就在她的菜園里忙碌起來。
菜園在村子南邊。菜園和村子之間隔著一處汪塘,汪塘是偌大的橢圓形,橫在村子前頭,立夏時(shí)節(jié),汪塘里的水輕輕蕩漾,泛著綠意。早起的村人,有的牽著牛到汪塘邊飲水;有的挎著籃子,踩著青石板,到水邊淘洗蔬菜;有的就是端著大盆,來到水邊漿洗衣服。衣服一件件浸在水里,用手搖啊搖的,水里泛著衣服的顏色,也泛著洗衣人的影子。也有在石板上搗衣的,木槌捶打在衣服上,發(fā)出“梆梆”的聲音,都能傳到汪塘對(duì)岸去。
在這“梆梆”聲里,祖母通常會(huì)挎著一個(gè)小籃子,拿著一把剜菜的刀,沿著汪塘邊的小路,到自家的菜園里去。
那時(shí),我們那個(gè)村莊,家家都有一個(gè)菜園,大都在村南,菜園挨著菜園,菜園里點(diǎn)瓜點(diǎn)豆,種著各種蔬菜。人們?cè)缙饹]啥事干,就會(huì)到菜園里侍弄侍弄那些綠色小菜,迎著面都會(huì)親熱地打個(gè)招呼,“大娘二娘”“三奶五奶”的,親熱得像一家人似的,然后便各在各的菜園里,彎下腰來,各做各的活兒。
我家的菜園,祖母也侍弄得好。里面種了蔥種了蒜,種了茴香還種了芫荽,胡蘿卜和蘿卜也是有的。各有各的好。家里炒菜時(shí),祖母便到菜園里,挖一些蔥和蒜回去,若是燒魚,那茴香和芫荽又是不能少的。這時(shí)祖母就會(huì)輕輕地掐一點(diǎn)茴香和芫荽的嫩心兒,在水邊洗洗,帶回家去。胡蘿卜和蘿卜在立夏前都吃得差不多了,現(xiàn)在只留少許做種。待到過些天,天真的熱起來,它們就開花了。胡蘿卜的花兒細(xì)密,凝結(jié)為一團(tuán),像一把把小小的傘;蘿卜的花兒白生生的,細(xì)碎又清脆地掛著。若有蝴蝶光臨,祖母是最愛看了。
其實(shí)讓祖母操心的還是她自己點(diǎn)種的那些南瓜。
立夏了,南瓜秧子長得飛快,一天不見就是一個(gè)樣子,蓬蓬勃勃的,就像變了聲帶、聲音發(fā)粗的高中生似的。祖母幾乎是每天早上都要帶著刀來修理它們。不修理它們,它們只會(huì)瘋長,并不結(jié)瓜,枉費(fèi)了青春。祖母為它們提秧,分杈,刪繁就簡,去掉多余的分枝,剪掉繁密的杈頭,掐掉過多的謊花,好攢更多的養(yǎng)分,專供開花結(jié)果。
剪下來的那些杈頭,掐下來的那些南瓜花,祖母并不扔掉。那其實(shí)是一盤好菜,祖母知道怎么調(diào)理它們。南瓜頭子和南瓜須子,剝掉表皮,可以切成段兒,配上小蒜,炒著吃,那味道里有鮮濕的泥土氣息,有酣暢淋漓的暮春氣息,是不錯(cuò)的。在我家還有另一種吃法,就是在支起鏊子烙煎餅的時(shí)候,做菜煎餅。母親燒著草,坐在鏊子前烙煎餅,祖母就把南瓜頭和南瓜須剁得稀碎,拌上一些作料,澆上一點(diǎn)蒜泥,做成菜餡。然后將這些噴香的菜餡夾放在兩張煎餅里,在鏊子上慢慢地煎,直到餅面焦黃,菜餡的香味恣意四溢,果真是好吃極了。
南瓜花更是不必說,拌上面粉,油煎,做成外焦里嫩的南瓜花餅,更是一道美味。
祖母說這叫嘗鮮。立夏了啊,要吃點(diǎn)新鮮的。農(nóng)家也沒有什么好吃的,吃一點(diǎn)南瓜花,也許,你就會(huì)和泥土又靠近一點(diǎn)吧。
祖母說這些話的時(shí)候,總會(huì)說到從前。從前的日子不好過,不像現(xiàn)在,菜園里那么多菜,南瓜花都可以做成香油餅吃了。很是慚愧,到現(xiàn)在我都不知道我祖母的名字。只記得小時(shí)候,生產(chǎn)隊(duì)需要寫我祖母的名字的時(shí)候,總是在我家姓氏的后面注上“王氏”,想來我祖母一定是姓“王”了。至于我祖母別的情況,我知道的便很少了。我倒是在祖母洗腳的時(shí)候看過她的腳。她的腳和村里其他幾個(gè)年齡相仿的老太太的腳差不多,有點(diǎn)像粽子。祖母的腳有幾根腳趾關(guān)節(jié)是斷了的,所以那幾根腳趾便枯萎了下去,跟著祖母枯萎了一輩子。祖母說過她小時(shí)候是裹過腳的,因?yàn)閷?shí)在太疼,就不裹了。后來,祖母經(jīng)人介紹就來到我的家,嫁給了我祖父;再后來,就做了我的祖母。
祖母會(huì)做南瓜花餅,她還會(huì)做槐花餅。春末夏初的時(shí)候,槐花開得旺,掛在槐樹的周身,一嘟嚕一嘟嚕的,一片片白色,老遠(yuǎn)就可以聞到槐花的香氣。祖母好像就喜歡這些土氣的花,她舉著竹竿敲打它們,那些槐花就從樹上落了下來。
槐花的味道確實(shí)清香。拌一點(diǎn)面粉蒸菜,蘸著陳醋和麻油吃,很是爽口爽胃。但是祖母的槐花多是用來做餅子。做餅子比較麻煩,祖母好像樂于給自己找麻煩。她把摻著槐花的餅子放進(jìn)油鍋里煎,鍋鏟子一點(diǎn)點(diǎn)動(dòng),慢慢地煎,并不急。那餅子酥酥脆脆的,就熟了,放到盤子里,用筷子夾著,慢悠悠地送到嘴里嚼,很快,那嘴里便滿是春天的味道。
這個(gè)時(shí)候,田野里麥子也灌漿揚(yáng)花了。祖母收拾好鍋碗,便背著籃子去麥田里看麥花。麥花很細(xì)碎,迷迷離離地開在麥穗上,像灑了一層淡綠色的細(xì)雪。祖母望著麥田,深吸了一口氣,像挺滿足似的,掐了一只麥穗,放在手心里搓,看看今年麥子的收成。還好,麥粒快要飽滿了。祖母往掌心吹了一口氣,那些麥殼兒都吹了去,留下來的皆是淺綠色的麥粒兒。祖母用指甲掐了一下,那乳白色的漿汁便流出來。祖母慢慢咀嚼著那些麥粒,就像慢慢咀嚼著一種生活,那口里滿是新麥清新的味道。
小滿
小滿就是待滿未滿。說到底就是還沒有豐滿起來。小滿通常說的是麥子,我們蘇北平原大多種麥子,麥子在風(fēng)月里長啊長,終于有一天長到了小滿。我們就會(huì)到麥田里去,看看麥子有幾成熟了,還要多久才能吃上新麥。所以小滿時(shí)節(jié),其實(shí)也是青黃不接時(shí)節(jié)。舊年的糧食已經(jīng)吃完,米缸見了底,而新麥還沒有下來。小滿到了,帶來了一種渴望,也帶來了一種憂傷。我總是覺得小滿是帶著饑餓的印記的,所以我的生命里渴望的其實(shí)是初滿,而不是小滿。
在等待開鐮的日子里,母親還會(huì)隔三岔五地到田埂上去,找一找可以充饑的綠瑩瑩的野菜。那些零落分布在田埂地頭的野菜,各有各的形態(tài),暗綠的,淺紅的,淡紫的,就像織在母親衣服上的那些細(xì)碎的小花,好看是好看,我卻大多說不上來名字。母親彎下腰,用尖尖的刀子剜它們。母親知道它們哪些是味苦的,哪些是味甘的,哪些清香,哪些有泥土的腥味;哪些可以喂豬,哪些可以喂羊,哪些是留給人吃的。母親把它們剜到籃子里,當(dāng)綠意初滿,母親就帶它們回家了。
在小滿之前的那一段時(shí)間,蒸野菜,常常是我們家的主食。野菜多是用芋頭面混拌,蒸熟了以后,就可以伸出手來抓著吃,并不需要什么調(diào)料,一點(diǎn)鹽,一點(diǎn)醋,簡單得就像那清貧又干凈的日子。
后來母親還是止不住又去了一趟麥田。麥子在小南風(fēng)里有點(diǎn)微醺了。母親取一支麥穗,在手心里搓著,一些黃澄澄的麥粒兒就蹦了出來。母親是高興的。她把麥粒掩在嘴里,用勁嚼著,那些麥粒兒成熟飽滿,都能嚼出面筋來。
當(dāng)云雀在云端之上孤單地高歌,蘇北平原上的收麥活動(dòng)就開始了。很多人,他們都是生于斯長于斯的老少爺們兒,割麥,拉麥,打麥,把麥子變成了面,把面變成了鄉(xiāng)村的煙火。
村北角的水車這個(gè)夏天一直沒有停下來。是誰踏著水車?深井里的水被水車翻了上來。那井水清涼,甘甜,勞碌的人掬起井水喝了兩口,便倒在樹蔭里睡著了。在那一年,母親的最后一次蒸菜,是用井水洗的,是拌了麥面的。并且,調(diào)料也破例地多了幾種。母親說麥面蒸的野菜是好吃的,調(diào)料要好一些,不能可惜了這白白的麥面。
夏風(fēng)疏朗,麥子都收完了,二姐養(yǎng)的蠶卻還處在初滿狀態(tài),還都沒有“上山”。這也是小滿之前我家屋子的一處充滿生機(jī)的風(fēng)景。二姐養(yǎng)的蠶并不多,或許是她的年齡恰好到了青枝綠葉的養(yǎng)蠶時(shí)節(jié),所以她的心性讓她養(yǎng)了一些蠶,在我看來,她多數(shù)是養(yǎng)著玩兒的,就像養(yǎng)一個(gè)夢(mèng)、養(yǎng)一個(gè)故事一樣。其實(shí)不光是二姐,我自小也喜歡蠶寶寶。總覺得這個(gè)小小的東西,小小的生靈,在嫩綠的桑葉上爬呀爬的,蠻可愛的,蠻讓人欣喜的。所以每到村街上來賣蠶的,我們便心照不宣地買一些蠶回來。反正蠶又不咬人,我們揣在懷里并不害怕。
其實(shí)母親也知道我們的把戲,但她并不揭穿,也不做表態(tài),只是她會(huì)趁我們不注意把籮筐竹匾放在明亮處,讓我們看到,僅此而已。于是買來的那些蠶寶寶都養(yǎng)在了竹匾里。怕它們冷著,凍著,夜里再被老鼠鉆了空子,二姐便用被子把它們捂住,蓋好,讓它們好好睡覺,不到“用膳”的時(shí)候,不會(huì)讓它們見到天光。
桑樹在村南水塘邊就有。一棵大的,幾棵小的,長相都不怎么好看,歪著脖子,枝杈的一半探到水邊,一半向往天空。桑葉純粹的嫩綠,正適宜摘下養(yǎng)蠶。桑葚還都小小的,還青著,要等到天更熱一些的時(shí)候,桑葚成熟了,發(fā)紅發(fā)紫發(fā)黑,我們小孩子便如猿猴一般爬到樹上去摘桑葚吃,弄得嘴唇發(fā)紫,十指烏黑。還有喜鵲也跟著胡鬧,在枝丫間叫喳喳地跳來跳去,跟我們爭食。
我家自留地里也有一棵老桑樹,老桑樹旁邊還有一棵老茶樹。后來記不清是哪一年,老茶樹招了蟲災(zāi),長得萎靡,被父親砍了。那老桑樹孤立著,看起來仿佛蒼老了許多。不過到了春天,老桑樹發(fā)出的枝葉都是新的,我二姐就會(huì)提著竹籃子,走近前,把那些嫩嫩的桑葉一片片采摘下來。
喂蠶時(shí)的情景是開心的。二姐掀開被子,陽光剛好照過來,落進(jìn)竹匾里。那些柔軟的細(xì)小的蠶兒,一律翹著頭,徐徐地律動(dòng)著,在各自極小的小圈子里爬動(dòng),好像是餓了找吃的似的。二姐喜上眉梢,把竹籃里的桑葉一片片輕輕地放進(jìn)竹匾里,那些小小的蠶慢慢地爬上來,沿著桑葉的邊緣沙沙地吃起來。
沙沙地吃。嘈嘈切切,嘈嘈切切。那種細(xì)微卻又清晰的蠶食聲,如一曲低聲部的音樂,會(huì)讓你聽著,聽著,慢慢地安靜下來。
這個(gè)時(shí)候,二姐就會(huì)幻想。在她的幻想里,那些蠶寶寶漸漸長大,長大……然后,它們的“大限”到了,它們要“上山”涅槃了。
其實(shí)沒有山。是二姐在幾天前就為蠶寶寶準(zhǔn)備好的笤帚把。笤帚把是高粱梢子做的,平時(shí)僅用來掃地,現(xiàn)在做了蠶寶寶們的“山”。二姐把笤帚把豎在竹匾內(nèi)側(cè),那些待產(chǎn)的蠶們便會(huì)沒日沒夜地往笤帚把上爬,以悲壯赴死的姿態(tài),在“山”上吐絲,作繭,把自己束縛在里面,決絕地不留一絲縫隙。
那“山”上結(jié)滿了繭,潔白的,一律掛著,像黑暗里一盞盞明亮的燈。
無聲的告白。也是歲月之于命運(yùn)的一段留白。
二姐坐在那歲月的燈下,坐在那陳舊的繅絲車邊,一圈一圈繅絲。一日一日。一年一年。織夢(mèng)。也織她青春的初滿。
芒種
“芒種”,是一個(gè)帶有古典意味的很美的詞,尤其是傳說賈寶玉生于芒種日,而黛玉葬花,偏偏又在芒種,暗合著時(shí)令的節(jié)拍,這“芒種”就又有了某種宿命性。它其實(shí)是一種指令,無聲地,在它該到來的時(shí)候就到來了。然后呢,“芒種”——該忙的忙,該種的種;既是播種,也是收獲。所以如果按照實(shí)際的情形,再說得直白一點(diǎn),“芒種”大約也就等同于“忙種”。不過是,“忙種”就是勞作,少了“芒種”那樣綠茵茵的詩意了。
在蘇北鄉(xiāng)下,芒種前后,那的確是又忙又種的。我對(duì)于“芒種”一詞最初的理解就是“忙種”,那個(gè)“芒”字所表達(dá)的意思,我在相當(dāng)長的時(shí)間里是困惑不解的。后來才漸漸明白,并且認(rèn)同,“芒種”就是帶有芒刺的夏季作物該收的收,該種的種。比如麥子和稻子。在每年的“六一”前后,當(dāng)孩子們歡欣鼓舞地慶祝自己節(jié)日的時(shí)候,在鄉(xiāng)下,緊張的夏收就開始了。
那是大片大片的麥子,黃澄澄的,鋪滿了整個(gè)蘇北平原。如果沒有風(fēng),那些散發(fā)著濃釅的成熟氣息的麥子,一律筆挺地站著,像從古代站到現(xiàn)代的士兵,它們擠擠挨挨,構(gòu)成了亙古龐大的麥子家族。如果有風(fēng)掠過平原,那些麥子又會(huì)翻起麥浪,一波一波的,起起伏伏,從眼前推到天際。熱風(fēng)陣陣,撲面而來,風(fēng)里是熱烈又急迫的躁動(dòng)的麥香。
黃金鋪地,老少彎腰。村子忙碌起來。
我家干活的主角永遠(yuǎn)是我母親和我姐姐。那時(shí),她們?cè)谔锏乩飺]鐮割麥,祖母因?yàn)樯狭四昙o(jì),且腳小行走不便,她就在家里蒸饃饃(我們蘇北鄉(xiāng)下叫卷子)。我之所以很少提及我的父親,那時(shí)因?yàn)楦赣H是個(gè)教書先生,在村里教小學(xué)的,他大約只會(huì)舉著教棍教孩子們領(lǐng)讀:“日月水火……”對(duì)于干農(nóng)活是不怎么在行的。
祖母在家蒸饃饃,先是在大鐵鍋里燒上半鍋大麥茶,麥茶燒開后,倒在大茶壺里,放在一旁涼著,然后才燒一鍋水,在鐵鍋外圍套上防止漏蒸汽的草圈子,在鐵鍋上放上蒸籠,鋪好籠布,把那些之前做好的饃饃劑子一個(gè)個(gè)排列在蒸籠里。在灶膛里添了木柴,燒大火蒸。
在蒸饃的時(shí)間里,祖母并不閑著。她要?jiǎng)兪[剝蒜,炒三兩個(gè)菜。蔬菜都是自家菜園里的,青菜,黃瓜,西紅柿,豆角,隨便抓來,經(jīng)祖母添油加醋那么一炒,幾個(gè)下飯小菜就上桌了。
這個(gè)時(shí)候,大饃饃剛剛蒸好,滿屋子升騰著熱氣,就像是在夏天里過冬天似的。
割麥的人回來了。很疲倦。在桌子兩邊,母親和二姐坐了下來。她們的臉上、手上,染著麥銹,黑一塊、黃一塊的。涼了的大麥茶正好喝,一碗下肚,周身緊繃著的筋骨都酥了。接下來拿起筷子,拿起大饃,開吃。
正常情況下,如果是天氣允許,我們村的麥子幾天也就收割完了。平原上,麥子沒有了,只剩下麥茬兒地。一場小雨淅淅瀝瀝落下來,不出兩天,那光禿禿的麥茬兒地就會(huì)綠意盎然起來。那是遺落在地里的麥粒開始發(fā)芽。帶著綠意和雨霧的麥茬兒地,此時(shí)成了麻雀的天堂。說不清是從哪兒來的,無數(shù)只麻雀落在麥茬兒地,就像不安分似的,從一處飛起,落在另一處,然后又飛起,又落在另一處。
在雨天,勞累了數(shù)日的村人們,不怎么出去串門了,都窩在自家的床上,伸直了腿睡覺,是要好好歇一歇了。麥子都收了上來,糧囤里滿滿的,應(yīng)該可以吃到年底了。
芒種,如約而至。
帶芒的麥子已收割完,帶芒的稻子該插秧了。其實(shí)我覺得應(yīng)該還有一種“芒”。那是除去麥芒和稻芒之外的燠熱夏日的光芒。歇了幾天的村人們,此時(shí)又都彎著腰在水田里插秧。天上有一個(gè)太陽,水里有一個(gè)太陽,農(nóng)人背脊上的汗珠里還有無數(shù)個(gè)太陽。那些太陽滾動(dòng)著,折射出的光刺在農(nóng)人的背上就成了炙熱的針芒。
我家的水田并不多,大概有幾畝吧。水稻栽插完以后,通常還有兩三種作物該在這芒種時(shí)節(jié)下種了,那就是黃豆、玉米和芋頭苗等旱田作物。我們小孩子禮拜天不上學(xué),點(diǎn)黃豆的時(shí)候,我們跟在母親后邊看著。母親手里端著干瓢,干瓢里是黃豆,另一手捏著黃豆往一個(gè)個(gè)小土眼子里點(diǎn)種,三五粒,不多也不能少。此時(shí)我們就把母親點(diǎn)過的黃豆眼子用松土抹平,再用腳在松松的泥土上輕輕地踩,輕輕地踩,就把黃豆蓋上了。如果下著小雨,泥土潮濕,隔了三五日,那泥土里的黃豆就會(huì)破土發(fā)芽。那些嫩嫩的鵝黃色的芽兒,有的矜持著,有的忸怩著,有的又猶抱琵琶,睡眼惺忪,都像是害羞似的。又隔了幾天,風(fēng)兒一頂,它們忽而又都展開了,露出了一個(gè)個(gè)翠綠的裙。
點(diǎn)種玉米,要比點(diǎn)種黃豆草率一點(diǎn)。自然也是在酥松的田地里刨出一個(gè)個(gè)土窩窩,按照點(diǎn)黃豆的樣子,把玉米點(diǎn)種進(jìn)去,用腳勾著土,埋上再踩踩,幾乎就可以了。如果遇到旱天,玉米苗是出不齊的,母親就會(huì)說這窩大黍(玉米)瞎了。還可以補(bǔ)種,總之盡量讓玉米家族的兄弟姐妹都到齊了才好。
黃豆,玉米,在風(fēng)里雨里長著,長成了茁壯的苗。這個(gè)時(shí)候就要施肥、松土,或者間苗、鋤草了。那是慢工細(xì)活兒,急是急不得的。也還好,作物點(diǎn)種時(shí)節(jié)并不是有多么繁忙,你看那些間苗、鋤草的農(nóng)人們,多是悠閑的樣子。他們太懂得芒種的意思了。
遇到雨倒是挺煩心的。地里都是雨水,那些作物的葉片上都是雨水,天地間都是雨水。在地里干活的人們披著塑料布,塑料布上都是雨水,雨水滴到頭發(fā)上,頭發(fā)上的雨水滴落到泥土里和自己的鞋殼里,是挺煩人的。不過,回到家,解開塑料布,脫了衣服,沖個(gè)澡,那點(diǎn)兒煩惱也就過去了。
栽插芋頭秧苗,這活兒父親是會(huì)干的。或是母親故意的——故意選在周日,父親不再去學(xué)校,他便只好配合著母親,干一點(diǎn)和泥土與日子有關(guān)的事情。總要用上一天或兩天的時(shí)間,我們家的那一畝三分芋頭地的秧苗才可以插完。至于芋頭苗后來會(huì)長得怎么樣,那就要看天氣、看它的造化了。
這些就是芒種時(shí)節(jié)的農(nóng)事。芒種哦,忙種。
夏至
劉禹錫在《竹枝詞》中寫道:“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在字面意思上,說的其實(shí)是夏至現(xiàn)象。夏至?xí)r節(jié)的天氣是變化無常的。明明是好好的晴天,太陽還在天上掛著呢,說下雨就下雨了,變化就是這么快,一點(diǎn)道理也不講。
這樣變化無常的情景,我是見過的。通常是在午后或者傍晚。你也許是在放羊,也許是在放牛,晴朗的天氣一忽兒就變黃了。起了風(fēng),也起了沙,就像到了末日似的。水塘南邊的天空上起了烏云,只有幾朵,團(tuán)聚,沖突,又決絕散開,你便立馬聽到了一種聲音在大地上“噠噠”奏響,那是雨的腳在人間疾行。走過之處,濺起一片塵霧,泛起一團(tuán)泥土的腥氣。然后呢,一陣疾雨掃過,一切復(fù)歸安詳,太陽從烏云里跳了出來。
人們說夏至到了。說是夏至這天,白晝是最長的,往后天就更熱了,雨就更多了。聽起來有點(diǎn)嚇人。我那時(shí)還小,并不明白夏至是什么意思,說這一天是最長的,為什么呢?我也不太想知道。既然是村里的老年人抽著煙袋翻著墻上的日歷,鄭重其事說的,大約也不會(huì)錯(cuò),這一天肯定是最長的。長就長吧,又有什么關(guān)系呢?
對(duì)于夏至,我們村里的人好像也不怎么講究,不像端午、清明那樣,要有像樣的儀式的。夏至這一天的到來,趨于平常,它不過是二十四節(jié)氣中的一個(gè)過客,該來的它就來了,該走的它自然會(huì)悄無聲息地離去,我們村里的人還會(huì)把土地和日子于平常狀態(tài)里經(jīng)營下去。
后來我聽說夏至日總還是有一點(diǎn)講究的,不過是我們村子太小,沒聽村里人說起罷了。講的是吃食方面。“冬至餃子夏至面”,“吃過夏至面,一天短一線”。如此說來,這夏至也是不容小覷的,夏至這一天是要吃面的。
我曾經(jīng)認(rèn)真回想過,我們家這一天是不是吃了面了,回想來回想去,也沒有什么清晰的記憶。也許這一天吃過面,也許這一天我母親或者祖母忘記了做面。但是,作為蘇北人,我們都是喜歡吃面的,所以我們家也經(jīng)常做面吃。平常就是這樣,也可能在夏至之前,也可能在夏至之后,不一定非是夏至這一天。
說起面,蘇北鄉(xiāng)下的面其實(shí)很簡單,沒有華美的前世今生,它就是面條,麥面搟成的面條,赤條條地下在開水里,就成了裸面。這樣說未免還是草率了些,在我們家,雖說經(jīng)常吃面條,但是它的做法又不是單一的。為了讓面條更好吃些,母親或者祖母總喜歡想著法子,別出心裁,做出一點(diǎn)花樣來。
就說搟面條吧,那是真正的手搟面。在夏天,中午,在堂屋的方桌子前,我祖母彎著老腰,兩手推著搟面杖,在那里搟面條。這就像是深嵌在我記憶里的一個(gè)鏡頭,一想到手搟面,我就會(huì)想起當(dāng)年做手搟面的祖母。祖母穿的是白紗粗布衣服,汗粘著白紗粗布,我都能看到祖母那干瘦的隆起的背脊。她搟著面,把一個(gè)圓形的面團(tuán),搟成了一張大大的薄薄的餅,然后祖母就把這張薄餅對(duì)折一些,再一道一道折疊,撒上一點(diǎn)面粉,用手撫了撫,撫均勻了,她就用菜刀從頭往后一刀一刀細(xì)密地切過去。她將她切好的條狀的鮮面散開來,又撒上一點(diǎn)干面粉,摻了摻,提起抖了抖,白生生、肉筋筋的面條就在祖母的手里誕生了。
燒開水,把面條下進(jìn)去,熟了,撈出。你吃一口,就會(huì)覺得真香,是麥子的香味。那時(shí)的手搟面才算是手搟面。
我喜歡吃不加鹽清水面條,這可能是我在吃面食方面有點(diǎn)另類的地方。除我之外,我們家人都是喜歡面條里有油鹽炸湯的。他們說那樣吃才叫好吃。或許他們是對(duì)的。祖母便在燒水之前,在鍋里炒了一點(diǎn)香料,把辣椒、生姜、蔥花炒香炒煳,然后加了青菜或是蘿卜絲,翻炒一下,這才添水燒開下面條。盛出來時(shí)還要加一點(diǎn)豬油提一點(diǎn)葷味,費(fèi)了這么些工夫,想必那油辣汪汪的面條果真是更好吃了。
這是面條。祖母還會(huì)做面皮,那面皮有點(diǎn)像餛飩皮的樣子。祖母把搟好的面皮捏巴捏巴,那面皮就變了樣,祖母說它們是“貓耳朵”。把“貓耳朵”放在鮮香的湯鍋里煮熟,吃的時(shí)候,軟糯、爽滑得很,你若再就一點(diǎn)辣炒的小干魚,哪怕是酸溜溜的雪菜,都過癮得很。我吃過的。的確是這樣。
除了這用麥面做成的面條、面皮,在那漫長的歲月里,我還嘗過祖母或者母親做過的綠豆面條和芋頭面條。綠豆面條內(nèi)里硬氣,顯然暗含了日月的精華,但表面有點(diǎn)兒糯,就像說話不能大聲,只能在口中呢喃。綠豆面條還自帶著綠豆的腥氣,這可能是它有別于其他面粉的迷人之處;芋頭面條是純樸的,發(fā)著黯淡的黑褐色,卻也還算柔滑,它有它的個(gè)性,它于苦味之外又自有甘甜,這該也是滿足吧。麥面,豆面,芋頭面,各有各的滋味,它們的滋味加起來,大約就是這不絕如縷的歲月的況味。
祖母去世后,她的搟面杖留給了母親。也不是刻意留給母親的,我們家就這一根搟面杖。幾年以后,我的母親做了我孩子的祖母。每當(dāng)夏至到來,我們?nèi)绻氤悦妫业哪赣H還會(huì)搟的,不過我的孩子喜歡上了方便面。
事實(shí)上,來到城里以后,我也不怎么吃面了。如果忽然有一天想到了面,想吃面了,我會(huì)到面館去,點(diǎn)一個(gè)小菜,要一碗他們的手搟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