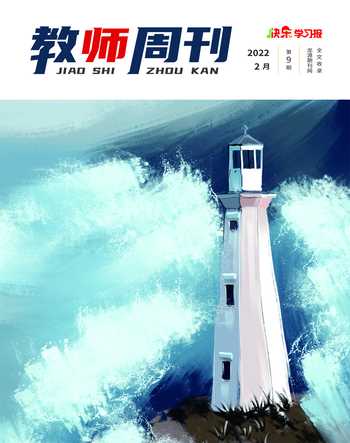《請買票》:女性主義的初步覺醒與局限
戴金喜
摘要:一戰期間,男性勞動力缺乏,大批女性得以擺脫家庭束縛服務社會,小說《請買票》敘述了幾位稍具女性主體意識的女售票員以非理性的方式反抗男性主導的的社會規范。這是一場女性主義的狂歡,非理性的斗爭方式意味著初步覺醒的女性主義的一定的局限性。
關鍵詞:女性主義;初步覺醒;局限
英國當代作家戴維·赫伯特·勞倫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不僅以長篇小說名揚世界,其短篇小說也精彩豐富,寓意深刻,其中《請買票》更是一篇短篇小說佳品。小說敘述的是穿行于礦區之間的一列單軌火車上的幾名女售票員和一名年輕的男檢查員之間的的情感故事。男檢查員托馬斯在車上沾花惹草,周旋于幾個年輕的女售票員之間。女售票員安妮一開始很抗拒托馬斯,總是和他保持一定的距離。然而在一次游樂會上,出于寂寞和尋找陪伴等原因,安妮終究與其廝混在一起,隨著兩人關系越來越近,安妮試圖更進一步走進托馬斯的生活,然而托馬斯卻逃避了,又和其他女售票員混在一起了。最后,憤怒的安妮和一群女售票員設計將托馬斯引誘進了休息室,一哄而上將其打翻在地,逼其選擇一人結婚。安妮雖被選中,但她卻沒有任何的勝利的喜悅。一眾女性卻是一片茫然,而托馬斯雖敗卻不失風度,整理好衣物揚長而去。作者勞倫斯通過這一早期創作的短篇小說一如既往地繼續探討其擅長的女性主題,塑造一群孔武有力,敢做敢為,甚至略帶粗魯的女售票員,正是她們的天不怕地不怕的特點,她們對試圖玩弄她們于股掌之間的男性采取了斷然的、極端的、非理性的暴力教訓和報復,流露了作者的女性主義的初步覺醒及其局限的思考。
女性主義初步覺醒的第一階段:雌雄同體的塑造
故事發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年輕力壯的男性都上了戰場,列車上的駕駛員要么是跛子,要么是駝背,在他們的把持下,乘火車猶如冒險一般危險。和這群羸弱不堪的男人截然不同的是車上的女售票員們個個四肢健全,身體健康,甚至孔武有力,根本不把周圍的男人放在眼里。這是一群“天不怕,地不怕的野姑娘”,只見她們“猛地撲向那些不買票就想下車的小青年,而對那些到站該下車的男人卻是一陣推搡。”“她們眼里可不揉沙子——別想找她們的便宜。她們誰也不怕——可人人都怕她們。”孱弱的男性與健壯的女性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既顯示了戰爭的殘酷,也隱喻了工業社會男性與女性的失衡狀態,正是由于男性較之以往的殘弱,女性的地位與身份便在此突顯出來了。男性勞動力的缺乏為女性擺脫舊有的家庭的窠臼般的束縛,走向工廠,走向社會,贏得比以往更廣闊的生存空間,因此,女性得以逐漸擺脫男性和家庭的人身依附,逐漸走向經濟自由與獨立,其自身的獨立身份地位意識逐漸萌發而愈發漸漸清晰起來。以安妮為代表的女售票員尤為如此,她“頗有點(好戰的)韃靼人的味道”,“堅毅專橫斷然,疑心頗重,隨時準備主動出擊,可以以一敵萬”。她踩了乘客的腳,理應道歉,而她卻不理會乘客的抱怨,還之以怒懟:“你應該把腳上的雞眼放到口袋你去!”孔武有力,粗野無禮的野丫頭形象,一反傳統女性的柔弱溫順,溫文爾雅的形象,大有顛倒乾坤之勢。其強硬的服務形象既是躋身于一群骯臟粗魯,滿嘴污穢的礦工之間的現實生存需要,更是這群女性自發的身份意識的覺醒:她們不弱于男性,無論身體上還是心理上,更在社會服務的勞動上,既然如此,這群逐漸走上社會勞動崗位的女性逐漸樹立她們的自信,無疑,這是人類社會的進步。而她們這般的反傳統的特立獨行的男性般的形象又恰恰是女性矯枉過正的缺乏自信的反映。她們要用強悍的外在行動掩蓋內心的虛弱與缺乏自信。因為她們難以確信這得來不易的與男性的平等地位是否穩固,是否會在一夜之間蕩然無存,于是,他們便色厲內荏。
女性主義覺醒的第二階段——訴諸暴力,解決問題
小說在開篇塑造了一群天不怕地不怕的野丫頭般女售票員的彪悍的形象,很自然地,便引發了這群女漢子們處理個人情感矛盾時他們的反應——暴力解決問題。
男同事托馬斯周旋于一群女售票員之間,如同動物般與他們發生關系卻不承擔任何責任。安妮一開始對他心存戒備,始終與他保持一臂之距,然而,強悍的安妮也許是孤獨了,或出于其他原因,漸漸地放松了對他的的戒備,在一次游樂會上,安妮開始與托馬斯有了親密的接觸,從此便一發不可收拾,安妮便與托馬斯走在一起了。她將此理解為愛情,感情的獨有性激發了一個女性對男性的占有欲望,而托馬斯卻僅僅將之視為一段性經歷而已,并沒有將感情注入其中,于是在發覺安妮步步緊逼后便及時逃避,更有甚者,他又于另一個女售票員鬼混。女性和男性的矛盾在此便產生了。愛情的專一性和排他性讓安妮覺得作為女性的正常情感歸屬無法實現,女性在這場情感活動中處于弱勢、不平衡的被動地位。女性的正常情感需求需要男性的的回應與肯定,而一旦男性表現出漠視或者離場,女性就處于被否定的地位。在這種不平衡的語境中,安妮的女性意識逐漸萌發,她感覺到這種不平等的境況必須改變,于是,矛盾爆發了,一群女性將托馬斯暴打了一頓。這是一場女性主體意識的狂歡,女人拋棄傳統的柔弱的形象,將男性制服!女性一反過去屈從于男性統治的被動地位,第一次將男性作為征服對象,這不僅僅是一場簡單的情感報復,這是一場女性主義的宣言,女性,作為一個社會群體,與男性一樣享有平等的地位。女性,絕不是柔弱可欺的符號,女性在爭取與維護自身的主體地位、自身權益方面有著堅強的決心和強大的力量。一場暴力便一反傳統社會形成的女性依附于男性的舊有習慣認識,革新了女性的社會形象:女性和男性一樣可以昂首挺胸地闊步與社會!
以安妮為首的一群“野丫頭”將風流成性的男檢查員打倒在地,狠狠地教訓了一下!這樣的行為有其合理性,即作為社會一成員的男性在與異性交往時托馬斯理應遵守公序良俗——情感的專一性和男性的情感擔當,這是文明社會的規則,而他卻與多名女性關系曖昧,這是赤裸裸地異化女性,將女性淪為性工具,遑論平等對待女性!因此,一群遭受戲弄侮辱的女性群起而攻之,采取暴力方式教訓托馬斯即是女性意識的自然萌發。被欺凌者維護自身的尊嚴,維護自身的權益,合情合理合法。不能將女性維護自身尊嚴與權益的行為簡單地等同于女性屈從于男性的地位。在制服托馬斯后,這群女性逼其選擇一人結婚之舉動,有論者將其視為女性最終難逃從屬于男性的被動地位。筆者恰恰認為這是女性在維護良性的社會秩序與婚姻的尊嚴——一夫一妻制。這是這群稍具女性意識的“野丫頭”合理的情感訴求與針對男性的反駁。宗教與世俗社會對婚姻的最簡單的本質要求——情感的專一,而托馬斯對文明規則的破環激起這群原本弱小的女性憤而反抗,采取暴力教訓越矩者,或許有其合理性!
誠然,暴力本身也是對社會規則的一大破壞!這一群爭強好勝的女性,她們處處以男人暗暗教會她們的方式和這個世界相處,性格上,她們像男人一樣悍強勢外向,行為舉止上,他們像男人一樣直線性思維,強硬頂嘴,不服輸,甚至像男人一樣直接動手解決問題。她們處處以男人為范,意圖自強,爭取她們與男性、與強者平等的地位,不得不說,這是女性爭取與這個世界良好相處的方式,因為處處流露出模仿的痕跡,或許,這種模仿的方式并不一定符合女性自身的生理和心理特點,因此,她們的這種探索便具備了女性主義初步覺醒的一些特征:探索性、模仿性和非自創性。面對強者,或許她們不得不采取這種非理性的方式維護自身利益。當然,這樣的非理性方式恰恰體現了女性主義初期階段的局限。
女性主義初期階段的局限還體現在暴力漩渦之中男人的表現和這場暴力的結果。托馬斯被一群女性打翻在地之后,小說作者著力刻畫一個細節必須引起讀者的注意,那就是一個詞“averted”重復了7次之多,“he lay at last quite still, with face averted”,“He made no sound nor sign,but lay with bright, averted eyes, and averted, bleeding face ”,“Again he averted his face”,“He was still prostrate, with averted face”,“He remained lying on the floor, with his torn clothes and bleeding, averted face”,“He, however, kept his face closed and averted from them all”小說此處的細節描寫具有豐富的含意。作者重復該詞意在向讀者傳達托馬斯即使被女性制服,但其心里仍然不將這群女性放在眼里,表現在眼神里就是不和她們面對面的對視。“將臉橫過一邊去”,暗含之意就是雖然被圍攻制服,被迫做出選擇,可托馬斯根本就不服輸,根本就不拿正眼去看這幫姑娘。最后一個細節也耐人尋味,姑娘們在他做出選擇之后將他釋放,只見他“誰也沒看,看到角落里的帽子,徑直走了過去,俯身撿起,戴上,……大踏步地邁向掛衣服的鉤子,穿上衣服,從上到下系好扣子,扣好皮帶”,一個多么淡定從容的形象,仿佛什么打斗也沒有發生過。倒是這群女性一片木然,一副失敗者的模樣,兩相比較,便折射出女性在樹立自身的主體地位所面對的巨大的阻力與困境——男性,像巨大的高山一樣,壓得女性喘不過氣來,不平等的狀態似乎像高山一樣不可逾越。小說結尾似乎暗示:挑戰男性長久形成的威權地位,對于女性來說,任重道遠!
以西蒙·德·波伏瓦為代表的所謂存在主義女性主義認為女性生存的一切外部環境和客觀條件,都將女性限定在被動的、客體的也就是他者的位置上;通過學校和家庭的教育、社會習俗的熏染、法律和倫理的約束,為處境所強加的他者特性逐漸內化為女性的自我意識,使婦女自愿地、積極地按照男性中心的教條和規范塑造自己,這是一種更深刻的自我鉗制。因此,婦女要獲得自由,必須擺脫現有的社會文化和意識形態對女性的限定,必須通過主動選擇和不斷行動使自己成為自由的人。
結語
簡單了解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英國女性地位有助于理解勞倫斯該小說的創作初衷。18,19世紀是無可挑戰的男性至上的時期,婦女處于依附地位。傳統家庭是:“男人耕田地,女人守鍋臺;男人佩刀劍,女人掌針線;男人有頭腦,女人有心地;男人發號命令,女人愿聽命。”她們在家服從父兄,出嫁后依附于丈夫,丈夫既是主宰者又是保護人。19世紀末20世紀初,為擺脫“婦女只屬于家庭”的觀念束縛,爭取平等的選舉權、就業權及教育權,英國婦女掀起了婦女解放運動的第一次浪潮。從19世紀中葉起,英國婦女開始投入了爭取政治權利的斗爭。一戰前的英國婦女參政運動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請愿階段(19世紀50年代至90年代),主要是中產階級婦女以請愿、宣傳、組織團體,向議會施加壓力等方式進行斗爭,這些活動在那個紳士風度的“維多利亞時期”都引起過不小的震動——窈窕淑女上大街游行,這在當時是不可思議的。但她們的活動并沒有取得很大成果,在紳士風度的英國社會中,女性雖然有“女士優先”的典雅特權,但婦女在社會和家庭中卻都依附于男人。1900年蘭開夏郡的紡織女工組織了請愿運動,要求婦女選舉權。1903年成立于曼徹斯特的“婦女社會和政治聯盟”開始了新的階段,作為婦女參政運動逐漸出名。聯盟的主要目標是爭取婦女能與男子在同等條件下享有選舉權。這一階段的斗爭形式主要是妨礙演說會、不服法律、不納稅、焚燒車站、搗亂會場、示威街頭等暴力手段為特征,參與者中、下層婦女居多。激進派的女權運動者認為男女平等權利不能靠企求,也不能靠當權者的“善心施與”,只有靠婦女自己進行有效的戰斗才能爭取到,因此,戰斗的婦女以“行動,而不是語言”為座右銘,展開了更加猛烈的運動,她們不僅使用請愿、游行、示威、集會、出版等常規手段,而且還搗毀會場、焚燒車站,甚至還在公共場合圍攻政府成員。作家勞倫斯對社會的敏銳的觀察而創作了一系列的小說《虹》(The rainbow 1915),《查泰萊夫人的情人》(Lady chartter’s Lover 1928)關注女性主體意識的覺醒。《虹》的安娜不再安于相夫教子的傳統生活方式,她要求在家庭中的獨立地位,要自由表達自己的意見,甚至要主持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厄秀拉逃離課堂,放棄宗教信仰,甚至依照自己的意愿選擇戀愛與婚姻。她要打破傳統文化給她的一切束縛。《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中康妮代表了處于傳統文明與現代文明夾擊下的女性形象。她內心崇尚自然,追求自由的生活,然而現實卻處處與其作對,使她在現代文明沖擊下內心充滿焦慮與緊張。她在尋找突破的力量,希望重新回到自然狀態下生活。與之一脈相承的《請買票》描述了戰爭背景下工業社會中的女性獲得身份的解放,將這種男女力量失衡的特殊歷史境遇濃縮于一列火車上,展現了女性對男性主導的社會規范極端的非理性的報復。從女性主義的立場,可以窺見女性重新站上歷史舞臺過程中自我身份確立的迷惘。必須正視的事實是,這場延續至今已達150年之久的女性主義運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女性的地位在世界上也發生了極大的改觀,但是女性在職場中遭遇的區別對待甚至是歧視還是很普遍。在政治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性別平等仍然還是任重道遠。
參考文獻:
[1]錢敏.請買票中女性自我身份確立的困境[J].北方文學,2019(09):50-52.
[2]王曉華.從平權意思走向自我意識——20世紀英國小說女性主體地位的變遷[J].西北民族大學學報,2021(02):166-172.
[3]王成玲. D·H·勞倫斯《請買票》中女性主義的半覺醒[J].青年文學家,2021(05):117-118.
[4]魏天真,梅蘭.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導論[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4.
[5]張巖冰.女權主義文論[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
[6]錢乘旦.20世紀英國的婦女與家庭問題[J].世界歷史,1996(05):2-9.
 [7]楊金才,王海萌.文學導論[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0:18-19.
[7]楊金才,王海萌.文學導論[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0:1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