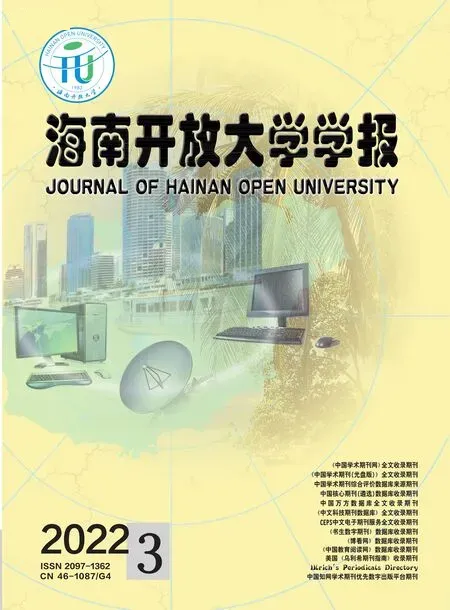田園敘事視域下E.B.懷特農場隨筆探究
年慧敏
(河南農業大學 外國語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0)
引言
西方文學中,田園敘事由來已久,源于古希臘詩人西奧克利特斯(Theocritus)的《田園牧歌》,把荒野與城市的中間地帶視為理想的人類生活環境,謳歌簡單純樸的鄉村生活,表達天人合一的幸福和喜悅,此外也擔憂農作的辛苦和城市的威脅,以及刻畫人性的丑陋和生活的殘酷。不過總體而言,這種敘事方式還是以訴說美好的田園生活理想為主,而且大致如威廉·燕卜蓀(William Empson)所說,田園敘事雖然是關于農民的作品(about the people),卻并非他們所寫(by the people),亦非為他們所寫(for the people)[1]因此,羅格?塞爾斯(Roger Sales)總結出了田園敘事的5R特征:避難(refuge),沉思(reflection),解救(rescue),安魂(requiem),重建(reconstruction)[2]。
美國作家E.B.懷特(E.B.White)是《紐約客》(The New Yorker)雜志從創刊伊始近六十年的編輯、新聞評論員、撰稿人,是《夏洛的網》《精靈鼠小弟》《吹小號的天鵝》三部世界著名童話的作者,更是出版數部散文集的風格大師。懷特雖然出生和成長在紐約,卻在三十多歲的盛年攜妻帶子舉家遷到緬因州一個偏遠的沿海農場,并在那里生活到去世,完成幾乎所有重要作品。其中奠定其作家地位的代表作品集《人各有異》(One Man’s Meat)和《懷特隨筆集》(Essays of E.B.White)主要以農場生活為題材,塑造出不同于以往的阿卡迪亞空間與農夫形象。國內關于懷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三部童話上,對其隨筆研究不多。本篇論文以這兩本作品集為研究內容,通過文本細讀,從田園敘事的角度分析作者選擇此地生活的原因、農場生活的辛苦及立體的鄉民肖像,肯定了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活方式,并通過探究這種現實阿卡迪亞空間的建構,對遵循本心生活、尋找心靈家園做出自己的闡釋。
一、阿卡迪亞審美空間的搭建
阿卡迪亞是田園敘事的關鍵詞,最初出現在古羅馬詩人維吉爾的《牧歌》里,是一個遠離現實的洞天福地。阿卡迪亞人以放牧為主,他們不需要勞作:大地不用栽種,自會供應一切糧食果蔬;紫熟的葡萄懸掛在野生的荊棘上,樹上流出甘露瓊漿;奶汁豐溢的羊群會自己回家,羊毛也不要染上種種假造的顏色,羊群自己就會改變色彩[3]。阿卡迪亞在地理上確有此處,是古希臘的一個地區,位于伯羅奔尼撒半島中部,因被群山包圍而與外界隔絕,據說是希臘神話中山林之神和牧神潘的家鄉。然而,維吉爾詩中描述的,并非這個現實中的荒僻之地,而是想象中的人間天堂。在鮮花盛開的草地上,或涼爽的樹蔭下,牧人們三三兩兩,或高談闊論,講述流傳下來的神話傳說,或獨自惆悵,思念離去的戀人,或引吭高歌,一較高下;阿波羅、俄耳甫斯、司歌女神、司命女神、山林女神等天神們可以和牧人們對話,互作酬答。這里是詩歌的天堂,音樂的故鄉,沒有辛苦勞作,沒有憂愁煩惱,更沒有戰爭政變的世事煩擾,人們悠閑自在地生活著,時間仿佛停滯,永遠春意盎然,鳥語花香。
阿卡迪亞的創造是維吉爾對田園敘事的重要貢獻,后人對田園的美好聯想無不源于此。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詩人桑納扎羅(Jacopo Sannazaro)和英國詩人菲利普·錫德尼(Phillip Sidney)都寫過題為阿卡迪亞的詩歌或戲劇。這片土地雖然是古代詩人想象出來的理想王國,當代作家懷特卻真的創建出了自己的阿卡迪亞,并幸福地在那里度過了一生。那個地方就是緬因東部海邊的一個鹽水農場。相比曾在紐約租過的八處公寓,緬因的那座農舍于懷特,就是真正的家,是心靈和身體獲得幸福和滿足的地方。
緬因州地處美國東北部,是新英格蘭地區六州中面積最大的一個,北部與加拿大毗鄰,東部被大西洋包圍,海岸線多巖石與島嶼。州內人口稀少,經濟落后,然而風景優美。地勢崎嶇,多丘陵、湖泊、峽谷及冰蝕峰;土地多為森林覆蓋。州內有數個州立公園和國家野生動植物保護區,還有新英格蘭地區唯一的一座國家公園——阿卡迪亞國家公園,一九一九年建立,原名為拉法葉國家公園,一九二九年改名為阿卡迪亞。十九世紀中葉,梭羅和他的同伴在印第安人的帶領下,考察了緬因州大大小小的森林、湖泊、瀑布、河流和高山,記錄下生長在森林里的高低樹木、灌木、花草、動物和各種鳥類,寫下了為后人留下珍貴材料的《緬因森林》。正是這片土地深深地吸引著懷特,讓他在人生正值盛年之際,離開了生于斯長于斯的大城市紐約,來到了落后、閉塞、偏遠的緬因海邊,并從此在這里扎根,度過了此后的幾乎所有歲月,甚至去世后也和妻子埋葬于此。
懷特與緬因的淵源早在他還是個五歲的小孩子時就已經開始了。每年和家人在八月從紐約坐十多個小時的火車,到離緬因首府奧古斯塔西北邊十英里的貝爾格萊德大湖群避暑,是他從童年到少年時期最美好的回憶,從他們一家人在那里游玩的照片就能想象得到美麗的湖水、森林和當時的歡聲笑語。在他十四五歲時,曾給這個大湖手工制作了一個宣傳單,上面寫著緬因是“這個國家最美麗的州之一,貝爾格萊德是緬因最美麗的湖之一”[4]。一九三一年,剛做父親不久的懷特攜妻兒去緬因東部海岸邊度夏,之后兩年都在夏天回到那里,并在一九三三年買下了四十畝農場和建于其上的一座農舍,挨著艾倫灣、藍嶺和一個叫北布魯克林的村莊。此后,這三個地名被署在了懷特源源不斷發往紐約的散文、隨筆和其他許多作品上,一起分享著讀者的欣賞、想象和向往。
這個懷特心中的人間樂園在文中處處留下身影,他的許多文章都是對這個家園的描繪。這片農場和此地其他緊鄰海邊的鹽水農場一樣,土地并不適合種莊稼,當地農民大都以養殖和捕魚為生。和傳說中的阿卡迪亞不同,緬因農場并非四季如春,而是季節分明,尤其有著寒冷漫長的冬天。然而,在懷特看來,每個季節都是美麗的。春天來臨的時候,暖氣回升,陽光鉆入積雪,溝渠漲水,活潑潑地汩汩流淌,青蛙在濕地的深處唱起雅歌,胡瓜魚游入小溪,燕子在電線桿上筑巢。“天氣晴朗的日子,陽光灑滿房屋南面的白粉墻,羊羔臥在谷場溫暖的草坡上,它們的前腿勻整地蜷曲,小小的臉頰上,流露出小小不言的滿足神情。郁金香在越冬時遮蓋的云杉枝條下爆出嫩芽。一只白母雞領著十三只黑色的雞雛顛來跑去,指點它們見識世界,還有這世界上的污池和小蟲子”[5]137。
夏天是農場里最快活最美好的日子。空氣充滿了花的芳香,丁香剛謝,蘋果樹開花了,蜜蜂飛來飛去。田野里,房子周圍,林子里,沼澤地里,到處都是小鳥在歌唱,戀愛,做窩,生機勃勃,“甚至把野草梗上的小絨球撥開,里面也會有一條青蟲。土豆藤上的葉片背后有馬鈴薯甲蟲發亮的橙色蟲卵”[6]。
豐收的秋季自不待說,就是漫長的冬日也有它獨特的魅力。綺麗的清晨,雪靜悄悄積在樹上,破曉時特異的天光,新一天的純凈和期待,清冽的空氣都讓人充滿喜悅。《人各有異》的最后一篇文章題為“苦寒”,寫于一九四三年一月,描述了當時的寒冷。實際上,翻譯成“苦寒”也許并不恰當,因為原文是“cold weather”,旨在表明天氣的寒冷,而并無“苦”字,通篇記錄人和動物對于寒冷的反應,洋溢著歡樂和興奮的氣息。首先,寒冷是一定的,一個多月以來,氣溫徘徊在零下十幾度,最高溫度不過零度。作為一名作家,作者眼里的寒冷并不是籠統的一種冷:晴朗而寒冷,陰晦而寒冷,有雪的寒冷,無雪的寒冷,凄風呼哨的寒冷,悄然無聲的寒冷,暴虐的寒冷和寬厚平和的寒冷。“清晨用熱水融解結冰的水桶,院子里布滿淌出的冰溜子。”“即使在用成噸干草封堵嚴實的谷倉里,奶牛鼻子的流涕也結成了小小的冰柱”,“不戴手套去抓門閂,鐵閂會咬住你的皮肉不放”[5]299。在這種日子里,維持生存是生活中的主要任務。然而,眾人個個歡天喜地,因為爐膛中的火焰、靈巧的連指手套、毛線襪子、點火的聲響、熱乎乎的飲料,還有與鮮艷帽子搭配的鮮艷襯衫。路遇的卡車司機“透過結了霜的擋風玻璃的縫隙,朝我咧嘴笑”,孩子們“哆嗦著,打打鬧鬧,等在路邊,檢查冰面是否適合冰鞋和雪橇”,因為校車無法發動,大家為會集體遲到而興高采烈。即使在這樣的日子里,“我”仍不愿用四季分明的新英格蘭換溫暖閑適的塔希提島,不愿意享受舒服便捷的現代文明和無所事事的生活;雖然明知在農場待久了,會不適應大都市的生活,仍不愿放棄。這里是天堂,是并不刻意避世的桃花源,是和外界時時互通有無的香格里拉。這是懷特喜歡的生活方式,別人認為的落后、閉塞、不便反倒是他心儀之處。
二、平凡又獨特的鄉民肖像
和其他作家相比,自身也埋首于農場勞作的懷特對和他比鄰而居的村民們的生活更感同身受,對他們的衣食住行喜怒哀樂觀察得更為仔細。更重要的是,他忠實于自己的眼睛,并不多加猜測鄰居的心思,也不去費思量他們的精神狀態及生活意義,只是如實寫下自己的觀察。他筆下并非這個地區的農民吟詩作賦的文藝生活,亦非對其黑暗悲哀命運的拷問,而是柴米油鹽婚喪嫁娶的日常。比如津津有味地閱讀并詳細記錄了鎮務報告,十二人為初婚,二人為再婚,有六人出生,二男四女。九人死亡,四女五男。四十二只雄犬,八只雄犬領得許可證。九十八名兒童看過牙醫,拔掉了六顆恒齒。這些民生民情利用散文特有的優勢一一鋪敘開來,直觀準確地記錄著當地歷史。當然,其間也不乏溫馨鏡頭:在村里的汽車修理廠,修理工在一邊鼓搗汽車,收音機的音量始終調得很低,音樂輕飄,頭頂的椽木上懸了翻新的舊輪胎,內胎碼放在架上的箱子里,一切都那么安逸寧靜。
從《人各有異》收錄的作品內容可以看出,作者目光所聚焦的地方,并不是這塊土地上的人,而是植物,動物及這塊土地本身。所以文中關于鄰人的描寫屈指可數,但不妨礙作者以深厚的功底寥寥幾筆,勾勒出一個人的肖像,傳神之處呼之欲出。他對他們的刻畫不美化,不夸大,不粉飾,不丑化,很少如對動物一樣帶有感情色彩。鄰居們大都老實巴交,充滿希望,勞動在臉上刻下褶皺,但并非千篇一律,人人如此。比如有一位見解獨特的鄰人,住在山脊上,冬夏的著裝總是一件短大衣,穿衣理論是,大衣可以御寒,也可以隔熱。他孑然一身,和兩頭母牛住在一起,共享安寧與污穢。對于每日擠下的許多牛奶,處理方式是想喝就喝,不想喝就扔掉。這種遺世獨立、我行我素的風格在民風樸素的鄉下并不多見,完全可以作為一個深挖人性探索心理的好素材,成就一篇犀利散文。但懷特的獨特之處就在于此,不刻意深交,不主觀評價,信筆寫來,隨意放在文中一隅,引人遐思。
雖然和鄰居們之間并沒有親熱到“漉我新熟酒,只雞招近局”的地步,更不用說“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農務各自歸,閑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7]93,或者“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7]91”,但“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的關系還是有的,其中也不乏相熟的鄉鄰。達默龍先生就是作者著墨最多的一位鄰居,估計也是打交道比較多的一位。讀者從多篇文章的只言片語里可以清晰勾勒出這位友鄰的畫像。他以捕龍蝦為業,熱愛閱讀,珍惜圖書;與“我”閑談海鷗與蛤蜊及鄰里之間的流言蜚語,還送過“我”一只海鷗。捕撈龍蝦時,將母牛拴在海岸處幾步開外,撒網歸來后,順手牽上它一道走在田野上,他拎著空空的油罐,它晃著飽滿的乳房。他以前在帆船上工作,后來改捕龍蝦,因為自由自在。每天清晨,他都駛往海灣,拖曳捕籠。中午回來,先是白帆出現在岬角轉彎處,接著是船身,隨后傳來他拖起最后兩個龍蝦捕籠時,發動機空轉后又加速的聲響。這種場景雖然和“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意境不同,卻頗有異曲同工之妙。達默龍先生每天出海極為守時,鄰居可以根據他往返的時間對表。他不操心任何人,只管自己,也沒人操心他。深秋時節,他用自己的索具,將船拖到自家的海灘上,拆下發動機,越過田野搬入柴棚,涂上機油,安頓在雜貨店裝貨的紙箱里。冬日夜晚,他拾起耽擱下的閱讀,編制魚餌兜,修補捕籠。春天陰冷潮濕的日子里,他找出柏油桶,油罷他的帆具,掛在灌木叢的隨便什么地方,像是在星期一洗晾日。然后,他付給州政府一美元,領取許可證,再花七十五美分,取得法定量尺,迎來又一個捕撈季。這種漁民生活和讀者之前的閱讀經驗大相徑庭,沒有風吹日曬、兩手空空的辛勞和失意,亦無生活艱難、終日奔波的窮苦,只有日復一日的平靜,忙閑有致的自得。這樣的描寫再一次印證了懷特在此部分的寫作風格:他是心懷好奇的生活記錄者,不是高高在上的評判家。
當然,外界城市和現代生活的喧囂不可能不給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帶來影響和變化。與選擇生活在鄉下的懷特相反,他的鄉下鄰居有越來越多的人和家庭離開此地,去往城市,進入工廠或政府部門,利用周末回來照顧鄉下的土地。路邊很多住宅門窗緊閉,讓人心酸。村里的女孩子羨慕外面的世界,希望去當長途客車售票員或空姐,以便有可能嫁個城里人。二戰期間都在農場度過歲月的懷特基于自身在鄉間感受到的樂趣,相信戰后的新世界應當圍繞重新拓土移民的鄉野美國建立起來,讓比例適當的一部分美國人投入土地文化。如果人口中有太大一個比例,靠貿易、實業、商業、工藝和城里人的百千萬組合來支撐自身,社會可能會過于復雜,難以保持平衡,勢必將時時處于某種失調狀態。而如果有相當數量的民眾,全部或部分時間參與體力勞動,直接提供自己需要,或認為自己需要的東西,則社會平衡將日趨牢固,很難顛覆。因此,面對這種變化,懷特感到悲哀,眼睜睜看著往日美好不再,卻無能為力。這種感傷是田園敘事一個很重要的主題,在不同時期有不同展現。也許正是因為對往日的哀思讓回憶變得美好,讓只存在于過去和頭腦中的田園更加不可企及。從這個方面來看,懷特的田園敘事遵循了傳統,同時填充了新內容。
三、繁忙復雜的農夫生活
無論是歐洲牧歌之父西奧克利特斯還是維吉爾,在描述牧人那無憂無慮的美麗世界時,都是身居城市受貴族庇護的學者和詩人,衣食無憂,是所描述的那個世界的旁觀者,而非生活在其中;后來寫出田園文學作品的詩人和作家無論是否生活在鄉村田間,亦大都沒有親身躬耕,體會稼穡之勞。而真正生活在農村的農民和牧人沒有審美距離,是不會歌頌自己的生活的。因此,“田園詩并非牧人自己的創造,它需要一個完全不同的視角”[8]。另外,對于生活在城市的人來說,田園生活代表著簡單、悠閑、自在和愉悅。這種對沒有經歷過的生活理想化,本是人之常情,一如辛苦備戰的高中生對大學生活的憧憬和向往。然而,一旦過上了理想的生活,就會發現理想和現實之間的差距。所以,對于很多人來說,田園生活是只能供向往而非真的去實現的。
懷特并非如此。他認認真真地過著幾十年的農夫生活,并作了真實的記錄,是他描述的那個世界的一分子,是農夫生活的實踐者而非局外人。文中的那個敘述者就是他自己,一個真心喜歡生活在農場里的城里人。選擇這種生活并非感情用事,也不是去消閑,那是他的生活。——雖然開始比較業余,且有玩票的心態,但漸漸地,面對繁瑣的農活,每天花許多時間在壘石砌磚,開膛破肚上,與繆斯漸行漸遠。懷特不認為去鄉下是為了逃避城市生活的壓力,因為據他的體驗,農場上的生活壓力遠比城市的大:各種農活讓人分身乏術,農產品的保存、貯藏與銷售也是不小的問題。尤其是農忙時節,作者爆料自己甚至因為沒有時間寫稿而不敢起床,因一旦起床就會淹沒于各種活計中,于是向妻子撒謊說生病了,需要臥床,以完成寫稿任務。
懷特覺得農場生活比城市要復雜得多。在紐約,僅操心工作的事情,而在農場,除了要做和在紐約差不多的工作以外,每日里的雞鴨羊群和種植采摘及修東補西之類的農活都需親力親為,還有不時碰上意想不到的問題同樣讓人絞盡腦汁。難怪他半開玩笑地說,所謂簡樸的鄉間生活不過是個神話。詩人冥想牛群在草場上徜徉,如一首其樂融融的田園詩,而赤裸裸的現實則是剛斷奶的羊羔因為離群哭哭啼啼,糧食口袋的鎖線器拒絕在黑暗中工作,廚娘歇工,孩子發燒,爐火燒不旺,脫脂器需要新的分離環,提燈沒汽油了,南面的窗子潲雨,透風,打濕了雞棚里鋪的干草等等。雖然都不是什么大事,但時間也就如此消耗掉了。
雖然懷特自謙只是喜歡同動物廝混,但他真心實意地想投入到農場生活,把農場侍弄好。他博覽關于虱子和螨蟲的文獻,看查爾斯·達爾文的《蔬菜霉菌的形成,寄生蟲的作用,以及對其習性的觀察》,喜歡讀馴犬、養雞等書和農業報紙,從中學習農場經驗。他高度贊揚《鄉間紐約客》,稱它是最偉大的報紙之一,因其除舊布新,對農民熱忱幫助,且設法保存和傳遞了對土地的感情——一種欣喜感,一種將聰明才智用于土地,在一年的時序輪替中求得完成的充實感。上面刊登的文章真實生動反映了農場主的生活,如用斑蝥粉涂抹小馬受傷的膝關節,溫馴的母雞將小雞啄碎,而后吃樟腦丸自殺,喜歡舔馬毛的母牛,用火油治療母雞搖頭等等。懷特還注意到生物的循環和互相利用:蟲子吃蘋果長肥,小鵝吃蟲蛀的果子長肥,人吃小鵝長肥,蟲子又等著人。此外還有,羊糞做草坪的肥料,修剪掉的草葉混入堆肥,堆肥施到菜園里南瓜秧上,南瓜秧結出的老南瓜又成了羊的食物。甚至物體本身也能自我利用:剪羊尾的時候,剁下羊羔的尾巴,在殘根部位敷上一小撮,讓血液凝結。
前文提到,徹頭徹尾的農民對躬耕放牧的生活很少有美的體驗,而對于那些心靈敏感,中途成為農夫的人,這種生活就不一樣,即使他們長期體驗,親自勞動,也無法抹去對農事和周遭自然環境的感嘆,時時停下腳步欣賞看到的各種美。比如在農場待過十年,并真的做過農夫的羅伯特·弗羅斯特(Robert Frost)。于他而言,平常的風景和勞作都充滿了歡喜和浪漫:桑樹是信徒該撒看見耶穌的地方;拎著水罐水桶去河邊取水會興高采烈,因為秋夜涼爽迷人,可以和月亮捉迷藏;修補鄰居之間的圍墻時會問“我會圍進什么,又把什么圍在墻外,有可能把誰的感情挫傷”[9];長柄鐮割草的聲音是在對大地低吟,去草場曬草時發現割草人對牧草中的一叢野花手下留情,引來蝴蝶飛舞,立刻從孤獨的感覺中擺脫出來,仿佛找到了知音。
然而,懷特并非這樣對花感嘆見月思鄉的類型。他從一開始搬到農場,就沒有表現出對這片土地的新奇,表達對看到的一花一草的贊嘆,對剛上手的農活詩情畫意的贊美。也許他起初心里就明白,這里是他的家,是生活而非抒情的地方。此外,他的性格和寫作風格亦非如此:他更擅長簡單直接地描述出自己的所見所聞,而非抒發強烈的感情。作為一名作家,他對生活有敏銳的觀察力,周圍的大事小情都在他的注視之下,都是文章里覺得需要和人分享的內容。他曾在一篇文章里寫鵝與羊羔為鄰,寒冷的冬夜,羊羔臥在鵝蛋上,享受舒適的草窩,同時防止鵝蛋結冰。這種動物的共生互存如果不是親自見識無論如何是無法寫出來的,即使寫出來,也不會有人相信。
果然,一分耕耘一分收獲,作為一個半道出家的半職業農夫,在那片遠稱不上肥沃的農場上,懷特憑著對農事的熱愛和掌握的各項技術,還有對家畜家禽們的關心,每年都交出一份驕人的答卷。每年都要養上百只雞和羊,數十只豬,生產上百磅羊毛、羊奶、雞蛋、熏肉和烤肉,捕撈鱈魚若干,種植燕麥、蘋果、南瓜、土豆等糧菜瓜果。這些數目頗大的產量和林林總總的產品鋪陳讓讀者真實地體驗到了懷特作為農夫的成就感。
結語
與眾多田園敘事作品相比,懷特筆下描述的阿卡迪亞是現實的,沒有唯美和浪漫的色彩,也沒有不勞而獲的幻想。那里的冬天漫長而寒冷,農場的工作瑣碎而繁多,鄉民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然而,在那里生活了四五十年的懷特,始終懷著滿腔熱忱,保持著對農事的興趣,樂觀地處理生活中遇到的各種難題,并以一位優秀作家特有的敏感,對周圍的季節變化、生物繁衍、風俗民情等一一看在眼里,以最平易的句子,最簡練的單詞,生動地刻畫記錄下來。作家自在愜意地享受著和諧的人與自然的關系,并不刻意以文人和局外人的眼光來打量這個其樂融融的鄉村世界,這些身臨其境的第一手資料,身體力行的農事勞作,毫不煽情的真實描述,余味悠長的藝術美感等是其他田園文學作品里很少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