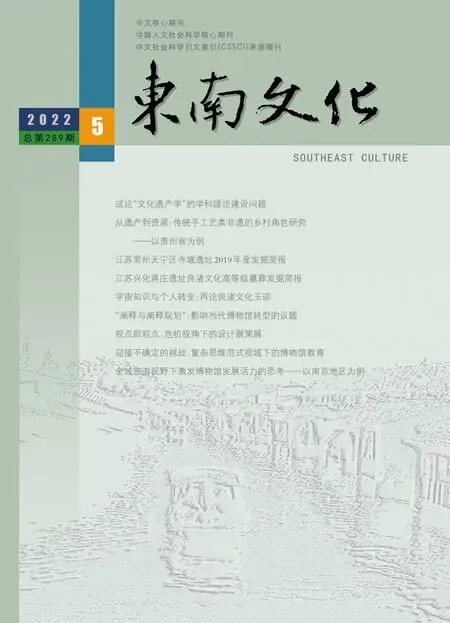博物館文物修復檔案的管理
馮向偉
(南京博物院 江蘇南京 210016)
內容提要:文物修復檔案在博物館文物修復管理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威尼斯憲章》發布后,對文物修復過程進行全面記錄漸成國際準則。我國博物館通過《博物館藏品保管試行辦法》和《博物館藏品管理辦法》等,逐漸確立了文物修復檔案的記錄機制,并在管理與利用上作了數字化探索。博物館在落實法規、政策的步調上并不一致,管理中依然存在機制不系統、檔案內容不完整甚至失真、記錄不規范、收集不及時、保管失當、利用不充分等問題。對此,在繼續加強立法與監督、提高博物館制度建設與管理積極性的同時,博物館還應主動建立文物修復檔案系統管理機制,擴大修復檔案記錄機制的文物覆蓋面,從而促進我國博物館文物修復檔案的合理利用和有效管理。
文物修復檔案在博物館文物修復中具有重要作用。相關立法與行業標準已就文物修復檔案的管理作出規范,但出于某些原因,博物館在法規、政策的落實上步調并不一致,管理中依然存在一些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制約了以傳統技藝為依托的文物保護行業的高質量發展。對這些問題進行梳理整改,構建系統、健全的管理機制具有一定的迫切性。
一、文物修復檔案的重要性
文物修復在一定意義上如同醫生行醫,既需“行醫資質”,又需一套規范的“醫療檔案”記錄機制。二者缺一不可,共同守護文物的“生命線”。文物保護修復檔案類似“醫療檔案”,是專屬文物的“病例”資料。規范管理的文物修復檔案能夠完整地反映文物被修復干預的細節,為此后的典藏、保護、研究提供完整的“病史”資料,以便采取有據、恰當的應對措施。因此,文物修復檔案被立法確認為藏品檔案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其檔案屬性有著明確的法律確認[1]。規范文物修復檔案管理,可以加強職業規范,預防不當修復,貫徹保護理念,深挖文物價值內涵,提升文物保護與研究的水平,增強文化傳播效能。有鑒于此,博物館文物修復檔案的重要性理應得到充分認識,其在博物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也應得到充分發揮。
(一)有利于加強職業規范,保障文物安全
文物修復檔案具有“原始記錄性”這一檔案的本質屬性[2],這使得它具有修復行為合理性與合法性的證明力;反之,當不恰當的修復行為發生時,它又成為逆向追溯的直接依據。因此,對其加強規范與管理,有助于加強文物修復從業人員的職業自覺,推進養成規范、良好的職業習慣,改善文物保護修復的安全環境。
(二)有利于規范修復管理機制,促進科學保護
博物館有健全文物修復管理制度的法定義務[3]。科學的修復檔案文本內容設置,可以對應分解和規范保護修復工作的各個步驟,成為規范修復工作管理機制的重要輔助,促進文物的科學保護。
(三)有利于貫徹保護理念,促進科學研究
我國的文物保護(如書畫、青銅器、木漆器等)往往依托于傳統的修復技藝,部分傳統修復理念對保護實踐依然有著深刻影響。傳統修復更加注重恢復文物的完整性,傾向追求文物的藝術價值。新時期的保護理念則追求“三大價值”(歷史價值、科技價值、藝術價值)的全面保護和科學保護。規范的文物修復檔案可以詳細記錄保護干預對歷史信息的擾動,這是必要情況下進行逆向操作的精確指南,也是未來在文物研究過程中準確甄別各項理化信息的科學依據,從而避免文物研究受到修復干預中物質交換等因素的干擾,保障文物研究的科學性,促進保護理念的貫徹。
(四)有利于積累數據資源,促進高質量發展
規范的文物修復檔案是一座蘊藏大量信息資源的寶庫,其內容包括文物的基本信息、歷史修復記錄、檢測分析數據、保護修復的時間和環境、技術路線、干預措施、保護日志、使用材料及其制備與工藝流程、保護前的病害情況、保護后的文物面貌等豐富信息。經過一定積累,文物修復檔案可以積微成著,形成寶貴的數據資源庫。這是借以總結改進保護修復技術的重要知識庫,也是以新材料為代表的、能夠迅速實現成果轉化和提高技術生產力的科研線索的寶庫,對博物館的高質量發展大有裨益。
二、文物修復檔案記錄機制作為文物修復準則的確立歷程
(一)國際文物修復準則的確立
國際文物修復理論的發源地無疑是意大利。1693年前后,意大利畫家卡魯羅·馬拉塔(Carlo Maratta)在修復梵蒂岡法路奈吉那回廊濕性壁畫時,運用“添筆”并重繪缺損部位,為保證修復部位與原作可以識別,馬拉塔詳細記錄了修復行為[4]。這大抵是近代文物修復中首次開展的具有檔案意義的記錄活動。18世紀,在啟蒙運動(The Enlightenment)的推動下,整個社會對科學與技術的熱情日漸高漲,關于文物古跡修復的深層討論日益升溫,近代意義的修復概念逐漸萌生,“18世紀大多數修復作業被記錄和保留了下來”[5]。值得一提的是,18世紀后半葉開始,行政力量開始介入古跡文物修復的管理,比如,1773年意大利威尼斯設立“公共繪畫審查官”制度,對特定修復對象加以修復授權約束;1778年又設立“公共繪畫修復監督官”,對修復過程加強監管[6]。公權介入使行政文書更加規范,直接推動了修復預備、修復行為、修復過程管理等各環節文書的改進。19世紀,國際修復實踐繼續在爭論中前行,例如是否應遵循可識別的原則、修復對象的“原品性”是否應被充分尊重、繪畫修復中是否應避免“添筆潤色”一類干預等,都是討論的焦點[7]。這些討論進一步豐富了國際文物修復的理論體系,但距產生國際共識還有很長的路。
直至20世紀60年代,意大利文物與藝術品保護專家切薩雷·布蘭迪(Cesare Brandi)的經典論著《修復理論》(Teoria del Restauro)問世,以其廣泛、深刻的影響迅速凝聚了文物修復界的廣泛共識。1964年,意大利威尼斯第二屆歷史古跡建筑師及技師國際會議(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Architects and Technicians of Historic Monuments)決議通過《威尼斯憲章》(Venice Charter),首次以國際憲章的形式確立了歷史文物建筑的修復檔案記錄準則,并明確規定“一切保護、修復或發掘工作永遠應有用配以插圖和照片的分析及評論報告這一形式所做的準確的記錄。清理、加固、重新整理與組合的每一階段,以及工作過程中所確認的技術及形態特征均應包括在內”[8]。1972年,意大利公共教育部通告發布《意大利修復憲章》(Carta Italiana del Restauro Norme del Consiglio Superiore di Antichita e Belle Arti per il Restauro dei Monumenti),在更為廣義的文物概念下,對文物修復檔案作出明確規定:“應事先對所有干預措施進行研究,并以書面形式說明理由,整個干預過程應按日期做好記錄。此外,對于在物理、化學、微生物和其他學科輔助下進行的所有研究與分析要做好記錄。所有這些文獻記錄的副本應提交相關主管部門留檔保存”[9]。此后,對文物修復過程進行全面的檔案記錄逐漸成為國際文物修復的基本準則。
(二)我國相關立法的淵源與發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我國博物館事業的發展深受蘇聯的影響。1957年出版的《蘇聯博物館學基礎》曾對我國博物館的各項工作產生廣泛、深刻的影響。其中,在關于藏品的科學編目方面,此書提出“要指明對博物館藏品進行修復的所有階段”,并“可以”在附注中“記載對物品進行修復或修理的資料”[10]。這是我國關于文物修復檔案最初的理論指導文獻。
1978年1月,《博物館藏品保管試行辦法》發布,明確提出一般藏品檔案除包括編目卡片外,還包括“動態記錄等一切有關資料”。按照這一規定,文物修復記錄資料自然也在其列。這是文物修復檔案的相關規范首次在立法層面得到支持。同時,《博物館藏品保管試行辦法》還規定博物館在進行藏品修復時,“修復前要做好照像記錄,修復過程中要做好配方、用料、工藝過程等記錄。一級藏品的修復必須經館長批準,由領導、群眾和專門技術人員共同制定修復方案,事后整理出修復總結,歸入一級藏品檔案”[11]。
1982年1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公布施行,規定“全民所有的博物館”對所收藏的文物必須“設置藏品檔案”,并“建立嚴格的管理制度”[12],但并未就藏品檔案與文物修復檔案的關系,以及藏品檔案的文本內容作進一步的規定。1986年6月,文化部(今文化和旅游部)發布《博物館藏品管理辦法》,進一步拓展并規范了修復資料歸檔管理的內容。如規定在藏品修復前后,不僅要做好照相記錄,還要做好“測繪記錄”,并且“應由有關專家和技術人員制定修復方案”;重申修復中“要做好配方、用料、工藝流程等記錄”,修復完成后,這些資料“均應歸入藏品檔案”[13]。至此,我國關于文物修復檔案的法治體系初步建立。2003年7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實施條例》進一步規定,“保管國有文物”的國有事業組織應建立“文物藏品檔案制度”和藏品的“保養、修復”等管理制度[14]。國家開始在法律與政策層面加強引導,以激發博物館制度建設的主動性,文物修復檔案的規范化邁入“建章立制”的新階段。
三、我國博物館文物修復檔案管理機制的探索和實踐
在200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實施條例》的指引下,國內博物館界開始著力推進文物修復制度的建設,這與文物修復檔案的規范管理息息相關。一系列內部管理辦法相繼施行,但多數博物館文物修復制度建設的重心在于文物修復過程的安全管理,重點強調修復場地人員進出、修復期間文物安全防護、危險化學材料使用等安全風險管控。這本無可厚非,畢竟規范修復管理機制的初衷就是保障文物安全,但彼時對于文物修復檔案的認識還不夠系統與深入,即使偶有涉及文物修復檔案資料的規定,也失于零散或不夠系統,明確且具行業影響的制度范例依然少見。
2007年,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故宮”)開始試行“文物修復檔案管理制度”。故宮的文物修復檔案管理在制度設計上起于文物的接收,終于文物的返還。按照文物修復預備、實施、總結三個階段,將修復檔案的管理對象確定為11項文本資料:首頁(文物送修記錄)、修前照片、修前繪圖、原件材料分析、原件制作工藝描述、修復(復制)方案、修中照片、工作記錄、修復報告書、修后照片以及文物提取記錄書。“首頁(文物送修記錄)”基本涵蓋文物送修時所具的全部信息,尤其是文物的歷史背景、損傷狀況、送修原因等。“修前照片”和“修前繪圖”兩項為反映文物修前保存狀況的記錄資料。“原件材料分析”為文物主體、附屬裝飾、附著物(包括修復粘接劑)等諸項的材質分析信息。“原件制作工藝描述”為反映文物制作方法的資料。“修復(復制)方案”為修復實施前的預定“方法與計劃”。“修中照片”和“工作記錄”兩項為修復實施過程的全面記錄資料,重點記錄對象為“措施”“方法”“設備”“材料”。“修復報告書”為修復過程的梳理與總結資料,主要包括三個記錄描述的重點:一為修復的過程、方法、位置改動,二為使用材料,三為“存在或需要進一步解決的問題”。“修后照片”為修復后文物狀態的記錄資料。“文物提取記錄書”為文物返還程序的記錄資料[15]。
故宮文物修復檔案管理制度無疑遵循了文物修復管理工作的一般邏輯,具有很好的示范與參考意義。緊隨其后,在博物館評級標準與國家級博物館認定條件相繼就相關制度建設提出明確要求的背景下,故宮文物修復檔案管理制度對我國博物館文物修復檔案的規范管理產生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它不僅確立了一套較為規范的文物修復工作機制,并且在立法規范的基礎上,進一步充實并確立了文物修復檔案的文本內容,為文物修復檔案的規范管理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此后,我國在陸續頒行國家推薦性行業標準時,基本吸收了其文本內容架構。但我國博物館在文物修復檔案管理和利用機制的探索過程中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較為偏重文物修復檔案的記錄環節,而沒有完全遵循檔案管理工作的一般規律;忽視了文物修復檔案的整理、鑒定、保管、統計、利用等管理環節,當然這也反映了整個行業的階段特點。
從目前國內博物館界的探索和實踐來看,關于文物修復檔案的資源整合與利用,業界基本形成較為一致的認知,主要思路是借力博物館信息化建設的趨勢,通過構建數字管理平臺來細化工作流程、規范文物修復過程管理,在此基礎上建立文物修復檔案的數字資源庫,依靠便捷的檢索查閱功能和強大的數據分析技術,突破紙質檔案在記錄載體、借閱、查詢等方面的效率瓶頸與其他制約,從而滿足博物館各個層面的工作需求。具體到平臺建設上,各博物館存在路線的差異。
以南京博物院(以下簡稱“南博”)的探索為例。南博將文物修復數字檔案的管理整合到文物庫房全流程管理線上平臺。在藏品管理子系統中建立“修復保護”模塊,模塊下設“修復過程管理”與“查看修復過程管理”兩個子菜單。“修復過程管理”菜單列出文物的編號、名稱、時代、質地、藏品等級、完/殘程度等信息,狀態欄可顯示文物修復前的圖片資料以及文物當前所處的修復狀態,“在修”文物標注有修復人員信息,“已修畢”文物則注明修復時間。“查看修復過程管理”菜單設有更為詳盡的子信息欄,主要分為“基本信息”“修復前圖片”“修復中圖片”“修復后圖片”“分析檢測附件”。“基本信息”除包括文物編號、名稱、年代、保存狀態、完/殘程度、質地類別、藏品級別、具體尺寸、藏品來源等信息外,多以文字形式反映文物修復的全過程,內容包括:修復人、修復時間、修復地點、修復環境、修復材料、運用設備、修復前狀況描述、修復中狀況描述、修復后狀況描述、分析檢測報告、備注等。圖片信息欄則以圖片資料的形式分別反映文物修復前的病害保存狀態、修復中的過程細節和修復后的保護效果。“分析檢測附件”附有各項分析檢測的具體信息。從系統功能看,線上“修復保護”模塊基本實現了文物修復過程的動態跟進記錄,實現了文物修復檔案的完整數字化。系統信息專人專責,定期維護,保障了文物信息的時效性。此外,通過登錄賬號性質分配使用權限,大大提高了文物修復檔案使用的便捷性,同時也為文物典藏、文物研究、展覽籌備等相關工作提供了便利[16]。
山西博物院也作了類似的探索。他們在“信息化發展規劃”的指引下,以智慧博物館建設為導向,在統一的集成系統中,構建可移動文物保護修復數據庫管理服務平臺子系統。其突出特點是將管理范疇從文物修復過程本身向前、向后延伸,以項目為單位實施全流程管理,讓系統兼具一定的辦公自動化(Office Automation,OA)功能。在修復數據的處理與利用上,一方面拓展了Word、TCS、TDS等類型文件的導入功能,以及Excel、PDF等格式文本的導出功能;另一方面在檔案數據的存儲上采取分區化處理方法,提高了數據篩選與分析的效率[17]。
上海博物館則建立了“文物修復檔案管理系統”。從系統命名看,管理對象非常明確。系統以檔案的記錄、內容與形式的規范、檔案的利用三個核心功能的實現來設定“檔案建立人員”“檔案審核人員”“研究工作人員”的相應職責權限;同時有效依托信息化手段,建立了線下、線上相結合的文物修復檔案管理機制。該系統的突出特點是豐富了文物檔案的記錄形式(圖片、音頻、視頻皆可),信息采集囊括“工作日志”。在修復數據的處理與利用上,又類分出文物修復元數據(“抽象出的復雜數字資源的屬性數據”),增加了數據檢索的深度[18]。
總的來看,文物修復檔案的整合重點在于檔案信息的采集深度,利用重點在于數字資源的管理深度和共享程度。尤其是在檢測分析數據部分,關鍵在于如何實現樣本與數據的有序持續積累,不斷挖掘數據管理與分析的深度,從而實現更大范圍的交互共享。
四、當前我國博物館文物修復檔案管理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制度方面
1.自主構建制度,管理水平參差不齊
在現行機制下,博物館的文物修復檔案管理并沒有一套自上而下的專門制度設計,博物館主體在制度構建上有較大自主性。由于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博物館微觀管理生態、自身發展歷史與定位等差異,各館制度建設的步調與管理水平并不一致。制度建設不夠系統,流于形式的現象不在少數。少數博物館依然存在制度空白、管理缺位的問題,以至于文物修復還停留在管理無序的狀態,沒有任何可供追溯、查詢的修復記錄。
2.偏重記錄環節,管理機制不夠系統
檔案管理的業務流程一般包括收集、整理、鑒定、保管、統計、利用等步驟。基于文物修復檔案的特殊性,其管理流程還應加上“記錄”這個環節。目前,立法規范與行業標準體系均側重于記錄,這一環節的管理機制相對完善。但整理、鑒定、保管、統計、利用環節的管理,尚未得到應有的重視,存在管理機制缺位的問題。修復檔案通常由修復人員記錄而成,由修復部門自行保管,定期向“本單位檔案機構或檔案工作人員移交”的機制[19]多數情況下并未在制度上得到確認或重申。這就在程序上破壞了文物修復檔案管理工作的連續性,違背了檔案保管的基本原則,也影響了后續的整理、鑒定、統計和利用等工作。從這個角度來說,系統的管理機制還未普遍建立。
(二)行業標準方面
截至2022年5月,我國現行規范文物修復檔案記錄的標準有推薦性國家標準和推薦性行業標準。前者分別為《館藏金屬文物保護修復記錄規范》(GB/T 30687-2014)、《館藏磚石文物保護修復記錄規范》(GB/T 33289-2016)、《古代壁畫保護修復記錄規范》(GB/T 30235-2013),后者分別為《館藏出土竹木漆器類文物保護修復檔案記錄規范》(WW/T 0011-2008)、《館藏絲織品保護修復檔案記錄規范》(WW/T 0015-2008)、《陶質彩繪文物保護修復檔案記錄規范》(WW/T 0023-2010)、《館藏紙質文物保護修復檔案記錄規范》(WW/T 0027-2010)。然而,博物館藏品門類較為豐富,僅按文物的材料,即可分為金、銀、銅、青銅、鐵、玉、石、陶、瓷、絲、毛、棉、麻、皮、骨、角、牙、木、竹器等幾十類[20],兩相比較,我國現行規范文物修復檔案記錄的標準遠非完備,一定程度制約了修復檔案記錄的文物范圍。
(三)管理流程方面
1.記錄環節:內容、載體和人員培訓有所欠缺
(1)記錄內容不完整
文物修復檔案產生過程中,由于修復工作工序多、周期長,密集操作期間難以時時記錄,容易出現忘記、補記、誤記等情況。修復人員習慣于集中精力進行修復作業,而兼顧檔案記錄會頻繁分散注意力,主觀上會有排斥情緒,容易出現怠慢、漏記、粗疏等問題。當制度訂立的標準低于行業標準時,還經常出現系統性的內容缺失。此外,先修復后補記檔案的現象也時有發生,通過追憶編造修復記錄等行為往往會造成檔案資料的失真。
(2)記錄載體過于單一
記錄載體停留在文字與圖片的情況依舊比較普遍,事實上我國在博物館學理論探索的較早階段即已提出豐富的檔案記錄形式,包括照片、拓片、測圖(結構、解剖、復原、花紋、裝飾展示等圖)以及錄音、錄像等[21]。隨著博物館檔案管理工作信息化建設的推進,文物修復檔案記錄載體宜多做加法,逐步豐富。
(3)記錄人員欠缺專業培訓
從行業現狀看,文物修復檔案記錄普遍由修復人員執行,而非專業的檔案管理人員。修復人員大多沒有接受系統的檔案工作相關培訓,對檔案工作缺乏深入理解,必然影響修復檔案的質量。
2.收集環節:收集工作不及時
及時的收集工作可以有效敦促記錄人員完成和整理相關資料記錄,確保文物修復記錄的規范與真實。管理中有時會因為收集不及時而出現檔案記錄不完整、不規范甚至檔案造假的現象。比如一些大型修復項目,涉及文物有時多達數百件,任務繁重且工作周期較長,如不能時時敦促和及時收集,很大程度上會影響修復檔案的總體質量。
3.鑒定環節:缺少必要的審核
文物修復檔案的收集應遵循檔案工作的基本要求:在形式上,必須是完整、齊全、真實、文字圖片清晰的原始記錄材料(電子記錄的打印材料必須是原始署名材料),載體規格也應符合規范;在記錄內容上,應遵守單位制度確立的標準,完整、規范、真實。但在管理實踐中,由于認識不足或把關不嚴,文物修復檔案收集有時會忽視以上要求;此外,對不符合歸檔要求的材料,沒有及時責成相關人員依規整改,導致檔案在形式或內容上出現種種失范問題。
4.保管環節:違反回避原則
各博物館落實檔案管理的責任機制不同,對文物修復檔案的重視程度不一。部分博物館受人力資源限制,專職檔案管理人員無法配置到位,加之管理機制未能明確檔案移交程序,因而會出現由修復人員兼職修復檔案保管員的現象。這既有違檔案管理“定期移交”與“集中管理”的法律準則[22],也違背了《事業單位人事管理回避規定》中關于履職回避的規定[23],損害了文物修復檔案的權威性。
5.統計利用環節:工作開展不夠充分
文物修復檔案屬于記錄文物修復過程的專門檔案,具有重要的資源屬性。意大利在20世紀30年代創建中央修復研究院時,即籌劃建立中央修復檔案館,以滿足各種總體性研究的需要,最大限度地吸取經驗與教訓,從而協調修復準則,完善修復方法,并為具體修復工程提供技術咨詢和成套資料借閱。相較于國外博物館的實踐,目前我國業界對于文物修復檔案的統計深度相對有限,檔案利用的頻率與效率并不高,文物修復檔案的資源潛能尚未充分開發。
五、加強博物館文物修復檔案規范管理的路徑與建議
(一)加強立法與監督,提高博物館制度建設與管理的積極性
法定義務是博物館法人推進管理工作的根本動力。現行法規雖有一定規范,但在核心文物保護法規中,“文物修復檔案管理制度”并未作為法定義務得到明確直接的立法確認。因此,立法層面仍有完善空間。此外,每年一度的國家級博物館運行評估和三年一度的博物館等級評定及復核,都是監督和促進博物館改進工作的重要抓手,如能在相應評估評定環節增加文物修復檔案管理的相關評估內容與評分權重,將對提高博物館文物修復檔案的管理工作產生積極促進作用。
(二)主動完善制度設計,建立系統管理機制
業界應充分認識文物修復檔案管理機制對于文物安全及博物館管理工作的重要性,主動完善制度設計,盡快建立包括記錄、收集、鑒定、保管、利用等環節的系統管理機制,有針對性地解決管理工作存在的突出問題。
1.記錄環節
可以參照行業標準構建文本內容框架(寧做加法、不作減法),以制式表格的形式明確各部應記內容與規范。圖片及其他記錄形式應明確格式與內容要求,形成統一體例。嚴格規定各部內容完成記錄的時間節點。通過恰當的培訓,提升記錄人員的檔案認知,培養必要的技能技巧,減少工作阻力。可結合單位實際,進一步豐富記錄載體,信息化程度較高的博物館可以結合數字平臺建設構建記錄與管理體系。
2.收集、鑒定環節
可建立文物修復檔案的定期、不定期核查機制。在檔案產生過程中就積極干預,加強監管。嚴格按時間節點,逐項收集,以確保檔案記錄及時、真實、完整。可在收集的同時,結合開展審核鑒定工作,從而及時發現檔案文本在形式與內容上的失范問題。收集人員應嚴格執行制度規定,對不符合規范的資料,要及時提出整改要求,杜絕囫圇接收,對不能更正的問題也應標注必要的說明。
3.保管環節
應加強檔案的定期移交機制,定期向單位檔案管理機構或專職檔案工作人員進行移交。沒有檔案管理專門機構或專職檔案工作人員的,檔案保管應嚴格執行回避原則。應參照檔案管理相關標準,設置專用庫房,建立規范的查詢與借閱程序,確保檔案資料的安全與權威性。
4.統計利用環節
文物修復檔案的整理統計應以病害問題為導向,以技術性資料為重點,以分期、器物類別等要素為緯度,進行多元化的科學編目,以便后續利用。原始的文物修復檔案資料在統計利用上有很多局限,如果未經數字化,統計利用是比較困難的。因此,數字化基礎上的數據分析技術才是文物修復檔案統計利用的未來。在數字化建設方面走在前列的博物館可以充分發揮技術優勢,優化數據統計與分析,提高文物修復檔案使用的便捷性。
(三)創新互鑒,擴大修復檔案記錄機制的文物覆蓋面
博物館在落實國家標準、行業標準的過程中,應提高能動性,舉一反三,加強制度創新。可以在體例上借鑒已頒行的行業規范,為沒有相應標準的文物類別建立修復檔案的記錄規范,將修復檔案的記錄范圍覆蓋到所有館藏品修復。
博物館的文物修復檔案在重要性上并不亞于人事、財務等行政檔案,從保障文物安全的角度講,其重要性更甚。因此,博物館不僅在制度層面上,更應在思想觀念上對文物修復檔案的管理和利用予以足夠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