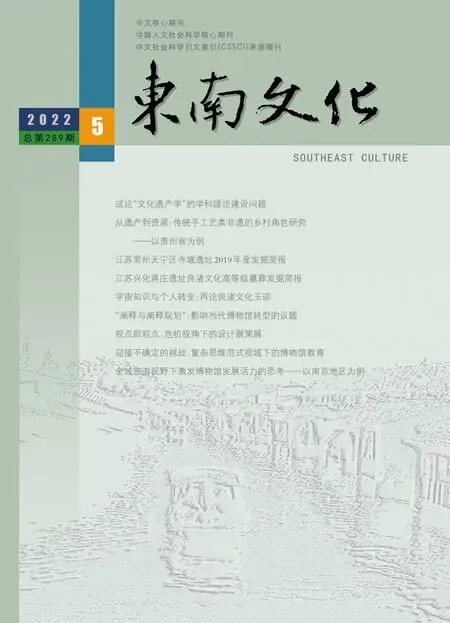“闡釋與闡釋規劃”:影響當代博物館轉型的議題
周婧景
(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 上海 200433)
內容提要:博物館需關注兩方面問題:依托博物館物的信息傳播、觀眾基于信息傳播的實際獲益。后者長期被忽視但重要性卻與日俱增,因此闡釋學這一旨在提升信息傳播中觀眾獲益的新議題被引入博物館領域。由于闡釋學的要義是鼓勵人們在更好地理解的基礎上創建個人意義,所以其將成為影響我國博物館由藏品導向向公共服務導向轉型的核心議題。目前北美博物館界已對這一問題給予高度重視并積極踐行。闡釋學的理論基礎主要源自哲學詮釋學和建構主義教育學。我國在引入闡釋學以推動博物館轉型的過程中面臨著理念、技術與制度三大困境,據此提出包含主題性、舒適性、組織性、相關性、趣味性、評估性六大要素的博物館闡釋模型,進而設計闡釋規劃的內容框架,以期從理論和方法上探尋中國博物館當代轉型的破解之道。
博物館說到底需關注兩方面問題:依托博物館物的信息傳播、觀眾基于信息傳播的實際獲益。但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們只是將前者視為博物館工作的全部重心所在,不僅如此,依托博物館物的信息傳播仍主要是以機構為本的信息傳播。公共博物館誕生之初,政府預算充足,博物館只要坐擁珍貴館藏、亮相家底,就能過上“養尊處優”的安樂日子[1]。當時博物館的主要職責是藏品而非觀眾[2],基本屬于純收藏研究機構。但自19世紀末起,博物館在經歷三次革命性運動后,逐步由純收藏研究機構蛻變為真正意義上的社會開放機構。首次革命始于19世紀晚期,到20世紀20年代發展至頂峰,后人將其稱為“博物館現代化運動”[3]。這場運動促使博物館社會職能初露鋒芒,但多數情況下其仍被認定是展示實物的場所。20世紀中后期,國際博物館界又相繼醞釀了兩場革命,均以美國為首并席卷全球,前一次是由內向型運營形態向外向型運營形態轉變[4],后一次則預示著觀眾的崛起以及對其的倡導[5]。此時,最大限度地為公眾提供服務成為博物館業務的重中之重[6]。基于此,博物館逐步擺脫窠臼,“不再僅是事實和想法的傳播者,而是致力于提供機會讓觀眾探索和塑造個人的世界觀和經驗”[7],實現了當代轉型和范式轉移。
如果說此前的博物館理應重視依托博物館物的信息傳播,那么時至今日博物館更應關注觀眾在信息傳播中的實際獲益,后者經由三次革命已成為評判博物館當代價值的重要標尺。這一背景下,旨在提升信息傳播中觀眾獲益的闡釋學被引入博物館領域,因為其要義是鼓勵人們在更好地理解的基礎上創建個人意義。正如山姆·哈姆(Sam Ham)所言,“闡釋不是魔法,也不是一套違背邏輯的花招和噱頭”[8],而是一套觀眾理解博物館的行之有效的理論方法。盡管闡釋行為如同人類的溝通一樣古老[9],并且自20世紀50年代起便肇興于自然資源、娛樂和公園、休閑的研究,闡釋服務和環境教育等多學科[10],但對博物館界而言,它依然屬于一個全新的議題,并將成為影響當代博物館轉型的核心議題。目前北美博物館界在闡釋和闡釋規劃的研究和實踐上已漸進趨熱[11]。鑒此,筆者在厘清闡釋及其規劃的定義和理論依據的基礎上,破析其在推動我國當代轉型中所遭遇的困境,并提出解決之道。如何從理論和方法上為我國博物館轉型尋找出路,始終是當前學界和業界共同面臨的難題,筆者認為闡釋及其規劃是破解該難題的關鍵議題,有望成為撬動我國博物館當代轉型的一個支點。
一、博物館領域的闡釋、闡釋規劃及其理論基礎
將闡釋學引入博物館領域,某種程度上意味著博物館對觀眾及其獲益的關注已從一種潛在的碎片化探索,上升至系統化的主流倡導。事實上在博物館開展闡釋研究前,教育人員、心理學家等都已開始探討觀眾在博物館信息傳播中的獲益問題。1889年,實踐型科學家喬治·布朗·古德(George Brown Goode)發表《博物館與未來》(The Museum and the Future)演講時,主張將博物館從收藏小古玩的“墓地”變為一個培養活躍思想的“保育室”[12]。1917—1920年,約翰·科登·達納(John Cotton Dana)出版“新博物館系列”(The New Museum Series)四本書,論及建立“用戶中心”的博物館,主張像吸引專業和休閑人士一樣吸引藍領工人[13]。1935年,心理學家亞瑟·梅爾頓(Arthur Melton)采用增加畫廊畫作數量的辦法,來檢測因畫作數量的增加而造成的平均觀看時間的變化[14],并就出口設置與觀眾參觀時長的關系展開實驗研究,提出觀眾的“右轉傾向”[15]。可見,博物館領域以藏品為中心的研究傳統正在發生改變,這種改變的集中爆發期是在20世紀70年代后,此時有關教育和觀眾研究的文獻無論是在數量還是質量上均獲得突破性進展,成為當代博物館研究蔚為壯觀的一道風景[16]。在這一趨勢流變下,通過有效溝通來實現個人意義構建的闡釋學,逐步進入博物館學視域并成為富有思想沖擊力的新議題。那么究竟何謂闡釋、闡釋規劃,其是否具備相應的理論基礎,諸多問題亟待我們探索與解答。
(一)博物館領域的闡釋界定
博物館領域有關闡釋的文獻,最早可追溯至1957年,呈現兩大特點:從文化遺產進入博物館領域,從其教育活動波及主要業務[17]。關于闡釋的定義,學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筆者認為其中最具權威性的有三個。第一個由弗里曼·蒂爾登(Freeman Tilden)提出:“闡釋是指一種教育活動,旨在通過使用原始對象、第一手經驗和解釋性媒體來揭示意義和關系,而不僅僅是傳達事實信息。”[18]在蒂爾登看來,闡釋其實是一種溝通,目的是揭示意義和關系以幫助訪客實現自我構建。該內涵的界定鞭辟入里,影響至整個文博領域日后與闡釋相關研究的話語體系,并在近三十年的研究中不斷得到印證。第二個權威定義由美國國家闡釋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Interpretation)[19]提出:“闡釋是一個以任務為基礎的溝通過程,在受眾的興趣和資源固有的意義之間建立認知和情感聯系。”[20]此定義揭示出闡釋的內核是讓資源與受眾建立聯系,并明確闡釋即為一種溝通方式。2013年哈姆以美國國家闡釋協會的定義為藍本,并借鑒蒂爾登的目的論,提出:“闡釋是一種基于使命的溝通方式,旨在激發受眾發現個人意義,并與實物、地點、人和概念建立個人聯系。”[21]從該定義中可獲悉,哈姆同樣肯定了闡釋就是一種溝通方式,同時圍繞溝通問題,吸納了美國國家闡釋協會的任務構成和蒂爾登的目的主張,并增補了任務導向。盡管這些定義具備排他性的穩定要素,但主要適用于美國國家公園等自然資源機構。博物館雖與之同屬非正式學習場所,但在傳播載體上有所不同,為特定空間內對物載信息的形象傳播。因此,盡管兩者指向的內涵趨同,但實際略有差異。筆者曾撰文指出,博物館領域的闡釋是指采用某種溝通媒介,向觀眾傳播藏品及其相關信息以促使觀眾參與的過程[22]。但目前看來,該定義在突顯觀眾主體性,特別是在參與方式和目的上稍顯不足。因此,筆者主張將定義修正為:一種立足博物館使命的溝通過程,在該過程中博物館依托博物館物與觀眾建立聯系,促使其構建個人意義。此處的博物館物既包括文化文物系統博物館中具備三度空間的實物展品和用以揭示其信息的輔助展品,也包括科技類、非物質文化遺產類等博物館中再現過程化現象[23](通常針對非物質信息)的設施設備。從闡釋概念中不難發現,觀眾不再是權威事實或觀點的被動接受者,而成為個人意義的主動構建者,但該意義也可能是不在預期范圍內的全新意義。
(二)博物館領域的闡釋規劃界定
闡釋規劃的相關討論始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伴隨美國境內兩大現象的出現而生成:公眾開始重視環境并獲得認知提升,聯邦立法授權公眾參與土地使用的規劃和決策[24]。典型代表為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U.S.National Park Service),其闡釋規劃的輝煌期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25]。例如,1965年,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首部《闡釋規劃手冊》(Interpretive Planning Handbook)問世;1988年,強化闡釋規劃目標的《闡釋的挑戰》(The Interpretive Challenge)付梓;1996年名為《闡釋規劃》(Interpretive Planning)的《闡釋和游客服務指南》(A Guideline for Interpretation and Visitor Services)出版,提出針對公園的綜合闡釋規劃(comprehensive interpretive plans),包括長期闡釋規劃(a long-range interpretive plan)、年度實施規劃(annual implementation plan)和闡釋數據庫(interpretive database)。可見,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在闡釋規劃方面獨領風騷,因此數以百計的戶外休閑和自然資源機構等后來者紛紛追隨,相繼仿效制訂闡釋規劃。由于博物館與此類機構性質類似,都旨在達成非正式環境中的學習,所以也躍躍欲試。2005年,美國博物館聯盟(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在印第安納波利斯(Indianapolis)組織了一場全國性博物館闡釋規劃座談會[26],會議圍繞博物館闡釋規劃的內容和實施展開討論,但遺憾的是最終并未出臺任何官方意義的文件。隨著麗莎·布羅許(Lisa Brochu)的《闡釋規劃:成功規劃項目的5-M模型》(Interpretive Planning:The 5-M Model for Successful Planning Projects)和約翰·維佛卡(John Veverka)的《闡釋總體規劃》(Interpretive Master Planning)等專著的誕生,博物館領域的闡釋規劃開始沿用環境教育、休閑研究和闡釋服務等領域的闡釋框架。
就博物館闡釋規劃而言,其研究史中最為標志性的事件無外乎2008年由《博物館教育雜志》(Journal of Museum Education)策劃的《博物館闡釋規劃》專刊。該雜志在第33卷第3期推出了名為“機構的各種闡釋規劃”(Institution Wide Interpretive Planning)專題,分別從綜合和總體闡釋規劃、轉型與闡釋、整合闡釋規劃、闡釋規劃的內容、評估及資源等方面展開探究。同時相關著作接連問世,并經歷了由著作的內容構成到圍繞該專題著書立說、由少量提及到高度聚焦討論的發展歷程。首先是闡釋規劃在著作的部分章節有所涉及。如1994年首版的《博物館手冊》(The Handbook for Museums)于第10—12章討論了一般闡釋、特定對象的闡釋和博物館教育[27];2005年出版的《吸引人的博物館:為觀眾的參與開發博物館》(The Engaging Museum:Developing Museum for Visitor Involvement)一書,在第四部分《參與的規劃:利用闡釋發展博物館陳列及相關服務》論述了有效闡釋在博物館展示中的作用[28];2006年面世的《博物館文本:交流框架》(Museum Text:Communication Frameworks)探討了文本如何通過恰當的語言選擇、觀點表達等與觀眾有效溝通;2007年編著的《原則與實踐:作為學習機構的博物館》(In Principle,In Practice:Museums as Learning Institution)一書的第二部分《讓受眾參與有意義的學習》包含有針對科學教育的闡釋規劃[29];同年《創造偉大的觀眾體驗:博物館、公園、動物園、花園和圖書館指南》(Creating Great Visitor Experience:A Guild for Museums,Parks,Zoos,Gardens,&Libraries)問世,啟發我們思考博物館如何設計受歡迎且更具價值的觀眾體驗[30];2021年的新作《闡釋遺產:規劃和實踐指南》(Interpreting Heritage:A Guide to Planning and Practice)在第三章專門論述了闡釋規劃[31]。其次,博物館界出現聚焦闡釋規劃的專門出版物,如2003年蘇格蘭博物館委員會(Scottish Museums Council)推出《闡釋規劃導論》(Introduction to Interpretive Planning)、《有效闡釋規劃的規劃》(Planning for Effective Interpretive Planning);2013年瑪塞拉·威爾斯(Marcella Wells)等人的專著《博物館的闡釋規劃:在決策中融合觀眾的視角》(Interpretive Planning for Museums:Integrating Visitor Perspectives in Decision Making)問世,主張對觀眾體驗做出規劃,同時將觀眾研究整合至闡釋規劃中[32]。
綜上,闡釋規劃已悄然被引介至博物館領域,并逐步在各項工作中掀起波瀾,但尚未蔚然成風,主流研究和做法仍是追隨環境教育、休閑研究、闡釋服務等領域。那么究竟何謂闡釋規劃?盡管其定義遠不及闡釋那么明確清晰,但筆者仍試圖對其進行梳理和廓清。根據出處的專業性和領域的相關性,筆者同樣選擇了三個較為重要的觀點。一是來自美國全國闡釋規劃座談會,該會將闡釋規劃界定為“一份書面文件,該文件概述了博物館希望通過各種媒介(如展覽、教育和出版物)傳達的故事和信息。它可能包括該機構的闡釋理念、教育目標和目標受眾”[33]。二是出自《闡釋規劃:成功規劃項目的5-M模型》一書,其認為闡釋規劃是指“將管理需求、資源,與游客的愿望和支付能力(時間、興趣和/或金錢)結合起來考慮的決策過程,以確定向目標市場傳達信息的最有效方式”[34]。三是威爾斯等在汲取先賢觀點的基礎上,提出博物館闡釋規劃是指“一個深思熟慮、系統化的過程,用于以書面的形式思考、決定和記錄教育和闡釋計劃,目的是為觀眾、學習機構和社區提供有意義和有效的體驗”[35]。可見,上述觀點分別將闡釋規劃視為一份文件或一個過程,但都旨在將受眾和機構資源相結合,使其傳播的信息能對觀眾有效和有意義,事實上它們都是機構系統規劃的結果。筆者在采擷這些觀點內核的基礎上,結合中國語境提出博物館的闡釋規劃是指“一份書面文件(有時是一個過程),是博物館基于使命的系統化決策結果,該文件思考、決定、記錄如何借助各種媒介讓博物館物與觀眾建立聯系,以促使觀眾理解其傳播的信息并構建個人意義”。
(三)闡釋及其規劃的理論依據:“哲學詮釋學”和“建構主義教育學”
通過溯源可發現博物館闡釋及其規劃的理論基礎與多個學科相關,包括哲學、傳播學、發展和認知心理學、教育學、娛樂和休閑科學[36],它們都將為該議題的探索提供理論依據和方法借鑒。
首先,與其最具相關性的是“哲學詮釋學”。詮釋學(hermeneutics)是一門脫胎于圣經注釋和古典語文學,與神學、哲學、文學等學科有關的學說[37]。“詮釋學”這個詞出現較晚,大約在 17 世紀[38]。不過在西方歷史上,詮釋學的工作始終存在。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指出“此在的現象學就是詮釋學”[39],“只有通過詮釋,存在的本真意義和此在本己存在的基本結構才能向居于此在本身的存在之領會宣告出來”[40]。1960年,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在《真理與方法——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征》指出,哲學詮釋學探討的問題是理解和對所理解東西正確解釋的現象,而非精神科學方法論的一個特殊問題[41]。所以哲學詮釋學說到底是關于理解與解釋的理論。盡管19世紀德國哲學家弗里德里希·施萊爾馬赫(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威廉·狄爾泰(Wilhelm Dilthey)使詮釋學發展成為一個系統理論,但并未超出方法論和認識論性質的研究,尚屬于古典的或傳統的詮釋學[42]。然而海德格爾及其繼承者伽達默爾卻將該問題的討論引至本體論,轉而探討“理解是什么”。伽達默爾提出“詮釋學的動作總是這樣從一個世界到另一個世界的轉換,從神的世界轉換到人的世界,從一個陌生的語言世界轉換到另一個自己的語言世界”[43]。綜上,從哲學詮釋學的內涵和方法,可獲得對博物館闡釋的兩點認知:一是博物館物也屬于詮釋學探討的對象,因為詮釋學研究對象不但包括文本或精神活動,還被擴充至對歷史、藝術品和文化的處理;二是博物館闡釋的重點在于理解,涉及翻譯和解釋。翻譯是指把不熟悉的物的語言變成熟悉的人的語言;解釋是對晦澀難懂的內容的轉化,使其從陌生的世界進入熟悉的世界。通過翻譯和解釋,結果是語言或內容被理解,即“視域融合”。
其次,與“建構主義教育學”研究內容不謀而合。每一個體都是被社會化塑造的社會結構的一部分,成為解釋學循環的生成力量,所以受眾擁有的新想法、概念及其意義是建立在現有知識和期望的基礎上,而這即為建構主義教育學所聚焦的問題。稍有不同的是建構主義教育學更側重主體本身,而闡釋學則重視兩者之間的關系處理,以實現資源如何更好地為主體所用。羅伯特·米爾斯·加涅(Robert Mills Gagne)和杰羅姆·布魯納(Jerome Bruner)指出外在信息和內部思維之間應建立“聯結”[44]。戴維·保羅·奧蘇貝爾(David Pawl Ausubel)對這種聯結作了深層探討,指出教師需要提供更為高級的陳述,關鍵是要在陳述者和學習者已有知識之間架起一座實現認知的“橋”[45]。20世紀初,弗雷德里克·巴特利特(Frederick Bartlett)創造的圖式(schema)概念對理解該理論具有推波助瀾的作用,是指對個人當前知識進行組織以便為未來理解創建框架。讓·皮亞杰(Jean Piaget)使用了該術語,認為圖式是針對物體的某些(生理的或心理的)動作的心理表征[46],是認知結構的起點和核心。他指出認知如同一個致力于平衡的自組織系統,主體若要同化一種新知識,必須讓其思維方式順應情境要求[47]。以上學者的觀點各有建樹,但同時也呈現出共同的局限,即把學習看作一種內在過程的結果[48]。與皮亞杰同時期的利維·維果斯基(Lev Vygotsky)就此進行補充,主張在社會文化框架下探究兒童的認知發展[49],外在環境因而得到重視。然而維果斯基的觀點直至20世紀60年代才引起美國心理學界關注。綜上,建構主義教育的優勢在于主張學習不是感官刺激在頭腦里留下的印記,也并非特定環境下的反射結果,而是一種主體自主的活動。由于該優勢尤其適合自由選擇的學習環境,所以博物館領域的學者先后對其展開討論并成為其擁躉者。1995年,洛伊斯·H.西爾弗曼(Lois H.Silverman)提出“意義創造”的概念,在博物館界引發轟動,主張應積極支持、促進和增強博物館中可能存在的多種意義,并將人的需求納入展覽目標和機構使命[50]。而將建構主義教育學引入博物館界的扛鼎之人是喬治·E.海因(George E.Hein),他在《建構主義博物館》(The Constructivist Museum)一文中指出,考慮到博物館觀眾的年齡跨度大,所以建構主義作為博物館教育的基礎尤為恰當。該理論要求我們將重點放在學習者身上而非學習的學科,這對博物館而言,意味著把重點放在觀眾而非博物館內容上,建構主義博物館主張使用個性化方法為各類學習者在頭腦中創造意義提供機會[51]。蓋亞·萊因哈特(Gaea Leinhardt)和明達·博倫(Minda Borun)等在研究中還強調了博物館空間及其體驗有助于促進家庭等的對話,以達成學習[52]。同時,我們也不能無視建構主義教育理論的缺陷可能對博物館闡釋產生的“危害”,主要表現為強化認知、弱化情感,強化內在、弱化環境,強化運算、弱化情境。
二、闡釋及其規劃在推動中國博物館轉型中遭遇的困境
既然闡釋及其規劃是博物館由藏品導向向公共服務導向轉型的有力推手,同時詮釋學和建構主義教育學也為其提供了扎實的理論支撐,那么為何該新議題在我國博物館界始終未迸發出強有力的生命力與沖擊力,進而引發熱議共鳴?筆者認為究其因,目前尚存在一些特殊困難。
(一)理念上:重視博物館物的信息傳播,而忽視觀眾基于信息傳播的實際獲益
隨著國際博物館界的理念由藏品中心向觀眾至上轉變,博物館不再是“為了收藏而收藏”,而是“為了公眾而收藏、研究、展示”[53]。被動參與變革的中國博物館雖也開始意識到這種轉變,但仍未通過重新調試來適應由公眾需求驅動的理念變革,根源在于我國“為物而物”的舊傳統與“人利用物”的新需求存在矛盾。這種矛盾導致觀眾與博物館物之間的親密關系被人為分割,博物館更在意的是對于物的呈現或物相關信息的輸出,而非觀眾能否從博物館物中獲益及其獲益程度。為解決該矛盾,我們應從理念上將“如何才能讓人更好地理解物”置于首位。
(二)技術上:我國博物館闡釋及其規劃方面的專業能力亟需提升
盡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博物館數量激增,展覽、社會教育等各項業務規模擴大,但多數情況下博物館對觀眾的受益情況不得而知。回顧“以觀眾為中心”理念的誕生歷程,我國基本停留在公共服務和傳播方式上的“以觀眾為中心”,還未真正企及深層,即在物及其所載信息的研究、轉化和重構中奉行“以觀眾為中心”。因此這方面的專業能力亟待提升,而闡釋及其規劃是該能力的重要構成。這種技術最早誕生在美國博物館界,近年來美國博物館不斷厘清規劃的定義,提出規劃的多種視角并將其付諸實踐,業已形成闡釋規劃的要素、框架及實施步驟。以美國科羅拉多大學自然歷史博物館(University of Colorado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為例,該館擁有超過400萬件藏品,但三個展區沒有統一的主題或使命。所以為找準定位和觀眾群,以明確自身使命和觀眾所獲體驗,2005年該館開始著手制訂闡釋規劃:首先由公共部門人員完成,再經主管驗收并提交全體員工審核和批準。隨著規劃問世,館方確定了資源定位、觀眾體驗的優先順序。在該規劃被采納一年后,公共部門又對其重新審定[54]。
(三)制度上:我國博物館包含闡釋規劃在內的規劃體系尚待建設
雖然制度建設會面臨可能預見的利益沖突,但卻能通過廓清權責、優化程序等來節約成本、提升效率、激發創新,以釋放“紅利”。然而當前“因物而物”的舊傳統使得“翻轉式”的制度創新遭遇極大障礙,同時現有管理體制也使制度創新的意識弱化、實踐受挫。在制度建設中最為突出的問題是忽視規劃體系建設,該體系包括使命、宗旨、長短期目標以及闡釋規劃。現有規劃側重于具體業務的落實安排,而非高屋建瓴的價值定位與導向。這種做法可能帶來的結果是注重展教做什么、怎么做,卻忽視為什么,即重視方法論,卻對認識論和本體論漠然視之。美國自然資源機構近年來在闡釋規劃方面成績卓著,尤其是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在這方面最為突出。《闡釋規劃手冊》《闡釋的挑戰》《闡釋規劃》等相繼出版,使規劃有章可依,為其創新提供持久動力,也為行動帶來可靠預期。正因如此,博物館界將其做法引入并斷言:深思熟慮和系統的闡釋規劃必不可少[55]。
三、探究闡釋及其規劃以推動中國博物館的當代轉型
盡管闡釋及其規劃在推動我國博物館轉型中遭遇三大困境,但我們已不能再將這場“由藏品到觀眾”的轉型視為一種超然,因為其“與社會力量所形塑的財富、知識和品味等多因素緊緊糾纏在一起”,顯然已勢不可擋[56]。為此,亟需在破解轉型困境的基礎上,為轉型尋找可能的治世良方,筆者認為對闡釋及其規劃議題的探究便是促成轉型的不二法門和有力舉措。以下,筆者將從闡釋模型的搭建、闡釋規劃內容框架的設計兩方面尋求解決之道,并主張將前者貫徹至后者之中。
(一)搭建博物館闡釋的“六要素模型”
在闡釋研究領域,被眾多學者公認的模型是TORE。TORE是指闡釋的基本要素,分別是:有主題(themetic)、經過組織(organised)、有相關性(relevant)和有趣味(enjoyable)[57]。博物館闡釋是諸多闡釋現象之一,和其他現象一樣都旨在鼓勵人們在更好地理解的基礎上得出自己的結論[58]。所以此四大要素可為博物館闡釋模型所用。同時,博物館闡釋也具有普遍性之外的個殊性,最大的差異在于傳播媒介的迥乎不同。所以筆者還借鑒貝弗利·瑟雷爾(Beverly Serrell)的展覽評價體系(judging exhibitions:a framework for assessing excellence)[59],以及《美國博物館國家標準及最佳做法》中的“教育與藏品闡釋”(education and interpretation)[60],提出適用于博物館的闡釋要素。之所以要參考這兩大來源,是因為前者判斷展覽的優劣與否是建立在展覽能否滿足觀眾高質量體驗的前提下,其歷時約4年,經過12次反復測試[61];后者提到的“教育與藏品闡釋”是博物館工作的核心,盡管在最佳做法上較難達成一致判斷,但依然能概括出卓越闡釋的特征。綜上,筆者認為博物館闡釋模型包含六大要素:主題性、舒適性、組織性、相關性、趣味性、評估性。
第一,主題性。主題可使博物館闡釋具備清晰的想法,為征集藏品、開展研究、策劃展覽、實施教育等提供取舍依據,以避免決策兩難。第二,舒適性。博物館需將觀眾的注意力吸引至博物館物的文化意義,若要實現該目標,首先應在身體、認知和情感上令人舒適。第三,組織性。優秀的博物館闡釋通常是經過組織的,這樣受眾在理解時就不會耗費過多精力,博物館傳播的信息、思路與意圖也更易于被觀眾掌握。第四,相關性。闡釋應能與觀眾了解的事物相關聯,這在建構主義教育學中已有過詳述。大衛·拉森(David Larsen)為此創造出一個名詞“普遍概念”(universal concepts),認為這些概念與所有人都能產生無形或象征性聯系,包括愛、恨等極端情感,生死、饑渴等生物需求,以及對懸念、宇宙等不確定性的迷戀[62]。有時并非博物館呈現的信息不夠完整,而是在于它能多大程度與多數人建立關聯。第五,趣味性。博物館的成功闡釋通常是有趣的、能吸引人的。趣味性并非簡單等同于闡釋輕松好笑,事實上即便有些可怕且傷感的闡釋也能吸引觀眾的注意,讓觀眾沉浸其中。第六,評估性。博物館的闡釋成功與否,最終的衡量標準并非取決于博物館的輸出,而取決于觀眾的獲益,獲益情況通常需借助科學評估。觀眾研究與闡釋工作息息相關,它們皆以觀眾為本,前者聚焦于觀眾行為、心理及體驗效果研究,后者探討如何幫助觀眾構建意義,所以前者是后者的基礎和前提。
(二)設計博物館闡釋規劃的內容框架
闡釋規劃已步入博物館學界和業界,其說到底是主動指導博物館進行解釋的文件[63]。正如前文所述,《闡釋規劃》一書根據時間將綜合闡釋規劃分為長期闡釋規劃、年度實施規劃和闡釋數據庫[64]。威爾斯根據闡釋深廣度提出區域闡釋規劃、闡釋總體規劃和項目闡釋規劃三級框架[65]。波莉·麥肯納-克雷斯(Polly Mckenna-Cress)曾將“展覽大綱”稱為“闡釋框架”[66]。從機構層面看,上述觀點基本都涉及綜合闡釋規劃(又稱“闡釋總體規劃”),而該規劃屬于布局謀篇的綜合定位和整體導向,所以本文主要探討的是此類規劃。參與者通常包括博物館管理者、展覽內容策劃者和形式設計師、教育人員、觀眾服務人員等。
威爾斯基于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將綜合性闡釋規劃的內容概括為兩方面[67]:第一是規劃基礎,包含公園用途和意義、闡釋主題、游客體驗目標/游客體驗聲明、其他基本要素、現有條件和游客描述;第二是針對特定服務和媒體的目標和建議,特定服務和媒體包括個體服務、正規教育服務、闡釋媒體、闡釋設施,注重游客體驗、可讀性、形式外觀、感知有用性。可見,闡釋規劃既要呈現對現有條件的系統梳理,又要將現有情況和目標建議聯系起來進行邏輯分析。成功的闡釋規劃能提出有助于理解博物館的合理且具體的建議,而這些建議來自對規劃的目標、現狀等清晰提煉與中肯剖析。
美國博物館教育實務專家貝斯·B.施耐德(Beth B.Schneider)圍繞休斯頓美術館(Museum of Fine Arts,Houston)制訂的闡釋總體規劃,論述了其闡釋規劃的重點、內容和項目[68]。她指出闡釋規劃的重點是為觀眾提供進入通道,讓他們能在博物館里觀察、思考、理解、欣賞和發現意義,包括明確觀眾、邀請其參觀、歡迎觀眾并提供機構信息、為媒介闡釋提供方向、鼓勵觀眾重復參觀并就體驗作出反饋等五項內容,囊括的項目有展覽、教育資源、網站、博物館內外項目、在線聊天版塊、互動空間和實踐材料等。可見,施耐德將包括展教在內的幾乎所有業務都納入美術館的闡釋范圍,內容主要集中在為觀眾提供機構信息、為闡釋指明可能方向、鼓勵觀眾前來并積極給予反饋。
綜上,通過對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和美術館闡釋規劃的實踐分析及觀點借鑒,筆者認為博物館綜合闡釋規劃(闡釋總體規劃)的內容框架可由兩大版塊構成:規劃的條件和基礎、闡釋項目的目標和建議。首先是規劃的條件和基礎。明確博物館的使命、愿景、長短期目標、闡釋主題、觀眾描述、目標觀眾、現有條件、相關規劃工作和其他背景信息,其中的觀眾描述和目標觀眾可借助觀眾研究成果。其次是闡釋項目的目標和建議。闡釋項目涵蓋藏品、展覽、教育活動、網站、文創、大眾傳媒和新媒體等博物館可利用的所有方式,博物館應規定這些項目的目標,并根據現有情況提出建議。除展覽按內容闡釋與形式闡釋分類之外,其他項目可以觀眾類型為分類標準,如教育活動可分為親子、學生、教師、老年、殘障、成人等活動類型。在擬定目標和建議時,應注意將闡釋模型的六要素融入展教等業務。
四、結語
雖然闡釋及其規劃誕生和發展于西方博物館界,但對西方博物館而言,其自身也正經歷著“開眼”向其他學科和機構主動學習的歷程,因為它們敏感地覺察到闡釋及其規劃的內涵和價值對博物館當代轉型的積極作用毋庸置疑。為此,我國博物館界亟需將闡釋及其闡釋規劃這一新議題納入視域,對其變革中產生的客觀結果作出全面性反思和本土化創新。本文在追溯闡釋及其規劃的定義和理論依據的基礎上,嘗試破析目前其在我國博物館界推行過程中所遭遇的三大特殊困難,由此提出我國博物館闡釋的模型和闡釋規劃的內容框架,以期為博物館真正走下“神壇”、走向“公共化”和“世俗化”提供理論指導和方法借鑒[69]。
觀眾帶著各自的入門故事走進博物館,把這些故事置于自身認知加工的背景之中,就構成了博物館環境下建構主義學習的哲學基礎。無論是展覽還是教育活動,無論是實體展品還是數字展品,都會與觀眾構建起熟悉或不熟悉的關系,而這些關系反過來也塑造了我們的總體理解[70]。當前博物館正處在“物人關系”的轉型時代,闡釋及其規劃這一新議題的出現,讓我們意識到并確信這種關系的重要性和復雜性,同時也必須看到我們對關系的重建能力,即將不熟悉的東西變成熟悉東西的能力正在增強,任務也更為緊迫。正如比爾·布朗(Bill Brown)所言,事物只有在重視它的社會才能作為對象存在[71]。研究闡釋及其規劃議題有助于博物館依托物促成觀眾與歷史、權威和偏見的公平對話。不可否認,步入博物館的每位觀眾都攜帶著自身的認知“地平線”,這既是他們認知的全部范圍,也是全部局限。博物館試圖幫助他們跨越歷史的差距、文化的差距、人與人的差距,“讓被認為獨自存在的視域發生融合”[72]。但必須明白的是,理解始終在路上,因為理解在闡釋過程中會不斷被顛覆和更新。為此,闡釋及其規劃還應在“社會之中”,需要立足社會需求,在使命導向下不斷調整和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