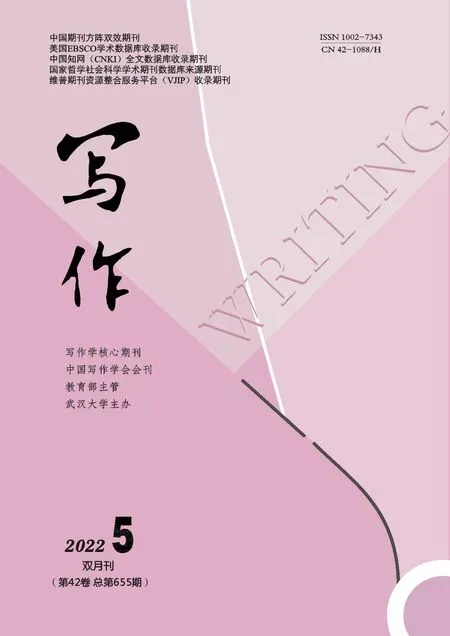廢名小說的接受與回響
——以沈從文對廢名的“誤讀”為中心
羅帥
關于廢名和沈從文在創作上的關系,學界已關注多年,且大都聚焦于兩人事實上的影響、藝術品位的投合以及小說作品題材和風格的接近。1935年,李健吾就曾比較兩人的小說特色:廢名更“內向”,接近“修士”,追求的不是“美麗”本身,而是一種境界;沈從文則“熱情地崇拜美”,展現一種“美化的生活”。他敏銳地把握了兩種創作的同中之異①劉西渭(李健吾):《〈邊城〉與〈八駿圖〉》,《文學季刊》1935年第2卷第3期。。經過1949—1976年廢名和沈從文研究的沉寂階段,進入新時期后,不少學者繼續探究兩人的文學聯系。先是凌宇將廢名營造山水意境和個人細微意識的文體命名為“詩體小說”,并將沈從文和蕭紅等人的寫作也納入其中②凌宇:《從〈桃園〉看廢名藝術風格的得失》,《十月》1981年第1期。。持有類似觀點的還有楊義、楊聯芬等,他們改用“抒情小說”或“抒情傾向”來概括廢名、沈從文一脈的小說③楊義:《廢名小說的田園風味》,《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2年第1期;楊聯芬:《中國現代小說中的抒情傾向》,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充實了這一譜系的內涵。吳曉東借用法國象征主義詩人古爾蒙提出的“詩化小說”概念,梳理了包括周作人等理論家,以及廢名、沈從文到汪曾祺等諸多小說家在內的文脈,認為這些作家都“追求詩意的語言、意境的營造與散淡的敘事”④吳曉東:《現代“詩化小說”探索》,《文學評論》1997年第1期。。吳曉東拓展了“抒情化”的理論邊界,這也開創了此后探討廢、沈小說風格、文體以及兩人創作聯系的常見思路。嚴家炎、楊聯芬等人也致力于廢名和沈從文的細部比較,在將他們都歸入“京派”“歸隱派”的前提下,探索其創作實踐的異同①嚴家炎:《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版;楊聯芬:《“歸隱派”與名士風度——廢名、沈從文、汪曾祺論》,《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2期。。已有研究的重點幾乎都放在了廢名與沈從文的聯系之上,而對他們彼此的質疑或者“誤讀”著墨較少。事實上,在沈從文對廢名保持持續關注、接受和反思的多年間,不僅自己的創作在逐步成熟,廢名的文學觀念和實踐也日漸轉變,評價不可能一成不變;沈從文的文學之路始于1923年的北京,1933年后又返平擔任《大公報·文藝副刊》主編,1946年后任北京大學教授,與廢名不乏事實上的交往,這也會影響到他的“廢名觀”;作為私淑廢名的小說家和批評家,沈從文對廢名小說的閱讀感受和藝術分析,恰是廢名小說接受情況的一個縮影,反映出廢名小說獨特價值的同時,也對當時的若干文學思潮形成了回應。
一、沈從文的“廢名評論史”
沈從文對廢名的評論起于1926年,終于1940年代,大體上可分為三個階段:1926年的起始階段,1929—1931年的發展階段,以及1940年代的完成階段。它呼應了廢名創作的演變過程,也與自我創作和閱讀體驗的變化形成互動。
1926年初,初涉新文學創作的沈從文廣泛涉獵了當時北京的主要新文學刊物及作家作品,綜合考慮報刊連載、社團流派等因素,寫下了《北京之文藝刊物及作者》,逐一予以評論,其中就包括了廢名及其小說集《竹林的故事》:
馮文炳的小說,最近才出了一個創作集,《竹林故事》,我個人是很喜歡他的東西的,不過因為窮的關系,我所見到他的幾篇文章,還是《語絲》同《現代評論》登載的,不知其他怎樣。他的創作寫得極其細致,但并不累贅,把自己兒時所得的印象,用女人似的筆致寫來,至少是我為他那篇《竹林故事》,(集中之一)已深深的感動了。在他集子上他自序他創作正是一種“悲哀的玩具”。他所見的人生,似乎就只是他創作中那類人生,使他感著親切。這只是人生的一片,但他能把這一片人生送給我們,(雖然他說是自己的悲哀玩具。)已覺得很不少了。
我的希望,是現在的文藝園圃中,能多產生一些這類美麗文字,才能給人一點安慰。②沈從文:《北京之文藝刊物及作者(續)》,《文社月刊》1926年第1卷第6期。
截至該文寫作的1926年1月止,廢名在《語絲》及《現代評論》發表過《鷓鴣》(1925年2月14日《現代評論》第1卷第10期)、《竹林的故事》(1925年2月16日《語絲》第14期)、《初戀》(1925年4月4日《現代評論》第1卷第17期)、《火神廟的和尚》(1925年3月16日《語絲》第18期)、《去鄉——S的遺稿》(1925年8月3日《語絲》第38期)、《花炮》(1925年10月26日《語絲》第50期)、《妓館(花炮之四)》(1925年11月16日《語絲》第53期)等。廢名“悲哀的玩具”一語,其實并不出自《竹林的故事·序》,而出自《語絲》刊登的該書廣告:
這是馮文炳先生的短篇小說集,現已出版。馮先生說:“這是我的悲哀的玩具,而他又給了我不可名狀的歡喜。”現在想將這歡喜分給他的讀者。定價五角。③《廣告·竹林的故事》,《語絲》1925年第54期。
沈從文從“悲哀玩具”談到“一片人生”的格局、兒時的回憶,以及美麗細致的文字風格,觀點與周作人都十分接近:
馮君所寫多是鄉村的兒女翁媼的事,這便因為他所見的人生是這一部分,——其實這一部分未始不足以代表全體……(按:省略號為引者所加)
馮君著作的獨立的精神也是我所佩服的一點。他三四年來專心創作,沿著一條路前進,發展他平淡樸訥的作風,這是很可喜的。①周作人:《竹林的故事序》,《語絲》1925年第48期。豈明(周作人):《〈桃園〉跋》,廢名:《桃園》,上海:開明書店1928年版。沈從文也指出了周作人的這一觀點,參見沈從文:《論馮文炳》,《沫沫集》,上海:大東書局1934年版,第2頁。
該序發表于沈從文時常閱讀的《語絲》,沈從文很可能讀到過并受到啟發,對《竹林的故事》的喜愛,也讓沈、周二人產生了共鳴。就上述小說篇目來看,兩人的評論基本道出了廢名早期小說的特征:以鄉土記憶為題材,話題不離婚戀娶嫁、迎神賽會等家長里短和黃梅地方風致,著重敘述“我”對早夭阿妹的縷縷思念,對銀姐的朦朧情愫,對三姑娘的淡淡懷戀,筆觸柔軟,情感細膩,彌漫著一絲淡淡的愁緒。多年后,李健吾再次談到這部集子,仍然流連于“他描繪的簡潔,情趣的雅致,和他文筆的精練”②劉西渭(李健吾):《讀〈畫夢錄〉》,《文季月刊》1936年第1卷第4期。,這是廢名的標志性特征,也讓沈從文為之癡迷。
1930年1月,沈從文于吳淞中國公學講授“新文藝試作”和“現代文學研究”③私立中國公學:《中國公學大學部一覽中華民國十九年》,1930年5月版,第94頁。。當年7月,又前往武漢大學教授同類課程④國立武漢大學:《國立武漢大學一覽中華民國十九年度》,1931年1月版,第8頁。,從歷史角度檢視新文學的整體,甚至感到“頭痛不過”⑤沈從文:《致王際真19300129》,《沈從文全集》第18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頁。。以此為契機,沈從文撰寫了若干評論,對新文學歷史與現狀的理性認知有了突破,其文學觀念和自我定位也逐漸清晰⑥沈從文1929—1930年撰寫的新文學批評篇目,屠毅力:《文學者的“政治”——對30年代京派形成的考察》,中國人民大學2013年博士學位論文,第103-104頁。,對廢名的欣賞與質疑,也都隨之走向成熟。1934年4月,沈從文出版新文學論集《沫沫集》,據已有材料看,其中大部分文章都曾于1930年前后發表,只有《論馮文炳》《魯迅的戰斗》未曾見刊。《論馮文炳》應作于1930年7月⑦吳世勇:《沈從文年譜》,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2頁。,對起始階段的廢名評價有所繼承,更有所突破。
沈從文首先總結了《竹林的故事》題材方面的優點,欣賞其“農村寂靜的美”和“靜中的動,與平凡的人性的美”,并將其原型追溯到作者生活的黃岡“小鄉村”⑧沈從文:《論馮文炳》,《沫沫集》,上海:大東書局1934年版,第3-4、2頁。,大體延續了《北京之文藝刊物及作者》中的觀點。在此基礎上,沈從文致力于尋找廢名鄉土小說的精神脈絡,將眼光對準了周作人的影響:
馮文炳君作品,所顯現的趣味,是周先生的趣味。文體有相近處,原是極平常的事,無可多言。對周先生的嗜好,有所影響,成為馮文炳君的作品成立的原素,近于武斷的估計或不至于十分錯誤的⑨沈從文:《論馮文炳》,《沫沫集》,上海:大東書局1934年版,第3-4、2頁。。
這一判斷符合周廢二人的看法。廢名曾將周作人“自己的園地”視為其小說的靈感來源之一⑩馮文炳:《序》,《竹林的故事》,北京:新潮社1925年版,第1頁。,周作人也明確表示,自己“叛徒與隱逸合一”的人生態度也深得廢名之心○1周作人:《竹林的故事序》,《語絲》1925年第48期。豈明(周作人):《〈桃園〉跋》,廢名:《桃園》,上海:開明書店1928年版。沈從文也指出了周作人的這一觀點,參見沈從文:《論馮文炳》,《沫沫集》,上海:大東書局1934年版,第2頁。。沈從文的獨到之處,在于試圖從兩人的傳承關系中,梳理出一條“從周作人到廢名”的文學史脈絡:
從五四以來,以清淡樸訥文字,原始的單純,素描的美,支配了一時代一些人的文學趣味,直到現在還有不可動搖的勢力,且儼然成一特殊風格的,提倡者與擁護者,是周作人先生。
……因為文體的美麗,最純粹的散文,時代雖在向前,將仍然不會容易使世人忘卻,而成為歷史的一種原型,那是無疑的。①沈從文:《論馮文炳》,《沫沫集》,上海:大東書局1934年版,第1、8、4-7、9-10頁。
沈從文將周作人的散文文體及風格影響力置于“五四”新文學發展的背景下考察,以“清淡樸訥”“原始的單純”和“素描的美”提煉周、廢共同的語言風格,從兩人對鄉村生活、地方風土和生活細節及自然事物的興趣上找尋精神聯系,不僅反映了沈從文敏銳的文學感受,也如同他這一時期所寫的《論中國創作小說》《現代中國文學的小感想》等新文學批評,展露出鮮明的新文學史意識②沈從文:《論中國創作小說(續)》,《文藝月刊》1931年第2卷第5、6期合刊;《現代中國文學的小感想》,《文藝月刊》1930年第1卷第5號。。
面對《竹林的故事》,沈從文不吝贊美之詞,觀點也基本保持前后一致,同時還不止一次地承認,自己深受其影響。除去《論馮文炳》中的自白外③沈從文:《論馮文炳》,《沫沫集》,上海:大東書局1934年版,第1、8、4-7、9-10頁。,一年前,沈從文的短篇小說《夫婦》發表于《小說月報》,結尾有一則附言:
自己有時常常覺得有兩種筆調寫文章,其一種,寫鄉下,則仿佛有與廢名先生相似處。由自己說來,是受了廢名先生的影響,但風致稍稍不同,因為用抒情詩的筆調寫創作,是只有廢名先生才能那種經濟的。這一篇即又有這痕跡,讀我的文章略多而又歡喜廢名先生文章的人,他必能找出其相似中稍稍不同處的。這樣文章在我是有兩個月不曾寫過了,添此一尾記自己這時的欣喜。時七月十四日,天熱,住樓上一天只是流汗。甲辰記。④沈從文:《夫婦》,《小說月報》,1929年第20卷第11號。
巧合的是,在《夫婦》出刊的同日,沈從文得知中國公學可能聘請廢名來替自己上三年級國文預科,顯得很高興,向胡適寫信,表示“于同學及從文本人皆為幸事”⑤沈從文:《致胡適19291110》,《沈從文全集》第18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28頁。,對廢名的欽佩溢于言表。這則附言點出廢名“抒情詩”筆法的同時,似乎特別強調與廢名的“稍稍不同”,且隱隱透露出一絲“欣喜”。既承認得到廢名小說滋養,又有意突出自我創作的超越性,是沈從文這一時期廢名批評的顯著特征,這在《論馮文炳》中也有明顯體現。文中談到,廢名的小說過于“寧靜”,缺少“靜中的動”,筆下的鄉土世界不夠全面,語言存在“八股式的反復”,將作品導向“病的纖細的美”⑥沈從文:《論馮文炳》,《沫沫集》,上海:大東書局1934年版,第1、8、4-7、9-10頁。。相比之下,自己的《雨后》《龍朱》《我的教育》《夫婦》等作品,能以“矜慎的筆”反映“強烈的愛憎有悲憫的情感”和“一切由生產關系下產生的苦樂”,突出了鄉村生活及人物的天然野性美,因而“較馮文炳為寬而且優”⑦沈從文:《論馮文炳》,《沫沫集》,上海:大東書局1934年版,第1、8、4-7、9-10頁。,在審美格調和表現范圍等層面皆有突破,顯示了其小說寫作和個人意識的成熟,并自居為“周作人—廢名”鄉土小說流脈的繼承者和發展者。之后,廢名走向長篇小說《橋》和《莫須有先生傳》《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后》的寫作,努力營造自己所癡迷的那個夢幻“心象世界”⑧吳曉東:《意念與心象——廢名小說〈橋〉的詩學研讀》,《文學評論》2001年第2期。,沈從文則著力打造充滿野性氣息的湘西世界,彰顯了各自的寫作個性。至于《論馮文炳》中對廢名等人“趣味化”傾向的反思,后文將詳細論述,在此不贅。
1939年,沈從文因躲避抗日戰火而身處昆明,擔任西南聯大師范學院國文學系副教授①吳世勇:《沈從文年譜》,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9頁。。1940年,將“各體文習作”課程的講義整理完善后,以“習作舉例”為總題,分三部分發表,分題為《從徐志摩作品學習“抒情”》《從周作人魯迅作品學習抒情》《由冰心到廢名》。前兩篇分別論述了徐志摩情感的“熱烈”和周氏兄弟散文的“冷靜”,是抒情散文的兩種風格;冰心、朱自清、廢名的文章則可稱為“境界散文”,重點在于描繪“當前”,而非徜徉于“過去”和“回憶”,境界“沉默而羞澀”,“或透明如水”。廢名“記言記行,用儉樸文字,如白描法繪畫人生,一點一角的人生。筆下明麗而不纖細,溫暖而不粗俗,風格獨具”,保持“田園風”的“自然生趣”,同時還能做到“文情相生,略近于‘道’”,但因為筆調隱逸氣太重,盡管筆下的農村確實存在,終究與讀者產生了隔閡②沈從文:《習作舉例三由冰心到廢名》,《國文月刊》1940年第1卷第3期。。這樣,對廢名的喜愛與質疑都得到了保留,而所謂“隱逸氣”和“文情相生”的判斷,也是有意呼應了周作人的看法③豈明(周作人):《〈莫須有先生傳〉序》,《鞭策周刊》1932年第1卷第3期。。然而,連天的炮火將廢名隔絕在了老家黃梅鄉下,這時的他并無任何小說新作,與外界也幾乎沒有聯系,得到的關注也驟然減少,沈從文的評論因而略顯孤獨。
可以看出,沈從文對廢名小說的接受,有一條較為明晰的發展脈絡,對《竹林的故事》等早期作品,不惜溢美之詞,青睞其筆觸細膩、情感深摯、鄉土風物、樸素文風,而對《桃園》《橋》和《莫須有先生傳》則頗有微詞,不滿其語言的蕪雜、結構的散漫和趣味的奇僻。沈從文堅持中有突破,理解中有反思,欣賞中有審視。考慮到《論馮文炳》《論中國創作小說》以及《由冰心到廢名》等篇目大都是新文學習作的講義,其觀點自然會因課程性質需求而偏于印象式,但其良好的文學感覺和自覺的文學史意識,依然為廢名評論增添了厚度,同時也揭示出文學史上一些關鍵問題,因此值得進一步討論。
二、《論馮文炳》與沈從文的“反趣味化”批評
如上文所述,沈從文1930年7月寫下了其廢名評論的代表作《論馮文炳》,主要討論周作人影響下的廢名鄉土小說。他認為就題材、語言等方面,廢名勝過張資平等“天才”的戀愛小說,并承認自己深受影響。更需要注意的,是沈從文對廢名的“揚棄”。在指出廢名小說太過平靜,缺乏靜中之動等不足后,沈從文更對其語言的“八股的反復”和“不節制”提出批評。對于廢名小說自成一體的文體和語言,其他批評者也有所留意。1929年,署名“拙亭”者發表《桃園》書評,揄揚了其“簡練別致生動,且多帶滑稽的意味”的小說語言④拙亭:《對于廢名〈桃園〉之批評》,《開明》1929年第1卷第10號。;1932年,灌嬰發表《橋》一文,從小說結構、人物形象、文化氛圍和語言美學等角度評價《橋》,以其“簡練”為“得”,“晦澀”為失⑤灌嬰:《橋》,《新月》1932年第4卷第5期。。當《現代》雜志的書評肯定廢名語言的曲折回環⑥《橋》,《現代》1932年第1卷第4期。,李健吾一針見血地將《橋》的語言形態總結為“抽象的絕句”,表現為“句與句間的空白”,盡管耐人尋味,但也“失卻藝術所需的更高的諧和”⑦劉西渭(李健吾):《讀〈畫夢錄〉》,《文季月刊》1936年第1卷第4期。,委婉地提出了批評。這與沈從文的觀點確實有異曲同工之處。沈從文將其成因歸結為“趣味的惡化”,這種“趣味”也和周作人的影響脫不開干系:
從北平所謂“北方文壇盟主”周作人,俞平伯等等散文揉雜文言文在文章中,努力使之在此等作品中趣味化,且從而非意識的或意識的感到寫作的喜悅,這“趣味的相同”,使馮文炳君以廢名筆名發表了他的新作,在我覺得是可惜的。①沈從文:《論馮文炳》,《沫沫集》,上海:大東書局1934年版,第6頁。廢名:《知堂先生》,《人間世》1934年第13期。
對文學“趣味”的玩味和孜孜追求,正是周作人和廢名的精神契合點之一。周作人認為,“滿足自己的趣味”,就足為經營“藝術與生活”的理由②豈明(周作人):《〈藝術與生活〉序》,《語絲》1926年第93期。,所寫的正是“趣味之文”③起明(周作人):《〈澤瀉集〉序》,《語絲》1927年第145期。;廢名在同時期的創作論《說夢》中,也借他人觀點自白道:“文藝作品總要寫得intersting。這話我也首先承認。”④廢名:《說夢》,《語絲》1927年第133期。到了30年代,更是津津樂道于“厭世派”文章作法之趣⑤鶴西、廢名:《郵筒》,《駱駝草》1930年第3期。。周作人最欣賞廢名的,也就是其從“中外文學里”所涵養出的“趣味”⑥周作人:《竹林的故事序》,《語絲》1925年第48期。,其小說的優點也正在其文章的“古典趣味”⑦豈明(周作人):《桃園跋》,廢名:《桃園》,上海:開明書店1930年版。。針對以周作人為核心的“趣味化”圈子,也早有批評之聲,觀點與沈從文相仿。1927年,成仿吾把周作人及周邊作家群描述為“以趣味為中心”的圈子⑧仿吾:《完成我們的文學革命》,《洪水》1927年第3卷第25期。,李初梨響應了這一觀點,并進一步概括為“趣味文學”⑨李初梨:《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文化批判》1928年第2號。;而關系較近的朱自清,也聲稱自己不能理解其“以趣味為主”的明代名士式追求⑩佩弦(朱自清):《燕知草序》,《語絲》1928年第4卷第36期。。周作人等及時回應,在《〈燕知草〉跋》中指出,俞平伯與明人最接近之處是“反抗”的姿態,補充了朱自清的觀點。而在《〈桃園〉跋》中揄揚了廢名的“古典趣味”后,周作人特意加上一句“(又是趣味)”,未必沒有對這一時期蜂擁而至的“趣味化”批評的不滿。廢名則更直白地挑明,為“時人所病的‘趣味’二字”,正是周作人最“近乎事理”處○1沈從文:《論馮文炳》,《沫沫集》,上海:大東書局1934年版,第6頁。廢名:《知堂先生》,《人間世》1934年第13期。。從師生的一唱一和,明顯看出其對“趣味化”的默認和自喜。
沈從文口中的“趣味化”和“趣味主義”,不只用于指稱周作人及弟子們的創作態度,這是他與其他批評者不同所在。在沈從文眼中,大部分新文學作品都可納入“趣味化”的序列:魯迅的《故鄉》《社戲》等開創了對鄉愁和鄉村風物趣味化書寫的先河,此后與周作人等人經營的“語絲體”,則形成了詼諧諷刺的趣味;郭沫若的小說語言夸張,結構松散,培養了粗率、夸大的興味;而張資平依靠三角戀小說,迎合青年官能化的低俗口味;后起的馮文炳、許欽文、王魯彥、蔣光慈等不同流派的作家,則在不同層面受到影響。這一經由兩代作家傳遞后形成的新文學整體趨勢,被他命名為“趣味化”:
從各方面加以仔細的檢察,在一些作品中,包含孕育著的浮薄而不莊重的氣息,實大可驚人,十年來中國的文學,在創作一方面,由于詼諧趣味的培養,所受的不良影響,是非常不好的把諷刺的氣息注入各樣作品內,這是文學革命稍后一點普遍的現象……過去一時代文學作品,大多數看來,皆不缺少病的纖細,前面說到的理由,是我們所不能不注意的。○12沈從文:《論中國創作小說》,《文藝月刊》1931年第2卷第5、6期合刊。
沈從文在什么意義上,擴大了“趣味化”的范圍,構成了與其他批評者的差別呢?這得從造成這一風氣的“理由”說起。他指出,1927年前后國民革命影響下,原本集中于北京的部分新文學者赴滬,從而形成了“北京—學院”及“上海—市場”兩大新文學聚居地,其連帶而來的學院化、商業化和政治化,正是新文學“趣味化”風氣的根源①沈從文:《論中國創作小說》,《文藝月刊》1931年第2卷第4號。。也正是不必靠寫作謀生的學院生活,使周、廢等的眼光局限于個人趣味:
在北平地方消磨了長年的教書的安定生活,有限制作者拘束于自己所習慣愛好的形式,故為周作人所稱道的《無題》中所記琴子故事,風度的美,較之時間略早的一些創作,實在已就顯出了不康健的病的纖細的美。②沈從文:《論馮文炳》,《沫沫集》,上海:大東書局1934年版,第10、8頁。
這席話道出了廢、沈二人的關鍵差異:廢名身處學院內,接受過嚴格的大學教育,大多數時間都在閱讀庾信、李商隱、莎士比亞、塞萬提斯、波德萊爾等古今中外文學經典,他對鄉村的回味和書寫,大都也帶著清雅脫俗的書卷氣和學院風;沈從文的創作資源很大程度上來自他逃學、爬山、涉水的豐富少年生活。他的最高“學歷”只有小學,15歲便當兵,輾轉于湘、貴、川等地,身體和精神中都積蓄了樸野、雄強、自然之力,而這些也是他眼中真正的美③沈從文:《蕭乾小說集題記》,《大公報·文藝副刊》1934年第126期。。因此,當廢名的小說中的隱逸氣一點點上升,文體走入“奇僻生辣”④豈明(周作人):《棗和橋的序》,廢名:《橋》,上海:開明書店1932年版,第4頁。一路后,其整體美學風格自然就不為沈從文所肯定,兩人的差異也浮上紙面。
沈從文此前并未如此明確地意識到自己與廢名的差別。1926年發表的《北京之文藝刊物及作者》中,對廢名的熱愛就溢于言表。《論馮文炳》則發展了這一觀點,還詳細闡述了自己所受到的影響,為自己的試筆階段的工作找到了精神依據。他早期的《畫家師兄》《臘八粥》《代狗》等,大都描寫恬淡溫馨的鄉村風光和人物關系,夾雜著些微鄉愁,模仿廢名的痕跡確實很重。1928年后,沈從文更側重湘西傳說、愛戀故事的書寫,《論馮文炳》中提到的湘西人野性、自然的一面,與廢名同期的《棗》和《橋》等詩化篇章的確風格有異,其創作個性日漸成熟,隱隱有自成一派的趨勢。當時拿他倆進行比較,分析兩人異同的聲音不在少數。毛一波起先看重廢、沈二人“用那一種簡練和緊湊的文字來寫小說”的相似之處⑤毛一波:《新作風》,《真美善》1929年第4卷第3號。,此后又連續發表關于廢名《竹林的故事》和《桃園》以及沈從文《入伍后》的評論,指出了廢名和沈從文在語言和題材上的區別,前者以“精煉素樸的文章”和“滑稽的諷刺”,描摹了黃梅鄉村和北京城里人的面貌⑥毛一波:《〈竹林的故事〉和〈桃園〉》,《真美善》1929年第5卷第2號。,后者則以緊湊的文筆,向讀者展示了一幅活潑的軍旅生活圖景⑦毛一波:《〈入伍后〉》,《真美善》1929年第5卷第2號。;翻譯家朱雯多年后也說,1930年前的短篇小說大都模仿廢名和沈從文的文風⑧朱雯:《朱雯致沈從文》,劉衍文、艾以主編:《現代作家書信集珍》,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9年版,第893頁。。這種對比沈從文一直有所耳聞⑨沈從文:《論馮文炳》,《沫沫集》,上海:大東書局1934年版,第10、8頁。。如此看來,他的評論則有“順水推舟”的意味,既不否認廢名帶來的滋養,同時前進一步,主動表白自我風格的獨特之處,在皈依“周作人—廢名”文學流脈的前提下,不惜以“情趣朦朧,呈露灰色”等評語夸張地強調廢名的“缺陷”,通過某種程度的“誤讀”,凸顯自己的獨特所在,對廢名則表現出“欣賞及不滿足”的態度。1934年,沈從文由滬返平,以《大公報·文藝副刊》主編的身份占據北方文壇要津,在這個時間點出版《沫沫集》,尤其是收入此前從未公開發表的《論馮文炳》,體現出了與前代作家對話的強烈意識,在批判中繼承京派文脈。
面對諸多批評,廢名不會不知道。在沈從文寫完《論馮文炳》的3個月后,廢名也對沈從文的《蕭蕭》做出了評論,稱其“文章寫得很好”的同時,更對小說中蕭蕭懷孕后族人的態度表示不滿,嚴厲批評作品的“輕薄氣息”和“下流”①法(廢名):《隨筆》,《駱駝草》1930年第25期。,顯示了兩人之間實際存在的審美和倫理觀念差異。廢名當時是否讀到《論馮文炳》不得而知,而4年后,收入此文的《沫沫集》正式出版,其他批評也日漸積累之時,廢名也未急于正面辯解,只是一方面為“趣味”正名,另一方面則在《知堂先生》《孔門之文》《三竿兩竿》《中國文章》等一系列文章中,大談陶淵明、儒家經典及小品文,跟進、聲援周作人的文章觀和“趣味”觀②廢名:《知堂先生》,《人間世》1934年第13期。。同時,他也從六朝文、晚唐詩、塞萬提斯小說、莎翁戲劇等文學資源中尋覓小說創作的依據,提煉出“玲瓏多態”的“亂寫”美學③廢名:《三竿兩竿》,《世界日報·明珠》1936年第6期。。沈從文、李健吾等人皆有微詞之處,恰恰是廢名津津樂道的“獨門絕技”,不僅顯示了不同的美學觀念,還暗含了周、廢等人與當時另一股鄉土文學思潮的對話。
三、“鄉土文學”視域下廢名小說的“歸類”問題
1935年,魯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中提到了諸如蹇先艾、許欽文、王魯彥等人的小說,統稱其為“鄉土小說”或“僑寓文學”:“凡在北京用筆寫出他的胸臆來的人們,無論他自稱為用主觀或客觀,其實往往是鄉土文學,從北京這方面說,則是僑寓文學的作者。”④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9、6-7頁。這也成了“鄉土文學”概念的經典論斷。同時,魯迅將廢名置于淺草社范疇內討論,而在鄉土小說部分只字未提:
后來以“廢名”出名的馮文炳……在一九二五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里,才見以沖淡為衣,而如著者所說,仍能“從他們當中理出我的哀愁”的作品。可惜的是大約作者過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了,不久就更加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閃露,于是從率直的讀者看來,就只見其有意低徊,顧影自憐之態了。⑤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9、6-7頁。
在此之前,就有研究者將廢名的小說納入“鄉土文學”或是“田園小說”中來言說⑥灌嬰的評論就有意突出了廢名小說的鄉土背景,見灌嬰:《橋》,《新月》1932年第4卷第5期。,這一論述傳統從30年代一直延續到今天,而持這一說法的,就包括沈從文。魯迅的不同看法,正反映了雙方對“鄉土小說”的不同認知。
對廢名小說中的鄉土回憶和黃梅地方特色的討論,貫穿了沈從文的整個“廢名評論史”,在《論馮文炳》中更是通過與許欽文、王魯彥等師從魯迅,并為魯迅所認可的鄉土作家比較,提煉出廢名鄉土小說所展現的“農村寂靜的美”和“地方性強”等出彩之處,進而勾勒出“周作人—廢名”鄉土文學脈絡,與魯迅的鄉土小說論構成了強烈的“互文”關系,顯示出兩種不同的鄉土文學觀。按魯迅的標準,不論從“僑寓”還是“鄉土”角度考慮,廢名都不應被忽略。魯迅不說,不是“不懂”,而是“不想”。《導言》中鄉土小說概念似乎可以套用在任何離鄉來京的作家身上,即如日后孫犁所言,“所有文學作品,皆可稱為鄉土文學”①孫犁:《關于“鄉土文學”》,《北京文學》1981年第5期。,這顯然不是魯迅的本意。其對“鄉土小說家”有條件的篩選,其實在無形中規約了“鄉土文學”的范圍。茅盾在《小說一集·導言》中對魯迅提及的彭家煌、蹇先艾、許欽文等作家的創作做了詳盡分析②茅盾:《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導言》,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26-31頁。,及時充實了魯迅的觀點;其一年后追述的“在特殊的風土人情而外,應當還有普遍性的與我們共同的對于運命的掙扎”③蒲(茅盾):《關于鄉土文學》,《文學》1936年第6卷第2號。,也接近魯迅所說的“叫喊和反抗”④魯迅:《我怎么做起小說來》,魯迅、郁達夫等:《創作的經驗》,上海:天馬書店1933年版,第2頁。,不啻為對魯迅的補充,體現了編者之間的合作和對話。《中國新文學大系》編者團隊前前后后的反復論證,表明這可能不只是魯迅個人的意見,更是編者們針對“鄉土小說”這一五四后興起的小說類型所展開的集體建構——主調應為“暴露”,“鄉愁”則應居次席。廢名則反其道而行之,在“沖淡”這一外衣下隱含深刻的“哀愁”,與魯迅等人所肯定的風格大異其趣,而風格正是魯迅遴選作品的另一層標準。
魯迅按“內斂和外露”兩種風格來大致區分五四以來的短篇小說。情緒可以有多種,如“安特萊夫式的陰冷”“熾烈”“大膽”等等,可以等而視之,但涉及表現情緒的方法、傾向,則有了“親疏”之分,談論風格“大膽”“外露”的作品,占用的篇幅較長,而論及風格內斂、朦朧的作家時,則幾句話帶過,多數還帶有批評性:楊振聲的《玉君》所追求的“藝術化”導致了作品“降生也就是死亡”的命運;凌叔華“謹慎”文風也只是多了一種可參照的創作方法⑤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3、11頁。。而被歸入“僑寓文學”的作品大都體現出“大膽”“外露”特征,那么廢名“以沖淡為衣”,又過分珍惜“哀愁”的小說品格,自然很難得到魯迅的認可。在這一點上,沈從文對《竹林的故事》缺少“靜中之動”,“缺少沖突”的評論,恰恰與魯迅的觀點不謀而合,不滿的都是其作品中烏托邦式的隱士風。盡管沈從文并不認同魯迅對“鄉土文學”的限定,但對待文學卻和魯迅一樣嚴肅,反對“趣味主義”作風。
1940年沈從文再談到廢名與鄉土小說關系時感嘆道:“然而這種微帶女性似的單調,或因所寫對象,在讀者生活上過于隔絕,因此正當‘鄉村文學’或‘農民文學’成為一個動人口號時,廢名作品,卻儼然在另外一個情形下產生存在,與讀者不相通。”⑥沈從文:《習作舉例三由冰心到廢名》,《國文月刊》1940年第1卷第3期。他的這通發言,既有回應《中國新文學大系》的意味,同時也是借他人之酒杯,澆自我之塊壘。1935年,《中國新文學大系》陸續問世,沈從文敏銳地意識到背后所蘊含的新文學經典化意義,隨即撰寫《讀〈新文學大系〉》,高度評價其對新文學史的價值,盡管沒直接提到《小說二集·導言》對“鄉土文學”的界定,但對魯迅的選文標準不以為然,指出其在編選過程中,過分抬高彌灑、沉鐘、莽原社⑦炯之(沈從文):《讀〈新文學大系〉》,《大公報·文藝》1935年第51期。。在《論馮文炳》中,沈從文也曾說道:“馮文炳君過去的一些作品,以及作品中所寫及的一切,算起來,一定將比魯迅先生所有一部分作品,更要成為不應當忘去而已經忘去的中國典型生活的作品。”⑧沈從文:《論馮文炳》,《沫沫集》,上海:大東書局1934年版,第12頁。顯然是將周作人、廢名的路數視為“鄉土文學”的正統。沈從文盡管沒有直接參與過“鄉土文學”“農民文學”等概念的論爭,但卻受到“波及”,首當其沖的正是代表作《邊城》。
1934年1月起,《邊城》在《國聞周報》連載,同年4月登完,并于10月由上海生活書店出版單行本。1935年1月,汪馥泉和王集叢發表《一年來的中國小說》,開門見山地提出“文壇無杰作”,隨后一一對沈從文的《邊城》、老舍的《小坡的生日》、穆時英的《白金的女體塑像》等新作展開批評。具體到《邊城》,汪文指出了三大“弊病”:首先,翠翠、爺爺、儺送等人物性格過于單純,茶峒的環境過于美好,屬于過去,缺乏現實性和典型性;其次,曲折的戀愛故事阻礙了思想性的呈現;再次,人物感情太節制,爆發力不夠,心理、感情描寫不夠深刻,難以體現人與人之間感情的濃厚,不足以打動讀者①汪馥泉、王集叢:《一年來的中國小說》,《讀書顧問》1935年第1卷第4期。。這明顯是以階級論、典型論的左翼視角進行批判。同年8月,李健吾發表《〈邊城〉與〈八駿圖〉》,反對汪馥泉的批評②李維音:《李健吾年譜》,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而沈從文1936年初發表的《習作選集代序》,也隱約有回應此類批評的意味:
這作品從一般讀者印象上找結論,我知道沒有人把他看成載道作品,也沒有人覺得是民族文學,也沒有人認為是農民文學。我本來就只求效果,不問名義;效果得到,我的事就完了。不過這本書(引者按:指《邊城》)一到了書評家手中,就有了變故。一個說“這是過去的世界,不是我們的世界,我們不要。”一個卻說“這作品沒有思想,我們不要。”很湊巧,恰好這兩個批評家一個屬于民族文學派,一個應屬于對立那一派。③沈從文:《習作選集代序》,《國聞周報》1936年第13卷第1期。
正因為沈從文“不問名義”,因而他也主張,鄉土書寫不應該只有一種方式,就像他同年給李寒谷的信中所說:“在這些差不多的文章里,不是寫農村破產,就是寫天災人禍,俱差不多。所以我偏寫中國人的美德,發揚中國人的美德,如我的《邊城》,也有這個意義。”④沈從文:《沈從文的來信》,轉引自蒙樹宏:《郭沫若、沈從文佚簡六封》,《昭通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1998年第2期。類似的觀點,廢名談到《竹林的故事》時也曾表露:“我的文章……意思是,方面不廣。別方面的東西我也能夠寫,但寫的時候自己就沒有興趣。”⑤馮文炳:《竹林的故事·贅語》,《語絲》1925年第14期。換句話說,沈從文雖然對廢名朦朧的情趣、厭世的意識和奢侈僻異的文字略有微詞,并在這一層面與魯迅等人不謀而合,但就風景畫的描摹、美好人性的譜寫、地方風土的展現等層面而言,他仍認同周作人、廢名所開創的鄉土文學傳統,與李健吾等“京派”批評家達成了共識。這一問題的爭論,某種程度上也延續到了1949年前后——郭沫若把沈從文、朱光潛、蕭乾等“京派”重將全納入批判范圍⑥郭沫若:《斥反動文藝》,《大眾文藝叢刊·文藝的新方向》1948年第1輯。,馮乃超也抨擊沈從文對熊希齡的揄揚之詞⑦乃超:《略評沈從文的“熊公館”》,《大眾文藝叢刊·文藝的新方向》1948年第1輯。,文藝分歧與政治問題已經夾雜在一起,難分彼此。而1949年初,樓適夷的一篇《一九四八年小說創作鳥瞰》終于也將廢名與沈從文擺在同一平面,點名批評《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后》為“厭世主義和神秘主義”⑧適夷:《一九四八年小說創作鳥瞰》,《小說》1949年第2卷第2期。。同年開春,北平解放,廢名開始閱讀《新民主主義論》,提筆撰寫《一個中國人民讀了新民主主義論后歡喜的話》,思想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轉變。在這之后的長時間內,沈從文和廢名都停止了小說創作,兩人的復雜往來和關系也少有人問津,直到新時期以后,兩人之間的精神聯系才逐步得到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