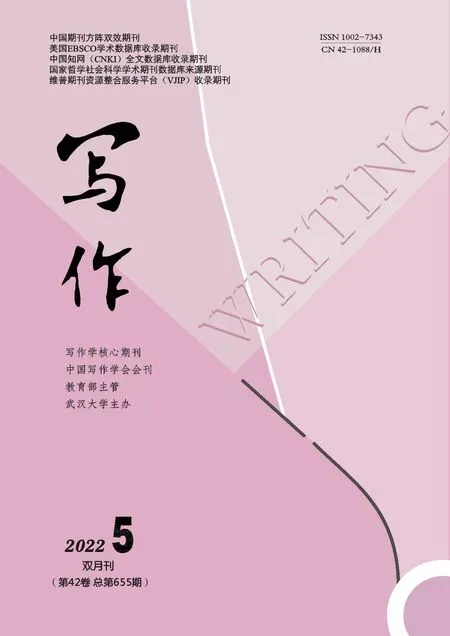方言的轉換與短篇小說形式的建構
——以葉煒短篇小說為例
郝敬波
多年來文學批評界有一種聲音:就小說創作而言,當下短篇小說整體上優于長篇小說。當然,這只是一種閱讀感受,缺乏學理性的論證。但這種聲音至少說明一點,即短篇小說創作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而且達到了讀者的某種閱讀期待。這種期待在很大程度上與讀者長期以來對短篇文體屬性的認知有關。短篇小說的獨特性早在現代小說觀念建立時就受到重視,比如胡適那個著名的短篇小說定義:“短篇小說是用最經濟的文學手腕,描寫事實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滿意的文章。”①胡適:《論短篇小說》,錢理群主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2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37頁。這個界定被認為開啟了中國現代短篇小說文體觀念的理論自覺。此觀念深受西方影響,借鑒了愛倫·坡、布蘭德爾·馬修斯等人的短篇小說理論。愛倫·坡是從“印象統一性”的角度標明短篇小說的獨立性,認為短篇小說家可以“利用較短的閱讀時間控制讀者的精神”,達到“效果或印象的統一性”②Edgar Allan Poe.“Review of Twice-Told Tales”,in Charles May eds.,Short Story Theories.Athens:Ohio University Press,1994.pp.46-47.。布蘭德爾·馬修斯繼承了愛倫·坡的觀點,進一步闡釋“印象統一性”的內涵,并使其得以廣泛傳播。無論是修辭意義上的“最經濟的文學手腕”,還是讀者閱讀感受的“印象統一性”,都指向了短篇小說世界建構的邊界,即該邊界顯示了短篇與長篇的差異性。那么問題是,什么元素造成了這種差異性?如果從現代語言學的角度來看,無疑是語言的選擇和使用,正如海德格爾所說:“語言是存在的家。人以語言之家為家。思的人們與創作的人們是這個家的看家人。只要這些看家人通過他們的說使存在之可發乎外的情況形諸語言并保持在語言中,他們的看家本事就是完成存在之可發乎外的情況。”①[德]海德格爾:《關于人道主義的書信》,熊偉譯,孫周興選編:《海德格爾選集》上冊,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年版,第358-359頁。可以說,語言選擇決定了小說世界的建構,決定了小說不同文類的邊界,短篇小說家的語言當然也決定了短篇小說的形式建構。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應該注意這樣一個現象:在創作發生時,許多小說家都是以方言來想象和建構世界的,在創作過程中又實施了方言的轉化。那么,方言的轉化與小說世界建構的內在關聯是什么?為了更集中地討論問題,我們選取一位“70后”作家——葉煒的短篇小說創作為例,并討論當下短篇小說的創新可能。
一、方言詞匯與小說的想象
“五四”白話文運動之后,現代白話文取代了文言文,確立了中國現代語言的基本狀態。在以后的國語運動中,方言問題一直爭論不休。特別是在現代文學語言的探討中,方言的意義更不可忽視,許多評論家和作家都賦予方言獨特的價值,比如胡適指出:“方言的文學所以可貴,正因為方言最能表現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話固然遠勝于古文,但終不如方言能表現說話人的神情口氣。古文里的人是死人;通俗官話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語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活人。”②胡適:《海上花列傳序言》,《胡適文存》第3卷,合肥:黃山書社1996年版,第365頁。周作人主張文學語言要吸收方言,以改善現代白話存在的詞匯貧乏問題。瞿秋白、劉半農、俞平伯等也就方言的問題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在創作實踐中,許多作家對方言也非常重視,“現代文學30年,絕大多數作家都是在兩者之間尋求平衡,就是既尊重普通話的權威,同時又在普通話的框架下,植入方言的內容,這種語言表層遵循普通話的規范,而內里面卻有著方言的活躍”③張衛中:《中國現代文學語言的發生與流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88頁。。在“十七年”和新時期以來的創作實踐中,作家使用方言呈現出節制和弱化的特征。“十七年”中由于國家層面對民族共同語、漢語規范化的強調,就像周立波、趙樹理這樣的作家也對方言的使用保持一種慎重的態度。新時期以來,由于西方文學的影響和作家代際的更迭,在創作中明顯呈現方言特征的現象并不算多。但值得注意的是,文本中稀疏散落的方言以及方言的轉換依然發揮著重要的審美意義。而這,應該是當代文學中方言運用的一個新變化,是文學語言變遷中值得重視的問題。由于短篇小說具有輕便、快捷的特征,方言使用的變化往往在其中更多地呈現出來;而且,在新的文學發展背景中,方言的留存與轉化為短篇小說的藝術世界提供了更多活躍和豐富的元素。
葉煒是近年來引起關注的“70后”作家,2019年獲得茅盾文學新人獎,其長篇系列“鄉土中國三部曲”(《富礦》《厚土》《福地》)和“轉型時代三部曲”(《裂變》《躑躅》《天擇》),都獲得了讀者和批評界的好評。如果閱讀葉煒,短篇小說是一個重要通道。葉煒的情感世界、經驗方式以及藝術氣質,都在短篇小說中呈現出來。從表面上看,葉煒的短篇小說不是方言特征非常明顯的文本,但方言卻發揮著不可替代的獨特作用。而這一點,也是目前新生代小說家創作中一個值得注意的語言現象。
方言詞匯是葉煒短篇小說世界想象和延展的起點。不難看出,葉煒并不打算過多地使用家鄉魯南地區的方言,沒有試圖在小說中更多地突顯方言特征。《母親的天堂》是這類小說的代表。《母親的天堂》是葉煒較早的一個短篇小說,他近期出版的短篇小說集也以此命名。小說寫的是母愛,是常見的題材。我們來看小說中的方言詞匯:大孩、砸紙錢、煎餅卷子、咸菜缸、干散活、煤黑子、沒吱聲、想的慌、姥娘,等等。方言并不算多,一般讀者也能夠理解。小說敘事是以母親去世展開的,敘寫了困苦的家庭、母親的辛勞、兄妹對母親的情感以及少年對世界的懷疑和迷茫。但這只是一種表層的描述,這種描述是以這些關鍵詞為中心的:鄉村,慈母,家庭,貧窮,含辛茹苦,勤勞持家,懷念。如果僅僅如此,小說就是一個帶有散文化特征或者慣常敘事方式的文本。值得重視的是,葉煒的小說想象是從方言詞匯開始的,這大大改變了小說敘事的走向。小說從“砸紙錢”的想象出發,進入回憶,敘述窘困的家庭和母親的艱辛,具體的情節漸次展開。而帶有“煎餅卷子”“咸菜缸”氣息的生活場景展現在小說世界中,也營造了小說的基本敘事氛圍。在這個基礎上,小說敘事并沒有生發更多的情節線索,而是依賴方言詞匯特殊的意義和情感色彩,簡潔有力地描述了一個家庭與命運的抗爭,同時表現了魯南鄉村的情感和精神世界,呈現了鮮明的地域文化風情和樸素的民間情感倫理。
同時,方言成為情節推進的重要元素,進一步豐富了小說的藝術內涵。由于短篇小說篇幅的限制,情節往往不能“旁逸斜出”,也不能做過多的鋪墊,否則就容易越過短篇邊界。此時,恰當的方言使用往往起到獨特的作用,方言詞匯在固有的內涵上能衍生出新的場景和人物,在受限的空間中起到拓展小說藝術的作用。《胡音聲聲碎》寫的是爺爺五義死后出殯的故事,小說敘事以此為中心延展開去,構成了一個別致、濃郁的鄉村風情世界。其中,“我”與前妻在爺爺葬禮上的相遇是一個重要的情節。而這一情節的發生,應該歸結于方言“破孝”一詞的使用。可以說,葉煒在這里對“破孝”進行了想象。小說對該詞沒有解釋,把理解的空間留給了讀者。“破孝”顯然不同于普通話的“開喪”一詞,在魯南方言中是指按照親屬遠近準備孝衣的慣例和行為,體現了該地域民間的孝道倫理。“我”的前妻是否可以“破孝”是喪事過程中一個討論的話題,前妻得以“破孝”則表現了兩個家庭在婚姻內外的復雜情感關系,這給讀者帶來了想象的空間,從而增加了小說的層次感。
可以看出,如果葉煒離開了方言的想象,小說世界不會是這個圖景;如果我們離開了對方言的體察和理解,也不可能與小說中所表達的經驗進行有效對話。方言元素有效參與了短篇小說世界的建構,并成為小說藝術形式的重要特征。
二、方言的轉換與話語方式
話語比詞匯和語句的意義廣泛,它包括話語主體、歷史文化等諸多因素。方言話語方式是指一個地域內的人們在歷史文化中形成的表達方式,它以方言為基礎,以特定的話語模式表達對世界的一種認知。“話語模式概括了特定歷史時期內某種話語的整體特征。話語模式既是一種言說方式,又是一種生存方式。它是言說者采用一定的言語方式觀照世界和表達自我的方式。①文貴良:《解構與重建——五四文學話語模式的生成及其嬗變》,《中國社會科學》1999年第3期。”話語模式作為話語方式的重要內涵,往往通過某種慣用方式呈現言說者的審美旨趣和審美態度。在方言的轉換過程中,方言話語方式對于小說世界建構的意義是極其重要的。
方言與普通話在語音上不同,許多作家在方言的轉換過程中,仍然基于方言語音的情感和韻味來開啟藝術世界的建構。相較于方言詞匯的使用,方言語音的轉換在小說方言特征的表現上要隱蔽得多,但它對小說世界的建構同樣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二姨》是葉煒一個篇幅很短的小說,開篇寫道:“二姨家離我們家很近,準確地說兩個村子之間只隔著一條河。河叫龍河,河北面就是二姨所在的村子北河沿,南面就是我們家所在的南河沿。”這看似平常的敘述,卻形成了整篇小說的敘事基調,而這個敘事效果與“河沿”的語音有關。“河沿”是魯南的方言,“沿”的讀音與其普通話的語音也不同,與“挨”的讀音相近。顯然,作家對這個方言語音進行了轉換。方言“河沿”的語音中有濃厚的情感色彩,“北河沿”“南河沿”具有關系緊密的意味。它們并置在一起,不僅指的是在空間上相近,而且在人們的感覺中二者是一體的,不是村與村之間的距離。如果不考慮語音,那么“北河沿”“南河沿”可以寫成“河北岸”“河南岸”,如此,語音的情感意味就消失了,接下來的小說敘事的意蘊就會寡淡很多。讓我們感興趣的是,葉煒正是從方言的這種轉換中開始了對小說的建構,敘寫了二姨與“我”家常來常往的關系以及二姨苦澀的命運遭遇。正因為“河沿”的空間、情感意義,小說敘事的延展才省略了許多鋪墊,呈現出短篇小說簡潔悠遠的文體特征。
一個地域慣用的表達方式是方言話語方式的重要內涵,它主要指方言在歷史過程中形成的固有表述習慣。這種習慣不僅表現在方言語法上,還表現在某種樸素、簡潔的“概括”方面,比如北方方言中的“瞎子嫁了啞巴”“說書唱戲過活”等。這種“概括”往往表現了民間關于生存、世界的認知,特別是關于人生命運的某種態度和立場。莫言著名的短篇小說《白狗秋千架》就是在“瞎子嫁了啞巴”的表述中展開想象的。小說中,活潑、漂亮的“暖”在打秋千中摔瞎了一只眼睛,命運從此改變。后來“暖”嫁給了鄰村的一個啞巴,生下的三個孩子也是“小啞巴”,她渴望能生一個會說話的孩子。莫言在小說中用“獨眼嫁啞巴,彎刀對著瓢切菜”來表達對女主人公命運的感喟,其表述方式顯然帶有方言的特征。“說書唱戲過活”是魯南民間對過去藝人的一種描述,這些藝人走鄉串戶,依靠說唱謀生。在艱難的生存過程中,藝人流落他鄉、經歷豐富,因此這樣的表述往往飽含了對人生命運的悲嘆,同時也融入了富含奇聞怪事等元素的藝術信息。葉煒的許多短篇小說正是如此,在這些文化意蘊中鋪展小說世界。《先世考系列》敘寫了家族中幾個先祖的人生命運。小說對每個人物的展開,都是從“唱戲”開始的。譬如,劉安邦從“戲班子”的角度切入,劉安慶以“戲子”為線索展開敘述。“唱戲”與人物的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有著特殊的關聯,這也成為葉煒創作情感的源起和小說世界建構的通道。《胡音聲聲碎》的敘事以“請響器”為中心進行延展,描繪別致的鄉村風情世界。“請響器”一詞,在魯南方言中應為“請喇叭班”,葉煒在這里進行了轉化。“喇叭班”中的二胡是最具特色的主要樂器,葉煒以此為基點實施想象,把唱戲、二胡、謀生、命運融合在一起,在“說書唱戲過活”的意蘊中敘述了爺爺五義頗具傳奇色彩的“二胡人生”。此外,《民間傳說三則》《市井兩題》等小說也具有類似的特征。
葉煒的短篇小說還通過對方言的轉換表達鄉土文明中的生存觀念,從而把小說主題進一步引向深入。《種在陽臺上的莊稼》是一篇構思精巧的小說。從題目可以看出來,小說突出了對城鄉關系的思考。小說中的事件并不復雜,寫進城的老爺子在兒子家的陽臺種莊稼的故事。小說出現的方言很少,但有一個表述值得注意:莊稼長在地里。在閱讀感受中,我們感覺這句話不能停留在普通話意義的層面,它具有對方言話語方式轉換的意味,是對魯南方言“都在地里哩”“到地里去呢”的一種理解和想象。譬如,小說中寫道:“東子說,哦,你說莊稼長在地里,那什么是地里?一句話讓老爺子愣了半天,這地里就是土地呀,就是……你看,這路兩邊的花壇里面都是土,成片成片的土就是地。東子似懂非懂地點點頭。”顯然,“老爺子”也語焉不詳,對自己的解釋也感到言不盡意。這里的“地里”從內涵來說,不同于普通話中“土地里面”的意思,不盡同于“土地”“田野”,包含了更多的語氣和情感因素。在魯南地區,方言“地里”一詞與“家里”相對,農民的世界就是由“家里”和“地里”構成,農民的存在要么“在家里”,要么“在地里”。而且,“地里”是家里的保障,沒有了“地里”,也就沒有了“家里”。方言中的“都在地里哩”“到地里去呢”的話語方式,即隱含著這些情感信息和認知觀念。“老爺子”住進了城里的樓房,也就失去了“地里”,他的世界就不完整,因而必須在陽臺建造一個“地里”的世界。這是讀者進入小說世界深處的通道,而這個通道也必須借助對方言的轉換及話語方式的理解來建立。
方言話語方式的吸收是作家與區域歷史文化的一種對話形式,這種對話往往是作家離開故土多年以后開始的。這個時候的作家可能淡忘了方言的詞匯,或者對方言詞匯進行了“雅化”處理,但是,方言的話語方式卻隨著童年經驗一起滲透到血液中,成為鄉愁的一部分,也成為對世界認知的一部分。我們在了解相關的方言后,并不難發現小說世界與方言話語方式之間的重要關聯。由于短篇小說具有“印象統一性”的文體屬性,這種關聯性就顯得尤為突出。更為重要的是,二者之間的關系往往構成了當代短篇小說獨特的藝術品格。
三、方言的轉換與文體的探索
從上面的討論可以看出,方言詞匯、方言的轉換在短篇小說的創作中具有獨特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這并不是一個簡單的語言特征問題,在文體探索的進程中,該現象提供了新的價值標準生成的可能性。
在當代文學的發展進程中,文體探索是一個重要的特征。“中國當代文學的各種文體都在反思中前行,在前行中反思,并且日益發展和進步,這是不爭的事實。但也存在諸多問題,其中尤為令人憂慮的便是在消費潮流裹挾下文學自身的迷失以及創造性的弱化。目前,中篇還沉浸在崛起的喜悅之中,正與長篇分享被消費的快感,長篇還在以‘重文體’的面目追求著史詩般的深度。文體等級化對文學性和藝術性本身的忽略與傷害無疑值得我們警惕。”①郝敬波、吳義勤:《新時期短篇小說文體反思》,《文藝研究》2012年第6期。耐人尋味的是,當代小說文體的探索如意識流的嘗試、結構的散文化、語言的試驗等等,大多較早出現在短篇小說中,可以說,短篇小說是文體探索的“試驗田”。那么,諸如葉煒短篇小說中的這種方言轉換是不是小說文體探索和前行的某種征候呢?
方言的轉換為小說敘事探索提供了更多的可能,能夠有效地拓展故事容量和情感內涵。就小說傳統承繼而言,古代的“話本”和“筆記體”對后來的小說創作影響顯著,前者重故事,后者重情蘊。1980年代的“新筆記體”小說名噪一時,其表現特點是“以敘述為主,行文簡約,不尚雕飾”“不重情節,平易散淡,文思飄忽”②李慶西:《新筆記體小說:尋根派也是先鋒派》,王曉明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論》第3卷,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416頁。。新時期以來,受到西方文學思潮的影響,許多小說家在情節設置、語言陌生化等方面進行了實驗。無論文學理論如何翻新,“故事”仍是小說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因此,故事容量依然是衡量小說創作成敗不可忽視的尺度。如何在有限的敘事時空中最大限度地擴大“故事”和“情蘊”的容量,上述短篇小說中的方言特征或許可以為我們帶來某種啟示,甚至可能成為一種新的評估標準。在創作過程中,小說家選擇的方言詞以及對方言的轉換,在很大程度上都負載了故事和情蘊的密集信息。一個地域的習俗、傳說、觀念等往往包含在方言中,一個方言詞匯和話語方式常常具有傳聞軼事講述的內涵,同時也隱含了人生體驗的情感表達,二者體現了民間特有的審美觀照和情感方式。方言詞匯和話語方式一旦出現在小說中,尤其在短篇小說的敘事方式中,那么它們所起到的擴容故事和情感的作用便顯現出來了。而且,經過藝術轉換,方言又傳遞著小說家的主體經驗與情感認知,進一步豐富了小說的藝術世界。
方言在轉換過程中對故事和情感擴容的特征,并不是表現在小說敘事的表層,而是依靠方言的獨特力量滋生在小說世界的深處,而這恰恰突顯了短篇小說雋永、綿遠的藝術品格。其實在創作實踐中,一些作家的短篇小說已經呈現出這樣的藝術特質,只是在創作思潮的不斷更迭中沒有引起批評界的重視。譬如,莫言的短篇小說《售棉大道》《大風》《石磨》《枯河》《秋水》《白狗秋千架》《草鞋窨子》《遙遠的親人》等都有方言的轉換特征,從而表現出莫言對短篇文體探索的努力。在短篇小說的創作中,葉煒在方言使用和轉換的路徑上延續了這種努力。小說《先世考系列》開篇介紹了劉安邦背負家族厚望去省府鄉試,路上得知鄉試已取消掩面大哭,之后便跟隨路上遇到的戲班子四處游蕩:“哭了半天,抬頭一看,戲班子已經走出好遠。劉安邦想了想,既然人家不舉狀元了,那還是往回趕吧。他三步兩步追上戲班子,問老者:老人家這是要到哪里去唱戲?老者笑著說:戲班子嘛,走到哪唱到哪!劉安邦也笑:那俺跟著你們去聽聽戲!既然考不成狀元,也就當是耍耍了!”上文已討論過,這種敘述與方言的轉換有著重要的內在關聯性。這段話講述了一個事件,或者說敘述了一個故事梗概,小說由此為起點展開其他情節。就此敘述而言,其中也有矛盾和沖突,一位追求名利的考生很快轉變為“戲班子”成員的身份,頗具戲劇化色彩。不僅如此,這種敘述也具有情感元素。讀者在情節之外,還能體悟這種敘述方式傳遞著民間的幽默和曠達,以近乎調侃的方式感受命運的轉變。顯然,對這種故事和情感的感知,我們是在方言語境中完成的。
故事容量和情感內涵的有效擴充,為小說敘事方式的創新提供了新的可能。新時期以來,小說的形式創新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說,新時期小說的發展史就是文體的創新史。借鑒西方藝術經驗,挖掘民族的文學資源,成為小說創新的主要路徑。近幾年來,如何講好中國故事、積淀中國經驗成為人們討論的話題,也是許多作家進行藝術創新的價值取向。從這個意義上說,在時代背景中對方言進行藝術處理,創作出更多故事和情感容量豐富的小說,無疑是培養、生成中國文學經驗的重要方式。在這個過程中,傳統的文學形式往往被賦予新的內涵,并煥發出新的藝術生機。譬如葉煒在《胡音聲聲碎》《民間傳聞三則》《市井兩題》《榆木彈弓》等小說中,就表現出對“傳奇”的小說敘事方式進行藝術創新的訴求,并呈現出宏闊而純凈的文體風格。當然,對方言的選擇和運用是建立在作家生活經驗基礎上的。葉煒通過方言來想象世界,實際上也是自己經驗世界的表達。這種表達往往是樸素的和感性的,呈現了具有地域特征的、豐富鮮活的生活和歷史場景。還應該注意到,在小說中方言提供的不僅是延展,同時也是一種限制。方言的意義有約定俗成的邊界,使用方言當然不能突破這種邊界,即使實施了方言的轉化,作家也只能把詞語的意義停留在方言的意義區間內。葉煒通過對方言詞語的選擇與轉化,有效把控了文體的自由與邊界,生成了個性化的短篇小說世界,并提供了文體探索的某種啟示。“小說的內在意義必定是具有創造性的,在創作過程中作家總是把一些分散的異質成分聚集在文本中,經過敘述者主觀審美意識的揚棄,融合成純粹的審美內容。”①李騫:《論鐵凝小說語言的敘事藝術》,《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0年第5期。小說家如何在創作中突破經驗局囿,拓寬審美視野,進行更為自覺的“方言實驗”,生成和積淀更為豐富的中國文學經驗,則是包括葉煒在內的當代作家需要長期面對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