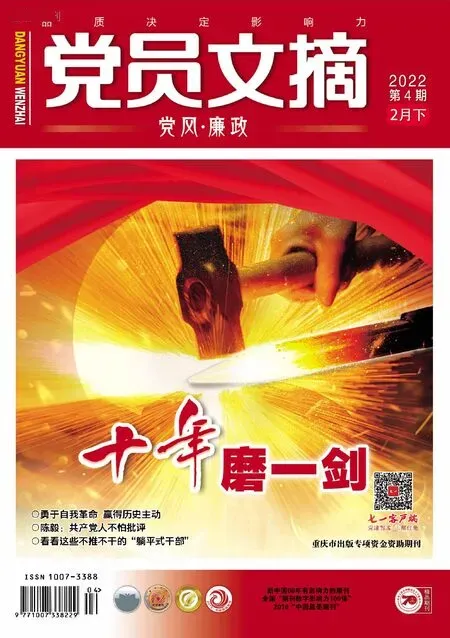古代官衙“三字箴”
馬軍

中國古代特有的政治文化內涵豐富,底蘊深厚。作為地方行政中心的古代官衙,其門楣上的三字官箴就是先人留下的一筆寶貴精神財富。
“公生明”三字最早語出《荀子·不茍》,“公生明,偏生暗”。也就是說,沒有偏心便沒有偏見,也就不會滑向偏激的泥沼;公正,便沒有先入為主,沒有影響判斷的各種人為因素的干擾。滄海月明三萬里,扶桑亮徹遍宇宙。物之理,事之理,天地之理,人之是非還能不明察秋毫嗎?明代時,泰安知州顧景祥認為,無論是做人還是做官,若能夠真正領悟這三個字的妙處,并能身體力行之,就不僅能夠走得穩健,更能走得長遠,一生無憂無慮。弘治十四年(1501年)八月,他以“公生明”三字為骨架,寫下一則《官箴》并刻石置于泰安府衙:“吏不畏吾嚴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則民不敢慢,廉則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這被有信仰、有理念、有操守的官員們所認同。
“公生明”三個遒勁有力的大字,每個進出衙門的食俸者隨時都可以目睹之,心念之,有公則有明,則不會生糊涂念頭,說糊涂話,做糊涂事,雖處風波之地亦可閑庭信步安然無恙矣。
《呂氏春秋·察賢》記載了這樣一個典故:春秋末期,孔子的弟子、魯國人宓子賤受命治理單父(今山東省菏澤市單縣),他沒有事必躬親的習慣,只是每天在堂上靜坐彈琴,就把境內治理得井井有條。境內百姓有口皆碑:“這是個好琴師,更是個好官。”宓子賤升遷到別的地方后,繼任者叫巫馬施。巫馬施終日披星戴月,晝夜不閑,最后治理得也不錯。巫馬施向宓子賤詢問其中的緣故。宓子賤說:“我的做法叫用人,你的做法叫用力。用力做事的人當然勞苦,用人建功的人當然安逸。”
這個境界就是“無為而治”。不過,宓子賤這個“無為”并非什么事情都不干,而是因勢利導,順勢而為,讓百姓感覺不到有人在管治他們,卻已經悄悄地、自然地、潤物無聲地實施了有效治理。宓子賤看似彈琴作樂不務正業,其實,他之所以能夠如此逍遙,安享太平,是因為下屬工作做得好。他連門都不出,如何才能這樣?顯然,是他的知人善任、政清事簡之故,所以才能收到事半而功倍的效果。可見,“鳴琴而治”,不只是一種高超的領導藝術,也是深得“大道至簡”的真髓,從而達成“以簡馭繁”。
歷代皇帝都很推崇宓子賤這樣的官員,不管能否做到,后來的官吏們都以宓子賤為標桿。于是,縣衙的二堂逐漸有了另一個名字“琴治堂”。“鳴琴而治”的核心是一個“仁”字,“琴治堂”的楹聯便是極好的詮釋:“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負民即負國,何忍負之!”
“清慎勤”,“清”即清廉,“慎”即謹慎,“勤”即勤勉。此三字由來已久。西晉時,晉武帝司馬炎對臣下語重心長地做了這樣的闡釋:“為官長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宋朝呂本中進一步引申曰:“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祿位,可以遠恥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明朝《功過格輯要》又有新的詮釋:“操持不外‘清、慎、勤’三字。清者大節,慎者無誤,勤則能理,昔人所謂三字符也。”
“清慎勤”三字,歷代都有良臣賢吏以生命釋之。“清”者,官之本,“慎”者,官之要,“勤”者,官之基。有“清”則氣正和諧,有“慎”則承平恒久,有“勤”則成事有望。心勤就會多智,腦勤就會多思,眼勤就會多看,耳勤就會博聞,腿勤就會多功,手勤就會多成。天道酬勤,萬古不易。
白居易在《自到郡齋題二十四韻》中寫道:“救煩無若靜,補拙莫如勤。”古人對此曾一再告誡:“業精于勤而荒于嬉。”哪怕再聰明,再能干,只要被“惰”字所俘虜,則一生必懈,必敗無疑。清朝政權是從朱明王朝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所以,清初的皇帝們個個都是勤于政務的“拼命三郎”,特別是雍正皇帝,平均每天批閱的奏章都有10000多字。雍正皇帝的勤政效果是顯著的,為后來乾隆時期走向全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無數事例都說明了一個淺顯樸素的真理,那就是,只要能勤,即可補拙、補缺、補陋,創造令人贊嘆的奇跡。
“儉”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老子說他平生有“三寶”,其中之一就是“儉”。孔子也大力提倡節儉,反對奢侈。諸葛亮曾以“儉以養德”教育其子。司馬光在《訓儉示康》中也著力論述了“儉”之于一個人厚德立業的重要性。商紂王成為一個遺臭萬年的亡國之君,究其原因,就是一個“奢”字。
晚清著名政治家曾國藩每餐只用蔬菜一品,絕不多設,被稱為“一品宰相”。他在年輕時添置的一件馬褂,一直穿了30年。他在家書中屢屢告誡子侄:“以奢為尚,漫無節制,此敗家之氣象也”,“勤苦儉約,未有不興,驕奢倦怠,未有不敗”。曾國藩深知,嚼得菜根,百事可做。守住一個“儉”字,便可以立于不敗之地,而貪圖物欲奢華,居江湖必為盜,居官衙必為賊,最終必定會身敗名裂甚至禍及子孫。與之相比,清清白白一生,堂堂正正一世,萬古流芳的廉潔之吏,不知要清醒睿智多少倍。
在專制閉塞的封建社會,政府衙門竟能倡行這樣富有遠見和智慧的政治文化,而且還有那么多有識之士終身篤行踐履,確實值得今天的我們省察、借鑒與深思。
(摘自七一網 七一客戶端/《北京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