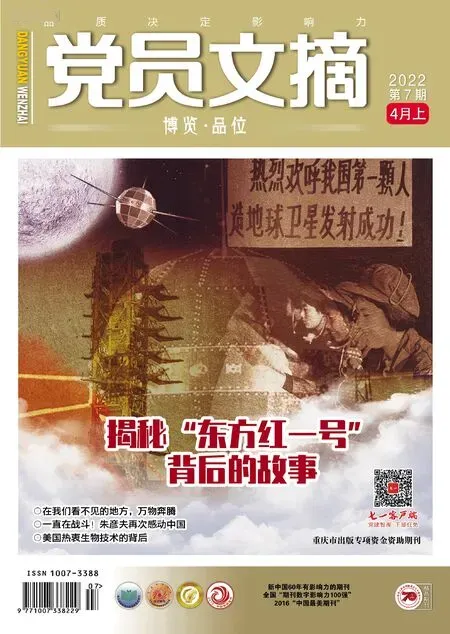從未松開與命運抗爭的手
江夢南 歐媚

江夢南。新華社
半歲時,因藥物導致失聰,在父母的幫助下,她通過讀唇語學會了“聽”和“說”,并憑借不懈努力,成為清華大學的一名博士研究生。
生活、成長、求學,每一步都是“困難模式”,她卻說:“我從來沒有因為聽不見,就把自己看成了一個弱者。我相信自己不會比別人差。”
她就是感動中國2021年度人物——90后姑娘江夢南。
在頒獎典禮上,主持人白巖松在對江夢南的頒獎詞中是這樣宣讀的:“你覺得,你和我們一樣,我們覺得,是的,但你又那么不同尋常。從無聲里突圍,你心中有嘹亮的號角。新時代里,你有更堅定的方向。先飛的鳥,一定想飛得更遠。遲開的你,也鮮花般怒放。”猶如她的成長之路一樣讓人尋味。
現在,讓我們一起來看看,江夢南講述自己的故事。
1992年8月,我出生在湖南省郴州市宜章縣莽山瑤族鄉一個瑤族教師家庭。我的父母覺得女兒隨父親姓趙取名不好聽,就讓我隨母親姓江,取名江夢南。
半歲那年,我因肺炎持續高燒。當時,父母遠在100多公里外的郴州市醫院照顧生病的外公。奶奶獨自在農村老家照看我,見高燒不退就帶我到鄉醫院打針,治療一個多星期始終不見好。
父親收到我高燒不退的信息后,急忙把我帶到郴州市醫院治療。又一個星期過去,我的高燒總算退了下來。然而,父母突然發現,我對外界的聲音沒有了反應。
父母急了,他們帶我到長沙湘雅醫院做檢查。醫生的診斷結果是:無聽力,系極重度神經性耳聾。
母親聽到結果后都癱軟下去了。可他們不相信,繼續帶著我跑遍長沙的大小醫院,后來又去了北京,最后不得不承認——他們的女兒就是聽不見了。
父母對我是抱有很大期待的。而我當時的情況,別說上大學,能像正常孩子一樣開口說話的希望都渺茫。
父母也考察過聾啞學校,但他們不甘心自己的女兒就此用手語交流過一輩子。他們始終相信,鐵樹都能開花,女兒也一定能開口說話。
既然聽力不能恢復,我的父母決定帶我走言語康復這條路,教我讀唇語,學說話。
每天,我背對著母親坐在她懷里,面前放著一面鏡子,通過鏡子我既能看到自己的口型,也能看到母親的口型。母親握住我的手,放在她的喉嚨上,讓我感受聲帶的振動和呼吸的氣流,再放在我自己的喉嚨上,學習喉嚨振動與口型變化的關系。
這是一個艱難的過程,準確地看懂和發出每一個音節,要經歷成千上萬次的練習和糾正。不管多么難,父母都沒有放棄我。有時候,父親會從睡夢中驚醒,滿頭大汗。
父親說,再難的時候都沒有最開始難,當我能發出第一聲“啊”的時候,一切都不難了。其實,他們也不知道經過這樣的訓練,我能否像正常孩子一樣開口說話,只是笨笨地一遍一遍地重復。

江夢南常常到圖書館看書。新華社
到我兩歲時,我的語言能力和同齡孩子已經相差不大了。我終于能清晰地喊出“爸爸”“媽媽”,還會說普通話和宜章方言。父母沒能從命運手中奪回我的聽力,但是他們卻教會了我讀唇,教會了我說話。這對我來說,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能力,是父母給我最珍貴的禮物。
當然,我曾經也向父母抱怨過,為什么我聽不見,為什么是我?父母跟我說,聽不見是既定事實了,與其怨天尤人,不如更加努力去克服困難。那時候我雖然還小,但已經意識到自己未來的路,要比身邊的小伙伴們更難走,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上小學后,因為我聽不見,只能看老師的嘴型,所以我都是坐在教室前排中央,時刻處在老師的監督之下,沒有辦法“開小差”,因此注意力高度集中。老師也不是每時每刻都面向我,所以只靠上課聽老師講,我很難理解消化全部的知識。父母預料到我的困難,總是帶著我提前學,比如上學前班時,就提前教我一年級的內容;上一年級時,就提前學二年級的內容。笨鳥先飛早入林,小學四年級以前,我一直都是班上的前三名。
雖然聽不見,但我從來沒有把自己當作弱勢群體。因為晚一年上小學,我想追上小伙伴的進度。四年級結束時,我向父母提出想直接讀六年級的請求。利用暑假,父母幫助我自學完成小學五年級的課程,學校考核合格后我直接升入六年級。
小學畢業,我作了一個大膽的決定:我要像那些學習優秀的孩子一樣,到離家100多公里外的郴州市上重點中學。

努力學習的江夢南。新華社
父母無微不至地照顧我生活,輔導我學習,給了我極大的愛,我非常感謝他們,但是我早晚要離開父母,我的未來在遠方。我聽不見,就更要盡快地適應外面的世界。
父母盡管舍不得,但還是支持我的決定。事實上,我遠沒有表現出來的那么堅強。到學校第一個月,人生地不熟,又看不懂老師和同學們的口型,同學們也不了解我的情況,我常常躲在被子里哭,自己選的路又不能后悔,真的很無助。
我初次離家遇到的困難,父母心知肚明,他們只是沒有說破。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一個周末,他們給我發了一條短信,是少年毛澤東離家求學時寫給他父親的“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父母每天的短信,成了當時我唯一的精神支柱。
在郴州讀書的那幾年,我真正堅強起來了,還交到了很多好朋友,融入了集體。獨立生活、獨立思考和自學的能力都得到很大提升,就連后來考上吉林大學,去幾千公里遠的東北,也是我獨自乘火車去的,沒要父母陪同。
這一路走來,可以說是不斷過關斬將。雖然我天性樂觀開朗,但是不得不承認,聽不見真的給我帶來很多困難和麻煩。
因為我是依靠面對面讀唇來和其他人溝通,學習上是通過看教材或者課件自學,可以說眼睛代替了我的耳朵。但是,生活中總是有看不見口型的時候。
比如,我報考清華大學的博士研究生,接到清華大學給我打來的復試電話時,我不知道對方在電話里說什么,只能看著手機屏幕干著急,幸好我的朋友及時回來幫我接聽電話;在機場,我聽不見廣播的聲音,容易錯過航班延誤或取消的信息;在學校上大課時,我需要花比別人更多的時間去理解老師在講什么。
我小時候想當醫生,覺得那樣或許能治好我的耳朵。后來我發現當醫生要戴口罩,那我就沒法和其他人交流,于是選擇了藥學。由于聽不見聲音,做化學實驗會很危險,在博士研究方向上,我又選擇了相對不那么受聽力限制的生物信息學。
這一路過關斬將,讀唇語、開口說話、上大學,需要感謝的人特別多,更感謝這個時代對特殊群體的包容和鼓勵。
上中學時,英語聽力考試都是老師幫我讀出來代替廣播;中考時,郴州市教育局專門為我設置了一個愛心考場,考場只有我一個人,兩名老師在我面前讀聽力;高考時,國家對殘疾人參加統一高考出臺了專門的政策,聽力障礙的考生可以按照筆試成績乘以系數計算英語聽力部分……這些竭盡全力對我的關愛,讓我能更加順利地學習和生活。
現在,我做了人工耳蝸,正努力學習把聽到的聲音和意義對應起來。我買了一套外國人學中文的教材,從簡單的詞語和對話開始學習。父母現在也經常給我發微信語音,我反復地聽,訓練聽力,似乎又回到了小時候訓練讀唇和發音的日子。
清華大學很大,我買了一輛自行車。騎車是小時候在湖南老家學會的,醫生說聽力障礙的人騎車會比較困難,很難掌握平衡,但我騎得很好。只有騎上高高的山坡,才能看到很開闊的風景。未來,我相信自己還能看到更遼闊的風景。
(摘自七一網 七一客戶端/《中國教育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