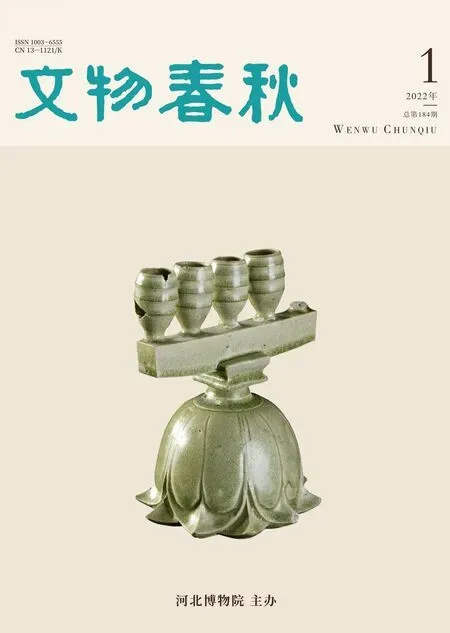民國時期建筑遺產科學保護史事探要
史勇
【關鍵詞】建筑遺產保護;史事;民國時期
民國時期的建筑遺產科學保護是在官方、專業人士和民間力量共同影響與作用下促成的。1947 年,國民政府行政院北平文物整理委員會曾強調指出:“文整事業,具有專門性、繼續性及全國性,必須養成特殊技術人員,盡量利用近代科學方法,以發揮古建筑之美點。”[1]梁思成關于中國建筑遺產保護修復的一個基本觀點就是:在保持古建筑原有面貌的前提下,要盡量使用現代技術[2]。中國營造學社總結提煉的可供中國借鑒的日本建筑遺產保護經驗之一亦是“應用科學設備,防止一切災害”[3]。20 世紀20 年代以后,一批專攻建筑的中國留學生相繼學成歸國:劉敦禎于1923 年創辦蘇州工業專科學校建筑工程系,梁思成于1927 年創辦東北大學建筑系,劉福壽于1928 年創辦中央大學建筑系[4],這既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民國時期建筑專業教育的發展,又為民國時期的建筑遺產科學保護提供了適宜的專業氛圍與人才儲備。1935年,中國佛教界人士赴日考察,對東瀛近鄰的古建筑科學保護感觸頗深:“(奈良東大寺)設備防火用水道費六千五百八十余圓,避雷針費四千八百余圓。因為修理工程之細密堅固,所以去年大阪京都關西一帶的大風災,大佛殿絲毫未曾搖動”,因此呼吁國內業界應重視古建筑之科學保護[5]。民國時期建筑遺產保護史上不乏科學之光閃現,是為中國文物保護史不應遺忘的重要史事。本文擬從三個方面探其要旨。
一、建筑遺產病害機理之認知
著名文化遺產保護史專家尤嘎·尤基萊托認為:“建筑遺產不斷經受各種各樣的破壞,包括風化、自然老化和因使用產生的破損……建筑物的損耗程度是由其結構類型和建造材料決定的。”[6]考諸史料,民國知識界關于建筑遺產病害機理之認知,大致可分三類。
(一)中國傳統木構建筑壽命有限成為共識因自然環境、生產力發展水平和建筑文化等方面的理念差異,中國古建筑始終對土木情有獨鐘,并保持了長期的一貫性和連貫性[7]。盡管民國知識界對于中國傳統木構建筑的價值和優點贊不絕口,但也并不否認其因自身材料特性導致的難以長久保存的事實。梁思成一方面認為“木建筑物之長久存在并不是完全不可能”,同時也承認自然因素對于木構古建筑的影響往往致命:“中國建筑自有史以來就是以梁柱為骨干的,而這骨干的材料一向以木為主;木本不是不朽的物質……千余年的風雨蝕剝,蟲吃蠹穿,也足以毀壞不少了……時代比日本奈良法隆寺相差四五百年的宋遼建筑已是中國稀有的古建筑,崩壞不堪,唐代遺物更不用幻想。”[8]早在民國初年,即有專業人士比較了因建筑材料不同而導致的中外建筑壽命的差異,認為中國傳統土木建筑壽命遠不如其他東方國家之石質建筑:“埃及印度諸國之古代建筑,則多以石為之。故尼羅河畔,至今猶有數千年前之大塔存焉,足以令游客一見而知其為文明舊邦也。我國古人所興之偉大建筑,雖史不絕書,然存者甚鮮。今即欲求千年前之宏大建筑物,已渺不可見。則因其皆為土木所成也。”[9]對中國傳統建筑有所研究的非專業人士亦多持類似觀點,如黃濬認為:“吾國雖以舊邦著于世界,然大建筑物,除長城外,鮮能保全,殿宇廨舍,率用木材,故也。”[10]
(二)科學分析石質建筑遺產病害成因除傳統木構建筑外,石質古建筑亦為中國建筑遺產重要組成部分。民國時期,中外學者對于影響中國古代石質建筑保存的自然因素多有科學分析。1914 年,法國人色伽蘭在中國西南地區進行田野調查時曾就四川漢代石質建筑遺產受雨水和植物影響而導致的堪憂保存狀況作如是描述:“四川漢代建物保存之程度不等,諸建物皆以沙石為之,惟產地與本質有別耳。渠縣之闕,以薔薇色細沙石為之,其細密部分,尚保存完好。梓潼之建物,以褐黑色沙石為之,石質粗而易毀,故多為雨水剝蝕。又如植物之生長,亦妨害建物之保存。梓潼之楊公扶壁,初與其主闕分離,旋為大樹所倒。綿州左方之闕,已因樹根生長,石層側面裂開。雅州高頤闕上有小樹一株,正在助其崩解。”[11]1929 年,趙邦彥在云岡石窟保存狀況調查報告中指出:“云岡諸巖,多系沙石所成,不易持久。風雨摧折于外,山泉漸滲于內,經歷千有余年,今所存者不過昔日三分之二。”[12]1934 年,上海《申報》記者陳庚雅考察云岡石窟時亦如是記述:“目力所及,皆有佛洞無數,長凡四五里,均為渾然一崖所刻成,惟久經風雨削蝕,朽壞較有殿宇之處為甚。然此自然現象之消失,或為人力防避所難及。”[13]1942 年夏,任乃強在西康考察時,認為該省境內古物“價值最高者,其唯樊敏碑乎”,同時分析指出,此種石質之碑“但如露立,與雨水接觸,或為植物根葉所侵,或受地面重濁之碳酸氣所蝕,則因其中所含石雜質解離,石質不復堅硬,稍細錘拓,即至剝敗”[14]。
(三)總結自然災害中的建筑遺產破壞特征以地震對建筑遺產之影響為例,民國時期強震多發,古建筑因此受創頗深。1920 年12 月16 日之海原大地震波及現甘青寧諸省,著名地質學家翁文灝曾就地震應力波導致的災區古建筑結構破壞現象進行過特征歸納與描述:“震中區域內,雖厚至數尺乃至丈余之城垣,亦多傾倒……愈高聳之建筑愈易坍塌,故城垣之雉垛及鐘鼓樓等,最易受損。他如鐵旗桿、神道碑等有截為二段者,力大可知。”[15]
二、建筑遺產科學保護方案之制定
1933 年,戴志昂曾以擬議中的洛陽白馬寺修復工程為例,強調在古建筑修繕工程中“復古”與“采新”同等重要,既要最大限度恢復歷史原貌,又要有針對性地應用新材料或新技術:“現所望于將來負責設計者,不在墻破補墻,梁斷換梁;而在注意于復古而不失其真,采新而不礙于全體之調合,則其有益之新于中國建筑,非淺鮮矣。”[16]在民國時期的建筑遺產科學保護方案中,應用鋼筋水泥成為較為普遍的現象。如龍門石窟之修繕,“建設廳已屢次派員赴龍門測勘,由技師劉文寶繪制修筑設計圖,大體就舊有寺院基址興建寺舍,其型式采用中國式,而為保存久遠計,材料參用鋼條水泥”[17]。四川省水利局制定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治標計劃綱要》中亦指出:“都江堰所有永久建筑物,以水泥砌筑,以求經濟性。”[18]24有的建筑遺產修繕工程方案還注重采用現代工程設備,如北平市政府關于北平游覽區名勝古跡修葺第一期計劃提出,為保證故宮午門、東西華門、紫禁城及角樓等修繕工程順利開展,擬購置修繕古建筑物特用工具一批,包括特制活動云梯兩具,拔草器、吸塵機各三具,汽車一輛,其他工具若干[19]。在前期相對扎實的調查研究基礎上,民國文物保護界還曾制定過注重整體保護和多種科技手段綜合應用的建筑遺產科學保護方案。茲引述兩例:
(一)定興縣北齊石柱整體科學保護方案20 世紀30 年代初,中國營造學社考察河北定興縣北齊義慈惠石柱后,提出了包括本體糾偏、水泥修補、化學清洗、防雷等科學保護措施的保存意見,具體方案如下:1. 石柱附近土質系普通黃土,日久雨水沖刷,必至崩潰影響柱之安全。尤以此柱基礎石質不佳,其一部露出地面上者,不宜令其永久暴露風雨中,受氣候之凌轔。宜速將柱礎附近低凹處,填筑使平,其上做水泥地面,掩護柱基,使微成斜狀,導雨水外流。2. 柱巔石屋,宜裝避電針。3. 石縫及一切孔穴,最易停留泥土,滋生草木,宜洗剔清凈,用純洋灰調色填補,使與石色一致。4. 石之表面,為防止受氣候影響,發生崩毀計,應全部洗滌,涂solution of sileate of soda(蘇打硅酸鹽溶液)及solution of chloride of caleium(氯化鈣溶液)類保護之。5. 嚴禁公私拓印頌文。保存意見特別強調“以上五項所費無幾,而于延長柱之壽命,收效頗巨”[20] 。
(二)登封古觀星臺整體科學保護方案1937 年春,國立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組織專家對河南登封古觀星臺(周公測景臺)進行勘察測繪,并提出了保護修繕意見。關于古測景臺之保護,專家組認為:“為恢復原狀計,自宜全部拆卸,重新裝配。但石質風化已久,裂縫極多,偶一不慎,即足發生破裂危險。為安全計,僅清理石面石縫,用洋灰調色鉤模嵌補,外部再以石欄縈繞,以資保護。”關于古觀星臺之保護,專家組一方面考慮到自然因素對古建筑本體的侵害,提出沿臺腳筑四呎寬散水道一周,防止雨雪下浸,將周圍樹木離臺基過近者移植他處,臺壁上雜草樹根全部刈除凈潔,另一方面指出,“該臺自建造至今,歷時六百余載,其基礎經長期間下沉之后,似不致再有走動危險,故亦無須根本改造……但修理工程,如拆去外側之磚,重新修砌,不但工費浩繁,完成之后,輪奐一新,亦足喪失古建筑之價值”,因此,方案側重于修舊如舊和最小干預,同時有針對性地應用現代建筑材料:“于磚欄下端盡頭處磚內加建鋼骨水泥柱,以期穩固。”“踏道與平臺臺面保存原狀,僅于磚下加做防水設備一層。其法先將臺面與踏道之磚,掘起三層,做四寸厚一·三·六鋼骨水泥,內加防漏漿,使插入欄墻下數寸,做成后,再按照原有形式,敷砌條磚一層。”值得注意的是,該方案還前瞻性地考慮到了建筑遺產利用特別是旅游開放問題,提出恢復古代天文測量活動,與游客進行互動:“觀星臺現存建筑系明人所筑,為恢復舊觀計,允宜全部拆除;但如高平子先生之意見,僅拆去中央一間,使日光自直漕上部可射至圭面,并于左右二室間架鐵梁,使距圭面之高度恰合元尺四十尺,游人至此,令守護人出景符以測日影,亦足增興趣不少。”[21]
三、建筑遺產科學保護之實踐
(一)攝影術在建筑遺產調查、保護與傳播領域的應用
清末民初,攝影術傳入中國并逐步普及。“吾國初得其術,尚屬濕片舊法,手術繁雜,能者無幾。迨干片法流行以后,法簡用繁,藉此營業者日眾,今則荒村僻野,時有其人,能者不奇,見者不怪。”[22]民國知識界亦隨之意識到攝影術在搶救保存建筑遺產資料、為建筑遺產修繕提供參考及留存建筑遺產修繕工程檔案等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召集之南京古跡調查委員會,在以青龍山梁陳古墓為目的進行的首次調查中,就將攝影作為重要調查手段:“先至陳代陳武帝之墓址,墓在青龍山麓,僅余殘碑斷碣數具而已。經詳察遺跡,就碑石等加以考察,并攝影數幀,拓碑文數紙。”[23]1935 年春,華北危機爆發,“薊北風云日亟,故都文獻有不保之虞”;同年7 月,朱偰“立志北征”,獲得故宮博物院特許,在故宮及景山大高玄殿、太廟、皇史宬等處攝影,“計窮二月之力,在京城內外攝影五百余幅,夫士既不能執干戈而捍衛疆土,又不能奔走而謀恢復,亦當盡其一技之長,以謀保存故都文獻于萬一”[24]。朱氏所攝照片后匯編為《元大都宮殿圖考》(商務印書館1936 年版)。20 世紀30 年代制定的龍門石窟修繕方案中,特別提出在動工前必須本著全面、客觀原則,由河南省民政廳和建設廳各派人員對其進行系統攝影以留存資料。方案強調:“以龍門造像為藝術遺跡,攝影時分段采景,應不雜藝術史之觀點,此種技術上之問題,商定由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駐洛人員勘察指導,以期收獲良好效果。”[17]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于此期間,亦從事詳密之調查,“藉為登記龍門古跡之實施,兼事采集詳細材料,以資日后之研究,并于修理時,作種種之貢獻”,龍門石窟修繕工程則于攝影初步完成后,再派工程隊前往工作[17]。明長陵修繕工程竣工后,北平市政府工務局曾編印《明長陵修繕工程紀要》,其中設有“明長陵建筑修繕前后對照攝影”專欄,收錄大紅門、內紅門、陵門、龍鳳門、明樓、神功圣德碑亭、祾恩門、祾恩殿、陵門內碑亭等明長陵標志性建筑修繕前后對照照片20 余幅,同時還收錄修繕工程施工現場照片多幅[25]。
民國相關文博機構也注意到攝影對于建筑遺產本體之負面影響。當時之攝影術尚存在一些技術局限,如在室內或光線不良條件下攝影就必須使用閃光照相法,時人就其弊端指出:“閃光藥尋常多為鎂粉或鎂帶,今市上又有閃光紙及閃光彈出售……閃光紙發光甚猛,溫度亦高,四周倘有易燃之物,須遷去以防火險。”[26]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因此在《管理石室壁畫塑像及其他古跡攝制照片及電影暫行辦法》中專門規定不得使用鎂光等足以熏黑石室古跡之燃燒性物品[27]。與此同時,民國文物保護界還將便于攝影作為相關建筑遺產修繕的一項內容,客觀上促進了建筑遺產影像留存和價值傳播。以西安碑林為例,20 世紀30 年代,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主任委員滕固等人參觀西安碑林時,感嘆“惜室內陰暗,且諸碑密刻,少隙地,不能攝影”[28]。1937 年4 月至1938 年3 月,西安碑林修繕過程中,根據梁思成之意見,除第二陳列室《開成石經》因固有序列不宜改動外,其余各室碑石均由橫排改為豎排,改善了采光條件,方便了游覽和拍照[29]。
(二)現代材料與技術在建筑遺產修繕中的應用
民國時期建筑遺產的科學保護,根據文物體量、保存狀況、設計思想和實際條件等因素,可分以下三類,茲以相應單體文物修繕舉例述之:
1. 應用現代材料的仿古修繕
城隍廟是上海著名古跡,早年失火焚毀。1926 年4 月,由黃金榮等人發起,委托公利打樣公司制造圖樣,久記營造廠重行翻建,1927年11 月25 日竣工。時人感慨道:“向來廟宇的建筑,是與宮殿一般式樣的;而建筑的材料,又不外乎用著泥磚竹木,從沒有像現在的大殿,竟然把鋼骨水泥制造的。而且仿造古式,絕無異樣,雕梁畫棟,金碧輝煌,那種含有美意的建筑,開全世界未有之奇觀;無論如何,不能再與以前破陋的情狀相比較咧。”[30]
2. 應用現代材料和技術的常態化修繕
都江堰作為一直沿用的重要水利工程,其保養維護屬于常態化工作。“都江魚嘴,塊石砌成之分水石堤,歷代修補,屢筑屢毀。迄自1935 年起,始用混凝土漿砌塊石,逐年培修深固,沿用至今。”[18]14與此同時,都江堰管護機構也意識到,因古代缺乏地質知識,修建都江魚嘴“雖曾加深掘,實未見實基,建筑于沖積層上,當時雖極盡堅固之能事,而終被毀于洪流,不明地質者,每諉之于天災”,為有的放矢,提高都江堰養護效率與質量,管護機構于1937 年在都江堰分水魚嘴內外二江進水口安瀾索橋兩端開展地質鉆探試驗,“鉆二孔,內江河心探深4.27 公尺,外江河邊探深5.69 公尺,始探得巖石,其質與兩岸山巖相同”。同時獲取了相應水文數據,為修繕工程提供了必要科學依據:“河身傾斜甚陡,水流速每秒3 米,水底工作甚為困難。夏季水深6米,冬季水深1 米,故一切工作,須在冬季舉行之。”[18]16—17
3. 綜合應用多種技術手段的樣板工程
南京棲霞山棲霞寺之隋代舍利塔在1930 年修繕竣工前,“以天時人事之侵損,石質剝蝕,時虞頹圮,觀者病焉”。時由香港居士何曉生伉儷發愿捐資修繕,委托葉恭綽主其事,中央大學建筑系教授盧樹森、中國營造學社劉敦禎擔綱。由葉氏所著《重修攝山隋舍利石塔記》可窺該工程相關重要史事:
一是秉持科學修繕理念:“抑近代保全古物不主妄加增削以失真相,若是乎莊嚴法相與保全古物殆不易兼顧。余乃謀中央大學建筑科諸教授盧君樹森暨劉君士能之言,曰塔之結構如人之筋骨,其雕飾即皮肉也,皮肉決不可增補以失真;筋骨則宜求充實以持久。”
二是應用物理化學多種技術手段:“今察塔石表已漸腐,且榫卯多松脫,施工次第宜用巨綆固束四周上下徐滌除其附緣之沙石草木。次則以人力推復各石之原狀,使鉤聯如故,再環以精鐵并間設撐拄令無枝梧,然后注入化學藥液為西方習用以延古物之壽者,使石理浸漬變化而加堅密且固其隙使無滋植物。如此則再千百年可不壞也。至外表雕刻及榱桷檐柱欄楯,凡非為保固所必需者概不加增飾。以藥液之石色力固將加瑩勝于施彩畫也。”
三是注重保持恢復歷史風貌:鑒于塔頂相輪久失,雨水易入塔心,“因加石頂三層,其式則仿北魏云中寺遺制”;在清除積土時,“始悉塔本有石壇,周如塔形而廣約加半,大致完好,再深掘復得石欄一堵,皆隋代遺物,埋沒殆數百載且不見于志乘,蓋山洪素烈泥沙壅積使之然也”,遂擴清積土、夷為廣場,修正壇址、補建石欄,“使一如隋式”;同時外加鐵柵“以期嚴凈”,“塔右及后方多為石磡以泄水且衛殿基一切經營蓋無遺憾”[31]。梁思成稱贊該修繕工程“照式補制,恢復舊觀”,全部重修工作除“塔剎形制或有可疑外,至為謹慎精審,開我國修葺古建未有之佳例”[32]。
余論
囿于史料所限和作者學識,本文觀點及引述之典型事例必有掛一漏萬之憾、班門弄斧之嫌,因此不敢以“研究”冠名而僅稱之為“探要”,目的是通過整理分析零星資料,盡力勾勒出民國時期建筑遺產科學保護的粗線條歷史圖景,以求拋磚引玉,為中國建筑遺產保護史研究提供一個新視角。
如前所述,民國時期的建筑遺產科學保護雖有可圈可點之處,但也必須正視其客觀存在的問題:一是建筑遺產科學保護缺乏官方背景的頂層設計,如古物保護法律法規中未見相關規定或表述,主管部門既未制定相應的工作規劃或標準,亦未設置必要的審批與監管等程序。二是目前所見之民國時期建筑遺產科學保護之典型事例或樣板工程,既有行政主管部門牽頭,也有建筑遺產管護機構、私立學術團體、民間人士自發實施,彼此各行其是,未成體系,不利于相互交流和理念、技術的提高。三是即使與其他建筑遺產研究領域如中國建筑史的研究相比,民國時期建筑遺產科學保護之理論探索與經驗總結也有相當差距,而且一些相對完備、科技含量較高的科學保護方案最終并未付諸實踐。四是相較于同一時期博物館事業中的科技元素,建筑遺產科學保護還處于起步階段——前者關于館舍設計建造(包括平面布置、采光通風、取暖制冷等)、藏品科學保護(包括日常養護、科技修復等)、陳列展覽與社會教育(包括展廳環境控制、電化手段應用)等方面,不僅在博物館學理論著作中有較多篇幅論述,而且大多在實體館得到體現。從總體來看,受制于當時國家整體科技水平的相對落后以及社會環境、經濟條件的影響,民國時期建筑遺產科學保護的指導思想和理論探索雖然有可稱道之處,但實踐尚處于初級階段,實際成效并不明顯。當然,這并不影響其在中國文物保護史特別是文物科學保護史上的應有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