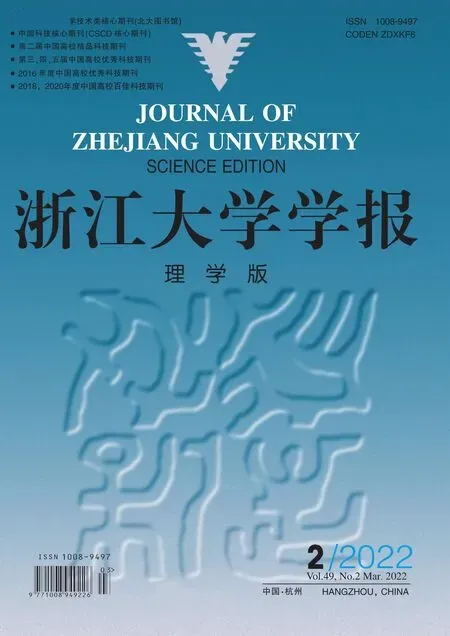背包客身份認同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
趙麗君,陳鋼華,2*,胡憲洋
(1.中山大學旅游學院,廣東 珠海 519082; 2.中山大學旅游發展與規劃研究中心,廣東 廣州 510275;3.陜西師范大學地理科學與旅游學院,陜西 西安 710119)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迅猛發展,社會利益日趨多元,社會心態也逐漸分化。部分個體積極向上、理性和平、自尊自信;另一部分個體則對自我的認識、定位愈發模糊,容易產生焦慮、不安等情緒,威脅其心理健康[1]。背包旅行能為當代個體提供一種追尋自我的途徑[2]。由于旅行持續時間較長、行程安排自主、注重交流與互動,能為背包客提供展露自我的“自由空間”,構建與“生活世界”不一樣的自我,即建構背包客身份認同[3-7]。已有研究表明,農村流動人口、黨員等群體的身份認同能顯著提升其主觀幸福感[8-10]。那么,背包客在“旅游世界”中形成的身份認同是否也能顯著提升其主觀幸福感,從而為他們的心理健康帶來積極效益呢?這是一個亟待系統研究的理論問題。
背包客身份認同是個體對背包客群體的歸屬認知,包含自我歸類、群體自我評價、群體自我價值3個維度[11]。 根據社會認同理論(social identity theory,SIT),個體對于群體屬性的內化程度影響個體心理塑造[12],促進積極的自我概念[13],并能增強個體歸屬感、信任感、安全感和支持感,為個體提供應對變化、挫折、挑戰的心理資源[14],最終形成持續的幸福感源泉。 且根據自我決定理論(selfdetermination theory,SDT),關系、自主和能力3 種內在的基本心理需要的滿足從根本上決定了一個人的幸福感[15]。自我歸類是指將自己歸屬于背包客群體的一員,帶來群體歸屬感,并與其他群體成員建立友好關系,彼此相互提供社會支持[16],滿足“關系”需要;群體自我評價中的“獨立”“自主”[3,6,11],能滿足背包客“自主”的基本心理需要;群體自我價值所蘊含的背包客身份的價值和意義,能提升背包客對自我能力的感知[17],滿足“能力”的需要。基于上述理論和對文獻的梳理,有理由推測,背包客身份認同可通過滿足以上3 種基本心理需要,提升其主觀幸福感。
為進一步檢驗背包客身份認同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機制,本文引入自尊作為中介變量。自尊是社會認同影響群體成員心理和行為的重要解釋變量,是社會認同與心理健康兩者關系中的重要中介變量[18-19]。具體而言,根據社會認同理論,人們通過群體間的社會比較,肯定“內群體”相對于“外群體”的優勢,從而提高自尊[18],而自尊是主觀幸福感的重要預測因素[20]。由此,推測自尊在背包客身份認同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中可能存在中介作用。
綜上,本研究將在社會認同理論和自我決定理論的雙重指引下,嘗試構建背包客身份認同、自尊和主觀幸福感之間關系的理論模型,并進行實證檢驗。在理論方面,將進一步完善有關背包客心理健康和生命質量的研究體系;同時,將對身份認同與主觀幸福感關系的研究拓展至非慣常環境,為這一領域的研究提供新的理論視角。在實踐方面,對進一步在我國推廣背包旅行與促進可持續發展具有指導意義。
1 文獻回顧及假設的提出
1.1 背包客身份認同
人們渴望沖破生活的“牢籠”,尋求生命的自由與解放[21]。旅游世界便是作為自由空間而存在的。在此,旅游者可以揭開“面紗”,展露真實的自己,甚至建構另外一個自我[3]。在眾多旅游體驗類型中,背包旅行因持續時間較長、采取自主旅游形式、熱愛與他人互動,最能擔此重任[3]。背包客在旅游世界中探索到與日常生活世界不一樣的自我,從而建構背包客身份認同[3-7,22]。
在背包客身份認同的3 個維度中[11],背包客自我歸類,即認同自己為背包客群體的一員,突出群體成員身份意識。例如,背包客通常將自己與普通大眾游客做比較,用“我們”和“他們”相互區分,認為自己是“背包客”“旅行者”,拒絕別人稱他們為“旅游者”“游客”,認為自己與普通旅游者,存在“依賴與獨立”“一致與個性”等本質區別。總之,背包客通過自我歸類提高群體認同感并鞏固其社會身份[11]。
群體自我評價蘊含個體對背包客群體共有特征的評價,代表背包客群體的行為規范。背包客擁有獨特的旅行方式和旅行文化,例如,在旅游世界中的穿著打扮、旅行裝備。具體而言,背包客的通常形象是“身著沖鋒衣、肩負背包、腳穿登山鞋”。這些裝備不僅是他們應對戶外惡劣環境的慣用工具,而且成為他們身份的象征符號[3,11]。背包客采用自助旅行的方式,獨立制訂彈性旅行計劃,限制旅行預算,偏好長期旅行,積極與其他旅游者和目的地居民進行互動、交流,具有冒險精神,不畏風險,偏好遠離大眾游客的旅游目的地,追求原真性的旅行體驗等[4,7,11],遵循群體規范,將自己與普通大眾游客相區分,在背包客群體內為自己贏得更高評價,并將一些不符合背包客群體規范及價值觀的人稱為“偽背包客”,不承認他們是背包客群體成員[23]。
群體自我價值反映了個體對背包客身份價值的感知和評價,具體包含:首先,背包旅行(當一名背包客)對個體的成長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6-7,11]。陳鋼華等[24-25]將通過背包旅行實現的個人發展劃分為能力的提升、技能的豐富、世界觀的改變、自我意識的增強、情緒的調整。其次,背包旅行能積極促進背包客的人生轉折。許多背包客將背包旅行作為人生的過渡階段(例如,畢業后步入社會、發生家庭變故、經歷感情危機、遭遇工作瓶頸等)。最后,背包旅行(作一名背包客)對于目的地和社會發展有重要意義,不僅能促進目的地的經濟發展(例如,提供就業機會,宣傳和提升目的地形象)[26-27],而且對增強目的地居民的文化自信、保護目的地傳統文化、促進社區文化變遷有積極意義[28]。背包旅行注重保護目的地生態環境,有利于促進旅游可持續發展[29]。
1.2 背包客身份認同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
主觀幸福感是指人們對生活質量的總體評價以及由此產生的積極情感主導的心理狀態,具有一定的主觀性、穩定性和整體性[30]。DIENER 等[30]將主觀幸福感劃分為生活滿意度、積極情感和消極情感3 個維度。生活滿意度是個體按自己的標準對生活狀況的總體評價,為主觀幸福感的認知成分。積極情感和消極情感則是個體在實際生活中感受到的情感體驗,為主觀幸福感的情感成分[31]。
社會認同理論認為,個體對于群體屬性的內化程度影響個體心理的塑造[12-14],能增強個體的歸屬感、信任感、安全感和支持感,為個體提供用于應對變化、挫折和挑戰的心理資源[20]。此外,來源于所屬群體的價值觀、目標也能賦予個體生活的目的和意義,為個體提供生活、奮斗的動力[32],從而為個體帶來持續的幸福感源泉,減少抑郁,促進積極情感,增加生活滿意度等[33]。
針對農村流動人口[9]、黨員[11]和教師[34]的研究都證實了身份認同對主觀幸福感的積極影響。此外,現有研究也表明,維持高水平的民族認同對主觀幸福感有積極影響[35]。由此可見,背包客身份認同與主觀幸福感之間可能也存在顯著正相關。
根據自我決定理論,關系、自主和能力是跨人群、跨文化普遍存在的心理需要;對3 種基本心理需要感到滿足的程度與幸福感呈正相關,且每種需要對幸福感的貢獻都是獨一無二的[15,36]。如果基本心理需要得到滿足,那么個體就會沿著健康的道路發展,從而體驗持續的幸福感[37]。因此,有利于滿足關系、自主、能力等基本心理需要的因素可提升幸福感;相反,有損于滿足基本心理需要的因素則會降低幸福感。
在實證方面,已有研究證實基本心理需要的滿足對幸福感有積極的預測作用[36,38]。例如,REIS等[38]的研究表明,3 種基本心理需要的滿足程度能獨立預測積極感情水平。MILYAVSKAYA 等[36]則在家庭、工作單位、學校等生活領域證實了基本心理需要的滿足與主觀幸福感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
在3 種基本心理需要中,“關系”是指能得到重要人的關懷與接納,具有歸屬感,得到較高的社會支持[39]。人際關系是幸福感的本質特征,是幸福感最活躍、最突出的構成要素和影響因素[40]。由此可見,“關系”對幸福感而言是十分重要的。
對背包客而言,通過自我歸類,將自己歸為背包客群體成員,產生群體歸屬感,并與群體內其他成員建立聯系[6-7,11],從而可能促進個體“關系”心理需要的滿足和幸福感的提升。據此提出以下假設:
H1:背包客的自我歸類對主觀幸福感產生正向影響。
H1a:背包客的自我歸類對生活滿意度產生正向影響。
H1b:背包客的自我歸類對積極情感產生正向影響。
根據“自主”被定義為自我管理的自由,是一種促進成長與適應功能的心理需要[15]。“自主”基于個體的內在興趣和價值觀[41],具有獨立、自由、自我調節、自我管理的涵意[42],能夠使人感到活動和目標是自我選擇的。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苗元江[43]提出,自主是一種自我調節、內部控制的感覺。有研究表明,缺乏自主性會降低個體生活滿意度,并令個體對生活產生沮喪或其他消極情感[44]。
在背包客群體自我評價中,獨特的旅行方式、旅行文化和個性特質等是個體對背包客群體共有特征的評價,同時也是背包客“自主”的集中體現。首先,背包旅行作為一種特殊的出行方式,蘊含個體強烈的內在動機(例如,自我成長、人際交往等),個體處于內在興趣、自我選擇的狀態[45]。其次,背包客倡導自主精神,按照自我意愿,自由、獨立地制訂旅行計劃,并采取自助旅行的方式[6-7,11],體現個體自我調節、自我管理和自我控制的能力。此外,背包旅行有利于錘煉其獨特的個性特質,例如,獨立、自主、自由等特質[11]。這些特質均能增強個體的自主性。
基于上述分析,有理由推測,個體在通過背包旅行體驗構建身份認同的過程中,隨著群體自我評價水平的提升,個體“自主”心理需要的滿足程度也得以提升,從而獲得更高水平的主觀幸福感。據此提出以下假設:
H2:背包客的群體自我評價對主觀幸福感產生正向影響。
H2a:背包客的群體自我評價對生活滿意度產生正向影響。
H2b:背包客的群體自我評價對積極情感產生正向影響。
“能力”是指個體能有效改變內外環境,有較高的效能感。持續的效能感對幸福感的提升有積極作用。BANDURA[46]的研究發現,自我效能感通過影響個體處理應激能力及個體的動機與行為保持心理健康。自我效能感令個體變得樂觀積極,自信心增強,從而提升主觀幸福感[47]。在背包旅行情境下,有理由推測,背包客群體自我價值中蘊含的自我成長、社會貢獻等能提升背包客的效能感[17],提升個體的自信心和樂觀積極的水平,從而提升個體的主觀幸福感。據此提出以下假設:
H3:背包客的群體自我價值對主觀幸福感產生正向影響。
H3a:背包客的群體自我價值對生活滿意度產生正向影響。
H3b:背包客的群體自我價值對積極情感產生正向影響。
1.3 背包客身份認同與自尊的關系
已有研究普遍證實了民族認同、種族認同、國家認同等與自尊之間的相關性[48]。根據社會認同理論,積極地進行群體區分可有效提高社會認同,從而提升自尊水平[49]。因此,對于背包客而言,自我歸類表明個體認同自己是背包客群體一員,將背包客群體劃分為“內群體”,將大眾游客群體等劃分為“外群體”。群體自我評價蘊含的內容是背包客群體的行為規范,也是與大眾游客群體進行比較時的重要維度。基于此,個體將自己所在的背包客群體與大眾游客群體進行積極區分,形成比較優勢,從而提升自尊水平[7,11]。
此外,自尊包含個體對自我能力、價值的評價[50]。群體自我價值也可能通過改變個體對自我價值、自我能力的感知和評價影響自尊水平。據此提出以下假設:
H4:背包客身份認同對自尊產生正向影響。
H4a:背包客的自我歸類對自尊產生正向影響。
H4b:背包客的群體自我評價對自尊產生正向影響。
H4c:背包客的群體自我價值對自尊產生正向影響。
1.4 自尊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
自尊涉及個體對自身的總體判斷,主觀幸福感則是個體對生活的總體判斷,兩者均屬于總體評價性變量[51]。個體自尊對主觀幸福感正向影響的預測作用已被證實[20,52]。例如,嚴標賓等[52]提出,自尊與主觀幸福感顯著正相關。對背包客而言,同樣可能存在更高水平的自尊帶來更高水平的主觀幸福感的情況。據此提出以下假設:
H5:背包客的自尊對主觀幸福感產生正向影響。
H5a:背包客的自尊對生活滿意度產生正向影響。H5b:背包客的自尊對積極情感產生正向影響。H6:自尊在背包客身份認同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中起中介作用。
基于以上分析,構建如圖1 所示的概念模型。

圖1 概念模型Fig.1 Theoretical model of this research
2 研究方法
2.1 測量量表
對背包客身份認同的測量選用陳鋼華等[11]編制的背包客身份認同量表(16 個題項)。代表性的題項有“我是一名典型的背包客”“背包客有獨特的旅行方式”和“背包旅行(作一名背包客)能增強我的自我認同感”等。測量主觀幸福感的量表來自苗元江[43]編制的綜合幸福問卷(11 個題項)。生活滿意度維度的代表性題項有“我的生活大多數方面與我的理想吻合”和“我的生活狀況良好”;積極情感的測度則從“高興”“愛”“愉快”“感激”“快樂”和“自豪”6個題項展開。自尊測量采用的是羅森博格自尊量表的中文版[53]。自尊量表的措辭效應為二因子結構,即正向陳述題項和反向陳述題項各屬于一個獨立因子,而實質上2 個維度測量的是同一自尊特質[54]。由于,負面陳述題項存在一定的測量偏差,影響測量效度[55],因此,本研究只保留6 個正向陳述題項。
預測試于2019 年8 月5—9 日在成都夢之旅國際青年旅舍進行。向中國背包客發放問卷48 份,回收有效問卷48 份(有效率100%)。對33 個題項的描述性統計結果表明,26 個題項的得分均值接近或大于4,說明受訪者普遍認同所測項目。從數據偏度和峰度看,偏度絕對值低于1.093,峰度絕對值低于1.300,符合正態分布標準。由此可見,問卷的題項設置基本合理。
2.2 數據收集
基于以往研究[6,11,24-25],本研究將背包客操作性地定義為大多數時間居住在青年旅舍、以背包作為主要行李工具的自助旅行者。問卷發放的對象為中國背包客。問卷發放和回收的時間及地點如下:
第1 階段為2019 年8 月10—31 日,在成都夢之旅國際青年旅舍,共發放問卷271 份,回收有效問卷262 份,有效回收率96.68%。
第2 階段為2019 年12 月26 日至2020 年1 月9日。在麗江背包十年青年旅舍,共發放問卷140 份,回收有效問卷138 份,有效回收率98.57%。
在上述2 個正式調研時段,合計發放411 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400 份,有效回收率為97.32%。
3 數據分析與結果
3.1 旅行特征和社會人口統計學特征的描述性分析
在旅行特征方面,受訪者普遍具有豐富的背包旅行經驗,背包旅行次數為4~10 次和10 次以上的受訪者分別占39.00%和27.50%,背包旅行次數為1~3 次的受訪者占33.50%。在旅行時長方面,普遍較長,旅行時長在6~10,11~20 和20 d 以上的分別占31.25%,31.25% 和26.75%;旅行時長在1~5 d的僅占8.25%。在性別及年齡方面,男性略多(58.25%),且普遍較為年青(21~35 歲,占71.75%;20 歲及以下,占19.25%;36~50 歲,占8.50%;51~65 歲,占0.50%)。在教育背景方面,受訪者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較高,50.75%的受訪者具有本科學歷,其次分別為大專(20.50%)、高中(13.75%)、研究生及以上(13.00%)。在職業方面,學生(34.25%)和企業職工(24.00%)較多,其次分別為個體工商戶(10.25%)、政府及事業單位職工(7.75%)和其他(23.75%)。在收入方面,個人月收入低于1 500 元的受訪者最多,占33.75%,其次分別為高于7 500 元的(30.25%)和6 001~7 500 元的(10.75%)。
3.2 正態性、信度和效度檢驗
各測量題項偏度的絕對值均低于1.118,峰度的絕對值均低于0.717,表明數據符合正態分布標準(偏度絕對值小于3,峰度絕對值小于8)[56],可進一步分析。用SmartPLS 3.0 軟件中的驗證性因子進一步檢驗各個構念(潛變量)的信度、聚合效度和區別效度,結果發現,題項PA-6、BIS-11 的因子載荷較低(<0.7),分別為0.497 和0.674。參考以往研究[17,57],按照因子載荷由低到高的順序逐一刪除上述題項,刪除后模型中仍有足夠數量的可靠題項,可再次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和其他統計分析。
用Cronbach'sα系數檢驗量表的信度。如表1所示,各個潛變量的Cronbach'sα系數均高于0.7,表明內部一致性良好。聚合效度指同一結構維度(潛變量)下不同測量題項(觀察變量)的相關程度。所有測量題項(觀察變量)的因子載荷均高于推薦門檻值0.7,所有潛變量的平均方差提取量(AVE)均大于臨界值0.5,組合信度(CR)均大于0.7,表明聚合效度良好。就區別效度而言,各測量題項在所屬潛變量上的因子載荷均大于在其他潛變量上的因子載荷;AVE 的平方根均大于其與其他潛變量的相關系數(表2);任意2 個潛變量之間的區分效度異性單性比(heterotrait-monotrait ratio,HTMT)均在0.279~0.627,小于閾值0.85。以上結果表明,潛變量之間存在足夠的區別效度。

表1 聚合效度、內部一致性參數Table 1 Convergent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表2 構念相關系數及AVE 平方根矩陣Table 2 Correlations for the constructs and the square root of AVE
3.3 多重共線性和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多重共線性是指構念之間存在較高的相關性,導致模型估計失真。因此,采用方差膨脹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檢驗多重共線性。SmartPLS 3.0 分析發現,外部模型VIF 值為1.607~3.852,內部模型VIF 值為1.221~2.040,小于閾值5,表明多重共線性不會威脅后續研究模型驗證的有效性。
共同方法偏差指由相同的測量環境、相同的數據來源、測量題項本身的特征、共同的題項語境等造成的人為共變,這種人為共變可能導致研究結果出現偏差[58]。因此,采用成熟量表,并在不同時間段、不同地點分別進行2 次數據收集,以盡可能避免出現偏差。研究還通過Harman 單因素檢驗法檢驗共同方法偏差[58]。具體而言,用SPSS 22.0 軟件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發現,第1 個因子只能解釋33.21%的方差,低于40%的閾值[58]。表明不存在某個因子解釋力過大的情況。因此,共同方法偏差不會影響后續研究結果的有效性。
3.4 研究假設檢驗
用SmartPLS 3.0 軟件對數據進行迭代運算,并根據運算結果評估結構模型:(1)用R2判斷模型的預測能力。判定系數R2用于衡量內生潛變量的總變異程度,FALK 等[59]推薦的R2的最小容忍值為0.1,表1 中,所有潛變量的R2均超過0.1,表明模型的預測能力符合要求。(2)用Q2衡量內生潛變量的預測相關性。通過運行SmartPLS 3.0 軟件的Blindfolding 程序計算Q2,表1 中,所有內生潛變量的Q2值均大于0,表明模型具有良好的預測能力。(3)通過整體擬合優度(GoF)判斷模型的整體預測能力。GoF 為共同度均值和判定系數R2均值的幾何平均數,其中,共同度均值等同于AVE,本研究模型的GoF 為0.395,高于臨界值0.36,表明模型具有較強的整體預測能力。
通過SmartPLS3.0 軟件的Bootstrapping 程序檢驗假設路徑。將抽樣次數設置為5 000,結果如圖2 和表3 所示,(1)自我歸類與生活滿意度呈顯著正相關(β=0.151,t=2.628,p<0.01),假設H1a 成立。(2)自我歸類與積極情感呈顯著正相關(β=0.147,t=2.305,p<0.05),假設H1b 成立。(3)群體自我評價與生活滿意度、積極情感的正相關關系均不顯著,拒絕假設H2a、H2b。(4)群體自我價值與生活滿意度(β=0.139,t=2.307,p<0.05)、積極情感(β=0.172,t=2.371,p<0.05)呈顯著正相關,假設H3a、H3b 成立。

表3 路徑假設檢驗結果Table 3 Results of path hypothesis test

圖2 結構模型結果Fig.2 Results of the structural model
注 對角線上的數值為AVE 的平方根。
在背包客身份認同的3 個維度中,群體自我評價(β=0.131,t=2.053,p<0.05)、群體自我價值(β=0.359,t=5.481,p<0.001)與自尊呈顯著正相關,因此,假設H4a、H4b 成立,拒絕假設H4c。自尊與生活滿意度(β=0.461,t=8.417,p<0.001)、積極情感(β=0.232,t=4.283,p<0.001)呈顯著正相關,假設H5a、H5b 成立。
3.5 中介效應檢驗
利用SmartPLS 3.0 軟件的Bootstrapping 程序檢驗中介效應。將抽樣次數設置為5 000,首先,需要判斷間接效應是否顯著,若不顯著則表明不存在中介效應,若顯著則需進一步判斷直接效應是否顯著,若直接效應顯著,則存在部分中介效應,若直接效應不顯著,則為完全中介效應。
群體自我價值對生活滿意度的間接效應顯著(β=0.166,t=4.642,p<0.001),且如表3 所示直接效應顯著(β=0.139,t=2.307,p<0.05)。因此,自尊在群體自我價值與生活滿意度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群體自我價值對積極情感的間接效應顯著(β=0.083,t=3.203,p<0.01),且如表3 所示直接效應顯著(β=0.172,t=2.371,p<0.05)。因此,自尊在群體自我價值與積極情感之間也起部分中介作用。可見,自尊僅在群體自我價值與主觀幸福感(生活滿意度和積極情感)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而在自我歸類、群體自我評價與主觀幸福感之間的中介作用不顯著。
4 結論與討論
4.1 結 論
研究結果表明,背包客身份認同的自我歸類維度、群體自我價值維度均對背包客的主觀幸福感存在顯著正向影響;同時,自尊在群體自我價值和主觀幸福感之間存在部分中介效應。基于此,進一步對背包客心理健康與生命質量的研究體系進行完善。
4.2 理論啟示
4.2.1 背包客身份認同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
研究發現,背包客的自我歸類水平越高,越認可自己為背包客群體成員,其群體歸屬感越高,并得到更多來自其他群體成員的社會支持,從而提升個體“關系”基本心理需要的滿足水平,以增加主觀幸福感。同時,背包客群體自我價值水平越高,通過背包客身份獲得的自我價值感、自我效能感的提升越大,對生活更加樂觀、自信,從而以更加積極的態度認識和應對事物,體驗更多的積極情感,并影響個體對自身生活質量的評價,生活滿意度得以提升,主觀幸福感也更強。
4.2.2 背包客身份認同與自尊的關系
研究發現,背包客身份認同的群體自我評價、群體自我價值維度能顯著正向影響自尊。其中,群體自我評價聚焦于背包客的獨特旅行方式、旅行文化、個性特質,而這些內容構成了與普通大眾游客區分的重要維度。背包客據此與普通大眾游客進行比較,并認為自己的旅行方式、旅行文化、個性特質等“優于”普通大眾游客,因而獲得比較優勢,提升自尊水平[7]。群體自我價值則蘊含“背包客”身份給予個體的價值體驗,包括通過背包旅行實現個人成長、提升自我認同,以及背包旅行過程中對目的地和社會產生的貢獻等[11]。自尊則是個體對自我能力和自身價值的整體性評價和情感體驗。因此,背包客群體自我價值通過影響個體的自我價值感建構,從而對自尊產生正向影響。
4.2.3 自尊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
背包客的自尊對主觀幸福感有顯著正向影響。與普通個體一樣,自尊是主觀幸福感最可靠、最有力的預測指標[20,52]。高自尊水平伴隨更高的群體自我評價,從而促進個體生活滿意度的提升[52]。并且,自尊蘊含個體的自我接納與自我喜愛,因此,背包客自尊水平越高,對待自己的態度越積極,越容易帶來積極的情感[20]。
4.2.4 自尊的中介效應
中介效應的檢驗結果表明,自尊在群體自我價值與主觀幸福感之間存在部分中介效應。群體自我價值注重對能力的認知和評價,自尊則是個體對自我能力和自身價值的整體性評價和情感體驗[50]。群體自我價值有助于建構個體對自我的認知和評價,進而影響情感認同,塑造自尊。因此,群體自我價值感知越高的個體產生的自尊水平越高,對自己持有更加積極的態度,帶來更高的主觀幸福感體驗[20,52]。本研究在旅游情境下驗證了自尊作為社會認同與群體成員心理解釋變量的中介作用。
4.3 實踐啟示
首先,研究證實了背包客身份認同為背包客個體帶來的幸福效益,進一步挖掘了背包旅行的積極意義,有助于更全面地認識背包旅行,消除對背包客、背包旅行的偏見,打消“背包旅行浪費時間”等顧慮。其次,各級政府、非政府組織應鼓勵背包旅行,并將其作為一種與正規教育互補的促進心理健康發展的重要渠道進行宣傳。同時,需增加對背包旅行產業的政策及資金支持力度,完善相應的法律法規,加強背包旅行的安全保障,營造良好的發展環境。此外,應考慮優化調整我國休假制度,為背包旅行創造更有利的閑暇時間和條件。最后,研究結論有利于加強背包旅行相關產業發展的信心,并更好地理解背包客市場,改進運營模式和服務水平。
4.4 研究局限及展望
對背包客身份認同與主觀幸福感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積極探索,但從研究內容和研究設計看,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采用自陳量表測量主觀幸福感,盡管這一方法有良好的測量信效度,但自陳量表測得的幸福感易受思維定式、記憶偏差等因素的影響,也可能會隨當時心境及其他因素的變化而變化。因此,自陳量表無法全面、準確地揭示幸福感。未來,可采用混合研究方法,即采用自陳量表和非自陳量表相結合等方法(例如,生理和行為測量法、昨日重現法等)進行數據采集,以更全面地測量幸福感。其次,雖然考察了背包客身份認同對幸福感的影響及自尊的中介效應,但背包客身份認同對幸福感的影響還可能通過其他中介變量實現。因此,未來可引入其他中介變量(例如,社會支持等)和調節變量(例如,人格特質等),以完善有關背包客身份認同影響主觀幸福感機制的研究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