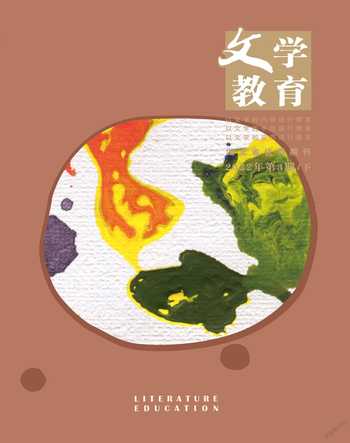以李娟、梁鴻作品為例析非虛構文學現象
李倩倩
內容摘要:2010年《人民文學》雜志開設“非虛構”專欄,“非虛構”文學逐漸進入到主流文學行列。通過對“非虛構”文學的發展概述,以李娟、梁鴻的作品為例,分析“非虛構”文學呈現的自然文化圖景和社會現實圖景,感悟“非虛構”文學對生態環境與精神困境的共性訴求,從而推動“非虛構”文學的繁榮發展。
關鍵詞:“非虛構”文學 圖景呈現 共性訴求
近年來,學界關于“非虛構”文學的作品日益增多,尤其是2010年《人民文學》雜志第2期“非虛構”欄目的設置。一時間,作家們筆耕不輟,紛紛對其進行創作,豐富了“非虛構”文學的內容。其中以李娟和梁鴻作品為例,它們透過社會現實表露作者的真實見聞與體驗,引發大眾對“非虛構”文學的關注和思考。
一.“非虛構”文學概述
“非虛構”文學最早出現在美國新聞界的“新新聞報道”上面,后因一樁真實的血案被美國作家杜魯門·卡波特以小說的形式發表《冷血》一書,“非虛構”文學以小說的形式真實再現了美國的現實生活,并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引進到我國文學界,雖然期間發展較為緩慢,但自2010年《人民文學》雜志設立“非虛構”文學專欄以來,其發展開始趨向繁榮。
1.“非虛構”文學的源起
基于美國中部堪薩斯州血案的調查和整理,美國作家杜魯門·卡波特于1965年著《冷血》一書,將新聞報道的真實性與長篇小說的表現形式結合,以敘述故事的真實性和敘述技巧,在文學上形成了一種新的文學形式——“非虛構小說”。實際上在“非虛構小說”以前,美國新聞界的“新新聞報道”就曾涉及過“非虛構”文學。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期,部分記者聯合起來發明了一種新的非虛構文學作品體裁。在撰寫新聞稿的過程中,他們用小說的技巧進行寫作,把自己的個人看法同小說特有的道德觀點融入到新聞報道當中。不論是“非虛構小說”還是“新新聞報道”,它們都強調文學與社會現實的聯系,注重其真實性。
2.“非虛構”文學在中國的發展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非虛構”文學被引入中國學界。董鼎山指出:“用小說的形式,用文藝的筆法報道事實,將文藝與新聞報道結合一起的新的藝術形式。”[1]但是縱觀整個“非虛構”文學的發展歷程發現其持續處于一個低迷狀態,直到二十一世紀初,“非虛構”文學才真正作為一種獨立的文學現象出現在大家的視野中。2010年《人民文學》雜志開辟“非虛構”專欄,“這一年刊發了韓石山的《既賤且辱此一生》(第2期)、祝勇的《寶座》(第5期)、梁鴻的《梁莊》(第9期)、慕容雪村的《中國,少了一味藥》(第10期)、李娟的《羊道·春牧場》等10篇題材各異、風格獨特的非虛構作品,引起讀者好評和評論界熱議。”[2]其中李娟和梁鴻的作品對“非虛構”文學的發展影響較為深遠。一方面,是因為它們的出現豐富了“非虛構”文學的內容,另一方面,是因為它們使得大家把文學視角聚焦到邊緣文學、鄉土文學,在不同程度上喚醒了大家對工業文明和鄉村文明的意識。
二.“非虛構”文學作品的圖景呈現
李娟通常以一種外來人的眼光審視著新疆的自然景觀,將它同生活經歷結合起來,在其情感的支配下進行文學創作,如“阿勒泰”系列作品大都是對阿勒泰地區自然風貌的描寫。而出生于河南的梁鴻則是以歸鄉者的身份重回梁莊,對自己的家鄉進行全方位的考察與思考,創作的“梁莊”系列作品基本上都與社會現實有關。因此,特基于兩位作家的經典作品,再現“非虛構”文學的作品圖景。
1.自然文化圖景
李娟的作品大多是對阿勒泰地區自然風景和各民族聚居生活場景的描述。在《摩托車穿過春天的荒野》中李娟坐在摩托車上看到了戈壁灘別樣的風景:“大地上雪白的鹽堿灘左一個右一個,連綿不斷地分布著,草色就團團簇簇圍擁著它們,白白綠綠,斑斕而開闊。”[3]倘若不是匆忙趕路,也不會發現“兩股雪白的旋風漸漸合為一股”的場景。所行之處皆為坦闊,所見之景皆用“茫茫”,大自然何其廣闊!在這里作者不單是對大漠的風景進行了描寫,還著重寫了自己乘坐摩托車的感受,使得作品更加真實。途中叔叔的摩托車因缺少汽油被迫中斷行程,李娟除了感受風很大之外,還收到了來自陌生人的善意。等再次上路時,李娟和叔叔先后進入了“褚紅色起伏地帶”“赤裸粗硬的野地”幾經迷失方向卻又于板結地面發現了“淡黃色滲著微紅血絲的透明瑪瑙”。“為讀者呈現出雪白荒蕪夾雜草色、褚紅色戈壁地帶與板結地面透明瑪瑙構成令人難忘的藝術地理空間。”[4]
不同于西北自然的廣袤圖景,位于河南穰縣的梁莊更多的是凸顯了我國內陸鄉村的一個整體風貌。在《我的故鄉是梁莊》中梁鴻坐在火車上透過窗簾看到夜色下的大地、樹木、莊稼、房屋等景象,內心不由自主地對此次歸鄉加深了些許期待與向往。比如在穰縣的橋上,她說她看到了世界上最美的月亮,淡黃的月亮如同宣紙一般,中間夾雜著清淡的云,清雅圓潤,給人一種不可言喻的美感。到了鄉村,看到它的巨變,她腦海里涌現的更多的是她求學途中的風景:沿河而行,空中盤旋的鳥兒,路邊的溝渠以及溝渠兩旁的小草和各色野花都有著難以言說的清新與柔美。除此之外,即使是被掩映在樹木里的村莊,給人的感覺也是安靜的、祥和的。其實像這種氛圍感,不僅僅存在于梁莊這一個村莊,中國大多鄉村都是如此。
“非虛構”文學基于作者的家園情懷、審美體驗等,強調生命的在場,以達到真實性與自然性相統一的目的。而且在作品中可以發現李娟和梁鴻這兩位作家,均把自身的人生經歷同自然社會緊密聯系起來,通過地理空間和時間記憶,詮釋出作者本身對現實自然環境的一個真實的情感體驗。
2.社會現實圖景
他鄉即故鄉,李娟將自己一家在阿勒泰地區的所見所聞,結合自己的體悟用筆記錄了下來,在這片土地上她解放了自己的天性,不斷用雙腳丈量著生命的脈絡。通過《喀吾圖》,可以得知作者一家在阿勒泰的牧場深處經營者一家雜貨鋪和裁縫鋪。在經營期間,同他們往來的大都是當地的牧民,為了長久的生存考慮,作者一家不顧語言不通、環境不熟悉等困難,向牧民們放債。緊接著作者又寫了牧民上門還債的情景,其中最為動人的還是要數那個牧人。因為好幾年都沒有來還債,李娟母親原以為不會收到,誰知牧人又出現了店里,在確認好自己的名字和字跡后,分批次還清了賬單。然而現在社會上有太多因“欠債不還”,導致雙方“反目為仇”的例子了,為什么就不能真誠一點、純粹一點呢?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中國人踏實本分的個性成就了中國特有的農耕文明。在“梁莊”系列作品中,梁鴻以自己家鄉梁莊出現的問題為焦點,影射了當今中國各個地方農村的社會現實。在《離鄉少年》中菊秀不愿放棄文青理想,拒絕跟隨爸媽在城市打拼,多次考試失敗后在家人的幫助下做了幾次生意也慘遭失敗。因為自己沒能成為讀書人,所以不顧家人阻撓也要和一位讀書人相愛、結婚、生子。婚后,讀書人的不作為讓她悔不當初,但她沒有沮喪,因為她又開始把自己沒有實現的理想強加在孩子身上。如果說菊秀的理想和浪漫是她的缺點,是她向往理想生活的絆腳石,那么當下的年輕人又該如何去平衡自己的理想和生活呢?反觀菊秀的育兒觀,有人說菊秀“望女成鳳、望子成龍”的心過于急切,但當前的諸位家長又何嘗不是?由此觀之,那些張嘴閉嘴都是“為你好”的家長,更應反思自己,反思自己是否真正做到了為孩子好。
文學來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李娟作品中的牧民上門還債以及梁鴻作品中菊秀的悲劇,無一不是對現實生活的真實寫照。同樣在“非虛構”文學作品中也可以從中看出自其出現以來,“非虛構”文學始終秉承著著真實性和文學性的理念,力求作者的行動和在場,講求遵循客觀實際,喚醒作者的社會責任感,同時再現文學真實的力量。
三.“非虛構”文學作品的共性訴求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類在精神困境、生存異化等方面,正如海德格爾所說的那樣:“人類正面臨著兩大生存困境,一是生存方式的技術化對人類過度控制造成的困境,二是人類的精神困境。”[5]通過對“阿勒泰”和“梁莊”系列作品的分析,從生態環境和精神困境的角度出發,解讀“非虛構”文學作品背后蘊含的共性訴求。
1.對生態環境的訴求
在“阿勒泰”系列作品中,李娟通過對自然界植被的描寫來說明當前人與自然的緊張關系。《木耳》中李娟詳細描述了母親最后一次進山采木耳的場景,文中最后一朵木耳和母親腳下踩的蛇,相比之前的觸目驚心,此刻的李娟呆立在那里注視著。最初母親采摘木耳是為了貼補家用,幾乎無人知道木耳的價值,也很少有人前去采摘,但隨著木耳價格的瘋漲,它不再只是大自然饋贈的一種食品,而成了一種身份的象征和謀生的途徑。一時間,人們皆為木耳疲于奔命,不惜鋌而走險,直到瘟疫的到來,才結束這場硝煙。人的欲望仿佛就是那條有毒的蛇,而木耳則是人心中殘存的善與理智。李娟對最后一朵木耳的隱瞞,更是對人性善的一種守護。人與自然原本是一種平衡互利的關系,而不是違背其生長規律,拋棄適度原則,造成“竭澤而漁”的嚴重后果。如果當下人類不加以克制自己的欲望,對自然一昧地索取,那么自然所為人類提供的各種資源,終將會歸向荒蕪。
無獨有偶,在“梁莊”系列作品中同樣存在這樣一份訴求。為順利推進鄉村建設,梁莊村民在政府的號召下,積極響應,開始對梁莊進行大規模地改造。在《蓬勃的“廢墟”村莊》中梁鴻不僅敘述了嶄新的樓房、承載回憶的坑塘以及背靠村莊的磚廠,也敘述了當今工業文明進程下鄉村改造存在的各種問題,比如承載著梁鴻無數回憶的坑塘,隨著建設的推進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坑塘里的水變成一灘死水,藻類植物上爬滿了蒼蠅,水面上扔著著各種生活垃圾,散發出的臭味兒直熏人的眼。除此之外,縣里為了更好地開發,還在河道附近開啟了采沙作業。河道周邊因政府采沙工作呈現出許多且不規則的沙窩,每逢汛期總有溺水事件發生。對于挖沙和生態的關系,副局長說“采沙對河的生態會有影響,但影響不大。”[6]試問采沙對河的影響真的不大嗎?縱有斗轉星移,滄海桑田之變局,也不能改變自然運行規律。在和自然相處的過程中人類應當尊重自然,敬畏自然,與自然和諧共生。
通過對“阿勒泰”和“梁莊”環境部分的描寫,在對人與自然的關系進行思考的同時,又更加確切了“非虛構”文學的寫作理念。為此“非虛構”文學的寫作應當立足于生態環境,基于作家的生活場所,傳達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態理念。
2.對精神困境的訴求
李娟在作品中不僅揭示了現代文明與傳統游牧文化的沖突,也抒發了自己對哈薩克族游牧文化消逝的焦慮和困惑。為了戈壁灘能夠更好地發展,政府實行退牧還草政策,即圈劃牧場,分區放牧。再后來因為植被逐年減少,生態環境惡化,政府又開始推行定居政策。“一到夏季,幾乎全空了,家家戶戶宅門深鎖,牛羊圈也空空蕩蕩,全村只留幾個男人懶洋洋地守著無邊的田地和水渠。”[7]雖然哈薩克族的傳統生活和勞動方式在短時間內適應了改變,但是在心靈上他們仍面臨著較為艱難的緩沖期。舍棄荒野求定居,一面是祖先千百年來的放牧生活,一面是當今下牧民美好的定居生活,禁不住讓人惋惜、擔憂,面臨傳統生活方式的消逝,人們的心靈又將歸棲何處?
梁鴻則在作品中揭露了鄉村在現代化進程中精神迷失的現象。梁莊小學曾是孩子接受教育的場所,如今它已關閉多年,成了村民的養豬場,墻上的“教書育人”甚是諷刺。在《今天的“救救孩子”》中作者梁鴻列舉了村里的留守兒童,由于長期缺少父母的陪伴,他們當中有的提早下學,走上打工的道路,而有的則是走上了犯罪道路。長此以往,“讀書無用”“上學不如打工”的思想更是充斥著整個村莊,使得村莊文化氛圍消失,文化凝聚力日益低下,教育水平甚是堪憂。但更為可笑的是,村民為了尋求精神支撐,開始信仰基督教,希望通過信教找到尊嚴、平等和被尊重。所以,在鄉村文化這一方面,有關部門應當立即做出調整,重視鄉村文化的建設,依托村民群眾發揮其向上之精神,重返鄉村文化務實之本質。
如果說“非虛構”文學的最大特點是真實性,那么時代性作為它的重要特點也是不容忽視的。“非虛構”文學的時代性要求文章的寫作目的或創作背景要結合當下的社會熱點來談,凸顯其時代性。總得來說,不管是李娟選取的游牧傳統文化的消逝,還是梁鴻筆下村莊精神文化的迷失,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現代文明進程中存在的社會問題。從讀者的角度來說,“非虛構”文學既讓讀者了解了社會現實,又讓讀者從中引發了對其問題的思考。
在李娟和梁鴻作品中,二者用自傳或他述的視角傳達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關系,呈現出作者對人類精神家園的回歸與渴望。不論是邊疆文學,還是鄉土文學,“作家的任務是出現在作品中,以一種個人的方式與讀者交流,而非將自己作為作品的唯一主體。”[8]所以,“非虛構”文學作家在創作時應平衡好自己與作品的關系,創作出以個人生存空間與審美體驗為基礎的“非虛構”文學作品,譜寫生命的戀歌和生態審美觀。
參考文獻
[1]董鼎山.所謂“非虛構小說”[J].讀書,1980(04):134.
[2]田裕嬌.新世紀“非虛構”文學中的中國圖景[D].山東理工大學,2018.
[3]李娟.我的阿勒泰[M].云南:云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0:18.
[4]周秀英.李娟散文中的自然景觀與文學呈現[J].新疆藝術(漢文),2020(05):46.
[5]袁雪.新世紀“非虛構文學”創作研究[D].山東師范大學,2019.
[6]梁鴻.中國在梁莊[M].成都:天地出版社,2017:52.
[7]李娟.阿勒泰的角落.[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116.
[8][美]雪莉·艾利斯.開始寫吧!——非虛構文學創作[M].刁克利,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77.
本文系國家級一流本科專業——塔里木大學漢語言專業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塔里木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