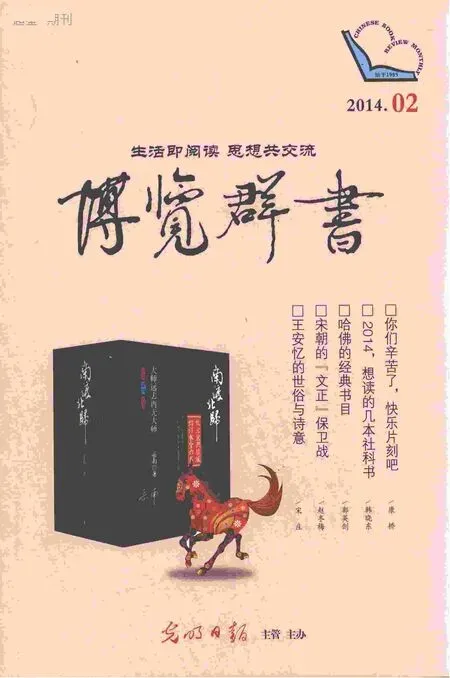到《我們家》感受四川麻辣
朱彩蓮

維特斯坦根曾在《哲學研究》中說:“想象一種語言意味著想象一種生活方式。” 汪曾祺也在《小說的思想和語言》說道:“寫小說就是寫語言。”在小說《我們家》(顏歌:《我們家》,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中,顏歌選擇用方言的想象和虛構,來貼近她所認知的現實。談到這本小說的緣起,顏歌說道:
本來是想要寫一家子知識分子怎么熱愛文學的故事。試著寫了一點以后,我不太喜歡作品中的“知識分子氣息”和“教師家庭倫理感”,干脆反其道而行之,嘗試著把主角從語文老師變成了豆瓣廠土老板。(陳曉勤:《顏歌:我一直在寫我們鎮上人的故事(華語文學傳媒獎)》,《南方都市報》,2013年4月28日)
要寫真實的川西小鎮,寫80年代真實的中國現實,顏歌選擇回到了地道的四川方言。從寫“平樂鎮”開始,她就意識到:
普通話是一種虛假的發明語言。在現實生活中的人們講的都是各自的土語、方言。……歸根結底,平樂鎮上的男男女女要說著四川話才能行走和活動起來。(同上)
因此,在盡量不影響非四川讀者閱讀的情況下,她盡可能地使用了方言寫作——不僅在人物對話,而且也在敘述中直接使用方言。最終,四川方言賦予了這個小鎮特有的地方性美學特征,塑造了鮮活立體的人物形象,一場活色生香的“麻辣”生活便這樣在西南小鎮上演。
“麻辣”特色對應的是“豆瓣”與“花椒”,這兩者“一主一副”,共同構成了這部方言小說的底色。雖然“豆瓣”是大生意,“花椒”是小攤攤,但“這兩件都是我們平樂鎮上人吃飯少不了的營生,我們鎮上的人吶,怎么說呢,可能從小就把舌頭打了洞,吃著海椒面生出來,喝口稀飯都少不了麻辣兩味”,顏歌這樣寫道。在《我們家》中,平樂鎮上最大的工廠,就是薛勝強經營的豆瓣廠,它來源于顏歌對故鄉郫筒縣的回憶。而“豆瓣”作為一種極富特色的地方代表物,不僅塑造了小說的地域特色,也塑造了核心人物薛勝強的現實性格。豆瓣廠教會了他攪豆瓣,也成為他性啟蒙的開始。在師傅的點撥下,他看著缸子里的豆瓣“發出水汩汩的呻吟,浸出紅燦燦的辣椒油,冒著銷魂的香氣”,兩眼瞇縫間,他想起了“紅幺妹”那火辣辣汗膩膩的床單。最終,薛勝強開起了豆瓣廠,當上了土老板;而他的風流多情,狀況頻發,也成了他這樣火火辣辣、大大咧咧的性格中的一部分。
而小說另外一條支線,也離不開“豆瓣”的搭檔“花椒”,它指向了大哥段知明。大哥與薛勝強的人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而他對大哥的復雜情感,也淋漓地塑造了其真實立體的形象。在得知大哥破天荒要回老家給母親祝壽之后,薛勝強從花椒西施周小芹那買了兩包花椒送給他。花椒里是過去的一段往事,更是薛勝強的人生轉折點;它包含著辛辣的嫉妒,還有一絲怨恨的味道。然而,隨著故事深入發展,平時滿腹牢騷,連通訊錄都不愿意看見大哥名字的薛勝強,在“眼見大伯的眼睛紅起紅起就像是油碟里的海椒”后,所有的怨氣和誤會化作了一句自罵,“老子真的是個悶墩兒哦!”他不禁怪罪自己組什么相親飯局,拿什么花椒做文章,所有沒說出口的安慰和解釋,也變成了全心全意把大哥的事當作自己事的決心。在小說結尾薛勝強的暢想中,大哥與花椒西施周小芹終于完婚,大哥的心愿就此了結,而他與大哥的心結也終于結束。
除了完美糅合極具特色的川地風情,方言還接通了最真實的生活體驗。在這些“麻辣”生活的背后,似乎還隱藏著一些深奧道理:
爸爸在豆瓣廠打滾了二十多年,從陳修良手下學得功夫,逃出生天,這才總算明白了一件事情:人活著就是為了出汗。吃豆瓣是為了出汗,吃花椒也是圖出汗,吃麻辣燙還是要出汗,跟婆娘睡覺就更是出汗了。熱汗嘛,出得越多人越舒暢,爸爸想,他想起了紅幺妹房頭那張火辣辣汗膩膩的床單。
“出汗”,在薛勝強的觀念里,它近似于某種本能的快樂。在這里,作者將“吃豆瓣”與“跟婆娘睡覺”并提。所謂“食色性也”,“男女”與“飲食”同樣快樂,同樣并不可少。而小說從薛勝強的視角來寫,就讓這個“弗洛伊德”式的道理顯得十分的樸素,它從這片土地里生長出來,具有強烈的地域特色。
當然,在顏歌的方言寫作中,真實的生活除了源自這塊西南大地的原始沖動,更多的還摻雜著日常的混沌,在一地雞毛中,四川人特有的幽默輕松、淡然豁達的性格特點,愈加鮮明。薛勝強作為小說的主視角,無疑最能體現這樣極具地域特色的人物形象塑造。顏歌曾這樣形容過這種性格:“他人說我我不氣,我的心中有主意。”薛勝強就是這樣一個大剌剌、粗魯魯的男子。面對家人和好友時,他內心時常充滿了抱怨,“龜兒子的,硬是把我當悶豬兒耍哦”,但真正做起來時,又總是“算逑了”,答應的該做的事,一件不落地都辦踏實了。這樣克制的一面,似乎與他放縱的一面相去甚遠。甚至連自己因長期生活工作習慣而得上的心臟病,他也總是一副“沒事”“不打緊”的模樣,幽默又淡然。奶奶八十大壽的前一天,薛勝強的心臟病又犯了,被一家子的大新聞爆炸突襲的他,剛來得及閃過一句“龜兒子!昨天搞忘吃藥了”,就倒在了眾人面前。然而在眾人忙得團團轉的時候,他卻在心里暗暗吶喊叫他們不要鬧,嘰嘰喳喳“叫得腦殼痛”。這時他腦海里“撞邪了一樣”開始了跑馬燈的畫面,但又不慌不忙地暢想了未來幾年的狀況。最后,他回過神來,“這些以后的事先不要提了……現在最重要的任務是醒過來,免得這些人把眼流花兒啊,鼻涕水啊,都往他身上揩。”然后隨著一句悠悠:“哎呀,小點聲,我沒事,不要吼嘛,沒事,還是先把媽的八十大壽過了再說。”薛勝強就醒過來了。這和他第一次心臟病發作如出一轍,那次生日酒席上,薛勝強突然眼睛一花,氣都提不上來了,一屋子的人都嚇壞了。好友鐘師忠看見他尿失禁,眼淚都包不住了,薛勝強卻在心里吶喊:“你哭錘子!老子又不是你婆娘,老子又沒死!”等緩過來之后,他也是一句悠悠的話:“哎呀你們龜兒子的小聲點嘛!”
在小說結尾,由著這樣樂觀豁達、大剌剌的性子,在樸素的欲望理念加持下,薛勝強最后居然原諒了自己出軌的“情婦”和與之偷情的司機。“都是男人嘛,互相理解。”看見小鐘癟下去的肚子,他心里十分過意不去,又塞給了她一筆錢。
然而,薛勝強的這種行為于在城市工作的大哥和姐姐眼里中,顯然是難以理解的。這也暗示了小說中互相隱秘對抗的兩種話語。對于在電視臺工作、操著一口清清淡淡的普通話的姐姐,薛勝強總是“收斂了他滿肚子的怪話,端端正正地,跟向大隊長匯報工作一樣”,說著家里都好。作為城市知識分子的大哥,在聽說了弟弟的事之后總是提醒他“好生處理”,處理不過來的話可以幫忙處理。對此,薛勝強卻很不服氣,娃娃和小鐘,他都舍不得處理,難道要把他處理了嘛!
這種話語和觀念的沖突,不僅僅是鄉鎮和城市之間的矛盾,更是方言作為一種話語與某種現代的官方話語之間的對抗。在當下我們已經習慣于“正統”的文學史,已經習慣于從“現代”的視角去觀察世界時,方言寫作給我們提供了得以進入“鄉土社會”視角的機會。在這里,人生道理和行事原則,不是夠不著的幾條“統一”規定,也不是移植的輕飄飄的現代理念,而是扎根生長于我們腳下的土地。敬文東在《被委以重任的方言》中,將這兩種互相對抗的話語歸為“正史話語”與“野史話語”,并將其理論支柱歸為“儒道”和“楊墨”兩種不同的思想。敬文東認為,比起“儒道”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楊墨”的核心思想“為我”“貴生”“兼愛”,更加貼合普通小民的心理。“楊朱”宣揚利我,“墨子”倡導“兼相愛,交相利”,這套建立在“利我”邏輯基點上的話語,隱秘地連通了地緣和宗族關系,也完美地連通了薛勝強“為我”的放浪形骸,以及面對親友家人的“貴生”“兼愛”。而這些,正是普通讀者從方言寫作中、從這個不同的視角里,找到共鳴的地方,正如作者自己在小說最后所說的那樣:“隨著故事的進行,隨著那個多年前的我繼續往下寫,我的憤怒逐漸消失了,到最后,我真心實意地喜歡薛勝強,與他和解了。”
另一方面,我們從人物塑造回到整個方言寫作中來看,小說中,薛勝強面臨的是來自大哥和姐姐的無形壓力(小說中“奶奶”對他們的喜愛更是無形中賦權了這種地位),似乎也在某種意義上象征著現代化進程中方言所面臨的被壓抑處境。從五四白話文運動倡導“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到1955年推廣普通話進行規范化改革,方言作為一種地方性的表征,一直面臨著被改造被收編的問題。1918年,胡適曾在《新青年》上發表過關于方言問題的看法:
并且將來國語文學興起之后,盡可以有“方言的文學”。方言的文學越多,國語的文學越有取材的資料,越有濃富的內容和活潑的生命。……國語的文學造成之后,有了標準,不但不怕方言的文學與他爭長,并且還要倚靠各地方言供給他的新刊料,新血脈。(胡適:《答黃覺僧君折衷的文學革新論》,《新青年》,1918年9月15日第5卷第3號)
這也成為在中國在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過程中,方言文學之于“國語”文學的關系經典表述。而這背后實際上是由五四運動的現代性邏輯決定的。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體》中談到了“民族標準語”對于民族共同體的重要意義,歐洲各現代民族國家正是在選取某種方言的基礎上,創制統一的“民族標準語”,在對抗拉丁語的支配中逐漸形成了民族認同。同樣地,在民族國家的探尋和建立的過程中,中國的方言也有著類似的遭遇。盡管在建立過程之中,“延安文藝講話”曾一度倡導“大眾的文學”,引導知識分子學習人民的語言,深入群眾宣傳。但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工業化建設中,由于“語言共同體必須在民族國家中與法律共同體重疊起來”(哈貝馬斯:《何謂民族?》,《后民族結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版,P12),這種“國語”則走向了更高的同質化,而方言的特殊性,以及方言作為語言本身所具有的美學特征,都更多地面臨著被忽視的處境。
1955年10月,《人民日報》發表了《為促進漢字改革、推廣普通話、實現漢語規范化而努力》社論。社論重申了語言的工具功能,并對文學作品的語言規范從政治上給出了合理性:“普通話是為全民服務的,方言是為一個地區的人民服務的。”“語言的規范化必須寄托在有形的東西上。這首先是一切作品,特別重要的是文學作品。”一方面,論者普遍接受了方言的差異是單純的語音的差異的觀點;而另一方面,方言文學的必要性似乎也被消解,正如茅盾所說:
我們不反對作品有地方色彩……但是地方色彩的獲得不能簡單地依靠方言、俗語。而要通過典型的風土人情的描寫,來制造特殊的氣氛。(茅盾:《關于藝術的技巧——在全國青年文學創作者會議上的報告》,《文藝學習》,1956年4月號)
似乎從這時候開始,不論從服務對象的正確性、還是工具的必要性上,方言都失去了它原本的地位,與其地域性所能體現的某些美學特征斷開了聯系。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上世紀70年代末,當文學的討論重新回歸到“人”上,地方和方言才又重新被喚醒。隨著“尋根文學”思潮的興起,尤其是莫言、韓少功的創作,方言作為一種語言對文學的影響,重新得到審視——也即寫作中的方言不僅是作為一種工具,更應是作為一種審美地把握世界的方式。區別于早年的“鄉土小說”,這一時期“尋根文學”的方言寫作更多是在現代性邏輯下,抵抗國內社會政治話語的一種需要,同時也是對話世界文學、展示本土文化生命的一種姿態。
而《我們家》的創作,無疑正是“尋根文學”的回響。它創作于顏歌美國訪學期間,正是因為在一個異質的文化地理中有了某種“局外人”對本土的關照,才激發了顏歌方言寫作的靈感;另一方面,在如今走向現代化工業化的時代,方言寫作或許也是一種對抗現代性的異化、尋回生命本質的方式。在《馬橋詞典》中,馬橋人對“夷邊”的高樓大廈患上了“暈街”癥,于是把停在路邊的汽車揍了個半死。而在《我們家》中,盡管小說背景已經轉移到了80年代的城鄉接合部,但仍透露出類似的隱憂和對抗:薛勝強發現,不知什么時候“鋼板廠關門大吉了,李裁縫的門面給移去了攤販市場,取痣的焦醫生丟了錦旗,所有的店招都統一換成了藍底白字的,一眼看過去真分不出個雌雄公母”;路變寬了,綠化帶栽上了移植的樹,家家都開著小汽車從東街堵到西街,去超市里排隊買菜。與之對應的則是薛勝強的痛罵:“一個二個長起腳的嘛!兩步路!買包鹽都要把汽車開出來!”這種爽直暢快、生動鮮活、承載著強烈地域特征和文化烙印的語言,或許正是我們個人得以在現代化的轟隆巨輪下,得以片刻呼吸、把握自身存在之所。也許,有一天城鄉接合部也會消失,也許有一天方言會被普通話漸漸打磨光滑,但個人與地域之間的聯系是永遠生動而真實地存在的,而這種聯系中誕生和活躍的語言,蘊含著關于個體的本源性的強大生命力量。它塑造了我們,反過來,也是我們把握現實存在的方式,所謂“我的語言的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想來即是如此。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2019級文藝學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