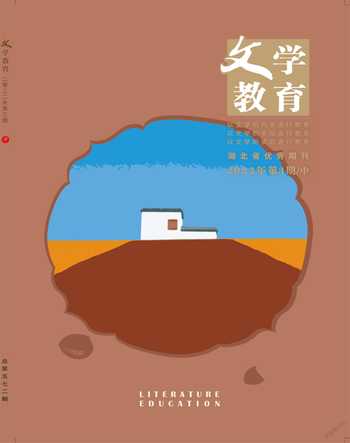《自殺論》中的道德危機(jī)與重建
陳倩穎 梁明月
內(nèi)容摘要:在法國(guó)社會(huì)學(xué)家涂爾干的《自殺論》問(wèn)世之前,人們對(duì)自殺的研究和認(rèn)識(shí)是淺薄的,自殺毋庸置疑根源于個(gè)人問(wèn)題。涂爾干通過(guò)實(shí)證分析,對(duì)自殺的共性和個(gè)性進(jìn)行深入探討,總結(jié)出自殺的原因與規(guī)律,在個(gè)人根源的背后還隱藏著以一個(gè)更具影響力的自殺驅(qū)動(dòng)力—社會(huì)。文章試圖基于涂爾干的已有研究,以探討現(xiàn)代社會(huì)的道德危機(jī)與道德重建。
關(guān)鍵詞:《自殺論》 道德危機(jī) 道德重建
《自殺論》作者埃米爾·迪爾凱姆(1858—1917,又譯為涂爾干),法國(guó)社會(huì)學(xué)家、人類學(xué)家,與卡爾·馬克思及馬克斯·韋伯并列為社會(huì)學(xué)的三大奠基人。
在短暫又漫長(zhǎng)的一生中,每個(gè)人都會(huì)遇到挫折、難過(guò)、悲痛,甚至萌生放棄自己生命的念頭。每個(gè)人也都非常清楚,自殺就是自己選擇放棄自己的生命。自殺的原因,要么是心理問(wèn)題導(dǎo)致的逃避現(xiàn)實(shí)世界,要么是人格障礙誘發(fā)的偏離正常行為方式。人們更傾向于相信,自殺者是因?yàn)樽陨韱?wèn)題無(wú)法得到解決,或者至少是在自殺那一刻無(wú)法勇敢面對(duì),從而選擇用結(jié)束自己生命的方式逃避自己無(wú)法解決的問(wèn)題,或者自認(rèn)為已經(jīng)預(yù)見(jiàn)將來(lái)的悲慘結(jié)局。
在《自殺論》問(wèn)世之前,人們對(duì)自殺的認(rèn)識(shí)和研究是淺薄的,得到的對(duì)自殺動(dòng)機(jī)的解釋無(wú)外乎對(duì)生活不抱希望,對(duì)塵世不再眷戀。在大眾看來(lái),自殺毋庸置疑根源于個(gè)人問(wèn)題。然而,在這個(gè)理所應(yīng)當(dāng)?shù)膫€(gè)人根源背后還隱藏著一個(gè)更具影響力的自殺驅(qū)動(dòng)力——社會(huì)。涂爾干通過(guò)實(shí)證分析,對(duì)自殺的共性和個(gè)性進(jìn)行深入探討,進(jìn)而總結(jié)出自殺的原因與規(guī)律。《自殺論》體現(xiàn)了涂爾干“社會(huì)事實(shí)只能用社會(huì)事實(shí)來(lái)解釋”的唯識(shí)論觀點(diǎn),為我們窺探社會(huì)暗地里靜悄悄地作用于我們的某些社會(huì)機(jī)制,將人性與社會(huì)互動(dòng)失調(diào)的種種案例呈現(xiàn)在我們眼前,為我們提供了一個(gè)社會(huì)研究的典范。《自殺論》無(wú)疑是對(duì)社會(huì)學(xué)的一大貢獻(xiàn)。
一.涂爾干的理論核心:社會(huì)與個(gè)人
作為社會(huì)學(xué)的奠基人之一,涂爾干希望從事的是能夠澄清當(dāng)代主要道德問(wèn)題、指導(dǎo)當(dāng)代社會(huì)發(fā)展的科學(xué),并擁有現(xiàn)代社會(huì)學(xué)所不具備的重建社會(huì)的宏大抱負(fù)。涂爾干認(rèn)為,工業(yè)社會(huì)的主要問(wèn)題在于各個(gè)機(jī)構(gòu)或部分之間的關(guān)系沒(méi)有得到有效規(guī)定,即“道德失范”問(wèn)題。他試圖找到社會(huì)混亂的根源和性質(zhì),并找到一種使混亂的機(jī)構(gòu)或部分調(diào)和起來(lái)的方法。
1.機(jī)械團(tuán)結(jié)與有機(jī)團(tuán)結(jié)
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分為機(jī)械團(tuán)結(jié)和有機(jī)團(tuán)結(jié)。機(jī)械團(tuán)結(jié),即低等社會(huì)形態(tài)里基于“相似性”的團(tuán)結(jié);有機(jī)團(tuán)結(jié),即通過(guò)勞動(dòng)分工的發(fā)展進(jìn)一步促進(jìn)產(chǎn)生的以協(xié)作性法律和恢復(fù)性制裁為特征的團(tuán)結(jié)。[1]
前者發(fā)生在低等社會(huì)中。該社會(huì)的法律以壓制性法律為主,勞動(dòng)分工尚未產(chǎn)生。個(gè)體之間存在一定的相似性,社會(huì)成員彼此吸引,進(jìn)而結(jié)合成社會(huì)。在機(jī)械團(tuán)結(jié)中,社會(huì)是由所有成員的共同情感和信仰組成,集體意識(shí)完全覆蓋或淹沒(méi)個(gè)體意識(shí)。此時(shí),個(gè)體只是一種“集體存在”,個(gè)體意識(shí)完全依賴于集體類型,追隨集體行動(dòng)。[2]
后者發(fā)生在勞動(dòng)分工產(chǎn)生并發(fā)展的社會(huì)中。分工,既使得個(gè)體之間保持聯(lián)系,又導(dǎo)致了社會(huì)的集中,這種集中又反作用于分工,使得社會(huì)各部分緊密聯(lián)系。分工,具有促進(jìn)社會(huì)各部分形成牢固關(guān)系的道德意義之外,還能以道德的形式滲透到所有利于促成合作團(tuán)結(jié)的關(guān)系中。在有機(jī)團(tuán)結(jié)中,社會(huì)以個(gè)體的個(gè)性和差別為基礎(chǔ)。個(gè)體通過(guò)專門化活動(dòng),借助于分工形成的相互依賴關(guān)系結(jié)合起來(lái)。[3]
2.失范與自殺
分工使社會(huì)工作的職能越來(lái)越專門化,意味著了解所有職能的人就越來(lái)越少。涂爾干并沒(méi)有完全線性地解讀分工的道德意義。集體意識(shí)弱化,個(gè)體意識(shí)增強(qiáng),隨之而來(lái)一系列“失范”問(wèn)題。在涂爾干看來(lái),現(xiàn)代社會(huì)的分化現(xiàn)象創(chuàng)造了個(gè)人自由的條件,這種個(gè)人主義的社會(huì)里,首要的問(wèn)題是保持“最低限度的集體意識(shí)”,否則,社會(huì)就會(huì)解體。[4]如果分工沒(méi)有產(chǎn)生團(tuán)結(jié),那不是分工本身的問(wèn)題,而是分化的各個(gè)機(jī)構(gòu)的關(guān)系沒(méi)有得到“規(guī)定”,進(jìn)而陷入“失范”狀態(tài)。[5]
涂爾干對(duì)自殺做了概念界定,即人們把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會(huì)產(chǎn)生這種結(jié)果的某種積極或消極的行動(dòng)直接或間接地引起的死亡。[6]對(duì)于自殺率提高的原因,涂爾干從道德結(jié)構(gòu)或者社會(huì)組織狀況出發(fā),區(qū)分了三種自殺:利他主義自殺、利己主義自殺和反常的自殺。
利他主義自殺與低級(jí)社會(huì)有關(guān)尤其明顯。正因?yàn)閭€(gè)人嚴(yán)格服從群體是這些社會(huì)的基本原則,所以可以說(shuō),利他主義自殺是低級(jí)社會(huì)集體紀(jì)律不可缺少的一種手段。如果一個(gè)人為了一點(diǎn)小事就不重視自己的生命,那么他就不是一個(gè)體面的人,而且,既然他不重視生命,那么一切都不可避免地成為他擺脫生命的借口。因此,這種自殺和這些社會(huì)的道德結(jié)構(gòu)之間有著某種密切的聯(lián)系。[7]
利己主義自殺來(lái)自相反的原因,“由于某些相反的原因,在個(gè)人的尊嚴(yán)是行為的最終目標(biāo)、人是人類的上帝的社會(huì)和環(huán)境中,個(gè)人很容易傾向于把自己當(dāng)作上帝,把自己當(dāng)作崇拜的對(duì)象。當(dāng)?shù)赖率紫戎铝τ谑箓€(gè)人十分看重自己的時(shí)候,只要有某些情況綜合在一起就足以使個(gè)人根本看不到有誰(shuí)高于自己。”當(dāng)然,個(gè)人主義不一定是利己主義,但接近利己主義,不可能激發(fā)個(gè)人主義而不進(jìn)一步加強(qiáng)利己主義。利己主義自殺便由此發(fā)生。[8]
反常的自殺是由于打亂了集體秩序。對(duì)平衡的任何破壞,哪怕由此而導(dǎo)致更大的富裕和生活的普遍提高,也會(huì)引起自殺。每當(dāng)社會(huì)機(jī)體發(fā)生重大的調(diào)整時(shí),不管是由于迅速的發(fā)展還是由于意外的災(zāi)難,人都容易自殺。[9]
整個(gè)道德的進(jìn)步和完善在某種程度上是和反常分不開(kāi)的。一定的道德素質(zhì)和一定類型的自殺是互相對(duì)應(yīng)和互相關(guān)聯(lián)的,兩者不可或缺,因?yàn)樽詺⒅皇敲恳环N道德素質(zhì)在某些特殊條件下必然要采取的形式,而這些特殊條件不可能不產(chǎn)生。
二.現(xiàn)代社會(huì)的道德危機(jī)
從現(xiàn)代人失喪的精神與病態(tài)的心智入手,理解涂爾干的《自殺論》。涂爾干筆下的三種自殺類型,都是個(gè)體在社會(huì)中的失衡狀態(tài)相關(guān)。涂爾干正是通過(guò)描述這些自殺類型,折射出個(gè)體背后的社會(huì)組織狀況和道德結(jié)構(gòu)。個(gè)體深深地感知到,自己實(shí)際處于邊緣化、去中心化的社會(huì)生存狀態(tài),所以個(gè)體強(qiáng)烈掙扎著投身到一個(gè)想象的、超越現(xiàn)實(shí)的集體中,殊不知,在自我創(chuàng)造能力中也潛藏著自毀能力。
現(xiàn)代人既能為自己締造日新月異的生活方式,也能將自己帶向自我毀滅的陷阱。人活著不再只是為了吃飽喝足,現(xiàn)代人的物質(zhì)比前現(xiàn)代人更加豐富有余,所以,人開(kāi)始渴望追尋人生的方向、價(jià)值和目標(biāo)。在這個(gè)時(shí)代,現(xiàn)代人深知自己不單可以摧毀生命,還可以摧毀生命的再造形態(tài);不單可以摧毀自己,還可以摧毀全人類;人不單可以摧毀某個(gè)歷史階段,還可以摧毀歷史本身。對(duì)現(xiàn)代人來(lái)說(shuō),未來(lái)是一個(gè)選擇,道德也只是一個(gè)選擇;而這些選擇,會(huì)在個(gè)體生命歷史的行進(jìn)過(guò)程中隨時(shí)被重新選擇。
現(xiàn)代社會(huì)的一切都呈現(xiàn)出多變性、復(fù)雜性、含混性等特點(diǎn),變得支離破碎,變得充滿矛盾和沖突。正是這樣一個(gè)殘酷的現(xiàn)實(shí),使個(gè)體的生活成為一種偶發(fā)性的經(jīng)歷,變得不可確定、無(wú)法預(yù)測(cè)。處于社會(huì)之中的個(gè)體變得隨遇而安,受突發(fā)事件和無(wú)法預(yù)見(jiàn)的環(huán)境左右;也變得隨遇而安,習(xí)慣于或主動(dòng)或被動(dòng)地被邊緣化;隨之,由人構(gòu)成的整體社會(huì)變得低幼化,個(gè)體自我嬌慣、自我欺騙、自我撒嬌,不愿意面對(duì)清醒的自我,成年人裝嫩,年青人裝不負(fù)責(zé)任、裝無(wú)辜。在現(xiàn)代社會(huì)種種力量的壓力下,成年人似乎比過(guò)去更脆弱了,他們自己更像孩子了;孩子似乎很快就成熟多了,似乎過(guò)早地見(jiàn)多識(shí)廣了。
生活在現(xiàn)代社會(huì)的年青一代,常常必須對(duì)早期的壓力和不成熟的期望作出反應(yīng),這種壓力和期望來(lái)自同樣處于普遍低幼化的成人。他們希望孩子們快快按照“自己腦海中假象的孩子們”的模樣長(zhǎng)大,但這似乎是不可能的、不切合實(shí)際的。后現(xiàn)代的孩子出生在一個(gè)能在有限的時(shí)空內(nèi)體驗(yàn)生活的各種可能性的社會(huì)中,他們看到的和體驗(yàn)到的世界變得越來(lái)越封閉,他們變得突然充滿了防備心。所以,創(chuàng)造親密,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身體上的親密感,智識(shí)上的親密感,對(duì)自我覺(jué)知、對(duì)社會(huì)運(yùn)轉(zhuǎn),同樣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如何產(chǎn)生這種親密感,個(gè)體需要通過(guò)基于個(gè)人自由的道德重建。但前提是,個(gè)體和社會(huì)需要意識(shí)到并且承認(rèn)自身確實(shí)處于道德危機(jī)之中。
總之,涂爾干通過(guò)對(duì)自殺的分類來(lái)描述現(xiàn)代社會(huì)中的個(gè)體以及社會(huì)本身,其實(shí)都處于極端狀態(tài)的痛苦之中。自殺傾向高漲的不是我們的文明日益光輝燦爛,而是一種道德上的危機(jī)和動(dòng)蕩狀態(tài),這種狀態(tài)的延續(xù)不可能沒(méi)有危險(xiǎn)。
三.基于個(gè)人自由的道德重建
涂爾干對(duì)于道德有其獨(dú)特的概念界定:一般而言,我們認(rèn)為道德規(guī)范的特性在于它闡明了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的基本條件。法律和道德就是能夠把我們自身和我們與社會(huì)聯(lián)系起來(lái)的所有紐帶,它能夠?qū)⒁蝗簽鹾现娮兂梢粋€(gè)具有凝聚力的團(tuán)體。任何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的根源,任何促使人們?nèi)ンw諒他人的動(dòng)力,任何對(duì)自身行為不帶私心的規(guī)定,都可以稱作道德,這些紐帶的數(shù)量越多、力量越強(qiáng),道德本身也就越牢固。[10]
涂爾干社會(huì)學(xué)思想的關(guān)鍵在于兩點(diǎn):一是,理解社會(huì)結(jié)構(gòu);二是,理解人性與社會(huì)之間的關(guān)系。道德是社會(huì)的產(chǎn)物,道德?tīng)顟B(tài)是個(gè)體社會(huì)性的體現(xiàn)。基于個(gè)人自由的道德重建的實(shí)質(zhì),即個(gè)人與社會(huì)關(guān)系的呈現(xiàn)。道德重建,既依賴于特定的社會(huì)條件,又依賴于人性基礎(chǔ)。人性本身由社會(huì)養(yǎng)成,人性的培育有其特定的社會(huì)條件,正是因?yàn)樯鐣?huì),人性才能獲得整體性。因而,現(xiàn)代人的教育應(yīng)當(dāng)科學(xué)、歷史、藝術(shù)并重。[11]在涂爾干看來(lái),教育的目的首先是使個(gè)人服從紀(jì)律的同時(shí)發(fā)展個(gè)性,在于使每個(gè)人具有自治、思考和選擇的意識(shí)。[12]
涂爾干充分關(guān)注個(gè)體自殺背后所要揭示的社會(huì)秩序。人是符號(hào)的動(dòng)物,而非理性的動(dòng)物。動(dòng)物具有實(shí)踐的想象力和智慧,而只有人才發(fā)展了一種新的形式:符號(hào)的想象力和智慧。[13]人,像動(dòng)物一樣,服從著社會(huì)的各種法則,但是除此以外,他還能積極地參與創(chuàng)造和改變社會(huì)生活形式的活動(dòng)。[14]同時(shí),人并非直接地,而是靠著一個(gè)非常復(fù)雜和艱難的思維過(guò)程,才獲得了抽象空間的觀念——正是這種觀念,不僅為人開(kāi)辟了通向一個(gè)新的知識(shí)領(lǐng)域的道路,而且開(kāi)辟了人的文化生活的一個(gè)全新方向。[15]人在不斷自我解放的歷程中,發(fā)現(xiàn)并證實(shí)了一種新的力量——建設(shè)一個(gè)自己的世界、一個(gè)“理想”世界的力量。對(duì)于涂爾干而言,人類之所以區(qū)別于動(dòng)物,正在于他的“道德生活”本質(zhì),有機(jī)團(tuán)結(jié)仍然需要某種道德權(quán)威的力量遏制個(gè)人的欲望,防止陷入無(wú)政府主義狀態(tài)。這也是涂爾干如此重視教育和社會(huì)化的根源所在。[16]
在涂爾干看來(lái),道德規(guī)范具備的要素有三:一是紀(jì)律;二是個(gè)體對(duì)群體的依戀;三是自主性或自決性。紀(jì)律是道德的首要要素,是約束或禁止的能力。個(gè)體對(duì)群體的依賴是道德的次要要素,是個(gè)體通過(guò)教育這一手段與周圍的社會(huì)建立聯(lián)結(jié)的必經(jīng)之路。自主性或自決性是道德的知性,是個(gè)體自愿接受規(guī)范的內(nèi)部驅(qū)動(dòng)和外在約束的共同體。道德規(guī)范的教授,不僅僅是灌輸,而在于理解。要讓道德成為一種建立在生命美學(xué)意義上的闡釋性和實(shí)踐性規(guī)范。如果個(gè)體不理解某一道德行為,也就無(wú)法理解該道德行為背后所傳遞的情感體驗(yàn)和智識(shí)內(nèi)化,這種道德就是不完全的、失效的、低級(jí)的道德。因此,涂爾干的關(guān)于社會(huì)與個(gè)人、現(xiàn)代社會(huì)的道德危機(jī)和基于個(gè)人自由的道德重建就與現(xiàn)代社會(huì)的教育問(wèn)題和教育學(xué)本身聯(lián)系起來(lái)了。
最后,借用涂爾干的一段話,“要防止這種集體的悲慘遭遇,至少要減輕集體的弊病,因?yàn)榍罢呤呛笳叩慕Y(jié)果和征候。我們已經(jīng)證明,為了達(dá)到這個(gè)目的,沒(méi)有必要人為地恢復(fù)過(guò)時(shí)的、僅僅體現(xiàn)生活表面現(xiàn)象的社會(huì)形態(tài),也沒(méi)有必要?jiǎng)?chuàng)造全新的、歷史上沒(méi)有過(guò)的社會(huì)形態(tài)。應(yīng)該做的是在過(guò)去的形態(tài)中尋找新生活的萌芽并促使其開(kāi)花結(jié)果。”[17]道德的本質(zhì)固然是社會(huì),但也要意識(shí)到個(gè)人作為道德有機(jī)體的內(nèi)在力量。
參考文獻(xiàn)
[1]鄭中玉,王雅林.作為社會(huì)工程的道德重建——基于對(duì)涂爾干社會(huì)理論的理解[J].社會(huì)科學(xué)戰(zhàn)線,2012(05):155-163.
[3]鄭中玉,王雅林.作為社會(huì)工程的道德重建——基于對(duì)涂爾干社會(huì)理論的理解[J].社會(huì)科學(xué)戰(zhàn)線,2012(05):155-163.
[2]埃米爾·涂爾干.社會(huì)分工論[M].渠東譯,北京:生活·讀書(shū)·新知三聯(lián)書(shū)店,2000:90-91.
[4]雷蒙·阿隆.社會(huì)學(xué)主要思潮[M].葛志強(qiáng)、胡秉誠(chéng)、王滬寧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221.
[5]埃米爾·涂爾干.社會(huì)分工論[M].渠東譯,北京:生活·讀書(shū)·新知三聯(lián)書(shū)店,2000:328.
[6]埃米爾·涂爾干.自殺論[M].馮韻文譯,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2001:11.
[7]埃米爾·涂爾干.自殺論[M].馮韻文譯,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2001:403.
[8]埃米爾·涂爾干.自殺論[M].馮韻文譯,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2001:403.
[9]埃米爾·涂爾干.自殺論[M].馮韻文譯,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2001:265.
[10]埃米爾·涂爾干.社會(huì)分工論[M].渠東譯,北京:生活·讀書(shū)·新知三聯(lián)書(shū)店,2000:356-357.
[11]吳柳財(cái).涂爾干視野下的個(gè)人主義與道德教育[J].廣東社會(huì)科學(xué),2021,(04):211-219.
[12]鄭中玉,王雅林.作為社會(huì)工程的道德重建——基于對(duì)涂爾干社會(huì)理論的理解[J].社會(huì)科學(xué)戰(zhàn)線,2012(05):155-163.
[13]恩斯特·卡西爾.人論[M].甘陽(yáng)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52.
[14]恩斯特·卡西爾.人論[M].甘陽(yáng)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350.
[15]恩斯特·卡西爾.人論[M].甘陽(yáng)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68-69.
[16]鄭中玉,王雅林.作為社會(huì)工程的道德重建——基于對(duì)涂爾干社會(huì)理論的理解[J].社會(huì)科學(xué)戰(zhàn)線,2012(05):155-163.
[17]埃米爾·涂爾干.自殺論[M].馮韻文譯,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2001:435.
本文系2019年浙江省高等教育十三五第二批教學(xué)改革研究項(xiàng)目“基于德育助推理論的《小學(xué)班級(jí)管理》教學(xué)改革研究”(課題批準(zhǔn)號(hào):jg20190129)的研究成果。
(作者單位:寧波大學(xué)教師教育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