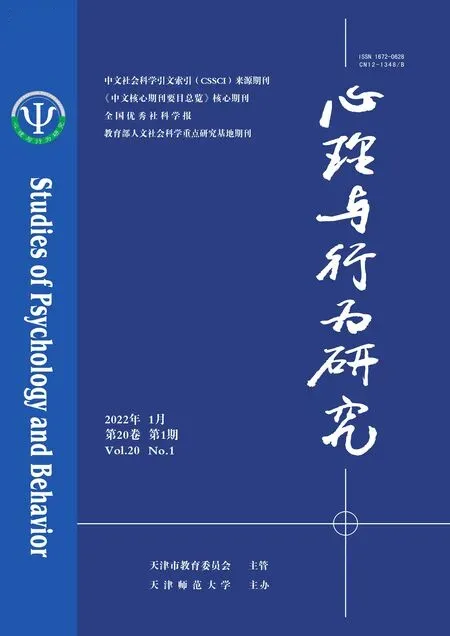成就目標與教師效能感、焦慮、工作投入的關系:基于變量中心和個體中心的視角
王嘉瑩 姚梅林 劉紅瑞
(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部,應用實驗心理北京市重點實驗室,北京 100875)
1 引言
教師肩負著教書育人的重任,是教育發展的第一資源。在學校這一成就環境中,教師動機(如,成就目標)是決定教師工作投入多寡的重要因素(Ames, 1992; Papaioannou & Christodoulidis,2007)。然而,以往針對成就目標(achievement goal)的研究大多基于學生群體,對教師群體的關注較少。事實上,教師作為課程和學生之間的重要橋梁(Papaioannou & Christodoulidis, 2007),其成就目標不僅會對學生產生至關重要的作用(Schiefele & Schaffner, 2015),也會影響其個人身心健康與專業發展(Kunst, van Woerkom, & Poell, 2018)。
教師成就目標反映了教師本人在教學工作中的目標追求(Butler, 2007; Gorozidis & Papaioannou,2016)。Papaioannou 和 Christodoulidis(2007)將成就目標的三分模型(Elliot & Harackiewicz, 1996)拓展至教師群體,包括:掌握目標,即以提高自身能力、掌握知識為目標;表現趨近目標,即以證明自身能力以獲得他人積極評價為目標;表現回避目標,即以避免顯得能力不足及由此引發的他人消極評價為目標。以往關注教師成就目標的研究大多基于變量中心視角展開,忽視了個體差異和多種目標共存時的相互影響。有研究者基于個體中心的多重目標視角,提出:(1)不同個體可能持有三種目標的不同組合模式,如同時持有三種目標或以某目標為主導(Barron & Harackiewicz,2001; Luo et al., 2011);(2)同時持有掌握與表現趨近目標比只持有掌握目標更具優勢(Payne et al.,2007)。國外基于上述視角的一項研究發現,教師成就目標可劃分為五個潛在類別,即平均型、中等掌握型、高回避型、表現定向型和成功定向型(即,高掌握目標、高表現趨近目標及低表現回避目標的組合);其中,成功定向型的適應性最佳,而高回避型的適應性最差(Kunst, van Woerkom, &Poell, 2018)。該研究更為全面、清晰地揭示了教師群體的不同成就目標剖面及其對教師發展的影響。然而,各國教師的工作環境不一樣,例如,我國教師的協同專業發展更加制度化,整個社會對教師抱有高期望等(Grant et al., 2013),能夠反映教師群體工作特征的成就目標剖面類型及其占比可能會有所不同,因此,有必要在中國文化背景下展開研究。
工作投入(work engagement)是指個體專注于工作并付出努力和熱情的意愿(Christian et al.,2011)。教學需要高度的自主性和自我調節能力,故教師個人動機是決定其工作投入的重要因素(Daumiller et al., 2019; Sabagh et al., 2018)。持掌握目標的教師將工作視為提升個人能力的機會,進而認真對待并全身心投入工作;持表現趨近目標的教師力圖在工作中展現個人能力,故在工作時也會付出努力與熱情;而持表現回避目標的教師往往將工作中的挑戰視為“威脅”,害怕失敗,而無法全身心投入(Daumiller & Dresel, 2020;Parker et al., 2012; Skaalvik & Skaalvik, 2013)。因此,不同成就目標與工作投入存在不同的關聯。進一步地,Elliott和Dweck(1988)的成就目標理論認為,個體的成就目標會對其認知(如效能感)及情緒(如焦慮)產生影響,進而影響其行為(Daumiller et al., 2019; Skaalvik & Skaalvik,2013)。這預示著效能感和焦慮在教師成就目標和工作投入間的潛在中介作用。
教師效能感是教師對自身是否有能力完成教學任務的主觀判斷(Cho & Shim, 2013; Skaalvik &Skaalvik, 2010; Tschannen-Moran & Hoy, 2001)。持掌握目標的教師致力于掌握知識、提升個人能力,持表現趨近目標的教師為獲得他人積極評價而進行專業能力提升,他們更可能成功完成教學任務,強化效能感(Janke et al., 2019; Nitsche et al.,2011);而持回避目標的個體傾向于從負面解讀任務,無法調動自身解決問題的積極性,進而削弱效能感(Elliot & McGregor, 1999; Janke et al., 2019;Nitsche et al., 2011)。此外,效能感具有動機作用,決定著個體采取行動、投入努力的程度以及在面對困難時的堅持性(Bandura, 1997),而這些正是工作投入所強調的內容。研究發現,擁有高效能感的教師具有較低的離職意向及較高的工作投入(Buri? & Macuka, 2018; Wang et al., 2015)。因此,教師效能感在成就目標與工作投入間起中介作用。
焦慮作為一種在教師群體中常見的消極情緒,對教師身心健康及專業發展具有消極影響(Chang, 2009; Frenzel et al., 2016; Wang et al.,2017)。根據成就目標理論,持有掌握目標的個體在努力過程中易產生適應性情緒,而持有表現目標的個體將成敗歸因為自身能力,面對失敗易產生高焦慮(Dweck, 1986)。但僅有少量研究探究了教師成就目標與焦慮情緒的關系,結果發現表現回避目標正向預測而表現趨近目標負向預測教師焦慮(Janke et al., 2019)。進一步地,情緒具有動機及調控作用(Izard et al., 2008)。作為一種消極情緒,焦慮可能會削弱教師工作投入水平。因此,焦慮在成就目標與工作投入的關系中可能具有中介作用。此外,教師效能感與焦慮也存在關聯。具有低效能感的教師傾向于認為自己沒有能力處理工作中的潛在威脅,因而體驗到較多的焦慮情緒(Frenzel et al., 2016; Pekrun, 2006)。因此,教師成就目標也可能會通過效能感到焦慮的路徑預測工作投入。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設。假設1:教師成就目標對工作投入具有預測作用,而效能感、焦慮、效能感-焦慮在其中起中介作用。假設2:成就目標在教師群體中呈現不同的組合模式(即剖面)。假設3:不同教師成就目標剖面在工作投入、效能感、焦慮上存在差異,且效能感、焦慮、效能感-焦慮在成就目標剖面與工作投入間起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被試
北京市1887名教師完成在線問卷填答。清理標準分數大于4(Cousineau & Chartier, 2010)的10個極端值后,對1877名教師的數據進行分析,平均年齡27.39±2.58歲,男性305名(16.2%),女性1572名(83.8%);小學教師1116名(59.5%),初中教師494名(26.3%),高中教師267名(14.2%)。
2.2 研究工具
2.2.1 教師成就目標
采用Papaioannou和Christodoulidis(2007)編制的教師成就目標問卷(Teachers’ Achievement Goals in Work Questionnaire)。包含3個維度,即掌握目標(如“我的目標是不斷地提高自己的教學能力”)、表現趨近目標(如“我的目標是比其他教師表現得更好”)、表現回避目標(如“我習慣于回避那些我做得不好的工作或事情”)。每個維度含有4個條目。采用李克特5點計分,“1”表示“非常不符合”,“5”表示“非常符合”,得分越高表示該目標的傾向性越強。在本研究中,總問卷及各維度的Cronbach’s ɑ系數分別為 0.67,0.86,0.82,0.81。
2.2.2 教師效能感
采用Tschannen-Moran和Hoy (2001)的教師效能感量表(Teachers’ Sense of Efficacy Scale)的6條目簡化版(Durksen et al., 2017)(如“在教學中,我能將實際教學與課程學習目標聯系起來”)。采用李克特11點計分,“1”表示“一點也不自信”,“6”表示“中等程度的自信”,“11”表示“極其自信”,得分越高表示效能感越強。本研究中,該問卷的Cronbach’s ɑ系數為0.90。
2.2.3 教師焦慮情緒
采用Frenzel等人(2016)編制的教師成就情緒問卷(Achievement Emotions Questionnaire for Teachers)中的焦慮維度,共4個條目(如“教學時,我通常會感到緊張和不安”)。采用李克特4點計分,“1”表示“完全不同意”,“4”表示“完全同意”,得分越高表示教師焦慮情緒越多。本研究中,該問卷的Cronbach’s ɑ系數為0.86。
2.2.4 工作投入
采用Klassen等人(2012)將工作投入(Utrecht Work Engagement Scale)(Schaufeli et al.,2006)用于教師群體的問卷。包含活力(如“工作時,我覺得干勁十足”)、奉獻(如“我對教師工作充滿熱情”)、專注(如“我經常沉浸在工作中”)三個維度,每個維度各3個條目。采用李克特7點計分,“1”表示“從不”,“4”表示“有時”,“7”表示“總是”,得分越高表示工作投入越多。在本研究中,總問卷及各維度的Cronbach’s ɑ系數分別為 0.95,0.92,0.93,0.84。
2.3 數據處理
在Mplus 8.3中驗證主要假設。首先,采用變量中心法檢驗假設1。其次,采用個體中心法檢驗假設2、假設3。主要涉及三個步驟:(1)采用潛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 LPA),識別潛在剖面;(2)采用方差分析確認潛在剖面類別差異;(3)構建潛在剖面的虛擬變量,檢驗教師效能感、焦慮的中介作用。為確定剖面數量,對以下指標進行評估:信息評價指標,即AIC、BIC和aBIC;似然比檢驗指標BLRT和LMR;Entropy。
在上述模型中,對人口學變量(年齡、性別、本單位工作年限、任教學段)進行控制(Kunst, van Woerkom, & Poell, 2018)。采用SPSS 22.0進行數據缺失分析(Little’s MCAR檢驗),結果顯示完全隨機缺失,條目缺失比例均小于1%。采用最大期望算法(expectation-maximization algorithm, EM)插補數據。采用Harman單因素因子分析法于Mplus軟件中檢驗共同方法偏差。設定公因子數為1,結果顯示模型擬合結果不佳,χ2/df=41.56,RMSEA=0.15,CFI=0.58,TLI=0.55,SRMR=0.12,表明本研究并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 結果
3.1 描述統計與相關
各變量均值、標準差和相關系數見表1。除表現趨近目標與焦慮情緒之間的相關不顯著外,三類成就目標、自我效能感、焦慮情緒和工作投入兩兩之間均存在顯著相關,且其方向性與預期相符。

表1 各變量的均值、標準差和相關系數
3.2 基于變量中心視角
假設模型擬合良好,χ2/df=5.39,RMSEA=0.05,CFI=0.99,TLI=0.97,SRMR=0.02。三種成就目標均能直接預測工作投入。同時,除表現趨近目標無法通過教師效能感(95%CI=[-0.001, 0.018],p>0.05)、教師效能感-焦慮(95%CI=[0.000,0.003],p>0.05)預測工作投入外,其他中介路徑均顯著,見圖1。

圖1 基于變量中心視角的模型路徑圖
3.3 基于個體中心視角
3.3.1 教師成就目標的潛在剖面
LPA結果見表2。隨分類數目增加,信息指數AIC、BIC及aBIC不斷減小,模型擬合不斷變好,且LMR和BLRT值始終顯著。保留2~6個類別時,Entropy值均超過0.80,表明這些分類模型的精確度均可接受。5類別模型除包含2、3、4類模型中的所有類別外,還包含在三個目標上得分均較高的一類,有助于更為細致地考察成就目標剖面差異。而6類別模型較為繁復,且分類精確度(Entropy)不如5類別模型。綜上,5類別模型最佳。

表2 LPA結果
基于每個類別在不同成就目標上的得分,將它們分別命名為掌握型、低掌握低趨近型、低掌握中等趨近型、高混合型、平均型(見圖2)。第一類是掌握型(C1; 46.3%),這一組的教師在掌握目標上得分最高,在表現趨近目標上得分位于平均水平,在表現回避目標上得分最低。第二類是低掌握低趨近型(C2; 6.07%),占比較少。該組教師掌握目標和表現趨近目標得分均最低,表現回避目標得分較高。第三類是低掌握中等趨近型(C3; 31.7%),這一組包括在掌握目標得分較低、在表現趨近目標得分位于平均水平、在表現回避目標得分較高的教師群體。第四類是高混合型(C4; 4.10%),這一組教師掌握目標得分較高,在表現趨近目標、表現回避目標上的得分最高。第五類是平均型(C5; 11.8%),該組教師在三個目標定向上的得分均位于平均水平,沒有明顯的傾向性。

圖2 教師成就目標剖面
3.3.2 教師效能感、焦慮和工作投入的組別差異
方差分析結果表明,上述五個剖面在教師效能感、焦慮及工作投入上存在顯著差異(見表3)。

表3 教師成就目標剖面的差異檢驗
3.3.3 教師效能感和焦慮的中介作用
低掌握低趨近型(C2)的掌握目標得分最低且適應性最差,故將其設置為對照組。結果顯示,除C3與C2、C4與C2在焦慮上不存在顯著差異外,其余所有路徑均顯著,見圖3。與C2組的教師相比,其他四組教師體驗到更多的教師效能感,C1、C5兩組教師體驗到較少的焦慮情緒,進而展現出更高水平的工作投入;同時,其他4組因具備較多的教師效能感而體驗到較少的焦慮情緒,進而與更高水平的工作投入相關聯。

圖3 個體中心的中介模型
4 討論
4.1 教師成就目標剖面
本研究識別了五種教師成就目標剖面。掌握型的教師以提升教學能力為目標,不會刻意避免展現能力短板;低掌握低趨近型與低掌握中等趨近型的教師,不以掌握教學知識、展現教學能力為目標,而更多關注避免表露出能力不足;高混合型的教師關注提高與展現教學能力,同時也回避能力不足的表露;平均型的教師沒有明顯的目標傾向。與以往針對西方教師群體的研究(Kunst,van Woerkom, & Poell, 2018; Kunst, van Woerkom, van Kollenburg, & Poell, 2018)一致的是,本研究也發現了平均型,且低掌握低趨近型、低掌握中等趨近型與前人研究的高回避型形態相似。另外,本研究中的高混合型曾在針對學生的研究中出現(Schwinger et al., 2016)。
教師成就目標剖面在分布上存在一定國內外差異。我國教師以掌握型為主,約占比50%,但針對國外教師的研究發現該類型占比較低(約10%),而平均型占比最多,達到50%(Kunst, van Woerkom, & Poell, 2018; Kunst, van Woerkom, van Kollenburg, & Poell, 2018)。結果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1)本研究關注的是中小學教師,而國外研究的樣本來自職業教育院校的教師,這些教師可能缺乏明確的目標(Kunst, van Woerkom, & Poell,2018; Kunst, van Woerkom, van Kollenburg, & Poell,2018);(2)與國外教師相比,國內教師可能面臨著更多的挑戰與壓力,如教師職稱評定需求、學生升學壓力、社會的高期待等,故努力提升知識水平和專業能力是他們的重要目標。
4.2 教師成就目標與教師效能感、焦慮和工作投入的關系
與以往研究一致的是,本研究發現掌握目標、表現趨近目標正向預測而表現回避目標負向預測工作投入(Daumiller & Dresel, 2020; Parker et al., 2012; Skaalvik & Skaalvik, 2013);掌握目標正向預測而表現回避目標負向預測教師效能感(Janke et al., 2019; Nitsche et al., 2011);表現回避目標正向預測焦慮情緒(Janke et al., 2019)。
與前人研究(Janke et al., 2019; Nitsche et al.,2011)不一致的是,本研究發現表現趨近目標無法顯著預測教師效能感。事實上,針對學生成就目標的研究發現,表現趨近目標對積極結果的預測作用并不穩定(Elliot & Moller, 2003)。同時,以往針對教師的研究曾發現表現趨近目標對焦慮的負向預測作用(Janke et al., 2019),而本研究發現其正向預測焦慮,但程度較弱。持表現趨近目標的教師可能會更多地與他人進行比較,害怕失敗,從而易產生焦慮。另外,本研究發現掌握目標負向預測焦慮,這可能是因為持掌握目標的教師使用的是自我參照的標準(Dweck, 1986)。
與上述變量中心結果一致的是,個體中心結果發現,掌握型的教師適應性最佳,即教師工作投入、效能感得分最高,焦慮得分最低;而低掌握低趨近型最差。故基于個體中心視角所得結果印證了變量中心結果,同時為了解不同成就目標類型教師的工作特征提供了重要信息。
4.3 教師效能感、焦慮的中介及教師效能感-焦慮的鏈式中介
變量中心和個體中心的結果均顯示成就目標可以通過教師效能感、焦慮間接預測工作投入。成就目標會影響個體面對任務時的心態、成敗后的體驗、參照比較的對象等,從而對其效能感和焦慮產生影響(Janke et al., 2019; Nitsche et al.,2011)。具有高效能感的個體,相信自己能完成任務,具有挑戰精神,能投入更多努力(Bandura,1997),從而表現出更高的工作投入(Schwarzer &Hallum, 2008)。同時,情緒具有調控作用(Izard et al., 2008),體驗到較少焦慮情緒的教師更有可能保持良好的心理狀態,將更多精力和熱情投入到教學工作中去。
本研究還發現了教師效能感與焦慮的鏈式中介作用。這一結果支持了Frenzel等人(2016)的教師情緒理論:教師對自身能否完成教學目標的感知(即教師效能感)會影響其教學情緒,從而進一步影響其教學行為。此外,根據社會認知理論(Bandura, 1997),效能感較低的個體在面對挑戰時會擔心應對能力不足,因而體驗到強烈的焦慮情緒。進一步地,焦慮對個體的認知能力具有消極影響(Bishop, 2007),阻礙個體的活動及功能的發揮,使工作投入減少。
4.4 研究意義與局限
本研究采用個體中心的方法,識別了五種教師成就目標剖面類型,并比較了這些類型在一些重要的教師結果變量上的差異。這有助于了解我國教師群體成就目標的類型與分布,加深對教師成就目標本質的理解,并為后續針對不同教師群體的干預與培訓提供參考。另外,本研究同時結合變量中心和個體中心的視角,揭示并探討了教師成就目標與效能感、焦慮和工作投入的復雜關系。這不僅進一步豐富和拓展了成就目標理論、教師情緒理論的實證研究,也對如何提高教師工作投入具有啟示意義。研究提示,學校領導應有意識地引導教師形成適應性的成就目標,注重緩解教師的教學焦慮情緒,適時、適當給予教師激勵與表揚等。
本研究依舊存在一些不足。首先,采用自我報告的測量方式,可能存在社會贊許性,使得教師報告的掌握目標得分較高,進而對潛在剖面的分類與分布產生影響。其次,教師樣本全部來自北京,雖樣本量較大,但結論仍需在其他樣本中加以印證。最后,本研究主要探討了教師成就目標的一些較為重要的結果變量,未來研究可以利用個體中心方法考察成就目標的前因變量和其他結果變量。
5 結論
(1)掌握目標、表現趨近目標、表現回避目標可直接預測工作投入,也可經由教師效能感、焦慮、教師效能感-焦慮間接預測工作投入;(2)存在五種成就目標剖面,分別為掌握型、低掌握低趨近型、低掌握中等趨近型、高混合型、平均型;(3)不同成就目標剖面的教師群體在教師效能感、焦慮、工作投入上的表現不同,其中掌握型教師的適應性最佳;剖面不僅可直接預測工作投入,也可經由教師效能感、焦慮、教師效能感-焦慮間接預測工作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