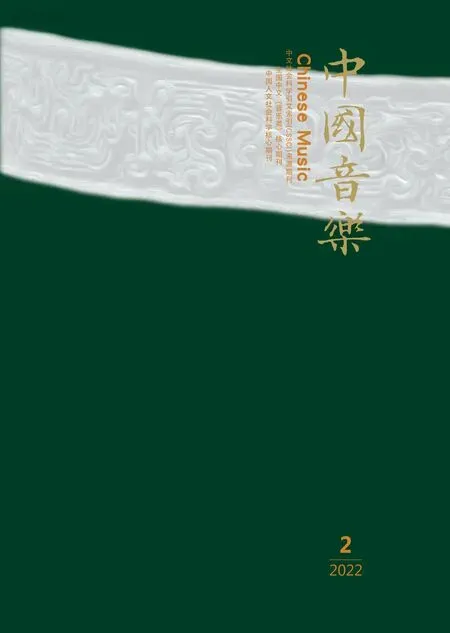漢代俗樂及其娛樂功能
○ 趙 倩
兩漢禮樂制度的重建及不斷完善、鞏固的過程,體現了漢帝王對國家統治權“正統性”的追求與實踐,也是統治者身份和地位的表征。其“雅樂”主要是為統治階級各種祭祀、禮儀場合服務,而當我們放眼處于漢代政治“大一統”、經濟力量逐漸強盛的環境中的音樂時,可以發現在禮樂“光輝”的映襯下,還有一幅由宮廷、官吏和庶民等階層共同描摹的、多姿多彩的,融合詩歌、音樂(含歌唱與器樂)、舞蹈、百戲等諸“樂”類型的用以娛人的俗樂審美圖景。音樂史家黃翔鵬認為秦漢魏晉時期中國音樂以“歌舞伎樂”為主要特征,而這一時期與春秋戰國的歌舞樂三位一體的樂舞時代不同的是:“歌、舞、器既獨立發展又相互結合而為清商樂演奏,這就進入了一個新的藝術時代。”①黃翔鵬:《中國古代音樂史的分期研究及有關新材料、新問題》,《樂問》,北京: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2000年,第167頁。在新的藝術時代中,從先秦時期便存在的“雅俗之爭”也產生了新的變化:俗樂興盛,雅樂式微。俗樂的表演充斥在帝王、貴族、官員、百姓等不同階層的宴飲、娛樂及風俗多種場合中。這些場合的俗樂表演,讓我們看到了俗樂的藝術特征—世俗性和娛樂性,看到了其娛樂功能的形成,與雅樂的式微、“楚聲”的功能及其影響以及人的主體意識覺醒等因素有關。
一、漢代俗樂表演的多元呈現
在漢代“大一統”的局面下,統治階級的用樂有不同的形態。如賈誼說:“故君樂雅樂,則友、大臣可以侍;君樂燕樂,則左右、侍御者可以侍;君開北房,從熏服之樂,則廝役從。清晨聽治,罷朝而論議,從容澤燕。夕時開北房,從熏服之樂。是以聽治、論議、從容澤燕,矜莊皆殊序,然后帝王之業可得而行也。”②王洲明、徐超校注:《賈誼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第289-294頁。他提到了帝王所用的幾種音樂類型:“雅樂”“燕樂”“熏服(樂伎)之樂”等,可見,宮廷的音樂,除了在郊廟祭祀、朝會、冊封等國家禮儀場合所用、以塑造統治者的王權和國家權威的雅樂外,還存在于各種宴飲場合、宮廷“私人性”場合的歌、舞及器樂等俗樂形態。
而從審美主體上看,俗樂的審美主體除了帝王到各級官員外,還有民間的百姓,他們有的便是俗樂的主要參與者。在漢代各種史料中,記載著他們的音樂素養和俗樂施用的場合及不同類別。
(一)史書中的俗樂書寫
“以史為鑒,可知興衰”,是中國歷代史書的核心價值所在,另外,“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需鴻筆之臣。褒頌紀載,鴻德乃彰,萬事乃聞。”③〔東漢〕王充:《論衡·須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07頁。那么,史書中對“樂”的“書寫”,目的也在于此,或記載歌頌王者鴻德之樂,以“樂其德也”,或記載經驗教訓,以表明立場等。在這些記載中,我們也看到了那些被褒貶不一的俗樂在漢代的不同面孔。
檢索漢代俗樂在宮廷及官員的日常生活及宴飲場合中的俗樂表演,首先引起注意的便是對帝王及官員們音樂才能的記載。如漢高祖劉邦,他定天下后,返沛,自作《大風歌》,以教歌兒習之。如《史記》所載:“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云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④〔西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第289;2 047頁。高祖常與戚夫人作歌舞。高祖欲立戚夫人之子為太子未成,安慰戚夫人道:“為我楚舞,吾為之楚歌”,遂唱起“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⑤〔西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第289;2 047頁。又《西京雜記》載:“高帝、戚夫人善鼓瑟擊筑。帝常擁夫人倚瑟而弦歌,畢,每涕下流漣。夫人善為翹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侍婢數百皆習之。后宮齊首高唱,聲入云霄。”⑥〔晉〕葛洪:《西京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2頁。由此可以看出二人音樂生活之豐富、音樂技能之嫻熟。
還有漢元帝,也是善音樂、通音律,如《漢書》所載:“建昭之間,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⑦〔東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3 376;3 349;2 380;324-325;4 023頁。除此,后漢的桓帝也“好音樂,善琴笙”⑧〔南朝宋〕范曄:《后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320;3 272;1 972頁。,漢靈帝則“善胡箜篌、胡笛、胡舞”⑨〔南朝宋〕范曄:《后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320;3 272;1 972頁。。此外,善舞的除了戚夫人,還有成帝皇后趙飛燕,少帝之妻唐姬等。他們的樂舞素養和活動,表明了宮廷對樂舞活動的娛樂功能的需要。
官員中,也有知音識樂的,如《漢書·張禹傳》載,丞相張禹“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后堂理絲竹管弦”,“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后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管弦鏗鏘極樂,昏夜乃罷”⑩〔東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3 376;3 349;2 380;324-325;4 023頁。。還有東漢的馬融,也是“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南朝宋〕范曄:《后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320;3 272;1 972頁。。
具備能歌善舞或能吹善彈等舞蹈或音樂技能,無疑說明了漢代社會樂舞文化的繁榮,更為他們參與到俗樂的審美和鑒賞,提供了便利,同時也為俗樂在漢代的盛行貢獻了主導或是引領的“力量”。史書中不乏對其樂舞場面的或客觀或否定的描述。
如《漢書·田蚡傳》中載,田蚡“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市買郡縣器物相屬于道。堂前羅鐘鼓,立曲旃;后房婦女以百數。諸奏珍物狗馬玩好,不可勝數”?〔東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3 376;3 349;2 380;324-325;4 023頁。。《漢書·成帝紀》對官員備女樂的情況也有記載:“方今世俗奢僭罔極。靡有厭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未聞修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或乃奢侈逸豫,務廣第宅,治園池,多畜奴婢,被服綺縠,設鐘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埋過制。吏民慕效,寢以成俗。”?說明官員在日常不同場合對鐘鼓之樂和女樂的使用已經超出了儒家禮制的規定,幾乎成了社會的風尚。《漢書·元后傳》載,當權外戚王氏兄弟間“僮奴以千百數,羅鐘磬,舞鄭女,作倡優,狗馬馳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彌望”?〔東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3 376;3 349;2 380;324-325;4 023頁。。其俗樂享樂的規模,同樣不容小覷。
而哀帝之所以“罷樂府”,其中原因即是以為漢室的宦官和外戚等達官顯貴,驕奢淫逸過度,俗樂的享樂之風太盛的緣故。正如《漢書·禮樂志》載:
是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強、景武之屬富顯于世,貴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哀帝自為定陶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即位,下詔曰:“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鄭、衛之聲興。夫奢泰則下不孫而國貧,文巧則趨末背本者眾,鄭、衛之聲興則淫辟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樸家給,猶濁其源而求其清流,豈不難哉!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同注⑦,第1 073;3 245頁。
從上述文字說明統治階級奢靡、混亂的享樂之風已經影響到了漢室的禮樂建設,但是漢哀帝罷“樂府”的行為背后,恰恰說明了俗樂的影響力已經滲透到了統治階級的各個環節。
到了東漢明帝后,被哀帝所禁的現象,仍然在一些宦者家中存在,如大量擁有“女樂”,大興宴饗娛樂之舉等。書載:“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同注⑧,第2 510;857;2 003;2 004頁。《后漢書·馬援列傳》言馬援的幾個兒子,也“多聚聲樂,曲度比諸郊廟”?同注⑧,第2 510;857;2 003;2 004頁。,這些記載描繪出后漢時代官員們聲色犬馬的享樂狀態。
此外,史書中還記載了漢代貴族階級在酒宴中的舞蹈類型,如長袖舞、巾舞、建鼓舞、盤鼓舞、鼗鼓舞,等等。此外,還有一些特殊舞蹈表演情形,如《漢書·蓋寬饒傳》:“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斗,坐皆大笑。”?同注⑦,第1 073;3 245頁。其中引人哄堂大笑的“沐猴與狗斗”,便是一種供人娛樂的民間舞蹈,而這種形態被稱為“即興起舞”或“自起舞”。除此外,還有一種舞蹈形式是“以舞相屬”?劉興珍、李永林主編:《中華藝術通史·秦漢卷》,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12-113頁。,如《后漢書·蔡邕傳》載:“酒酣,智起舞屬邕,邕不為報”?同注⑧,第2 510;857;2 003;2 004頁。,描述的正是漢時酒宴中相約起舞的“以舞相屬”習俗,即一人下場起舞,再邀另一個人跳舞。由此可見,“歌舞技藝在當時社會中,并非‘倡’和職業的‘歌舞者’才能掌握這種技能;歌舞在當時的社會生活中,是一種極其普遍的娛樂活動”?劉青弋主編,彭松著:《中國舞蹈史(秦漢卷)》,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10年,第89頁。。
而對于民間生活中俗樂的記載也不在少數,如《鹽鐵論》載:“然民鮆窳偷生,好衣甘食,雖白屋草廬,歌謳鼓琴,日給月單,朝歌暮戚……然民淫好末,侈靡而不務本,田疇不修,男女矜飾,家無斗筲,鳴琴在室。”?王利器校注:《鹽鐵論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41-42頁。《后漢書·蔡邕傳》中也提及蔡邕在陳留,鄰人邀其赴宴,其中便有“客有彈琴于屏”?同注⑧,第2 510;857;2 003;2 004頁。的記載。從中亦可看出,西漢昭帝時期的民間音樂生活中,琴樂已成為是富裕家庭娛樂的方式之一。
總之,俗樂的表演均與不同階層的娛樂需求密切相關。
(二)文學作品中的俗樂書寫
毋庸置疑,兩漢時期的文學,已經表明了文學自覺時代的來臨。雖然中國早期歷史中的史官與文人在身份上往往存在同一性,史官本身就是文人,他們筆下的歷史與文學是緊密相連的,如《史記》就被魯迅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魯迅:《漢文學史綱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3頁。。不過,文學作品與史書還是存在一定區別,即文學作品偏于情感的表達,而使其對政權穩定、社會進步的功用不及史書的價值。但是,在漢代以寫實主義精神書寫的文學作品如漢賦如班固的《東都賦》《西都賦》、司馬相如的《上林賦》、揚雄的《蜀都賦》、張衡的《觀舞賦》《南都賦》《思玄賦》、傅毅的《舞賦》等,其中對于音樂、舞蹈、百戲等的書寫,雖然有夸張的手法,但是一定程度上也是對歷史的復原,可以作為史書的補充,用來關照漢代俗樂的形態及其功能的研究。
《上林賦》描寫了一種帝王在上林苑中狩獵之后的歌舞享樂之氣象,其有載:“……荊吳鄭衛之聲,韶濩武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鄢郢繽紛,激楚結風。俳優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于前,靡曼美色于后……”?朱東潤:《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上編》第一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28頁。
傅毅在其《舞賦》中同樣對帝王的樂、舞享樂有著細致的描寫,但主要的描述對象是漢代以盤鼓為舞具的長袖舞。其中的“羅衣從風,長袖交橫。駱驛飛散,颯擖合并”“委蛇姌裊,云轉飄曶。體如游龍,袖如素霓”?龔克昌等:《全漢賦評注》,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2003年,第134、135頁。等描寫,展現了漢代舞蹈的動態之美。
張衡《南都賦》中也有:“于是齊僮唱兮列趙女。坐南歌兮起鄭舞。白鶴飛兮繭曳緒。修袖繚繞而滿庭,羅襪躡蹀而容與。翩綿綿其若絕,眩將墜而復舉。翹遙遷延,蹩躠蹁躚。結九秋之增傷,怨西荊之折盤。彈箏吹笙,更為新聲。”?費振剛、胡雙寶、宗明華編:《全漢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460頁。其展現了漢代南陽俗樂表演中樂舞相融的藝術形態。
此外,東晉王嘉編寫的古代中國神話志怪小說集《拾遺記》載:“初平三年,游于西園,起裸游館千間,采綠苔而被階,引渠水以繞砌,周流澄澈。乘船以游漾,使宮人乘之,選玉色輕體者,以執篙楫,搖漾于渠中。其水清澄,以盛暑之時,使舟覆沒,視宮人玉色。又奏《招商》之歌,以來涼氣也。”?〔前秦〕王嘉:《拾遺記》,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44頁。描述了靈帝驕奢聲色的歌舞娛樂情景。不僅如此,在他的影響下,使得“京都貴戚皆競為之”?同注⑧,第3 272頁。,歌舞娛樂之風彌漫大漢京都上下。
《淮南子》中對俗樂有這樣的記載:“夫建鐘鼓,列管弦,席旃茵,傅旄象,耳聽朝歌北鄙靡靡之樂,齊靡曼之色,陳酒行觴,夜以繼日”?陳廣忠譯注:《淮南子》,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40-41頁。,“夫窮鄉之社,扣甕拊瓶,相和而歌,自以為樂也。”它描繪了“瓴缶之樂”、相和而歌的音樂形態和自娛自樂的審美趣味。漢武帝時大興郊祀,令民間或二十五家立一社,或百家共立一社,各自祭祀,而此時民間的祭祀“尚有鼓舞之樂”?同注④,第472頁。。可見,在民間的祭祀場合中,“瓴缶之樂”、相和歌與“鼓舞”均為俗樂的形態。
可以說,文人群體對樂舞的記載與論說,在修辭上營造了豐富的聯想,一定程度上構建了漢代俗樂藝術形態的面貌,也是對俗樂發展的一種推動,它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審美者—漢代文人的審美標準和意趣,是他們對樂舞作品美的評判。他們作為樂舞審美活動的重要參與者、審美活動的主體,其審美評判一定程度上也影響到表演者的審美風格的變化,以及技藝水平的提高。不僅如此,漢代文人階層對于樂舞的喜愛,擴展了女樂歌舞百戲的發展空間和演出范圍,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藝人隊伍的發展壯大,也提高了娛樂性歌舞在當時社會主流文化藝術形態中的地位,對推動歌舞藝術的發展,無論是歌舞技巧、技能的提高,歌舞表演形式的豐富,還是審美品位的提升,無疑都會產生重要作用”?何軍:《漢代文人的社會音樂生活與創作考略》,《音樂創作》,2016年,第6期,第88頁。。
(三)漢代俗樂的表演形態
需要指出的是,盡管不同文獻的書寫具有鮮明的政治目的,因此,對于每一次俗樂表演形態的記錄也并不是十分清晰,有的提到了聲樂、器樂,有的提到了女樂,均沒有關于樂器、樂器組合等信息的描述。但是,不同樂、舞的藝術呈現,大多數情況下并非單一門類藝術的表演,大部分情形下,漢代俗樂(樂舞)的表演都是多種具體藝術形態的多聲部“重奏”,只是在組合方式或演出程序上有所差異。在文字記述語焉不詳的情況下,借助當下漢代音樂圖像的資料和研究成果,可以為我們進一步認識漢代俗樂的具體表演形態,提供幫助。藝術史家朱青生認為,圖像時代的來臨,為我們研究歷史提供了又一條路徑,進而形成了歷史學—考古學—藝術史方法三法并舉的研究模式:“樂舞研究,都不大能單純地以文獻的考證或者實物的考古、圖像的考辨來單獨完成,應該三者結合起來推進。”?朱青生:《漢代圖像中的樂舞形象研究》,《北京舞蹈學院學報》,2020年,第1期,第30頁。
在山東、河南、四川等地大量出土的漢代畫像磚、石中,用圖形的形式,記錄和呈現了漢代官宦階層在宴飲場合中的繁盛的音樂文化景象。如《中國音樂史圖鑒》收錄了河南方城縣東關漢畫像石中有鼓舞的圖像?劉東升、袁荃猷編撰:《中國音樂史圖鑒》,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08年,第40;37頁。:上層是羽葆建鼓,下層圖像是3人跪坐,中間者似在吹排簫,另外兩人似在做游戲。
還有山東沂南東漢末年畫像石的樂舞百戲圖?劉東升、袁荃猷編撰:《中國音樂史圖鑒》,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08年,第40;37頁。(見圖1):下方一人跳七盤舞,右側三排樂手在伴奏,其中第一排為五位擊鼓樂手,第二排為吹排簫的樂手,最左邊一人同時還在敲擊鉦(鐸),第三排最左邊一人在彈箏或瑟,一人在吹塤(笛),一人在歌唱,最右一人在吹竽。上方還有一人敲擊羽葆建鼓,右側有一人敲鐘、一人敲編磬。該圖中的樂隊即為較大型的俗樂伴奏樂隊。

圖1 山東沂南漢畫像石 樂舞摹本
另外,在《中國音樂文物大系》各省卷、《中國畫像石全集》等已出版的大型圖書中,均可以找到各類俗樂表演的圖片,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俗樂在漢代的基本面貌。
從漢代圖像資料看,漢代俗樂樂隊的樂器組合,多種多樣、不盡相同。從樂器分類上看,有金石樂隊、絲竹樂隊和鼓吹樂隊,但是從歷史發展脈絡上看,金石樂隊在進入漢代后,出現了衰微,代之的是絲竹樂隊的興起與大量使用,為歌唱或舞蹈伴奏。絲竹樂隊更多地用在帝王、官員的私宴等場合,與祭祀場合所用的雅樂,具有鮮明的娛樂功能。
二、娛樂:俗樂的功能之一
人們創造各類音樂、舞蹈等音樂形態的行為,一定是為了達到特定的目的、實現特定的功能,如“大一統”的政治統治、悲喜從心的情感表達和感官體驗的審美娛樂等。翻閱古代文獻,談論“樂”的“娛樂”功能的文字比比皆是。如《呂氏春秋·侈樂》載:“凡古圣王之所為貴樂者,為其樂也。侈則侈矣,自有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失樂之情,其樂不樂。樂不樂者,其民必怨,其生必傷。”?張雙棣等譯注:《呂氏春秋譯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130頁。認為音樂的作用在于使人快樂,而音樂若不具有使人快樂的功能,則會有害于人民的生活和國家的治理。從上文的文獻梳理中,我們可以看出,不管是帝王、官員還是百姓,在日常生活、宴飲等場合中的俗樂表演和欣賞,體現出了對“娛樂”功能的需求,而帝王或官員們作為統治階級對于各種藝術技能的掌握,則同樣能夠證明這一點。因此,雖然表演形式、表演場合和表演類型不盡相同,但是俗樂所體現的重要娛樂功能,則是一致的。
賴祥亮認為:“娛樂,是為了獲得愉快,而不是為了獲得利益;藝術以及文學,它們的一個方面,也是給主體以快感、以愉悅。”?賴祥亮:《論漢代文學的娛樂精神—以漢賦為例》,《重慶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2008年,第12期,第135頁。藝術活動和文學的創作行為,應該說,都是以獲得愉快的娛樂目的為旨歸的,因此,不管是史書還是文學作品,盡管文本表述不一樣,娛樂,都是其重要的功能表達。而楊樹達在《漢代婚喪禮俗考》中也提到了喪葬儀式用樂的情況:“喪家于來吊者,饗之以酒肉,娛之以音樂。”?楊樹達:《漢代婚喪禮俗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8頁。也說明了這樣一個情況:喪葬儀式用樂的功能之一,便是為前來吊唁的親友提供娛樂。當下廣泛存在于民間喪葬儀式中的鼓吹樂、戲曲或曲藝表演的功能,同樣如此,娛樂—以樂待客,答謝客人對儀式的參與,正是儀式中需要有“樂”的重要目的。
漢代辭賦對俗樂形態極盡其能的描繪,不僅僅是作為文體的辭賦在修辭上的娛樂性的表征,更是樂舞本體形式之美高度發展的結果,它所產生的各種審美意象,能讓觀者產生強烈的、異于雅樂的審美感受和情感體驗,這正是俗樂娛樂性的表現。如《上林賦》中呈現的樂舞類型多樣,雖然并不都是俗樂,且體現了夸張的修辭手法,但司馬相如的表述則認可了包含俗樂舞在內的音樂功能,即“娛耳目樂心意”,娛樂是重要的價值取向。同時,文人們筆下那高超的演奏技藝、舞蹈技藝的書寫,也正表明了社會對于俗樂的接納程度,表明了人們對于“娛樂”的審美需要。
再以漢代樂府詩歌而言,其功能并不只是為了“觀風俗”。潘嘯龍認為,其功能主要還是為了滿足宮廷及貴族階層的娛樂之需?潘嘯龍:《漢樂府的娛樂職能及其對藝術表現的影響》,《中國社會科學》,1990年,第6期,第25-29頁。。樂府詩歌的書寫行為本身,也是漢代世俗化的娛樂精神的寫照,如劉玲研究的《雞鳴》《相逢行》《長安有狹斜行》三首歌詩:“并不是下層勞動人民對貧富不均的控訴之辭,而是歌舞藝人以取悅和娛樂富豪貴族為目的而創作的奉承之歌,是世俗化、娛樂化的藝術消費品,是盛世風氣中的歌頌文學。”?劉玲:《〈雞鳴〉〈相逢行〉〈長安有狹斜行〉與漢樂府的世俗娛樂精神》,《中國詩歌研究》,2017年,第1期,第235頁。這一方面體現了漢代俗樂在社會上的繁盛程度,另一方面也證實了俗樂的娛樂精神內涵。
此外,蕭亢達認為:“漢代俗樂主要是宴會之樂,是皇室貴族吏民宴飲時在北房、后堂演奏的樂舞,旨在娛樂,抒發感情。”?蕭亢達:《漢代樂舞百戲藝術研究》(修訂版),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19頁。他首先肯定了漢代俗樂與郊廟、上陵等等場合雅樂的區別,其次指出了俗樂的功能,即情感表達及藝術欣賞體驗。
那么,通過上文的梳理,我們看到了漢代俗樂在不同語境中的生存狀況,看到了俗樂形態的豐富性和審美行為的多元性:從帝王到百姓,均與俗樂發生著方方面面的聯系。他們有的是知音識樂的“專家”:或善歌、或擅樂器或擅舞蹈等;有的親自參與到樂舞創作和表演中;還有巨大的樂人群體以供審美之需。而從俗樂適用場合來看,主要是發生在宴飲(含其他民俗場合中的儀式用樂),且都體現出了明顯的娛樂功能。
三、娛樂功能的形成背景
漢代俗樂娛樂功能的形成及表現,有外部原因,也有自身的原因,可以肯定的是,它與漢代俗樂的興盛過程是一致的,大致受到以下三個層面因素的影響:一是雅樂的式微;二是“楚聲”的功能及其影響;三是人的主體意識的覺醒。
(一)雅樂的式微
俗樂在漢代的興起是“延續了春秋戰國時期快速發展的趨勢”?朱志榮主編,王懷義著:《中國審美意識通史·秦漢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57;250;250頁。的結果,與雅樂地位的式微密切相關,也是漢代人對“雅與俗”這一問題的思考與實踐的結果。
其實,自春秋以降,雅樂的地位已經隨著“禮崩樂壞”而受到沖擊,以鄭衛之音為代表的“新樂”已經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影響。到了漢室“大一統”之時,雅樂就更加難以順利為禮樂制度的重建貢獻力量,正如《漢書·禮樂志》所載:“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大樂官,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同注⑦,第1 043頁。可見,連傳承雅樂的樂官都不能準確知曉雅樂舞的意義,就更不要說其他官員或普通百姓了,因此“這些因素的存在為鄭、衛等俗樂的興盛提供了空間:以奢華、靡麗、靈動、變化為特征的地方歌舞在漢代迎來了它的盛世”?朱志榮主編,王懷義著:《中國審美意識通史·秦漢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57;250;250頁。。
同時,漢代的知識分子在觀念上也對雅樂和俗樂具有開放、包容和變通價值觀,如劉安在《淮南子·汜論訓》就說道:“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末世之事,善則著之。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故圣人制禮樂,而不制于禮樂。”?同注?,第722頁。王懷義認為,劉安的言論在探討雅樂的創制機制的同時,實則“為漢代俗樂的盛行提供了思想基礎”?朱志榮主編,王懷義著:《中國審美意識通史·秦漢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57;250;250頁。。
此外,統治階級的喜好也影響著社會的音樂審美趣味。“自漢之興,而平民為天子,社會階級之觀念全變”?錢穆:《秦漢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33頁。,而劉姓皇室正是起于平民階層,其熟悉的音樂類型不是雅樂而是俗樂,這也影響了雅樂的地位,使得俗樂成為宮廷和民間的主流,即便是在原本的雅樂場合中,也不乏俗樂諸形態的身影。不得不說,在漢代雅樂與俗樂的轉換過程中,樂府是一個關鍵機構,宮廷中俗樂的大量引入并得以施用,正是由樂府來完成,使得“崇俗”之風盛行于漢代宮廷。而這也對俗樂娛樂功能的塑造產生了積極的推動意義。
(二)“楚聲”的功能及其影響
音樂如同方言一樣,對于特定文化區域中的人具有認同的功能,引起人的自我文化歸屬感和身份認同感。
楚聲,是劉姓的家鄉音樂,是身份認同的表征。因此,從漢高祖教沛中歌兒百余人習其《大風歌》,到“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再到惠帝時,在宗廟祭祀中,又以沛宮為原廟,“皆令歌兒習吹以相和”,均為“楚聲”作為身份認同的符號在國家禮樂層面的記載。而在宮廷俗樂中“楚聲”的存在,則從娛樂的層面體現出漢代帝王對于楚文化的認同功能及其重要地位。
隨著漢室統治力量的加強,“楚聲”的功能又超越了作為身份認同符號的功能,轉而成為武帝成就“文化大一統”的催化劑。形成了以“楚聲”為中心的“鄭衛新聲”繁盛的局面,從劉邦開始到武帝“重立樂府”,“鄭衛之音”被逐漸用于郊祀、朝會等國家禮儀場合,使得出現了“今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調均,又不協于鐘律,而內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于朝廷”?同注⑦,第1 070-1 071頁。的境況,應該說這始自于漢武帝的“樂府”政策。雖然,俗樂一直受到儒家正統觀的詬病和批判,甚至也曾經遭到皇帝的罷減,但是,它依然在漢代國家禮樂體系中得到了發展壯大。
而以“楚聲”為代表的俗樂的興盛,也說明了即便是在國家禮樂體系中,樂舞原有的“宣德”“娛神”等核心功能,也逐漸讓位“娛人”的功能。而在民間樂舞的使用和欣賞,也在民俗性功能上凸顯了藝術性的審美功能。王懷義以《南陽李相公莊樂舞畫像石》中的器樂演奏和舞蹈表演為對象,解讀了樂舞與普通民眾生活的關系,認為:“在日常生活中,沒有樂舞是不可想象的,參與游戲和欣賞樂舞讓生活變得充實而圓滿;反過來說,對樂舞的欣賞也讓人們的日常生活獲得了生存意義:樂舞由此轉變為純粹的審美對象。”?同注?,第243;256頁。他所強調的正是俗樂的娛樂功能。
俗樂之所以能夠吸引人,從音樂風格上看,主要是由于重教化的雅樂旋律單一,節奏緩慢,因而顯得沉悶、乏味,缺少人的情感的參與,故難以喚起各階層的審美共鳴。而重娛樂的俗樂則被以管弦,旋律曲折動聽,具有“悲美”“靡麗”等特征,很大程度上釋放了人性,符合漢代人“濃烈深厚的生命情感調質”?同注?,第243;256頁。,這無疑進一步強化了俗樂的娛樂特性。
(三)人的主體意識的覺醒
人是一切藝術活動的核心,應該說,漢代俗樂勃興與漢代審美意識的形成具有同樣的背景,即政治文化的寬松、社會的安定和人民生活的殷實等因素而引發的人的自我意識的覺醒與凸顯。人們關注現實生活和自我情感的表達,于是以娛樂為核心的審美需求逐步顯現,享樂之風盛行。尤其是受到劉姓皇室身份轉變的影響,平民階層的社會地位得到了提升,審美的需求變得迫切,并且也得到了不斷實現和滿足。《鹽鐵論·散不足》中對人們娛樂用樂形態的記載,則體現了漢代審美意識的轉變:“古者,土鼓塊枹,擊木拊石,以盡其歡。及其后,卿大夫有管磬,士有琴瑟。往者,民間酒會,各以黨俗,彈箏鼓缶而已。無要妙之音,變羽之轉。今富者鐘鼓五樂,歌兒數曹。中者鳴竽調瑟,鄭舞趙謳。”[51]同注?,第353頁。由此可以看出,上至宮廷和官員、下至平民,娛樂的形式出現了從簡單到復雜、從簡樸到奢華的變化,這一變化的背后原因,與社會的安定和人民生活的殷實關系密切。
文獻中,不論是對帝王及官員用樂的記載、還是對民間用樂的記載,都可以說明漢代社會從宮廷禮樂到民間日常,俗樂已經成為主流。從功能上看,俗樂是最好的情感表達工具,王懷義認為“在接續春秋戰國俗樂發展的基礎上,以‘楚聲’‘鄭聲’‘新聲’等為代表的民間俗樂成為漢代音樂的主體,它們承載了兩漢時期各個社會階層的情感需求,是時代的心聲”[52]同注?,第298頁。。以舞蹈為例,不管是漢高祖教唱《大風歌》時,至動情處“乃起舞,感慨傷懷,泣數行下”的“即興之舞”,或是“以舞相屬”的表演形式,“生動、真摯的漢代俗樂舞,悲歡離合,可歌可泣,常常即興表演,直抒胸臆”[53]同注?,第114頁。,這都是舞者情感的直接表達,同時也能夠喚起觀者的情感共鳴和融入。
再如,馬融在《長笛賦》中“繁手累發,密櫛疊重”的描寫,所體現出的也是對俗樂興起背后人的因素的關注。從樂器演奏上看,說明了樂曲的音符較密、指法豐富,旋律起伏多變,說明了樂曲創作中具有細膩雕琢的成分,而細膩的音樂創作,需要創作者投入情感,這是音樂動人、滿足聽覺審美需要的潛在的藝術特質。而早在《左傳·昭公元年》中也有“繁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的記載,則是另外的思想表達,它代表著儒家正統的音樂美學思想,認為復雜多變的音樂會蕩心塞耳,讓人喪失平和的本性,因此,君子是不聽的。但是,這恰恰也寫出了先秦俗樂的特點。這一前一后的音樂描述和話語主旨轉變,所蘊含的,除了表明俗樂的生生不息之外,不正是在人的主體意識覺醒以及在其影響下審美意識的娛樂轉向嗎?
漢代樂府詩的生產,同樣與漢代人的娛樂需求有著密切關系,劉玲對此有較深入的分析:“在漢代社會,這些歌詩藝術作品的消費者,就是以宮廷貴族、達官顯宦、富商巨賈為主的上層名流社會階層。他們生活富庶,有殷實的經濟基礎,在享受著豐厚奢侈的物質生活的同時,精神上也產生了休閑娛樂的訴求。這種訴求使他們產生了對歌詩藝術的需要,在飲酒作樂的時候,他們還希望享受視聽之娛,需要聽著歌舞藝人唱著動聽的音樂,講著喜聞樂見的故事。這就是歌詩作品的呈現形態,它是在貴族豪門廳堂殿庭演唱表演的藝術。而其消費者的訴求正是歌詩藝術產生的原動力,這也就決定了歌詩藝術作品的文學功能是審美娛樂,是給它的觀眾帶去歡聲笑語,帶去視聽之娛,帶去與他們的心態相契合的藝術表達。”[54]同注?,第239頁。
此外,人的意識的覺醒還表現在,兩漢皇帝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中,興起了影響全國的“求仙長生”之風,但是理想與現實的差距,使他們表現出強烈的生命意識和關注對人生的感受。于是“及時行樂”與“尚悲”觀念并存,較多地體現在漢代詩歌創作中,更是音樂風格形成及表演形態變化的重要因素,其“悲”“巨”“眾”等審美特征也與此相關。
結 語
通過史書、文學作品相關描述及批評文本折射出的漢代俗樂的娛樂功能,彰顯了不同階層鮮活的、樂觀的生活激情,它是社會各階層共同的審美意識的表現之一,也是不同文本的書寫者——史官和文人的禮樂及政治思想的表達。究其原因,則可以說在雅樂的式微、“楚聲”的功能及其影響等客觀因素的背后,人的主體意識的覺醒,不僅是俗樂興起的內在動力,更是其娛樂功能得以彰顯的關鍵因素。此外,由于漢代的政治、經濟、藝術等諸多方面的形態及其美學觀念的發展,在中國歷史進程中具有承前啟后的重要地位,因此,關注漢代俗樂及其功能,對于把握中國古代音樂美學思想的演進,也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