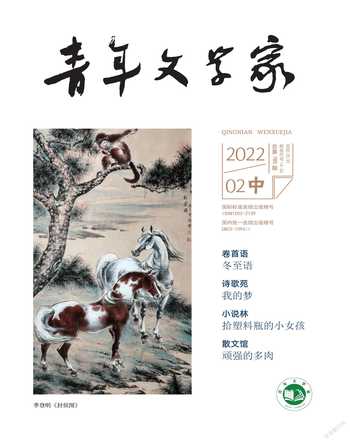《論語》“恭而無禮則勞”之“勞”補釋
周思佳

《論語·泰伯》“恭而無禮則勞”中的“勞”在學界有不同的解釋,我們根據字義、《論語》語境和先秦的相關文獻對“勞”在《泰伯》篇中的含義進行探討、補釋,認為現有諸說中“徒勞”說可取,“疲勞,勞苦”或“憂煩不安”只是“勞”的理性意義,“勞” 還有身體盤旋、進退周旋等貶義色彩的感情意義。
《論語·泰伯》“恭而無禮則勞”之“勞”在學界的解釋存在分歧,其原因在于對“勞”字的理解停留于字面意義而缺少對“勞”所在《論語》語境以及先秦其他相關文獻的綜合考察。對本章“勞”字的深入分析,有助于我們對《論語》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有學者認為,通行本“則絞”下的“君子篤于親,則民興于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當另為一章。程石泉:“《十三經集解注疏》本將此章并入前章。實則此章與前章所言者截然兩事,不應合為一章。劉寶楠《論語正義》謂:‘舊說不主合為一章。’言必有據。”因此本文研究的對象不包括“君子篤于親”及以下諸句。
《論語·泰伯》:“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馬融曰:“絞,絞刺也。”鄭玄注:“言此四者雖善,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葸,愨。絞,急也。”何晏注:“葸,畏懼之貌,言慎而不以禮節之,則常畏懼。”相對而言,“葸”“絞”比“勞”“亂”更為生僻,所以早期學者給予了更多關注。后世學界針對“勞”字也有了解釋,但觀點不一,歸納起來有以下四種:第一,疲勞,自為勞苦。皇侃說:“夫行恭遜,必宜得禮,則若恭而無禮,則遜在牀下,所以身自為勞苦也。”邢昺《論語正義》:“勞謂困苦,言人為恭孫而無禮以節之則自困苦。”皇、邢將“勞”釋為“自為勞苦”。楊伯峻、李運益、金良年、來可泓、潘重規、鄧球柏、李澤厚等學者持此觀點。第二,憂煩不安。陳祥道《論語全解·卷一》解此句為“有是徳性而無禮以節之,故恭則不安而勞”。姚式川、錢穆、孫欽善等學者持此觀點。第三,勞民。王闿運《論語訓》將“勞”釋為“勞民”,認為“恭而無禮則勞”指“如果供給沒有按禮節制的話就會使民受勞”。第四,徒勞,勞而無功。王熙元《論語通釋》認為“勞”為“徒然勞苦”,高照成將“勞”釋為“勞而無功”,他說:“雖然你非常莊重、非常恭敬但不符合禮節,依然不會為人所接受。忽視禮節的恭敬只能收到事倍功半的效果,這樣的恭敬甚至可能是過猶不及的。”高照成也以“勞而無功”釋“勞”,但沒有注意到《論語》及《禮記》等文獻中的相關資料。安作璋、幺峻洲、金池、林道生、王維平等學者同樣持此觀點。
可見,學界對本章“勞”字的理解頗有分歧。與此相關,有的《論語》研究成果還顯示出無所適從的困境:其注釋是一個意思,翻譯是另一個意思,如張以文將“勞”釋作“煩勞”,譯文則作“勞而無功”;藍光中對“勞”有“勞倦”和“徒勞”兩種解釋,其譯文則作“徒勞”;等等。對此,我們認為有必要就相關問題作進一步的討論。
我們需對上述幾種觀點進行分析、檢討。“疲勞,勞苦”說和“憂煩不安”說,前者側重于體力,后者側重于心情。不論哪方面,回到本章具體語境,說“恭而無禮”就會“勞苦”或“憂煩不安”,其理據不明,亦遠于情理,我們認為這兩種說法不妥。“勞民”說也令人質疑:若依此觀點,本章四句的主語理應為“君”,因為其行為有“使民受勞”的效果。但是本章無“君”,且就事理而言,其主語或行為實施者不一定為“君”,行為對象也不一定為“民”,添“民”有增字解經之嫌。所以,“勞民”說難以成立。再看“徒勞”說,“徒勞”就是白白辛苦而無功效,我們認為,此說可據。但僅以“徒勞”作釋,其與“恭而無禮”之間的邏輯聯系并不明朗,讀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此,我們將據字義、語境及相關文獻等方面對其加以補釋,以證明“徒勞”說接近《論語》原義,增加其可信度。
從字義來看,“勞”本指“辛苦”“疲倦”。《說文·力部》:“勞,劇也。從力熒省。熒,火燒冖,用力者勞。”段注:“燒冖,謂燒屋也。斯時用力者取勞矣。”“勞”從力,其本義為用力甚或身體上的辛苦。古文“勞”從“悉”,“悉”從心,則與精神情緒相關。《釆部》:“悉,詳盡也。從心從釆。”桂馥《義證》:“本書勞古文從悉,馥謂詳盡則勞劇。”“詳盡則勞劇”,可以理解為行事過詳到達極致就會導致無謂的辛苦。同時,古文“勞”從悉,悉從心,說明“勞”之本義與“力”與“心”相關。所以,“勞”釋“劇”即“辛苦”,包括“勞身”和“勞心”兩方面。“勞”的這個用法在《論語》及先秦文獻有充分的體現。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論語·里仁》)皇侃曰:“諫又不從,或至十至百,不敢辭己之勞,以怨于親也。”此處以“勞”為辛勞。呂伯恭曰:“救父母于無過之地,左右前后,千方百計,盡其心力,即形神俱弊,亦不敢怨。”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論語·憲問》)皇《疏》引李充云:“愛之不能不勞心。”劉寶楠《論語正義》:“勞當訓憂。”“憂”顯然是勞心。心、勞連用,更顯二者關系之密切。如:《尚書·周書·周官》:“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孔安國注:“為德,直道而行,于心逸豫而名曰美。為偽,飾巧百端,于心勞苦而事日拙,不可為。”“心勞”“于心勞苦”,古人早已深切體會到“勞”的感受和對身心的影響。《邶風·雄雉》:“展矣君子,實勞我心。”鄭箋:“君子行如是,實使我心勞矣。”所以,“勞”就是“辛苦”“勞倦”,包括“勞身”和“勞心”。這一解釋證明有關“勞”的諸說中需有“勞苦”義。
邢昺對本章疏釋說:“勞謂困苦,言人為恭孫,而無禮以節之,則自困苦。……亂謂逆惡。言人勇而不以禮節之,則為亂矣。……絞謂絞刺也。言人而為直,不以禮節,則絞刺人之非也。”楊伯峻對本章的譯文是:“注重容貌態度的端莊,卻不知禮,就未免勞倦;只知謹慎卻不知禮,就流于畏葸懦弱;專憑敢作敢為的膽量,卻不知禮,就會盲動闖禍;心直口快,卻不知禮,就會尖刻刺人。”此處以“不知禮”釋“無禮”似欠妥,因為“不以禮”并不代表其不知禮,知禮者中也有妄為者。
從語境看,《論語》“恭而無禮則勞”與其后“慎而無禮則葸”以下三句的句法相同,對“慎而”以下三句的解釋有助于對“勞”的正確理解。
“慎”“勇”“直”是孔子提倡的品格,但即使具備這些品格,其言語行動也要受禮的節制,否則,就可能變得畏縮、妄動和言語傷人,出現“過猶不及”(《先進》)的情況。孔子在這里強調了“禮”的重要性,正如邢昺所說:“此章貴禮也。”《學而》也說:“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同樣,“恭”也是孔子提倡的品格與態度,《顏淵》載子夏的話說:“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恭、敬互文,意謂君子待人恭敬且有禮才會避免失誤,才能實現言行的預期目的。《學而》又說:“恭近于禮,遠恥辱也。”《論語》反復闡揚“恭”和“禮”的相互聯系,無不彰顯以“禮”約束言行的重要性。至此,我們可以明確:恭、慎、勇、直都是儒家思想體系中所提倡的美德,勞、葸、亂、絞都是應該避免的結果,避免的方法或手段就是用禮。從這個角度看,本章的詞語既有理性意義,也有情感色彩意義,恭、慎、勇、直屬褒義,勞、葸、亂、絞屬貶義,“疲勞,勞苦”或“憂煩不安”只是“勞”的理性意義,還不足以反映它在本章語境中的情感色彩意義。
在“恭敬”義上“恭”“敬”有別,“敬”側重于內心的真誠恭敬,“恭”側重于指儀容言行的嚴肅認真。《尚書·洪范》:“貌曰恭。”孔疏:“貌能恭,則心肅敬也。”“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論語·子路》)《集注》云:“恭主容,敬主事。恭見于外,敬主乎中。”待人“恭”的目的無非要表達尊敬或友善,但對待的人各有差別,“恭”的表現也應有相應規范或差異,規范或差異的依據是什么呢?就是當時的“禮”。不依“禮”或不受“禮”之約束的“恭”,往往失于“過”或“不及”。所以,“過”或“不及”的“恭”實現不了表達尊敬或友善的目的,無謂折騰,冤枉辛苦,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徒勞”。
與《泰伯》“恭而無禮則勞”意思相關的內容也見于《論語·公冶長》。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公冶長》)孔安國注:“足恭,便辟之貌。”“便辟”亦作“夸毗”。《說文·舟部》:“般,辟也。象舟之旋,從舟。從殳;殳,所以旋也。”段注:“《人部》僻下曰:‘辟也。’”此辟字義同。《投壺》曰:“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說文·辟部》:“辟,法也。”段注:“又引申之為盤辟。如《禮經》之辟,鄭注‘逡遁’是也。”《詩經·大雅·板》:“天之方懠,無為夸毗。”傳曰:“夸毗,體柔人也。”孔疏引李巡曰:“屈己卑身,求得于人,曰體柔。”可知,“便辟”亦作“盤辟”“便僻”或“便嬖”,“足恭”“便辟”“夸毗”義近,均指身體盤旋,形容卑躬屈膝、諂媚順從、進退周旋的樣子。這樣的“恭”是沒有“禮”之調節的結果,令人生厭,難以實現其表達尊敬或友善的目的。所以,“無禮”的“恭”只能是“徒勞”,是達不到目的的、無謂的辛苦。
裘錫圭、鄔可晶、劉嬌《中國古典學的重建叢書·叢書序》說:“古代書篇在流傳過程中發生變化的情況是很復雜的……而且,基本相同的內容可以出現在兩種以上的書篇中。”《論語》的內容在流傳過程中同樣存在類似情況。《泰伯》“恭而無禮”章的有關內容還見于《禮記》。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禮記·仲尼燕居》)《禮記》“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和《論語》“恭而無禮則勞”二者句式相同,思想內容有聯系,但用詞有異。“恭而無禮則勞”下劉寶楠引《禮記》之文說“與此言勞、葸、亂意近”。“恭而不中禮謂之給”下孔疏“恭而不中禮謂之給者,給謂捷給,便辟、足恭而不合禮是謂捷給、足恭之貌”。“給”訓“捷給”指擅長做某類事,如《公冶長》“御人以口給,屢憎于人”,孔安國說:“佞人口才捷給,數為人所憎惡。”“口給”就是善于言辭,長于爭辯,“恭而不中禮謂之給”之“給”則是指儀容身體方面善于諂媚順從,便辟足恭。《論語》之“口給”謂以口柔人,《禮記》之“給”則是以體柔人,結果都是“徒憎于人”,不能實現其表達尊敬或友善的目的。所以,恭而無禮之“勞”、恭而不中禮之“給”都是事與愿違的,“徒勞”的。
綜上所述,《泰伯》“恭而無禮則勞”之“勞”,已有諸說中,“徒勞”一說可取,但其理據比較隱晦,讀者據現有注釋或譯文難以知其所以然。“恭而無禮則勞”之“勞”其理性意義為“徒勞”,同時含有情感色彩意義,即身體盤旋、諂媚順從、進退周旋等意思,從詞的感情色彩來看,“勞”與“葸”“亂”“絞”一樣,屬貶義。通過對本章“勞”的解釋,我們認識到對《論語》字詞的訓釋,不能只憑其字面意義,還要結合語境,參考與《論語》相關的文獻進行綜合分析,揭示其內在涵義,才能準確解讀《論語》所蘊含的深刻而精妙的思想內容。